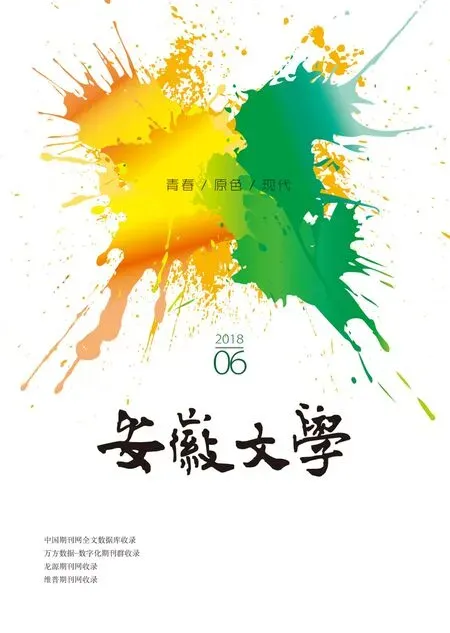朱寿昌孝行探析
谭 逊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元代郭居敬辑录的《二十四孝图》影响深远,其中收录的孝道故事也成为后人教育子女的典范。宋朝入选《二十四孝图》的仅有两人,一为黄庭坚,另一人便是朱寿昌。黄庭坚因在诗歌、书法等领域颇有成就而为人所熟知,但对于朱寿昌,大众便感到相对陌生。尽管目前学术界有考证其生平事迹、孝行等方面的相关文章,但很多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并不能系统地了解此人。本文以可以收集到的材料为基础,希望能够做出一个相对全面的探究。
一、朱寿昌的家世与生平
朱寿昌(1018-1087),字康叔,扬州天长(今安徽省天长市)人。其祖先详尽事迹已不可考,只知原居于彭城(今江苏省铜山县),后因避五代之乱迁家于淮南(今安徽省淮南市)。朱寿昌的祖父曾被赠与刑部尚书,其父朱巽一生仕途较为平坦,咸平三年(1000)进士及第后,授将作监丞、州通判,后特恩迁著作郎、直史馆、知制诰,历任知州,官至工部侍郎。
景祐四年(1037),朱寿昌二十岁,以父巽荫守将作监主簿,此后历任知州、通判,官至中散大夫。朱寿昌曾与顾氏结为夫妻,有一子瞻之,做过雒县尉;其孙朱英为元丰年间进士;曾孙朱棫为绍兴八年(1138)进士,曾做过蒲圻县县学教授。此外,朱寿昌的伯父、堂兄弟、侄子也曾做过官,诸如其堂兄(弟)朱齐卿,曾为高邮主簿,其季女适曾易占,生下曾布、曾肇二子,他们后来均在政坛及文坛上声名天下。①
由此看来,朱氏家族在当时较为显赫。这种出身名门的身份令他日后的孝行(因后文论及,此不赘述)更易获得当朝及后代人的关注,带来名利,同时也使得他与文同、苏轼等名士结为好友。
朱寿昌与文同(字与可)的初次交游今已不可考,现存史料中,最早著录二人来往的是南宋祝穆的《方舆胜览》。②治平元年(1064),时为阆州(今四川省阆中市)太守的朱寿昌在牙城建造了东园,文同闻之,赋十咏诗赠之,不过他们此时尚未相见。直至熙宁三年(1070),文同自蜀还台,于临潼(今陕西省临潼区)结识朱寿昌,二人倾心畅谈。当寿昌言及母子相失五十年而不得见时,与可唏嘘良久,而后夜不能寐。此后朱寿昌寻得母亲,文与可也曾作诗赞扬他的孝行。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二人的来往虽不频繁,但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
朱寿昌与苏轼的首次交往,大致发生在其寻得母亲之际。据《苏轼年谱》可知,苏轼当时在京师,而朱寿昌奉召入京,二人当与此时初次相见。他们来往最为密切的时期当属元丰三年(1080)—元丰五年(1082)。此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谪居黄州,朱寿昌并未如其他畏祸之人一般唯恐避之不及,而是成为苏轼最为重要的精神寄托之一。他曾收到苏轼为其所作之词两首,文二十三篇。遍观这些作品,可发现从野步于山水之间到复归庭闱之乐,从生活趣事至社会问题,他们推心置腹,无话不谈。苏轼也曾在送别朱寿昌的词中抒发不平之气:
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
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不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③
苏轼在此词中分别化用三国时期祢衡遭曹操、黄祖迫害的典故及李白、崔颢的诗句,借对历史人物的品评抒发心中愤懑郁勃,这种直露心迹的词作在苏轼惧怕作文的黄州期间并不常见,以此也足以见二人关系之亲密。纵观朱寿昌与苏轼的交往,他们主要靠书信来谈论问题,真正见面的次数并不多。从这些诗文、书信中可以感受到平淡自然的君子之交。
朱寿昌在政绩上的突出表现也值得重视,此为其留名青史的又一重要因素。嘉祐二年(1057),朱寿昌权知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为保百姓安康,曾借巧计惩治水盗,而其治水盗之法后来也多为邻郡借鉴。嘉祐六年(1061),他以比部员外郎奉命出使湖南时,宽恤民力,考察当地实况,上奏采金须有度,令朝廷大规模开采金矿之意作罢,避免了百顷良田被毁。嘉祐八年(1063),朱寿昌以虞部郎中知阆州(今四川省阆中市),当地大姓雍子良仗势杀人,他则明察善断,不畏财势,依法惩治。元丰二年(1079)至五年(1082),朱寿昌任鄂州太守期间,就生子不育的社会问题与苏轼进行探讨,并推行了明立赏罚,鼓励当地富人捐助等一系列措施,取得了良好成效。上述政绩体现了他除孝子身份外受到尊敬的官员形象。
由上可知,出自名门的朱寿昌不仅与社会名士广有深交,在孝行与政绩上也享有美誉,为我们呈现出一个近乎完美的历史人物形象。
二、弃官寻母事件及其影响
(一)朱寿昌的孝义之行
朱母刘氏身份低微,是朱巽的一个小妾。朱寿昌三岁时,刘氏被遣出家门,嫁与百姓党氏为妻,后来育有一子一女。熙宁二年(1069),朱寿昌五十二岁,离广德(今安徽省广德县)任,以浮屠法灼臂烧顶,刺血写经,不食酒肉,立誓寻母不得便不归家,最终于熙宁三年(1070)在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县)寻得老母,刘氏当时已七十余岁。母子团圆后,朱寿昌将其迎回身边奉养,同时接回的还有其同母异父的弟妹。三年之后,其母无疾而终,但朱寿昌此后对他的弟妹照顾地更加无微不至,甚至为他们买田建房,由此可见其纯厚天性。
以上论述中,“以浮屠法灼臂烧顶,刺血写经,不食酒肉,发誓寻母不得亦不归家”这样一点应当引起注意。“不食酒肉”是佛家戒律,而“以浮屠法灼臂烧顶,刺血写经”这般以伤己身来尽孝的行为则更反映出佛教的孝道对于俗众尽孝行为的影响。后一种情况在前代也并不鲜见,如卧冰求鲤的王祥,恣蚊饱血的吴猛。二人为分别为三国、晋朝人,他们为了行孝,均作出了不惜躯体之事,这与朱寿昌的孝行有某种相似性。一般认为,佛教在两汉时期传入中国,且在传入的早期不断受到儒家的非难,指责其不行孝道。我们或许可以从王祥和吴猛的孝行中看到佛家为适应本土化的发展而做出的改变。
如果说上面两个例子因时间相对较早而具有一定偶然性,不具说服力,则《宋史·孝义传》中大量出现的伤及发肤的孝子故事可以提供更为充分的证据。如太原人刘孝忠,为给生病多年的母亲治病,割股断乳;莱州人吕升,为救几近失明的父亲,剖腹探肝。类似的毁伤身体的行为在佛教的孝道故事中也很常见。《报恩经》中的《议论品》便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波罗奈国为了救治父王而忍受太子之辱,甚至“断骨出髓,剜其双眼”④。经学者考证,《报恩经》的翻译年代便应在东晋之后⑤。
佛教发展至宋代,此前对其不符孝道的批评也已完全消除,且“中国佛教孝亲观的系统化即完成于此时。这种系统化的完成,以宋代禅僧、‘明教大师’契篙的《孝论》为标志。”⑥契嵩的生卒年为公元1008-1072年,与朱寿昌(1018-1087)的大致相同。那么,契嵩在《孝论》中所论及的戒孝关系等方面便恰好反映出当时佛教的影响。虽然佛教的孝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终归劝人行孝,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大众心理,故而会被广泛地仿效,社会上折射出佛教色彩的孝行故事也因之增加。
(二)弃官寻母事件的影响
朱寿昌弃官寻母的事迹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送朱郎中诗序》中对此记载较为详细:
当时士大夫相逢遇,欢然骇异称叹,谓非世之所有,在昔亦无几矣。其秋,康叔侍太夫人入都,都人逐板舆,前后拥观。至所居,闾巷谈说,抃蹈嗟咨,至有感慨堕泪而不能自语者。如是阅月而后已。⑦
此诗序为文同作于朱寿昌母子团圆之后,序中或有夸张的成分,但由于与《东都事略》等史料中所记载的“由是天下皆知其孝”⑧的情况相符,故应出入不大。我们可从文中看到上至士大夫,下至平民百姓对此事的热烈反应。可以说,朱寿昌的孝行在当时产生了震动朝野之效,对社会风俗的教化应起到了积极作用。
朱寿昌的孝行也给个人带来了名利馈赠。王安石、司马光、苏颂、苏轼、文同等士大夫知其寻母事后纷纷作诗文赞扬之,加速了其事迹的传播,令他更快地获得了良好的名声。时长安大尹钱明逸亦上书朝廷,乞求皇帝褒奖朱寿昌:
朱某向弃官,本繇寻母。今既得之冯翊矣,宜还之旧秩,且褒宠之,以劝激天下。⑨
宋神宗得知此事后,特别召见,对他进行嘉赏,恢复其官职,并赐其母刘氏长安县太君的封号。事实上,朱寿昌职位的恢复是破例的,对此,钱明逸的另一封奏章可以作出一定证明:
寿昌称疾寻医弃官,而寻医法须二年乃赴御史台看验。乞不俟寻医限满,复其差遣。⑨
可知,按照正常的程序,朱寿昌想要复其差遣,需待其寻医看病期限年满之后才可以,皇帝的特殊表彰则缩短了等待的时日。
朱寿昌的孝行不仅在本朝引起轰动,后代也多有人赞誉之。元人郭居敬曾将其事迹收录到自己编纂的《二十四孝》中,进入此名单的宋代人物仅有黄庭坚与朱寿昌而已,足以见其重要地位。即使到了清代,朱寿昌的孝道也常被人提起,纪昀曾在其《阅微草堂笔记》中夸赞朱寿昌“若有神助”“精诚所至”。⑩
在此过程中,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即现存的史料对朱寿昌寻得母亲后在仕途上为河州府通判的事实并不存在疑问,然而对此事的缘由却依旧存在争论,下面便进行辨析。
于这一问题,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朱寿昌是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而自请通判河中府,如文同《送朱郎中诗序》中所提到的“康叔请,愿且倅河中,庶近母前,所在慰之。诏许”⑪等。另一种认为朱寿弄昌原本应被派遣地位更高的职务,但因王安石的上下其手,无奈落得此结局。究此说法之源流,为《续资治通鉴长编》:
先是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丧,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寿昌,及寿昌至,但付审官院。寿昌前已再典郡,于是折资通判河中府。⑫
此则史料认为朱寿昌得通判河中府是因王安石所忌的缘故,但在王安石写给朱寿昌的诗中,情况却并非如此,现摘录其赠诗如下:
送河中通判朱郎中迎母东归
彩衣东笑上归船,莱氏欢娱在晚年。
嗟我白头生意尽,看君今日更凄然。⑬
在这首诗中,王安石将朱寿昌比作身着彩衣以娱父母的老莱子,对其孝行大加称颂,并由朱寿昌的母子团圆联想到自身境况,不禁唏嘘感叹。我们能够从这首诗中看到王安石对朱寿昌寻母事迹的肯定之意,此后也应不会对其仕途进行阻碍。此外,查阅对新党人物多有贬低的《宋史》的相关章节,也未发现王安石排挤朱寿昌的论述,且文同等人为朱寿昌同时代之人,其说法更为可信,故以《长编》为代表的那种观点是没有依据的。
三、朱寿昌孝行的独特性分析
《宋史·孝义传》中收录的行孝施义之人有75位之上,与朱寿昌为对母亲尽孝而放弃与付出的程度相较,诸多人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为何仅有朱寿昌在后世引起较大反响,进而入选《二十四孝》,其他人却几近湮没无名呢?这说明朱寿昌的孝行与其他宋代人物的孝行存在共性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特质。
首先,朱寿昌的成名自有其时代机遇。儒学发展到宋代,更加注重社会伦理秩序的建构,如北宋时期的邢昺便曾注释《孝经》。此外,个人论述孝道的著作也多有问世,诸如司马光的《涑水家仪》《家范》、袁采的《袁氏家范》等。上层统治者希望借助对这种美德的赞扬与提倡令民德归厚,进而维护其政权的稳固性。然而六亲不和乃有孝慈,对其重视恰恰说明了当时可能缺乏此类善行,社会上败人伦、薄教化的行为依旧存在,由于这类行为不利于维护统治秩序,故不可被容忍。朱寿昌在此时顺应而出,成为君主宣扬孝道的工具,符合时代需求。
其次,新旧党争将其推向风口浪尖。朱寿昌自熙宁二年(1069)开始寻母,至次年(1070)五月找到母亲,秋天得皇帝召见,复其官职,历时一年有余。在这段时间内王安石除参知政事,变法开始。当时属于变法派阵营的李定正遭遇保守派对其不服母丧的批驳,被认为是不孝之士。在此情形下,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朱寿昌的地位便得以提升。与朱寿昌交好的苏轼在他寻得母亲之后,曾作诗一首:
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去岁得之蜀中。以诗贺之
嗟君七岁知念母,怜君壮大心愈苦,羡君临老得相逢,喜极无言泪如雨。
不羡白衣作三公,不爱白日升青天。爱君五十着彩服,儿啼却得偿当年。
烹龙为炙玉为酒,鹤发初生千万寿。金花诏书锦作囊,白藤肩舆帘蹙绣。
感君离合我酸辛,此事今无古或闻。长陵朅来见大姊,仲孺岂意逢将军。
开皇苦桃空记面,建中天子终不见。西河郡守谁复讥,颍谷封人羞自荐。⑭
苏轼在这首诗中不仅表达了对于好友朱寿昌的赞颂,诗中“感君离合我酸辛,此事今无古或闻”一句更被后人是为讥讽李定而发。其实,仅论李定的不孝与朱寿昌的孝,并无特别之处,但当二人卷入新旧党争,成为旧党借以攻击新党乃至变法的矛头之后,性质便发生了一定的转变。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政治对个人命运的影响。这也是其他同时代的孝行故事中所未体现的,故而成为朱寿昌区别于一般孝子的重要因素。
除上述缘由之外,家世与佛教因素也凸显了朱寿昌孝行的与众不同。《宋史》及《二十四孝》中所收录的孝子大都家境清寒,生活贫苦,如此似乎更符合大众的审美理想。而朱寿昌的家道却并非如此,除其自身外,他的父辈、同辈、子辈也多做过官。处于社会上层的人尤重孝慈且身体力行,意义便相对不同,也更具导向作用。同时,这样的身份令他结交之人也多为名士,日后他们所作的诗文加速了其名声远扬,这在以往的孝子中并不多见。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朱寿昌在立下寻母之誓时,有“饮食罕御酒肉,用浮屠法灼背烧顶,刺血书佛经”的行为,表明佛教在当时对个人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样的情形在《宋史》及《二十四孝》所收录的孝子故事中虽有体现,但大都仅涉及伤及身体,相较之下,朱寿昌的孝行中展现的佛教色彩更为浓厚。
综上所述,朱寿昌的寻母事迹是中国古代孝道故事中的缩影之一。其青史留名反映出古代社会尤其是宋代对于孝道的重视,一切有利于宣扬礼教的行为均将受到肯定,施行孝义之人也会得到相应物质上的报酬,这背后实质上是统治者对于统治秩序的维护。而朱寿昌本人的孝行在恒河沙数的孝道故事中得以凸显,自有其复杂的成因。这种近乎完美的人物在历史中不胜枚举,虽然稍显单薄,不够立体,但却符合了中国古代大众的审美理想。
注释
① 以上材料主要来自于:吴延燮.北宋经抚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1984:184,258,298,311,341;(宋)周淙.乾道临安志[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明)邵时敏,王心.(嘉靖)皇明天长志[M].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② (宋)祝穆.方舆胜览[M].北京:中华书局,2003:1175.
③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335.
④ 敦煌研究院主编.敦煌石窟全集:报恩经画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96.
⑤方一新,高列过.从佛教词语考辨《大方便佛报恩经》的时代[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147.
⑥王月清.中国佛教孝亲观初探[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6(3):31.
⑦ (宋)文同.文同全集编年校注[M].胡问涛,罗琴,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9:891.
⑧ (宋)王偁.东都事略[M].孙言成,崔国光,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00:1019.
⑨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8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253.
⑩纪昀.阅微草堂笔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52.
⑪ (宋)文同.文同全集编年校注[M].胡问涛,罗琴,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9:891.
⑫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 15 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5:5143.
⑬ (宋)王安石.王荆文公诗笺注[M].(宋)李璧,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617.
⑭ (宋)苏轼.苏轼诗集:第 2 册[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386.
[1](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孔凡礼.苏轼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8.
[3]王月清.论宋代以降的佛教孝亲观及其特征[J].南京社会科学,1999(4).
[4]谢桃坊.朱寿昌寻母事辨[J].文史杂志,2009(6).
[5]陈晓燕.朱寿昌生卒年考辨[J].文史杂志,2012(2).
[6]王佩,王法贵.善于孝而勇于义——皖东先贤朱寿昌生平事略[J].孝感学院学报,2012(3).
[7]陈晓燕.朱寿昌入《二十四孝图》原因探析[J].文史杂志,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