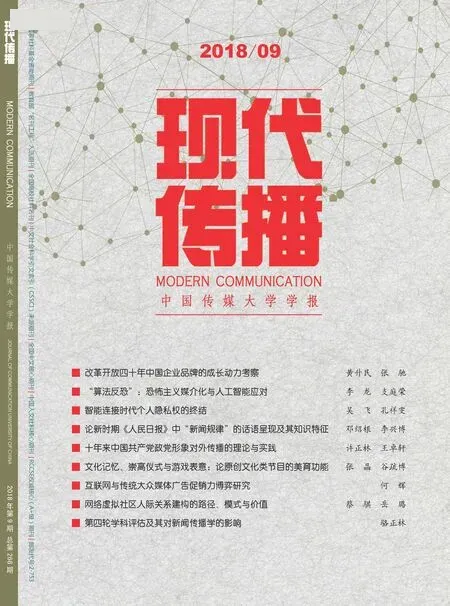文化记忆、崇高仪式与游戏表意:论原创文化类节目的美育功能
■ 张 晶 谷疏博
在文化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传媒生态环境下,电视综艺的娱乐属性被无限放大,并引向一种极致的快感文化,而脱胎于精英文化语境的文化综艺节目反其道而行之,在这种快餐化、同质化发展成普遍趋势的背景下,选择了对传统文化、对理性的复归。超越了讲坛式、专题式的呈现方式,电视文化类节目步入了以原创为主导,融合各种综艺元素的创新发展阶段,通过对艺术因素与趣味性的挖掘,激发人们的文化艺术兴趣,以熏陶、感发等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人与社会走向完善与和谐。
与此同时,在近年来,虽然我国美育建设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从总体而言,美育仍然是国民教育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如美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尚处于弱势、边缘地位;审美教育实践尚未体系化,同时功利化趋向制约审美教育的发展,其中核心的问题在于,由共同价值观念的衰落所导致的个体存在意义流失等问题,仍然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
而“本体的安全”不仅是个体独立性建构、产生行动与认知的基础和驱动力所在,它的建构亦是审美教育的核心价值所在,而人性的完满的实现也要基于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即本体安全的复归。对其实现的路径笔者以为应该回归传统,从延续千年的文化记忆中求取那些具有稳定性、延续性的部分,重建人们的价值认同感,而这也正是当下文化综艺节目在内容层面开掘的方向所在。
一、回归传统唤醒文化记忆
德国学者简·奥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是一个集体概念,所有通过一个社会的互动框架指导行为和经验的知识,都是在反复进行的社会事件中一代代地获得的知识,通过文化形式(文本、纪念碑等)以及机构化的交流(背诵、实践、观察)而得到延续”①。人们的集体记忆源于其所诞生的历史与文化,由此形成了个人身份的认同与群体认同的凝聚。作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文化记忆是一个带有延承性的概念,也是内蕴于每个享有共同文明与历史的群体心理的“集体无意识”。它一方面通过保存代代相传的集体知识来确证文化的连续性,并以此重构后人的文化身份;另一方面通过创造一个共享的过去,再次确证拥有集体身份的社会成员,在时间和空间方面都向他们提供一种整体意识和历史意识,②从而获取个人对所属群体的感情依附和认知,找到“我或我们是谁”的答案。
对每一个国人而言,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传统文化积淀便是整个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记忆”,文字、诗词歌赋、书法、戏剧、绘画、音乐等均是文脉得以延续、文化记忆得以传承的文化符号,内蕴着中华文明的根脉基底与精神品格,毫无疑问,它们可以成为电视文化综艺节目的“素材”或者说是“原材料”,如《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以“汉字”为核心,通过现场“听写”“评判”“解读”的方式联通场内外的同步参与,直指当下电子技术飞速发展所导致的“提笔忘字”现象,呼吁人们回归传统的汉字书写,领略汉字之美;《中国诗词大会》以“古诗词”为内容,以“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为节目宗旨,让国人重寻自《诗经》起便已深入骨髓的“诗性基因”;《诗书中华》围绕“诗礼传家”“诗教家风”的主题,以古诗词、古诗文为主体,同时将中华传统的家风、家训、家史的传承发扬融入到节目中;《传承者》将传承千年之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传承人的生动演绎呈现在我们的视线里,以中国意象为主体将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得以彰显,提升国人的文化自信与自豪感。编导通过对“原材料”进行二度挖掘,实现传统文化的新意表达,帮助人们在共同的文化基因中重寻自身于集体之中的共性感知,唤起人们关于文化、关于美的潜在记忆进而走向完满的人生,从而消解本体安全与存在性焦虑。
作为文化记忆的载体,传统文化符号是激活人们文化记忆进而建构认同感的基础,而对符号所指意义的逐层挖掘是方法论层面上唤醒国人文化记忆、建构价值认同的途径,笔者以为生成与挖掘符号意义的关键,在于叙事原理与戏剧性挖掘的介入。“故事曾经是人类了解历史、熟悉自然、感悟自身的通俗方式,它构成了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原型文化,在人类的血脉中播下了讲‘故事’、听‘故事’、爱‘故事’、迷‘故事’的基因”③,文化记忆的激发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人们共同接受心理而产生共鸣感的故事性元素。
如在《国家宝藏》中,明星守护人被赋予了与国宝密切关联的历史人物角色或是直接将自身拟物化为所守护的“国宝”,追溯它的前世经历。在这个过程中,表演者在塑造先人的信仰时,也获得了他们的信仰,并将这份信仰借由戏剧化的表演得以传达。从前世传奇引出今生故事,两个故事的结合又为我们讲述了又一个故事,即关于传承的故事。如第一期由国宝守护人梁家辉演绎的石鼓前世传奇中,他饰演的司马光在缅怀父亲司马池昔日为寻找、守护石鼓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整个舞台借助灯光的设计将两个时空联结在一起,司马光由儿时不懂得父亲为辨石鼓真假而倾尽所有,直至长大后理解了父亲所说的“华夏民族的信仰就是自己的文字和历史。如果连这点信仰都糊涂,那我们何以为人”的真意。从古代到现代,梁家辉引出了梁金生及其父辈、祖辈三代人用身体力行守护石鼓的故事,从“二战”时期守护石鼓南迁到梁金生用7年时间点存故宫现存的186万余件文物。从古代到近现代再到当代,新时期年轻的国宝守护团队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传承着老一辈国宝守护人的精神,继续着石鼓的守护事业。30分钟的节目时长,我们通过石鼓看到了它的背后不仅有“书同文”的历史轨迹,还有“择一事,终一生”的忠诚守护,更有对中华文脉绵延千年、承传至今的根本原因的揭示。由石鼓生发出来的三个故事(即前世、今生以及传承故事)营造出了一个我们共享的过去和正在经历的当下,在一代代守护者通过身体力行解读出的中华文化基因密码中,找到自己的坐标和定位——知来路,识归途。正如《国家宝藏》总导演于蕾所说:“这种文化一直活着,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当我们把它展现在你面前,你会发现它一直活在身体里。”④
通过挑选、截取每个时期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将其连缀、整合在一起并以故事化的方式呈现,以通俗、亲和的方式带人们了解历史、感悟自身,这在契合受众爱故事、迷故事心理的同时,亦将共同的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植入人们的内心。
如果说故事化呈现激活了潜藏在意识深处的文化基因与价值认同,那么戏剧化的挖掘则因主题集中、悬念迭起而加深了人们对于节目中关键信息的摄取与记忆,其影响也是更为深远且持久的。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认为,“戏剧因素理所当然地应该渗入到叙事因素中去,并且会提高艺术作品的价值”。⑤在《朗读者》节目中,通过每一期主题(如家、眼泪、礼物等)的设定由点及面,将同一主题的不同诠释维度以及由此联结的经典文学作品得以集中。节目以“朗读者”命名,突出强调了“朗读者”中“者”的内涵,以作品朗读的“人”为主体,以自我为媒介,将情感的表达与熏陶传播、辐射到更多的受众,产生更为广泛的情感认同。如在“眼泪”为主题的一期中,斯琴高娃通过贾平凹《写给母亲》的散文追忆、怀念自己逝去的母亲,相似的感悟与共通的情感,朗读者与文学作品的创作者由此产生了内在的关联与对话关系,读罢难掩激动之情的斯琴高娃又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分享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所有人都有爹有娘,我希望在座的人如果爹娘还在的话,从现在做起不晚。好好爱他们,好好伺候他们,好好地哄哄他们,别太多犟嘴,不然后悔来不及。”基于移情与共感心理基础上的真情流露,触发了观众内心的共鸣与对孝道问题的重新反思,这样的情感与价值认同是基于对戏剧性规律的把握与重新架构上,戏剧性的产生基础在于事件作用下的人物及人物之间关系的情状,正是基于此,受众才产生了审美反应,及由审美反应所激发的审美情感。
节目将朗读嘉宾自身的情感和生活经历与所朗读的文学作品中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联结在一起,这样的呈现方式类似于化学中物质间的化合反应。贾平凹的《写给母亲》让斯琴高娃心底埋藏多年对母亲深深的思念得以酣畅淋漓的释放,同样斯琴高娃也赋予了《写给母亲》这篇散文以新的灵魂和新的解读,而它是植根于当时情境中的直觉的反应,随着朗读进程中那些触动心灵的词句、情节,以及现场场景化生活空间的营造所感发、兴起的,它是一触即觉、未经事先谋划的经由朗读者的主体情感延展至观众的自我审视的情感生成。仁义礼智信、知恩图报、孝道等都是潜在于每个人心中的共同价值观念,也是自古以来就传承下来的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朗读者》为例的文化综艺节目通过对叙事层面的挖掘为个体身份赋型、重构,使受众产生深入内心的情感共鸣,以引发对于感恩、对于孝道等共同价值观念的重新审视。
对于文化记忆,我们既可以将它理解为一个过程,一个传承、保护和延续的过程,同时也可以将它看作一个结果,被筛选、被揭示、被重新发现和重新架构之后的一个结果。当下的电视文化综艺节目可以看作是从两个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浩如烟海的文化符号中选取哪些,如何延续既存的文化记忆,怎样通过对它的揭示与架构在冲突与断裂的社会中重建价值认同,这些电视文化综艺节目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对于传统文化符号背后蕴藏的丰厚增值的开发正是他们共同的选择。以内容层面的挖掘为基础,我们还需要建构象征性符号系统,借助仪式传播对节目内容进行重组与整合,以此实现基于个体独立性建构之上的集体心理的认同。
二、仪式化传播建构的“电视崇高感”
“仪式”产生于人们的祭祀活动,涂尔干将其界定为对信仰的表达和强化的行为手段。对于仪式而言,它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它所营造的隆重气氛可在人们心中唤起神圣、崇高的情感⑥。电视作为大众媒介,本质上具有诉诸大众感官层面的直接效用,而“仪式化”本身正是充满了感性魅力。自电视普及以来,仪式便如影随形,节庆、竞赛、祭祀(祭拜祖先)、表彰等作为仪式呈现的主题,借由节庆晚会、颁奖晚会、开闭幕式晚会、特别节目等载体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以直播的方式呈现。通过仪式的共享、共有等特性将拥有着共同文化记忆、文化体验以及信仰的人们联结在一起,激发人们在神圣时间与背景下的内心崇高感与社会认同感。
在当下的原创文化综艺节目中,编导有意识地将“仪式”融入其中,突破了电视仪式固有的传播方式(即在固定仪式时间、地点以直播的方式)以及传统意义上的传播内容(即全民狂欢式的节日庆典、体育赛事等)限制,通过创造一系列图像符号、实物符号、行为符号、音乐符号、色彩符号以及象征性角色符号,建构起经由“仪式”传播产生的“电视崇高感”。而这种“电视崇高感”,在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中,在国家实施美育的系统工程中,是能够产生强烈审美效应和美育效果的“高光点”,⑦对于整合体验、强化价值观与审美感知,促进社会和谐、加强社会认同等美育功能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电视崇高感”最早由米尔佐夫教授提出,他认为:“在电视上观看纳尔逊·曼德拉这类事件是有某种意义的,它提供了一种也许可称电视崇高感的东西,即某个在现实中很少有人能亲眼目睹的时间似乎把我们带出了日常生活,尽管只是片刻之间。”⑧综观当下的原创文化综艺节目,“电视崇高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带给人以惊颤、震撼的心理感受,使人们暂时抽离日常生活而获得审美惊奇,进而强化审美感知;二是在于其呈现的仪式化的内容触发了受众内心的崇高感,唤起敬畏、钦佩、激昂的情感。前者基于视觉表现,而后者是思想、心理层面的。
笔者选取了三档兼具社会影响力与美誉度的文化综艺节目,通过列举其仪式化传播中的符号创造,探析“电视崇高感”何以产生(见表1)。

表1 《国家宝藏》《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中使用的象征性符号
如上文所述,仪式的建构依托的是象征性符号系统,而文化综艺节目中的仪式,则是对文字、灯光、音响、道具、舞台美术以及角色行为等符号进行艺术化、视听化、综合化创作的结果。以《朗读者》为例,节目中“门”作为实物符号的设计成为了“仪式”传播的一个载体,对于每位朗读者而言,“门”的两次打开与关闭意味着他整个朗读行为的始与终,“门”既意味着心门,也意味着和受众一起分享的交流之门。它的第一次打开,朗读者随董卿一同进入了访谈室,分享自己与即将朗读内容之间的关联与故事,将一个人与一段文紧密地勾连在一起。随着大门的再次开启,朗读也随之发生,伴随着朗读行为开始与结束的时间节点,全场观众会一同起身鼓掌致意。
朗读,一个日常看来极为平常的行为,在节目中通过一系列象征符号的建构与组合,升华成为一种仪式,甚至可以说是近乎神圣的行为,借助舞台设计、背景画面、经典音乐等符号的烘托,唤起并强化人们内心崇高的感情。
而每期开场的“寻找朗读者”活动,则是节目营造“电视崇高感”的又一方面。“朗读”因为一个实物符号——“朗读亭”,将全国各地、各民族、各职业、各年龄层的大众凝聚在了一起,他们排起长队、不分昼夜,仅是为进入“朗读亭”将自己内心所要表达的情感借由一份朗读材料、一个狭小的密闭空间、一支话筒得以外化,“朗读亭”由此成为一个“仪式”运行的载体,它区隔开了现实世界和人的内心世界。走进这里,仿佛也走入了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在此找到情感抒发和表达真实情绪的理由,受众在领略他们的故事的同时,陶冶自己的情操,在审美移情中产生共鸣感与认同感。
《国家宝藏》节目将“仪式”融入整个节目流程之中,从明星守护人分别在九大博物馆与国宝邂逅、接到来自馆长的国宝守护任务,直至将守护印信带入节目现场,演绎前世传奇引出今生故事之余,每一件“国宝”在呈现过后均被赋予了一个庄重而神圣的仪式行为——为守护人颁发国宝守护印信并宣读守护誓词。涂尔干认为“仪式的功能在于提供共同体验的瞬间”⑨,颁发印信宣读誓词的仪式行为将人们对于国宝从陌生到熟悉、从浅表到深入、从感动到志在传承的认知过程得以高度凝练与情感强化。“守护历史,守护中华文脉、中国剑魂、华夏初音、绿水青山、律法初心、国之瑰宝……”仅仅十个字组成的守护誓词,涵盖、浓缩了华夏文明的文字、书画、陶瓷、乐器、法律等多方面领域,通过象征符号——文字,以凝练概括、以少总多的方式对文化记忆进行基于当下社会现状的重新揭示与架构。
而宣读守护誓词的明星与素人则被视为电视机前共同参与仪式的观众们的代表,受众的情绪通过前序前世传奇与今生故事的不断积累,在这一刻得到释放与爆发,获得了在信仰、情感和意愿上的高度一致,激发了内心的崇敬、震撼、自豪等心理感受。在最后一期的特展揭晓盛典中,编导直接借用了电视颁奖晚会的创作形式,将别具匠心的道具、凝练概括的国宝揭晓辞,以及平行蒙太奇联动场内外仪式行为等象征符号进行组合,将其塑造为一场涵养心灵的集体仪式,一个与中华文明重逢的狂欢节。同时,《国家宝藏》以中国风独特的古典韵味结合现代舞台科技,构建了华丽纷繁的台型变幻⑩,将话剧舞台的质感融入节目之中,营造出震撼大气、逼真自然的效果。全息影像技术、3D幻影立体显示特效、冰屏柱、巨型环幕以强烈的空间纵深感和层次感以视觉上的冲击,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魅力展露无遗。而利用“纱盒”的立方体空间及投影模式所呈现的独立的舞台空间,真实再现了国家宝藏的影像全貌,以超真实的直观影像给人以多维度视角的审美震撼。
经过仪式化了的电视文化节目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感应,同时触碰到了集体深层的心理认识。在上述举例中,由象征性符号所建构的仪式感,或是唤起受众的崇高的情感,或是以实物符号融合非实物符号所营造的视觉奇观而带给人的震撼感,或是强化了人们对于人生、对于个人发展的审美感知,并对日常生活产生了直接的正向影响,如在各大城市中掀起的朗读热潮,全民范围下所推崇的国学热、诗词诵读热,以及以家庭为单位进入美术馆、博物馆去近距离接触国宝文物,这样的结果不是通过强制产生的,也并非德、智、体教育之下的产物,而是一种在寓教于乐、潜移默化影响之下产生的自发行为,高度契合美育的社会性、自发性及愉悦性等特征。仪式感所唤起的内心的崇高感、价值感以及共鸣感,使得受众获取了情感的共通,与经由国脉、文脉传承下来的共同心理,从而将个体整合到社会全体之中,维持并强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秩序。
三、“游戏化表达”契合美育精神的本质
综观时下现象级文化综艺节目,无论是对内容的挖掘,还是对角度的选取,都始终与“美育”价值的实现密切关联,激活文化记忆旨在帮助人们建构个体独立性,而仪式传播则以文化记忆为基础深入到了集体深层的心理认知,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大有裨益。而就外在结构形式而言,当下文化综艺节目的共性在于选择了一种更为契合美育精神本质的表达,即游戏化的表达,通过营造一个有益有趣的环境,将美育寓教于乐、润物无声的熏陶作用得以凸显、放大。
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席勒认为,近代社会之后严密的社会分工与等级差别使得人们身上的理性与感性两方面分裂开来,一种致命的冲突就使得处在和谐状态的人的各种力量互相矛盾了。故而需要形成一种更高的“游戏冲动”以弥合人的“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对立,即通过美育的路径让人们从“感性的人”变成“审美的人”,重新复归于古希腊时期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完整的人。席勒认为:只有当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而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席勒将游戏冲动的对象称作“活的形象”,这个概念指现象的一切审美的性质,即最广义的美。同时他又指出:“人应该同美仅仅进行游戏,人也应该仅仅同美进行游戏。”如前文所述,美育的根本目标即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曾提出过“人也要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重要论断,认为人们只有通过美才能走向自由。二者的观点不仅为美育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方法论层面上的依据,更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
每一个人都本能地对游戏带有着强烈的渴望和冲动,这份渴望便是源自人们对于自由的渴求,而人类精神文化最早的形态更可能源于原始艺术,对艺术的起源最妥当的说法便源于以游戏说与艺术的本性最为吻合——追求自由与超越,游戏也成为艺术不断创新发展的原动力。荷兰著名学者约翰·赫伊津哈在其《游戏的人》中,为游戏给出的定义是:“游戏是一种自愿的活动或消遣,在特定的时空里进行,遵循自由接受但绝对具有约束力的规则,游戏自有其目的,伴有紧张、欢乐的情感,游戏的人具明确、不同于“平常生活”的自我意识。”基于“游戏”对于审美教育的重要作用以及人们对游戏的本能的狂热天性,文化综艺节目将哲学美学概念之下的“游戏”概念或是“游戏精神”转化成节目创作中的“游戏化表达”,即在非游戏情景中使用游戏元素和游戏设计技术,利用节目中的环节设计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物关系得以外化。
如《中国诗词大会》通过挑战与应战、攻擂与守擂的“内循环搏击擂台赛”实现游戏化的表达;《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则以团队为单位,通过选手逐一登场的车轮战产生胜负;《诗书中华》以家庭为单位,在分工与配合中与其他家庭争夺晋级资格;《国学小名士》采用百人团挑战七星选手的游戏方式;《中华好诗词》则是通过选手挑战明星关主最终进入排位赛争夺……上述节目均将悬念保留到了最后一期,通过“竞争”产生了一个程序性的终结,即“总冠军”的产生,既符合游戏的内在逻辑,同时又契合作为游戏的典型结构,即闭合式结构。
而在以游戏元素为支撑的外部结构以外,节目内部的环节、流程也融入了游戏元素,如以《中国诗词大会》为代表的节目中,“飞花令”是一个广受观众喜爱的环节,它源于古人饮酒助兴时的文字游戏,围绕一个关键字,通过轮流背诵含有这个关键字的诗句决定胜负,选手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整说出一联诗句,这是诗词储备与心理素质的双重考验,其观赏性、紧张程度与竞赛感随着双方交替式的精彩表现而层层升级,“飞花令”也因此成为最能激发人们诗词基因、唤起诗心的环节。此外,《诗书中华》的兰亭雅集、曲水流觞取用古人欢庆娱乐、诗酒唱酬的休闲活动,并以此为主题建构一个唯美、古韵的诗词游戏场,而《国学小名士》中将古时军事战略得以游戏化处理,设置如“九攻九距”“分进合击”等游戏攻守环节。与此同时,节目播出的过程中设置了与场上选手同步答题赢取奖励的线下环节,激发了受众热衷游戏的本能与天性,参与者与受众被共同纳入到了同一游戏之中,受众与自身、与其他参与线下答题的受众以及与现场的选手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游戏与竞争关系,其参与度以及与节目的粘合度无疑变得更为紧密。
现象学代表人物伽达默尔辩证地阐释了游戏的理论,他强调游戏的真正主体是游戏本身,而不是游戏者,它既使游戏者自身得到表现,又使观赏者也参与了游戏,游戏就是由游戏者和观赏者组成的统一整体,其意义在于每时每刻的生成之中。文化综艺节目的游戏化表达便是基于此,它为参与者与受众建立了一个现实之外的世界,如流觞曲水雅集的娱乐场域、星云密布的“军事化战略”对战场域,通过参与者与观赏者在其中随着游戏的规则与推进过程发挥席勒所说的“创造力的自有表演”,消融于游戏的一体化之中。同时通过游戏的审美移情作用,将汉字、诗词、谜语、成语、信件、散文小说等文化符号得以人情化,拉近人与文化符号间的距离。节目以汉字之美、诗词之美、国学之美等为表现对象,并在其中融入了游戏的规则、游戏的设计,契合了人们游戏精神的心理本能,以轻松愉悦的态度走向本真的自我,即通过游戏的媒介作用促使自由、理性、感性统一的全面发展。诚然,游戏化的表达赋予了文化类节目美育功能实现的有力支撑,同时它也是契合当下消费市场环境下的有益探索与尝试,但是需要警惕的是,打着游戏化的旗号行文化主体性消解之实现象的出现。
美育的力量在于通过直接参与审美活动、艺术活动的实践,实现人性的完善,帮助人们走向精神境界的升华与审美的人生。在这个实现的过程中,提高人们整体的文化教养、关注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对其心灵的深刻影响,以及建构价值认同是关键所在,当下电视文化综艺节目已然做出了这样的尝试,综观时下的文化节目,它们的共性在于直指美育的本质,从激活文化记忆建构价值认同,到“仪式化”传播再到游戏化表达,笔者从内容、所选取的角度以及结构形式三个维度进行阐发,从内核到外壳,唯有形成合力方能使审美教育的作用发挥到最大。诚然,电视文化综艺节目促进了观赏文明的进步,同时对学校美育、社会美育的实施产生了正向影响与参考借鉴,但是如何产生持续性的影响,而非仅停留在因节目热播而产生的短暂美育效应,文化综艺节目如同抛砖引玉中的“砖”,通过激活人们共同的文化基因,产生与“美”游戏的冲动,而如何将这份兴趣与热情延续下去,进而转化为国人的日常习惯,笔者以为今后文化综艺节目的策划可以考虑与学校美育、家庭美育之间的联动与呼应,在两者之间建立一条通路,并在节目建立反馈机制,这不仅可以丰富电视文化综艺节目的表现主题,同时还可以在彼此联动中反观美育的发展状况。
注释:
①② 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3、12页。
③ 高鑫、贾秀清:《21世纪电视文化生存》,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④ 《贵圈|让国宝成为网红,〈国家宝藏〉靠什么征服了00后》,腾讯娱乐,https://ent.qq.com/a/20171221/027568.htm,2017年12月21日。
⑤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⑥ 何昊:《电视颁奖晚会的仪式感研究》,《电视研究》,2008年第3期。
⑧ [美]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倪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
⑨ [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⑩ 《〈国家宝藏〉舞台多媒体及灯光机械的秘密》,炫群科技百家号,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85468501805940291 & wfr=spider & for=pc,2017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