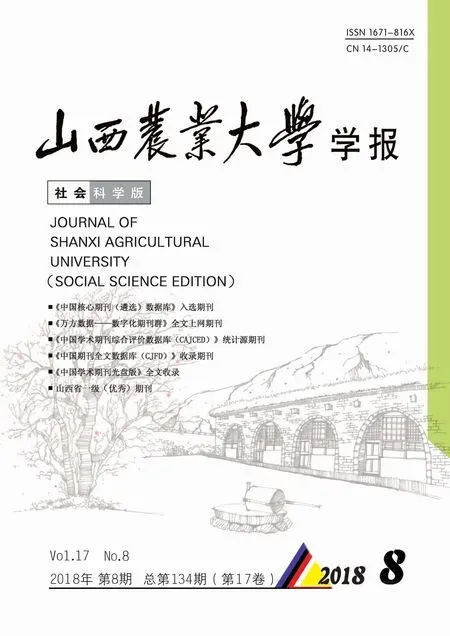安徽花鼓灯舞蹈服饰审美特征研究
孙强
(蚌埠学院 艺术设计系,安徽 蚌埠 233000)
地域性民俗文化的研究有两个基本着眼点:首先是人地关系研究,这关系到这种民俗文化生成与发展,属于文化研究的时间维度;其次是地域性文化之间的比较,这关系到民俗文化特征的定性,属于文化研究的空间维度。安徽花鼓灯历史悠久,自宋代就流传于淮河流域的凤台、怀远一带[1]。花鼓灯文化是淮河流域民间艺术文化丛的优秀代表,徐习文在其《民间艺术的文化审美意蕴及其保护》一文中提出了“文化丛”的概念,指出民间艺术的“文化丛”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民间手工艺、舞蹈、音乐等相关的技术事项;二是与手工艺、舞蹈、音乐相关的宗教禁忌、风俗惯例等行为事项;三是由技术事项的行为事项延伸的人文精神象征[2]。它源于傩、藏于佛、流布于宋代俗艺,其人地关系指向是社会底层民众的一种生存性艺术,从欢畅的展演背后,可以透视出淮河文化丛的整体文化意涵与特征,以及淮畔民众长期持守的风俗惯例。其中的服饰作为花鼓灯文化中重要的视觉元素,随时代发展而呈现核心清晰、边界模糊的形态格局,核心清晰指花鼓灯舞蹈服饰核心的淮河文化风格相对固定,边界模糊指具体的装饰手法、色彩搭配、形制样式灵活多变,善于吸收不同时代的审美元素。花鼓灯舞蹈服饰在空间的审美维度上则体现出多种民族元素融合、多元文化呈现的综合审美特征。
一、花鼓灯舞蹈服饰的形制特征
服装对于艺术的表现,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可以使演员的身体之美得到充分展现,所谓“衣必常暖,然后求丽”[3]。二是对扮演的角色、地位进行区隔的意义,不同角色的服饰暗示着不同的表演内容。三是传统服装取自自然,其色彩、装饰乃至款式则是人的设计思维的表达,因此它从本质上揭示着人与自然的关联,彰显了人与自然统一的关系。花鼓灯表演中,服饰具有多重意义,在满足舞蹈表演的实用功能前提下,其符号、装饰意义会得到充分凸显,这种装饰和符号的意义,从诸多层面强化花鼓灯艺术的表现力,使花鼓灯舞蹈服饰成为价值和意义的载体。在舞蹈和仪式中对服饰的选择予以高度重视,这种做法在传统中早有先例,例如董仲舒指导地方官员和百姓如何使用巫术求雨:
早春求雨……小童八人,皆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
夏求雨……壮者七人,皆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
季夏祷山陵以助之,令县邑十日壹徒市……丈夫七人,皆斋三日,服黄衣而舞之。
秋爆巫尪至九日,无举火事,无煎金器……鳏者九人,皆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
冬舞龙六日,祷于名山以助之……祝斋三日,衣黑衣,祝礼如春。
花鼓灯在远古时代由傩演化而来,最初是一种驱邪避灾的巫术,对服饰设计的重视有其必然性。由于花鼓灯在后世逐渐从仪式型活动向娱乐型展演转变,其服饰的样式并非如古代仪式服装那样固定,而是随着时代需求以及地域文化交流表现出复杂的开放性特征,但服饰的设计一直有明确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规律。因此,当前一些花鼓灯学者忽视花鼓灯舞蹈服饰的价值,认为花鼓灯舞蹈服饰仅为民间服装的简单融合,没有独特风格的观点是不客观的。
(一)从对宋代中原传统服饰的继承到多民族服饰文化的融合
淮河流域自古以来是中原地区的核心地带,著名的“四渎”之一,繁荣的文化为花鼓灯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花鼓灯舞蹈服饰,则是淮河流域的花鼓戏曲、花鼓灯歌表演这一系列花鼓灯文化服饰的总称,属于中原服饰大系的一个分支。服饰的意义既在保护身体,又在表现身体。《白虎通义》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制”[5]正说明服饰可以使人类摆脱野蛮状态迈向文明的功能。花鼓灯舞蹈服饰从社会角色服饰以及典型道具的角度,画龙点睛地塑造花鼓灯艺术形象,强化花鼓灯舞蹈角色的性格特征。因此其服饰的形制款式、色彩搭配、图案装饰,无不是民间生活与审美的高度浓缩,从整体的年代和地域特征来看,花鼓灯舞蹈服饰总是有意无意的浓缩着宋代中原服饰的影子,尤其是“鼓架子”包头巾的形象,成功塑造了宋代农民的典型形象。相比怀远县和蚌埠禹会区的花鼓灯,颍上县花鼓灯舞蹈服饰更加严格地遵循传统程式,其男装更加贴近宋代中原农民的服装,衣服领口、下摆、盘扣等设计都表现出浓浓的宋代传统意味。
具体而言,花鼓灯舞蹈服饰对宋代中原传统服饰的继承,又通过两种途径,一是日常劳动服装的继承,另一个是代表着人生着重符号的婚庆礼服的继承。前者体现艺术来源于生活,追求日常生活的趣味性以及劳动之余娱乐表演的便利性、即兴性;后者体现艺术高于生活,强调花鼓灯舞蹈的仪式性特征。由此,花鼓灯舞蹈服饰设计从物质层面向我们展示了花鼓灯文化内涵的丰富与深刻。
“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6]。”文化之间的异同是一个互动的、相对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元代以后因异族统治导致民族的高度融合,花鼓灯舞蹈服饰也逐渐形成了不同地域民俗服饰风格的多元格局。例如花鼓灯男角“鼓架子”下身的服装常为宽松大档配黑色布靴,具有显著的胡服特征。还有短褂上的立领,这是满族服饰的独特元素。如今的花灯舞蹈服饰更是吸收借鉴了许多当代的时装及舞台表演服装的特征,尤其是女角的服饰,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各种服饰审美元素混搭,形成更加丰富多彩的服饰样式。作为一种民间以娱乐为目的的展演文化,花鼓灯舞蹈服饰始终以博得大众的喜好为目的,因此很大程度上民众喜爱什么、民间流行什么,舞蹈服饰就怎样设计,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文化多元性。然而归根结底,无论继承宋代中原服饰还是多种服饰元素的融合,花鼓灯舞蹈服饰的传承都离不开民众的日常生活。
1.对婚庆礼服的继承
花鼓灯舞蹈服饰在朴素简单的服装上大量采用婚庆礼服中的吉祥元素,既为展演增添喜庆的氛围,婚庆礼服也是穷苦的演员们最高档的衣服,他们希望借此在心理上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汉代的贾谊就曾对服饰区分人高低贵贱的重要性进行深入的阐述,他在《新书》中说:“人之情不异,面目状貌同类;贵贱之别,非人人天根著于形容也。所持以别贵贱明尊卑者,等级权利,衣服号令也[7]。”花鼓灯的演员全部来自社会底层的穷苦农民,心理上追求平等的社会权利、提高社会地位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这种心理特征常常在花鼓灯服装和表演中不断地暗示着。例如花鼓灯舞蹈角色兰花的通常妆扮为:长款红色百褶裙,刺绣着花开富贵的吉祥纹样且有复杂的花草图案装饰。此外,花鼓灯女角所穿的鞋是绣花鞋,这是受女子出嫁时所穿红色绣花鞋的传统影响,这种鞋的传统做法是绸缎做成两边的鞋帮,彩色丝线从鞋头到鞋跟甚至鞋底和鞋垫上都绣上繁缛华丽的纹样,是明清时期新娘出嫁的必备妆扮。花鼓灯的男、女角色均由男性扮演,直至近代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升,女性才逐渐承担了花鼓灯的相应角色。因此,实际上女角的舞蹈动作、服饰扮相、角色唱词和对白等自古是由男性确立的,是男性眼中的女性形象的是一种呈现。如图1所示,这种女性装扮有时因男性的身材略作改动,例如精巧的绣花鞋无法穿在男性的大脚上,于是将绣花鞋中塞一块木板,倾斜的木板增加了鞋底的面积,成为“翘板鞋”,男演员穿着这种“翘板鞋”表演,步伐姿态类似于女性穿高跟鞋的婀娜多姿。男角“鼓架子”的服饰同样常体现婚庆吉祥的装饰意味,短褂或背心的衣襟,下摆处常有演员自己绣花装饰,大多为黄、蓝色的吉祥图案,服装本身的底色也不再只是白色,而是黑、灰、蓝或藏青,面料也改为更加飘逸的绸缎,有时看上去有点像劳动便装与男子婚庆礼服的混合风格。既体现男性的粗犷与大气,又展现着欢乐、喜庆和诙谐的风格。男角的服饰变化还体现在对襟处的衣扣上,为了增强扣子的装饰作用,有时扣子也设计成彩色,同时改变传统的五个扣子均匀分布的特征,设计成六个甚至七个扣子,集中在衣服的上部,使得服饰的款式富有变化。从男、女服饰的对比来看,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男女性别角色的差异所导致的服饰妆扮的不同,男性简洁、有力,女性妩媚温柔的形象对比展现的淋漓尽致。

图1 花鼓女角图片来源:安徽省怀远县文物管理所。
2.对日常劳动服装的继承
传统易象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传统的青铜、陶瓷、建筑、礼乐、车舆、服饰图案等传统艺术文化具有实用和审美合一的逻辑性和必然性[8]。在传统思维观念的影响下,作为一种全民参与的、集表演性与娱乐性为一体的花鼓灯舞蹈服饰,在设计的主观考量上,一方面,高难度的舞蹈技巧要求服饰必须合身且行动便利,另一方面舞蹈文本塑造的一个个鲜活的角色形象,需要服饰来配合表达。为了同时达到服饰的善舞性以及贴近生活的真实感,日常劳动服装显然是一个合适的选择。例如典型的颍上县花鼓灯 “鼓架子”的服装设计,头上裹着宋代中原风格的头巾,与腰带形成呼应,展现喜庆的氛围。上衣是深蓝色对襟无袖背心,下衣则是灰色的肥大裤子,简洁中透露着喜庆的艺术效果。这种服装作为舞蹈的表演服饰,还有两个客观原因:一是花鼓灯表演原本是社会下层的民众,在饥寒交迫的年代,这种表演时常用作街头乞讨招揽看客的手段,因此没有条件穿得更好;二是花鼓灯舞蹈也是劳动之余在田间地头的即兴表演,人们在树下、在田边空地自娱自乐,没有必要专门准备一套服饰进行表演。当个体生命以其超越性来面对美的问题的时候,这其实正预示着一种摆脱现实羁绊,使审美自由得以无阻碍实现的开端[9]。花鼓灯演员们常常将自己日常的劳动服装,简单做一些装饰,与日常略作区别就成为舞蹈服饰,这样的妆扮实际上更能拉近演员与观众的情感距离。
几千年来的演变中,花鼓灯舞蹈服饰在日常劳动服装和民间婚庆礼服元素的继承中,有了巨大的变化。例如,原本较为宽松的衣袖,经过更加窄紧甚至无袖的设计,表演者在表演高难度的舞蹈动作时显得更加便利,在成群结队的花鼓灯班进行集体舞蹈时,表演者往往还在腰间增加了红色或花色长绸,以渲染喜庆的表演氛围。此外,宋代传统服饰是不收腰的,而花鼓灯舞蹈女角的服装从民国时期开始逐渐采用收腰的款式,以强调女性优美的曲线。
(二)戏曲服饰中的吸收借鉴
花鼓灯舞蹈服饰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出能非常灵活地随着不同的时代、不同地域而变化的开放性特点,这与其十分善于吸收其他文化的特性有关。唐代之后,宫廷舞在我国过早衰落,戏曲服装在舞台表演服装中属于极为独特的一种形式,它以符号化的象征意义拥有其它舞台表演服饰不具备的审美语言,花鼓灯服饰恰恰继承了这一宝贵特征[10]。
1.非对称
戏曲服饰设计中大量出现非对称的设计手法,宋代之后中原平民的日常生活服装基本上都是对称结构,花鼓灯舞蹈服饰继承了宋代中原风格,在细部的装饰中,演员们时常故意打破这样缺乏变化的对称样式,依靠纹样处理、色彩搭配、扣子、腰带等辅助装饰非对称处理,表现出跳跃的、运动的非对称效果,审美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体现在具体的感性行动中。在日常生活特征突出的花鼓灯舞蹈服饰中,如果没有服装差异使审美具象化,花鼓灯文化整体都极易被日常生活的琐碎民俗活动所湮没,最终失去艺术价值。例如怀远花鼓灯女角兰花的服饰造型,兰花要间系着围裙,既体现着古代家庭妇女的典型特征,又提供了很好的装饰部位,围裙上刺绣的吉祥纹样大多是不对称的。鼓架子短褂对襟时常有龙纹的刺绣装饰,一般也不对称。此外,演员手持的道具岔伞、帕巾、带的红花等等许多都以不对称的方式显现,有时还特意强调这种效果。至于岔伞的样式,童忠良的《中国传统乐学》中就有记录:“柄以竹之,朱漆,以片藤缠结,下端蜡漆铁桩,雕木头冒于上端,又用细竹一百个插于木头上,并朱漆以红丝束之,每竹端一寸许,裹以金箔纸,贯以水晶珠[11]。”非对称手法的运用,是花鼓灯舞蹈服饰的一大突破,它显示着花鼓灯舞蹈服饰真正从日常生活服装中解放出来,是对实用性设计的一种超越,成为更具艺术审美特征的装饰性设计。
2.夸张
夸张是戏曲服装表现人物个性的主要方式,花鼓灯舞蹈服饰常常根据不同的表演主题,不同的人物性格展示需求对服饰的局部进行夸张处理。花鼓灯舞蹈中,演员的头、腰、手等是最常进行夸张装饰之处,这些部位利用道具、装饰纹样、异色进行强调,可以帮助演员塑造人物的性格特征,提高舞蹈的叙事性。例如花鼓灯男角服饰的肩部有时会增加一块小布片,这块布片无实用价值,但是可以夸张表现男角肩部的宽厚,以此体现男性的魅力,再如女角头部常佩戴大绸花,大绸花原本就是戏曲服饰中夸张处理的典型,在花鼓灯服饰中进一步夸张,硕大的绸花以非常夸张的装饰增强演员的主角地位。
3.简化与俗化
花鼓灯舞蹈作为在社会上长期流传的一种民间舞蹈,经常与戏曲服饰一样借鉴吸收社会各阶层的服饰特征,又将这些服饰特征异化,以满足自身的舞蹈动作和风格需求。例如手绢和折扇的借鉴和使用,戏曲服饰也常把手绢和折扇作为道具,体现了花鼓灯舞蹈服饰对传统服饰的俗化处理。手绢在传统商业是中国女性用品,常被用作体现女性含蓄、温文尔雅之美。折扇则是士大夫阶层的常用品,明清之际流传的“手中无折扇,地道庄稼汉”民谚就体现了这是一种古代雅士的象征。戏曲服饰使用手绢和折扇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变化,但风格特征一直保持着高雅的审美旨趣。这两种道具在花鼓灯舞蹈中表现的效果都完全不同,几乎所有的舞蹈文本都将其作为男女调情的工具,叫做“盘手绢”“盘扇子”,如图2所示,其俗化的处理与花鼓灯舞蹈的整体风格相协调。这种带有情色因素的俗化,使人在观看中获得情感的释放,同时消解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性,使下层民众因此获得心理上的自尊,因而可以获得很高的大众认同。

图2 盘扇子图片作者:叶浅予。
除了俗化的处理特征之外,花鼓灯舞蹈服饰还体现对戏曲服饰的简化处理,女角兰花的肩部有时会装饰一种网状云肩,这种云肩与戏曲的云肩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只是为了降低服饰的成本,同时避免装饰过于繁琐影响演员高难度动作的发挥,花鼓灯的云肩更加简洁但同样充分地体现了基本的审美形式的构成原则。正如竹内敏雄所说:“无论什么样的艺术家,只要他想创作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那么即便是潜在的也好,他都在跟本上遵循一般的审美形式原理[12]。”
二、花鼓灯舞蹈服饰的审美特征
(一)花鼓灯舞蹈服饰的时代性审美特征
自古以来,淮河流域都是灾害战乱频繁,在这里,艺术从来就不是人们丰衣足食之后的纯粹的精神享受。赵树冈指出:“战争和自然灾害对皖北造成的影响似乎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13],在民俗文化的研究中,现代的许多学者提出应当将民俗文化作为动态来进行系统地考察,注意到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文化是“活动着的、运动着的”。“十年九荒”的历史背景使得花鼓灯文化具有一定的心理安慰功能,为了达到对大众精神关怀的目的,其表演形式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以满足底层民众的审美要求,舞蹈服饰的审美也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马林诺夫斯基指出,游戏、游艺、运动和艺术的消遣,把人从常规故辙中解放出来,消除文化生活的紧张与拘束[14]。花鼓灯舞蹈服饰是一种将精神诉求进行物化的艺术形式,服饰装扮本身可以帮助调剂乏味的生活,减轻痛苦生活中的精神负担。花鼓灯文化讲究悲剧人生,喜剧表现,因而其服饰具有显著的逆向性特征。有别于传统美学品格,花鼓灯舞蹈服饰的设计虽然属于传统设计,却又显现着一种异于传统的“野性思维”,具有草根的、泥土的、不屈不挠的旺盛生命力,同时不失滑稽幽默、本色性情。除了逆向性特征之外,宋代之前的花鼓灯还具有很强的仪式性特征,这直接导致花鼓灯舞蹈服饰采用礼服风格。唐末宋初,花鼓灯逐渐繁盛,且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娱乐化,最终奠定了花鼓灯舞蹈服饰主要采用宋代的服饰为原型的服饰特征。元、明、清时期,由于外族的统治,花鼓灯舞蹈服饰又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服饰特征,例如男角的大裆裤,裤脚裹腿、黑色布短靴与胡服相似,对襟短褂、盘口背心以及镶边立领的造型又融合了满族的特征。民国及抗战时期,花鼓灯舞蹈服饰又吸收了传统的长衫以及近代农民的妆扮。到了现代,花鼓灯文化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分为传统的橱窗型花鼓灯,大众娱乐健身型花鼓灯广场舞以及舞台表演型花鼓灯,甚至如今还出现网络视频传播性花鼓灯表演,每种形式都有其自身的服饰特点。例如橱窗型在花鼓灯舞蹈服饰追求传统花鼓灯舞蹈得最典型特征,将其作为文化标本进行传承。大众娱乐健身性花鼓灯广场舞,由大众自发准备服饰,其特征更加日常生活化,同时对利用折扇、帕巾、大红花等标志性道具等对花鼓灯文化特征进行提取和深描。舞台表演性花鼓灯舞服,强调民俗文化的现代传承,利用现代的化妆、道具来表现花鼓灯的文化特征,其服饰带有大量传统与现代时装相结合的设计意味。网络传播的花鼓灯则更加多元化,体现出一定的后现代特征。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花鼓灯舞蹈服饰设计表现出很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对不同时代的文化做出各自的审美回应。
(二)花鼓灯舞蹈服饰的民俗性审美特征
花鼓灯最初仅是社会底层人民的一种俗艺,清代逐渐成为淮河两岸最受欢迎的民俗艺术形式,甚至在如今各种网络文化、流行艺术的冲击之下,众多民俗艺术需要特别保护才不致消失的背景下,花鼓灯依然是淮河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这一艺术被推向价值的顶端,其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它的服饰装扮与人的民俗生活最亲近,最能够在日常的情感层面触动人内心深处的隐秘。按照中国传统天人感应的理论,服饰装扮越是能够在审美层面打动人,便越能够“天人合一”,由此构成了花鼓灯舞蹈服饰的民俗价值谱系。建立在封建礼之基础上的传统宫廷舞蹈和戏曲艺术,虽然风格高雅并对人的行为有着劝勉的教育意义,但同时以约束任性为目的的主导性意图也体现在其中。对于民俗大众来说,这些艺术形式缺乏情感层面上的关怀,花鼓灯则是一种闹剧式的展演,可以满足生活在苦难中的民众的心理需求,狂欢之后,人们压抑的情绪得到缓解。表现在舞蹈服饰上,那就是对日常民俗风格的坚守和宽厚的包容性。例如,封建歧视女性的意识认为女性演出“有伤风雅”,因此兰花的装扮长期以来都系扎“勒子”“遮脸羞”,而清晚期的花鼓灯,率先扬弃封建陈腐思想,表现出对于女性劳动者的同情和包容。淮河文化的亲民性与多元性决定了花鼓灯舞蹈服饰的包容性。从花鼓灯舞蹈服饰的传承特征即可发现花鼓灯舞蹈服饰独特的艺术魅力。
关于服饰的意义,董仲舒说过:“凡衣裳之生也,为盖形暖身也。然而杂五彩、饰文章者,非以为益肌肤血气之情也,将以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亟行,使化易成,为治为之也[4]。”服饰既有“盖形暖身”的实用功能,又有“使教亟行”的教化和象征意义。当实用价值得到满足之后,服装的审美价值就得到了凸显,花鼓灯舞蹈服饰的历史发展充分体现了这两种价值的融合与统一,也正是这种融合与统一,才使得花鼓灯舞蹈服饰在整个花鼓灯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现代花鼓灯的研究中,应予以应有的重视。
参 考 文 献
[1] 谢克林,中国花鼓灯艺术[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14.
[2] 徐习文.谢建明.民间艺术的文化审美意蕴及其保护[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4):41.
[3] 刘向.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522.
[4] [汉] 董仲舒.春秋繁露[M]. 周桂钿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1:267,101.
[5] [汉] 班固.白虎通德论[M].[明]胡文焕校注.影印本.衣裳.
[6] [战国]庄周.庄子[M].陈涛编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61.
[7] [汉]贾谊.新书[M].方向东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2:67.
[8] 赵辉.易象思维的特征及文化表达[J].文艺研究,2007(6):43.
[9] 刘成纪.自然的人化与新中国自然美理论的逻辑进展[J].学术月刊,2009(9):19.
[10] 孙强.花鼓灯舞蹈服饰的传承与意义[J].枣庄学院学报,2014(6):115.
[11] 童忠良.中国传统乐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61.
[12] 竹内敏雄.艺术理论[M].卞崇道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43.
[13] 赵树冈.当代凤阳花鼓的村落:一个华北农村的人类学研究[M]. 台北:唐山出版社,2003:78.
[14] [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 费孝通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