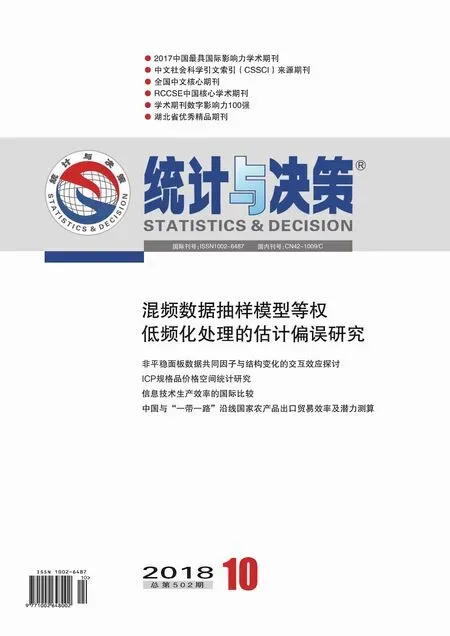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作用路径的实证检验
王 锋,张 芳,刘 娟
(中国矿业大学 管理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0 引言
随着我国进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去产能、调结构,实现经济健康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目标。然而,落后产能的淘汰、产业结构的调整,势必导致众多钢铁、煤炭等工业企业的破产或重组,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冲击。因此,找到正确途径解决由于调整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所造成的负作用成为现阶段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方面,金融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如 Bonfiglioli(2007)[1]、Gehringer(2013)[2]均发现,金融业可以通过加速资本积累、降低交易成本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此外,国内相关学者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如于斌斌(2017)[3]、徐鹏杰(2018)[4]均认为,产业结构与金融集聚具有较强的相互促进关系,金融集聚有助于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升到2016年的57.8%,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愈发凸显。与现实相一致,国内外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存在密切关系。如Hofmann等(2013)[5]从区域经济学理论出发,认为产业结构的变迁对城镇化具有重要拉动作用。孙叶飞等(2016)[6]认为新型城镇化通过发挥其“选择效应”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生产率,有效促进了经济增长。徐传谌等(2017)[7]认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能够显著地正向影响城镇化水平。
综合来看,大量文献研究了金融集聚、城镇化、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但鲜有文献探讨金融集聚和城镇化在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作用过程中的传导效应以及两者在作用效应力的大小问题。因此,本文将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以产业结构为自变量,经济增长为因变量,检验金融集聚和城镇化的作用路径与作用效应。
1 研究设计
1.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各省2005—2016年的面板数据,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历年统计年鉴。
1.2 模型构建
如果自变量X通过影响变量M来影响因变量Y,则称M为中介变量[8]。中介效应路径示意图如图1所示。

图1 中介效应示意图
其中,c是X对Y的总效应,ab是经过中介变量M的中介效应,c′是X对Y直接效应。如果自变量X同时影响多个中介变量Mi来影响因变量Y,则存在一元并行多重中介效应。在对一元并行多重中介效应进行估计时,假设所有变量已做中心化处理,则可分三步进行检验。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i=1,…,n,c是X对Y的总效应,c′是X对Y的直接效应,aibi为个别中介效应。
如果存在多个中介变量表现出顺序性特征,形成中介链,则存在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如图2所示。

图2 链式多重中介效应图
1.3 变量选取和假设提出
产业结构水平(IS):以第二产业产值占三次产业产值的比重表示(%)。自英国以工业革命实现经济腾飞之后,费夏、赤松要、里昂惕夫等经济学家从产业结构的视角出发一致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首先应该大力发展第二产业,依靠制造业推动经济增长是实现国富民强的不二法门。因此,提出研究假设1:产业结构水平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金融集聚(FG):目前衡量金融集聚程度的指标主要包括行业地区集中度(CR指数)、赫芬达尔指数(H指数)、空间基尼系数(EG系数)和区位熵(LQ)。参考文献[9]并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区位熵(LQ)作为衡量金融集聚的指标。区位熵也称为地方专业化指数,是根据基尼系数构造的衡量地方产业专业化程度的指标。

公式(4)的实质涵义是j地区的i产业在全国的区位熵系数。其中LQij表示区位熵值;qij代表j地区i产业的产值;qj代表j地区的总产值;qi表示全国i产业产值;q代表全国总产值。区位熵系数的值越高,表明地区产业集聚水平就越高。
城镇化水平(UZ):通过年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理论上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的崛起,势必会通过集聚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等吸引更多企业的集聚,而工业企业又往往是资金的需求方,因此,工业占比较大的区域也会是金融集聚水平较高的区域。其次,第二产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产业的不断发展需要大量劳动要素的投入,而地区人口的增长又直接造成城镇化率的提升。以往的研究也表明,金融集聚和城镇化率的提升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因此,提出研究假设2:金融集聚水平、城镇化率在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均具有显著正向中介效应。
经济增长(EG):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较多,包括GDP、人均收入、经济增长率等,结合所要研究的问题以及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选取经济增长率衡量经济增长。
早期的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剩余”的出现引起了资本的积累,资本的积累同时构成了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从而加大了就业规模和社会生产规模。“剩余”引起的“资本积累”需要金融业的扩张予以支持,资本积累构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直接促进了城镇化的进程,从而最终作用于经济增长。此外,陈立泰等(2012)[9]、王弓等(2016)[10]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与城镇化水平互为因果关系。因此,提出研究假设3是:产业结构→金融集聚→城镇化→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城镇化→金融集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作用效应。
2 实证结果与分析
2.1 金融集聚、城镇化的中介效应检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金融集聚与城镇化是否在产业结构至经济增长之间均存在中介效应,首先分别对FG和UZ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1。

表1 金融集聚、城镇化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表1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为0.3278。加上金融集聚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存在直接正向促进作用,其值为0.2853;金融集聚的中介效应大小为0.0425(2.0833×0.0204),占总效应的12.97%。若单独考虑城镇化,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仍表现为正向直接促进作用;城镇化的中介效应大小为0.0186,占总效应的比例为5.68%。该实证结果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2,亦即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金融集聚和城镇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部分中介效应。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这是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密切相关的。即以第二产业为主的高耗能产业对经济增长起到决定性作用,亦即第二产业所占三次产业的比重能对经济增长发挥巨大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现阶段去产能、淘汰高耗能产业需要有序推进。第二产业主要为工业企业,是资金的主要需求方,因此,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的提高需要大量金融资源的支持,从而引发地区金融集聚现象的出现。此外,工业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因此,产业结构水平的提高也会大幅增强对劳动要素的需求。金融集聚会通过金融集聚效应、扩散效应和金融功能效应促进地区经济增长[11],城镇化主要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集聚推动经济发展[12],因此,金融集聚和城镇化均在产业结构至经济增长之间表现为正向部分中介效应。
2.2 金融集聚、城镇化的并行中介效应检验与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金融集聚、城镇化在产业结构至经济增长之间的中介效应大小及其差异,需做一元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检验,估计结果见下页表2。
对于金融集聚与城镇化的并行中介效应的分析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总体中介效应的估计与检验。第二步,个别中介效应的估计与检验。第三步,个别中介效应间的比较分析。通过回归方程发现,金融集聚和城镇化的个别中介效应均不显著,这是因为金融集聚和城镇化水平存在较强相关性。因此,金融集聚和城镇化在产业结构至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相互独立的并行中介效应。

表2 金融集聚与城镇化的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2.3 金融集聚与城镇化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由于金融集聚与城镇化不存在并行中介效应,且考虑到金融集聚与城镇化之间的关联性,进一步做金融集聚与城镇化的链式多重中介分析。因此,首先对IS→FG→UZ→EG链式多重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估计结果见表3。

表3 IS→FG→UZ→EG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根据EG(1)至EG(3)模型的估计结果: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总效应为0.3278;加入产业结构水平后,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的系数为正;加入产业结构、金融集聚后,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正向作用并不显著。根据UZ(1)和UZ(2)模型的估计结果:产业结构有助于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加入产业结构水平后,金融集聚对城镇化存在正向影响。FG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对金融集聚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UZ(1)至FG模型结果,产业结构对城镇化的直接效应为0.4077,总效应为0.5679,金融集聚经由产业结构→城镇化的部分中介效应为0.1602(2.0833×0.0769),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8.21%,即在相关传导路径中金融集聚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处于次要地位。EG(1)至FG模型结果表明,产业结构→金融集聚→城镇化→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为 0.0343(2.0833×0.0769×0.2143),占总效应的10.47%,即产业结构通过先影响金融集聚进而作用于城镇化最终影响经济增长。
进一步做IS→UZ→FG→EG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的正向总效应为0.3278;加入产业结构水平后,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系数为正;加入产业结构、城镇化后,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正向作用并不显著。FG(1)和FG(2)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对金融集聚存在正向影响;加入产业结构水平后,城镇化对金融集聚具有正向作用。UZ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对城镇化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4 IS→UZ→FG→EG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FG(1)至UZ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虽对金融集聚具有负向直接效应,但其总效应为正;城镇化在产业结构→金融集聚表现为正向部分中介效应。综合EG(1)至UZ模型结果,产业结构→城镇化→金融集聚→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为0.0033,占总效应的1.02%。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05—2016年的省份面板数据,从城镇化与金融集聚的角度,对产业结构至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同作用路径进行了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金融集聚和城镇化在产业结构至经济增长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向部分中介效应,其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12.97%和5.68%。
(2)经由金融集聚、城镇化的并行多重总体中介效应不显著。
(3)产业结构→金融集聚→城镇化→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但不是主要的传导路径,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0.47%。
(4)产业结构→城镇化→金融集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部分中介效应,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02%。
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现阶段,中国经济正面临产业转型的重大挑战。因此,结合产业结构亟待调整的现实以及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本文发现,第二产业占比大的产业结构模式不仅对经济增长有正的直接效应,且会促进金融集聚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推进新型产业结构与去落后工业产能并不相悖,政府可以一方面大力淘汰煤炭、钢铁、水泥等高污染、产能严重过剩的企业,另一方面通过政策优惠等措施引进信息工业、智能工业、电子工业等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少、经济效应好的新型工业企业,争取实现产业结构由中后期到后期的完美过渡。
第二,加速金融业的发展,增强地区金融集聚水平。本文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在产业结构至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部分中介效应,所以,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能够部分抵消去工业产能对经济发展的冲击,从而达到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大力发展金融产业,不仅要维护国有商业银行、保险、证券等机构的利益,还要注重保护小型私营金融企业的发展。此外,国家应致力于协调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基金等各种金融机构的全面发展。由于金融机构一般存在“门槛效应”“嫌贫爱富”等特性,故政府更应对金融行业或工业企业提供相对优惠政策,以深化金融与企业的合作,发挥金融业的宏观经济调节作用。
第三,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在理论上,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解决城镇企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有序推进城镇化进程,最重要的是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合理鼓励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生活。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不仅是城镇行政区域范围的扩大和城镇人口的增加,还必须要有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否则行政化的城镇化不仅不能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助力,甚至会成为经济前进的阻碍。
[1]Bonfiglioli A.Financial Integration Productivity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7,76(2).
[2]Gehringer A.Growth,Productivity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n the Cas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Finance,2013,25(1).
[3]于斌斌.金融集聚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吗:空间溢出的视角——基于中国城市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7,358(2).
[4]徐鹏杰.金融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8,(1).
[5]Hofmann A,Wan G.Determinants of Urbanization[R].Asian Development Bank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2013.
[6]孙叶飞,夏青,周敏.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11).
[7]徐传谌,王鹏,崔悦,齐文浩.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2000—2015年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2017,(6).
[8]温忠麟,侯杰泰,张雷.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J].心理学报,2005,37(2).
[9]徐晓,光许文,郑尊信.金融集聚对经济转型的溢出效应分析:以深圳为例[J].经济学动态,2014,(11).
[10]陈立泰,刘倩.我国西部地区金融集聚与城镇化互动关系实证分析[J].城市问题,2012,(9).
[11]王弓,叶蜀君.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6,(1).
[12]刘军,黄解宇,曹利军.金融集聚影响实体经济机制研究[J].管理世界,2007,(4).
[13]蔺雪芹,王岱,任旺兵,刘一丰.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J].地理研究,2013,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