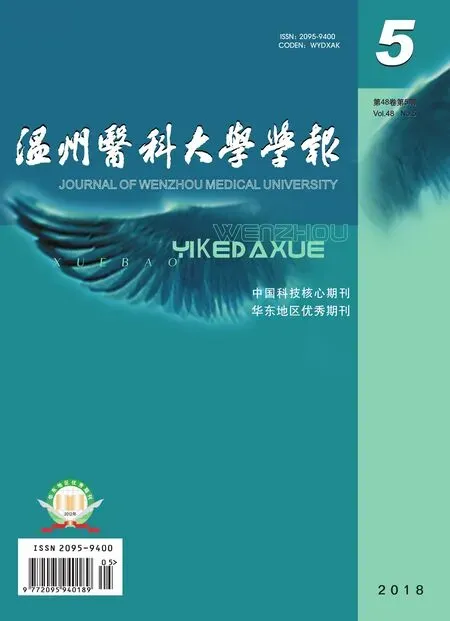缺血性结肠炎的临床特点及CT征象
赵奋华,单康飞,黄朝晖,朱伟华
(东阳市人民医院 放射科,浙江 金华 322100)
缺血性结肠炎(ischemic colitis,IC)又称结肠缺血,是由于肠壁血液供应不足或回流受阻所导致的肠道缺血性损伤,是缺血性肠病中最常见的类型[1]。该病好发于中老年人,随着人口老龄化,发病率逐渐增加,主要临床表现为急性腹痛、便血、腹泻,因发病较急,早期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而易误诊,CT检查对该病的早诊早治有重要价值。本研究回顾性分析2010年至2015年经确诊的39例IC患者的资料,旨在探讨其临床特点及CT征象,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并提高诊断准确率。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10年6月至2015年12月间东阳市人民医院经CT、结肠镜证实的39例IC患者的临床及CT资料,排除乙肝肝硬化、腹部肿瘤及其他急腹症患者。其中男14例,女25例,年龄35~83岁,平均(62.4±10.9)岁;50岁以下3例,51~60岁18例,61~70岁8例,71岁以上10例;伴有高血压15例,高血脂8例,冠心病3例,糖尿病1例,高血压合并糖尿病2例。临床表现:39例患者均因不同程度急性腹痛、血便、腹泻数小时至数天入院。实验室检查:大便常规隐血阳性34例(占87.2%),血常规白细胞升高33例(占84.6%),其中28例行D-二聚体检测,均有不同程度升高。
1.2 检查方法 使用Philips Brilliance 64排螺旋CT,Toshiba Aquilion 16排螺旋CT进行全腹部平扫、双期增强扫描。扫描参数:管电压120 kV,管电流150~250 mA,重建层厚/层间距分别为5 mm/5 mm,1 mm/1 mm,螺距1.03,矩阵512×512。增强扫描采用双筒高压注射器经肘静脉团注碘海醇(300 mg/mL)80~100 mL,速率3.5 mL/s。动脉期延迟28~35 s,静脉期延迟60~65 s。将薄层图像发至EBW4.1工作站,分别再运用多平面重建(multi-plane reformation,MPR)、曲面重建(curve plane reformation,CPR)和容积再现(volume ren-dering,VR)等方式进行图像重组。扫描范围从膈顶至耻骨联合水平。
1.3 图像分析 由2名从事腹部影像诊断的副主任以上职称医师对CT图像进行回顾性阅片,以横断面图像为主,并根据需要进行三维重建。观察病变肠管受累范围、肠壁厚度、密度改变及强化程度、肠管积气积液情况,以及有无肠壁及门脉积气、肠系膜水肿渗出、腹腔积液征象等。并通过薄层及重建图像观察腹主动脉及肠系膜血管斑块、血栓等情况,评估管腔狭窄程度。
2 结果
39例行CT平扫及双期增强扫描,10例行腹部CT血管成像(CT angiography,CTA)检查。CT表现:①病变累及的肠段:39例病例共累及97个肠段,平均累及2.5个肠段,累及升结肠9例,横结肠(含肝曲)13例,结肠脾曲27例,降结肠36例,乙状结肠11例,直肠1例。②肠壁厚度:受累结肠肠壁不同程度增厚,6~22 mm不等,平均厚度14.3 mm。③肠壁密度及强化:受累肠壁密度减低,增强扫描黏膜下层肠壁强化减弱,黏膜强化相对明显,增厚肠壁呈分层改变,表现为“靶征”“蟒纹征”(见图1A)。④肠管积气积液情况:27例受累结肠肠腔萎陷,11例肠腔内见少量内容物及积液,7例肠管有节段性扩张(见图1B),均未见明显气液平面。⑤肠壁周围系膜渗出、腹腔积液情况:10例病变肠段周围系膜渗出、脂肪间隙模糊,9例有腹盆腔积液(见图1CD)。⑥腹主动脉及肠系膜血管情况:10例行腹部CTA检查,其余病例通过对动脉期图像进行拆薄重建,共检出腹主动脉钙化斑块25例,累及肠系膜上、下动脉开口8例(见图1E-F),肠系膜上动脉轻中度狭窄4例,重度狭窄2例,肠系膜下动脉中重度狭窄2例,未见明确动脉瘤、动脉夹层及血管栓塞病例。
所有患者入院3 d内行结肠镜检查,并行病理组织学活检。39例患者均行保守治疗,21例患者在首次检查后的2周至1个月内行增强CT复查,其中20例肠壁水肿消失,1例肠壁水肿持续存在。

图1 IC患者典型CT征象
3 讨论
3.1 IC病因及临床特点 IC是由于闭塞性或非闭塞性的动脉供血不足或静脉回流受阻所导致的结肠缺血性损伤[1],占缺血性肠病的50%~60%,为除痔疮外下消化道出血的第二大病因。最早于1963年首先提出,1966年将其命名为IC并分型,分为一过型、慢性型和坏疽型,临床上以一过型最多见[2]。也有研究[3]将其分为非坏疽性及坏疽性两型,非坏疽性又分为一过型和慢性型,为可逆性肠缺血。本组经CT复查随访的21例病例中20例在短期内恢复正常,为一过型,1例肠壁水肿持续存在,考虑慢性型,在后期随访中,有2例一过型IC患者在1年内因再发IC入院,无坏疽型病例。
IC最主要的病因是血管因素,非闭塞性缺血所致的肠系膜血管血流灌注不足、急性动脉闭塞(栓塞性、血栓形成性)、静脉血栓形成均可造成IC,其中非闭塞性缺血是引起结肠缺血的主要机制,由一过性的血流减少引起约占95%[4]。一般认为本病与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相关,如动脉硬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本组有21例患者存在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基础疾病,并有8例患者存在血脂偏高,支持这一观点。临床上绝大多数患者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急性腹痛、便血、大便次数增多,便血症状通常为一过性,部分患者住院后期大便隐血试验即转阴,与之前研究[1]一致。IC可发生于任何年龄,以60岁以上老年人最常见,约占90%[5]。HIGGINS等[6]研究认为40岁以上人群发病率明显增高。本组患者平均年龄(62.4±10.9)岁,60岁以下21例,超过总病例半数,较既往报道患者年龄更趋年轻化,女性患者多于男性,比例为1.8:1,其流行病学特征仍有待多中心大规模病例进一步统计。
3.2 IC的CT特征 IC的主要CT表现有以下特点:①累及部位:从解剖学上分析结肠缺血在“分水岭”区域容易出现,结肠脾曲的血供为肠系膜上、下动脉移行部,此处吻合支较少,故相对容易发生缺血。本组病例中累及降结肠的最多,为92.3%,结肠脾曲次之为69.2%,直肠受累最少见,占2.5%。因降结肠主要由肠系膜下动脉供血,可能与其血管腔较肠系膜上动脉细小,易受血管斑块累及以及容易发生血栓有关,故降结肠及结肠脾曲是最常见的受累部位。而直肠为肠系膜下动脉与直肠动脉双重供血,故直肠受累少见。②结肠壁增厚:正常结肠壁厚度通常<3.1~3.5 mm,>3.5 mm即认为肠壁增厚[7]。结肠血流灌注不足会造成肠壁不同程度水肿增厚,为CT诊断IC的重要征象,有学者[8]将肠壁增厚程度以2 cm为界分为轻度增厚和显著增厚。本组病例平均厚度14.3 mm,以11~15 mm轻度增厚最多,重度增厚2例,肠壁增厚通常在CT平扫即可发现,故对急诊未行CT增强的病例亦有一定的提示意义,但肠壁增厚<6 mm时较难发现,可能出现漏诊。③肠壁密度及强化特征:结肠壁由内到外分别由黏膜层、黏膜下层、固有肌层和浆膜层组成。结肠缺血时可以累及肠壁某一层或几层,甚至整个肠壁,其中以黏膜和黏膜下层最易受累。平扫表现为低密度,当黏膜下有出血时可表现为密度增高。增强扫描肠壁强化不同程度减弱,典型表现为肠壁分层,即黏膜下层肠壁强化减弱,黏膜强化相对明显,增厚肠壁形成双环或三环征即“靶征”“晕征”[9]。笔者认为“靶征”是对肠管横断切面的描述,而结肠黏膜皱褶较多,走行曲折,其在纵行切面时,长段受累的结肠黏膜强化与蟒蛇纹路非常相似,提出用“蟒纹征”来描述更为贴切,在CPR或MPR时表现更为明显。随着肠壁缺血、水肿加剧,黏膜层及肠壁全层强化均减弱,此时“靶征”及“蟒纹征”均可不典型,有学者[10]认为如果增厚肠壁的黏膜层不强化,提示黏膜剥离或坏死,肠壁坏死的可能性明显增加,需考虑坏疽性IC,需急诊手术治疗。故此征象是评估肠壁血供情况的重要标志,对评价IC的缺血程度有重要参考价值。④肠管积气积液:本组超过2/3病例受累结肠肠腔均萎陷,肠管扩张较少见,可能与受累肠段出血水肿程度较轻,肠激惹蠕动加快,内容物排出加快有关,随着肠壁组织缺氧加剧,水肿程度加重,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液体渗出聚集在肠腔内增多,同时肠蠕动减弱,肠管扩张积液情况增多[11]。⑤肠壁周围系膜渗出、腹腔积液:近1/4病例存在病变肠段周围系膜内渗出、浆膜面脂肪间隙模糊征象,9例存在腹盆腔积液,随着肠壁水肿程度加重,肠系膜内渗出及腹水出现几率越大。⑥腹主动脉及肠系膜血管:通过CTA及动脉期薄层图像重建,共检出腹主动脉钙化斑块25例,超过一半的病例检出腹主动脉斑块,提示IC的发生与动脉粥样硬化存在一定相关性,但近4/5以上病例并没有肠系膜血管病变的直接证据,与文献报道有出入,一方面可能与CT分辨率有关,CT对肠系膜动脉主干及其二级分支的解剖情况较可靠,但对观察三级及以下分支不够理想[12],另一方面可能与肠缺血的一过性有关,未形成血栓或血管闭塞。另外因肠系膜下动脉通常较细小,CT对其管腔狭窄程度的评判可能存在误差。所有病例均未见肠壁积气、门静脉积气等提示不可逆性肠缺血的征象,与本组均为非坏疽型IC病例有关。
3.3 IC内镜检查及鉴别诊断 一般认为,结肠镜加病理活检是诊断IC的金标准[13]。本组39例均行结肠镜检查,内镜下表现为肠黏膜多处斑片状充血、水肿、淤斑,黏膜下出血,血管纹理模糊消失,病变肠管呈节段性分布,与正常肠管界限清楚。充血水肿严重时可见糜烂,部分黏膜坏死脱落、溃疡形成。镜下病理组织学可见炎细胞浸润,黏膜下层有红细胞渗出,大量纤维素血栓和含铁血黄素细胞,为此病特征[14-15]。鉴别诊断:主要需与溃疡性结肠炎相鉴别,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临床表现多为腹泻伴黏液便或脓血便,内镜检查溃疡浅,充血,出血明显,且病变分布连续,绝大多数直肠受累。另外IC患者症状消失迅速、恢复快[16],也是与其他肠病相鉴别的关键点。
综上所述,IC典型CT表现为结肠壁增厚水肿、强化减弱、肠壁周围系膜渗出、伴或不伴肠腔积气积液,部分患者可检出肠系膜血管病变,累及降结肠及结肠脾曲最常见,增强扫描肠壁黏膜强化可呈“蟒纹征”改变,对肠壁缺血情况的评价有重要参考价值。CT的及时应用可有效提高诊断准确率,对该病的早诊早治有重要作用。随着人口老龄化及心血管疾病发病率的增加,IC的发病有年轻化趋势,临床上对于急性腹痛、便血伴腹泻的患者应考虑该病的可能。多数IC患者通过纠正潜在病因与补充容量等内科保守治疗后可痊愈,预后较好。
参考文献:
[1] 张莹, 任华, 李长锋, 等. 106例缺血性结肠炎患者内镜诊断及临床的回顾性分析[J]. 中国实验诊断学, 2015, 19(7):1195-1196.
[2] 阮水良, 朱华丽, 顾小江, 等. 嘉兴市缺血性结肠炎近年发病趋势和临床特征回顾[J]. 中华消化杂志, 2014, 34(12):805-810.
[3] GANDHI S K, HANSON M M, VERNAVA A M, et al.Ischemic colitis[J]. Dis Colon Return, 1996, 39(1): 88-100.
[4] REEDERS J W, TYTGAT G N. Ischemic colitis: serial changes in double-contrast barium enema examination[J].Radiology, 1987, 162(2): 583-583.
[5] 吴本俨. 老年人急性缺血性肠病的诊治[J]. 中华老年医学杂志, 2009, 28(4): 268-269.
[6] HIGGINS P DR, DAVIS K J, LAINE L. The epidemiology of ischaemic colitis[J]. Aliment Pharm Ther, 2004, 19(7):729-738.
[7] 王豪杰, 朱希松. 16层螺旋诊断缺血性结肠炎的临床价值[J]. 医学影像学杂志, 2013, 23(4): 558-562.
[8] 袁雁雯, 杨立. 多排螺旋检查缺血性结肠炎临床价值分析[J]. 医学影像学杂志, 2016, 26(4): 683-686.
[9] WIESNER W, KHURANA B, JI H, et al. CT of acute bowel ischemia[J]. Radiology, 2003, 226(3): 635-650.
[10] CHOU C K, WU R H, MAK C W, et al.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poor CT enhancement of the thickened small-bowel wall in patients with acute abdominal pain[J]. Am J Roentgenol, 2006, 186(2): 491-498.
[11] 高云, 郑晓林, 杨沛钦, 等. 肠系膜动脉供血障碍性肠缺血肠管可逆性表现探讨[J]. 影像诊断与介入放射学, 2016,25(4): 311-315.
[12] RESCH T, LINDH M N, SONESSON B, et al. Endovascular recanalisation in occlusive mesenteric ischemia—feasibility and early results[J]. Eur J Vasc Endovasc, 2005, 29(2):199-203
[13] SREENARASIMHAIAH J.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ischemic colitis[J].Cur Gastroenterol Rep, 2005, 7(5): 421-426.
[14] 缺血性肠病诊治中国专家建议写作组. 老年人缺血性肠病诊治中国专家建议[J]. 中华老年医学杂志, 2011, 30(1):1-6.
[15] 阮水良, 顾小江, 官俏兵, 等. 缺血性结肠炎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国内文献分析[J]. 中华老年医学杂志, 2015, 34(5):565-569.
[16] 陈小微, 陶丽萍, 陈坛辀, 等. 非坏疽型缺血性结肠炎结肠镜与CT表现比较分析[J]. 温州医学院学报, 2011, 41(1):8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