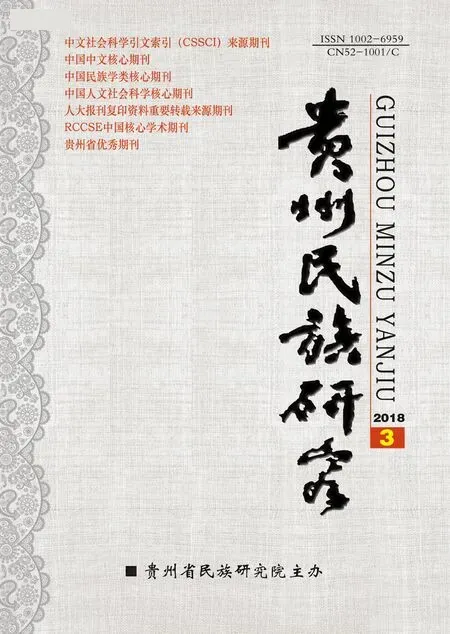社会身份的视觉性表征:苗族刺绣的身份认同探析
叶荫茵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5)
“人生而裸露,但是无论哪里的人都穿着衣服。”[1]人类学家特纳的这句话几乎概括了人类学关于服饰研究的核心:在人从生物存在转向社会存在的过程中,服饰的功用和意义。乔安娜·艾彻(Joanne B.Eicher)通过梳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人类学服饰研究英文文献,总结不同时期和地域,针对不同族群的研究的共同观点:服饰是社会身份认同的一种呈现方式和交流媒介。[2]台湾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结合古代典籍和川西羌族的田野调查,将服饰视为一种社会认同和区分的表征。[3]由此可见,人类学聚焦于服饰和认同的关系。特纳将服饰称为“社会皮肤”(social skin),也意在强调以服饰为媒介,人的多重社会和文化身份的视觉性展现和表达。
一、苗族的区分标志和文化表征
在人类学的族群研究中,服饰首先是族群认同的重要表征和族群性的组成部分。这一点从族群服饰的定义中得以体现。所谓族群服饰,是指族群成员共同穿戴的,用于认同本族并区分他族的服饰。[4]在人类学关于族群性的研究中,族群服饰逐渐固定为“区分族群的外观标记” (surface marker of group differences),并成为“族群性的核心要素” (the core element of ethnicity)[5]。这一认识普遍存在于族群认同理论的根基论/原生论(Primordialist)中。根据根基论的阐释,族群性由一系列先赋和内在的,且不受社会和政治影响的稳定特质而构成,譬如祖先、亲属关系、宗教信仰、语言、地域和服饰。由于族群性的一些特质(譬如祖先和亲属关系)是非社会公开性和不易察觉的,服饰便以其强烈的视觉特征来区分族群并划分边界。[6]根基论虽然自70年代后遭到了来自以巴斯(Barth) 等学者为代表的族群边界论和以伍德(Wood)为代表的族群工具论的批判,但族群服饰仍然一直被认为是族群性的重要视觉标志和文化表征,甚至于巴斯也认可服饰区分族群的功用和有效性[7]。概括而言,族群服饰和族群认同密切相关,族群内部成员凭借共同的服饰来认同彼此,族群外部凭借不同的服饰来区分不同族群。
服饰对于族群的区分功能和意义对于生活在贵州的民族尤为重要。首先,贵州世居民族没有明显的体质形态上的区别,从外在特征(如肤色和面部结构)上不易辨别。其次,由于贵州高原山地的地理特征,民族在地域分布上呈“大杂居、小聚居”和“既杂居、又聚居”的形态。贵州有相当多的村寨都是苗汉杂居、苗侗杂居和苗、布依族杂居,从地理空间上划分族群亦有难度。再次,元明清时期,贵州少数民族居住呈现流动的状况。大量汉族移民和少量回族、蒙古族进入贵州,世居少数民族被迫迁移至山林,也造成了如何区分移民群体和主体民族的问题。在此背景下,语言和文化成为贵州各民族主要的区分方式,而其中最直观的则是各个族群的民族服饰。[8]
以服饰来区分贵州苗族各支系散见于各类历史文献和当代文献中。譬如,清康熙年间黄元治《黔中杂记》载:“饮食起居,诸苗亦相若,惟衣裳颜色则各从其类”。又如,清康熙年间陆次云《峒溪纤志》云:“苗部所衣各别以色,散处山谷,聚而成寨。”以上两者皆是以服饰作为苗族支系分类的主要依据。[9]又如,清朝编绘的《百苗图》以图册配以诗文的方式,识别了当时居住于贵州省的82个族群。该系列抄本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以服饰来对不同苗族支系进行分类,如根据衣服颜色而命名的红苗、白苗、青苗、黑苗和花苗。[10]之后很多学者关于苗族支系的研究大都受到了《百苗图》的影响。如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根据他在1905年西南地区对苗族进行调查的结果而撰写的《苗族调查报告》,就是以《黔苗图说》为蓝本,对苗族各支系进行识别和研究。他在其中特别指出:“纯粹之‘苗’……系依据其服色及刺绣等而为土俗学上之区别”[11]。凌纯声在《苗族的地理分布》中沿用了《百苗图》的分类方式,依服饰颜色将苗族主要亚支系划分为五种。再如,杨万选《贵州苗族考》提出汉族命名苗族支系的两大方法,“一为地理性的,一为装饰性的”[12]。这里所说的装饰,就是各支系的服饰区别。依服饰(颜色) 对苗族支系进行分类,虽然在当下被批评为理论依据不足而显得粗糙和片面[13],但对外部观察者而言,基于服饰视觉特征而对所看到的苗族进行归类,也是对所属文化环境秩序的一种创造。
二、苗族支系内部社会文化秩序的视觉化体现
对于族群成员来说,服饰的区分功能则更为复杂和细致。在贵州省黔东南台江县施洞镇的田野调查,具体阐释施洞苗族社会女性刺绣服饰在性别、年龄和阶层的塑造和区分。
(一)社会性别的区分和建构
在施洞苗族社会,刺绣服饰是施洞苗族女性的专属,具有明确的性别区分功能。施洞苗族男性有传统苗族服饰,但一方面,男性传统服饰上仅有一条镶有银片的织花腰带,和女性满身刺绣的服饰形成强烈反差;另一方面,男性多是在节庆(如龙船节)象征性地穿戴传统服饰,以示自己的施洞苗族身份。在日常生活中,施洞男性的服饰已经和汉族并无二异,而制作和穿着刺绣服饰依然是苗族女性最重要的日常生活实践。更重要的是,女性的刺绣实践是苗族社会建构女性性别角色的重要方式和对女性的核心期待。在施洞,“绣花绣得好”几乎是对一个女性最高的赞美,其中包含了对女性品德、智慧和能力的肯定。
在大多数东西方文化中,刺绣都被视为女性的活动和工作,并用来建构女性气质(femininity)并规定女性的性别角色(gender roles)。其中最为突出的著作是罗斯卡·派克尔(Rozsika Parker)的《颠覆之针:刺绣和女性的塑造》。派克尔的核心观点是: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起,刺绣就变成了压制女性,使她们归于顺从的一种手段。从十六世纪起,教授年轻女性刺绣技艺旨在向她们“反复灌输顺从,谦恭,默从和贞洁”的品德。至十九世纪,女性的刺绣活动已被完全视作“女性本性的自然流露”。由此,女性和刺绣之间刻意的文化界限被模糊了,而被置换成“女性天生是刺绣者,刺绣者天生是女性”的全等于关系(女性≌刺绣者)。这种关系的建立,实质上是为了维持男性在公共空间和家户空间内相对于女性的优势地位。正是因为刺绣培养并体现了女性的柔弱和耐心,所以她们需要被男性保护在家户空间内,并且顺从于男性。[14]
相对于派克尔“女性主义色彩”较为浓厚的论述,格蕾丝·方(Grace Fong) 则从身体规训的角度,阐述在晚期帝制中国,刺绣作为一种身体性的训练是如何培养女性的心性和德性的。[15]在福柯对身体规训的阐释中,权力关系能够直接控制、干预、训练和折磨肉体,以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16]为了获得一双灵巧的双手,女性的身体长期处在紧绷的状态中。格蕾丝描述道:“刺绣是一种身体和视觉的训练: 长时间地弯坐在刺绣架上,或手握刺绣绷子,在手指上下翻飞的同时,还需要仔细地盯着不断展开的图案。更何况刺绣是一种无休止的重复的活动”。[17]由此,格蕾丝认为对女性而言,刺绣的作用和背诵佛教经文类似,即都是在虔诚的身体姿态中,通过无休止的重复,不断积累谦卑,专注和忍耐的美德。换言之,女性刺绣技艺的习得,同时也是对其身体的规训。而基于儒家文化中思想和道德的紧密联系,这一规训的最终目的,则是培养女性勤勉,细致,谦逊和耐心的女子性情。
在施洞苗族社会中,女性通过刺绣所表述的个体价值和所得到的社会认可,直接关系到她们的婚姻选择。“姑娘不绣花,找不到婆家”这句俗谚在施洞广泛流传,强调不会刺绣对苗族女性的婚姻造成的影响。苗族史诗“寻找祭服”中也有类似的叙述:“七姐名字叫阿丢,嘴笨不会说情话,手拙不会绣衣服,妈妈心里好忧愁,嫁给谁家作媳妇?把她嫁给汉人家,起初拿她当丫头,后来娶她作媳妇。”[18]这段看似轻松俏皮的叙述,实际上具有强烈的警告意味:不会刺绣意味着失去族群身份(被迫和汉族通婚)和配偶身份(低人一等的丫头)。
刺绣技艺好的年轻女性,在婚姻市场上能够获得择偶优先权。在苗家婚俗中,有“背着娃娃谈恋爱”的说法。这句谚语的真实意思并不是字面上所显示的开放的婚恋观,而是指苗族女性展示刺绣技艺的方式。适婚女性背着亲手所绣的空背扇,意在向社会显示自己的刺绣技艺,力图在婚姻市场上获得尽可能多的青睐,由此拥有更广的配偶选择权。施洞苗族女性的刺绣服饰制作和穿戴,不但是性别的外显区分,更是苗族社会建构女性性别角色的重要方式,并通过婚姻这一社会制度来对女性的刺绣实践进行考量和评价。

表一 苗绣颜色的年龄对应
(二)婚否和年龄
在施洞苗族地区,女性的婚姻状况和年龄是通过服饰上刺绣不同的颜色而体现。具体来说,施洞服饰刺绣部分主要以两种红色和五种蓝色为主,尤其体现在对襟衣衣袖花的部位。笔者综合了大约十位施洞女性的访谈,将七种主要的刺绣颜色分别代表的年龄段概括为下表(表一):
施洞苗族女性年龄层次的变化和婚姻状况基本是以刺绣从明亮色到暗调色的渐变为标志的。年轻女性多穿红橙、宝蓝等较为明快的颜色;中年女性的色彩范围较广,大多偏向中等亮度的红色和蓝色;而老年女性则固定在偏暗色系的蓝色上。在节庆时,几乎所有年龄段的女性都可以穿红色刺绣盛装;在赴宴的服装选择上,苗家讲究客随主,即根据宴会主人服饰的颜色来选择相近的颜色。此外,年龄和婚否的标志还根据发型、头饰和身上佩戴的银饰综合而定。甚至连刺绣主体颜色和其他点缀颜色的搭配,在施洞苗族女性眼中都意味着年龄的差别。正如台湾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在对羌族妇女服饰进行研究所言:“妇女服饰上些微的差别……在当地人的意识中却有非常的重要性。”[19]换言之,女性年龄在施洞服饰上的体现,属于较为隐秘的“地方性知识”,留待更多的学者去探讨。
(三)社会阶层的区分
苗族刺绣服饰显示了社会阶层的区分。从概念的界定来说,此处的社会阶层(social stratification)指的是由于社会各成员或群体所占有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不同,由此导致的不同成员和群体之间结构性的不平等[20]。在西方社会分层的两种理论传统中,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主要以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即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作为阶级的划分标准;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则认为阶层是由经济地位(个人收入和拥有物资的总和)、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三方面不平等的综合作用而造成的。两者都指向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对社会阶层的影响。
在九十年代之前,苗族服饰被视为施洞女性珍贵的物质财富,并体现了她所在家庭的经济地位。具体来说,这体现在苗族女性拥有刺绣服饰的数量和质量上。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和贵州省民族研究所于1956-1963对贵州省台江县的苗族女性服饰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其中统计了施洞苗族女性在出嫁前后两三年内刺绣服饰的占有情况(见表二)。[21]虽然这一阶级划分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但依然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施洞苗族的贫富分化状况。从统计数据看,施洞女性刺绣服饰的占有率是和所在家庭的阶级(经济地位)成正比的。与此相对应,在笔者的田野中,刺绣服饰的缺乏,是几乎所有年纪较大的苗族女性对于那个贫苦年代的深刻记忆。一些女性清楚地记得出嫁时只能穿便装的窘迫;另一些女性则有当时家里只有一件刺绣嫁衣,几个姊妹出嫁时轮流穿的相似经历。

表二 施洞各阶级女性刺绣服饰占有比较
制作苗族刺绣服饰是一件非常费时的事情,一件刺绣盛装大概需要2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因此,只有生在富裕家庭,不需要承担过重农活的苗族女性才有大量的时间来刺绣新衣。而对于贫困家庭的苗族女性来说,繁重的农活和家务几乎占据了她们的所有时间,因此十几年才能完成一件刺绣服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苗族女性所拥有的刺绣服饰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她们在农活和家务之余闲暇时间的累积,而农活和家务的负担轻重取决于女性的家庭经济状况。
这一点类似于美国社会学家托斯丹·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 在他著名的《有闲阶级论》中提出的论断——闲暇时间体现了阶级的区分。具体而言,有闲阶级是指那些有资产,不需要承担过多的工作和劳动,生活以休闲和娱乐为主的阶级。他们显示自己和劳动阶级的区别在于通过对“时间的非生产性消费”(non-productive consumption of time),显示他们有“资力来负担闲散的生活”(pecuniary ability to afford a life of idleness)[22]。
虽然托斯丹·范伯伦的理论是对19世纪末期工业化背景下,美国上流阶级炫耀性的消费习惯的批判,但以闲暇时间来作为不同阶层经济地位的标志同样适用于其他社会。譬如,刺绣工作(crewel work)在新英格兰乡村是一种“高贵的专利品”(patent of nobility),因为被人支配而每日忙碌的人,是不可能有大量空闲时间来做刺绣的。[23]在明清时期,刺绣象征了富裕之家给予女性的闲暇生活,这成为她们与那些双手粗糙的农家妇女的区别。[24]同样的,在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施洞,刺绣所需要的空闲时间是由充裕的财产和相对轻松的环境来保证的。女性的刺绣数量间接体现了她们的经济地位和所对应的社会阶层。换言之,刺绣不但是苗族女性的物质资本,也是象征资本。
余 论
当下,苗族刺绣不仅仅是族群的历史文化符号和族群性的组成部分,更是贵州省的一种特色民族旅游工艺品。原本为族群内部自用,作为族群性标志的刺绣成为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在此背景下,苗族女性利用自己的苗绣技艺和资源,努力寻找新的生计机会以及向外发展的空间,由此改变了苗绣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然而,在探讨商品经济向苗族乡村经济的渗透及带来的变化时,需要回归到苗族刺绣在族群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方面的重要性。若不能理解苗族刺绣和女性的刺绣实践在建立和维系苗族社会性别制度和社会秩序中的作用,便无法探寻苗族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本源和变异。
参考文献:
[1]Turner T S.The Social Skin[J].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2012 2:2,486.
[2]Eicher J B.Dress and Ethnicity:Change Across Space and Time [M].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1995:300.
[3]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M].台北:中华书局,2008:265.
[4]王明珂.羌族妇女服饰:一个“民族化”过程的例子[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8,69(4):841-885.
[5]Taylor L. The Study of Dress History[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2:206.
[6]WallP G,Yang A P L.Planning for Ethnic Tourism[M]. Farnham: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14:5.
[7]Barth F.Ethnic groupsand boundaries: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culture difference[M]. Long Grove:Waveland Press,1998:1-38.
[8]Harrell S.Reading threads:clothing,ethnicity,and place in Southwest China[J].Politic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2009,1:4.
[9]伍新福.略论苗族支系[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3):87-91.
[10]杨正文.苗族服饰文化[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26.
[11]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30-31.
[12]杨万选.贵州苗族考[M]. 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170.
[13]吴荣臻,吴曙光.苗族通史(一) [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54.
[14]ParkerR.The subversive stitch:embroidery and the making of the feminine[M]. Saint Paul:Women's Press,1984:11,60-64,128,189.
[15]Fong G S.Female hands:embroidery asa knowledge field in women's everyday life in late imperial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J].Late Imperial China,2004,25(1):1-58.
[16]Foucault M.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M].Sheridan A,New York:Vintage Books,1979:25.
[17]Fong G S.Female hands:embroidery asa knowledge field in women's everyday life in late imperial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J].Late Imperial China,2004,25(1):19.
[18]吴一文,今旦,马克·本德尔.苗族史诗[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2:538.
[19]王明珂.羌族妇女服饰:一个“民族化”过程的例子[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8,69(4):841-885.
[20]Giddens A, Griffiths S. Sociology [M].Cambridge:Polity Press,2006:432.
[21]参见《施洞各阶级女性刺绣服饰占有比较表》,引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贵州省编辑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271.
[22]Veblen T.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M].Mineola:Dover Publications,2009:33.
[23]Wheeler C.The Development of Embroidery in America[M]. New York:Harper&Brothers,1921:35.
[24]Bray F.Technology and Gender:Fabrics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M]. 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