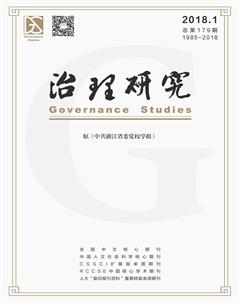比较法视角下我国文化行政法制的建构挑战
卢超
摘要:近年来,随着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领域的发展,我国相对滞后的文化行政法制建设越发不适应法治政府的要求。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文化行政法存在强调自由市场与精细化监管的北美模式,以及文化产业政府扶持为特征的东亚模式这两种类型,这两类文化法建构范式在法治实践中各自具有优缺点。我国文化行政法的发展需要从本土实践出发,并吸收域外文化法制建设经验,从政府监管组织体系、文化产业促进模式以及社会整合功能等多重角度着手,对我国文化行政法制体系进一步予以重塑改革。
关键词:文化监管;文化产业;政府规制;国家治理;比较法
中图分类号:D92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8)01-0119-007
引言
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所做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建立健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有利于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文化法律制度。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把行之有效的文化经济政策法定化,健全促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的制度规范”。可以说,文化行政法制建设已然成为当前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议题之一。然而从我国现状来看,我国文化行政法体系的构造尚显零乱、规范级别较低且不成体系。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化产业的发展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但与此同时也给文化监管带来诸多负面挑战,如何实现文化产业发展与政府监管之间的恰当平衡,既对快速发展的文化市场进行适度监管又不妨碍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进而探索寻找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政策均衡点,这需要从比较法的角度寻找相关制度借鉴。宽泛而言,文化行政法的建构模式存在北美(市场导向)与东亚(政府扶持)两类区别显著的制度形态,这两类处于制度光谱两端的文化法制模式,可以为中国本土文化规制体系的构建提供两种崭新的发展思路。
一、精细化监管与自由市场导向:文化法的北美模式
(一)美国联邦宪法为基石的文化自由市场模式
从文化立法体系模式来看,以文化自由市场为主导理念的美国,其缺乏一部调整和规制文化市场的统一基本法,涉及文化事项的法律法规分散在诸多不同文化行业领域内,其中较为代表性立法如《国家艺术及人文事业基金法》、《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法》、《电信法》等法律均与文化事业及产业的发展紧密相关。《国家艺术及人文事业基金法》是美国制定的第一部支持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法律,依据该法创立了美国历史上首个致力于艺术与人文事业的机构——国家艺术与人文基金会(National Foundation on the Arts and the Humanities),该机构宗旨在于制定文化发展政策、扶持文化艺术的发展并奖励从事文化艺术活动的优秀人员。①《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法》作为联邦层面一部规制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的法律,其立法目的旨在为图书馆与博物馆这两个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搭建一个崭新的合作平台,其反映了图书馆与博物馆这两类文化场域之间业态合作的历史趋势。敖晓梅:《美国图书馆法的演进与经验》,《四川图书馆学报》,2011年第4期;崔春:《美国〈图书馆服务与技术法〉2010年修订版解读》,《图书馆杂志》,2013年第7期。美国与文化产业、事业发展相关的法律数目庞杂,尤其是基于联邦主义体系的国家构造,各州针对自身的特点与需求,州层面针对文化事项也有大量的立法调控政策出台。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几乎所有的文化产业政策规范都与美国宪法言论自由条款有着难以剥离的关联。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立法……限制言论自由或者出版自由”,按照原旨主义的宪法解释,该条款针对的仅是最为传统的出版与个人言论领域,随着信息社会与网络时代的剧烈变迁,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适用范围也突破了原旨主义的狭义解释,而逐步从个人表达自由、出版自由领域扩展至广播传媒、网络信息产业的发展,可以说通过司法审查的钳控机制,宪法第一修正案为信息网络时代下的文化产业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从美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发展历程观察,其实质就是围绕宪法言论自由条款所进行的产业自由与政府监管之间的制度博弈,这一点尤其反映在广播电讯产业的政府规制历程之中。
(二)美国广播电讯规制:独立规制机构与内容监管
基于联邦宪法中言论自由条款的限制,美国政府对文化市场领域的直接干涉较少,这一特点尤其体现在传统的出版业市场。唯一例外的是,传媒广播影视等信息文化产业受到来自政府层面较多的管制拘束。早在上世纪20年代,美国依照1927年《广播法》成立了联邦广播委员会,由其专门负责广播电台与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政府监管事项。随后,为了应对广播业蓬勃发展带来的传媒市场竞争和行业垄断弊端,1934年国会通过《通讯法》,并依据该法成立了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取代了先前的联邦广播委员会,专门负责监督和管理当时全美无线电事务。随后国会又先后颁布了《公共广播电视法》(1967)、《有线通信政策法》(1984)以及《电信法》(1996)等法律,通过独立规制委员会的组织模式对广播电视市场进行监管。此外,联邦通讯委员会(FCC)作为美国广播电视市场的独立规制机构,往往会根据实际需要,审慎且适时地制定一系列行政规章,对广播电视行业进行精细化、专业化的政府监管。Mark S.Fowler,Regulatory Reform at the FCC,2 Benchmark 269,pp.269-272(1986).思想文化多样性作为内容监管的一项公共利益,被视为美国广电管制的最高规制目标之一,Lili Levi,The Four Eras of FCC Public Interest Regulation,60 Admin.L.Rev.813,pp.826-834(2008).在政府监管方式选择上,联邦通讯委员会最传统的监管工具仍然是审批许可制度,按照监管机构的规制理由,电波是一种具有一定稀缺性的“公共资源”,获得广播电视许可的私营广播电视公司需要履行政府设定的公共服务义务(例如播放一定数量的非营利性节目,分配适当的时间讨论社会公共问题等)。相关中文讨论可见,郑海平:《美国文化市场监管的经验及其启示》,《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宋华琳:《美国广播管制中的公共利益標准》,《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拘束,使得联邦通讯委员会对于传媒信息内容的监管始终受到较为严格的司法拘束。可详见,Jonathan W.Emord,The First Amendment Invalidity of FCC Content Regulation,6 Notre Dame J.L.Ethics & Pub.Pol'y 93,pp.115-170(1992).尤其是联邦通讯委员会对于色情内容的管制政策遭到司法严格限制,1996年国会通过的《通讯风化法》(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被收编于1996年《通讯法》的第五部分,可以视为美国保守团体试图在网络革命时代对信息内容进行规范的一项重大举措,其以反淫秽的名义设定的管制标准夹杂了诸多政治诉求,Patricia Daza,FCC Regulation:Indecency by Interest Groups,2008 Duke L.& Tech.Rev.1,pp.2-7(2008).因此遭到了从广播电视业到新兴互联网业等视听产业界的激烈反对,经过1997年产业界发起的连串诉讼之后,最终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违反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为由裁决该法案中的反淫秽条款(anti-indecency provisions)违宪无效。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判定认为网络行业需要获得类似于出版行业的同等保护,而不能适用政府针对广播媒体的严格规制标准。可见,Reno v.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521 U.S.844(1997).1998年国会通过的《儿童在线保护法》,其立法宗旨在于禁止以牟利为目的通过互联网向未成年人传播有害内容,经过若干年诉讼之后,该法案也因为涉嫌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而被判无效。Ashcroft v.ACLU,542 U.S.656(2004);ACLU v.Gonzalez,478 F.Supp.2d 775,813(E.D.Pa.2007).该案评析可见,Lindsay Weiss,The FCC's Crackdown on Indecency,28 J.Nat'l Ass'n Admin.L.Judiciary 577,pp.607-614(2008).另外需要说明的是,除了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监管模式之外,以行业自律为导向的自我规制(self-regulation)模式在美国广播影视类文化产业规制体系下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功能。Lili Levi,The Four Eras of FCC Public Interest Regulation,60 Admin.L.Rev.813,pp.853-859(2008).
(三)加拿大广播电讯规制:社会整合与国家认同功能
在文化规制体系的建构模式上,加拿大同美国相类似,均是更为强调“自由市场”模式的功效,可以归类为文化法模式的同一制度谱系。然而在加拿大文化规制领域中,基于多元民族文化的特质,广电传媒规制体现出鲜明的、不同于市场逻辑的国家建构主义色彩。加拿大广播电讯政策进程中,加拿大广播电视与电信委员会(CRTC)作为独立规制机构,在广播电信规制政策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除了对于淫秽信息内容的监管等相对常见的规制政策之外,加拿大广电传媒规制还附带有较为特殊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目标。Robert Miller,The CTRC:Guardian of the Canadian Identity,17 J.Broad.189,pp.196-198(1972-1973).就加拿大广播电信规制政策的社会目标而言,其要求广播系统需要反映加拿大独特的社会和文化属性,包括官方双语、多种族和多元文化共存等规制议题。为了应对国内分离主义,维护国家团结是加拿大文化体系领域的重要议题,另外作为传统移民国家,多种族混居融合、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结构现实,使得促进文化融合与塑造身份认同成为加拿大广播政策的一项重要规制目标。姜文斌:《政治、文化、经济目标之平衡:加拿大广播电视产业政策演变及其启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7-100页。而对于广播电信规制政策的政治目标而言,维护国家认同和保障文化主权是加拿大广播规制政策的重要基石。基于特定的地缘政治因素,边境毗邻和语言共通使得强势美国文化极易涌入加拿大境内,如果政府不对文化产业进行积极干预与政策扶植,不对本土文化产业提供财政支持和资金保障,国家认同和文化主权恐怕就此受损。因此,加拿大各个时期出台的广播规制政策报告和广播法案中几乎均将维护文化主权作为加拿大广播规制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Peter Johansen, the Canadian Radio-television Commission and the Canadianization of Broadcasting,26 Fed.Comm.B.J.183,pp.183-208(1973).為了达到捍卫文化主权的政治目标,对广播产业附加的“加拿大内容要求”成为一项核心政策,加拿大政府对广播的内容生产、传输、播放等诸多环节都进行了规制干预,此外,对文化产业外资的进入限制,以及在国际贸易协定中提出的“文化例外”原则,也主要是为了捍卫加拿大的文化主权而设立。周菁:《加拿大对文化例外原则的应用及启示》,《传媒》,2014年第10期。可以说,加拿大以捍卫文化主权为核心的一系列文化规制政策取得了较大成功,“文化例外”原则也逐步扩散并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和效仿。王军:《文化例外的历史演变及当代启示》,《理论月刊》,2017年第2期。
(四)中国文化监管机构与规制工具的不足
从文化法制的北美模式不难推断出,以独立监管机构作为组织框架,针对特定文化事项的精细化监管构造,是北美文化行政法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而且与一般政府监管事项不同的是,文化监管功能并不局限于经济效率目的,而往往带有鲜明的社会整合与国家认同的非经济价值目标(Non-commodity values),Mike Feintuck,“Regulatory Rationales Beyond the Economic:in Search of The Public Interest”,in Robert Baldwin,Martin Cave,Martin Lodge 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Regul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39-63;Tony Prosser,“Model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gulation”,in Dawn Oliver,Tony Prosser,Richard Rawlings eds.,The Regulatory State:Co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34-49.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加拿大广播电讯规制事项上。从制度借鉴角度而言,与之相比,我国文化监管机构存在职责权限划分不清的弊端,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文化部在诸多领域存在行政权限的交叉模糊地带,中宣部作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也分享了部分文化监管权限,并且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来临,文化市场领域愈发网络化、线上化,新成立的网信办也需承担重要的文化监管职能,但诸多机构之间并没有明晰的法定化职责分工,法定监管与意识形态管控之间往往也晦涩难分,典型譬如,新闻广电总局出台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把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办成讲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的通知》(新广电发【2017】163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真人秀节目管理的通知》(新广电发【2015】154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主持人和嘉宾使用管理的通知》(新广电发【2015】129号)等一系列涉及电视广播信息内容管理的规范性文件。使得文化监管的机构独立性与法治主义要素均相对不足。不仅如此,我国文化规制体系也缺乏精细化的监管工具,日常监管仍然主要依赖于传统的行政许可、处罚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带有“软法”色彩的约谈工具在文化行政执法中被大量运用,约谈手段尽管能够节省行政成本、促成市场主体的合规行为,但也存在法定程序不足、难以获得司法救济的弊端。有关政府监管中行政约谈工具的分析,可参见,郑毅:《现代行政法视野下的约谈》,《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胡明:《论行政约谈——以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为视角》,《现代法学》,2015年第1期。文化市场监管领域除了行政约谈工具之外,另外一项值得关注的监管工具则是“黑名单”制度,2016年文化部出台《文化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试行)》中,对于文化市场“黑名单”工具的适用范围和惩戒效果进行了初步规范,文化市场“黑名单”制度作为信用监管的重要工具,被认为是行政审批改革之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有效手段。但在实践运行中也出现了若干难题,譬如针对文化市场个体商户的惩戒效果不佳、联合惩戒机制匮乏等等诸多问题。可以说,我国文化领域监管体系远远达不到精细化标准,今后需要通过正式化的许可、处罚工具并辅以约谈、黑名单等非形式化监管机制,完整地构建起文化市场领域的精细化监管体系。
二、产业振兴与政府扶植机制为主导:文化法的东亚模式
正如前文所言,北美模式下国家针对文化市场尽管存在精细化的监管架构,但自由市场模式是更为主流的范式,这种自由市场精神尤其反映在文化产业发展上。以美国为例,通过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行业发展并引导资金投向是美国政府在文化产业、事业领域常用的行政激励与放松规制(De-regulation)手段。对于美国文化产业而言,联邦税法中的税收优惠政策(501c)是其实现文化规制目标,推动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发展的灵活规制工具。所谓501c是指《联邦税法》中的第501条c款,针对文化产业、文化事业的资助者,联邦税法规定减免资助者的税额,并鼓励各类基金会、公司和个人主体投资文化产业,引导市场资本涌入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领域。李妍:《美国税收政策如何助力艺术博物馆的发展》,《中国博物馆》,2016年第1期。这些免税资金实际上成为支持各类文化事业发展的隐性“税式支出”,而且这类隐性“税式支出”的份额已经远远超过了政府的直接资助规模。Jennifer McCrabb Black,Reforming 501(c)(3):Putting the Charity Back in the Charitable Deduction,13 Rich.J.L.& Pub.Int.251,pp.251-254(2009-2010).这类间接性的税收激励政策成为美国刺激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也显著区别于欧洲以及东亚国家政府所采取直接财政资助的文化扶持模式。
不同于北美更为强调“自由市场”模式,东亚地区在文化监管体制与产业发展模式上体现出显著的“发展型国家”特征,关于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的介绍可见,[美]禹贞恩:《发展型国家》,曹海军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版。国家层面对于文化产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指导帮扶作用。最为典型以韩国为例,韩国在促进文化产业的政策法规层面,出台了以《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为核心骨架,辅之以《电影振兴法》、《游戏产业振兴相关法》、《音乐产业振兴相关法》等一系列具体行业振兴法为构造的文化法治体系,其中政府担负的行业规划、行政指导与财政帮扶等法定义务机制扮演了重要的扶植角色。与之类似,文化产业极为发达的日本其背后亦有《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帮扶支撑。
(一)韩国文化产业振兴法律体系
按照2009年修订的《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的规定,韩国政府为了有效地扶持文化产业的振兴和发展,特设立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文化产业振兴院为法人单位,振兴院以外的个人或团体不得使用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的名称。文化产业振兴院“专门负责研究策划促进文化产业振兴的政策与制度;进行文化产业实际情况的调查与统计;制定文化产业专业人才的培育计划;促进文化产业创业、经营、流通、海外出口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事项”。韩国《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第31条。并且,2006年修订的《影视振兴法》中,韩国在文化观光部下专门设置了电影振兴委员会,该委员会具备法人资格,该法中对于委员会的人员构成、议事规则以及职责要求进行了详尽规定,按照韩国《电影振兴法》第14条的规定,电影委员会的职责主要包括:“制定与实施电影振兴运营计划;电影产业培育的调查研究事项;韩国电影认定、海外市场开拓与国际交流相关事项;电影振兴基金的管理与使用事项;韩国电影义务放映制度实施等其他事项”。为了韩国电影艺术的质量提高和电影产业的振兴,该法还专设了电影振兴基金,并对电影振兴基金的设立、组成与用途作了专项规定。按照韩国《电影振兴法》第35条之规定,振兴基金必须用于“韩国电影创作的支持;韩国电影出口与国际交流的支持;小型、短篇电影的制作扶持;电影放映场所设施的维修及改善的扶持;电影团体以及社会组织的活动扶持等事项”。2008年,韩国修订《游戏产业振兴相关法》,其立法宗旨在于建构游戏产业基础,制定游戏产品使用的相关规定,促进游戏产业振兴并确保健全的国民游戏文化,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文化生活质量的提高。在该法中,对于游戏产业专业技术人才的培育、技术开发的促进激励政策、产品标准化体系推进、游戏产品流通秩序以及海外業务的拓展均有详尽规范。详见韩国《游戏产业振兴相关法》第4-15条。与之相类似,2009年修订《音乐产业振兴相关法》,则对于音乐产业振兴综合计划的制定实施、技术开发与人才扶持机制、练歌房业的许可规制以及唱片的流通标识与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等事项做了细化规范。详见韩国《音乐产业振兴相关法》第4-14条。
(二)日本《文化产业促进法》的扶持框架
除了韩国以外,日本作为一个文化产业非常发达的国家,其动漫、电影、游戏等文化产业的国际影响力举足轻重,文化产业亦是受到日本政府重点扶持的战略性产业。基于相似的文化产业背景与政府激励模式,日本同样也有类似的文化产业促进法规范,全称是《关于促进内容的创造、保护及活用的法律》(以下简称为“文化产业促进法”),这部文化促进法于2004年6月正式实施。2004年《文化产业促进法》第2条对于本法所谓的“内容”做了明确界定,其是指“电影、音乐、戏剧、文学、摄影、漫画、动画、计算机游戏和其他由文字、图形、色彩、声音、动作或图像,或这些元素组合而成的作品,或提供此类信息的程序(指计算机指令),是人类创造性活动产物中属于教育或娱乐范畴的部分”。日本《文化产业促进法》中以大量篇幅分别规定了产业促进主体、文化管制激励工具以及实施机制等方面的内容,这构建起日本文化产业促进体制的骨架。日本《文化产业促进法》第9-16条。《文化产业促进法》还进一步设定了若干项产业振兴的必要激励措施,譬如多渠道的资金筹措制度、针对侵权行为的维护措施、公平交易体系的构建机制、海外文化产业促进机制以及针对中小企业的照顾机制等。日本《文化产业促进法》第17-22条。
(三)我国文化产业促进法体系的现状及发展
可以说,尽管日本与韩国在文化法体系上存在一定差异,但从制度共性角度来看,基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治理特质,日本与韩国的政府宏观战略与直接财政支持对于文化产业发展均起到了核心助推功能,这亦是其与西方国家自由市场模式之间最为明显的差异。与韩国、日本相类似,政府支持为导向的文化产业扶持政策亦是我国文化法制体系的一项重要特征,这其中财政部出台的文化产业专项资金政策起到了极为关键的扶植功能。《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教【2010】81号)对于文化产业专项资金的管理、拨付以及企业申报事项做了原则性详细规定,除此之外,在金融、税收政策领域,《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银发【2010】94号)、《文化部、人民银行、财政部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文产发【2014】14号)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则从文化企业金融扶植的政策角度做出若干部署。另外,针对影视、动漫游戏、音乐等不同新兴业态的文化产业,中央及相关部委亦有专门的产业扶植政策文件,譬如《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大力推进我国音乐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广出发【2015】81号)、《文化部关于扶持我国动漫行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文市发【2008】33号)、《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财教【2014】56号)等数目繁杂的产业扶持文件,对各项文化产业的促进发展发挥了针对性的支持功能。然而尽管如此,与日韩等东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有的文化产业促进法制体系极为零散,尽管实践运行有大量的文化产业扶持政策,但均是以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散见于不同文化行业的监管部门,法律规范效力较低且零乱不成体系,文化产业扶持政策的法治化建设水平还处于较低的水准。蔡武进:《我国文化产业法体系建设的进路》,《福建论坛》,2014年第10期。另外,近期值得关注的文化立法进程是2016年《电影产业促进法》的出台,作为电影行业单行的产业促进法,该法的颁布出台不仅对电影行业的发展起到重要激励功能,也将为今后出台统一的“文化产业促进法”提供立法经验。于浩:《电影产业促进法:大荧幕进入法治时代》,《中国人大》,2017年第2期。但必须指出的是,“文化产业促进法”的立法推动由于涉及面极广,牵涉到不同的文化行业与监管部门,需要不同部委之间的利益博弈与协调磋商,现在仍处于部委内部酝酿阶段,距离正式立法颁布还有不小的距离。
三、我国文化法体系建构的启示
首先,我国现有的文化监管组织体系需要借鉴域外经验进一步予以改革。就我国目前的文化监管机构设置而言,分业监管模式是文化监管的主要方式,中宣部、文化部、中央网信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工信部等诸多部门在其各自特定权限范围之内行使文化监管职能,然而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三网融合”趋势与各类新媒体的涌现,使得各类跨部门监管难题层出不穷,文化领域内传统分业监管模式就此面临极大的挑战,网络视听领域内的监管难题便是较为典型的例证。张仁汉:《视听新媒体协同监管体系建设研究——以国家文化安全为视角》,《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6期。从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设置规制权限相对独立的监管机構,明确界定独立监管机构的权限权责,是应对新媒体监管难题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譬如联邦通讯委员会(FCC)等独立监管机构体制的优点在于监管权力相对集中,规制措施与行政决策快捷迅速,能够有效防止多个政府监管部门之间权限不清甚至推诿塞责的弊端。有关美国独立监管机构制度的介绍,可见,Marshall Breger,Gary Edles,Independent Agen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Law,Structures,and Poli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我国现有的文化监管机构权限划分模式之下,诸多行政部门之间的监管权限不够明晰,意识形态监管与法律监管往往混为一谈,部门利益分割严重,协作监管能力相对较差,现代化的政府监管工具较为匮乏,导致文化监管事项往往是通过“运动式治理”予以短期遏制,缺乏制度建设长效性,唐贤兴:《中国治理困境下政策工具的选择——对运动式执法的一种解释》,《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2期。因此,需要借助独立监管机构的行政组织法改革进一步予以法治化。
其次,我国现有的文化产业扶植模式需要进一步审视检验。从域外经验来看,韩国、日本等东亚发展型国家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倾向于采用政府财政扶持模式,并在影视、出版、新闻通信等领域出台了精细化的产业扶植振兴立法。而与之相比,美国等西方国家则更侧重于税收减免等隐性财政支出方式,政府并不会过分主导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更为强调市场动力机制。就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而言,正如前文所述,早在2010年财政部就出台过《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管理办法》,通过中央财政与专项基金模式来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并且还出台了大量的税收与金融政策对文化产业予以优惠扶持。但从现有政策效果来看,我国当前各类财政税收优惠政策较为零散不成体系,尚未形成有效的文化产业扶植合力,并且从财政项目制的角度来看,尽管借助财政专项基金的“项目治国”模式逐渐成为主流范式,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但也必须看到项目制模式也有可能导致区域以及行业之间发展不均的弊端。另外,与韩国、日本等国家相比,我国的文化产业促进立法尚处于初始阶段,仅在电影领域有所突破,2016年年底颁布了《电影产业促进法》,在该法中专门设立了电影产业专项基金与税收优惠政策,《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7条:“国家引导相关文化产业专项资金、基金加大对电影产业的投入力度,根据不同阶段和时期电影产业的发展情况,结合财力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综合考虑、统筹安排财政资金对电影产业的支持,并加强对相关资金基金、使用情况的审计”。第38条:“国家实施必要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电影产业发展,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税主管部门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第45条:“国家鼓励社会力量以捐赠、资助等方式支持电影产业发展,并依法给予优惠”。然而,更为统一且深远的“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制定,仍还处于探索立法阶段。就总体而言,我国文化产业立法仍然较为落后,且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需要学习东亚诸国文化振兴模式予以进一步精细化立法。
最后,我国文化法建构与文化监管需要进一步融入国家治理的整合视角。正如前文对于加拿大广播传媒规制的功能分析,加拿大广播传媒规制带有极强的促进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建构目标。这种社会目标不仅仅局限于传媒规制领域,在新闻出版、电影等诸多文化领域均有体现。可以说,文化法的整体框架需要超过传统的产业市场逻辑,进一步引入国家建构与社会整合的宏观思维,尤其对于我国而言,需要借助文化立法来弥补城乡之间、民族之间的文化发展差距,进一步增进国家认同与制度认同,典型的立法代表譬如,2016年通过的《公共服务保障法》中第35条规定:“国家重点增加农村地区图书、报刊、戏曲、电影、广播电视节目、网络信息内容、节庆活动、体育健身活动等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面向农村提供的图书、报刊、电影等公共文化产品应当符合农村特点和需求,提高针对性和时效性”。第46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增加投入,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重点扶助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国家鼓励和支持经济发达地区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援助”。需要指出的是,与文化产业的经济目标不同,文化法的社会整合功能往往难以量化考核,作为一项软指标往往会被“地方发展型”政府所有意忽略,郁建兴、高翔:《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制度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因此,建立一套客观合理的评估体系是实现文化法的社会整合功能的前提保障。
(责任编辑:胡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