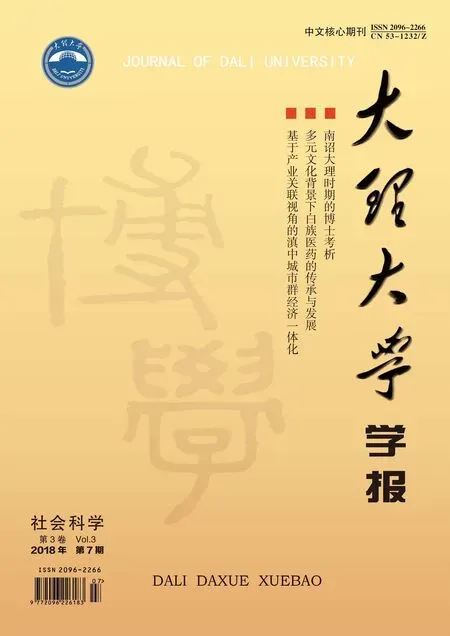南诏大理时期的博士考析
杜成辉
(四川文理学院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四川达州 635000)
在南诏大理时期,也有博士的称谓,见于《僰古通纪浅述》《南诏图传》等典籍和出土文物文献,但对于其性质,尚未见相关研究发表,容易引起误解。在此结合唐宋时期和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对南诏大理时期的博士性质作初步探析。
一、雇匠性质的博士
崇圣寺三塔位于今大理古城西北1.5千米处,中间大塔又名千寻塔,高69.13米,共十六级,为典型的密檐式空心四方形砖塔;南北二小塔均为十级,高42.17米,为八角形密檐式空心砖塔。关于三塔的建筑年代,历来记载不一,但都认为大致建造于唐代,也即南诏时期。南诏时期的“博士”一说,最早见于与三塔建造有关的《僰古通纪浅述》:
(保和)十年癸丑,令博士修崇圣寺三塔。大塔十六层,高一百八十五尺,旁二塔各高一百八十五尺,砌塔博士乃徐正,磉博士史端,木匠娇奴、和苴、李宜。用工力夫役匠七百七十万八千一百四十一工,金银、布帛、绫罗、缎锦,值金四万三千五十四斤。自保和十年兴工,至天启九年七月十五日毕,凡八年。〔1〕66-67
南诏劝丰祐保和十年癸丑当唐文宗太和七年(公元833年),天启九年当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前后应为16年。说明早在劝丰祐保和十年时,南诏已有“博士”之称。磉为柱下的石礅,也即础石,所谓“砌塔博士”“磉博士”应为主持设计和督造的工匠,当是史端主管下部打基础,徐正主管上部砌塔,二人均为雇匠性质的“博士”,应当来自唐朝内地,与木匠娇奴、和苴、李宜等人一起,负责崇圣寺千寻塔的建造。
清蒋旭《蒙化府志》卷一《蒙氏始末附》中也载南诏劝丰佑时:
修崇圣寺,遣博士徐正等更修三塔。费工数百万,三年乃毕。立文苑于峨崀玉局峰,训化士庶,明三纲五常之道。〔2〕
这里的博士,实际上为雇佣的工匠,是古代对茶坊伙计、手工艺者的尊称。王崧《南诏野史》云:
改元天启。开元元年,建大理崇圣寺,基方七里。圣僧李贤者定立三塔,高三十丈,佛一万一千四百,屋八百九十,铜四万五百五十斤,自开元中至是完工,砌(一作匠)人恭韬、徽(义)、徐正(一作立)。立官教二人,张永让,益州人,赵永本,国人。〔3〕132
天启元年当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说明徐正等乃砌匠。本年南诏在玉局山和峨崀设立两座“文学”(国学),以张永让与赵永本为分管玉局山与峨崀文学的教官,并供奉杨波远、杜光迁、杨蛮佑、郑回四人为教主(先圣先贤)〔4〕。唐代中叶,内地已出现将雇匠称为博士的情况。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载:
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怀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请为之。伯熊著黄衫、戴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歠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为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入。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煎茶博士。鸿渐游江介,通狎胜流,及此羞愧,复著《毁茶论》。〔5〕
说明唐代把会煎茶的人也叫做博士,其社会地位不高。再如日本僧人圆仁(793—864)《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载:
开成五年五月十七日,……开堂礼拜大圣文殊菩萨像,容貌颙然,端严无比。骑师子像,满五间殿在,其师子精灵,生骨俨然,有动步之势,口生润气,良久视之,恰似运动矣。老宿云:“初造此菩萨时,作了便裂。六遍捏作,六遍颡裂。其博士惆怅而云:‘吾此一才,天下共知,而皆许孤秀矣。一生来捏作佛像,不曾见裂损之。今时作此像,斋戒至心,尽自工巧之妙,欲使天下人瞻礼,特为发心之境。今既六遍造,六遍皆摧裂,的应不称大圣之心。若实然者,伏愿大圣文殊菩萨为我亲现真容。亲仿与而造。’才发愿了,开眼见文殊菩萨骑金色师子现其人前良久,乘五色云腾空飞去。博士得见真容,欢喜悲泣,方知先所作不是也。便改本样,长短、大小、容貌仿取所现之相。第七遍捏作此像,更不裂损,每事易为,所要者皆应矣。”〔6〕281
这里的博士是对某些多才多艺的老工匠的称呼,犹如今称“师傅”,带有尊重的意味,比如上文中的博士实为泥塑匠。其记会昌元年(公元841年)事有云:“(四月)十三日,唤画工王惠,商量画胎藏帧功钱。”“十五日,……晚间博士王惠来,画帧功钱,同量定了,五十贯钱作五副帧。”〔6〕385说明画工王惠也被称为博士,且受雇者的工钱由商量决定,可证博士在此是雇匠的俗称〔7〕230。
《僰古通纪浅述》又载:
(天启)八年丁卯,唐宣宗立,改元大中。十年己巳,建五华楼,唐博士赵迁都此。〔1〕70
南诏五华楼在今大理城西,三塔之南。南诏天启八年丁卯当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十年当唐宣宗大中三年(公元849年)。“都”可能为“督”之笔误,这里明确指出赵迁为南诏延请的唐朝博士(雇匠),负责督造五华楼。根据《僰古通纪浅述》的记载,南诏在崇圣寺三塔建好后,次年又开始建造五华楼,其建筑工匠为自唐朝内地聘请的“博士”。
五华楼为南诏时期的另一雄伟建筑,高达五层,可容万人。冯甦《滇考》载:
大中十年,于东京建五华楼,以会西南夷十六国大君长。楼方广五里,高百尺,上可容万人。〔8〕
东京当作西京。可见五华楼规模宏大,在南诏大理时期是官方聚会及宴请贵宾的地方。十六国即天竺(今印度),当时南诏以武力使天竺境内各国君长臣服,五华楼主要用来接待各天竺属国君长使者。
在敦煌遗书中,至归义军时期(851—1036),名目繁多的“博士”,频繁出现于寺院经济生活中。《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将“博士”释为“有技艺的人”〔9〕。姜伯勤先生在《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一书中对“都料”与“博士”等雇匠的情况有深入研究,如“泥匠博士”(即泥匠,P.2039背〈a〉,925年)、“上饰埿博士”(即加工窟顶的泥匠,P.2032背,939年)、“泥沙麻博士”(与泥匠或塑匠有关,P.2032背,939年)、“木博士”(即木匠,P.2032背)、“造床博士”(即木匠,同上)、“造火炉博士”(即泥木匠,同上)、“政(正)毂博士”(即木匠,同上)、“造钟楼博士”(即泥匠和木匠,P.2032背《己亥年西仓破》)、“作斗博士”(即木匠,P.2032背《癸卯年正月一日已后直岁沙弥广进面破》)、“疗治釜博士”(补锅匠,P.2032背)、“幹毡博士”(擀毡匠,P.2032背)、“撩(疗)治仏炎(焰)博士”(木匠或画工,P.2032背)、“硙博士”(操作碾磨的劳动者,P.2049背,〈b〉,931年)、“造斋博士”(厨工,P.2032背)等〔7〕230-234。通过与敦煌文书的对照,我们可以知道南诏时期对雇匠的称呼“博士”,也与内地一样。南诏和唐朝关系密切,深受唐文化的影响,在延请唐人主持学校教育和建筑修造的同时,一些唐人使用的称呼也一并传入。
二、学官性质的博士
《南诏图传》为南诏时期美术和文学的代表作之一,由图画卷和文字卷两部分组成。《南诏图传》图画卷在“骠信蒙隆昊”“中兴皇帝”“巍山主、掌内书金券、赞卫、理昌、忍爽臣王奉宗”“信博士、内常侍、酋望、忍爽臣张顺”等礼拜观音图之后,有题记四行,文如下:
巍山主、掌内书金券、赞卫、理昌、忍爽臣王奉宗等申,谨按《巍山起因》、《铁柱》、《西洱河》等记、并《国史》上所载图书,圣教初入邦国之原,谨画图样并载所闻,具列如左。臣奉宗等谨奏。
中兴二年三月十四日,信博士、内常士(侍)、酋望、忍爽臣张顺,巍山主、掌内书金券、赞卫、理昌、忍爽臣王奉宗等谨。
南诏舜化贞中兴二年戊午当唐昭宗光化元年(公元898年),此年王奉宗和张顺等编纂《南诏图传》上奏。《南诏图传》文字卷末书:
赞御臣王奉宗,信博士、内常侍、酋望、忍爽张顺等,谨按《巍山起因》、《铁柱》、《西耳河》等记,而略叙巍山已来胜事。
时中兴二年戊午岁三月十四日谨记。
《南诏图传》的上呈者之一为“信博士、内常侍、酋望、忍爽张顺”,也说明南诏置有博士。此博士与前述雇佣工匠不同,为古代学官名。“信博士”当为儒学博士,为南诏儒教“五学”中教授信学的博士。“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乃中国伦理价值体系中最核心的因素,《南诏图传》文字卷中另有“遵行五常之道,再弘三教之基”“遵行五常”等语,表明南诏也遵行三纲五常的理念。
王崧《南诏野史》载:
蒙舜化(贞)唐昭宗乾宁四年立,年十岁,改元中兴,上书于唐。唐欲以诏答之,王建言,小夷不足辱诏,从之。立五学教主。〔3〕177
据此,则在南诏王舜化贞中兴元年(唐昭宗乾宁四年,公元897年),南诏设立“五学”,由教主主管其事。
《滇云历年传》也载:
光化元年,舜化贞立五学教主。〔10〕
其记南诏设立“五学”的时间为唐昭宗光化元年(舜化贞中兴二年,公元898年),比王崧《南诏野史》的记载晚一年。
胡蔚《南诏野史》载:
舜化贞于“昭宗光化二年,立五学教主”。〔3〕178
据《南诏图传》文字卷,舜化贞改元中兴应在唐昭宗乾宁四年(公元897年),唐昭宗光化二年(公元899年)当舜化贞中兴三年。胡蔚《南诏野史》所载南诏设立“五学”的时间比王崧《南诏野史》的记载晚二年,比《滇云历年传》的记载晚一年。在古史中类似的记载误差比比皆是,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由于从决策到实施有一个过程,一般需要一两年,二是属于史官记载或传抄失误。虽然诸书记述时间略有不同,但我们可以肯定大体在舜化贞中兴二年(公元898年)时,南诏已设立了“五学”。此五学教主,从文学教主的情况看,也当与文化教育有关,说明南诏的学校教育规模继续扩大。
“博士”最早为一种官名,六国时有博士,秦因之,诸子、诗赋、术数、方伎皆立博士。汉文帝置一经博士,武帝时置“五经”博士,职责是教授、课试,或奉使、议政。唐代设置国子、太学、四门等博士,另有太常博士、太医博士、律学博士、书写博士、算学博士等,府学、州学、县学博士之称,均为教授官。“信博士”当为儒学博士,“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孔子提出“仁、义、礼”,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为中国传统伦理价值体系中最核心的因素。此五学当为五所儒教学校,分别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五教)命名,主要研究儒学经典义理,张顺当为信学之博士,也即教官,其性质与汉代的五经博士有类似之处,但也并不相同,五经博士各治一经(《诗》《书》《礼》《易》《春秋》),而五学博士则全面研究儒学经义。
另一证据是,同一时期僧人玄鉴撰有《护国司南抄》,署“内供奉僧、崇圣寺主、义学教主、赐紫沙门玄鉴集”〔11〕,说明当时有义学,玄鉴为义学教主①关于玄鉴撰作《护国司南抄》时间,有唐昭宗乾宁元年甲寅(公元894年)和郑买嗣安国六年(公元908年)两说,多数学者认同后说。。玄鉴既是崇圣寺主,又是义学教主,可能当时义学设于崇圣寺。传统义学有三种含义:一为讲求经义之学。《后汉书·儒林传下·杨仁》云:“宽惠为政,劝课掾史弟子,悉令就学。其有通明经术者,显之右署,或贡之朝,由是义学大兴。”〔12〕二为佛教教义的学说,如般若学、法相学等。《陈书·徐陵传》载:“少而崇信释教,经论多所精解。后主在东宫,令陵讲《大品经》,义学名僧,自远云集,每讲筵商较,四座莫能与抗。”〔13〕佛教义学即名相训义之学、理论之学,又称解学,如俱舍、唯识之学,分析法相之名目与数量,并详细规定修行因果阶位之组织与文字章句之解释,也即有关教义理论的学问。佛教义学通常只是一种学问,并无专设的机构,也无教主之称。三为旧时各地用公款或私资举办的免费学校。《新唐书·王潮传》载:“乃作四门义学,还流亡,定赋敛,遣吏劝农,人皆安之。”〔14〕南诏的义学则不同于以上三种,而是属于官方教育机构,为“五学”之一,主要讲求儒学经义和佛学义理。五学之教主为主管官员,不再是“文学”中的先圣先贤,教主之下,设有博士,担当教授之职。
就现存资料来看,儒教义学在大理国时期仍然存在。大理五华楼新出《故大理路杨氏躬节仁义道济大师墓碑铭并序》载:
公姓杨,讳公。曾祖大师,讳圆慧,建德皇帝尊为师。祖智天大师,讳慧升。从祖戒辩大师,讳慧福。父释号智明,讳升宗。母义学教主赵德馨之长女。公为人温恭直亮,孝娣慈祥,乡里归其仁,朋友交其信,知进退,善始终,自少及老,言未尝诞。每习威仪,勤道业,讽释典,念真孜孜不怠,纯□人也。〔15〕
大理国建德皇帝为段正兴(公元1147年至1171年在位),说明直到大理国末期,儒教之义学仍然存在。杨公虽出身于佛教世家,却为儒雅之士,具有很高的儒学修养,如文中称其“温恭直亮,孝娣慈祥,乡里归其仁,朋友交其信,知进退,善始终,自少及老,言未尝诞”,均符合儒学“五常”理念,这当与其外祖父为义学教主赵德馨有关,说明大理国的学校教育也沿袭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义学”为南诏时期“五学”之“义学”的延续,以教授儒家经典为主,兼及佛、道。
1977年,在千寻塔维修过程中,于塔顶和塔基内清理出南诏大理时期的佛像、写本佛经等文物600余件,为研究南诏大理时期的历史、宗教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978年在崇圣寺千寻塔塔刹基座内发现的金属刻片上有:
明治四年庚子岁六月十三日换,通天人、当寺博士史真、化(在?)智、焉左奴、永富、六斤、智返、惠药师、惠坦八人,记之。
内容为向修葺千寻塔捐资的记录。明治为大理国王段素英(公元985年至1009年在位)的年号,明治四年庚子岁当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说明大理国时也有博士之设。“通天人”当为大理国科举名目。寺院中通常无博士,但南诏大理时期在崇圣寺设有儒教“义学”,这些博士当为在寺院里教授儒学的学者,属于学官。佛教中无“通天人”和“博士”的称谓,这些称谓均来自儒学。“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天”指自然界,“通天”即与自然界相通、相应,天人相应。中国古代哲学中儒、道两家都主张天人相应,天人合一,认为人和自然是一气相通的。庄子最早阐释了这一思想,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将其进一步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思想。南诏时崇圣寺设有儒学义学,大理国时崇圣寺之博士,是否为教授义学的博士,尚难确定,但为儒教“五学”之教官,则可能性比较大。温玉成先生在《〈南诏图传〉文字卷考释》中,认为其“内容是授予八人‘通天人、当寺博士’称号,应是婆罗门教徒所为。‘博士’即‘班的达’之谓也。‘通天人’,沟通梵天者也。佛教中无此称谓,但此件铜板纳入佛塔,可知大理佛寺内亦兼弘婆罗门教”〔16〕。其解释非是。姑且不说大理国时期有无婆罗门教尚难确定,即便是有,其也无如此势力。大理国时期流行儒释道三教,史书中有明确记载,兹不赘述。
〔1〕尤中.僰古通纪浅述校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2〕蒋旭.蒙化府志(卷一)〔Z〕.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翻印,1983:34-35.
〔3〕木芹.南诏野史会证〔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4〕胡玉萍,杜成辉.南诏学校教育考〔J〕.大理学院学报,2009,8(9):20-23.
〔5〕封演.封氏闻见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51-52.
〔6〕释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M〕.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修订校注.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
〔7〕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8〕冯甦.滇考(卷上)〔M〕∕∕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11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24.
〔9〕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43.
〔10〕倪蜕辑.滇云历年传〔M〕.李埏,校点.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154.
〔11〕侯冲.大理国写经研究〔C〕∕∕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报(第四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21.
〔12〕范晔.后汉书(卷79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5:2574.
〔13〕姚思廉.陈书(卷26)〔M〕.北京:中华书局,1972:334.
〔1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492.
〔15〕方龄贵,王云.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10.
〔16〕温玉成.《南诏图传》文字卷考释〔J〕.世界宗教研究,2001(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