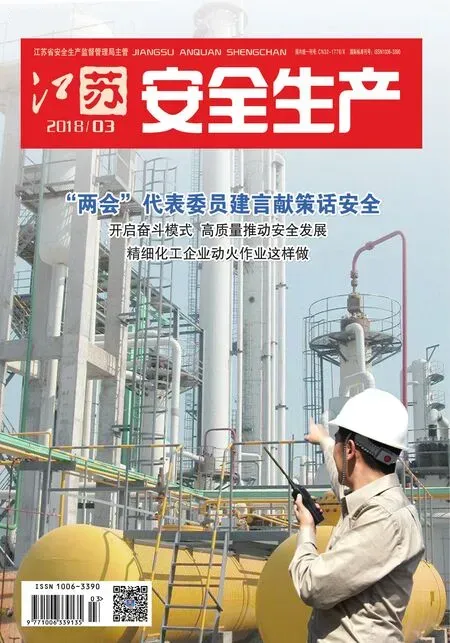特种设备安全事故中责任人年收入该如何计算

2016年12月底,恒飞公司发生一起特种设备作业亡人事故。事故调查组作出的事故调查报告指出:“对事故责任人的认定及处理……李某,恒飞公司总经理,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对公司的安全生产负全面责任,对这起事故负次要责任。”调查过程中,恒飞公司及主要负责人李某未对事故调查报告内容表示异议,恒飞公司依要求提交了当事人李某在事故发生上一年度收入为19万元的收入证明。
有执法人员认为,恒飞公司提供的李某收入证明不能采信,理由是作为大型企业高层领导,李某提供的年收入数据与社会认知相比较明显偏低;作为利害关系人,公司为李某出具的证明可信度和效力较低,应该采用征税、养老金、住房公积金缴纳记录、银行个人账户记录等第三方提供的材料推算李某的上一年度收入,这样更为准确真实。笔者认为,能否采信恒飞公司提供的李某收入证明关键在于对安全生产事故责任人年收入内涵的理解。
一、安全生产事故责任人年收入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安全生产事故责任人年收入顾名思义就是负有安全生产岗位责任的当事人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岗位工作所获得的年收入,即岗位年收入,包括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岗位工作所获得的工资、奖金、补贴、津贴、福利等。而其他收益如当事人的债权、股权、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等收入,利息收入,偶然所得(如彩票中奖)、继承所得、投资所得、不动产租金等,这些收益不该计入安全生产事故责任人的年收入当中。因为他们的取得与当事人履行企业安全生产负责人工作岗位职责并无关联。
当事人在从事安全生产工作所获得年收入中已被税务机关征缴的税收也应该从年收入中剔除,否则可能重复计算当事人年收入;当事人获得的奖金如果是与其履行企业安全生产负责人工作职责直接相关,如因获得安全生产先进个人、先进集体等荣誉而发放的奖金,都与其履行企业安全生产负责人工作职责直接相关,但假如这些奖金与其履行企业安全生产负责人工作职责并无直接关系,不宜计入当事人年收入;另外当事人通过加班获得的加班工资是否应该计入当事人年收入?笔者认为,当事人加班也是在履行企业安全生产负责人工作岗位职责,这些收入也是当事人在履行企业安全生产负责人工作岗位职责过程中获得,也应该计入当事人年收入。
二、安全生产事故责任人年收入的确定有无法定标准和统一规定?
《安全生产法》《特种设备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均对安全生产事故责任人的担责方式作出“年收入”一定比例的罚款,却并未对年收入组成部分及计算标准作出统一规定。
笔者认为,当事人未能依法履职尽责造成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发生,当然需要追究其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但“过罚相当”“处罚法定”的行政处罚原则意味着当事人只需承担有限责任而非无限责任,且当事人受到的处罚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不能由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自由演绎和推论。执法者既要保证严格执法,让违法者付出成本和代价,彰显法律的尊严,同时也要承认、尊重和保护违法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当事人年收入确切含义及计算标准的情况下,当事人有权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理解方式和计算标准,笔者认为这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不违反法律。
三、第三方提供的年收入证明一定更准确?
与恒飞公司相比,税务机关、社保、银行等第三方与当事人没有利益关系,其提供的资料对于计算当事人的年收入是否更为准确和真实呢?笔者认为未必。
税务机关的征税记录是对当事人所有合法收入进行征收的,无需对当事人的收入进行“岗位收入”和“其他收入”分类征收,所以单从税务机关的征税记录中无法推算当事人的年收入。人社局的养老金缴纳记录和住建局的住房公积金缴纳记录都是根据个人工资基数进行计算的,也不能反映当事人获得的奖金、福利等其他岗位收入。银行的个人账户记录也存在类似情况,推算出来的当事人收入情况也与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要求存在较大距离。
当事人所在单位作为法人机构,依法具有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资格和能力,必须为自己所出具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假如其提供的当事人收入证明是虚假的,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制裁。任何证据都没有绝对的效力,每一件具体的案件都有较适宜的证据,就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而言,恒飞公司提供的证明材料是本案较为理想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