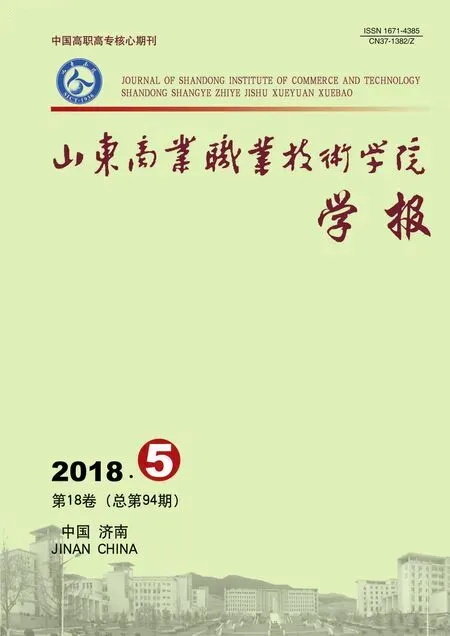强势文化中的寻根
——《沉沦》与《芝加哥之死》解析比较
付元红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3)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陆和台湾的很多作家无论在创作风格上还是在文化心理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相似性,表现出在共同的民族心理积淀之下的一脉相承性。郁达夫和白先勇虽然分属浪漫抒情派作家和现代派作家,在地域上又分别居住在大陆和台湾,但在《沉沦》和《芝加哥之死》的写作中却体现出了惊人的相似。他们在其写作中,凭借特定的历史语境,分别对留学生在东方(日本)和西方(美国)的强势文化面前所经历的痛苦的心理裂变进行了具象的描绘,对其中的“他”和吴汉魂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进行了共同的确认,从而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中,进行了两次前后相续的、强势文化中的寻根。
一、强势文化面前的悲哀
在《沉沦》中,主人公“他”作为一名留学生,在日本的强势东方文化之下,经历了极大的心灵的痛楚。作为一名日本人眼中的支那人,主人公无疑是一个低等人,作为一名“中国人”的清醒认知时时刻刻在提醒着他进行一种“身份自觉”,在心理上自觉地和外界进行疏远,人为地造成了自己的孤独。所以在文章的开头作者就写到:“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作者继续写到:
他的同学日本人在那里欢笑的时候,他总疑他们是在那里笑他,他就一霎时的红起脸来。他们在那里谈天的时候,若有偶然看他一眼的人,他又忽然红起脸来,以为他们是在那里讲他。他同他同学之间的距离,一天一天的远背起来,他的同学都以为他是爱孤独的人,所以谁也不敢来近他的身。
在这里,身份的自觉促使了这种“恶性循环”式的孤独。我们可以说,这是作为一个战败国的国民的自卑,但文中的“他”作为一名留学生,也可以说是在一种强势文化面前的自卑。而在《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也面临着同样的境地。白先勇写到:“吴汉魂觉得坐在椅垫磨得发亮的沙发里,十分别扭,十分不习惯。打字机上那几行字又象咒符似的跳入了他的眼帘:‘吴汉魂,中国人,三十二岁’。”在这里,吴汉魂在自己的简历上把“中国人”写在前面,一方面是中国人身份的自觉,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在美国强势文化面前的身份敏感,其自卑之心是隐含于其中的,他后来到酒吧的放纵正是心灵长期受到压抑的结果。
在文艺学中,“世界-作者-作品-读者”是文艺完成的一个流程。我们先抛开读者这个因素,可以看出,世界、作者与作品这三者的关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世界是作者创作的源泉,作品是世界在作者心灵中折射的结果。故而,在很多情况下,作品中的主人公经常会成为作者的代言人。在这里,《沉沦》中的“他”与《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正是郁达夫和白先勇的心灵代言人。“郁达夫等创造社抒情小说家,多以自叙传的形式抒写青年知识者生的烦恼、性的苦闷,非常直露地展示自己内心的隐秘,抒发自己的情感。”[1]《沉沦》的主人公就成为了郁达夫抒写自己苦闷的自叙者。而白先勇在写作《芝加哥之死》时亦是“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生动叙述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学子在陌生的美国丢失了心魂,无可依托而终至毁灭的悲剧。谁也无法否认,白先勇和他笔下的人物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他们的感受、他们的心情是相通的,而他们的灵魂也是一样的深负重荷。”[2]为什么这两部作品中主人公的情感经历及所作所为会明显相似呢?我们可以从作者身上来寻根探源。
郁达夫出生于一个闭塞偏远的小县城的书香世家,但其三岁丧父,母亲整天忙里忙外,所以童年的郁达夫更多的是浓郁的寂寞。在其孤独的童年生活中唯一相随的是女仆翠花。童年孤寂的生活造成了郁达夫的性格特征:自卑、胆怯、害羞、敏感,他常把孤独和柔弱挂在嘴上,写在脸上,形成了他的自恋倾向。后来郁达夫随其兄到日本留学。鉴于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地位关系,当时的中国学生在日本是受到歧视的,加上他童年经历的阴影,其多愁善感的性情便紧紧伴随着他。所以《沉沦》主人公的性格和人生经历几乎就是郁达夫的照搬。白先勇虽出身豪门,但七八岁的他却患上了二期肺病,被窗外的热闹世界隔离在了一间小屋中。一直到十二岁病愈,这段时间里,陪伴他的只有他家的绍兴厨子以及薛丁山的故事。病愈后他虽重返学校,但长期与世隔离的他变得孤独、敏感而好强,从《寂寞的十七岁》中我们亦可窥见端倪。1963年他得到全额奖学金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创作班学习。母亲的病逝给了他很大的打击,加之初涉异国他乡,所以他在《漠然回首》中写到:漠然回首,我感到脱胎换骨,骤然间,心里增添了许多岁月。黄庭坚的词:“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不必十年,一年已足,尤其是在芝加哥那种地方。所以,白先勇便把他此时的所思所感以及情感的波动倾泻在了吴汉魂的身上,作者和文本主人公便有了极大的重合。郁达夫和白先勇的人生经历和情感历程有着极大的相似,他们都有童年的孤独,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并且他们在经历这些事件时的年龄都十分相似。这两部“留学生文学”,可以说是两位作者极为相近的外部创作世界在作者身上折射出的相近的心灵外现。当然,两个文本中主人公的性格、心理等在细微层面上还是有区别的。《沉沦》中的“他”时处中国“五四”时期,所以出身于弱势文化的中国的“他”到日本后虽是埋头苦读,但在心理上自觉地保持了与当地强势文化的疏离。主人公的忧郁多感的性格,是五四知识分子感到的外部压力后的结果,也是他们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进行省视的结果。“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得的这种孤独,倒比一个人在清冷的地方感得的那种孤独还更难受。”主人公的这种忧郁与孤独不仅源于他的敏感,更源于他的那种无法被外部世界认同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则时处20世纪60年代,他是从台湾到美国去的一个留学生。在美国的物质世界中,主人公的自我身份曾经出现了迷失,他的名字吴汉魂可以隐喻“无汉魂”,他到美国后曾极力向美国的强势文化靠拢,力图在这个世界中有立足之地,学位与职位是他苦行僧生活的终极目的。所以,他在强势文化中的扩张投射与身份迷失是同步的。当他从这种虚幻中清醒过来后,才发现他在异国的一切努力换取的仅仅是一种向往的破灭,才发现他自身在母体文化和异域文化之间的两难处境,母亲的叮咛“你一定要回来”才又一次回荡在他的耳畔。“吴汉魂既不能也不具备条件向西方文化进行全身心的倾注,同时他也在向传统文化远离告别时依然牵挂着种种难以忘怀的恋恋不舍。”[3]
二、寻根——中国意识的共存
我们可以把这两篇作品称之为“寻根”文学,但由于文学是特定地区、特定时代、特定环境的产物,所以我们在这里谈的寻根和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一文中所倡导的寻根文学并不等同。简而言之,这里所说的寻根是指在外国的强势文化面前中国的留学生在国外对自己“中国人”身份的一种确立,这与韩少功所说的“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不茂”并不具有相同的涵义。
按这两部作品所产生的时间来看,历史的车轮已向前滚动了40多年,但在他们中间却都涌动着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外寻根的苦痛。在《沉沦》自序中作者写到:
《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三篇小说,都是以留日学生的生活为题材,“带叙著现代人的苦闷。”那里面有作者的影子在内。[4]
作为“五四”时期的爱国青年,郁达夫在日本的求学生活是苦闷的,也可以说是“带叙著现代人的苦闷”。在对《沉沦》进行分析时,经常提到里面所表现出的三种苦闷:生的苦闷、爱的苦闷、性的苦闷,这几种苦闷无论在作者身上还是在文本主人公身上都是共存的。其中,生的苦闷是主要方面,爱的苦闷和性的苦闷只不过是生的苦闷的发泄口。当然,这里面既有爱国的情绪,也有情欲的苦闷,二者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情欲苦闷中深切感受到弱国子民的屈辱,也可以说主人公在感受到弱国子民的屈辱后从情欲中寻找麻醉。这个孤僻自卑的青年,在对自己身份的寻根中,确立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他深感沉重的民族压迫,深感离开人群的凄冷,他才迫切的需要爱情,他在日记中写道:“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正因如此,他才会有“在被窝里犯的罪恶”,才会偷看别人洗澡,偷听别人幽会,才会走向妓院的大门,最终走向道德的堕落。远离祖国,身处异邦,主人公深深感到,他像一个失去双亲的孤儿,寻根的意识更加清醒。作品末尾,当主人公选择大海作为自己的归宿时,他喊出了埋藏于心底的声音: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这里,“与其说是一个孤僻自卑者的性格悲剧,倒不如说是一个社会悲剧——由于国家衰弱和民族歧视而造成的悲剧。”[5]在自己的身份自知中,主人公终于投身大海,来完成向祖国的最后的寻根。
白先勇在台湾时就与大陆相隔绝,到了美国后更是与祖国相隔遥远,他在谈创作《漠然回首》时说:“去国日久,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乡愁日深,于是便开始了《纽约客》,以及稍后的《台北人》。”《芝加哥之死》就是《纽约客》的第一篇。由于中国人在美国的社会地位、衣食住行、婚姻爱情等方面都与西方文化产生严重冲突,从而使他们常常产生孤独、空虚、绝望等情绪,白先勇便将自己这种“无根”的痛苦、断奶的痛楚通过吴汉魂这一形象展示出来。於梨华借牟天磊之口喊出了“我们是无根的一代”,吴汉魂亦是其中的代表。他怀着对西方文化的渴求来到美国,为了得到学位和职位,他牺牲了爱情,违背了中国“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蛰居在一间简陋的地下室里,每天要为洗衣店送衣服,为饭店洗碟子,来赚取学费。但当他拿到文凭后,才突然感到自己的空虚,感到这些年来向西方文化做出的靠拢终究没能达到最终的目的。他在自己的简历中首先写到的是:“吴汉魂,中国人……”,在萝娜叫他“Tokyo”时,他说:“我是中国人。”由此看来,在他内心深处,他仍是以中国人的身份来看待自己,中国意识仍牢牢地存在于他的大脑中。“吴汉魂内心深处的一切痛苦和矛盾的根本核心即是源自他的这一身份定位。”[6]在他接到母亲去世的电报时所诵读的《荒原》的诗句:
四月是最残酷的季节,
使死寂的土原爆放出丁香,
参杂着记忆与欲念,
以春鱼撩拨那委顿的树根。
冬天替我们保温,
把大地盖上一层忘忧的白雪——
可以看作西方文化的象征,虽然在西方的大地上有一层“忘忧的白雪”,但难以掩盖它那“荒原”的本质。此时他拿《荒原》来诵读,表明了他内心当中对西方文化的某种规避。而文中母亲的形象则是具有多重含义的,一是指血缘上的母亲,二是指祖国母亲,也代表着吴汉魂内心的母体文化——汉文化。他对萝娜的真面目的认知,代表着他对西方文化本质的认清。当他受到萝娜的勾引后投湖自尽,则与《沉沦》的主人公投海自杀具有相同的意义,均以自己的死来向祖国进行着最后的寻根,走向他那梦中一直召唤他的“母亲”。
郁达夫和白先勇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化作为他们的母体文化已经在他们的内心扎根。郁达夫自小就能吟诗作对,擅辞赋,而白先勇则从小对古典小说充满了兴趣,他对《红楼梦》的点评更有其独到见解。中国古典文学对他们的影响亦能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中。在《沉沦》中远在异邦的“他”作一七律来表达对故国的思恋:
蛾眉月上柳梢初,又向天涯别故居。
四壁旗亭争赌酒,六街灯火远随车。
乱离年少无多泪,行李家贫只旧书。
夜后芦根秋水长,凭君南浦觅双鱼。
在《芝加哥之死》中,作者让吴汉魂读《荒原》来疏离西方文化,并通过“母亲”形象来完成他对中国母体文化的追随。
三、以景衬情与“性”在寻根文本中的运用
在《沉沦》和《芝加哥之死》两部文本中,运用了大量的景物描写、心理描写,均使用了象征与暗喻的手法,并且都触及到了“性”的问题。在此,主要就景物描绘和性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来解读它们在主人公寻根历程中的作用。
我们常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这种古典文学中的常用技法在郁达夫和白先勇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运用。身为浪漫抒情派的郁达夫,在《沉沦》中运用了大量的景物描写。他以文本中主人公的主观印象为媒介去表现自然景物。以此来渲染气氛,表现情感,借此来展示主人公的情绪、想法,突出其个性。如作者写到:
呆呆的看了好久,他忽然觉得背上有一阵紫色的气息吹来,息索的一响,道旁的一枝小草竟把他的梦境打破了。他回转头来一看,那枝小草还是颠摇不已,一阵带着紫罗兰气息的和风,温微微的喷到他那苍白的脸上来。在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里,在这澄清透明的以太(ETHER)中,他的身体觉得同陶醉似的酥软起来。……
这段温柔境界的描写,展现了主人公在异国他乡渴望得到一种平静的生活,展示了主人公的柔弱与孤独。而“他”到N市后所看到的景物:“远远里有一点灯火,明灭无常,森然有些鬼气。……窗外有几株梧桐,微风动叶,咄咄的响得不已。”则形象地展示出主人公此时在异国的孤单,暗含着对家国的悲思。主人公在经历了道德的沉沦后,他看到“远岸的渔灯,同鬼火似的在那里招引他。细浪中间,映着了银色的月光,好像是山鬼的眼波。”这里展现出孤单的主人公在强大的异域文化中堕落后的苦痛,后来他看到“那灯台的光,一霎变了红一霎变了绿的在那里尽他的本职。那绿的光折射到海面上的时候,海面就现出一条淡青的路来”,这段描写则是客观景物和主观心理的合一,暗示了主人公以投海自杀来洗刷自己堕落的寻根之路,具有象征的意味。
在《芝加哥之死》中也有大段的景物描写,如吴汉魂从萝娜那里出来走到大街上时,白先勇写到:“吴汉魂站在街心中往两头望去,碧荧的灯火,一朵朵象鬼火似的,四处飘散。幽黑的高楼,重重叠叠,矗立四周,如同古墓中逃脱的巨灵。……吴汉魂走到了灯塔下面,塔顶吐出一团团的蓝光,投射到无底无垠的密歇根湖中。”这段景物描写出自现代派作家白先勇之手,极富象征意味,并且和《沉沦》中的主人公自杀时所运用的景物描写有着惊人相似,都用了关于鬼火的隐喻,都用了冷色调。这段描写展示出,经历了6年拼搏与6年迷失之后吴汉魂所真正认识到的芝加哥的形象。这时,他才明白他与西方社会的无缘,明白了他在这个强势文化面前的孤单与无助。在经历了狂欢之后的冷静审视之后,他终于迈入了密歇根湖中,来与这个西方世界作一个彻底的诀别。
现实生活中,郁达夫对女性采取泛爱的态度,而白先勇则有同性恋的倾向。可以说,在性的问题上,二者是迥然不同的。但在《沉沦》和《芝加哥之死》两个文本中,两位主人公在“爱与性”两个方面的经历却是相似的。究其原因,性在这里并不等于赤裸裸的肉欲,而是具有超现实的象征意义。它是主人公在异域长期受到压抑后,在那个文化圈中的一次堕落,但又是对那个文化圈的一次反抗,是主人公对他所生存的那个世界的最后一击,并促成了两位主人公在文化寻根之后的投水自杀。他们都在异国压抑了自己的爱情,压抑了自己性的欲望。虽然这是一个正常人的基本生理需求,但在异域的强势文化面前却无法得到正当宣泄,从而导致了他们人格的畸变。故而,《沉沦》的主人公由自慰、偷窥到步入妓院,完成了他道德上的堕落;吴汉魂也在地下室中对外面女人的腿子感到躁动,最终在萝娜的引诱下堕落。这是堕落,也是反抗。他们都在最后得到了人的基本需求——性的满足,来反击了压抑他们的异国文化,但在道德上却又违背了自己的母体文化。所以,他们都选择了死亡,以死来响应母体文化在冥冥之中对他们的召唤,“隐喻着主人公产生了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7]
四、结语
时隔约半个世纪,横跨海峡两岸,郁达夫和白先勇分别对中国知识分子在日本和美国的强势文化面前所受到的压抑与迷失、对他们对母体文化的中国寻根作出了自己独到的剖析。由于他们所处的外部世界境况的相似以及他们人生经历和身份的相近,他们才跨越了时空的限制,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留下了这相似而又惊人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