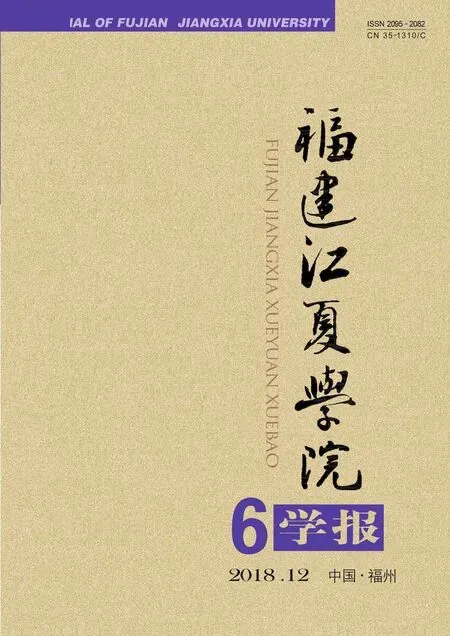戏曲表演中“做”与“唱”的相互关系
刘雪颖
(闽江学院蔡继琨音乐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在作为歌舞剧的戏曲的范畴里,“做”必须和“唱”密切相结合,形成完整统一的有机体,才能充分发挥艺术的效能。梅兰芳认为:“昆曲细致繁重的身段,都安排在唱词里面,唱词的意思就要用动作来告诉观众。讲到‘歌舞合一、唱做并重’昆曲是可以当之无愧的。”[1]313从其观点可以看出,戏曲“做”“唱”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缺一不可,只有“做”“唱”紧密配合,才能更好的表现戏曲所要展示的内容。
一、烘托关系
“做”与“唱”,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烘托映衬。如高登的抖扇,是在显示他的狂傲凶戾;项羽的颤帖一怒,是在倾泻他的愤懑激情;赵云的抓帔,是在呈现他的救主之诚;黄天霸的摊袖,是在展现他的意外之惊。“观众看到的并不是戏曲演员在舞台上运用内功,而是各个剧中人物在完成他们应当表现的舞台行动线”[2]。
(一)情景烘托
根据唱词进行准确的表演,以更好地表现舞台情景,通过手、眼、身、步等各种艺术手段,将规定情景中的人物内在活动表现出来,就是情景烘托。
例如,《贵妃醉酒》中杨玉环唱“玉石桥斜倚把栏杆靠”这一句时的“做”的身段:当唱“玉石桥斜倚”时,走到上场门台口,旋转身躯面向台左,微蹲腿,左手拎裙子的中幅,右手扶桥栏杆,做准备“上桥”的姿势;在“杆”字唱腔里用小碎步往桥上走,欲高先低,即先蹲下身,再逐步长身,来模拟踏着石级走上桥顶。这种“做”“唱”更细致地将杨贵妃的身份、从容不迫的仪态、气度烘托出来。如果只唱不演,观众就无法感受到这么直观的舞台效果。
还有《凤还巢》中的三次偷窥。程雪娥上来唱到:“堂前遵父命,屏后看才郎。”她是奉命而来,心里很坦然,然而走的脚步却小心翼翼。因为这是第一次经历此事,所以她的步法中带有害羞的状态。第一次“偷觑”,眼皮微微的向上一挑,展示出她眼前一亮,接着唱:“看这位公子”,说明头一眼就留下好印象。第二次“偷觑”就是认真地看了,“偷觑”的眼神是实的,看清楚后她满脸笑吟吟地唱:“爹爹好眼力”。第三次“偷觑”则是欲前又止。正是“做”“唱”的协调一致和互相烘托,才使得这些表演格外赏心悦目,不需要过多的解释,情景就能浮现在眼前。
(二)情绪烘托
这类“做”“唱”关系中,动作和生活原型通常有一定距离,有的在从生活进入戏曲舞台的过程中,变形程度很大,不加解释很难看懂。然而,此类表演可塑性大,常常借助扇子、水袖、髯口、手绢、翎子、马鞭、长绸、头发等道具。通过演员的形体活动,把它和前后情节结合起来,让观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如水袖中的“旋袖”,可以成为欢乐的表现,也可以反映出悲哀的情绪。《挂画》中的叶含嫣,喜悦的水袖,当听到迎亲的锣鼓声时,边唱边旋转着水袖,忙着换嫁衣,表现妙龄姑娘得到如意伴侣,要做新娘子的喜悦心情。而同样的“旋袖”动作,用在《打神告庙》中桂英的身上,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变成用旋转的水袖发泄心中的悲情。
《红娘》中有一段精彩的表演【叫张生】。这段表演中,“做”“唱”配合十分有看点。其中,棋盘和水袖随着优美的唱词,翻飞起舞。形似荷叶状的水袖技法,让人赏心悦目,把红娘活泼、机敏、善良、正直的性格出神入化地揉进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舞蹈之中。
在《窦娥冤》中,窦娥辞别乡邻后,为了见到婆婆,匆忙的往公堂上赶。一路上,她边唱“辞别了众高邻”,边做身段。先出左手,上左脚,再出右手,紧接着一个巧妙的转身,把右手水袖直线扔出,曲线收回后,“左臂耍大刀花,急急下场”[3]。此处的水袖配合唱词,烘托感情,水袖的运用一定要起到烘托人物内心的作用。这样一个“做”“唱”的组合,甩袖动作衔接十分紧凑,表现出了窦娥焦急紧迫的情绪。
以上所列举的“做”“唱”,显然都来源于生活,但又都进行了艺术加工。角色的身份、环境、事件都不相同,通过“做”与“唱”的结合,表现在舞台上,各有千秋,产生不同的艺术魅力。这些都是“做”“唱”相结合的典范,可以看出“做”“唱”之间,烘托关系的重要性。
二、呼应关系
“做”,指通过面部表情以及形体动作来刻画人物的心理、性格,揭示戏剧冲突与剧情发展。“唱”,指唱腔,通过唱词来展现角色的形象、性格,叙述故事情节。“做”“唱”之间,用表演来呼应唱腔,用唱腔来配合动作,相辅相成。
(一)人物呼应
“昆曲的身段,是用它来解释唱词”[1]324。戏曲中的“做”“唱”,始终贯穿于其表演体系中。如昆曲经典剧目《牡丹亭》中的“游园”,就是“做”“唱”呼应关系的典范。这一出戏,用典雅恬静的“做”“唱”,边唱边舞,将渴望自由平等、渴望幸福爱情的少女的心思描绘得淋漓尽致。“游园”中,杜丽娘和侍女春香在整个表演过程中,十分注重“做”“唱”之间的关系。表演的距离、动作的先后、位置的高低等,都明确了主仆二人的身份,做到了人物呼应。如在【好姐姐】曲牌里,“啼红了杜鹃”这一句的身段中,可以通过扇子的表演看出“做”功的精致:杜丽娘左手轻轻捏住右边袖子的一角,左脚向前半步,右脚跟在后面,上半身微微向左倾斜,左肩膀指向左上角,右手倒提着扇子,逆时针画小圈子,扇子是由内向外画了个圆。此处的“做”“唱”,柔和而轻松,有着无限的诗意。“声声燕语……呖呖莺声”的身段,是要把扇子打开,“并肩和侍女春香走云步”[1]160-161。杜丽娘和侍女春香两人,在花园里的动作、走位和身段,有分有合,有高有低,有点有线,都是呼应对照的形式。他们的距离时远时近,时分时合,有时并肩,有时斜对,做得自然、大方、圆滑、紧密。[1]168这些边唱边做的表演,实际上就是在呼应着唱词和剧情。
再如《坐楼杀惜》中,阎惜姣唱的【望家乡】。“不怨宋江心肠狠”时,起小“站步”(即起脚的时候低一点儿),走“赶步”,追着张文远,两手舞着绸带。张文远则半蹲着,头向前向后一晃一晃地摇动,绕着桌子逃,一面绕桌子转,一面自己还要翻身转。就这样,两人绕着桌子转一圈,回到原位置时,阎惜姣唱第二句“都只为私通与你他才绝情”时改走“碎步”,手里耍绸带,并用绸带去掸他。张文远这时也改用耍甩发逃走,两人还是绕着桌子转。阎惜姣接唱第三句“不想你今日多薄情”,唱到“多薄情”三个字的时候,从下场门口走到台中心,用手里的长绸带“抽”张文远。唱“多”字时,用左手掸,唱“薄”字时,用右手掸,唱“情”字时,用双手“抽”。随着她的“抽”,张文远一个“抢背”,爬起来在地上跪着。阎惜姣一边唱一边走“碎步”追赶,手里还是舞着绸带。等到阎惜姣走到右边台口,张文远在下场门口时,阎惜姣赶上去,两人“漫头”,对换位置,然后再归台中。阎惜姣用绸带套住张文远的脖子,接唱最后一句“不捉你来捉何人”。在唱的时候,阎惜姣用绸带拉着张文远前后摆动,张文远跟着摇摇晃晃地前后走动。到唱完末一句,张文远归至舞台中心,阎惜姣稍偏舞台左侧。“张文远脸朝向外,阎惜姣斜对他,用手收紧绸带,张文远就慢慢地用‘软缰尸’摔倒在地上”[4]。
(二)情节呼应
这类“做”“唱”关系,通常由生活琐事,如开关门、上下楼、骑马、坐轿、行船、狩猎、穿针引线、织布穿梭、采桑挖菜、喂养家禽等提炼而来,经过艺术加工后再现于戏曲舞台。这种身段表演直接反映生活状态,表演动作和真实生活距离很近,像与不像的尺度较严格,因此观众很容易理解动作所表现的含义。这部分身段表演动作,重点要求的是动作的准确性和表演的真实感,以求更好的“做”“唱”配合效果。
在《贩马记》的“哭监”一折,很好地体现了“做”“唱”关系对剧情的呼应。“哭监”中,李桂枝在监中受责哭诉,边唱【二黄】边表演,运用她的眉、眼、唇、急促的气息等,表达人物焦灼、急切、愤懑的情绪。唱到“拷打春华”时站起来,扬左手做打状。唱到“悬梁自尽”时双手在颈旁做出悬梁的样子。唱到“落下尸灵”时,走到合中,双手先向里斜举,作落尸的样子,然后蹲身翻袖,表示放在地下。唱到“我继母败人伦”时,双手在脸前比划一下。这些“做”“唱”的配合,恰恰都是为情节做的呼应。
再如《宇宙锋》中,哑奴的作用。装疯是哑奴最初给赵女的提示。装疯有两次,一次是在【反二黄】中“摇摇摆,摆摆摇,扭捏间”之前,赵女不等哑奴提示,就已经明白要做些什么,只用一个娇痴的抖袖,就带过去了这一次的指导。还有一次是在【反二黄】中“随儿到红罗帐”之前,“是用极端痛苦的心情,水袖两拂把哑奴还不曾比划出来的手势压回去了的”[5]。“哑奴在演出中的任务就是要把赵女在装疯卖傻之余真实痛苦的面目显露出来,她是把赵女的满腔悲愤传达给观众的一个媒介”[1]151。这就是“做”“唱”关系中的一种舞台上的情节呼应。
三、补充关系
“做”和“唱”,都是塑造人物的主要艺术手段,为塑造人物服务,不仅是戏曲“四功”中重要的表演手段,也是戏曲表演艺术的表现形式。狭义上讲,两者似乎是互不干扰。广义上讲,两者又是相辅相成。戏曲“手、眼、身、法、步”五种基本表现技法,以及韵律化、舞蹈化的表演形式,都体现出“做”和“唱”之间互为补充的关系,具体可分为性格补充和剧情补充。
(一)性格补充
戏曲表演,离不开舞蹈和歌唱。戏曲演员不但要唱得好听,舞得优美,而且要善于运用舞蹈和歌唱来表现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刻画人物性格和塑造人物形象,对人物性格进行补充。
《吕蒙正赶斋》中,当吕蒙正从窑门跨步而出的时候,外面是漫天大雪。吕蒙正腰背踌躇,他一边用手遮着脸,一边缩着脖子,两眼发直,即使脸上是悲苦的表情,也仍然可以找到读书人的斯文。下面两句唱的是“吕蒙正出窑来风雪挡道,老天爷杀穷人不用钢刀”,这时北风怒号雪花纷飞。在唱“风”字之前,他先斜拂水袖,用来表现单薄的衣衫被寒冷的北风吹动。紧接着,屋檐上落下一个冰凌子,正落在他的衣领内,“一股冷气直透他的脊背,他不禁把头一缩,唱出了‘雪’字”[6]。此时表情要苦中有乐,先是挂着悲惨的苦相,然后在愁苦中慢慢地透出一丝无可奈何的笑意来。这样比一味哭哭啼啼的表演要更深一层,更能表现吕蒙正这样的人物性格。
《单刀会》的【二黄】中,有“上船来只觉得神清气爽,坐舟中丹凤眼细观端详。(夹白)大舟船——大舟船干百只依靠岸上(夹白)小舟船——小舟船密匝匝好似蜂房。江风起淡云消天晴日朗,对岸上东吴将站立两厢。”关羽去赴宴,既抱有大无畏的精神,又有充分的布置。在此前提下,观望下江景也是完全可能的。这段表演中,主要通过一些动作来表现关羽在观江景时的神情,如唱第一句“上船来只觉得神清气爽”,关羽右手捋胡子,左手抓蟒袖,撑于腿上。周仓趁势以刀头挑船舱门帘,再回过头去,左手向右推托,出去,表示透过舱门看江水,接唱“舟船”。场面起【搓锤】,周仓见水,很活跃,走龙形,理耳毛子。走到台口,出大刀,转到关羽右边,左手掸扎,右手抱刀,与关羽同向左边观看,右手举刀与关羽配合着做身段。关羽从正面坐舟中丹凤眼细观端详,接唱“大舟船千百只依靠岸上”。这时周仓又走龙形,理耳毛子,走到台口,出大刀,回到关羽左边,右手掸扎,左手抱刀,与关羽同向右边观看,亮住。关羽唱“小舟船密匝匝好似蜂房”。在这几句唱词里只见周仓在舱内走来走去,关羽没有什么动作,只是向前、左、右三个方向注目观看,至多推一下、捋一下髯口。然而,正是要这样表演才合乎关羽的身份。关羽这时已是五十开外,又身为统帅,不能像青年人一样晃荡。这段“做”“唱”将关羽的情绪补充的很到位。
(二)剧情补充
戏曲中的“做”和“唱”,要求演员的表演既要遵循程式化的手法,又要符合戏曲美学的规律;既要“做”“唱”合情合理,又要配合情节发展;既要视觉上美观耐看,又要经得起仔细推敲。因此,只有让一动一静,一言一笑,手、眼、身、法、步,都具有丰富的内涵,贴合人物的思想感情,才能在各个不同的剧目中创造出各具特色、真实、生动、优美的艺术形象,对剧情进行恰到好处的补充。[7]
《霸王别姬》中,项羽抱着马头的两句唱词“莫非是你看到大势去矣,故而你在槽下叹息长嘶”,更加渲染了悲剧气氛。虞姬也更加难受,赶紧以斗篷挡面,示意太监快把马牵走。项羽唱完后也不忍再看宝马,只是用右手轻推马鞍,意思是你去吧!这一推除了表达项羽对宝马的深厚情谊和忍痛割爱的悲痛心情,也提前暗示了项羽大势已去的剧情。
《洪洋洞》中杨六郎临死的那个身段,先把身子往下蹲,两腿作“罗拳腿”状,两手撑着膝盖。“去见先人”的“人”字,是个长腔,他随着唱腔又把身子慢慢往上长,长到两腿都伸直了,再把脚跟提起,脚尖着地,脖子再住上挺,显得人比平时高。“同时嗓门愈唱愈低,唱成一线游丝好像只剩了一口气才倒下去的”[1]427。这样演绎一个临死的病人的形状,应该说是刻画到位了。
四、结语
我国戏曲综合了“唱”“念”“做”“打”等一系列表演形式,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戏曲表演的独特性在于,在有限的舞台上创造出众多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与戏剧情节。因此,“这种创造需要通过唱腔与手、眼、身、法、步等多种艺术手段相结合的形式来塑造人物性格、揭示剧情发展”[8]。戏曲表演,离不开舞蹈和歌唱。戏曲演员不但要唱得好听,舞得优美,还要“善于运用舞蹈和歌唱来表现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刻画人物性格和塑造人物形象”[9]。只有“做”“唱”密切结合,“表现才有生命和感染力,描写手段才会丰富,从而塑造出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