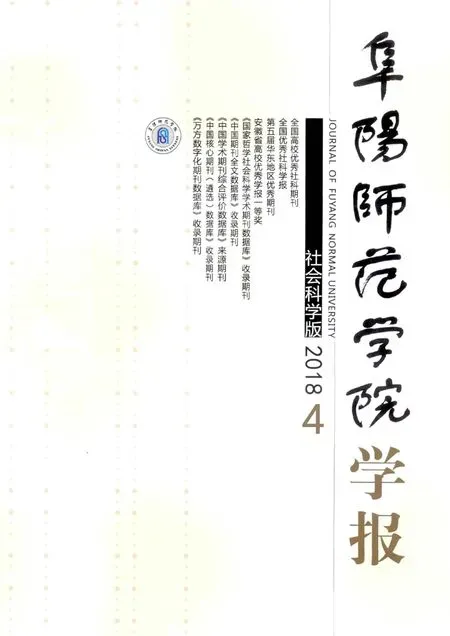论吴淇对《文选》中拟诗的认识
张明华
论吴淇对《文选》中拟诗的认识
张明华
(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对于《文选》中的63首拟诗,清代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中有具体而深入的论述。拟诗所模拟的“原诗”,或者原为某一首诗,或者原为某一组诗,或者原来根本无具体模拟对象。对此问题,吴淇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就模拟方法而言,吴淇总结出模拟字句、模拟格调以及备人与备体三个层次。就拟诗达到的境界而言,吴淇将其分为逼似古人之形神、改变古诗之形义和自赋新意三种。就拟诗取得的成就而言,吴淇认为有不及原诗、与原诗相当和超越原诗三种情况。不仅如此,吴淇还勾勒出拟诗的发展历史,并揭示出其对后世诗歌的积极影响。
拟诗;六朝选诗定论;原诗;模拟方法;境界
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过程中,拟诗曾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现象。《文选》所收诗歌有“杂拟”一类,见于卷三十、三十一两卷,包括陆机的《拟古诗十二首》、张载《拟四愁诗一首》、陶渊明《拟古诗一首》等63首。对于这些作品,古人曾有所论及,其中清代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一书的论述最为具体,也最为精彩。
一、 与“原诗”比较
一般来说,既然是拟诗,总要首先有被模拟的诗作,本文称之为“原诗”。与“原诗”比较,是吴淇研究拟诗的起点。他将拟诗与原诗的关系分为三种:
第一种,对于原诗明确的拟诗,吴淇直接将二者加以比较。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陆机的《拟古诗十二首》。对于这组诗,陆机在题目中即已明确指出了所拟的原诗。如《拟行行重行行》所拟的原诗即是古诗中的《行行重行行》。吴淇在《拟行行重行行》一诗后说:
此诗首尾全依原诗,中间小错。“惊飙”二字,拟原诗“浮云蔽白日”句,是晋人伎俩。“伫立”二句,稍脱原诗,故佳。“揽衣”句,从“衣带日已缓”句变来,若无“循形”句累之,则亦居然汉句矣。[1]246
对比了两诗之后,吴淇认为陆机的拟诗非常接近原诗。又如在论述袁淑《效曹子建乐府白马篇一首》时,他说:“太尉诗仿子建,一种豪侠之气,顾盼生姿。其风骨不减建安。在宋、齐之交,尤为难得。”又说:“太尉主意,不是作乐府《白马篇》,要仿曹子建乐府。”[1]333这也明确地指出袁淑拟诗与曹植《白马篇》之间的模拟关系。
它如张载《拟四愁诗一首》、王僧达《和琅邪王依古一首》、刘铄《拟古诗二首》,以及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中的多数作品,都属此类。
第二种,有些拟诗并非模拟某一首诗,而是模拟某一组诗或某几首诗。既然无法在某首原诗中寻找到对应关系,吴淇就竭力挖掘拟诗作者呈现出来的思想和艺术特点。正是因为不是模拟某一首诗,所以拟者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甚至可以借此抒发自己的感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吴淇在这组拟诗后说:
凡拟古人之诗不是古人话说,却是自己话说,特借古人做个题目耳。故既拟诸子之诗,于每篇之上各缀数语,略如卫宏之小序、元晦之诗柄,而又代文帝总序于首,文更较著也。盖康乐自伤其才大不偶,故于诸子止写其丧乱流离之苦,或写其人品卓荦与不乐仕宦之意。即间有优渥之言,不过在游戏饮燕之小礼,总非有国士之知也。[1]380—381
虽然《邺中集》今已不存,其中的多数作品已经失传,但是不可否定的是,谢灵运8首作品当是模拟该集中诸人的作品,而非模拟某一首诗;而其呈现的特点也没有某首原诗可以对照。吴淇在评论江淹《杂体诗三十首·鲍参军照》时说:
此拟鲍参军《拟古》三首之意。旧注云:“险侧自快,婉然明远风调。但未极俶诡靡曼之致。”不知未极俶诡靡曼,正所以善拟文远。盖明远长于乐府,故古诗中皆带有乐府意,乃明远之体也。此诗险侧自快,正是诗中稍带乐府意。若更极俶诡靡曼,则是拟明远之乐府,而非拟明远之诗矣。诚观此通篇无一处不是险侧自快,俨然一乐府体,但中间于序行处用“殉意[义]非为利”,于序藏处用“铩翮由时至”,全无一些俶诡意,洵为古诗,非乐府也。[1]479
从吴淇的分析看,此诗虽然拟自鲍照之古诗,但并非拟自某一首诗,而是拟自其三首诗。江淹模拟鲍照古诗,且能得其古诗之意蕴,还是比较成功的。
与模拟某一首诗往往注重字句、章法不同,古人模拟一组诗时更加重视原作的风格,从而体现出不同的特色。对这个问题,吴淇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
第三种,有些作品并无具体模拟对象,吴淇则只能立足于拟诗本身或者拟诗作者本身进行分析。有些拟诗没有明确的模拟对象,故只能指出模拟的大致范围。如对陶渊明《拟古诗一首》,吴淇说:
以中间“歌竟”二句关锁前后两段,似与“采菊东篱”同格。世人动云“诗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此妄语也。诗无不可解,若有不能解者,当于虚字上寻讨,若虚字上更寻讨不出,则与诗前后照看。如此诗的是怨情。首四句,全不露怨意,关要虚字只一“美”字。若非后六句,何由知其为怨,且怨之深也?“日暮”二句,以云静风和写清夜之美。佳人既以为美,当不空负此清夜矣。于是且酣且歌,以为庶几不负此良夜,及且酣且歌,自夕达曙,亦只是目酣自歌耳。歌阑更思不空负此酣此歌乎?既空负此酣此歌,即空负此清夜。觉彻夜酣歌,皆自夕至曙之愁闷矣,那得不长叹!乃见前之美清夜,正是怨清夜耳。“持此”,“此”字固承悲叹,并上“日暮”四句来。此句不重所感之人,正说其怨足以感人。“感人多”,犹言深也。怨不深,感人亦不深。天“明明”句,从“无云”生,“灼灼”又从“月”看出,然非实境,藉以喻年华易逝,以见良时不可空负。美人之所叹者在此,旁人之所感者亦在此。[1]292—293
虽然陶渊明在题目中已经标出“拟古诗”,也就是说其模拟的对象应该是汉末古诗,但到底是哪些,却难以确知。吴淇的分析也是从这个角度立论,赞其具有《古诗十九首》那样的风格。类似的作品还有袁淑《效古诗一首》、鲍照《学刘公干体一首》《代君子有所思一首》和范云《效古一首》等,吴淇都有具体的论述。
有时,拟诗仅仅标明模拟何人,如鲍照的《学刘公干体一首》。刘桢诗今尚存多首,那么鲍照所拟是哪一首或者哪几首呢?根本就没有办法确定。吴淇在这首诗后说:
此诗旧注,以雪比小人,桃李比君子,非也。有一辈小人自有一辈小人行事,前人之术巧矣,后人更有巧者。前人必为后人所倾,故小人猖獗肆志,各有其时,把个时势尽是小人回转据住,何日是君子道长之时乎?
此诗“□风吹朔雪,千里度龙山”,谢诗“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唐诗“朔风吹早雁,日夕渡河飞”,此三诗递相祖述,各有其妙。雪是无自力的,故曰吹,曰渡,全凭风之外力。雨稍有自力,故于雨上加一飞字,是半虚半实,故不曰度,曰来,乃自力与外力合并。雁之自力犹强,故于曰吹、曰度之外,更加一飞字,全是虚字。古人之精神体物如此。[1]339
上引两段话,一则从内容上分析鲍照的心理,一则从艺术上评价该诗的长处,都是立足于拟诗和拟诗作者进行的评价,甚至没有考虑拟诗在风格上与刘桢是否类似。
《文选》中的拟诗与原诗的关系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或者模拟某一首诗,或者模拟某一组诗或几首诗,或者模拟某一个类别,或者模拟某一个人。正因为如此,吴淇在比较二者关系时也不得不采用了不同的角度。
二、 探讨拟作方法
古人模拟前人的诗歌,主要采用那些方法呢?吴淇对此也进行了认真而细致的探讨。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层,模拟字句。这是最基础的模拟方法。拟作者不仅照搬原作的结构,甚至保留原来的语句,有时只是更换其中的某些字句。在论及张载《拟四愁诗》时,吴淇说:
《楚辞》宋玉《招魂》,有四方土[上]下之文。张平子用其意,作《四愁》以寄其思。当时所惨淡经营者,止首一章,其余三章,止逐句换字耳。然却有次第深浅之妙,故衍为四章,以明不滞于一方,盖亦不得已耳,其境界可谓至偪者矣。后人拟之不能另创一意,亦止有逐句换字之法耳。此诗换字特工,如出原手,故得存于《选》……[1]209
在论及陆机《拟古诗十二首》时,吴淇又说:“凡拟诗者,古人之格调,已定不已,但有逐句换字之法。苟酌炼字句一毫不到,便要出丑。故孙矿曰:‘多拟古,诗道自进。’”[1]245当然,除了这样的“比葫芦画瓢”,拟作者有时还会略加添减。在陆机《拟古诗十二首·拟今日良宴会》后,吴淇说:“原诗只声音一意,写出许多妙理,有独茧抽丝之妙。此作添出‘高谈’二句,竟把声音看做谈笑一例。”[1]245这里举出的是“添出”的例子。在同组《拟古诗十二首·拟明月皎夜光》后,吴淇说:
凡拟诗字栉句比,止有添无减。原诗“牵牛不负轭”下,有“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二句,谓朋友不是显然绝我,但只是虚名,即杜子美所谓“泛爱不救沟壑辱”也。此却丢失此二句不拟,只“织女”二句便住,更觉蕴藉有味。[1]253
这里举出的是“丢失”的例子。“添”也好,“减”也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诗的结构,但模拟字句的基本特点并没有改变。
第二层,模拟格调。这是比模拟字句更高一个层次的模拟方法。关于其产生的必然性,吴淇在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题目之后说:
谢之拟诗,与陆不同。陆之拟诗并拟其字句,谢之拟诗止拟其声调。盖陆有诗斯拟,原有本诗样子在此。若谢欲拟邺中八诗,在原诗有文帝《芙蓉池》一作,《公宴》止刘桢、王粲、子建、应玚四首,余陈琳、徐干、阮瑀三人,诗不见于《选》,势不得字摩句效,只得取其平日之声调气格为之,平空代构。三子既为代构,余五首若仍如陆之字摩句效,则八首不相伦矣,故索性连五首亦正拟其声调气格也。江之拟法则兼陆与谢。[1]380
在组诗中《徐干》一首之后,吴淇这样分析说:
首五句,少无宦情。“外物”三句,有箕颍之心事,迫于世乱而不得遂。“末涂”以下,仕世多素词也。末“昔心”二字,应序“心”字,应首“昔”字。盖昔在临淄,曾见礼于汉室诸王之门,不过弄瑟置酒,原未有其事;今之在邺下,清论奏歌,游戏于魏诸公子之前,犹之在临淄时汉诸王之见礼,未尝有所变塞也。呜呼!抚今追昔,怅怅若失。此中之感慨最深,又不关箕颍之心事遂与不遂也。要知伟长是箕颍之心事,不是沮溺之心事。沮溺以乱而隐,箕颍以治而隐。伟长在康乐自拟中,乃无用之用。“少无宦情”,拟其少无竞进之情。“仕世多素词”,若假以权,不事纷张,素位而行。“有箕颍心事”者,功成名遂身退,乃打算及末后一着也。[1]386
在这段话中,吴淇并未过多论及风格,但他紧紧扣住徐干的生平来分析诗歌,显然是认为该诗的格调与徐干的作品近似。反过来,如果拟作的格调与原作者不类,吴淇就会提出批评。如在江淹《杂体诗·卢郎中谌》一诗后,吴淇说:“只是贪用赠刘题目大耳,然其赠刘乃四言诗,与此不合。故又杂采《赠崔温》及《答魏子悌》诗,以簉成此篇,然郎中《时兴诗》最佳,何不拟之?”[1]468吴淇认为,江淹的拟诗表面看来是拟卢谌赠刘琨之作,但卢谌原作是四言诗,江淹拟诗为五言诗,所以彼此差别较大。在《杂体诗·袁太尉淑》一诗之后,吴淇的说法更有意思:
袁太尉原诗虽不存,然观其《白马》等篇,甚跌荡有气。文通乃取颜光禄之诗字摩句拟,硬作太尉,是何异用玉环之貌为飞燕写真,其肥瘦长短之形尚相径庭,又安能传其神乎?[1]477
吴淇说江淹所谓的拟袁淑之作,所拟的对象实际上却是颜延之诗歌,这就更离谱了!
第三层,备人与备体。除了以上两种比较明显的模拟方法,吴淇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备人”与“备体”的说法。他在江淹《杂体诗·王侍中粲》后说:“康乐备人,故全拟八首;文通备体,故只效前四首。此四首皆用《公宴》为题,而旧注妄分四题,可噱也。”[1]461所谓“康乐备人,故全拟八首”,就是说谢灵运之所以拟八人之诗,并非因为他们的诗歌多么优异,而是他想为每人作一首诗以述其生平。当然,如果这方面做得不成功,他也会给予批评。在《陈琳》一诗后,吴淇说:
八诗中惟拟孔璋一诗最丑。盖诗之首重者品,世未有无人品而能诗者。既曰“袁本初书记之士”,琳固于袁氏有优渥之恩矣。此诗却比袁氏于董卓,而甚至斥为蟊贼,果孔璋而出此,人品扫地矣,尚可言诗哉![1]385
所谓“文通备体,故只效前四首”,是说江淹拟诗主要模拟不同的诗体。他在《杂体诗三十首》序后说:
文通胸中初无所感,只《序》中品藻渊流,便是作诗主意。盖取自汉至梁作者三十余家,于三十余家中取其平生最有名诗,各效其体作一首,以概其余……[1]454
正因为如此,在模拟建安作家时,江淹只选择了曹丕、曹植、刘桢、王粲四人的名作加以模拟。
不过,“备人”与“备体”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如吴淇虽然认为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属于“备体”,可是他同样强调了其中的“备人”成分。他在《李都尉陵》一首后说:
他诗俱拟原人所有,此诗独补原人之缺。按《选》中载苏、李共七:苏诗四首,李诗三首。其“良时”与“骨肉”等,俱以三首相对,而李独缺“结发为夫妇”一首,此诗补作一首。本无原词可以拾摭,俱皆自运,但取李都尉他诗之清澈气味。本是用李摩苏,先有李诗而后有此诗,而其主意却是代李倡苏,读者反觉先有此诗而后有原诗也。譬之学弈然,有两国手谱势于此,吾只见一着白,二着黑,三着白,四着黑,五着白,六着黑,至七着白,却已轶失,止见八着黑。我欲学此国手,定须细细揣摩,此八着黑何为下子在此路,必是应他七着白在某路矣。揣摩得着,便是善学此国手,亦并学得彼国手矣。[1]456
在《休上人》一诗后,吴淇又说:
《选》无僧人之诗,无赠僧人之诗,亦无以佛语入诗者,独此为拟僧人诗。拟僧人之诗,不惟不以佛语入诗,且用极艳者以反其意,示后世或僧、或赠僧人一切之法。唐宋之问《浣沙篇》赠陆上人,颇得此意。惜其末犹用佛语解释,较此少趣耳。[1]480
“备人”也好,“备体”也好,其中都包涵着一定的创新成分,跟模拟字句、模拟格调那样一味重视模仿有很大的不同。不过,就拟作者而言,其强调的毕竟是模拟而不是创新,它们与模拟字句、模拟格调共同构成吴淇所说的几种主要模拟方法。
三、 评论拟诗境界
拟诗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呢?针对这样的问题,吴淇也有具体细致的分析。这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逼似古人之形神。关于拟诗所要达到的境界,吴淇在论及陆机的《拟古诗十二首》时这样说:
拟诗始于士衡。大抵拟诗如临帖然。古人作字,有古人之形之神。我作字,有我之形之神。临帖者,须把我之形堕黜净尽,纯以古人之形,却以我之神逆古人之神,并而为一,方称合作。不然,借古人之形,传我之神,亦其次也,切勿衣冠叔敖。[1]245
在这段话中,吴淇认为拟诗的最高境界是具有古人之形神,如果仅有古人之形而无其神,就差了一个档次了。在评价刘铄《拟古诗二首·拟行行重行行》的时候,他说:“拟诗必兢兢以古人之格调字句,寸寸模仿,然字句之间,可以出入,凭我自运。而其格调之大关键处,则不可遗也。”[1]331这里更多强调的是“形似”的一面。在评价陆机《拟古诗十二首·拟涉江采芙蓉》一首时,他说:“冲澹古雅,句句模拟原诗,却不见模拟之痕。”[1]247这似乎指的是“神似”的一面。他还曾这样称赞江淹的《杂体三十首·卢郎中谌》:“凡拟诗者,在得故人之意,此诗虽不合郎中之体,而颇会其意。”[1]469不论是“形似”,是“神似”,还是兼得古人之形神,都是强调逼似古人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所拟不似,吴淇对其的评价就不高。在谈及张载《拟四愁诗》时,他说:“平子原诗,饶有风骚之致,而孟阳所拟,不无少减,则只可有一之说,未尝无谓。”[1]212
第二层,改变原诗之形义。在谈到陆机《拟古诗十二首·拟青青河畔草》的时候,吴淇这样说:
词虽句句模拟原诗,而义迥不同。原诗是刺,此诗是美。曰“纤”,便是女子正业。曰“当轩”,便不算楼上招摇。“灼灼”一句,是下文叹息之根本。“良人”二句,是叹息之缘起。“空房”二句,之子一腔心事,也只是一声叹息,并无如许态度、如许话说;就此一声叹息,也只在空房无人之处;也只在中夜无人之时,真良人举止也。
原诗写娼妇,故用岸草园柳,青青郁郁,一片艳阳天气,撩出他如许态度、如许话说。此诗止用靡靡江蓠,一草起兴,偷引起“悲风”云云,言之子一腔心事,只如车轮在心头暗转。不是空房悲风,逼得他紧并此一声叹也,迸不出来。此诗可用“妇叹于室”作题。[1]248
在吴淇看来,陆机的《拟青青河畔草》虽然“句句模拟原诗”,即得原诗之形貌,但义理却有所区别,特别是“刺”与“美”的差异更加明显。又如在评论陆机的《拟西北有高楼》时,他说:“此疑亦臣不得于君之意,但原诗就歌者意中写,此诗就听者意中写。”[1]251虽然都是写“臣不得于君之意”,但拟诗与原诗在形貌即视角上却有显著的不同。尽管吴淇似乎并不看重这样的境界,但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拟诗中更加普遍,因为受拟者自身条件的限制,拟诗总会在或形貌或义理等方面体现出一定的变化来。
第三层,自赋新意。相对于以上分析的两种境界,吴淇对拟者自赋新意的一面也特别重视。这主要体现在他对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的评价上。他在《平远侯植》一诗后说:
余初读此诗,便疑为感庐陵之事,未敢以为确是。及反复细玩,至此“西顾”四句,始洞然信其不谬也。子建诗曰“甘赴江湘,奋戈吴越”,若此徒为子建咏也,则宜向东南而写,如左太冲之左顾右盼矣。而乃云“西顾”“北眺”,不宜背乎?此明明故放破绽,以起问者,见此诗题虽云“平远侯植”,实是庐陵王义真替身耳。按宋史:武帝北代[伐],以幼子义真从。及刘穆之死,宋武仓卒南还,留义真于关中,则西北故庐陵所经营之处,故曰“顾”曰“眺”,代为庐陵惜之也。若庐陵当年能抚而有此,今日安肯受制于人也?因以“太行”暗替仲宣诗中“函崤”,以“邯郸”暗替仲宣诗中“伊洛”,最有线索,最有力气。怅望修涂,白杨袅袅,庐陵已被谗而死矣。仍写其忧生之嗟者,殆死而犹有余悸欤?[1]390
经过吴淇的一番阐释,谢灵运的一首拟诗竟然变成了替庐陵王刘义真鸣不平的现实诗了!在《王粲》诗后,他说:“诸子中唯仲宣才高而望重,故康乐首取以自况。”[1]383吴淇认为,谢灵运拟王粲诗,其实是为了“自况”。在《应玚》诗后,他又说:“汉末党锢祸起,一时节义之士多出汝颍之间,如李元礼、陈仲举辈,故康乐取德琏以寓意也。”[1]387不论吴淇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但他指出拟诗中存在这样一种境界也是非常难得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拟诗虽有追求逼近古人的一面,但也有改变形神甚至自赋新意的一面。
四、 论断拟诗成就
拟诗,也就是前人所讥笑的“屋下架屋,愈见其小”。从这个意义上说,拟诗似乎永远达不到原作的水平。对此,吴淇有清醒的认识。但与此同时,他又觉得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从他的具体论述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拟作不如原诗。这是自古以来学人的主流观念。吴淇在谈及张载《拟四愁诗》时说:“不知拟诗不如原诗之工,从古皆然。泥此,则是拟诗一体,尽可废矣。余甚不欲以此阻后世才子之文人也。”[1]212在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潘黄门岳》后,吴淇又说:
悼亡诗,潘郎已关至极,后人无处下手。但原诗从恭朝命而来,途中闻讣起,直写到遵朝命而去。盖甫及周期也。此诗“殡王”云云,是从周期接着说起。原诗“荏苒冬春树,寒暑忽流易”,是说生前之日月易迈,以伤其人之亡。此诗首“青春”二句,是周期后之日月,以写其凄怆无终毕之意。“美人”句,文法须倒转在前,观末日代序为结,可知。
世称王夫人神情散朗,有林下风。此语甚妙。尚不及此诗“明月”二句传美人生前之神情,尤属妙思。[1]464
既称“潘郎已关至极”,则拟作不如原诗已是基调。明乎此,则引文虽多次指出江淹拟作的佳处,其实都是在认为其不如原诗的前提下的评价。对于所论及的大多数作品,吴淇的态度都是如此。
第二种,拟诗与原诗相当。吴淇虽然从总体上认为拟诗的价值不及原诗,但在具体论述时,却又无法忽视一些拟诗的成就,认为有些作品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原诗的水平。他在袁淑《效曹子建乐府白马篇一首》后说:
闳壮而腴密,兼有文质,却与陈思作不甚相似,然其亚也。陈思作只说得一个少年,独茧抽丝,此却聚得许多少年,众毛攒毡,全于离合中取态致。盖言秦地多游侠之士,且形艺[势]地足以容天下士,故荆、魏客从之,而壮士少年,皆风雨而来,与之交欢,宴饮结要而去。此以务远作结,归之于大,陈思以赴难作结,归之于正,差相当。[1]334
如果说在这里吴淇还仅仅是说拟作与原作“差相当”,也就是略差于原作,他对江淹《杂体诗三十首·陶征君潜》的评价更高:
……昔人以武侯舍耒而仕,为得出之正;吾亦以元亮操耒而隐,为得处之正。《文选》不识此意,故于陶诗取舍未尽合。文通却深识此意,故于拟诗独得其神。其诗曰“种苗”云云……当其荷锄苦矣,浊酒一乐。运柴苦矣,稚子候一乐。桑麻苦矣,纺绩成一乐。一事计之,有一事乐也。耕织苦矣,耕织既成而朋来,总一大乐也。此乐即孔、颜之乐也。使元亮得志,吾知其必能以养者养人,即以养人者教人,其事业必有可观者焉。此文通拟陶之妙,不下于陶之自制耳。[1]473—474
吴淇对这首诗的评价虽高,但并算不出格。北宋苏轼写作和陶诗时,就曾误把江淹的这首拟诗当作陶诗了。
第三种,拟作高于原诗。从吴淇的分析看,这样的例子不多。在《拟古诗十二首·拟兰若生朝阳》之后,他说:
原诗云:“兰若生春阳,涉冬犹盛滋。愿言追昔爱,情款感四时。美人在云霄,天路无期夜。光照隔玄阴,长叹念所思。谁谓我无忧?积念发狂痴。”按原诗,首四句俱就时写,未免稍弱。此诗首句地,二句方言时。早于言地处,因“朝阳”二字,偷带出“时”字,而以凝霜照之,更有力量。三句不渝其地,有抱柱之坚。四句不变于时,有靡他之贞。觉原诗尚是儿女子情态,原诗“美人”云云,专写美人光彩,带出高旷。此专写美人之高旷,带出光彩。力足相敌。原诗末句“积念发狂”,已是鲁矢之末。此诗“引领”云云,从高旷生来,犹自余劲矫矫。此《选》之所以独存拟诗也。[1]249
吴淇首先引出原诗,然后分析陆机的拟诗,认为比原诗更好,以至于萧统编纂《文选》时舍弃了原诗,而单单保留了陆机的拟诗。不过就总体情况而言,拟诗比原诗好的例子很少。陆机的这首拟作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
最有意思的是,吴淇有时还会将同一首诗的不同拟作进行比较。他在评价刘铄《拟古诗二首·拟行行重行行》时说:
前半虽紧依原诗,然遣词处亦自有清丽可颂。“日夕”以下,稍为自运,如“明灯”云云,将一片幽思,写得黯黯惨惨。末急收以“愿垂”二语,遂振起一篇精神,故较士衡,此拟尤胜。[1]331
由于陆机、刘铄都曾模拟古诗《行行重行行》,所以吴淇将两首拟作进行了比较,认为刘作的收尾比陆作更胜。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吴淇对拟诗成就的认识是非常通达的。他虽然认同拟诗不如原诗的基本观点,但又敏锐地看出有些拟诗已经与原诗不相上下,甚至有超越原诗的情况,并大胆予以肯定。
五、 勾勒拟诗历史
吴淇不仅着力分析了六朝拟诗的各种特点,还着意勾勒出拟诗的历史。在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之后,他说:
拟古之诗昉于陆机。陆自恃其才可敌古人,凡遇古便拟,初无成局。至宋谢灵运,更自负兼人之才,于是宗陆意而拟《邺中集》诗八首。其取材于邺下者,何也?才之难也。生不必同时,同时者未必聚之一地,又未必有人焉集之一处一时;而诸子生同时矣,魏武又能聚之一地,而文帝又能集之一宴之上,此真亘古未有之奇。而此八人者,又各各手笔不同,或清或艳,或正或奇,咸能自竖坛坫。谢贪其如此,因而取材,人各一首,盖直欲合天下之才以为一人之才者也。题曰《邺中集诗八首》,若地之有八维,遂成一横局。至梁江淹时,汉道既备,而菁华亦将竭,于是上自古诗、李陵,下及休上人,千余年间,凡得三十家。仿其体,人各一首,是又欲以一人之才分为古今之才者也。题曰《杂体诗三十首》,若月之有三十日然,遂成一从[纵]局。惟陆随篇而拟,无成局,故有去有存。而谢与江之诗,总是一篇,故存则俱存耳。[1]379-380
在这段话里,吴淇以作者为线索勾勒出六朝拟诗发展的大致历程:其一是晋代陆机。他认为“拟古之诗昉于陆机”。正因为是创始,所以陆机的拟诗“初无成局”。其二是刘宋谢灵运。谢“直欲合天下之才以为一人之才”,从而创造出“亘古未有之奇”。其三是齐梁江淹。江“欲以一人之才分为古今之才”,气魄比谢灵运更大。至于这里的说法是否正确,或者仍有探讨的空间,但他对拟诗历史的探讨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
吴淇探讨拟诗的发展,不仅是为了就事论事,也是为了揭示其对之后诗歌发展的意义。他在评价范云《效古》时说:“诗虽效古,开唐人炼字法门。‘寒沙’二句,‘平’‘ 惊’二字炼得好。‘风断’二句,‘断’‘失’二字炼得好,遂振起一篇精神。”[1]444评价一首拟诗,吴淇并没有在意该诗与古诗之间的关系,反而把重点放在对唐诗的影响上,这是很有意思的。在逐首分析了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之后,他总结说:
江淹《别赋》为古今绝唱。观此诗以《古别离》起,以《怨别》终,两诗俱极,一称前茅,一称后劲。今千载而下,读此三十首,篇篇“黯然销魂”之意,工于赋别,斯工于《别赋》耳。
齐梁以来,一派浮气滞气,被此一首扫除将尽,已与唐人风气有暗入处。故文通《杂体三十首》以苏李为首,以《古别离》作弁,所以继古诗苏李之后,以此诗居后,所以开唐人之先,盖诗家之会也。昭明《选》诗,以韦孟《讽谏诗》为首,以《补亡诗》作弁,所以继《三百》之后,亦用此诗开唐之先。盖诗之元也,诗人之会,消长于其间焉。故《三百》至《选》诗,中间相隔数百年,《选》诗至唐,止数十余年,风气所使,不可强也。即推之一代之运,一人之世,莫不皆然。[1]481
《别赋》是江淹的杰作。吴淇不仅认为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为“工于赋别,斯工于《别赋》”,而且特别强调了其“已与唐人风气有暗入处”的一面。
对于古代的拟诗,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中的认识不仅具体深刻,而且全面系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即使到了今天,也未见有人超越。当然,受时代和思想的局限,吴淇的认识也有前后矛盾甚至不正确的地方。比如,他既认为拟诗不可能达到原作的水平,又认为个别拟诗比原作更佳。对于这个矛盾,他始终没有给以合理的解释。又如,他在分析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的时候,坚持认为谢灵运借王粲以自况,借曹植以比刘义真,都显得比较牵强,难以令人信服。不过,比起他取得的成就,这些不足是次要的。
[1]吴淇.六朝选诗定论[M].汪俊,黄进德,点校.扬州:广陵书社,2009.
Wu Qi’s Understanding of Imitation Poems in
ZHANG Ming-hua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41, Anhui)
As for the 63 limitation poems in, Wu Qi, a scholar in Qing Dynasty, has a concrete and deep comment in his. According to Wu, the “original” poem(s) imitated are either original poems, or a group of poems, or there are no objects being imitated at all. Of that matter, Wu has a sober understanding. Wu summarizes three imitation methods: language imitation, style imitation and figure/genre re-creation. In terms of grades of realms of imitation poems, Wu recognizes resemblance of classics, change of form and meaning of classics and addition of new meaning. For achievements of imitation poems, Wu argues that some imitation poems are not so good as, some are as good as, and some are better than the original poems. Furthermore, Wu outlines the history of imitation poems and reveals its influence on later poems.
imitation poem;; original poem; imitation method; grade of realm
2018-04-22
张明华(1967-),安徽阜阳人,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安徽省重点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8.04.14
I206
A
1004-4310(2018)04-007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