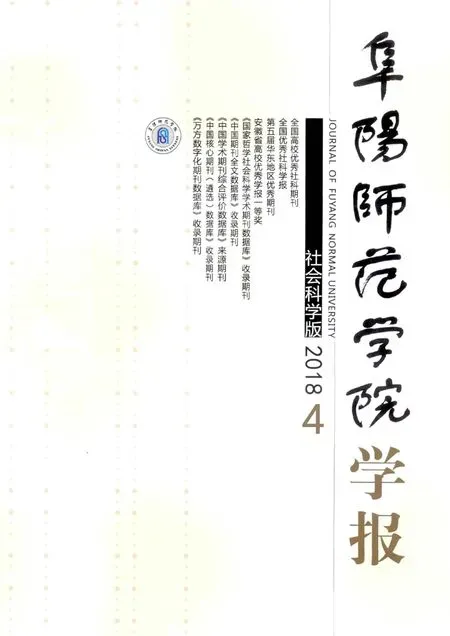论清华简《管仲》篇的儒学化倾向
张 杰,张艳丽
论清华简《管仲》篇的儒学化倾向
张 杰1,2,张艳丽1
(1.山东理工大学 齐文化研究院,山东 淄博 255000;2.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传世文献所记载的齐桓公和管仲是明君贤臣的典范。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首霸中原的不朽功业一直被后人所称颂,但他们的道德缺陷也不断为后人所诟病。《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中的《管仲》篇则改变了这一形象。它通过齐桓公问、管仲答的对话形式,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典型的儒家内圣外王的君、臣形象。这可从重视学习,重视“人道”, 承、辅的设置以及有道之君、无道之君等四个方面得到证明。这使清华简《管仲》篇具有明显的儒学化倾向。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管仲》篇;齐桓公;管仲;儒学化;倾向
《管仲》篇是《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中的一篇重要文献。学术界对此篇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简文的释读。主要有李学勤主编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1]110-117,清华大学出土文献读书会的《清华六整理报告补正》[2]3-7,子居的《清华简〈管仲〉韵读》[3]1-23,简帛网中的《清华六〈管仲〉初读》[4]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深入理解《管仲》篇原文提供了很大便利。二是《管仲》篇的字迹研究。如李松儒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之〈管仲〉字迹研究》,认为《管仲》篇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为同一抄手所写[5]34-45。三是对《管仲》篇介绍与研究。这以刘国忠《清华简〈管仲〉初探》为代表,他在整体介绍《管仲》篇的基础上,对《管仲》篇所蕴含的治国理念如“为君与为臣孰劳”及其所含的阴阳五行思想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认为《管仲》篇虽然与《管子》在体例、思想方面有相通之处,但所探讨的具体内容完全不同,“应当是属于《管子》一书的佚篇”,并且“可能是刘向本人未曾见过的一篇文献”[6]88。
本人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认为《管仲》篇不但包含着一定的阴阳五行思想,而且具有明显的儒学化倾向。传世文献所记载的齐桓公和管仲是明君贤臣的典范。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首霸中原的不朽功业一直被后人所称颂,但他们的道德缺陷也不断被后人所诟病。然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中的《管仲》篇则以齐桓公问、管仲答的形式为我们刻画了一个典型的儒家内圣外王的君、臣形象。这可从重视学习、重视“人道”、 承、辅的设置以及有道之君、无道之君等四个方面得到证明。
一、 重视学习
重视学习是《管仲》篇的重要内容之一。《管仲》篇首段言:“齐桓公问于管仲曰:‘仲父,君子学欤?不学如何?’管仲答曰:‘君子学哉,学乌可以已?见善者服焉,见不善者戒焉。君子学哉,学乌可以已?”[1]111
“君子学欤?不学如何?”其大意为:齐桓公作为齐国君主,向其宰相管仲请教统治者需不需要学习这个问题。当然这个学习不是普通的学习,而是偏指加强道德修养而言。这在下文有详细论述。“见善者服焉,见不善者戒焉。”其大意为:看见善的东西加以效法,看见不善的事情要引以为戒。
《管仲》篇有关“学”的论述,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学”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管仲》篇首节内容就是“学”。这充分说明“学”的重要性。而重视“学”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特征。先秦儒家的重要典籍《论语》首章为《学而》篇。有关“学而”篇次的重要性,梁皇侃在其《论语集解义疏》中说:“自《学而》至《尧曰》凡二十篇首末相次无别科,而以《学而》为最先者,言降圣以下皆须学成。故《学记》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明人必须学乃成。此书既遍该众典以教一切,故以《学而》为先也。”[7]1这说明《学而》虽然因篇首为“学而”两字而得名,但就其内容而言,全部为怎样提升道德修养而展开。除《论语》外,《荀子》首篇也与“学”有关。其首篇为《劝学》。对此,熊公哲解释说:“劝学即勉人努力学问。荀子之学,以礼为归;故其论学,目的在为士,为君子,为圣人。方法在诵经读书。”[8]1《礼记·学记》记载:“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9]1051《论语》《荀子》将“学”放在首篇,《礼记》把“教”与“学”放在建立国家、治理民众的首要地位,这些都说明“学”在儒学中的重要地位。正因为如此,儒家才强调要时刻学习。《论语·学而》载:“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10]1《荀子·劝学》载:“学不可以已。”[11]1清华简《管仲》篇载:“君子学哉,学乌可以已?”可谓异曲而同工,都强调学习的重要性。
第二,“学”的主旨是提高道德修养。
《论语·雍也》载:“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10]71不迁怒别人、不犯同样的过失,这很显然是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的标志。《礼记·大学》载:“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又载:“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9]1592“大学之道”同样以“修身”为本。在“学”的过程中,其方法多种多样,如读诵六经、温故而知新、见贤思齐等等。《荀子·劝学》载:“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11]11可见荀子把诵六经作为学习的方法,把成为士、圣人作为学习的意义。《论语·子张》载:“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10]256《论语·为政》载:“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10]19这些都说明温故而知新是学习的重要方法之一。《论语·里仁》载:“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10]51-52《论语·述而》载:“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10]92这些记载与《管仲》篇所记载的“见善者墨焉,见不善者戒焉”,大同小异。由此可知《管仲》篇首段具有强烈的儒学化倾向。
二、 重视“人道”
《管仲》篇第二段言:“齐桓公又问于管仲曰:‘仲父,起事之本奚从?’管仲答曰:‘从人。’”其大意为:齐桓公问管仲做一件事从哪里开始?管仲回答说:从人道开始。
那么人道的内容是什么呢?《管仲》篇第三段载:“桓公又问于管仲曰:‘仲父,其从人之道可得闻乎?’管仲答:‘从人之道,趾则心之本,手则心之枝,目、耳则心之末,口则心之窍。趾不正则心逴,心不静则手躁。心无图,则耳、目野,心图无守,则言不道。’”此段的大意为:齐桓公又问管仲:“仲父,人之道能够闻见吗?”管仲回答说:“人之道,足为心之根本,手为心的枝叶,耳、目为心末梢,口为心的孔窍。足不正则心动摇,心不静则手躁动。心中无所图谋则耳目怠惰,心中有所图谋但没有底限则不合道义。”
《管仲》篇第二、三段说明了三个问题:
其一,重“人道”是先秦儒家和道家的重要区别之一。
道家重天道,以人道效法天道。如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2]。《荀子·解蔽》则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11]393。这说明重天道、重视无为自然之道是先秦道家的重要特点之一。与道家不同,儒家则重人道轻天道。如孔子提倡仁德,主张“克己复礼”[10]157;孟子主张人性善,提倡仁政和王道;荀子主张人性恶,提倡隆礼、重法及霸道。他们的思想主张虽然有所差别,但重人道是其共同点。先秦儒家重人道的特色在《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中更有突出表现。《性自命出》载:“道者,群物之道也。凡道,心术为主。道四术,唯人道为可道。其三术者,道之而已。”[13]道有四术,以人道为主。《管仲》篇则认为做一件事情起于人道,这是《管仲》篇儒学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其二,儒、道虽然都论心术,但目的不同。
战国后期心术即心与四肢、九窍的关系,成为当时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其中以儒、道最有代表性。道家的代表之一即是《管子》四篇。《管子·心术上》载:“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见色,耳不闻声。”[14]759《心术上》论心与九窍的关系是为求“道”服务的。《心术上》载:“道不远而难极也,与人并处而难得也。虚其欲,神将入舍。扫除不洁,神乃留处。”[14]759“神”,郭沫若释曰:“这道……可以称之为无,称之为虚,称之为心,可以称之为气,称之为精,称之为神。”[15]道不远离人但普通人难以企及,其原因是内心被情欲或嗜欲所充满。只有摆脱物欲或嗜欲对人的束缚,“道”才能停留在人心。而摆脱嗜欲的束缚,也是达到“心处其道,九窍循理”的不二法门。可见以《管子·心术上》为代表的心术论是为道家的“道”服务的。
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同样论述心术,但他们的心术论则是为人道服务的。《孟子·告子上》载:“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16]312又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16]314孟子认为体有大、小之分。人欲属小体,人心属大体,小体应该服从大体。孟子论述心与身体、九窍的关系是为人性善服务的,属于人道的重要内容之一。《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载:“‘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耳目也者,悦声色者也;鼻口者,悦臭味者也;手足者,悦佚愉者也。心也者,悦仁义者也。此数体者皆有悦也,而六者为心役,何也?曰:心贵也。有天下之美声色于此,不义,则不听弗视也。有天下之美臭味于此,不义,则弗求弗食也。居而不间尊长者,不义,则弗为之矣。何居?曰:几不□胜□,小不胜大,贱不胜贵也哉!故曰心之役也。耳目鼻口手足六者,人□□,□人体之小者也。心,人□□,人体之大者也,故曰君也。”[17]上述引文无疑与孟子的大体、小体说内容密切相关,它们同属人道的重要内容。《管仲》篇第三段所论述的心与身体、九窍的关系,其内容虽与《孟子·告子上》《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有些差异,但它们都为人道服务。可见《管仲》篇第三段有关人道、心与身体、九窍的关系的论述,同样是《管仲》篇儒学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其三,《管仲》篇的治国思想以人道为主,即使涉及天道,也多为人道服务。
《管仲》篇自第四段至第十一段的内容都与治国密切相关。第四段、第五段论述设置承、辅的问题,以及施政之道的问题。第六段论述千乘之君在面对刑政已废、百姓懈怠、佞臣当政的情况下,如何治理国家。第七段讨论怎样守成的问题。第八段讨论有道之君怎样保邦?第九段、第十段分别讨论距离他们时代较远与较近的有道之君及无道之君的问题,第十一段讨论佞臣的特征。上述七段内容都是人道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体现,这些内容很少涉及天道,即使有极少内容涉及天道,也多为人道服务。
如第五段在论述施政之道时,曾谈到“正五纪”。对此,刘国忠注曰:“五纪,见于《书·洪范》:‘协用五纪’,‘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亦见于《管子·幼官》:‘五纪不解,庶人之守也。’”[1]115《尚书正义》将“五纪”释为“岁”“月”“日”“星辰”“历数”[18]306,可见在《尚书·洪范》中的“五纪”虽与天时有关,但最终为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历数”即历法服务,其人事特色明显。二是《管子·幼官》中的“五纪”,郭沫若解释说:“‘五纪’当作‘五终’,下文云‘贫富之终五’,‘纪’字涉上‘六纪’而误。终者,总也,统也。”[19]“贫富之终五”,钟肇鹏注曰:“《管子·立政》:‘国之所以富贫者五’,即繁殖森林,疏通沟渎,广植桑麻五谷,繁育六畜、蔬果,发展女红手工业。终,统也。”[20]可见《管子·幼官》中的“五纪”当作“五终”,也就是国家使百姓致富的五种策略。可见无论是《尚书》还是《管子》中的“五纪”,都与人事密切相关,与道家中的天道相差甚远。
再如第七段在探讨守成之道时,曾提及与天道有关的内容。其内容为:“桓公又问管仲曰:‘仲父,既设其纪,既顺其经,敢问何以执成?’管仲答:‘君当岁,大夫当月,师尹当日……’”刘国忠解释说:“《尚书·洪范》:‘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1]115《尚书正义》释曰:“王之省职,兼总群吏,惟如岁也。卿士分居列位,惟如月也。众正官之长各治其职,惟如日也。此王也,卿士也,师尹也,掌事犹岁月日者,言皆无改易,君秉君道,臣行臣事。则百谷用此而成,岁丰稔也。”[18]322可见《管仲》篇中的“君当岁,大夫当月,师尹当日”,是把国君、大夫、师尹各自的职责比喻成岁、月、日,其目的是强调君臣职责分明,不得变其职守,只有如此治理好国家。
由此可见,《管仲》篇在论述治国之道时,虽然偶尔出现了天道方面的内容,但并不是以老子为代表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的治国思路,而是或者强调天道中与人道密切相关的历法,或者通过岁、月、日天然的职责强调君臣要分清职责,各尽其能。这些内容虽然与天道有关,但还是儒家外王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承、辅的设置
《管仲》篇第四段探讨了如何设置承、辅的问题。“齐桓公又问于管仲曰:‘仲父,设承如之何?立辅如之何?’管仲答:‘贤质不枉,执节缘绳,可设于承;贤质以亢,吉凶阴阳,远迩上下,可立于辅。”其大意为:齐桓公问管仲怎样设置承、辅?管仲回答说:不邪曲、依法执法的贤质之士可立为承,知识渊博极知吉凶、阴阳、远近、上下之事的贤质之士可立为辅。
有关“承”“辅”的问题,《大戴礼记》《尚书大传》等儒家经典中都有相关记载。《尚书大传》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承,左曰辅,右曰弼。天子有问无以对,责之疑;可志而不志,责之承;可正而不正,责之辅;可扬而不扬,责之弼。”[21]可见:“承”“辅”与“疑”“弼”同为辅佐的天子肱股之臣。其中“承”具有充天子之志的职责,“辅”具有矫正过错的职责。《大戴礼记·保傅》载:“笃仁而好学,多闻而道慎,天子疑则问,应而不穷者,谓之道。道者,导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诚立而敢断,辅善而相义者,谓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过而谏邪者,谓之弼;弼者,拂天子之过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闻强记,接给而善对者,谓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遗忘者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22]根据《大戴礼记》的记载:“道”“辅”“充”“弼”为辅佐天子的四种重要官职,分别由周公、太公、召公、史佚等贤臣担任。由上述可知,《管仲》篇中的承、辅的职责虽然与《大戴礼记》《尚书大传》的相关记载不同,但其性质一样,都是帮助君王充善、改过的官吏,这是儒家理想中的贤明君王才能够设置的官吏。而这一类官职的担任者如周公、太公、召公、史佚等,无不是德才兼备的贤臣。我们由“承”“辅”的设置,也可以看出《管仲》篇儒学化的倾向。
四、 有道之君和无道之君
《管仲》篇第九段和第十段分别描绘了古代以及近世的有道之君和无道之君的形象。这里的有道之君、无道之君分别是儒家正面、反面的典型代表。
1. 有道之君
《管仲》篇第九段前半部分为我们列举了古代有道之君的典范。古代有道之君以商汤为代表。《管仲》篇载:“桓公又问于管仲曰:‘仲父,旧天下之邦君,孰可以为君?孰不可以为君?’管仲答曰:‘臣闻之,汤可以为君。汤之行正,而勤事也,必哉于义,而成于度,小大之事,必知其故。和民以德,执事有恪,既惠于民,圣以行武,哉于其身,以正天下。若夫汤者,可以为君哉!’”《管仲》篇认为汤能够成为古代有道之君的典范,是因为他既能修身于己,又兼能施惠百姓并给全天下人带来福祉。

2. 无道之君
《管仲》篇第九段后半部分为我们列举了古代无道之君的代表¾¾商纣王。“及后辛之身,其动无礼,其言无义,逞其欲而纟亘其过,既怠于政,又以民戏。凡其民人,老者愿死,壮者愿行,恐罪之不竭,而刑之放,怨亦未訾,邦以卒丧。若后辛者,不可为君哉!”此段的大意为:商纣王,动而无礼,言而无义,放纵欲望而穷尽过错,既怠于政事,又戏虐百姓。商王朝的百姓,年老者希望早死,年壮者希望远行,惟恐罪及无辜。商纣王恣肆刑罚,不思民怨,最终丧失商王朝。像后辛一样者,不可为君王!
《管仲》篇第十段后半部分为我们列举了商纣王之后无道之君的代表──周幽王。“及幽王之身,好使佞人而不信贞良。夫佞有利气,笃利而弗行。若幽王者,不可以为君哉!”根据子居解释,“佞人”指虢石父[3]。根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载,他为人的最大特点是“佞巧善谀好利”[23]149,周幽王重用此臣,导致民怨沸腾,社会各种矛盾激化。此段的大意为:周幽王喜好重用佞臣而不信任贞良之臣。佞臣有贪利之气,什么有私利的事不会去做呢?像周幽王者,不可为君王!
《管仲》篇第九段、第十段分别列举了两位有道之君和无道之君。有道之君为商汤和周武王,无道之君为商纣王和周幽王。商汤、周武王是儒家心目中的理想君王。《论语》大力赞扬周武王的文治武功,《孟子》中则把商汤作为仁人的代表,并把他与尧、舜、禹、文王都看作先代圣王,至唐代韩愈则把商汤、周武王都看作儒家道统的代表人物。《管仲》篇把商汤和周武王分别作为古代和当时有道之君的代表,其儒家特色明显,此其一。《管仲》篇在树立商汤和周武王有道之君的形象时,既注重他们的高尚品德以及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又注重了他们治理天下的文治武功,这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明显体现,此其二。与之相反,商纣王则是儒家无道之君的代表,他放纵私欲,懈怠政事,导致天怒人怨,身死国亡。而周幽王重用贪利之臣,更是违背了儒家重义轻利的宗旨。我们由《管仲》篇所记载的有道之君、无道之君的标准也可看出其儒学化的倾向。
与《管仲》篇第九段、第十段相类似,《管子》中也称类似的有道之君、无道之君的提法。刘国忠在注释《管仲》篇中的“四称”时说:“四称,《管子》有《四称》篇,注云:‘谓称有道之君、无道之君、有道之臣、无道之臣,以戒桓公。”[1]115我们通过比较《管子·四称》与清华简《管仲》篇中“有道之君”记载的差别,也可看出前者虽受儒学影响,但并没有儒学化的倾向。《管子·四称》记载管仲在回答齐桓公关于有道之君的提问时说:“夷吾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庙、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其武臣,宣用其力。圣人在前,贞廉在侧,竞称于义,上下皆饰。形正明察,四时不贷,民亦不忧,五谷蕃殖。外内均和,诸侯臣伏,国家安宁,不用兵革。受其币帛,以怀其德,昭受其令,以为法式。此亦可谓昔者有道之君也。”[14]615这段文字说明两个问题:(1)《管子·四称》在一定程度上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其证据有二:第一,“徐伯”即徐偃王,他以好行仁义著称。对此,张固也考证道:“篇中(指《管子·四称》)最引人注意的是,四段管子之言都是用‘夷吾闻之于徐伯曰’的口气引出。……《荀子·非相》《韩非子·五蠹》及汉人多称徐偃王好行仁义,其时代诸说有异,韩非称为楚文王所灭,则略早于管仲,与齐联姻之徐君当为其子,或即此所谓徐伯。如果其说可信,则此篇中带有一些早期儒家的气息,就不足为奇了。”[24]242“徐伯”有可能为徐偃王,而徐偃王以好行仁义著称。《管子·四称》中以“吾闻之于徐伯曰”引出“有道之君”以及后面的“无道之君”“有道之臣”“无道之臣”,这明显受到先秦儒学的影响。第二,文中出现的“圣人在前,贞廉在侧,竞称于义,上下皆饰”“形正明察,四时不贷,民亦不忧,五谷蕃殖”,与先秦儒家提倡的贤人政治、重仁义、重道德修养等主张类似,由此可以看出其在一定程度上受儒家文化影响。(2)《管子·四称》虽受儒家文化影响,但没有儒学化的倾向。这主要表现为:第一,“敬其山川、宗庙、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与《管子·牧民》篇中的“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的意思相同,这与管仲的治国思想一脉相承。第二,从目录的编排来看,“《小称》《君臣》上下与此篇编在一组,而同为论述君臣问题的《七臣七主》不与焉,疑亦由于此处诸篇都有浓厚的儒家气息”[24]243。第三,文中的“外内均和,诸侯臣伏,国家安宁,不用兵革”“受其币帛,以怀其德,昭受其令,以为法式”的言论与《国语·齐语》《管子》“三匡”、《史记·齐太公世家》等典籍中有关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中原的史实有密切关系。由此可证《管子·四称》“有道之君”的记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其主旨仍为管仲及其后学思想的发挥。这与清华简《管仲》篇的儒学化倾向形成鲜明的对比。
综合上文可知:《管仲篇》描绘的齐桓公、管仲形象是品德修养与治国平天下兼顾的儒家内圣外王的典范,与传世文献记载的齐桓公和管仲形象却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两点:其一,齐桓公和管仲在外王方面堪称典范,也就是说,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建立了春秋首霸的不朽功业。对此,不但《国语》《左传》《史记》以及《管子》等典籍中都有详细记载,而且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也大加赞赏。《论语·宪问》记载了孔子对齐桓公和管仲建立的功业进行了高度的评价:“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10]191“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10]192其二,齐桓公和管仲,尤其是齐桓公的道德修养不值得后人提倡,更不是修身的楷模。《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桓公好内,多内宠”[23]1493,《管子·小匡》记载齐桓公自认为有三大缺点,即好田猎、好酒、好女色,其嗜好程度足以影响政事[14]446。可见传世文献既肯定了齐桓公和管仲的霸业功绩,又指出其道德修养方面的种种缺陷。而《管仲》篇则通过齐桓公问、管仲答的对话形式,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典型的儒家内圣外王的君、臣形象,因而具有明显的儒学化倾向,这可从重视学习,重视“人道”, 承、辅的设置以及有道之君、无道之君等四个方面得到证明。这充分说明清华简《管仲》篇不但“包含了较多阴阳五行的思想”[6]89,而且包含了许多儒学思想,并且出现了明显的儒学化倾向。《管仲》篇儒学化倾向使我们在使用时更要注意辨别其所记载史料的真实性、其学派倾向以及和以《国语》《史记》《管子》等为代表的传世文献的区别和联系。
[1]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下册[M].上海:中西书局,2016.
[2]清华大学出土文献读书会.清华六整理报告补正[DB/OL].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2016-04-16)[2017-07-17].http://www.ctwx.tsinghua.edu.cn/ publish/cetrp/6831/2016/20160416052940099595642/20160416052940099595642_.html.
[3]子居.清华简《管仲》韵读[DB/OL].中国先秦史,(2017-01-14)[2017-07-17]. http://xianqin.byethost10.com/2017/01/14/363.
[4]清华六《管仲》初读[DB/OL].简帛网,(2016-04-19) [2017-07-17].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 tid=3348&page=4.
[5]李松儒.《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之《管仲》字迹研究[J].书法研究,2016(4).
[6]刘国忠.清华简《管仲》初探[J].文物,2016(3).
[7]皇侃.论语集解义疏[M]//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8]熊公哲.荀子今注今译[M].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1.
[9]李学勤.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0]李学勤.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1]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2]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69.
[13]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36.
[14]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5]郭沫若.青铜时代[M]//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63.
[16]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7]庞朴.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M].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76-77.
[18]李学勤.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9]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管子集校[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112.
[20]钟肇鹏,孙开泰,陈升.管子简释[Z]//齐文化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69.
[21]范晔.后汉书[M].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897.
[22]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3:54.
[2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4]张固也.《管子》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6.
2018-05-23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管子治国理政思想的传承与发展研究”(17CLSJ03);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子治国理政智慧的历史维度研究”(J17RA071)。
张杰,男,山东理工大学《管子学刊》副编审,副主编,现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张艳丽,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8.04.01
B226.1
A
1004-4310(2018)04-0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