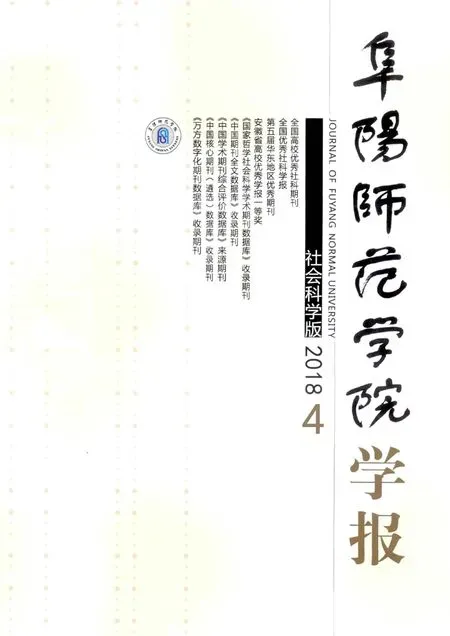班昭《东征赋》女性意识探微
叶 月,王启才
班昭《东征赋》女性意识探微
叶 月,王启才
(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班昭不仅是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位女史学家、女教育家,也是一位女作家。在礼教社会下,女性很难与旅行产生联系。永元七年,班昭随子赴任,著有《东征赋》。《东征赋》作为东汉女性所写的一篇纪行赋,其在视角、景物描写、取材用典,感情抒发等方面,都渗透着独特的女性意识。探讨《东征赋》女性意识形成的原因,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对于全面认识班昭,推进班氏家族、辞赋、旅游文学、女性文学等的研究,均有助益。
班昭;《东征赋》;女性意识;意义
班昭(约公元49年—120年),“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1]2 238,范晔称其“博学高才”,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史学家,其兄班固著《16H21H21H21H汉书》,八《表》及《天文志》未竟而卒,班昭奉旨入东观藏书阁,续写《汉书》;也是一位著名的女教育家,被后世奉为“女圣人”,东22H22H22H汉和帝多次召班昭入宫,让皇后贵妃拜其为师,23H23H23H邓太后临朝后,曾参与政事,其《24H24H24H女诫》对后世影响很大。除此之外,班昭还是东汉有名的女作家,《后汉书·列女传》录其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共16篇,《隋书·经籍志》录《班昭集》3卷,今多亡佚,赋、颂可考者,惟有《东征赋》《大雀赋》《针缕赋》《蝉赋》(残)、《欹器颂》等,其中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东征赋》。
《东征赋》系模拟乃父班彪《北征赋》而作,全文不长,仅610字,因昭明太子25H25H25H萧统编入《文选》,幸被完整保存下来。李善注引《大家集》曰:“子穀,为陈留长,大家随至宫,作《东征赋》。”又引《流别论》曰:“发落至陈留,述所经历也。”[2]127该赋作于永元七年(公元95年),班昭时年46岁,主要写她随儿子26H26H26H曹成去陈留赴任沿途的所见所感,以及离开京城的悲伤与长途跋涉之劳苦,并缅怀先贤,体察民难,最后教导儿子洁身自好、坚守正道,敬业慎行。
《东征赋》是汉代纪行赋的代表作,目前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作年考证、主旨及文学史意义上,因其文学性不太突出,不少辞赋论著仅把它作为从班彪《北征赋》到蔡邕《述行赋》之间的过渡,或一笔带过,对于文中所渗透的女性意识,台湾学者郭苑平在《女旅书写中的时间、空间与自我追寻——重读班昭<东征赋>》一文,将其称为“看不见的风景”,并认为这是“女性旅者的局限”[3]98,个中原因,未予深究;而其他论著,鲜有提及。
所谓女性意识,实际上就是关于女性的观念。法国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把女性作为屈从的一方,并界定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载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4]23乐黛云认为,女性意识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是社会层面,从社会阶级结构看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第二是自然层面,以女性生理特点研究女性自我,如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经验;第三是文化层面,以男性为参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独特处境,从女性角度探讨以男性为中心的主流文化以外的女性创造的‘边缘文化’及其所包含的非主流的世界观、感觉方式和叙事方法。”[5]1
“中国历代的女性意识还植根于中国历史的土壤,是中国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以及小农意识的产物,它集中体现为男尊女卑的轻视女性的价值观和束缚女性的道德礼教观。”[6]1早在《易经》中就有崇阳卑阴的倾向,但先秦女性还有原始自由的一面。到了汉代,受儒术独尊和封建礼教的影响,女性开始有了规范与约束,董仲舒《春秋繁露·天辨在人》曰“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礼记·郊特牲》曰“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男尊女卑、“三从”之规,加之班昭《女诫》“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德的提出,封建女性的道德规范基本形成,女性已失去了自由与地位。尽管如此,汉代也是封建女性意识觉醒的关键期,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中坚贞勤劳的秦罗敷、《古诗为焦仲卿妻所作》中刚烈不屈的刘兰芝,都是文学史上动人的女性形象。刘向编著《列女传》、班昭著《女诫》、蔡邕著《女训》,范晔《后汉书》独创“列女传”体例,女性教育与规范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女性的社会角色更加清晰。
作为汉代才女的代表,班昭既是女德规范的遵循者,又是制定者,其作品无疑具有典范意义。在封建礼仪制度下,女子很少出门,很难与旅行创作产生联系,然而班昭不仅出行,还留下名篇,所以本文通过纵横比较,探析《东征赋》所透露出来的女性意识,就别有一番意义。
一、 《东征赋》女性意识的体现
(一) 女性视角下独特的景物描写
《东征赋》在文体上属于纪行赋,“征”者,行也。从西汉末刘歆《遂初赋》开始,纪行赋在东汉蔚为大观,后代赋家对其程式多有论述。马积高《赋史》说:“这种以征途为线索的写法,虽略仿屈原的《涉江》《哀郢》,而历举途中各地掌故以讽喻世事,则非屈原赋所有,故为创格。”[7]80王琳《简论汉魏六朝纪行赋》将这种“创格”归纳为两点:1.记述与经历之地有关的人文掌故;2.摹写经历之地的山水景观。冯小禄《汉赋书写策略与心态建构》书中又将其概括为“地—人—史—景”[8]144。由此可见,对沿途风物景观的描写,睹物思人、即景抒情是纪行赋的一大特色,然而将班昭《东征赋》与其他男性作家的纪行赋比较,不难发现其独特之处。如下表所示:

文章出处作者篇名路线景物描写 《全汉文》刘歆《遂初赋》太行山—天井关—黎侯旧居—高都—五原 薄27H27H27H涸冻之凝滞兮,茀溪谷之清凉。漂积雪之皑皑兮,涉凝露之隆霜。雁邕邕以迟迟兮,野鹳鸣而嘈嘈。望亭隧之皦皦兮,飞旗帜之翩翩。回百里之无家兮,路修远而绵绵。 《全后汉文》班彪《北征赋》长安—瓠古玄宫—云门、通天台—郇邠—赤须—义渠—泥阳(班氏祖庙)—彭阳—安定—长城—高平 阝齐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风猋发以漂遥兮,谷水灌以扬波。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皑皑。雁邕邕以翔兮,鹍鸡鸣以哜哜。游子悲其故乡,心怆忄良以伤怀。 《全后汉文》班昭《东征赋》 洛阳—堰师—成皋—荥阳—卷县—原武—阳武—封丘—平丘—蒲城—长垣 历七邑而观览兮,遭巩县之多艰。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皋之旋门。既免脱于峻崄兮,历荥阳而过卷。食原武之息足,宿阳武之桑间。涉封丘而践路兮,慕京师而窃叹。 《全后汉文》蔡邕《述行赋》京洛—大梁—中牟—圃田—管邑—荥阳—虎牢—巩县蔥山—墰坎—洛水—巩都—偃师—返回 寻修轨以增举兮,邈悠悠之未央。山风汩以飙涌兮,气懆懆而厉凉。云郁术而四塞兮,雨濛濛而渐唐。
由上表比较可知:1.四位赋家都历经多地,所以不是短时一地的旅行,空间处在不断变换中,他乡的景物不断映入眼帘;2.与三位男性作家的辞赋相比,《东征赋》中的风物景观总被一笔带过。爱德华·W·索亚认为: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在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和居所的生产。而在这种生产过程中,人类主体总是要与环境产生复杂的脉络联系,其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9]122。虽然作为空间的一份子,但是传统的女性没有男性那么容易就与陌生的环境建立联系;3.蔡邕与班昭行进方向虽相反,但路线有大量的重合,然二人在景物描写的数量上,相差甚多。4.班昭对路途中地标的叙述,比其他三位男性清晰,在旅途中班昭显示出女性特有的敏感。
(二) 彰显女性意识的取材与用典
从汉代四篇纪行赋作者看,多是史学家,对历史典故熟稔,均采用由地及史的书写模式,应该说,班昭的事功意识也是比较突出的,但她与其他三位男性作家相比,取材与用典明显不同。男性作家多着眼于外在的建功立业,苍生苦难,民族兴衰,抒发忧愤之情、兴亡之感,视野开阔,气魄较大,如刘歆借晋人自毁公族以致亡国等史实,抒发了忧亡之感;班彪用义渠王秦宣太后之乱、蒙恬筑长城御匈奴、汉文帝以德怀边绥远等典故,表达了对乱世的感叹;蔡邕更是在行程中从夏王开始,追述了佛肸为赵简子管理中牟、管叔蔡叔勾结殷商后裔作乱、信陵君杀晋军主帅夺兵权等历史故事,抒愤兴叹。《礼记·内则》曰:“男不言内,女不言外。”作为女性,班昭对攸关国家命运的大事关注较少,抒发的也不是民族兴亡的感慨,而是关注个体内在的道德修养以及儿子的仕途成长,《东征赋》征引孔子困厄、子路勇义、蘧伯玉之贤能等典故,都是君子楷模,做人的典范,表现了一位随子远行的母亲对爱子的期许,抒发的是一种慈母情怀,这是一种典型的女性身份,女性意识。
(三) 缠绵细腻的女性感情抒发
《礼记·内则》曰:“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早年寡居、在深宫任教的班昭,“夫死从子”,因儿子陈力就列、外任就职,不得不选择跋山涉水,抛头露面,其情何堪?纪行赋本祖于骚,抒情乃题中之义,但情感书写得那么细腻缠绵,那么复杂多变,那么悲怆无奈,则非女性作家莫属,男性实有所不及!《东征赋》精心选择良辰吉日出行,说明她对这次“随子东征”多么重视,可随着540里旅程的展开,作者的感情一波三折:先是抒发离京时难舍难分、身不由己的悲情,以致夜不能寐,借酒浇愁;再抒发风餐露宿、长途跋涉之苦情;进而过匡、卫等地,抒发缅怀先贤的怀古之情;还有看到荆棘丛生的蒲城23H28H28H28H丘墟,对“农野之民”油然而生的怜悯之情;最后“乱”辞又直接抒情:既然寿夭在天、富贵难求、吉凶难料,那就只好敬慎谦约、清静少欲、听天由命吧!欲求不得,欲争不能,欲罢不甘,心有千千结,苦闷无奈之情又喷薄而出。辞赋作品如此动情,如此缠绵细腻地抒情,《东征赋》可谓尽显女性作品的心路历程,个性特点。
二、 《东征赋》女性意识的成因
《东征赋》凸显出女性意识,仅仅是因为出自女性之手吗?是,又不全是。下面试探讨其女性意识的成因。
(一) 写景较少,暗合女性写作心理
比较四篇纪行赋,《东征赋》写景最少,为何会出现景物描写的缺失?在汉代,有目的的休闲旅游尚未产生,山水尚未进入人们的审美流域,描写景物仍是为了抒情的需要,写与不写,写多写少,取决于作家的个性与客观需要。《东征赋》写景较少当有两种情况:其一,恪守封建礼教,女性在征程中一路端坐车内,未赏风景;其二,对风景“视而不见”。班昭《女诫》要求女性“耳无途听,目无斜视”,她是否真的做到了这一点?答案是否定的。试想,一位母亲送儿子去赶任,实在没有必要在亲人面前恪守这些礼节,细读文本,也的确如此。“望河洛之交汇,看成皋之旋门”“聊游目而遨魂”,“望”“看”直接写出了作者对异域景观的关注。相比直接的“望”“看”,“游目”一词则更富意味。李善将其注为“楚辞曰:忽反顾游目”[2]127,而下一句即是“将往观乎四荒”,可见“游目”是为了“观四荒”,暗指作者仍牵挂故乡,不忘国事。如《兰亭集序》中紧跟“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一句的,是“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王羲之在纵观天地万物后,舒展眼力,尽情享受视听的乐趣。所以,俯仰观览,是“游目”,“游目”既往复游驰,心亦徘徊驰骤,游目即游心。由此可见,“游目”一词是旅游景观进入游者视野的见证,班昭并没有端坐车内“目无斜视”。既然如此,又为何对沿途风景“视而不见”呢?
1.女性生理上的认知特点
环境心理学认为,男性有较好的视觉和空间能力,男性在绘制认知地图方面优于女性。在同样的旅程中,女性更强调街区和地标,而男性更关注路径结构[10]76。所以,在女性认知地图上地标之间的路径并不多,但地标很多,这是女性在认知上的特点。显而易见的是,同样历经多地,只有班昭在文中明确“历七邑”这一准确数字,然纵观刘歆、班彪、蔡邕等男性赋家的纪行赋,其文中均没有如此明确的记录,这更证实了女性对地标的关注。
环境心理学还认为:男性似乎在寻路上更为自信,而女性在寻路时表现出的焦虑水平较高。因为过去和未来都不存在于眼前的地理景观中,面对这种与过往一切断裂的茫然,男子尚且有“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11]17的愁苦,那么身为女性的班昭,肯定会比男子有更多的茫然,而焦虑茫然,会使人的心智下降,对外在风景的关注度降低,视野变窄,以致对外在风景“视而不见”。
2.女子善怀的心理机制
中国自古就有“女子善怀”的创作特点,《诗经·载驰》云:“涉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众稺且狂。”[12]54许穆夫人对卫国的思念眷恋、对卫人阻挠的愤怒,奠定了《载驰》的感情基调。与男性相比,女性更易动情的心理机制,实际上是为自己的写作找到了内在动力。班昭之前,其姑祖班婕妤即善抒怀,《玉台新咏》曰:“昔汉成帝班婕妤失宠,供养于长信宫,乃作赋自伤,并为怨诗。”[13]24班昭亦如是,《东征赋》满是愁思,如“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怆悢而怀悲。明发曙而不寐兮,心迟迟而有违。酌樽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女性对以自我中心的生活环境的改变,较男性更为敏感,所以,班昭悲愁为之“不寐”,对路途的直接感受,就是“历巩县之多艰”!又因地及人,生发出怀古、怜悯等情感。
3.女性抒情所托之物不同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曰:“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14]49冯小禄《汉赋书写策略与心态建构》一书指出:“述行类汉赋,远宗屈原《离骚》《九章·涉江》《哀郢》等作的放流漂泊之思,而直接抒发被迫迁徙流窜、辗转季世风尘的念时忧生悲慨。”[8]145纪行赋不仅祖述楚辞,且在书写手法上与楚辞相类。王逸《离骚经序》指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15]3可见,汉代辞赋在书写上讲究引类譬喻、情景相合,其空间景物的书写是基于抒情的需要。正如约翰•伯格《观看之道》一书所说:“我们从不单单注视一件东西,我们总是在审度物我之间的关系。”[16]5班昭从小饱读诗书,可能达到了“读万卷书”,续写《汉书》,精通天文,时常入宫给皇后贵妃授课,其广博的学识就是证明,但她毕竟是一位女性,抛头露面,“行万里路”、欣赏祖国大好河山的机会,也不会很多,加之女性纤细情感的抒发,所寄托之物,多是具体有形的物件,如失宠的班婕妤,作《团扇歌》,班昭本人写过《大雀赋》《针缕赋》《蝉赋》等,所以,一旦有机会出门远行,其感情的寄托物,一时难以与大的山川风物联系起来,达到“神与物游”的境界,故而她能准确描述针缕“熔秋金之刚精,形微妙而直端”的特点,却难于对沿途风景进行描摹。
再者,班昭《女诫》说:“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旅行是一种空间迁移,季节、景物、心情都会随之变化,而“刚性美是流动的,柔性美是静的”[17]180,所以,流动的行程中进入眼帘的,多是壮阔的景观,“壮阔的景观承担了如此迫切而沉重的问题”[18]173,刘歆等人可以登山临野,触目伤怀,借北方的苍茫辽远、雄阔凄怆,来表达其哀世叹乱之情。宇宙的力量可以移山倒海……莫测的天气、变换的路径、更迭的场景,班昭若是将父女、母子之情喻于其中,无异于方枘圆凿,情景不谐。所以,班昭将沿途所见之景一笔带过,是其自觉选择的结果,这也是其女性意识有所觉醒的表现。
(二) “效法先君”“重在训子”,凸显“母师”形象
关于班昭《东征赋》的创作主旨,有人认为是“效法先君”,也有人认为是“重在训子”[19]556,然而无论是哪种情感,都是女子柔情的抒发,凸显的是“母师”(1)形象。
“文艺作品都是把一种心情寄托在一个或数个意象里。”[17]180与景观选取、描写所体现出来的女性特有的生理和心理机制不同,《东征赋》典故的使用体现了女性的自觉担当意识。
班昭《女诫·序》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她才高命苦, 早年丧父,5岁时,班彪去世;中年丧夫,丈夫早卒,《后汉书·班昭传》曰:“世叔早卒,有节行法度。”朱维铮《班昭考》认为曹寿“早卒”,是在班昭奉和帝诏入东观续补《汉书》之前,即永元四年(公元92年)之前[20]12。永元四年,在班氏家族、班昭人生当中又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班固因“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受牵连被捕死于狱中。《后汉书·班彪传下》曰:
及窦宪败,固先坐免官……及窦氏宾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系固,遂死狱中。时年六十一。
袁宏《后汉纪·和帝纪上》曰:
(永元四年)诏收宪大将军印绶……宪、笃、景皆自杀,宗族免归本郡……于是何敞、班固免归家,敞子与瑰善,固党于窦氏也……及宪宾客皆被系,兢因此捕系固,遂死狱中。
班固之死的直接原因,是洛阳令种兢为报己被班固家奴醉骂之仇,根本原因则是其溺爱、疏于管教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的结果。其兄班固冤死,班昭的人生从此进入了转折点,摆在她面前的是残酷的现实:由于另一兄长班超远在西域,他要撑起班氏家族的一片天地,要承担子女以及班氏家族后代的教育任务;受诏续写《汉书》;担任皇后贵妃的教师,时常要到宫中授课……所有这些担子先后向她压来,身为柔弱的女性,她必须像男性那样坚强。特别是儿子曹成首次外任,责任重大,又无人可指引,她不能袖手旁观,也不能一味的“卑弱”,而是勇敢地承担起了“母师”的责任。
关于其子曹成,有关典籍的记载如下:
(永元七年)夏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帝引见公卿问得失,令将、大夫、御 史、谒者、博士、议郎、郎官会廷中,各言封事。诏曰:“元首不明,化流无良,政失于民,谪见于天。深惟庶事,五教在宽,是以旧典因孝廉之举,以求其人。有司详选郎官宽博有谋、才任典城者三十人。”[1]396
齐相子穀,颇随时俗。曹成,寿之子也。司徒椽察孝廉,为长垣长。母为太后师。征拜中散大夫。子榖即成之字也。[21]126
由以上记载可知,班昭教子有方,儿子曹成德才兼备,首次外任即担任长垣长,后来官至齐相。关于曹成首次外任的背景,《后汉书》交代得非常清楚,永元七年因日食出现,和帝下诏求贤,弥补政阙,所以曹成东征任职本身就意义平凡,他不仅肩负着安抚百姓、改善统治者形象的神圣使命,而且要公正廉明,取信于民,以维护汉朝的稳定。
既然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就不能令朝廷失望,就得辅导儿子,助其一臂之力,让其成长成熟,堪当大任。这从班昭注其兄《幽通赋》也可以看出来,其注曰:“言己孤生童,微陋鄙薄,将毁绝先祖之迹,无阶路以自成也。”“言己安静长思,不欲毁绝先人之功迹。日月不居,忽复大远。”在注中她除了明志外,还兼训其子。又,班昭《女诫》曰:“战战兢兢,常惧黔辱,以增父母之羞。”正与《东征赋》中“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相呼应,这些都表明班昭训子齐家之自觉,担子之重。
既然齐家训子责无旁贷,班昭就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训教儿子,在《东征赋》中,她对眼前的山河胜景、对历史上的大事件关注不多,兴趣点全集中在训子上。她不顾跋山涉水颠沛之苦,精心选择孔子、子路、蘧伯玉等的美德、贤仁典故,告诫儿子为官应具之德、应做之事,进德修业,不负重托。
波伏娃《第二性》说,母子关系是一个母亲整个生活的一部分,且认为“如果说她身为妻子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人,那么她作为一个母亲却是这样的人:孩子就是她的快乐,就是她生活的意义”[4]261。所以《东征赋》有“且从众而就列兮,听天命之所归”“唯令德为不朽兮,身既没而名存。惟经典之所美兮,贵道德与仁贤”等训子之语。方伯海曰:“前赋《北征》,重在悯乱;此赋《东征》,重在训子。题目相似,而用意不同。”何义门亦云:“(诫子之词)儒者之言,不愧母师女士矣。”[19]353
以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勇于担责的“母师”形象。与汉代的其他女性相比,班昭的表现令人钦佩。虽然她在《女诫》中倡导卑弱、顺从,可她实际表现出的,却是不屈与坚强。不似其失宠的姑祖班婕妤《团扇歌》“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的哀怨,也不似乐府民歌《古诗题为焦仲卿妻作》中刘兰芝“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无论是班婕妤的哀伤,还是刘兰芝的自杀,都表现了女性面对生活挫折时的消极和逃避,相比之下,面对生活的重重打击,身为女性的班昭,其“母师”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进取意识,委实令人赞叹!
三、 认识与评价
客观地说,班昭的《东征赋》从命意、结构、语词都存在着对其父班彪《北征赋》的模拟现象,加之该赋景物描写较少,文学色彩不足,在中国辞赋史、文学史上的地位不是很高,这是汉代乃至中国辞赋史、文学史不重视它的主要原因。“横看成岭侧成峰”,但若换一种角度,该赋因出自女性之手,在内容上、风格上别具一格,其价值与意义亦不容轻忽。《昭明文选》只选三篇纪行赋,把该赋与其前班彪《北征赋》、其后潘岳《西征赋》并列,作为人们学习的典范,是很有眼光的。
班昭的《东征赋》在中国辞赋史、中国女性文学史是有开拓贡献的。在汉以前,只有在上层社会中极少数女性因家庭等原因,才有受教育的机会;能留下作品的,寥寥可数。物以稀为贵,因为难得,所以珍贵。再就《东征赋》作品本身看,其凸显的女性意识,丰富的史学修养,清晰的线索,典雅渊懿的语言风格,特别是其题材由渲染帝国声威向书写个人日常转化,加之议论手法的带入,对促进汉大赋在内容与风格上向抒情小赋转变,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从纪行、旅游文学角度看,《东征赋》作为汉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女性旅行之作,其价值弥足珍贵。传统中国的女性被禁锢在闺房里,抛头露面少,与旅行联系更少。胡锦媛指出:在家庭中缺席的是男性,而在旅行中缺席的则是女性,尤其在传统的礼教社会[22]269-286。因与外界接触交往不多,女性作家的视野也大受限制,表现在创作中,大多是反映婚姻家庭生活,抒发一己爱怨之情,很少触及闺房以外的领域。班昭则不然,她将女性与旅行联系起来,开拓了女性题材的表现领域。作为文学史上女性旅行者的先驱,班昭在继承前人纪行赋书写传统的同时,向人们展示了女性在旅途中独特的视角和心理特征,在这种女性意识的观照下,“女人”被发现、被解读、被重视,女性文本独立于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得以凸显,同时也为男性作品多了一种比较视角与参照系。
从文献角度而言,《东征赋》只有短短610字,却化用了《周易》《尚书》《毛诗》《楚辞》《左传》《老子》《文子》《论语》《荀子》《韩非子》《鶡冠子》《淮南子》《韩诗外传》《史记》《汉书》《礼记》《法言》《孔子家语》以及《神女赋》《长门赋》等20余部经典的语词,自然流畅,词若已出,显出其惊人的经学素养,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
从班昭出现的历史文化意义看,“女圣人”“旷世才女”班昭,续写《汉书》、作《女诫》《东征赋》,为兄(班超)上书,为兄(班固)注《幽通赋》,像代父从军的花木兰,经典黄梅戏《女驸马》中冒死救夫、偶中状元的冯素贞一样,巾帼不让须眉,都是古代女英雄的代表或化身,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她们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女性的自主意识与奋斗精神,彰显了女性身上特有的魅力与价值。
最后,《东征赋》所透露出的女性意识,可以补历代班昭《女诫》研究之缺憾,使人对班昭有更全面更丰富更真实的认知,可以推进班氏家族、辞赋、旅游文学、女性文学等领域的研究,特别是班昭渊博的学识,高尚的人格,面对生活坎坷时由柔弱转化出的刚毅品格、担当意识、进取精神,以及对后代子女教育的高度重视,仍值得今人学习和借鉴。
当然,班昭也并非完美无缺,她也有对男性依附的一面,其《东征赋》亦透露出无可奈何的消极情绪,特别是《女诫》,其初衷与客观影响并不一致,对后世女性的发展确有束缚与限制的一面。
注释:
(1)母师:《后汉书》李贤注曰:“母,傅母也。师,女师也。”刘勰《文心雕龙·诏策》曰:“班姬《女诫》,足称母师也。”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萧统.文选[M].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郭苑平.女旅书写中的时间、空间与自我追寻——重读班昭《东征赋》[J].东海中文学报,2008(20).
[4]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M].桑竹影,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5]乐黛云.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J].文学自由谈,1991(3).
[6]吴晓红.中国古代女性意识——从原始走向封建礼教[D].苏州:苏州大学,2004.
[7]马积高.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冯小禄.汉赋书写策略与心态建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9]爱德华·W·索亚.“第三空间导论”——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与想象地方的旅程[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10]保罗·贝尔,托马斯·格林,等.环境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1]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55.
[12]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3]徐陵.玉台新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4]刘勰.文心雕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5]王逸.离骚经序[M]//楚辞章句补注.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16]约翰.伯格.观看之道[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7]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8]阿兰·德波顿.旅行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19]费振刚.全汉赋校注[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
[20]朱维铮.班昭考[J].中华文史论丛,2006(2).
[21]赵岐.三辅决录[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22]胡锦媛.台湾当代旅行文学[C]//台湾旅行文学论文集.台北:五南出版社,2006.
A Probe into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Ban Zhao’s
YE Yue, WANG Qi-ca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37, Anhui)
Ban Zhao is not only a female historian and educator in Chinese history, but also a female writer. In a society of rites, it is difficult to relate women to travel. In the seventh year of Yongyuan, Ban Zhao followed her son to his post and wrote theAs a documentary Fu written by a woman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has the unique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the aspects of perspective, scene description, material use,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so on. It is helpful to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ofand its value and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Ban Zhao;; female consciousness; meaning
2018-04-11
叶月(1987- ),女,安徽淮南人,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王启才(1966- ),男,安徽阜阳人,阜阳师范学院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8.04.15
I207.224
A
1004-4310(2018)04-008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