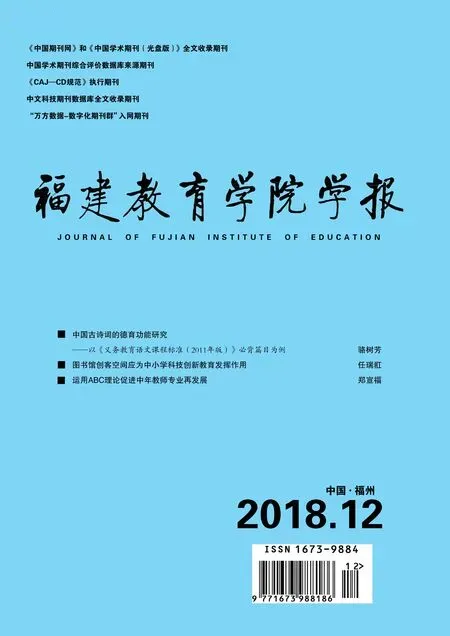唐宋时期杏花意象的发展衍变管窥
——唐宋诗歌杏花意象比较
赖丽青
(福建教育学院语文研修部,福建 福州 350025)
古诗中花卉入诗现象极为普遍。花卉入诗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逐渐发展成为意象。意象是对可感的“实”的具象与虚的情思和意蕴的整合。不过,情思与物象由各自独立到融合是逐步发展衍生而成的。这可以从唐宋诗歌中杏花意象的异同衍变窥其端倪。从有关统计来看,《全唐诗》等唐代文献中,有关杏的诗句有430句左右,专门歌咏杏的诗歌有48首左右。而《全宋诗》中描写杏花或者与杏有关的意象的诗共有104首,其中提及杏的单句作品不胜枚举。[1]这些数据表明,杏花诗歌在唐宋期间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而尤以宋代为最。宋代杏花诗除了量上的增加,内容与艺术形式上也比唐代跃进了一大步。单从杏花由物象到意象的转化来看,唐宋之间的杏花诗就呈现出由客观物态描写向主客观融合的发展趋势,而这一点也是唐宋诗歌杏花意象发展衍变的典型特征。
一、从杏花的美感特征看唐宋诗歌杏花意象的文化内涵衍变
杏花是我国一种普遍栽培的花卉。《夏小正》的记载说明杏花很早就存在,但直到南北朝时咏杏的作品还是很少。到了唐代,随着花卉的观赏性成了主要价值,唐宋时期,吟咏杏花的作品数量逐渐增多。杏花意象在唐初多见于应制诗,偏于客观物象的静态描写。后来在文人诗中也成为一个较常见的物象,且表现方式逐步精细化动态化。宋代因其社会原因,应制诗不被重视,杏花意象在宋代主要见于文人诗中。宋代杏花诗不仅在杏花的色香姿态的外表描写手法更为精巧多样,还拓展了表现的范围。审美情趣由唐诗的绚烂复归于平淡。
(一)杏花在唐代应制诗中的美感特征
初唐诗中的杏花意象较多见于应制诗。应制诗是君——臣语境中的言说的一种政治话语,唐朝是其发展成熟期。由于应制诗是在特定语境下的言说,为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应制诗通常金玉满眼、文藻宏丽、堆砌华美,多以大量的名物来堆积烘托出一种宏大的皇家气派。尤其是唐朝前期的应制诗常常雕章镂句、五彩黼黻、精细缛丽、辉煌耀目、珠光宝气、,喜庆祥和。[2]初唐诗人宋之问就写有《奉和立春日侍宴内出剪彩花应制》:“金阁妆新杏,琼筵弄绮梅。人间都未识,天上忽先开。蝶绕香丝住,蜂怜艳粉回。今年春色早,应为剪刀催。”从诗中的“金”“琼”“绮”等修饰语词,可以看出应制诗雕章镂句、富丽堂皇的特点。在这种语境下,诗中的“新杏”只是作为一种名物起雕饰烘托的作用。由于应制诗的宫廷色彩,其命题写作的特点造成了代笔捉刀的束囿,用意也多所限于歌颂功德、粉饰太平,受此影响,这里的“新杏”偏于客观物象,缺乏个人情感,没有寓意和深刻思想内蕴。至于杏花之所以入于应制诗,则与杏是唐代园林植物景观中的重要花木有关。且作为早春的应景花卉,杏花艳丽符合宫庭诗喜庆华美的热烈气象,属于可供烘托宏大的皇家气派的名物之一。
(二)杏花在唐宋文人诗中的美感特征及其衍变
唐宋诗人对杏花的审美大都集中在对杏花色香姿态等形象的审美,以及对建立在杏花自然属性美基础上的,体现了杏花的风格、神态和气质的神韵美的审美。由于诗人对杏花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其笔下对杏花的描绘比较客观真实。着眼于杏花色香姿态的形象与神韵并加以艺术表现的诗歌,主要见于文人诗。虽然唐宋文人诗中的杏花意象都重视杏花的观赏价值,宋代杏花诗在内容与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拓展提升,比较而言,着重于杏花美感特征的诗还是唐代的比例更大。只不过相当部分诗歌的描写手法较简单,多是白描。如王维《春中田园作》“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就是以白描的方式描绘了早春时节杏花开放,整个村子掩映在白茫茫的杏花中的景象。王涯的“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满园深浅色,照在绿波中”同样寥寥数笔,写出了早春江边成林杏花刚刚开放,满园杏花色彩有深有浅与江水相映成趣的美景。这些杏花描写虽然简练传神,但大多止于色彩、形态的整体观感,相对比较粗略。从杏花的神韵来看,关注的也主要是它的清新、鲜嫩、自然、美丽的风致方面。
杏花描绘的精细繁采是随着杏花类咏物诗涌现而促成的。如司空图《村西杏花二首》:“薄腻力偏羸,看看怆别时。东风狂不惜,西子病难医。肌细分红脉,香浓破紫苞。无因留得玩,争忍折来抛。”这里的“肌细分红脉,香浓破紫苞”就是在形态、香气等方面的细致描绘。温庭筠《杏花》:“红花初绽雪花繁,重叠高低满小园。”这两句写杏花初绽时颜色艳红,等到繁花盛开后就变得如同雪花一般洁白;重重叠叠的花枝,高高低低地布满了小小的院落。不仅写出了小园杏花盛开时生机盎然,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色,而且写出了杏花由初开到盛放时颜色的变化,足见诗人观察细致,下笔具体而微,描绘准确,细节典型。概而观之,杏花诗中的杏花描写在唐朝明显存在一个由粗疏到精细的过程。
与唐代相比,宋代文人之间相互酬唱杏花之作逐渐增多,不少诗描写了诗人与友人对酒赏花的欢快愉悦之情。如梅尧臣的《依韵和王几道涂次杏花有感》、文天祥的《次约山赋杏花韵》,就是文人间的互相唱和。[1]宋诗在唐诗的基础上进一步细致生动地描绘杏花的色、香、姿态,诗人将其作为需要深入观察的对象,创作时灵活运用拟人、移情、联想、象征等多种表现手法,致使杏花在宋代诗人笔下更是各具特色。如王禹傅《杏花七首》中的“红芳紫兽怯春寒,蓓蕾粘枝密作团”,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描写杏花未开时娇羞的姿态。“陌上纷披枝上稀,多情尤解扑人衣”运用比喻的手法描写杏花凋落时的独特之态。王安石的《杏花》更是构思新颖别致:“石梁度空旷,茅屋临清炯。俯窥娇娆杏,未觉身胜影。嫣如景阳妃,含笑堕宫井。怊怅有微波,残妆坏难整。”这首诗描绘了水波由静到动以及花影在这过程中的变化,既有杏花的身姿,也有临水的倒影,交相映衬,可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此外,受儒释道思想影响,宋代也出现了一些追求理趣、思理绵密的杏花诗。如叶绍翁的《游园不值》“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所写的杏花就是蕴含理趣的杏花。比较而言,宋诗中的杏花更多泛着幽韵冷香,在宋诗不张扬情感的整体特性下,其审美情趣由唐诗的绚烂复归于平淡。
二、从情思意蕴看唐宋诗歌杏花意象的文化衍变
意象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有意味的艺术形象。从杏花意象内蕴的情思意蕴来看,杏花物象与诗人情思意绪的联系存在由唐初的隔离到宋代的融合,由物象到意象的较为明显的衍变过程。
(一)即物达情的思想情感内蕴及其衍变
唐代的杏花诗多数是着眼于杏花的色香形态描写,但不少诗歌与起兴手法相结合,触物起情,即物达情,开始了由物象向意象的文化生成。尤其盛唐时期正处于咏物诗向着即物达情、深婉蕴藉的方向发展的阶段,咏杏诗即物达情的运用推动了杏花诗从静态观赏而感情游离于杏花的表现方式,发展到通过对杏花的具体描写而注入思想感情的表现方式。这与盛唐时期的咏杏诗人走出了魏晋至初唐的宫廷园林或皇家禁院,身份由原来以宫廷文人或文学侍从为主转向以士大夫为主有关。
虽然主观思想意绪因诗人与时代的不同而使杏花意象有不同的内在意蕴,杏花物象与情思的不同整合也常常同时并存,总体上看依然呈现出从游离到情景结合再到情景交融的衍变趋势。具体地说,应制诗中的杏花意象多是静态观赏而游离于诗人情感的。情景结合的杏花意象可以储光羲的《钓鱼湾》为例:“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草木葱茏、翠色欲流的钓鱼湾岸边,杏花繁盛,纷纷飘落,雪白、粉红的杏花,这鲜艳多姿的景象描写的是客观物象,不过这一客观物象,又因后面的“日暮待情人”一句,使得杏花的纷纷繁繁与诗中人物的心情相吻合,衬托了他此刻急切的神情。又如唐朝司空图《故乡杏花》:“寄花寄酒喜新开,左把花枝右把杯。欲问花枝与杯酒,故人何得不同来。”此诗寄情于花、酒,欣喜于花的盛开,触物兴怀,想起故人,问询花枝与杯酒:故人为何不能一起来?该诗花与情相应,但杏花在此主要是一个引发感兴之物,融合度不高。情景相融则可以王安石的《北陂杏花》为代表:“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作尘。”诗人以池塘边的杏花即使被春风吹落成雪,也胜过落在南边小路上被碾作尘土,表达了超俗孤傲的情怀,这是他的心境写照。杏花意象在这里以托物寄兴的方式直接将诗人的情感意绪付于杏花,真正实现了物象与诗人情怀的融合。
以即物达情方式生成的杏花意蕴较为丰富,有针对盛开的杏花的,有针对飘零的杏花的,主观感情上有红颜易逝、年光渐迈的悲慨,有怨别离恨、羁旅愁思的慨叹,也有品质的比附与褒贬。例如唐代诗人戴叔伦的《苏溪亭》就是借暮春花草烟雨抒写美人怨别离恨之情:“苏溪亭上草漫漫,谁倚东风十二阑。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春事晚,杏花寒,明面上写一片迷蒙烟雾笼罩着沙洲,杏花已失去了晴日下的容光,内蕴的思想情感则是感伤游人未归,女子青春消逝,承载着对光阴虚度,年光渐迈的叹惋。宋代诗人欧阳修《镇阳残杏》的诗句“但闻廉间鸟语变,不觉桃杏已开阑。人生一世浪自苦,盛衰桃杏开落间”,也是借杏花衰败来抒发、感叹人生的变幻无常,抒写自己的心境。由此,杏花意象从物态描写以显示春光无限,走向了“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的红颜易逝、失意惆怅、羁旅漂泊、脱俗孤傲的神韵美。
(二)人文品格象征的杏花意蕴衍变
杏花意象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人物形象比类与人文品格象征。在人物形象比类上,杏花最开始是因其娇艳姿容被视为青春少女形象,不过随后就是更常见的以美人形象相比拟。而杏花的艳性、不端庄、易衰易谢特性又将之归入青楼女子与容易变节的凡夫俗子一类,此外也有部分与高尚人格有关,最常见的就是诗人高尚人格的自比。
以女性形象比类来看,唐代白居易《重寻杏园》:“忽忆芳时频酩酊,却寻醉处重徘徊。杏花结子春深后,谁解多情又独来。”就是以杏树的花、果递变来抒发女子花期短暂、时光流逝之感。宋代文人们也喜欢将杏花与女性等意象联系起来。如“独有杏花如唤客,倚墙斜日数枝红”“玉人半醉晕丰肌,何待武陵花下迷”等呈现的就是以杏花比拟美女形象。[1]宋代王安石《杏花》:“石梁度空旷,茅屋临清炯。俯窥娇娆杏,未觉身胜影。嫣如景阳妃,含笑堕宫井。怊怅有微波,残妆坏难整。”也是以景阳妃这一美女形象比拟杏花。
至于杏花女性形象的贬抑定位,唐朝时即已出现,如唐朝诗人薛能《杏花》:“活色生香第一流,手中移得近青楼。谁知艳性终相负,乱向春风笑不休。”杏花有了“青楼女子”的人格象征意蕴,不过此时尚不普遍。到了南宋时期,随着理学的发展,文人的道德品格意识高涨,受“比德”倾向影响,杏花不再作为美好人格的象征,而是作为艳客形象出现,被普遍视为一种薄幸之花。不少诗歌着眼于杏花妖烧艳丽的姿态,将杏花与风月之地、流莺偷宿等意象联系起来,例如“下蔡嬉游地,春风万杏繁”“唯有流莺偏趁意,夜来偷宿最繁枝”等诗句。其余如“林下风流自一家,纵施朱亦不奢华,冷香犹带溺桥雪,不比春风桃杏花”等诗句也充分体现出对杏花的贬抑心态,[2]杏花的人文品格意象由此得到了较为彻底转换,以“红杏出墙”为标识的风情万种如娼妇的形象成为其人文品格象征的一部分。
就非性别特指形象来说,所指常具世事人情的普适性。如罗隐的《杏花》:“暖气潜催次第春,梅花已谢杏花新。半开半落闲园里,何异荣枯世上人?”这是以杏花的开落比类世人的荣枯。再如宋代王禹偁《春居杂兴二首》(其一):“两株桃杏映篱斜,妆点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以有功无过的桃杏与黄莺竟不被春风所容,来隐喻诗人的遭遇,这里的杏花意象就是一个无辜而被贬斥的有功者形象,是诗人的自我投射。而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的 《暮春归故山草堂》:“谷口春残黄鸟稀,辛夷花尽杏花飞。如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诗中这些凋零的杏花,在诗人笔下都成了屈俗变节、易衰易谢、经不起考验、与时浮沉的凡夫俗子了,与代表坚贞高洁的幽竹相比有着天壤之别。[3]
总体上看,唐代诗歌更多关注杏花清新、鲜嫩、自然、美丽的风致,宋代由于伦理道德意识的高涨,由于杏花的生物属性确实很难寄托诗人的理想,反而与青楼、娼妓、变节者等有内在一致性,使得杏花的美丽形象发生了普遍性的意义转换。[4]
(三)“杏”“幸”谐音而来的吉祥美好寓意与文化生成
中国文化中,杏有着“与名俱来”的吉祥寓意功能,“杏”者,谐音“幸”。且南朝任昉《述异记》记载: “杏园洲在南海中,洲中多杏,海上人云: 仙人种杏处,汉时尝有人舟行,遇风泊此洲五六日,食杏故免死。”杏树由此而有仙境之树之称,更加固了其吉祥美好的象征寓意。
杏花吉祥美好寓意还与唐代的科举制度有关。由于杏花是幸运之花,受科举制度强大社会、文化心理作用的推动,人们将杏花与科举相联系,取杏花的幸运吉祥之意,赋予杏花“春风及第花”的称谓,杏花由此有了“春风及第”的科举功名象征之义。这可以从唐代的一些诗歌中看出。如郑谷《曲江红杏》:“女郎折得殷勤看,道是春风及第花。”唐代高蟾《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诗云: “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高蟾的这首诗中的“红杏”所指也与春风得意的新科及第者有关。[5]
综上所述,杏花意象在唐宋时期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在宋代发展到一个顶峰。唐代杏花诗主要专注于杏花明丽清新形象的审美价值,宋代杏花诗无论是数量还是题材内容、内涵意蕴,表现形式,审美认识等都有较大的拓展。由于杏花的艳性、不端庄、易衰易谢特性难以比类高洁品格,杏花的人文品格象征存在从褒到贬的发展趋势,在南宋时期基本形成了杏花的独特象征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