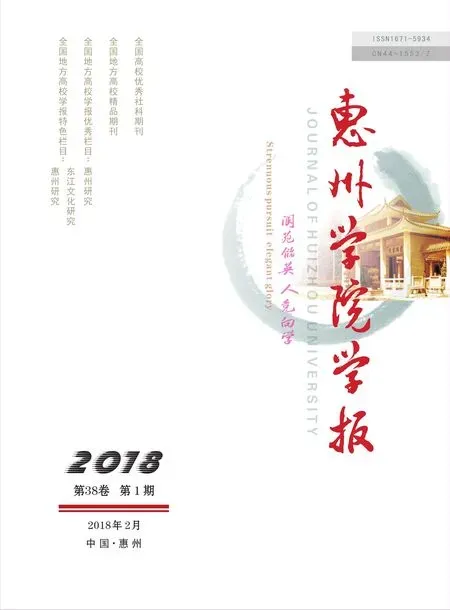明末清初山西士人戴廷栻处世理念与易代思考1
王丹妮
(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广东 广州 510055)
关于明清之际士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遗民、贰臣概念化的区分辨认后的相关研究。而对于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士人来讲,伴随时间推移,身份认同、生活环境、价值体认存在一定的变迁。关于该文的研究对象戴廷栻,笔者不试图去辨析其身份,而是将他置于明清易代时空中去探讨其个体化的精神世界。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主要述及戴廷栻的生平事迹、交游状况、文集的相关信息等问题。文本在试图丰富戴廷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为明清易代北方士人的研究做一些基础性工作。
戴廷栻(1618-1691)是明末清初山西祁县的一位出身官宦家庭的士人。戴廷栻与易代山西名士傅山的关系以及他在易代卓越的文化成是笔者所关注的。文章试图以戴廷栻《半可集》为切入点,通过几个方面的解读,走进这位易代士人的精神世界。
一、为文之道
戴廷栻作为一位地方名儒,他对文章创作有独到见解。戴廷栻“乐道天下之善以传焉,古今忠臣义士孝子烈妇行敦而名不彰者,于公文见之。独以表幽阐微为己任[1]1”,这是对戴廷栻文章创作应该秉持的初衷与担当、书写与传承最精要的概括。
戴氏的好友对戴氏的文章给予了极高评价。作为戴廷栻的挚友,傅山认为“枫仲为文写人物则毕肖其生,摹语句则新脱诸口,叙事断案则活现目前,描画精理则曲尽世情。皆得史汉之精思。而排场机趣句字转换之奇变,亦熟得其妙,如庄之奇,列之逸,管韩之雄峭,荀扬之劲深,无不包罗,真文人之雄也[1]8”。能够得到一代名士傅山如此高的评价,显然戴廷栻在文章方面必有自己一番体悟。在毕振姬为戴廷栻《半可集》所作序文中,以戴廷栻的文章来反驳世人认为山西无文的看法是荒谬的。他认为“见枫仲之人则知其文,今见其文,文诚如其人者也。以其人为近古深山大泽之冠服,龙蛇草木昭回其气。是殆文之规矩准绳也。以其文为近古水流行云散徙,不主常声,乃天地之果瓜蔬实莫不有理。是殆人之耳目手足也[1]7”。
戴廷栻对于为文之道的看法,其一,文章生于气节。戴氏认为韩愈之文“北斗泰山,起衰八代”,在世人将韩愈仅视为文章之士时,戴氏提出文章之作,实出于气节。韩愈辅佐晋公时,入汴游说韩弘,“协力廷湊之变,慨然入镇,数语动悍藩,复使命。”因而单以文章之士概括韩愈,着实单薄与片面。“世之人不知文章生于气节,见名雕虫诸多败行。至以文行为两不知,彼其知所谓文,非其文也”[1]45。其二,文章乃雕虫计,戴廷栻更看重士人自身的行为方式对儒者志于道、经国济世的践行。他在为自己的三立书院同学郭九子的文集《旷林一枝》作序时,便为其仅以文章之士为世人所知多所慨叹。“惜也,先甲四年而物故,使袁门少此一争气士而仅仅以晋之诗人终矣[2]5”。他也为历来名士或被帝王、或被士人偏执地仅以文章或画艺所标识而忽略了他们身上匡复朝纲的政治才华而感到惋惜。如对王羲之的才华,戴氏为之抱憾。世人以其书法之精妙,而蔽其才干。“会稽安石万石诸书,记君国之忠,恳恳言际,可以一临池蔽乎?[1]35”其三,戴氏认为,文见兴衰。文章虽小技,但从一代之文章可了解一代之气运,即文见兴衰。他曾这样提道:“一代人品出其中,学术出其中,将相名卿事功节义尽出其中。宜千百世不可变者也。然不可变者,祖宗之法,不得不变者,亦自然之气运也[2]19”。提到晚明气象之时,戴氏也认为从制举中也能看出其气运之所归。“一代休明之运,必于文章见其始终。文章之道不一。寄兴深微,可以知治乱者,莫过于诗[2]5”。可见,戴氏对于诗文创作的重视。
二、交友之道
身处易代的戴廷栻,与众多名士有广泛结交。山西境内的如傅山父子、魏象枢、白居实、薛宗周、毕振姬等,其他全国各地名士如阎尔梅、顾炎武、王弘撰、李因笃、阎若璩等。特别是在入清之后,他创建丹枫阁,聚天下名士,集四方宾旅。他对于交友之道也有一番识见。
交友广泛自然是值得肯定的,自我锢闭,被认为不利于士的自我造就。屈大均曾说:“士君子不幸生当乱世,重其身所以重道。天下无道,栖栖然思有以易之,惟圣人则可。不然者,宁为辟世,勿为辟人。至于辟人,而其失有不可言者也矣[3]32”。至于学人,更以交游问学为成学的条件。顾炎武曾说:“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若既不出门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4]90”。戴廷栻曾引用孟子的言论“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故朋友之道坏,则忠孝之道穷[1]5”,表达了对于讲求朋友之道的重视。当然,戴氏认为应慎重选择交友对象:“与善人交,有终身了无所得者,与不善人交,动静语默之间,亦从而似之,何耶,人情好逸为不善。近于逸。修身难于择,交人宜反求诸己,绝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不可高自位置,存可者与之。不可者拒之之意尔[1]54”。因而交友须慎重。朋友之间是需要时常互相德行勉励的,戴氏曾言:“不见吾叔鸾,乃敬黄叔度[1]1”。此句借用“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吝啬之心必生矣”表达结交朋友的重要性。
交友之道,不仅在于择取善者而从之,同时在于严省自身。顾炎武也曾在给戴氏的书信中言“大难初平,宜反己自治[4]62”。如何“求诸己”,戴氏认为应戒一“妄”字,“妄字从亡,亡,失也。失其真也。从女何也,一切瞒心昧己,美我嫉人,好私好得,皆女人之阴性故也。……吾每每对子弟说此者,以人终不可欺,欺人人无奈我何,神之听之,业报不小。所以五戒皆可勉行,只一妄字随觉随□,苟非真正至诚君子难去此病。诸子弟当操持一段实踏踏地步,好放脚跟也[1]54”。戴氏从一妄字入手,告诫子弟戒妄,脚踏实地,方不失交友初衷。
寻求知音是戴廷栻交友原则中更高层面的诉求。阮千里弹琴,不问识与不识,有求必应,且从未有半点忤色。《晋书》中写识者因而感慨其性情恬淡,不视荣辱。戴廷栻却有自己独到之见解:“只自己好弹耳,于人无与也。然目中总无着意人,乃能如此[1]36”。即知音难觅之意。伯牙子期的绝妙契合,世间罕见,多少也是戴廷栻由于动荡的社会环境而对自身遭遇的另一种书写。
三、戴廷栻的出处观
易代之际,士人除却生死的抉择,活下来的人,必然面临出处之选择,戴廷栻也不例外。“君子苟无际遇,宁隐而无仕[1]9”,这便是戴氏的出处观。在戴氏的出处观中,主要包含了君臣之道与易代的选择等问题。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关于君臣之道,戴廷栻认为“君之视臣为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1]5”。尊君、重臣应该是君臣间相处之道。戴廷栻首先强调君臣间的信任感,即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戴氏借曹沬劫持齐桓公复仇一事,反衬李陵降贼“欲得其当以报汉”武帝刑迁而族陵家。李陵“有报人之心而人不备,曹沬却盟以报鲁,有报人之心而人不疑[1]24”。通过这两个案例之间的对比,戴氏希望当世君王在行军作战、委贤任能时,能够给予臣下充分的信任。此外,戴氏对君王“狡兔死,走狗烹”的行为方式表达了不满,戴氏借功臣刘文静被唐高祖所杀,而唐太宗坐视不救一事对君臣之义提出了声讨:“有唐三百年来事业,是刘公一眼一手看得底,拓得底,率被老李膪货杀之,太宗此时自当以死救,亦悠乎数语,何耶,若子以死救一人,父即暴,未必不解此情理也。……独怪太宗漫然无术,坐视杀元勋,父子大愤闷人[1]38”。此外,戴氏认为君王应别具慧眼、识才善用。怪不得戴氏感慨“惜乎不展所蕴,江左独有右军,君臣皆置之于无用之地[1]36”。
戴廷栻在入清之后一直游离于清政权,此后,伴随复国无望、清朝国运日渐稳固昌隆,身边同志日稀,同时伴随政权更迭而带来的地方权力重组之后对于戴氏及家族的胁迫,都使戴廷栻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无奈出任闻喜训导及曲沃教谕。但回头历数戴氏入清这段时光中的近四十年,都秉持着自身的出处观。
隐士,在讲求气节、不惧生死的基础上,能够游刃有余、智慧巧妙地避开一些敏感关节,自我保全的智慧是为戴廷栻极为称道的。阮籍“有志济世,见时不可为,尤谗畏饥口,不臧否人物,姑隐于酒以自全耳[1]31”。且能极其智慧地避开文帝之为武帝求婚于籍,是戴极为欣赏的。戴氏称孟陋为高士,“少孤,清操绝伦,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娱,口不及世事。”婉言拒绝简文帝和桓温的两次征召,而能“辞婉而意严,无一毫矜胜之气,真高士哉,而遇乱世,如此始可以免矣”[1]37。从古人之行迹中寻求出处之最佳路径与智慧。用舍行藏,需要的是一种智慧与远见。顺乎天意,恣乐其中。唐代李泌三进三出,而能从容应对,正是戴所欣赏之处。李泌“一生出而能入,妙哉有而不居,观其答张说论奕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方圆动静,自传其天,卑卑世史,何足与知之[1]42”。
四、易代反思与批判
明清之交的士人学者所拥有的独特性,因缘于这个易代的特殊性,在这些士人学者身上,不仅体现出经验的深刻性,同时也体现出其批判倾向与批判性思考的广泛。戴廷栻的易代反思主要集中对于儒家学说的批判性继承、对晚明时局的看法,集中表现于对明亡原因的追究上,进而借助历代人物与史事的分析对君臣伦理、君臣相处之道阐发自己的观点,并且对于为官之道颇多论述,这当然与这批士子们讲求经世致用的实学不无相关。
戴廷栻认为,儒家学说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也应该跟随时代环境的变迁而不断跟进。“循古不必是,而行今未必非。二语可破儒家是古非今之滞也[2]37”。他认为是古非今这样滞后的观念是应该予以摒弃的,世人也应该保持着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儒学的改革与演进。
站在明清易代的动荡关头,戴廷栻的态度更为豁达与长远,“如此一区宇中,自古来据而有之者,非一二家[1]37”。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朝代更迭是世之常态,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一朝一代的盛与衰,主要因缘于世运、气运之转迁。“气运循环如日,自旦而中,中而晡,一代中自有一代之混濛,有一代之开阖,有一代之文明,有一代之销陨。大抵富盛之极必尚骄夸,骄夸之人自然刻薄,刻薄之事遂兆兵戈,兵戈之祸,使富贵不保其富贵,贫贱不安其贫贱,君子野人襍然无统,斯时求为草衣木食上巢下窟而不得孑然一二故老,智力已衰,其少壮者,生长兵戈之间,目未习富盛骄夸之事,然后返朴还淳,复归太古。此气运之自至,岁圣哲无如何也[1]46”,充分体现了戴氏本人哲学观中辩证的观点。物极必反、福祸相依,统治者应该保持居安思危的心态。
面对明朝的覆灭,一方面是由于气运之衰亡,这是人力所无以挽回的败落局势,同时戴氏认为士大夫们行为的逾越礼制对于明朝灭亡也是难辞其咎的,“是故礼乐之兴由于学士大夫,礼乐之坏亦由于学士大夫。”“今缙绅家舆服宫室种种踰制,姑不具论。其甚悖者,如品官职衔,有勋有阶以次而受,今则一概混列矣。名器国家之大典而斜封墨敕,遍于庸隶矣。贵家妻女竞为宫妆后饰矣。此数事者,非止风俗之坏,实所谓人臣无将,将而必诛者也[1]47”。如上被戴氏列举的诸事,是他将世风的日趋转下,国运的衰亡归因于作为这个社会知识精英的士人阶层自身行为的失当。
戴氏认为,当世之士子多“病贫”。一个人是否能称作贤士,与经济上的是否贫困无关,“而其下之奴鄙无衣食之人,亦以颜子为口实,不过欲以贫贱骄人,问其所为我之仁义,乌有也。一贫贱无用之人已耳[1]7”。戴廷栻进一步认为“颜子之贤不贤于屡空,而贤在于用舍行藏。子贡之才不在屡中,而在存鲁且知性与天道[1]6”。戴廷栻眼中的贤士,在于此人是否善于用舍行藏之道。戴氏为此对当世之人提出谆谆劝诫:“学道之君子,宁大无骄无小无奴无鄙。虚则不骄,容则不小,高则不奴,文则不鄙。子弟之欲登孔子之堂者,读书做人可也[1]8”。此外,戴氏对于明季用人多徒以言貌取人多有诟病。此种人“今有稍能声律之人,其使事之切,自居之严,世界之分。术疏而情露。言愈张而胆愈怯,声愈雄而气益夺。”这是戴氏对于明朝浮躁士风的披露,同时对用事之人缺乏慧眼的反思。用人无方,是明朝迅速败亡的重要因素。而戴氏认为晚明之气运将衰,是可以从制举中了然窥之:“天启壬戌以来,其晚明之时乎,士子平日读书简练,揣摩以干禄为主,富贵利达之念盘踞胸中,而精神手眼胥靡焉,从之阅其闱书。割子裂史离经叛道,于夫空疏腐庸杂见其中,邪诡之气先兆于文章而后中于家国。吾之所谓不得不变,亦自然之气运者,正谓此耳[2]19”。
戴廷栻,身处易代时空,凭借自己卓越丰富的文化活动、充实广泛的交游,奠定了自身在这个特殊时代更为显著、独特而不可或缺的文化地位。重构戴廷栻这位名士的精神世界,是文本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他有自己作为士而共有的道义担当,也有对这易代所发出的独特声音与反思,他是众多易代士人中的一个具象,他的思考与实践充实关于易代的想象与重建。
[1]戴廷栻.半可集备存:上册[M].常赞春,辑.云文斋石印本,1916.
[2]戴廷栻.半可集备存:下册[M].常赞春,辑.云文斋石印本,1916.
[3]屈大均.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一一九册·翁山文外:十八卷[M].清康熙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顾亭林.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以一则正统十一年商人家庭阄书为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