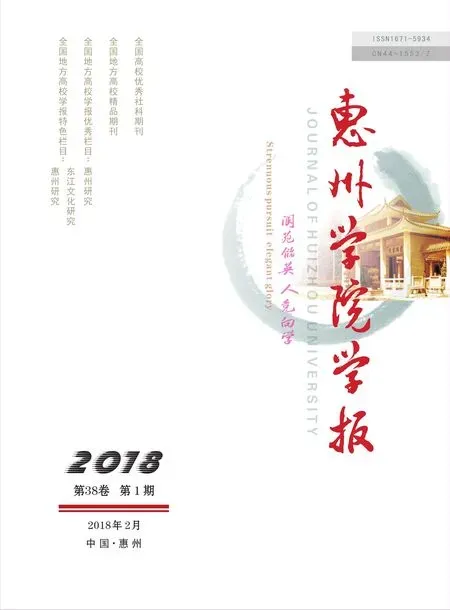悦德关系中的三种偏见1
许小委
(惠州学院 政法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
所谓悦德关系,即存在于“悦”与“道德”间的稳固的、必然的联系。该问题同西方伦理学背景下的“德福关系”问题有很大程度的重合。但也存在一个较明显的差别。区别就在于,较之于“福”这种综合性、复多性的快适满足(它总不免与现实利益、物欲满足和感官享受纠缠在一处),“悦”更多地是指较纯粹的、精神性的愉悦(怡悦),是一种“自由自足完满”的情态或心境。当然不能说,“悦”作为精神的怡悦畅适,同物质利益和感官享受根本无涉,或谓其间完全不含由物欲满足而来的快乐成分,然而物欲满足和感官享受却仅充当悦的激发因素,真正的悦乃是由对种种“生物学快乐”的提纯和升华而来的畅适怡愉之情感状态,严格说来单指主体内在的、精神性的、超感官的怡悦和畅适。此种作为“精神怡悦”之情态的“悦”,基本等同于清代哲学家唐甄的理解,“悦者,非适情之谓,非徇欲之谓……顺乎自然,无强制之劳,有安获之益,吾之所谓悦者,盖如是也[1]47”。缘于此一区别,在德福关系框架中展开的讨论,则终难撇清物质利益的疑难和干扰,总会遭遇到道德与现实利害在互释方面之困难。也就是说,既无法以利益说明道德——对实际利益的追求并不引发道德;也无法以道德说明利益——道德并不产出实际的利益。道德根本上是同现实利益无关的,道德反倒是对现实利益的超越;而讨论悦德关系则自有一种便利:由于悦被规定为一种纯粹的精神怡悦畅适,它事先就同掺杂了物质利益的“福”划清了界限,亦即免除了道德与现实利益无法互释的困难,故而更容易较切近地揭橥悦德之间的本真关系,洞见“道德实践(生活)”同“精神的怡悦之境”的原始关联。而唯有借助对“悦德一体”之本质关系的原则领会,才能不仅使道德的独立地位和本有意义获得确立,并且为现实的道德实践提供持久稳固的动力基础。因此,文章稍稍变更了讨论方式,将德福关系问题转换为悦德关系问题。
然依其实质而言,悦德关系无非就是简化了、纯化了的德福关系。是故对悦德关系的探讨,乃无从游离于渊深久远的德福关系理论而独立展开,须于德福关系之话语谱系中方可获得准确定位和全面理解。就此而言,悦德关系也分享着德福关系的历史,受益于其理论资源且受制于其话语负担。换种说法就是,在悦德关系问题上同样历史地形成了诸多特定的理解和观点。倘若不对其作必要的清理和批判,本真的悦德关系恐难于自遮蔽它的迷雾中显露自身。特别是部分在当下仍有较大影响的观点,对其展开实质性的反思和审查乃是亟须之任务。抛开大量的琐碎细节不论,仅就基本理解和一般观点论,在当前流行的关乎悦德关系之看法中,主要存在如下三种失之偏颇的观点,它们在理论上是欠圆融的、在实践上是有危害的。
一、悦德相分论
即以为悦德之间或是非相关的,或仅有一种“选择亲和性”,总之不存在本质性的关联。初看起来此种观点似乎着实有理。因为,虽然存在一种显明的事实,即人处在愉悦情态中更容易做出道德行为来。但并不需要特别地搜求穷索,就能找出许多在“愉悦”时做出不道德的行为的反例。也就是说,即便从经验观察的层面来看,愉悦状态引发的道德行为的比例,明显地大于其引发非道德或不道德行为的比例,它也终不过是说明,悦德之间存在着某种“选择亲和性”。而由于愉悦既能导出道德行为,也能导出不道德行为,这就从根本上表明,愉悦与道德间不存在必然的、本质性的关系。这就是持悦德相分观点之人的一般论证。但是经验告诉我们,愉悦与道德的“亲近关系”并非是局部的、临时的和松散的,而是普遍的、长期的和重复出现的,因此它绝无可能在“偶然性”名义下获得完整说明。因为,根本不存在所谓“可重复的偶然性”,该说法无非是一种逻辑悖谬,故而仅具有修辞学上的意义。依其本质而言,“可重复的偶然性”乃就是“必然性”。按此当可断定,愉悦与道德之间确乎存在某种稳固的、必然的联系,即便关于此种联系的本性及其作用机制尚不甚明了。实际上,说愉悦也产出不道德,这本身就是一种误解。秉持悦德相分观点的人,通常将法律术语中所谓的“激情犯罪”,视作是愉悦也产出不道德行为的典型例证。在激情犯罪中,犯罪者处于极度的兴奋或癫狂中,受过份强烈的情绪或感受驱使,不可自抑地做出了对他人的损害行为。他们以为,此间促成犯罪行为发生的乃是快乐或愉悦,并且是强烈的快乐和愉悦。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前文已然指出,悦(乐)指的是一种“愉悦自足平和”之情态或心境,它完全有别于“生理性快乐”,而是对生理性快乐的净化和升华。因此,很明显在激情犯罪中,促使犯罪行为发生的那种极端的兴奋或快乐,并不是真正的悦,而毋宁说恰是真的不悦。因为悦的第一个要件是自由,是行为的“出乎自己”和“无待于外”,而我们在激情犯罪中看见的,恰恰是完全受制于异己之物的不自由。可见,由于错将不悦当成悦,所举例证根本无法说明其观点。相反,倒有理由说,在激情犯罪中,行动者所以做出不道德(犯罪)行为,正因为他处于真正的不悦当中,亦即是说,不道德行为并非出自悦而恰是出自“不悦”。
另外,就其理论渊源来看,认为悦德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关系,大概也得到了康德的支持。康德在“自由意志自我立法”的意义上理解道德,道德因此只与出自纯粹理性的法则(理性的道德法则)相关,为了确保道德法则的至上性和道德行为的纯粹性,对外在的幸福祸患和内在的情感体验的考量都须予以摈除。“纯粹实践理性的真正动力就具有这样的性质;它无非就是纯粹道德法则自身[2]96”“一切通过德行法则的意志决定的本质性东西就是:它作为自由意志,因而不但无须感觉冲动的协作,甚至拒绝所有这种冲动,并且瓦解那能够与上述法则相抵触的一切禀好[2]79”。也就是说,康德事实上将德、福视作不相关的领域,作为基本不相干的事物,德福之间是谈不上“真正的关系”的。“德行的准则与个人的幸福准则就它们的无上实践原则而论是完全各类,远非一致的[2]124”。显然,在康德的理解中,德福之间既不存在因果性关系,也不存在生成性关系,易言之,两者之间不只是没有此种关系或彼种关系,而是根本就不存在必然的关系,最多也只是偶然的松散的联系。这无疑增强了认为悦德之间没有本质关联的那种主张的信心。然而,问题在于,倘若说悦德之间全无关系,那么现实中又凭什么来担保人们行道德的意志呢?道德的动力又从哪里发生呢?康德自己也意识到此一困难,由于纯粹理性推论不出悦德间的必然关联,因此他不得不求助于上帝,通过“一个理性而同时全能的存在者的完满意愿”[2]121来担保“德福统一”,实际上还是对德福之间的必然关联做出了变相的承诺。由此可见,否认悦德之间的必然关联,无异于取消了道德意志的现实根基,亦即抽空了道德动力的世俗养分,作为后果则只会消解道德意志和延宕道德实践。因此,对于此种表面看似无害的观点,亦当保持必要的清醒和戒备。
二、“悦出于德”论
所谓“悦出于德”,即认悦是道德的产出物或回报物。将愉悦视作是道德的回报,是道德行为生成当中的伴生物或生成之后的衍生物。此种观点,不仅在西方德福伦理学传统中有其渊源,也部分地受到儒家对“孔颜之乐”的正统见解的支持。在苏格拉底那里,对道德的偏爱和追求并不具有自为性,而是指向一明确的终极目的,即幸福的达成。文德尔班对此写道,“他的机智、敏锐、辩证的灵活性全都被用来反对智者学派,被用来证明,到达永恒幸福之最有把握的道路,甚至唯一可靠的道路在于在任何情况下服从道德伦理的命令,服从法律的道德[3]113”“他认为,有德行的人的这种符合于目的的行为实际上达到了它的目的并使他幸福。幸福或福利是德行的必然结果[3]115”。同样,于亚里士多德而言,虽不能武断地认定道德仅被他视作达成幸福的手段①,然而确定无疑的是,幸福(愉悦)在他看来终究是道德生活的某种效验或成果。他说:“我们选择每种事物都是为着某种别的东西,只有幸福除外,因为它就是那个目的[4]304”。譬如,荣誉、智慧以及各种德行,人们固然也因其自身而选择它们,但说到底还是“为幸福之故而选择它们[4]18”。幸福是一切行为的最高目的,而同时它无非也就是快乐,“人人都认为幸福是快乐的。也就是说,人们都把快乐加到幸福上。这样看是有道理的[4]222”。可见,快乐(愉悦)归根到底不外乎是善之生活的产物。将道德问题收纳入“幸福论”框架的传统,对西方的德福问题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斯多葛派的禁欲主义、伊壁鸠鲁快乐主义,以及中世纪以道德生活为拯救之凭证的一般观念,甚至在康德划清道德与幸福界限的试图里,以及在黑格尔通过理念将两者重新联结的做法中,那种传统的影响同样清晰可辨。
此外,将乐(悦)视作道德的成果,也部分地存在于儒家学说当中。儒家的道德学说总体上无疑是一种“德福一致”论,但同时也包含有认为悦乐是道德之后果的看法。夫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此种非常人所及的悦乐能力、可贵的大乐之境,其所以可能,恰建基于圣贤道德的修成。亦即是说,惟当道德修为进至一定层级,才能收获那种无上的悦乐。到宋明儒那里,“孔颜之乐”作为至高的大悦乐境,不仅是道德成就的回报,是道德成就的直接明证(所谓“学至于乐则成矣。笃信好学,未知自得之为乐。好之者,如游他人园圃;乐之者,则己物尔。然人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难能也[5]127”),更是道德主体在行道德过程中的“自受用”,是道德生活或道德境界本身。周敦颐论颜回乐境日,“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富至贵、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齐,故颜子亚圣[6]38”。显然,颜回乐境在周子看来无非就是道德之境。就此而言,“孔颜之乐”虽则可被理解为修成道德之后的一种回报,根本说来却就是“悦德一体论”,是审美境界和道德境界的统一。
以上观点在大众话语中则表现得更为直白和功利。如人们常讲的,施善者自有福报,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好人好报等,都表明同一个意思:道德会带来福乐(悦)。它甚至成了人们行道德的唯一动力。普通的道德说教抛开这条就等于完全的空无。即使是自诩超出了自我关切的当代“慈善伦理”,本质上仍受制于“行善得福”的逻辑。根本说来,将悦(乐、福)视作道德的成果存在明显的副作用,因为当许诺给德行的最终悦乐幸福表明通常是无法兑现时,道德的根基就开始摇晃,行道德的动力也就奄奄一息了。也就是说,由于总是在作为终极目的的幸福之下筹划道德,道德就无法获得其独立的地位,不是出乎道德自身的原因,不将道德看作自为的终极可欲的,就是褫夺了道德的自足的完满的意义,也就是把道德降低到某种工具性的地位,这最终不可避免地会败坏道德,尤其是对一个超越的“天国”或“来世”受到根本质疑的时代而言,其带给道德的损害乃是巨大的和持久的。
三、悦乐害德论
更有甚者,以为悦(乐)会损害和妨碍道德的生成。即认为悦是一种腐化道德或使道德蒙受“污秽”的事物,是为“悦乐害德”或“淫乐败德”。这类看法以不同形式和程度存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禁欲主义或道德纯洁主义之中。在柏拉图那里,由灵魂趋近真理而来的安宁,是唯一真正值得欲求的幸福,而其他一切与身体相关的享受、愉悦和快乐都是灵魂认识真理的纷扰,因此是不义的和需要克制的,甚至身体本身都是可厌弃的和有待被克服的,“因为带着肉体去探索任何事物,灵魂显然是要上当的[7]15”。在这里,由于感官的愉悦总体上败坏灵魂对真理的认识,而知识对柏拉图而言就是德性,所以也就是妨碍了德性的生成。对斯多葛派来说,“他的美德是淡漠无情[3]227”,因此为达致道德的目的,须抑制一切感情的强烈变化,抵制因感官刺激而来的激情状态,首要的是弃绝享受、快乐和愉悦。因为在他们的理解中,愉悦和快乐无疑会伤害到那种德性的实现。至于通常被冠以快乐主义的伊壁鸠鲁派,严格说来,在他们那里,肉体的激情和享受是不配作为享受对象的,唯有那精神的或灵魂的快乐才是正当的享受对象。实际上,对他们而言,精神和灵魂快乐的获得,同样以压制肉体的愉悦为前提,甚至是必要的前提。“保持心境宁静,这是伊譬鸠鲁的原则;这条原则也正包含着:放弃那种以及许许多多种一方面使人快乐、但是另一方面支配着人的东西——自由、轻快、恬静、没有不安、没有欲望地生活着[8]76”。因此,“享乐主义的粗俗的东西、感性的东西消逝了[3]230”。之所以如此,乃出于这样一种理解:对感官愉悦之类的个人幸福的追求,必定会影响到人的道德成就,亦即对那种真正之快乐的占有。整个中世纪,从奥古斯丁说出“人的目的(destiney)就是认识上帝”[9]25开始,通过远离世俗享受和感官快乐的禁欲主义而接近上帝(收获德行),就成了实现那一目标的基本路径甚至是唯一的路径。在那个时代,道德直接源于对上帝的认识与对上帝诫命的恪守,而这无非意味着对世俗幸福的摈弃,与感官快乐的争斗,必须压抑同上帝之纯粹性、精神性、圣洁性相抵触的情欲、妄念、享受、快乐、愉悦、满足等一切虚妄不洁的东西。在某些极端的教派那里,甚至要求整个地熄灭身体的感觉,通过一种极度刻苦和艰辛的练习,以适应和准备在上帝之城中的生活。此外,即便是在康德那里,也存在着类似的看法。康德说:“它们(德、福)虽然同属一个至善而使之成为可能,却在同一个主体之中竭力相互限制,相互妨碍[2]124”。亦即是说,对幸福悦乐的追求很可能妨碍到道德,而对道德的追求也极容易会缩减个人的幸福。如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哲学史上,存在着一条清晰的理解线路,即主要由禁欲主义传统昭示出来的悦乐害德的观点。倘若对其进行追根溯源地分析,这种观点可归因于古老的灵肉分离观念。根据灵肉区别的观念,人实际上由两个部分组成,灵魂/理性的人和肉体/动物性的人,并且两部分大体上乃是相互掣肘而难于一致的。德行与灵魂相关,属于灵魂的成就,而愉悦快乐源于肉体欲望的满足,故而属于肉体感官的快乐定会妨碍到灵魂对真正道德的寻获。也可以说,正是将幸福快乐愉悦主要理解为属于肉体感官的满足,才产生出“悦乐败德”的看法。
认为悦乐害德的倾向,在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里间或有之,然远不如西方那么明显。儒家虽然讲“义利之辨”,但主要是倡扬以义导利、利以义归,因而基本上没有禁欲的意思。朱子有“灭尽人欲,复尽天理”之说,然从其内在理路来看,人欲指的是不当或过度的欲望,而天理乃是常行不废之道。所以,要灭的仅是那些不合天理纲常的欲望,不正当的欲望,并非要将人的全部感性的快乐和愉悦一并取销。老子哲学强调“朴”,当然内含了过度的物质欲望和感官享受伤害到德性的意思,但也未发展出那种“悦乐”与“道德”相互对立的观念。准确地说,国人对悦乐妨害道德的看法,较多地体现在被称作“忧患意识”的普通意识中。照中国的一般理解,快乐愉悦诱人沉迷且极容易超出恰当的限度,因而多会蒙蔽本心良知,进而损害个人的道德修为,不止于此,它也常扰乱人的清醒判断,从而败坏外部的现实功业。所以,即使无须整个地弃绝愉悦快乐,也须对其保持必要的谨慎,务使它们处于恰当的范围和限度中。诸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哀兵必胜”“生活太优渥,工作就会被生活所累”“肉食者鄙”等说法,都或多或少地表达了对享乐和愉悦的本能提防。总而言之,在普通意识看来,从愉悦快乐出发基本上是难于通达道德的,至少不是一条近路。换句话说,道德无非就是受苦,通向道德的路途是艰难的,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这与当代西方宣扬的忧患伦理学颇为相通:以乔纳斯(Hans Jonas)为首的伦理学家,主张一种“低沉的情绪”、“忧患意识”和“远程意识”,主张必须如临大敌般诚惶诚恐地应对复杂的环境条件,方有可能使道德行为得以发生。在乔纳斯看来,由于技术的可怕成就和席卷世界的全球化,“人类行为的可能结果的规模已经超出了行为者的道德想象力[10]255”,也就是说,由于技术和全球化,人类行动已变成“远程”行动,行动的后果也已经变成“远程”后果。选择和行动及其所引发的后果,在空间和时间上造成的影响将更加深远,因而也将变得益发不可预知和难于监控。在此意义上,鲍曼赞同乔纳斯的见解,他说:“现在我们似乎需要一个全新的伦理。……这种伦理的‘首要责任’,再次用乔纳斯的话来说,就是‘使科技事业的远期效果形象化’。这种伦理必须受‘关于恐惧的启发式论据’和‘关于不确定性的原理’指导:即使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的观点恰好平衡,‘关于厄运的预言比关于幸福的预言更应当受到注意’[11]327”。可见,忧患伦理或“远程伦理”(long-distance ethics)建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道德主体将不可避免地在愉悦和快乐中迷失,而唯有某种提心吊胆般的、惶恐的、低沉的情绪才能使其清醒和有力。正因如此,忧患伦理学要求道德自我须睁大眼睛,保持谨慎细致和高度敏感,始终虑及那些潜伏的、尚在远处的、未曾显形的危险,始终保持对世界和未来的担忧和紧张状态。然而,在此必须指出的是,道德并非是建立在对(包括感官快乐在内的)愉悦的总体压制之前提上的,以压抑和窒息快乐愉悦而达成的道德根本说来乃是不道德的。真正的道德只能从戴震的“体情遂欲”的层面上来寻获。如将道德看成是同愉悦异质并且两相对立的东西,则只会使道德变成一桩单纯的艰苦差事,从而让普通民众望而生畏。
结语
如上,不论是认为悦德之间不存在本质性关系,还是认为悦无非是道德的产物,抑或认为悦会妨碍败坏道德,都存在着论证上的困难,亦即缺乏理论自身的圆融性,并且从其后果看来都会妨碍到道德实践的光大和复兴。此种困境迫使我们回到儒家的“圆善境界”,即回到“孔颜之乐”理论上来。扼要言之,孔颜之乐作为“与事功利益无涉的精神满足”,作为道德与审美合一的境界,清楚表明了在“道德”中即在“自得”(乐)中。道德实践和道德生活,乃就是作为“自得”的“乐”、“悦”。乐(悦)就是对道德生活的体悟、领会、感受和“自受用”。“德者,得也”(《乐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学至于乐则成矣。笃信好学,未知自得之为乐。好之者,如游他人园圃;乐之者,则己物尔。然人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难能也[5]127”。很清楚,儒家历来都视“道德生活”为有得于己的“自得之乐”,儒者的修为恰在于摆脱一切外在目的、出乎自己的道德生活,此种道德生活和道德实践本身就是最真实的受用和自得。道德与“自得”既非手段与目的之关系,亦非原因和结果之关系,而是“德、得同一”的关系。此间的“自得”、“自受用”,显然不是物质性的、功能性的满足,而是“退安陋巷颜回乐”“我心处处自优游”“富贵不淫贫贱乐”[5]482,也就是那纯粹的、超越的精神之悦。这种“得”、“受用”与富贵功名无关,而是“纯乎天理”的精神性怡悦畅适。道德每进一分,乃有一分“自得”。进到圣贤的地步,则是“通天同体”之乐;同样,“自得”每增一分,则道德也进一阶段。及至通达“浑然与物同体”(大程子语)之乐,便是圣贤道德境界的修成。因为,悦(乐)作为自由之境和对自由的感觉,乃是使行为具有道德意义,亦即使道德行为成立的前提;悦(乐)作为和解同一之境,已然启动了对他者负责的机制,因而本身就是道德的;悦(乐)作为自足和圆满,总是意味着对共在的记起和对世界的亏欠,意味着为了他者给出的意愿和能力。也就是说,悦(非功利的精神之乐、怡悦畅适)直接就是道德境域的崭露和实现。显然,依其本质而言,“孔颜之乐”乃就是“悦德一体”论,是对悦德关系的本质阐明:道德即“自得”、道德直接就是悦(乐),在道德中即在怡悦畅适中;精神性的怡悦畅适本质上乃就是对道德生活的必然体验和固有感受。可见,唯建立在“德、得同一”基础上的“孔颜之乐”,即儒家的“悦德一体”论,方是对悦德关系的本质阐明,是最为圆融的悦德关系理论,它不仅贞定了道德本有之价值、确立了道德的独立地位,同时也给道德提供了自为之基础和可靠之动力。
注释:
①虽然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某些论述,可以推出道德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之结论。但就其思想整体来看,亚里士多德可谓是主张“德福一致”的典型代表。参见何益鑫《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德福一致的两种范式及其当代意义》,道德与文明,2014年第3期。
[1]唐甄.潜书校释[M].黄敦兵,校释.长沙:岳麓书社,2011.
[2]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册[M].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4]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程颢,程颐.二程集[M].王孝渔,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
[6]周敦颐.周子通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7]柏拉图.斐多[M].杨绛,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8]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9]St.Thomas.Summa Theologica(III)[M].Trans.by Fathers of the English Dominican Province,Revised by Daniel J.Sullivan,William Benton.Publisher,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1988.
[10]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M].张成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1]齐格蒙特·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M].郁建兴,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