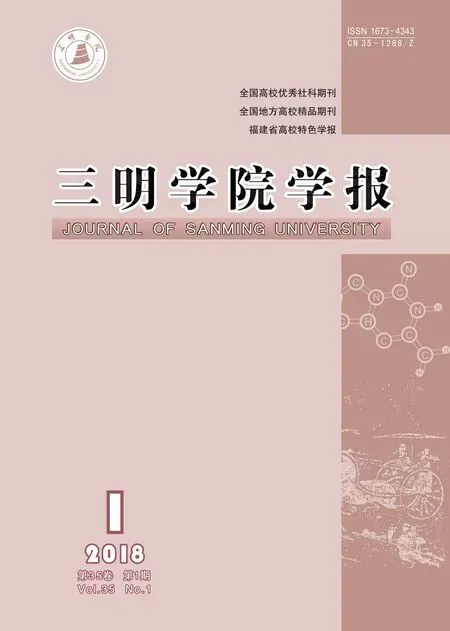朱熹对教育类书籍的编刻及其影响
金雷磊
(三明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朱熹是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伟大教育家,一生多半时间在从事教育和著书立说活动。朱熹每到一地做官,往往重视发展当地教育,创办书院。他亲自创办了考亭书院、紫阳书院、武夷精舍,培养学生数以千计,其中有名可考者400多人。学术界对朱熹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教育史、教育思想史以及福建教育史的通史或断代史著作中,为我们深入研究朱熹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其实,朱熹既是教育家,也是出版家。若把二者结合起来,考察朱熹教育类书籍的编纂与刊刻活动,分析书籍在传播知识和文化方面的功劳,对士子从事科举考试的影响,以及朱熹的教育传播思想等,则更有意义。本文所说的“教育类书籍”,主要是从宽泛意义上界定,既包括朱子编刻的小学阶段和乡野自学之士所需教材,也包括严谨的学术著作。
一、朱熹对教育类书籍的编纂
朱熹教育类图书主要以教材为主。朱熹编撰的教材有《小学》六卷,淳熙十四年(1187)编成,主要记录古圣先贤言行,分内外两篇,内篇包括《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包括《嘉言》《善行》,是当时有影响的蒙学教材。此外,还编有《童蒙须知》《训蒙斋规》等针对童蒙教育的教材。《近思录》是朱熹与吕祖谦合编,完成于淳熙二年(1175),该书主要记载周敦颐、张载、二程语录,共十四卷。《近思录》是朱熹编撰的理学入门教科书。
朱熹教育类图书还包括严谨的学术著作。《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耗时最多、用功最勤的一本书,淳熙四年(1177)完成,朱熹知漳州时,于绍熙元年(1190)初刻。该书雕印出版后,即传布天下。元代皇庆二年(1313),该书成为科举考试教材和取士的标准答案,其地位直线上升,甚至超越《五经》,影响中国科举考试数百年。此外,朱子还编纂《上蔡先生语录》,有具体材料为证:
因念往时削去版本五十余章,特以理推知其决非先生语,初未尝有所左验,亦不知其果出于何人也。后籍溪胡先生入都,于其学者吕祖谦得江民表 《辨道录》一篇读之,则尽向所削去五十余章者,首尾次序无一字之差,然后知其为江公所著而非谢氏之语益以明白。夫江公行谊风节固当世所推高,而陈忠肃公又尝称其论明道先生有足目相应之语,盖亦略知吾道之可尊矣。而其为言若此,岂差之毫厘,则夫千里之缪有所必至而不能已者耶?因书以自警,且示读者使毋疑。旧传谢先生与胡文定公手柬,今并掇其精要之语,附三篇之后云。[1](P36-37)
朱熹作为当时的理学家和知名学者,治学严谨,经他编纂的书籍质量有保证,深受读者信任,受到大众欢迎。因此,有些著作还没有编好,就已传播出去。编订《上蔡先生语录》,就是此种情况,还未完稿,就被传播出去,刊板赣上:
熹顷年校定《上蔡先生语录》三篇,未及脱稿而或者传去,遂锓木于赣上,愚意每遗恨焉。比因闲暇,复为定著此本,然亦未敢自以为可传也。[1](P36)
书商偷去朱熹书籍,主要是看到朱熹编纂的书籍在市场上有销路,想要把书据为己有,从而盈利。淳熙四年(1177),朱熹在建阳编写《论语集注》,思考还未成熟,编纂没有完成之际,这些著作就被建阳书坊老板窃出先行出版。朱熹曾对门人杨道夫说:“《论语集注》,盖某十年前本,为朋友传去,乡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觉,则已分裂四处而不可收矣。其间多所未稳,煞误看读。[2](P77)朱熹这番感言,就是针对市场上打着他的名号出售书籍的书贾。此书当时已经在市场上普遍传播,但朱熹认为,书中内容却经不起推敲,只会误导读者。由此可以看出,朱熹对自己书籍广受欢迎十分高兴,又对书坊主粗制滥造的行为表示不满。同时,也对读者和学生群体因接受书中错误内容而担忧。
朱熹热爱编书事业,当无书可编时,主动向友人寻求,如他曾找向伯元索要过书籍:“御书古文《孝经》有墨本否?欲求一通。此书无善本,欲得此雠正也。 ”[3](P159)正是朱熹对书籍编纂和出版事业的极度热爱,才使得朱熹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编书、著书、刻书与印书的事业当中,为宋代教育出版事业和文化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朱熹对教育类图书的刊刻
朱熹是南宋著名刻书家,他之所以自己刊刻书籍,有“二原因说”和“三原因说”两种代表性观点。“二原因说”代表为武汉大学教授曹之,曹之认为,朱熹刻书原因:一是传播文化,二是谋生。[4](P213)“三原因说”代表为地方文史专家方彦寿,方彦寿认为,朱熹刻书原因:一是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传播其学术思想,以及整理前辈理学家著作,便于继承和发扬光大。二是解决其所办书院生员的教学用书。三是弥补其俸禄之不足,维持生计。[5](P65)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朱熹为官所至之地,几乎都有刊刻图书,足迹遍布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等省。如朱熹曾在福建建阳刊刻《论孟精义》《程氏遗书》《程氏外书》《上蔡语录》《游氏妙旨》《近思录》等书;在江西南康刊刻《周子通书遗文遗事》《太极图》《拙赋》等书;在浙江会稽刊刻《勒喻文》《古易》《音训》等书;在湖南潭州刊刻《稽古录》。其中,以在福建刻书最多,这与朱熹一生在福建生活时间最长有关。据统计,朱熹一生刊刻图书 40多种。[4](P214)另据徐德明考证,朱熹刻书共达54种,其中,闽地刻本26种,外地刻本28种。[6](P266-275)这些图书当中,既包括朱熹本人的著作,也包含其他学者作品;既有教科书,又有学术著作。
朱迎平认为,朱熹所刻书中,“除少量文史类书籍外,主要是对儒学经典的‘道学’阐释,其主要目的无疑是对道学的宣传和推广,因而一些基本典籍在多处反复刻印,一刻、二刻乃至三刻,并在传播过程中修订完善”[7](P250)。从朱迎平的观点来看,朱熹某些特定书籍出现过多次印刷出版的现象,这种现象对当时大多数文人来说,比较少见。某些书能够多次出版,这对当时学者来说,是莫大的殊荣。这也是出版史和传播史上一次特殊的现象。
朱熹作为一个官员,无论是在何地任职,所到之处都从事图书雕印与传播活动,可以说是一个书籍传播家,通过书籍这种文化载体来传播理学思想。“与一般私宅刻书不同的是,这些学者刻印的图书多为自己的著作,在编辑、校勘、版式等方面体现出强烈的文士风格,为福建刻书业起到示范作用,提高了福建刻本的学术品味。”[8](P371)比如,朱熹在漳州刊刻《四经》(《诗经》《尚书》《周易》《左传》):
敢昭告于先圣至圣文宣王、先师兖国公、先师邹国公:熹恭惟六经大训,炳若日星,垂世作程,靡有终极。不幸前遭秦火煨烬之厄,后罹汉儒穿凿之缪,不惟微词奥旨莫得其传,至于篇帙之次,亦复殽乱。遥遥千载,莫觉莫悟。惟《易》一经,或尝正定。而熹不敏,又尝考之《书》、《诗》,而得其小序之失。参稽本末,皆有明验。私窃以为不当引之以冠本经圣言之上,是以不量鄙浅,辄加绪正,刊刻布流,以晓当世。工以具告,熹适病卧,不能拜起,谨遣从事敬奉其书,以告于先圣先师之廷。神灵如在,尚鉴此心。式相其行,万世幸甚!谨告。[9](P274)
以上材料所述,就是朱熹刊刻四经完成之后,为祷告先圣所写的一篇文章。这篇小文当中,也流露出了理学家朱熹鲜明的传播思想。这从“不量鄙浅,辄加绪正,刊刻布流,以晓当世”等语句当中可以体现出来。虽然说的是“以晓当世”,让当时学士大夫都能知晓,但是书籍刊刻与传播事业本身就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朱熹此举功莫大焉。与此同时,朱熹还在漳州刊刻 《四子》(《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故今刻四古经,而遵及乎此四书者以先后之。且考旧闻,为之音训,以便观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于此者,附于其后,以见读之之法,学者得以览焉。抑尝妄谓《中庸》虽七篇之所自出,然读者不先于《孟子》而遽及之,则亦非所以为入道之渐也。因窃并记于此云。绍熙改元腊月庚寅,新安朱熹书于临漳郡斋。[10](P55)
朱熹知漳州时,在漳州刻书,改变了漳州历史上无刻书的历史,他是漳州第一位刻书家。他在漳州所刻书籍除了“四经”“四子”外,还有《乡仪》《家仪》《近思录》《楚辞协韵》等书。 “这些书基本上都是朱子为其创建的书院,或为整顿当地官学而印行的教材。”[11](P215)可见,朱熹出任地方长官时,重视图书出版、文化传播和教育事业。“作为宋代理学大师,为了形成并完善其理论体系,为了宣传和推广其理论主张,朱熹一生撰写了大量著作”[12](P19), 其中就包括教育类著作,对地方教育出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再如《语孟精义》等书,最初也是朱熹在建阳刊刻:
熹顷年编次此书,锓版建阳,学者传之久矣,后细考之,程、张诸先生说尚或时有所遗脱。既而加补塞,又得毗陵周氏说四篇有半于建阳陈焞明仲,复以附于本章。豫章郡文学南康黄某商伯见而悦之,既以刻于其学,又虑夫读者疑于详略之不同也,属熹书于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号“精义”者曰“要义”云。淳熙庚子冬十有一月己丑朔旦,江东道院拙斋记。[13](P405)
《语孟要义》初名为《语孟精义》,始刻于乾道八年(1172),锓版于建阳。时过八年,淳熙七年(1180)豫章郡文学黄商伯再次刊刻于豫章郡学,改名为《语孟要义》。再次刊刻此书,朱熹经过了进一步的编辑和修订,补充了之前所遗漏的程、张诸先生的说法,还附录了一些内容。书被改名后,考虑到读者对前书和后书内容详略不同的疑问,黄商伯特嘱托朱熹为改名后书籍作序加以说明。《语孟要义》后又改名为《语孟集义》。
三、朱熹编刻教育类书籍的影响
朱熹作为理学型编辑出版家,其编刻的教育类书籍,传播了先进的教育理念,这种理念既有普适性,又具独特性。朱熹编纂的书籍,既不同于同时代教育家所编图书,又超越了前代教育家编书的水准。随着朱熹所编教育类图书的不断传播,图书媒介对地方和全国教育事业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对地方教育事业而言,促进了福建教育的发展;对全国教育事业而言,又带动了全国教育理念的改变。
与同时代教育家相比,朱熹编刻的教育类书籍,重新建构了儒学经典体系。新儒学虽然以北宋五子开端,但“他们多以义理阐述孔孟思想,各自著述,未经提纯,也未形成完整体系”[14](P74)。朱熹通过诠释儒家经典著作来复兴儒学,发展儒家学说,建构新的体系。特别是其《四书集注》,采用阐发义理的方式,代替了传统考据之学,在研究儒家经典上面,开创了一种新的范式。朱熹通过义理的阐发,希望儒者加强身心修炼,穷理致知,只有这样,内圣外王的境界和天下有道的世界才有机会得以实现。这种建构从哲学层面上实现,朱子哲学观是朱子对世界本体的认识。朱熹提出 “理气观”,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理和气构成,理是万事万物的根本,气则根据理的形式运动。这种“理气观”解决了宇宙的本体问题,对宇宙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和全面,为朱熹新儒学的形成提供了依据。
与宋代之前教育家相比,朱熹所编刻的教育类书籍具有鲜明的理学特色。比如《近思录》,此书是朱子耗时数年,在寒泉精舍完成,与学者吕祖谦合著,是理学的入门书籍。该书引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的语言,在此基础上,表达了自己的理学思想,形成了自己的理学体系。“这本书后来成为道学的基本教科书。 ”[15](P4)除此之外,朱子理学思想著述代表性作品还有《太极图说解》《西铭解》《通书解》《四书集注》《通鉴纲目》《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等。这些书籍凝聚着朱子的心血,蕴含着丰富的理学思想,并且都是在寒泉精舍完成。“寒泉精舍的数年,是朱子学问大进、著述丰硕的数年。 ”[15](P3)
朱熹对教育书籍的编刻,促进了福建教育的繁荣。北宋以来,由于开明的文化政策和统治者对文教事业的重视,使得到了南宋后,地处东南一隅的福建教育事业随之得到发展。朱熹在福建的活动时间最长,他对教育类书籍的编辑、出版与传播,进一步推动了福建教育的繁荣。学生接受教育的范围扩大,人数越来越多,学习所需的教材也得到满足。特别是建阳,作为朱子的活动地和当时全国三大出版中心之一,出版的教材不仅能够满足福建教育所需,还能远销全国甚至海外。福建各府、州、县学纷纷建立,读书之风盛行,科举事业兴盛。书院教育异军突起,成为福建教育领域里面的一匹黑马,崇尚授徒讲学、自由辩论之风。书院和官办学校双峰并峙,构成了福建教育的整体格局。
朱熹对教育书籍的编刻,带动了全国教育理念的改变。吴邦才、陈国代曾把朱熹对全国教育事业的贡献归纳为三个大的方面:一是“从政为民,立教厉俗”。朱熹是在崇文抑武的国策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大儒,主张抗金,“终身不忘恢复中原失地”。从政期间,积极从事教育活动,加强学校管理,在发展教育方面功劳甚大。通过教育来传播理学,实施教化。“朱熹不仅在各地施教于民众,灌输正心诚意的理念,还冒死在奏章中提出‘格君心之非’以‘正君心’,要求限制皇权不使私欲膨胀,以端正治理天下的根本。”[14](P73-74)二是“与时俱进,编著教材”。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继承和发扬了北宋以来二程、周敦颐、张载和邵雍的学说,形成了庞大而完整的体系。朱熹学术研究包罗广大,内容涉及经学、史学、文学等各个方面。“广注儒家典籍,为广大士子提供最佳读本,用以抵御异端邪说。”[14](P75)三是“家居讲学,接引后来”。朱熹始终把“家居讲学,接引后来”作为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来做,他通过讲学,传播知识,培养人才。在其讲学50余年生涯当中,教过的学生有姓名可考者就达482人,这些学生分布全国各地。因此,朱熹也“成为最具影响力、最为后世景仰的教育大家”[14](P75)。
吴邦才、陈国代全面概括了朱熹对全国教育事业的贡献。其实,朱熹对教育事业的贡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教育类图书的刊刻、印刷与出版。教育类图书的出版,传播了其教育思想,这些思想给当时全国教育界带来一股新风。朱子的很多教育理念在当时都具创新意义,对后世仍有启示价值。比如,朱熹对基础教育的重视。朱熹认为,少长阶段,从八岁开始,应学习礼仪和六艺。“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16](P3672)“及其少长,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间,各有以知其义理之所在而致涵养践履之功也。”[17](P227)通过小学这样一个阶段的学习和准备,为大学阶段学习义理之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总之,朱熹作为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出版家,他不仅编书,还刻书,促进了教育出版事业的进步。他在宋代教育出版史甚至整个古代教育出版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朱熹所编刻教育类书籍质量过硬,内容充实,对学校教育和知识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举子参加科考提供了质量过关的参考书籍。朱熹所编刻的自己的著述,里面凝聚了他本人宝贵的教育思想。随着这些书籍的普遍传播,书中的观点和思想也逐渐被读者所接受与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朱熹编刻的教育类书籍,传播和推广了自己的教育理念。这种教育理念不仅对当时教育事业有启示意义,而且对当下教育工作者从事教育活动,也有借鉴作用。朱熹教育理论和教育传播思想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1]朱熹.谢上蔡语录后记[M]∥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52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2]王懋竑.朱熹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8.
[3]朱熹.与向伯元[M]∥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5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4]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5]方彦寿.建阳刻书史[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
[6]徐德明.朱熹刻书考略[C]∥朱杰人,严文儒.朱子全书与朱子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7]朱迎平.宋代刻书产业与文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8]卢美松.八闽文化综览[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
[9]朱熹.刊四经成告先圣文[M]∥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53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10]朱熹.书临漳所刊四子后[M]∥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51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11]林振礼.朱熹新探[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12]朱迎平.南宋文人参与刻书活动初探[C]∥邓乔彬.第五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
[13]朱熹.书语孟要义序后[M]∥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5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14]吴邦才,陈国代.朱熹对教育的贡献新论[J].海峡教育研究,2013(3).
[15]朱杰人.朱子全书前言[M]∥朱熹.朱子全书: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6]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朱熹.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7]朱熹.答吴晦叔书[M]∥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46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