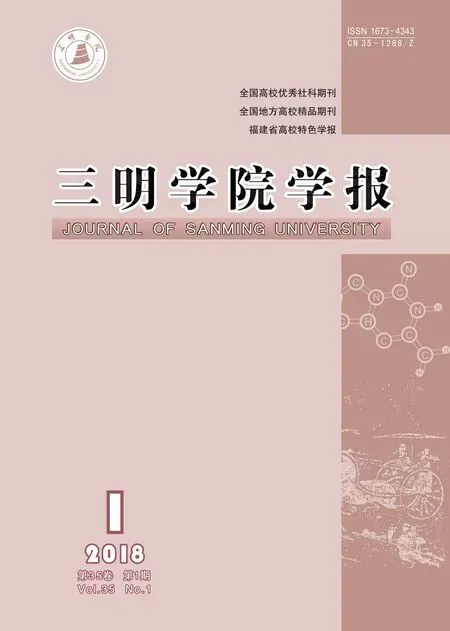从中医情志学看元稹的疾病及死亡
陈家愉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元稹(779—831)在《闻乐天授江州司马》一诗中写道:“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1](P606)这是他被贬通州时听闻白居易被贬江州时的作品,论此诗多关注元白的友谊,元稹的疾病极少提及。就元稹研究而言,其家世门第、诗歌创作与理论、仕宦品节、《莺莺传》等方面可谓众多,而元稹“垂死病中”的相关问题却鲜有人专门论及。据笔者统计,他有40余篇诗文作品提到了自己的疾病,吐露了他饱受疟疾、头风等病症的摧残,尤其是在元稹被贬江陵后,此类作品渐增。除了各种直接反映疾病的作品,还有诸多饮酒诗,更有表现一贬再贬之后困顿与苦闷,这些都是情志致病的诱因。笔者就从中医情志学视角,结合元稹相关诗文材料,以及其行动交游,分析他的疾病及死亡的相关问题,从而更好地把握诗人的作品主旨与心灵世界。
一、关于“情志”与元稹疾病的说明
“情志”是传统中医学上对情绪包括情感在内的特殊称谓,是对七情五志在内的情绪活动与变化的总称。乔明琦、张惠云编著的《中医情志学》将“情志”定义为:“人和高级动物共有的对内外环境变化产生的生理心理的复杂反应。”[2](P36)张丽萍在《现代中医情志学》将此概念进一步细化,认为“情志”是“在脑神的调控下,五脏精气变动而产生的喜、怒、忧、思、悲、恐、惊等,以情感(情绪)为主体兼顾认识、意志过程,具有体验、生理和行为等变化的多维结构心理现象”[3](P32)。具体来讲,我们可以通过情志的外在表现来管窥一个人的内心情志体验,因为元稹早已作古,这种表现就不能依靠情绪心理学中的面部表情、声音表情和身姿表情来分析,而应该将政治处境、饮食习惯、环境因素、致病因素等纳入考察范围,而这些将主要通过元稹的诗文作品进行捕捉分析。
元稹的诗文中最早涉及患病的是创作于贞元二十年至二十一年(804—805)的《病减逢春,期白二十二、辛大不至十韵》,述说了他疾病初愈时的情形,其中有“病与穷阴退,春从血气生。寒肤渐舒展,阳脉乍虚盈”[1](P298),乍暖还寒,气血不和。在元和四年(809)七月他的发妻韦丛去世后,元稹被贬江陵,由于水土不服外加丧妻之痛,大病一场。“江瘴气候恶,庭空田地芜”[1](P44)就是江州环境的写照。一直到元和十年(815)再贬通州以前他都长期受疟疾的折磨。《遣春三首》《遣病十首》《痁卧闻幕中诸公征乐会饮因有戏呈三十韵》等典型的疾病诗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元和十年(815)到元和十三年(818)在通州任上,元稹更是患上了筋骨病、头风、失眠等病症,身心俱疲。《遣病》《感梦》《献荥阳公诗五十韵》等诗都有所提及。离开通州北归后,元稹的疾病诗歌锐减,仅在长庆年间有两首诗歌提到自己的疾病,而且均属于回忆性质。元稹生命的最后十年为武昌军节度使,历任同州刺史、越州刺史、浙东观察史等职,奔波辛苦积劳成疾,大和五年(831)遇暴疾而亡。而史书中对他的死记载极其简略:“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疾,一日而卒于镇,时年五十三,赠尚书右仆射。”[4](P4336)寥寥数语,并不确切。故笔者拟就元稹情志疾病书写最为密集的三个时间段即被贬江陵、再贬通州、浙东六年为主线,从中医情志学以及病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元稹疾病、健康与死因问题。
二、元稹的疾病与健康问题
从现存诗文材料看,元稹的疾病主要是在江陵、通州和浙东这三个时期,患病原因与当地气候环境不可分割,元稹有云:“通之地,丛秽卑褊,烝瘴阴郁,焰为虫蛇,备有辛螫。 ”[1](P95)同时也与妻儿逝世、敷水驿受辱等意外事件相关。接二连三的打击使本就羸弱的身体愈加难以招架。另外,元稹在不少作品中都透露了自己时常处于饮酒醉酒的状态,加剧病情,危害甚大。“情志为病,并非单一情绪致病,而是多种情绪交织结合为病。”[2](P118)就此来看,综合多重内外因分析元稹的情志健康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一)被贬江陵的情志分析
元稹被贬江陵的直接原因是元和五年(810)的敷水驿事件。是时,元稹奉旨由洛阳回京,途径敷水驿,与之后到来的宦官产生争执,被其鞭打伤面。《旧唐书·元稹传》:“宿敷水驿,内官刘士元后至,争厅,士元怒,排其户,稹袜而走厅后。士元追之,后以箠击稹伤面。执政以稹少年后辈,务作威福,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4](P4331)《新唐书·元稹传》记载类似。箠,即马鞭,元稹遭受这一伙人鞭打,落荒而逃,承受了心理和身体的双重打击。而依照唐制,元稹为先到一方,毫无过错。这件事在《元稹评传》中考辨清晰,吴伟斌认为这背后是御史台与宦官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6](P141-151)而在此之前的一年,他的爱妻韦丛不幸去世,这对他的打击不必多言,《素问·疏五过论》:“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始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7](P821)亲人的骤然离去,自然感到痛苦悲伤。事后多年依然写下了《遣悲怀三首》这样的动人诗篇,感情真挚。“稚女凭人问,病夫空自哀。”(《城外回谢子蒙见谕》)[1](P589)这是元稹扶灵柩回洛阳时的诗句,情志过度波动后他已经身染疾病。经受连串打击,年仅32岁的元稹就开始出现了白发,创作于元和五年(810)的《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宁牛终夜永,潘鬓去年衰。”[1](P305)说明他元和四年(809)就有了白发,情志郁结,悲伤思虑过度。
元稹就是在沉郁哀伤之中踏上了江陵的路途,元和五年(810)初到江陵以后并未痊愈,在他赠友人的诗中还是流露病态:“他乡元易感,同病转相矜。”(《纪怀赠李六户曹崔二十功曹五十韵》)[1](P319)频繁宴饮也是他长期不愈的重要原因,这年他就创作了《先醉》《独醉》《宿醉》《羡醉》《同醉》《狂醉》等饮酒诗,既有对饮:“醉伴见侬因病酒,道侬无酒不相窥。”(《病醉》)[1](P511)也有独饮:“桃花解笑莺能语,自醉自眠那藉人。”(《独醉》)[1](P508)这样的过度饮酒对身体危害极大,产生了“酒伤”。《黄帝内经》的多个篇目均有涉及,禄保平归纳了酒伤的主要表现、病因病机的主要认识以及饮酒禁忌。[8](P146-147)《素问·厥论》:“酒入于胃,则络脉满而经脉虚。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阴气虚则阳气入,阳气入则胃不和,胃不和则精气竭,精气竭则不营其四支也。”[7](P402)喝酒直接损伤脾胃,阴津亏虚,气血不和。元稹此时身体虚弱,情志不畅,甚至已经出现了腹胀、耳鸣、眼翳等症状,“胀腹看成鼓,羸形渐比柴……耳鸣疑暮角,眼暗助昏霾。”(《痁卧闻幕中诸公征乐会饮因有戏呈三十韵》)[1](P348)这其中也有一些症状属于疟疾范畴,但喝酒导致胃胀和气血不畅得到印证。《灵枢·论勇》:“其(酒)入于胃中,则胃胀,气上逆,满于胸中,肝浮胆横。”[9](P538)气机上逆,盈满于胸,同时损害肝胆。元稹自己也意识到了饮酒对情志健康的影响,“昔在痛饮场,憎人病辞醉。病来身怕酒,始悟他人意。 ”(《遣病十首·其四》)[1](P196)“昔愁凭酒遣,今病安能饮?”(《遣病十首·其四》)[1](P196)尽管颇有悔悟之意,但他的诗中还是不断出现饮酒描写,这是除气候因素外元稹长病不愈的重要原因。
除了饮酒导致内脏精气的损耗外,江陵湿热恶劣的生活环境让元稹患上了更加严重的疟疾。“秋(元和八年),元稹患疟,日久未愈。”[10](P123)从他的组诗《遣病十首》可以窥见病情严重,“服药备江瘴,四年方一疠。岂是药无功,伊予久留滞。滞留人固薄,瘴久药难制。去日良已甘,归途奈无际。”(《遣病十首·其一》)久滞瘴乡,长期服药,未来却渺茫无期。“瘴气”多被理解为南方湿热山林间致病的毒气,也是南方地方病的代名词。宋代地理名著《岭外代答》就对瘴气有过相对完整的论述:“南方凡病,皆谓之瘴,其实似中州伤寒。盖天气郁蒸,阳多宣泄,冬不闭藏,草木水泉,皆禀恶气。人生其间,日受其毒,元气不固,发为瘴疾。轻者寒热往来,正类病疟,谓之冷瘴。重者纯热无寒,更重者蕴热沉沉,无昼无夜,如卧灰火,谓之热瘴。”[11](P152)他已经认识到瘴气致病与南方渒湿环境相关,把它分为冷瘴和热瘴。其实,瘴气或瘴疠是极其模糊的一种称谓,是多种病症的泛指,而疟疾是这类疾病中危害最大的一种,由疟原虫经按蚊叮咬传播,死亡率很高。所以,元稹才会有“巢燕污床席,苍蝇点肌肤……炎蒸安敢倦,虫豸何时无”(《苦雨》)之语。从元稹的具体症状上看,“痁”即是“热疟”。寒热交织,困倦乏力。“卧悲衾簟冷,病觉支体轻。炎昏岂不倦,时去聊自惊”(《遣病十首·其八》)[1](P196),正是其痛苦的表现。如此情形再加上前面提及的过度饮酒,发展为腹胀、耳鸣、眼翳等症候。好友白居易还曾经寄药给元稹,白诗《闻微之江陵卧病,以大通中散、碧腴垂云膏寄》云,“未必能治江上瘴,且图遥慰病中情”[12](P811),拳拳深情,关怀备至。可惜的是他的疟疾一直未彻底好转,到了通州更加严重,一直困扰着他。同时疾病正加速着元稹的衰老:“忆初头始白,昼夜惊一缕。渐及鬓与须,多来不能数。壮年等闲过,过壮年已五。华发不再青,劳生竟何补。”(《遣病十首·其五》)[1](P196)此诗作于元和八年(813),四年前始见白发,现如今已再无黑发,而他此时还不到40岁。
在元稹元和五年(810)至元和九年(814)的江陵岁月里,疾病哀痛伴随始终。在此期间亲人朋友也与世长辞,元和五年(810)元稹在李景俭的介绍下纳了一个妾安仙嫔,并生育子荆、女樊,不幸的是元和九年(814)安氏就卒于江陵。后来在《葬安氏志》中曰:“始辛卯岁,予友致用悯予愁,为予卜姓而受之……予虽贫,不使其若是可也。彼不言而予不察,以至于其生也不足如此,而其死也大哀哉!”[1](P1384)此外曾帮助自己的裴垍和友人吕温均于元和六年(811)相继去世,元稹有《感梦》:“自从裴公无,吾道甘已矣。”他也为吕温留下了《哭吕衡州六首》《哭吕衡州诗》等悼亡之作,感人至深。
(二)被贬通州的情志分析
元和十年(815)元稹移任通州司马,见《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前序:“元和十年(815)三月二十五日,予司马通州。二十九日,与乐天于鄠东蒲池村别,各赋一绝。到通州后,予又寄一篇。寻而乐天贶予八首,予时疟病将死,一见外不复记忆。”[1](P365)同诗首联下有注:“元和十年(815)六月至通州,染瘴危重,八月,闻乐天司马江州”[1](P366)通州即现在四川的达县,这里就明确了元稹被贬通州和具体到达的时间,到任后不久就复发了严重的疟疾。《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全诗也是巴蜀瘴地环境和自身病态的真实反映。“气浊星难见,州斜日易晡。通宵但云雾,未酉即桑榆。 瘴窟蛇休蛰,炎溪暑不徂。”[1](P366)这样湿热难耐的环境比起江陵更加难以应付。
元稹初到通州不久就染疾,《感梦》云:“我病百日馀,肌体顾若刲。气填暮不食,早早掩窦圭。阴寒筋骨病,夜久灯火低……答云痰滞久,与世复相暌。重云痰小疾,良药固易挤……何不善和疗,岂独头有风。”不单单是疟疾,他还患上了筋骨病,头风,咳痰等病。每到阴寒潮湿的夜晚就备受折磨,“秋茅处处流痎疟,夜鸟声声哭瘴云”(《酬乐天寄生衣》)[1](P628)。但百日以来他的病痛还是没能缓解,“瘴色满身治不尽,疮痕刮骨洗应难”[1](P625)。由于长期的气血亏虚情志不遂,引起了脏腑气血阴阳失调。元稹在此境遇下还承受着与家人分离的痛苦,“孩提万里何时见,狼藉家书满卧床”[1](P606)。元稹当年九月赴兴元治病,直到元和十二年(817)秋冬之际才回到通州。关于元稹疗疾的细节记载无从得知,然而从其在兴元的诗歌反映的状态来看,此行收效有限。《景申秋八首·其三》言:“嗢嗢檐溜凝,丁丁窗雨繁……强眠终不著,闲卧暗消魂。”[1](P480)雨夜还是难以入眠,胃不和则卧不安,这仍是他前期饮酒腹胀的结果。夜不能寐的病因固然很多,主要还是由于“情志失畅、劳逸失度、久病体虚、饮食不洁等导致机体阴阳失交、阳不入阴而成”[3](P109)。好在他的头风有所好转,元稹在元和十一年(816)的《献荥阳公诗五十韵》中提到:“传癖今应甚,头风昨已痊。”虽然在此后一年的作品中写到了“土膏蒸足肿,天暖痒头风。似觉肌肤展,潜知血气融”[1](P489),但他自身已经感觉情志复归畅达,气血融合。
经过一番辗转后,元和十二年(817)元稹又回到了自己任职的通州,疾病和颠簸悄无声息地加速着他的衰老,“病瘴年深浑秃尽,那能胜置角头巾。暗梳蓬发羞临镜,私戴莲花耻见人。白发过于冠色白,银钉少校颔中银。我身四十犹如此,何况吾兄六十身。”(《三兄以白角巾寄遗发不胜冠因有感叹》)[1](P616)此时的元稹只有 39岁,却已经是满头尽白,甚至有些秃顶了。在他和好友白居易的酬和诗中仍不时提到自己的病情和对友人的思念。“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酬乐天频梦微之》)[1](P621)两人一在通州,一在江州,在极度疲敝之际,元稹心中依然惦念着挚友。又如:“病煎愁绪转纷纷,百里何由说向君。老去心情随日减,远来书信隔年闻。”(《酬乐天叹穷愁见寄》)[1](P632)体质虚弱外加情志刺激思虑过深,产生郁症,而和老友恢复书信往来后则能得到有效疏导。
上文着重分析了元稹在被贬江陵和通州时期的情志病症,以疟疾为主兼有不寐、头风、眼疾等多种病症,其发病持续时间长,对情志健康破坏极大。元稹长期不愈的根由一半是天灾,一半是人祸。一方面,其长期过量饮酒的习惯和亲友故交的相继离开造成他屡受打击,情志不舒、心情抑郁;另一方面,瘴地苦恶湿热的环境让北方人元稹难以适应,水土不服,故感染疟疾,长病不起。如陈正平所言:“元稹在通州水土不服,得疟疾是真,但‘病心’却是他愁苦的根源,遣悲怀,枉凝眉,通州成了放逐他的伤心地。”[13](P26-30)
(三)浙东六年的情志分析
长庆三年(823)八月,元稹由同州刺史改任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史,一直到大和三年(829)末,他从宰相之位被贬同州,尔后又到了浙东,这意味着元稹逐渐远离政治权力的中心,内心是十分落寞的。元稹作《初除浙东妻有阻色因以四韵晓之》:“嫁时五月归巴地,今日双旌上越州。兴庆首行千命妇,会稽旁带六诸侯。海楼翡翠闲相逐,镜水鸳鸯暖共游。我有主恩羞未报,君于此外更何求。”[1](P670)诗中虽然多宽慰语,不过末二句还是有郁郁不得志之感。
离开同州后元稹一行先后途径泗州、润州、苏州,十月中旬到杭州并见到了时任杭州刺史白居易,白诗《答微之咏怀见寄》:“分袂二年劳梦寐,并床三宿话平生。”老友相逢二人都非常高兴,短短几日唱和不断。白居易赋《元微之除浙东观察使喜得杭越邻州先赠长句》,元稹回有《酬乐天喜邻郡》,只是元稹在欢快中又有一丝壮志难酬之感。稍作停留后元稹一行当年末赶到了越州,此后的几年元白二人的唱和却一直没有间断。两人的交往和酬和给元稹带来了莫大的安慰,使其心情得以平复。另一方面长庆四年(824)唐穆宗的死也使元稹感到心灰意冷,其《题长庆四年历日尾》云:“残历半张馀十四,灰心雪鬓两凄然。定知新岁御楼后,从此不名长庆年。”[1](P672)心中凄苦惆怅,另一首《长庆历》:“所叹别此年,永无长庆历。”[1](P223)因为在长庆一朝,元稹曾官至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内心非常感念穆宗。此时情志刺激是一种突发而强烈的状态,最易导致血气凝结,心悸昏厥。诸多作品里都有一种迟暮怅惘之感,如《馀杭周从事以十章见寄词调清婉难于遍酬聊和诗首篇以答来贶》:“多缘老病推辞酒,少有功夫久羡山。”[1](P667)“自惊身上添年纪,休系心中小是非。”(《酬复言长庆四年元日郡斋感怀见寄》)[1](P663)“良时年少犹健羡,使君况是头白翁……君今劝我酒太醉,醉语不复能冲融。”(《酬郑从事四年九月宴望海亭次用旧韵》)[1](P789)可见他的宴饮活动还在继续,元稹在浙东时期嗜酒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唐摭言》中得到印证:“元相公在浙东时,宾府有薛书记,饮酒醉后,因争令掷注子击伤相公犹子,遂出幕。”[14](P143)此事的真伪难以辨别,但也算是他爱喝酒的旁证。
浙东的六年除了和众多的同僚朋友酬和结集外,元稹仍然关心民生。他刚刚上任时就向朝廷进了《浙东论罢进海味状》想减轻人们的进贡负担。他首先告知了进贡的数量品种,“浙江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当管明州每年进淡菜一石五斗,海蚶一石五斗”[1](P1004)。随后说明了中间传递运输的人力成本,“每十里置递夫二十四人,明州去京千余里,约计排夫九千六百余人。假如州县只先期十日追集,犹计用夫九万六千余功,方得前件海味到京。”[1](P1004)接着叙述先皇体恤臣民,宗法尧舜等,应停止进贡海味。此状最终得以采纳,着实帮助当地减轻不少负担。宝历元年(825)元稹还倡导大家兴修水利,作《禹穴碑铭并序》颂扬了大禹治水的功绩。白居易《元稹志》:“又明年(宝历元年),(元稹)命吏课七郡人,冬筑陂塘,春贮雨水,农人赖之,无凶年,无饿殍。在越八载,政成课高。”[12](P3737)章孝标也有《上浙东元相》一诗对此诗进行赞扬,诗云:“黎庶已同猗顿富,烟花却为相公贫。何言禹迹无人继,万顷湖田又斩新。”[15](P5790)
元稹在浙东虽不得志,但仍勤勤恳恳,为国为民。此时与文人交往频繁觥筹交错,不免遭受病痛侵袭,“病痛梅天发,亲情海岸疏”(《醉题东武》)[1](P1563-1564),亦伴有思乡之绪,如:“故乡千里梦,往事万重悲。小雪沉阴夜,闲窗老病时。”[1](P471)
三、元稹的死亡
前面引述了《旧唐书》中关于元稹因暴疾而亡的记载,除此之外白居易在《思旧》一诗中云:“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12](P2023)认为元稹之死源于服用道家方术提炼的这种药物,这些记载都过于简略。今人吴伟斌认为元稹衰弱的身体、抑郁的精神状态和长期的贬谪生活是他暴亡的间接原因,而直接原因是巡视灾区中暑昏厥而亡。[6](P472-473)这一说法多主观想象的成分,要落实元稹的真正死因,还是要回归他晚年出任武昌节度使时的仕宦行事,出行交游中。
据《旧唐书》:“会宰相王播仓卒而卒,稹大为路歧,经营相位。四年正月,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4](P4336)元稹是在牛李党争之中被迫离任的,他于大和四年(830)正月接到改任诏书,随即同裴淑赶赴武昌。是时裴淑恸哭,人问其故,答云:“岁杪到家乡,先春又赴任,亲情半未相见,所以如此。”元稹当即赋《赠柔之》:“穷冬到乡国,正岁别京华。自恨风尘眼,常看远地花。碧幢还照曜,红粉莫咨嗟。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裴氏接着答曰:“侯门初拥节,御苑柳丝新。不是悲殊命,唯愁别近亲。黄莺迁古木,朱履从清尘。想到千山外,沧江正暮春。 ”[16](P64-65)这两首作品的写作背景不一定是如此,但我们可以得见元稹夫妇间的琴瑟相和,元诗末一联道尽半生漂泊的无奈。“元稹节度武昌,奏巩自副”[5](P5242),随后征召窦巩为副史,卢简求、周复亦入幕。窦巩初到武昌即和元稹时常宴饮,两人曾不止一次登上黄鹤楼,互有酬和。其《忝职武昌初至夏口书事献府主相公》云:“白发放櫜鞬,梁王爱旧全。竹篱江畔宅,梅雨病中天。时奉登楼宴,闲修上水船。邑人兴谤易,莫遣鹤支钱。”[15](P3041)元稹有“莫恨暂櫜鞬,交游几个全。眼明相见日,肺病欲秋天”之句,梅雨季节一般在农历五六月,此前大和三年(829)元稹在浙东时就作诗:“病痛梅天发,亲情海岸疏。”可见梅雨天气下他还是承受着病痛,这和此前通州时期情况相近。元和六年(811)六月他初到通州,作《感梦》云:“十月初二日,我行蓬州西……我病百日馀,肌体顾若刲。”[1](P200-201)也就意味着元稹六月刚到通州时就已经染上疟疾,这和他在浙东梅雨季节犯病的时间相近。此外,除了窦巩的《忝职武昌初至夏口书事献府主相公》记录了他们二人的宴饮之外,皇甫枚的《三水小牍·元稹烹鲤得镜》也有体现:“丞相元稹之镇江夏也,尝秋夕登黄鹤楼。 ”[17](P2)这里出现的时间变成了秋季,故推断他们时常宴饮于此。这一年元稹另有《赠崔元儒》:“今日头盘三两掷,翠娥潜笑白髭须。”[1](P585)头盘就是行酒令所用的器具,说明在他晚年的生活中酒一直是重要的存在。可以说,饮酒贯穿了元稹的仕宦生涯,即使在他重病期间也少不了以酒解愁。这也是其病长期难以彻底治愈的原因。
元稹逝世的时间是大和五年(851)七月二十二日,在他死前不久当地还爆发了水患,“是岁,淮南、浙江东西道、荆襄、鄂岳、剑南东川并水,害稼,请蠲秋租”[4](P543)。作为地方长官的元稹必然要采取措施减灾防灾,他在同州期间也有过《旱灾自咎贻七县宰》《祈雨九龙神文》《报雨九龙神文》这样应对灾害的作品。而据白居易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也提到了 “在鄂三载,其政如越”[12](P3737)。这些都表明无论是在浙还是在鄂,他的政绩都是突出的,也是关心百姓安危的。“请蠲秋租”表明灾害发生秋季以前的夏季,这与元稹逝世的时间相近。夏季疟疾的高发季节,元稹在通州和浙东都有病发史,而夏季的连续降雨,泛滥成灾,使得赈灾救灾后身体疲惫虚弱的元稹旧病复发,暴疟而亡。总之,元稹的死亡固然与他贬谪多处的恶劣气候环境致病相关,也和他毫无节制的酗酒导致疾病反复发作密不可分。如此看来,元稹53岁早逝也是其“早岁癫狂伴”的必然结果。
[1]周相录.元稹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乔明琦,张惠云.中医情志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
[3]张丽萍.现代中医情志学[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
[4]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吴伟斌.元稹评传[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
[7]南京中医药大学.黄帝内经素问译释[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8]禄保平.《黄帝内经》“酒伤”理论析要[J].浙江中医杂志,2004(4).
[9]河北医学院.灵枢经校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10]周相录.元稹年谱新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1]杨武泉.岭外代答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2]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3]陈正平.司马元稹笔下的通州风土人情[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7(4).
[14]王定保.唐摭言[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5]彭定求.全唐诗[M].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
[16]范摅.云溪友议[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17]皇甫枚.三水小牍[M].北京:中华书局,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