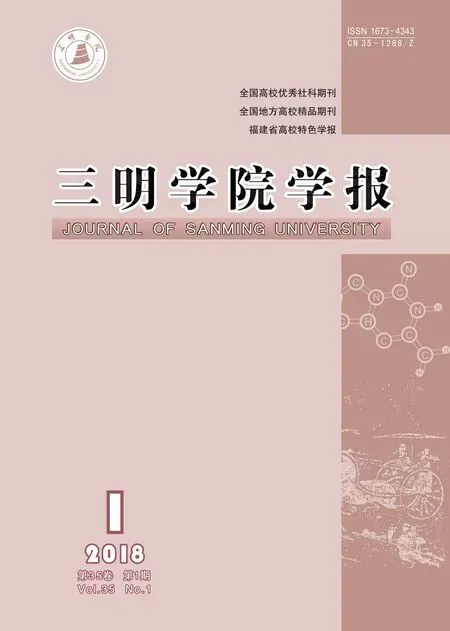晚唐闽地律赋兴盛原因新探
金沛晨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晚唐闽地律赋创作兴盛的原因,前人已有论之。可大部分观点,要么认为王审知爱好文学,为律赋兴盛创造了优渥环境[1](P49-53),要么把闽地律赋兴盛的原因用该地文学生态环境一以贯之[2](P23-28),却忽略了闽地与外地相比,文学发展既有共同条件也有特殊条件。
从黄滔《莆山灵岩寺碑铭并序》[3](P8700)中可知,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黄滔与陈蔚等人葺宅于闽莆山东峰读书。此外,《莆阳黄御史集》所附《年考》云:“公之生,其文宗开成庚申岁乎?”[4](P370)又《莆阳黄御史集·南海韦尚书启》云:“计奔岁贡于九州,榜擢词人于都省。”[4](P198)另据《唐方镇年表》,韦荷镇岭南东道为乾符元年(874)五月至四年(877)[5](P1042),以上可知唐懿宗咸通十五年(874)年黄滔年约35岁,才开始他的科举之旅。即黄滔35岁之前在闽,期间有十五年时间隐居山中读书。此时王审知尚未入闽,黄滔却早已辗转科场。
另据《登科记考》,徐夤于唐昭宗乾宁元年(894)中进士第[6](P899),乾宁二年(895)黄滔中进士第。[6](P908)黄滔此时应有五十多岁。《唐摭言·海叙不遇》记载:“谢廷浩,闽人也。大顺中颇以辞赋著名,与徐夤不相上下,时号锦绣堆。”[7](P114)可知徐夤虽在大顺中以前就有辞赋名,却直到乾宁元年(894)才中进士第,亦是久困科场。故他们的律赋作品,不管用于纳省卷还是投行卷,大部分应作于准备科举的这段时间。
此外据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考证,唐昭宗天复四年(904)徐夤、黄滔科举结束返闽所作多为应制酬唱作品。[8](P944-974)故不管黄滔还是徐夤,该时期的创作重心均不在律赋。王棨比徐、黄二人年代要早,更与王审知没太大关系。
一、中唐以来闽地教育发展为律赋兴盛奠定基础
中唐以来闽地教育水平提高,常衮、陈椅作出重要贡献,并早有以欧阳詹为代表的知名进士。关于此点,陈庆元《福建文学发展史》已有讨论。[9](P32-51)但这种教育发展只是律赋兴盛之基础,而不是主要因素。《唐摭言》载《会昌五年举格节文》:“其凤翔、山南西道东道、荆南、鄂岳、湖南、郑滑、浙西、浙东、鄜坊、宣商、泾邠、江南、江西、淮南、西川、东川、陕虢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超过一十五人,明经不得过二十人……金汝、盐丰、福建、黔府、桂府、岭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超过七人,明经不得超过十人。”[7](P2)可知福建在科举上属于劣势地区,进士名额较少。然而,一些进士名额比闽地多的地区,科举情况却没有闽地出色。如荆南地区,《登科记考》载:“刘蜕,《北梦琐言》:‘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解。’刘蜕舍人,以荆解及第,号为破天荒。《摭言》:‘大中四年,刘蜕舍人以荆府解及第。时崔魏公坐镇,以破天荒钱七十万资蜕。”[6](P815)刘蜕中第已是大中四年(850),而《登科记考》又载:“周匡物,《永乐大典》引《清漳志》:‘元和十一年,周匡物进士及第。’《太平广记》引《闽川名士传》:‘周匡物字几本,漳州人,唐元和十一年王播榜下进士及第,时以歌诗著名。’”[6](P665)元和十一年(816)与大中四年(850)相差34年,这从侧面反映闽地教育水平比荆南高。
可在《会昌五年举格节文》中,桂府与福建被列为同一科举地域,桂府也没有出现 “破天荒”的说法。据《旧唐书·王晙传》:“景龙末,累转为桂州都督。桂州旧有屯兵及转运,又堰江水,开屯田数千顷,百姓顿之。”[10](P2985)另《新唐书·韦丹传》:“还为容州刺史(今广西容县),教民耕织,止惰游,兴学校,民贫自鬻粥者赎归之,禁吏不得掠为隶。始城州周十三里屯田二十四所,教种茶麦,仁化大行。”[11](P5689)由此可知,中唐以来桂府经济、教育亦有较大程度发展。
所谓桂林三才子:曹邺、曹唐、赵观文,除曹唐进士身份存疑外,曹邺与赵观文俱为《登科记考》可考进士。如“曹邺,《唐才子传》:‘曹邺字业之,桂林人。累举不第,为《四怨三愁五情诗》。时为舍人章愨所知,力荐于礼部侍郎裴休,大中四年(850)张温琪榜中第。”[6](P814)“赵观文,《唐诗纪事》:‘乾宁二年崔凝下第八人登第。是年,命陆扆重试,而观文为榜首。’”[6](P907)曹唐是否中进士第,《登科记考》虽无记载,可《唐才子传校笺》云:“唐,字尧宾,桂州人。初为道士,工文赋诗。大中间举进士,咸通中,为诸府从事。唐与罗隐同时,才情不异……遂作《大游仙诗》五十篇,又《小游仙诗》等,纪其悲欢离合之要,大播于时。”笺证认为:“‘工文赋诗,大中间举进士’云云,为辛氏据己意而有所增益者……其时唐有为容管从事之意,唯因事稽留。(似留京应举)。是则唐于宝历前已返初应举,未必晚至大中时也。其举进士当在大和年间。”笺证又引:“《北梦琐言》:‘唐进士曹唐, 游仙诗才情飘渺……”[12](P491-492)故知曹唐亦为进士。
桂林虽和福建具有相同科举地域劣势,以及相似的教育、经济发展情况,但把桂林三才子和闽地律赋三大家相比,可知他们各自擅长的文体、题材俱不同。桂林三才子中,除赵观文今天流传作品太少无法窥其全貌,曹邺是著名现实主义讽刺诗人,曹唐的创作主要为游仙诗。哪怕是荆南“破天荒”的刘蜕,其诗作也大多直面社会黑暗现实。这充分说明了地方经济、教育文化水平的发展只能影响该区域的整体文士水平,却无法决定兴盛的文体和题材。闽地之所以律赋创作兴盛,虽以地方教育发展为前提,但最终影响他们创作风貌的必然是闽人特有的内在生命体验。
二、闽人边缘化意识对律赋创作的影响
《旧唐书·狄仁杰传》:“仁杰以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极为凋弊,乃上疏曰:臣闻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10](P2889)刘长卿 《送乔判官赴福州》诗亦云:“扬帆向何处,插羽逐征东。夷落人烟迥,王程鸟路通。江流回涧底,山色聚闽中。君去凋残后,应怜百越空。”[13](P1508)其中“夷落人烟迥,王程鸟路通。”二句可看出唐人对闽地的边缘化思考,即闽地属于人烟稀少的化外之地。这种边缘化建构虽出自京都文化圈对闽地的文化印象,可闽人也产生了被边缘化的意识。如欧阳詹《上郑相公书》:“某代居闽越,自闽至于吴,则绝同乡之人矣;自吴至于楚,则绝同方之人矣。过宋由郑,逾周到秦,朝无一命之亲,路无回眸之旧。犹孤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耘耨所不及,家家溉灌所不沾。”[3](P6026)从所引文章看,闽地举子这种文化边缘孤寂感来源于文化上“南隔五岭”的夷狄之感。欧阳詹类似的文章还有《送张尚书书》①,谈及赴京考场路上,闽地举子的窘迫与贫困,此处不具引。
事实上,欧阳詹在闽地早已声名大振,甚至出仕前名声已传到京师。李贻孙《〈故四门助教欧阳詹文集〉序》:“建中、贞元时,文词崛兴,遂大振耀,瓯闽之乡,不知有他人也。会故相常衮来为福之观察使,有文章高名,又性颇嗜诱进后生,推拔于寒素中,惟恐不及。至之日,比君为‘芝英’,每有一作,屡加赏进。游娱燕飨,必召同席。君加以谦德,动不逾节。常公之知,日又加深矣。君之声渐腾江淮,且达于京师矣。时人谓常公能识真。”[3](P5514)故陈庆元《福建文学发展史》将欧阳詹目为闽地第一个走向全国的文学家,评价可谓中肯。按理说,欧阳詹正处于意气风发之时,可《上郑相公书》《送张尚书书》却极力渲染他的窘迫与迷茫,这大概来源于闽地文人心中的文化自卑感——哪怕文学才能再怎么突出,若没通过科举得到京都文化圈承认,那么自己也没法抬头挺胸做人。是以闽人为摆脱这种心理,便只能全力准备科举,来寻求中央文化圈的认同。有关闽地文人这种文化边缘自卑感与中央文化圈之间的关系,杨亿力《走出“蛮荒”的阴影:唐代科举与闽地文士的认同》一文探讨十分深入。[14](P100-104)需补充的是,这种闽地文化边缘自卑感极易与一般寒士的孤苦之情相混淆。如魏晋南北朝以来左思、鲍照在诗中抒发的寒士不平之情,其实也是想通过做官施展抱负,并获得中央主流文化圈的认同。在科举盛行的唐代,文士这种孤苦之情更比比皆是。不同地方在于,闽地文人这种“远人”意识是集体的、带有强烈地域色彩,这从他们反复重申自己为“闽人”或“闽越人”可得知。黄璞的《闽川名士传》、黄滔的《泉山秀句集》②等记录闽地先贤事迹及整理其创作的集子,也是地方急于向中央文化圈证明自己的文化边缘自卑感之体现。这就区别于一般寒士的悲叹,而变成了集体文化意识。
闽人林宽《送李员外频之建州》诗云:“勾践江头月,客星台畔松。为郎久不见,出守暂相逢。鸟泊牵滩索,花空押号钟。远人思化切,休上武夷峰。 ”[13](P6999)闽人只有通过科举这一途径来实现自身“思化切”的目的,以此被京都文化圈承认,从而能真正成为有文化自信的闽地文人。黄滔 《答陈磻隐论诗书》:“且风本乎国风王泽,将以刺上化下。 苟不如是,曷诗人乎? ”[3](P8671)强调创作的教化论。实际上黄滔为闽地律赋创作三大家之一,律赋多咏古凄艳之作,说明黄滔虽认同诗教说,可长达几十年的科举之路让律赋深刻于他的骨髓之中。更何况,律赋正是其获取京都文化圈文化认同的最重要凭证,只要闽地举子还在举场应试一天,对律赋的钻研便不会停止。
三、闽地科举创作榜样对后来者的影响
闽地科举名额稀少及闽人文化自卑感促使闽人努力训练自己的律赋技巧,在此基础上,已进士及第的故乡先贤们自然会成为闽地举子的创作榜样。张籍《送李馀及第后归蜀》:“十年人咏好诗章,今日成名出举场。归去唯将新诰牒,后来争取旧衣裳。山桥晓上芭蕉暗,水店晴看芋草黄。乡里亲情相见日,一时携酒贺高堂。”[13](P4332)由这首诗我们清楚,举子一旦进士及第,连脱下的麻衣都会被人抢去。一般举子如此,更何况远比一般人更执着于科举的闽地举子呢?因此,在科举考试中具有突出表现的同乡人便成为闽地举子的学习标杆。在晚唐律赋大家黄滔、徐夤之前,有突出律赋创作实绩且名声响亮的闽地文士只有王棨一人。
欧阳詹在闽已名气大振,声名远达京师。黄滔《莆山灵岩寺碑铭》云:“初侍御史济南林公藻与其季水部员外郎蕴,贞元中谷滋而业文,欧阳四门捨泉水而诣焉,其后皆中殊科。御史省试珠还合浦赋,有神授之名。水部应贤良方正科擅比干之誉,欧阳四门之号,与韩文公齐名,得非山水之灵秀乎? ”[3](P8699)可知黄滔对欧阳詹无比尊敬。
然而,具体影响黄滔创作的人是王棨。虽现存黄滔作品中,对王棨并没有像对欧阳詹这般直接表达自己的崇拜之情,却并不代表他不受王棨影响。欧阳詹在全国名气虽比王棨大,可欧阳詹是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是韩愈古文运动团体中的中坚力量。意味着其创作实践也以古文为主。对于急于参加科举获取功名却长时间不第的黄滔、徐夤来说,以欧阳詹为学习榜样没有现实意义。
王棨之所以能以文闻名天下,主要靠律赋。从科举考试的现实意义上看,黄滔以王棨的律赋作为自己的学习榜样最适合不过。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相对于时代较远的欧阳詹,离自己年代相差不远的王棨显然更具有学习价值。据《登科记考》:“王棨,黄璞《王郎中传》:‘王棨字辅之。’按下文引《送王棨序》又作辅文,未知孰是。福唐人也。咸通三年郑侍郎从谠下及进士第……其年等第虽破,公道益彰,凡曾受品题,数年之间及第殆尽……公十九年内三捷,其于盛美,盖七闽未之有也。 ”[6](P840)咸通三年(862)王棨中进士第,而自大中十三年(859)黄滔葺宅于闽莆山东峰读书,至咸通十五年(874)参加科举开始的这一段时间里,王棨正好风头正劲,黄滔不会注意不到。上引《登科记考》关于王棨的材料中,还有两点非常值得注意。一是当时王棨名气十分大,以至于受到他品题的人,在几年内全都成了进士。这虽说有夸张成分在,但从侧面反映出王棨的科场地位。二是王棨在十九年内三捷,“盖七闽未之有也”,反映出王棨的科场生涯比较顺利,十九年内连续三捷,在闽地十分罕见。闽人后进不管黄滔还是徐夤,困在举场许久才成功登第,与王棨形成了鲜明对比。综上所述,结合闽地科举困难的现实及闽地举子的文化自卑心态,王棨这个律赋创作成就高超且科举应试十分顺利的闽人自然成为了闽地举子的学习榜样,这种榜样的作用是地域性的。
从文体角度看,李调元《赋话·新话》评王棨《回雁峰赋》《梦为鱼赋》:“证佐典切,比拟精工,凡此数联,犹不失比兴之遗意。”又说“《文苑英华》所载律赋至多者莫如王起,其次则李程、谢观,大约私试所作而播于行卷者,命题皆冠冕正大。逮乎晚季,好尚新奇。始有《馆娃宫》《景阳井》及《驾经马嵬坡》《观灯西凉府》之类,争妍斗巧,章句盖工。”“唐王棨《曲江池赋》中忽缀五字句云:‘有日影云影,有凫声雁声。’横空盘硬,音韵铿然,真千古绝唱。但一往皆轻俊之气沉郁浑古,不逮前贤,盖唐赋之后劲,宋赋之先声也。”[15](P5-18)虽李调元所举晚唐好尚新奇的律赋中大多为黄滔作,但其中《西府观灯赋》是王棨作品。据上例可知,王棨的作品既有“犹不失比兴遗意”的冠冕正大,也有“唐赋之后劲,宋赋之先声”的好尚新奇一面,将其看作黄滔、徐夤全然“好尚新奇”的律赋先导没有问题。陈庆元指出:“王棨的《倒载干戈赋》《三箭定天山赋》《玉不去身赋》等赋作都是冠冕正大的题目,可在其笔下,律赋成为了抒情的工具,所以王棨的律赋是由贞元、元和间命题的‘冠冕正大’转变到晚唐的‘好尚新奇’的关键。”[9](P53)反映出王棨律赋创作给之后黄滔、徐夤等人的创作施加的巨大影响。
从交游看,王棨、黄滔两人的交游圈有重合的部分,更直接说明黄滔能够通过他与王棨共同的朋友来接受来自王棨的影响。如写《王郎中传》的黄璞,是黄滔的兄弟。今《莆阳黄御史集》有《寄从兄璞》③诗。黄璞究竟和王棨有没交游,已不清楚。但作为《闽川名士传》的作者,肯定要四处搜集闽地名士资料,那么通过搜集资料必然对传主有所了解。更何况,黄璞本人也是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的闽地文士。据《登科记考》:“黄璞,《新书·艺文志》:‘璞,字绍山,大顺中进士第。’按徐夤《赠黄校书先辈璞诗》曰:‘驭得骊龙第四珠,退依僧寺卜贫居。’是璞以第四人及第。”[6](P895)因此黄璞为联系黄滔与王棨的一座桥梁。
陈黯是黄滔与王棨之间存在的第二个交点。陈黯实际与王棨有过交游,因黯有《送王棨序》:“去岁自褒中还辇下,辅文出新试相示。其间有《江南春赋》,篇末云:‘今日并为天下春,无江南兮江北。’某即贺其登选于时矣。何者?以辅文(应为“之”)家于江南,其词意有是,非前关耶!今春果擢上第。夏六月,告归省于闽,命序送行。某辞以未第,言不为时重。辅文曰:‘吾所知者,惟道与义。岂以已第未第为重轻哉!’愚繇是不得让。鳞群之众也,必圣其龙;羽族之多也,必瑞其凤。凤非四翼,龙非二首,所以异于鳞羽者,惟其稀出耳。”[3](P7983-7984)这篇序所透露出的不仅是陈黯与王棨关系较好,而且显示出闽地举子对进士身份的重视。黄滔有《颖川陈先生集序》:“滔即先生内侄也。 ”[3](P8655)点出了黄滔与陈黯之间的关系。
第三个交点是郑諴。《八闽通志·人物》:“郑諴,字中虞,闽县人,会昌中及第。文笔峭绝,累官国子司业刑部郎中,郢、安、邓三洲刺史。《唐·艺文志》载其有集。同乡人林滋字原象,亦会昌中及第。长于词赋,尝为《边城哓角赋》……又有詹雄者字伯镇,长于诗,格高笔壮。时称諴文、滋赋、雄诗为‘闽中三绝’。”[16](P463)林滋之前黄滔已经写碑文称赞过。至于郑諴,黄滔之前为了进士及第还曾向他行卷过。《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晚唐卷》考证,唐僖宗乾府三年(876)九月:“黄滔本年约三十岁,时在长安向刑部郎中郑諴行卷乞援,并代郑諴撰写多篇启文。”又乾符四年(877):“黄滔本年约三十八岁,在京落第将东归,时有书上书右丞崔沆,倾述食贫计尽,难寓长安之境况。又有留辞刑部郎中郑諴诗。”[8](P852-945)之所以认为郑諴是王棨与黄滔之间的交点,是因为王棨很有可能也向郑諴投过行卷。据谭泽宁《王棨研究》考证,唐僖宗咸通元年(860)王棨应前往郢州向时为郢州刺史的同乡郑諴求援,并推断862年王棨从郑从谠中第,应有郑諴举荐之功。[17](P27)这是完全可能的。据投行卷的规矩,投行卷需要先投给社会上有地位的人,然后由其帮忙举荐。郑諴早年已有文名,而且时任郢州刺史,还是王棨同乡。因此王棨向他投行卷求取引荐,再合适不过。
关于徐夤生平的资料更少,但他与黄滔关系很好。《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晚唐卷》考证,唐昭宗乾宁元年(894):“黄滔约此时有诗(《寄徐正字夤》)寄徐夤。”又昭宗天复二年(902):“徐夤约本年或稍前离汴梁返闽,旋为王审知所辟。时与黄滔、杨沂、王淡等人诗赋唱和。”[8](P852-945)知此后黄滔、徐夤在王审知幕下继续有交游。又徐夤有《赠黄校书先辈璞闲居诗》,可知徐夤与黄璞早有认识。《唐才子传校笺》:“徐师仁《序》引《九国志》本传云:‘乾宁初举进士……是岁释褐秘书省正字。’知夤于乾宁元年登第后,当年即授秘书省正字。《才子传》云‘鬓发交白始得正字,未知所凭。若据此,夤是年当已过五十岁’。”[12](P293)若是据《校笺》推论,则徐夤的年岁当与黄滔相仿,二者又是莆田人,所以早年相识的可能性极大。徐夤在诗学理念上亦 “崇尚晚唐”,他的《雅道机要》④就以学习晚唐为主。所以接受王棨影响应比黄滔来得更直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徐夤诗为“亦不出五代之格,体物之咏尤多……然当时文体,不过如斯”[18](P1302)。在这样的创作理念指导下,王棨能为徐夤树立一个值得学习的创作范式。总而言之,当黄滔和徐夤在律赋创作中紧随王棨而同样达到较高高度时,以这三人为中心,闽地的律赋创作文化圈便就此形成。王棨的律赋开启了地方性律赋创作与钻研的风气,而出于科举原因不得不以王棨为创作榜样的闽地举子,尤其是黄、徐二人则反过来以自己的创作来加强此风气,这就解释了为何晚唐律赋独能在闽地走向兴盛。
此外,晚唐律赋多以咏古抒情为特点。抒情暂不论,早在科举律赋命题时就已有用古事为题,如《登科记考》载开元二十二年(734)博学宏词科,注云:“是年试《公孙宏开东阁赋》,以‘风势声理,畅休实久’为韵,见《文苑英华》。”[6](P267)又贞元十九年(803)博学宏词科注云:“是年试《汉高祖斩白蛇赋》。”[6](P564)是故闽地文士多以咏古为题材是受到了科举律赋命题的影响。闽地文士的文化心态及大多困于考场多年的现实迫使他们不断进行律赋训练与律赋创作,此前科举考试既然有以咏古事命题,那么闽地文士也必会在这个题材上下功夫,更何况他们的创作榜样王棨,在创作上已趋向咏古抒怀,后进举子断不会忽视此点。久困科场,晚唐连年起义战乱势必会继续加重举子心中的文化边缘感,使他们用来科举求仕的律赋朝抒情化方向发展。律赋本身创作程式在当时也并无完全僵化,在限韵和篇章结构中,尚有较大自由度,同样便于举子抒情。曹明纲《唐代律赋的形成、发展和程式特点》一文中已论述较为详尽。[19](P115-119)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提到贞元末至元和年间出现的功利主义思想,随着政局变化而逐渐消退。咏古爱情题材大量出现,士人心态发生了变化。[20](P222-224)说明咏古亦是时代大风气。 但律赋兴盛与律赋创作水平息息相关,也与文士对文体的喜好偏向有关。闽地举子需要通过学习同乡榜样的律赋创作来提高自己写作水平,律赋因此成为闽地举子的文体偏好。
综上所述,晚唐闽地律赋创作兴盛的根本原因,是晚唐著名律赋作家王棨凭其高水平的律赋创作和科场地位,成为因文化自卑而急于科举及第的闽地后继举子们的学习标杆。律赋的创作、切磋由此成为地域群体性活动。在这个地域创作群体中,以辞赋著名的文士如黄滔、徐夤,又以他们的作品继续弘扬律赋创作的风尚,最终导致闽地律赋的兴盛。因此,地方教育水平发展只是提高了该地文士的整体文化水平,而时代风气也主要决定了律赋的题材以咏古为主。若仅仅以地方教育水平或时代风气来解释晚唐闽地律赋的兴盛,却忽视闽地文士的特殊心理状态和人生经历,则既不全面也不准确。
注释:
① 该文主要侧重描写闽地文士进京赶考路上的穷困潦倒。见《全唐文》卷五九六,第6024页。
② 《新唐书·艺文志》卷五十八载:“黄璞闽川名士传一卷。”第1485页。卷六十载:“黄滔泉山秀句集三十卷。”注云:“编闽人诗,自武德尽天佑。”第1625页。
③ 由此可知,璞是滔兄弟无疑。
④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二载:“雅道机要二卷。”注云:“前卷不知何人,后卷称徐夤撰。”
[1]何绵山.五代闽国文学探论[J].文史哲,1997(6).
[2]陈毓文.唐末五代闽地文学生态述论[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7,32(6).
[3]董浩,阮元,徐松,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黄滔.莆阳黄御史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5]吴廷燮.唐方镇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徐松.登科记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王定保.唐摭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傅璇琮,陶敏,李一飞,等.唐五代文学编年史[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
[9]陈庆元.福建文学发展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10]刘昫,张昭远,贾纬,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1]宋祁,欧阳修,范镇,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傅璇琮,储仲君,吴企明,等.唐才子传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3]曹寅,彭定求,沈三曽,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4]杨亿力.走出“蛮荒”的阴影:唐代科举与闽地文士的认同[J].文艺评论,2015(4).
[15]李调元.赋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6]黄仲昭.八闽通志[M]卷六十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17]谭泽宁.王棨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2.
[18]永榕,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9]曹明纲.唐代律赋的形成、发展和程式特点[J].学术研究,1994(4).
[20]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