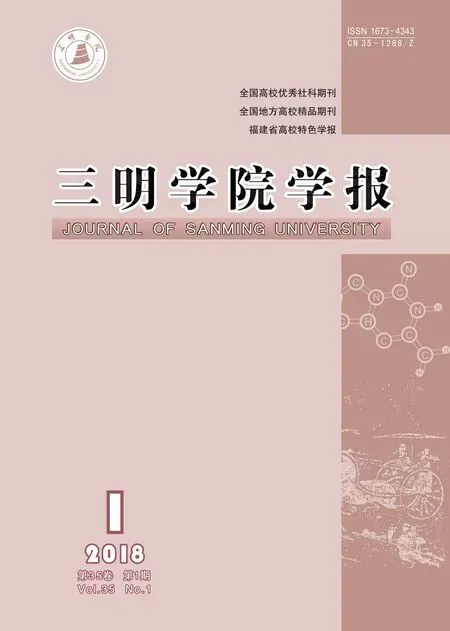从《寇变纪》看福建宁化县之黄通民变
金丹
(渤海大学 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0)
“民变”是一个概念宽泛的词语。长期以来,对于明末的民众运动,无论是农民起义、奴变或者是城市的民众事件,往往统称为“民变”①。晚明诸生李世熊所写之《寇变纪》,记载了宁化及其附近地区的农民起义等情况,详录了明末清初时期宁化地区民变及“贼”“寇”叛乱后的地方社会状况,是研究宁化民变的重要史料。本文选取其中黄通民变之史料,对民变发生的原因及影响进行探讨。
一、黄通民变原因之多样性
宁化,古称黄连峒,位于武夷山东麓,福建西隅。明洪武元年(1386),改汀州路为府,宁化属福建布政司汀州府,清朝袭之。宁化地区以“山水为营卫”[1](P465),“叠嶂驶流,控带雄远”[1](P460),其民“性气刚愎”[1](P622)。此外,与江西省石城、广昌等县相邻,边界长达百余公里,管理较为松散,为民变频发之地。县志也记载该地 “其治日常少,乱日常多”[1](P445),而黄通领导的民变发生在明末清初时期。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闯贼陷燕京,至尊义殉社稷,勤王之旅骚动南北,奸宄飚举”[2](P32),福建地区的“寇”“贼”叛乱对宁化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
兴、泉之乱,馘斩数千。余孽漂入漳州,旋及万人。抚军张公肯堂,提师捕之。贼复旁扰汀邑。[2](P32)
时有粤寇萧声、陈丹等,率众数千,号阎罗总,剽掠虔州部境,亦渐逼临汀。郡邑告急,抚军乃遣兵五百援汀,督以把总林深、郑雄、傅玉麟。时贼已陷汀之古城镇,焚戮备惨。[2](P32)
(十月十八)贼亦退瑞金属境。是时钟玲秀之余党张恩选者号猪婆龙,聚众数百人与阎总遇,欲与之合。而粤寇狼戾甚于张,彼此藉为声势而已,终不能合也。而杭、永、瑞金诸村落萧然无鸡犬矣。邑中大戒严。乙酉春正月张抚军驻上杭,以宁化知县于华玉监纪。阎寇从汀境出宁化之淮土,大肆焚掠,邑大震。[1](P448)
由此可以知道,福建沿海地区的兴州府和泉州府的贼寇叛乱发生后波及位于福建山区的汀州府,后虽派兵镇压,但都被击溃,以至于宁化周边的上杭、永定、瑞金等地百姓闻风而逃,宁化处于戒严状态。
至八月,粤寇又“由故道驻松溪”[2](P33),在宁化周边地区的泉上里和泉下里两个地方均设乡兵驻扎,乡民收取军饷给乡兵:“凡食租一石者,征米一升而已。屯坝上者八日,给粮一升。屯莲花峰者,人给粮一升半。 ”[2](P33)莲花峰为松溪到宁化的要路,于是当地居民堵守十日多,导致供应的物资缺乏,乡民苦之。在这时期,明廷逐渐增加各种苛派,主要有辽饷、练饷、剿饷等名目外,又加派房号税、契税、典铺税等。[1](P513)虽然在此期间实行“一条鞭法”,但“条鞭所派均徭诸目费既十倍于明初”[1](P528),且“以轮甲则递年十甲充一岁之役;条鞭则合一邑之丁粮充一岁之役也。轮甲则十年一差,出骤多易困;条鞭则每年零办,所出少易输。譬十石之重,有力人弗胜,分十人运之,即轻而举也。夫十年而输一两固不若一年一钱之轻且易也。人安目前孰能岁积一钱以待十岁后用者,又所当之差有编银一两而幸纳如数者有加二三至倍蓗,相仕百者名为均徭,实不均之大矣”[1](P527)。可见此时期赋役是十分不合理的,这些严重的经济负担对于本来就生活困苦的乡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进一步加速了民变发生的进程。
除此之外,就黄通本人来说,存在黄通与黄氏族人以及黄通与官府之间的矛盾。据 《寇变纪》记载:崇祯庚戌[辰]辛巳年间,黄通的父亲黄流名与中宜地李留名[民]、李简以及半寮的宁文龙等为死党,“颇剽掠,诸村落莫敢谁何”[2](P34)。后来与石城(江西省)民众温□等争夺“市利”,杀死数十人,石城民众进行控告。知县徐日隆带领民兵前往拘捕李留名和李简,留名率众相抗。后汀州推官宋应星“单骑入中宜地”[2](P34),诱李留名入狱。但政府想要“长系留民,而释其余党。简脱网后,益集党蚕食诸邻境。徐令乃重悬赏格购简党。于是四乡各执其倡乱者,而简党皆就擒,惟黄流名幸免。 ”[2](P34)因此活下来的黄流名“祭祖归宗,鹰眼枭声,犹雄视其族”[2](P34)。 同族的无赖黄整很是气愤,杀了黄通之父流名,流名的七个孩子,将其告到官府,黄整因此入狱。当地的有司知道流名一向行为不轨,心里很高兴黄整将流名杀了,不理会黄通的诉讼,因此黄通开始同其族与官府势不两立。于是,迁居留猪坑(位于宁化县城的北部)的黄通等黄氏族人就与居住在宁化县城的黄氏族人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这样的背景下,黄通率领佃农武装一度攻进宁化城进行起义,《寇变纪》中有明确记载:“隆武二年丙戌六月二十六,而宁化有黄通破城之变。 ”[2](P34)这在《宁化县志》中也有明确记载:“丙戌六月二十六日,长关黄通率田兵千数百人袭入邑城。”[1](P448)也进一步印证了黄通民变的发生。顺治四年(1647),黄通从乌邨点关返回下埠时,遭伏击致死,至此黄通领导的民变宣布结束。
二、黄通民变影响之双重性
纵观晚明时期南方发生的民变,都对当地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江苏宜兴民变对当地的影响,一方面,在民变发生过程中,政府对豪奴的惩治警醒了一部分士绅,使他们约束自己的奴仆,减弱对农民及佃户的催征力度;另一方面,宜兴陈一教等乡绅,利用自己的财富、权势及深厚的政治背景,官绅勾结,为害地方,造成了江南社会的动荡。[3](P50-P58)苏州地区的民变使国家的经济政策松动并进行了调整,导致苏州地区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但是苏州民变的次数多,时间长,对当地的破坏已经很深,加上自然灾害不断发生,致使社会秩序遭到破坏[4](P23-P24)。由此可以看出不同地区的民变,其影响都是不同的。黄通领导的民变对宁化当地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也有其独特性。
一方面,黄通领导的佃农运动有进步性的因素。
首先,在钱粮方面,提出了减少佃户负担的口号,并带领乡民开展抗租运动。
凡黄族田产附近留猪坑者,通皆据而有之。通思大集羽翼,乃创为较桶之说。盖吾邑以二斗(二十升)为一桶,凡富户租桶有大至二十四五升者,比粜米则桶仅一十六升,沿为例。而田主待佃客亦尊倨少恩。通遂倡谕诸乡,凡纳租皆以十六升之桶为率,移耕冬牲豆粿送仓储例皆罢。[2](P34)
黄通占领同族地主土地,号召减少“佃租”,将交租的测量模具的容量减少20%,农民的负担能够有所减轻,于是民众纷纷归顺黄通,使得黄通获得了诸乡农民的支持。
其次,当黄氏家族内部产生的矛盾达到无法调节的地步时,黄通在留猪坑将县管辖下的各里联合起来,建立了 “长关”的军事组织。“(黄)通因连络为长关,部署乡之豪有力者为千总,乡之丁壮悉听千总所调拨。通有急,则报千总,千总率各部,不日而千人集矣。”[2](P34-35)这种军事组织在当地起到了防卫乡里的作用,“二十八早,贼取道泉下,泉下率乡兵阻之。乡兵望帜而靡,贼遂杀武进士邱隽、武举人吴维城、庠生邱浙、武生邱沐、庠生邱澍之妇谢氏,余无足纪。贼由城门钟坑出中沙,杀黄通长关兵数十人”[2](P36)。在这种情况下,长关兵仍能坚持斗争,“已过禾口石壁,长关兵追之,乃反戈而焚其巢,径出长汀入赣境”[2](P36)。 说明长关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当地社会秩序的稳定。
此外,“长关”不仅是军事组织,而且是一种政治组织,“通所部词讼不复关有司,咸取决于通。通时批行于诸千总,自取赎金而已”[2](P35)。黄通将词讼权力收归己有,当有诉讼时,皆取决于通,从而把握了地方的刑事权。在建立“长关”组织的过程中还制定了“长关编牌册”,“至丁亥二月,而通之兄弟始至吾乡,连长关编牌册,通弟黄赤登坛点阅,虽青襟孝廉俯首坛下伺之”[2](P36-37)。“长关编牌册”是一种户口登记账簿,按地区登记了各县居民的情况,由黄通的弟弟即“青襟孝廉”的黄赤进行管理,所以长关组织也具有一定的私属性。总之,“长关不单纯是一个具有战斗性的军事组织,而且转化成为具有政治色彩的组织,并逐渐转换成为连接各县‘诸乡’之间的地域性的权力组织”[5](P36)。
在宁化黄通领导的民变影响下,附近州县的民众也相继进行斗争,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瑞金的田兵斗争。清顺治三年(1646),田主肆意加租欺压佃农,加之官府额外苛索,佃农生活困难。邑人河志源、沈士昌等聚集各乡佃农,揭竿起义,“效宁化、石城故事,倡立田兵,旗帜号色皆书‘八乡均佃’。均之云者,欲三分田主之田,而以一分为佃人耕田之本,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6](P390)。 知县刘翼理解佃农的所作所为,满足了他们的部分利益。“立盟,捐额租,除年节等项旧例。粮户不敢出一言,唯唯而已。 ”[6](P391)后来这部分田兵与宁化以及石城的佃农一起进行斗争,但是都被统治者剿杀,可他们反对不平等以及为自己争取正当利益的精神还是值得认同的。
另一方面,黄通领导的佃农抗租运动也带来消极的影响,造成了当地统治秩序的混乱。
首先,黄通将个人的情感放在首位,劫掠富户,造成了当地经济的凋敝。“通时时有入城复仇语”[2](P35),一心只想复仇,而且跟随黄通的诸佃客也 “思入城, 快泄其平时之睚眦”[2](P35), 结果“邑民之贸食四乡者,通党皆剥掠之”[2](P35)。 更严重的是杀其族诸生黄钦镛的侄子黄招,抢掠富室百数十家,将城外的庭院焚毁,摧毁城垛十余丈,直接的损失达数万。
其次,黄通建立的“长关”的军事组织以及“长关编牌册”的人口登记册,使地方社会结构有所改变。因为这种组织具有了政治性,所以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通已连吾乡,则断决罕坑李应、李黄苟之讼。李应破资至五百金,应之姻家罗朝辅颇染指,通弟黄吉诛责之,有违言。吉怒,遂焚朝辅之屋,拘朝辅,责赂二百金乃释。”[2](P37)黄通利用手中的词讼权力收受贿赂,扣押举人曾文灏时,要求交纳的赎金高达一千二百两。这是“长关”组织对于当地民众不利的一面。
最后,从李世熊对于黄通民变的记叙来看:“隆武二年丙戌六月二十六,而宁化有黄通破城之变。 ”[2](P34)“破城”二字体现出民变对社会秩序的破坏程度。黄通死后,他的军事力量仍残留着,宁文龙为了取代黄通,继续与其他势力进行斗争。为了支持明朝,乡人张简带领士兵二百余,与宁文龙、罗庭相呼应,驻扎在魏坊峒。“九月初一,宁、罗兵三千余,突从中溪出吾乡。吾族家累辎重及合里居民皆未徙, 惶遽失措。 ”[2](P38)因此造成地方的混乱,而因叛乱迁来的移民也对当地社会秩序造成了破坏,“二十五日,罗庭之部卒孙某、连某者,亦率数百人,各挟所掠妇女辎重由将乐至吾乡,诘责前日之夺彼资物者,大索竟日,必返其故璧乃已。吾乡之破藩篱不复振顿自是始也”[2](P40)。
三、结语
农民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激烈的社会冲突,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当统治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不断对农民进行压榨时,农民就会起来反抗,同封建制度进行斗争。在福建地区的民变中,佃变占有很大一部分比重。[7](P328)地主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不断对佃农进行压榨,宁化地区也是如此,比如在收租时:“盖邑以二十升为一桶,曰租桶。及粜则桶一十六升,曰衙桶,沿为例。”[1](P448)这是官方的租税,而“凡富户租桶有大至二十四五升者”[2](P34), 可以看出地主对佃农的剥削程度。除此之外,几乎每一次农民战争都与当时的自然灾害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即使发生一些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时并没有很大的自然灾害,可引发这些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小范围农民战争,大部分是在灾荒之年,或者说是在当地极度混乱的情况发生的。本文探讨的福建宁化县的民变就是在当地极其混乱的情况下逐渐发展的:“寇”与“贼”以及福建地区南明政权中以彭妃为代表的反清势力的活动等都造成了社会的混乱。这是民变发生较为重要的一部分因素。
黄通领导的民变,对于减轻地租,缓解了农民的赋役压力;建立长关组织,保护地方安全,维护区域秩序;号召其他地区佃农反抗地主对自己的不平等待遇等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民变对地方社会秩序的破坏却是不可估量的。民变发生后“四乡之薪米,旧输县者,通皆禁阻之”[1](P448),且“破城中资财不可算”[1](P448),造成地方社会的混乱。通过黄通领导的民变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在受到巨大压力进行民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民变中烧杀抢掠,对当地民众造成生活的不便。因此,我们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今天的中国,农业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仍是重中之重。只有使广大农民生活稳定,国家才能繁荣富强,人民才能得到更好的生活。
注释:
① “民变”的定义可参见商传的《走进晚明》第141-164页,201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黎景曾,黄宗宪.民国宁化县志[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2]李世熊.寇变纪(后纪、寨堡纪、堡城纪附)[M]//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清史资料(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李迎军.明末宜兴民变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5.
[4]唐光蕾.晚明苏州民变初探[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1.
[5]森正夫.寇变纪的世界——李世熊与明末清初福建宁化县的地域社会[J].中国文化研究,2005(冬之卷).
[6]郭灿修,黄天策.瑞金县志[M].故宫珍藏丛刊第117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
[7]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