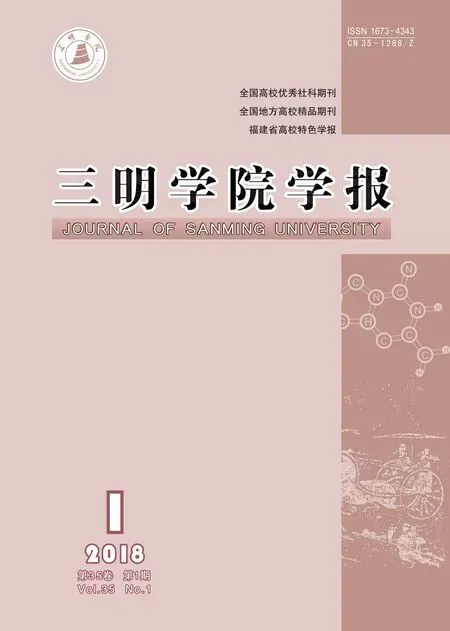《诗林广记》格法评释
邱光华
(三明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诗林广记》是宋末元初杰出诗评家福建建安(今建瓯)人蔡正孙编纂的一部诗学著作,约成书于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明清三代均有刊版行世,至今仍流传不替。据蔡正孙自序,该书一个主要的功能是 “课儿侄”。以此之故,《诗林广记》非常注重对诗歌格法进行辨析和阐说,既择取大家名家的诗篇作为范例,又汇集诸家评注以示堂奥。所谓“格法”,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领域,是指诗的写作规则和法式,虽不无对内容意义的关注,但主要倾向于形式技巧方面,这在宋代以来表现得尤为突出。[1](P346-386)具体到《诗林广记》,基于格法视角或以格法为对象而展开的评注,颇为全面地反映了蔡正孙的诗法观和批评旨趣。对于《诗林广记》中的格法论述,此前马婧《〈诗林广记〉研究》一文曾予以探讨,颇得体要。[2](P42-47)另外,曹艳贞《〈诗林广记〉的诗学观》一文也曾在“作诗之法”的层面论及“造语”“用事”“立意”。[3](P49-53)或许因二文的研究重点并不在于此,故仍有未尽之处。本文拟进一步对《诗林广记》格法评释的各项议题进行梳理,厘清情状,显现特征,并揭示观念旨趣及其背景。
一、音律、用字与用事
《诗林广记》中的诗作,绝大多数为律体诗。律体诗有一套精密的声韵法则,合乎格律是其中一个基本的要求。作为一部以诗学教育为主要编纂旨趣的著作,此书对平仄、用韵等音律问题当然不会忽视。如,前集卷二选入杜甫《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得寒字》《谢严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苏轼《次韵韶守狄火夫见赠》(二首之一)、韦应物《雪夜下朝呈省中一绝》等“平仄变体”之诗作,并经由评注标示“变体”的意义以及某些变体形态的兴替。[4](P40-41)又如,后集卷五选入黄庭坚《观伯时画马礼部寺院作》诗及胡仔的效体之作,称引胡氏评语,对“促句换韵”的法式进行解析;卷八韩驹 《进退韵近体》、李师中《送唐介》二诗后,分别称引胡仔和《缃素杂记》的评注,标示“进退韵”格的性质、起源及含义。[4](P307,P380-381)在“正体”之外标举若干“变格”,一方面是介绍诗歌的格法知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有意借此提示创变之途。蔡正孙这一“正”“变”兼容的格法观,同样也体现在他对诗歌史上某些用字方式或用字现象的评注上。
作为诗歌创作的一项基本技法,用字在南宋以来的诗学批评中颇受关注。蔡正孙对此也很重视,如他编纂的《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下文简称《联珠诗格》),卷四至卷十九所标诗格约二百余目,都是以用字为中心的字格;在具体评注中,还屡屡点明诗作下字成功之处,或是指出用字方面的特点。[5](P233-239)实际上,此前《诗林广记》对用字的论列,已反映出蔡氏在这一议题上的基本态度和观念趋向。如,前集卷七贾岛《题李凝幽居》诗后称引“《刘公嘉话》”的记载,展现诗人对下字的讲究。[4](P128-129)又如,后集卷六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诗、陈师道《早起》诗之后,分别称引《潜溪诗眼》《诗话》与《艺苑雌黄》的记载,标举李白、王安石、陈师道诸人诗的下字佳妙之处。[4](P333)再如,前集卷三李白《宫词》诗后称引胡仔评语,拈出李白、杜甫、韩愈诸人诗中用字不合情理的地方。[4](P46,P54)对于诗歌写作中的用字技法,可谓再三致意。
不仅仅是指陈诗歌写作上用字的得与失,蔡正孙还曾揭示出用字的若干功能和意义。如,前集卷四、卷五分别选入刘禹锡《生公讲堂》诗、柳宗元《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见寄》诗,蔡氏称引《洪驹父诗话》《谢叠山诗话》《漫叟诗话》,借以表明用字关乎诗篇题旨的表达。[4](P72,P90)又如,前集卷九王驾《晴景》诗后,称引《苕溪渔隐丛话》所载意见:此诗经王安石改正七字后,“语工意足,了无镵斧之迹”[4](P165)。蔡氏借此表明,用字关乎诗作整体的艺术境界。再如,后集卷九魏野《晨兴》诗后,称引“《欧公诗话》”的见解,表明用字关乎诗作的审美格调和韵味。[4](P388)
此外,《诗林广记》还注意到一些用字方式或用字现象。其一是“重叠用字”,即在一首诗中重复用到同一个字。如,前集卷四刘禹锡《赠白乐天》诗的颔联和颈联都用了“高”字,蔡氏称引《三山老人语录》,点明唐代以来诗人对“重叠用字”所持态度之变迁。[4](P77)其二是“下双字”,也称为“下连绵字”。如,前集卷五王维《秋雨辋川庄作》诗的颔联上下句分别用了“漠漠”和“阴阴”,蔡氏称引《石林诗话》《雪浪斋日记》所载诗例及评点,对王维、杜甫、韩愈、王安石、苏轼等唐宋诗家在其诗作中下双字所达到的高妙境界加以标举。[4](P95)其三是“借对字”,也称为“借对体”,即借助同音或同义的字词以满足诗句对偶的要求。如,前集卷八孟浩然《裴司功员司士见寻》诗后,称引《诗体》所载孟氏、李白、杜甫诸人诗例,展示此一用字现象。[4](P135)其四是“吴歌格”,又称为“子夜体”,其最大的特色是谐音双关语的使用。如,后集卷三苏轼《席上代人赠别》诗即运用了这一字格,蔡氏于此诗后称引赵次公的评注并下按语,疏解这一用字现象,点明其实质是“借字寓意”,还列举出古诗及刘禹锡、杜牧的相关诗作,由此展示此诗格的源远流长。[4](P255-256)其五是用字颠倒。如,后集卷五黄庭坚《有怀半山老人再次西太一宫韵二首》诗后,称引《艺苑雌黄》《汉皋诗话》对韩愈、王令、黄庭坚诸人颠倒词序之诗例的评注,演示此一用字现象,并加按语指出其流风泛滥之弊:用字虽不必完全拘于常程,但颠倒字序应“无害于理”,且不可轻率为之。[4](P284-285)可见,对于诗史上形式各异的字法或用字现象,蔡正孙往往从诗歌创作的传统和惯例的层面进行观照,态度颇为通达。
与用韵、下字一样,用事也是诗歌创作的核心技巧。《诗林广记》选入的诗作,大多数都涉及用事。对于这一颇具普遍性的诗法现象,蔡正孙倾向于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如,前集卷二杜甫《示宗武》诗后,下按语曰:“前辈云:‘用事多填塞故实,谓之点鬼簿。’如少陵此诗,未尝不用事,而浑然不觉其为用事,可谓精妙者也。”[4](P31)不认可前人对用事的鄙薄,并标举杜诗用事之范例,对此予以辨证。又如,沈约、任昉、李商隐、苏轼等人皆喜用事,《溪诗话》对此有过评议,蔡氏在后集卷三所选苏轼诗的评注中予以称引,从中可看出他同样不以多用事为不妥,对全篇用事而能“流便”的苏诗尤为称赏。[4](P230-231)再如同卷苏轼《戏徐君猷孟亨之不饮》诗,胡仔称叹其“全篇用事清切”,蔡氏也特别予以称引。[4](P232)所谓“流便”“清切”,以及“不觉其为用事”,其实也是诗歌用事艺术的目标或境界。
对于诗歌的用事,蔡正孙还提倡以“意”为主。如,后集卷三评苏轼《赠子真秀才》诗,称引《石林诗话》对诗人用事之得失的论说,云:“苏子瞻尝两用孔稚圭鸣蛙事。如 ‘水底笙歌蛙两部,山中奴婢橘千头’,虽以笙歌易鼓吹,不碍其意同。至曰 ‘已遣乱蛙成两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则‘成两部’不知为何物,亦是歇后。盖用事宁与出处语小异而意同,不可尽牵出处语而意不显也。”[4](P232)从表情达意的角度评议用事是否恰当,此又体现在前集卷五王维《山中送别》诗及所附无名氏送别诗的评注当中。王维诗的后两句“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无名氏诗的后两句“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蔡正孙称引胡仔评语,指出前者用《楚辞》“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之语,契合于题旨和诗意,可谓“善用事”;后者所用“柳条折尽”之语,源于古乐府《折杨柳》,本意在于“寄相念”,而非“言其归”,故批评其用事“未尽善”。[4](P96-97)
二、句法与章法
从诗歌的语言组织结构来看,诗法可相对划分为字法、句法、章法。上文已对《诗林广记》中有关字法的评释作了梳理,这里对其句法与章法层面的评释进行论列。
句法作为格法的一项基本内容,在诗歌创作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范温《潜溪诗眼》提出“句法之学,自是一家工夫”之论断。[6](P330)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认为诗歌创作“用工有三”,句法即在其中。[7](P103)今人钱志熙先生也认为:“最能见诗法之精及诗人一家之诗法,就在于句法,创造独特的诗歌风格,也必须有独到的句法作为保证。 ”[8](P193)宋代以来,句法一直是诗歌批评的重要议题,各种体例的诗学著述,诸如诗话、诗评、诗格等,几乎都会有所涉及。《诗林广记》作为融诗选、诗话、诗评于一体的诗学著作,往往经由摘句评点,显现诸家格法之异同、造诣之高下,其中也包括对句法的辨析和论说。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以句法为观照视角,或以之作为衡量尺度,对诗人诗作进行评议。如,前集卷七孟郊《泛黄河》诗后,称引《临汉隐居诗话》所载评语:“孟郊诗蹇涩穷僻,琢削不暇,真苦吟而成。观其句法、格力可见矣。 ”[4](P126)孟郊的“苦吟”诗人形象,集中体现在诗歌创作的构思和造语这两个层面,句法则是一个有效的观照视角。又如,前集卷八卢仝 《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与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二诗题材相类,蔡氏称引胡仔评语:“玉川自出胸臆,造语稳妥,得诗人之句法;希文排比故实,巧于形容,宛成有韵之文,是果无优劣耶。”[4](P141)“句法”在这里既作为观照的视角,也是评判优劣的主要依据。再如,后集卷四“黄庭坚”条总论部分称引《豫章先生传赞》,云:“自黔州以后,句法尤高,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 ”[4](P278)着眼于“句法”,视之为诗人格法造诣与艺术境界的表征,据此标举其谪居黔州以后的诗作。
其二,将句法本身作为评释对象,列举范例,辨识特征,标示源流。如,前集卷二杜甫《绝句》诗后,称引《漫叟诗话》的评注,谓此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二句虽为 “拙句”,却“不失为奇作”;附录“唐人绝句”,称引胡仔评语:“有杜子美意趣。其句虽拙,亦不失为倔奇也。”[4](P20-21)可见,此处所谓“拙”,乃相对于雕琢刻削而言,是对句法特征的描述;所谓“奇”“倔奇”,指诗句或诗篇呈现出来的审美风貌,而创作主体的意趣则是其根柢。
蔡正孙不仅留意“拙句”,也关注“惊人句”。如,前集卷五韩愈《古意》诗有句曰“开花十丈藕如船”,被蔡正孙称为“句之惊人者”;随后,附录白居易《东城桂》诗(其三)“遥怜天上桂华孤,为问嫦娥更有无?月中幸有闲田地,何不中央种两株”,称引杨万里的论说,指出乐天此诗以及杜甫《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一百五日夜对月》、韩驹《衡岳图》、杜牧《池州送孟迟先辈》、李贺《李凭箜篌引》等诗篇中的“惊人句”。[4](P87-88)这里所标举的诗句,皆凭借奇特的想象以及与此相应的造语和修辞,使诗句的格调、语意变得更为“陌生化”,由此给读者带来“震惊”的审美感受。
此外,还论及已形成特定体例或写作规则的句法。如,前集卷七贾岛《渡桑干》诗后,称引《冷斋夜话》,点明此诗及《赴长江道中》诗的句法都是影略句法;又于《赴长江道中》诗后称引《古今诗话》对郑谷《咏落叶》诗的评析,点明其句法特征,实质上即“言用不言名”。[4](P127-128)又如,后集卷二王安石《寄蔡氏女》诗后,称引《西清诗话》所载苏轼评语,点明此诗承接《离骚》句法;《勘会贺兰山主》诗后,称引黄升评语,又加按语,并列举诗例,指出王氏此诗及陶渊明《问来使》、皇甫冉《问李二司直》二诗皆效仿屈原《天问》体。[4](P217-218)从选入的诸家诗作来看,这主要是着眼于句式特征而作出的判断。又如,后集卷三苏轼《赠子真秀才》诗后,蔡氏下按语指出此诗颔联“五车书已留儿读,二顷田应为鹤谋”为折句法;又列举欧阳修、卢赞元、黄庭坚、胡仔诸人相关诗句,由此显现这一句法的形式特征,即“上三下四格”。[4](P237)又如,后集卷八秦观《睡足轩》诗,称引《冷斋夜话》评语,列举“香稻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缲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林下听经秋苑鹿,江边扫叶夕阳僧”等诗例,展示错综体的特征,并借此点明此一句法的诗学旨趣。[4](P360-361)再如,后集卷五黄庭坚《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诗颈联“物色看王会,勋劳在石渠”,将古人名姓嵌入诗句,按通常的看法,此难免“点鬼簿”之讥,而胡仔则认为“不可执以为定论”,并列举黄氏这类诗句进行辨证。[4](P287-288)蔡氏称引胡氏的意见,借此显现句法观念与写作惯例的变迁。同卷选入黄氏《病起荆江亭即事》诗,将同时代人陈师道、秦观二人之字嵌入诗句,蔡正孙称引胡仔评语:“山谷以今时人形入诗句,盖取法于少陵。……近世风俗谀甚,悉以丈相呼,更不复知其字,畴敢形入诗句,必相顾而失色。 ”[4](P296)这里,也是经由胡氏的论列,标示出此一句法的渊源所在及其流变趋向。
章法层面的评释是蔡正孙诗歌批评的又一重要内容。诗歌章法,简而言之,指的是诗篇整体的结构形式及谋篇布局的方法。在宋代诗学批评中,律诗句与句之间的结构方式和逻辑关系,逐渐成为诗法论述的一个重要议题;其中,“起承转合”之法的基本内容要素,在当时的诗歌章法理论中也已经形成。[9](P115-118)宋末元初,以起承转合为范畴或视角评论诗歌,蔚为风气,如周弼《唐三体诗法》、方回《灜奎律髓》及刘辰翁的诗歌评点。之后,迄于旧题杨载的《诗法家数》及旧题傅与砺述范德机意的《诗法源流》,遂正式提出了“起承转合”之法。[10](P17-19,P241-242)
蔡正孙对诗歌章法的评释,不外于这一诗学史进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在《联珠诗格》一书中,他着重讨论了绝句的“起”与“伏笔”问题。[5](P244-245)《诗林广记》则论及律诗的“起”与“结”。如,前集卷三李白《浔阳紫极宫感秋》诗后,附录苏轼和诗,称引胡仔的评议,有云:“东坡起语清拔,优于太白。”[4](P59)又如,前集卷二杜甫《缚鸡行》诗后,称引洪迈评语,表彰此诗“结句之妙,非它人之所能企及”;称引真德秀评语,揭示结句在诗篇中的地位,即“一篇之妙,在乎结句”;称引《步里客谈》评语,标举结句的方法、惯例,即“古人作诗,断句辄旁入他意,最为警策”[4](P42)。此外,诚如马婧所指出,《诗林广记》也注意到与对偶体式有关的谋篇布局方法。[2](P46)如,前集卷七贾岛《下第》诗后,称引《笔谈》对“蜂腰格”这一对偶体式的解说,点明此诗颔联上下句的结构方式以及颔联与首联之间、颈联与前二联之间的语意关系。[4](P129)又如,前集卷八郑谷《吊僧》诗后,称引胡仔评语及所举诗例,呈现了使用“扇对格”(“隔句对”)这一对偶体式之诗作的篇章结构。[4](P143)
蔡正孙还特别重视诗篇结构的浑然。如,后集卷三苏轼《戏问章质夫》诗后,称引《复斋漫录》评语,主张诗句的对偶应“出于自然”,表彰此诗颔联二句“浑然一意,无斧凿痕”[4](P238)。又如,前集卷二杜甫《游子》诗后,称引《潜溪诗眼》的分析与评议,云:“古人律诗,亦是一片文意。语或似无伦次,而意若贯珠。……今人不求意趣关纽,但以相似语言为贯穿,岂不浅近也哉!”[4](P25)着眼于整体的诗意表达与诗语组织,强调以“意”或“意趣”作为谋篇布局的关纽,提倡意脉连贯、结构浑成。
三、诗语或诗意的袭用、摹仿与创造
效法、摹拟与创新,乃诗学史上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宋代诗学中也受到高度重视,如宋诗话即于此多有论述。具体到诗歌创作领域,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诗语”“诗意”的承袭、借鉴或创造性转化。相应地,这也成为以指导写作为主要旨趣的诗学著作的一个重点内容。如魏庆之《诗人玉屑》,该书卷八专门设置了“沿袭”“夺胎换骨”“点化”三个主题,著录相关诗话 43则。[11](P249-270)《诗林广记》是一部以“课儿侄”为主要编纂旨趣的诗选和诗话批评汇编文本,约有50余则评注文字直接讨论这一重要的诗学议题。从中可以看出,蔡正孙的关注点和评释范围,大抵不逾于《诗人玉屑》之论列。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诗句语辞或诗句语言结构形式的效仿。如,后集卷三称引《复斋漫录》《王直方诗话》的评语,借此指出,周邦彦诗句“化行禹贡山川外,人在周公礼乐中”以及秦观诗句“风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将军俎豆中”,是对苏轼《寄题刁景纯藏春坞》诗中“年抛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屦中”一联的效仿。[4](P228)又如,后集卷五黄庭坚《寄黄几复》诗颔联“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蔡正孙称引胡仔评语,点明汪藻诗句“千里江山渔笛晚,十年灯火客毡寒”以及胡氏本人诗句“钓艇江湖千里梦,客毡风雪十年寒”,皆效仿“山谷体”。[4](P285-286)
其二,诗意的承袭或摹仿、引申,以及诗语的改造或点化。如,后集卷二王安石《梅花》诗后,称引胡仔评语,借此指出,诗中后两句“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以及韩驹《咏梅花》诗句“那知是花处,但觉暗香来”,虽本于古乐府诗句“只言花是雪,不悟有香来”之诗意,但“思益精”“语益工”[4](P226)。又如,后集卷六陈师道《示三子》诗后,称引谢枋得评语,揭示晏几道词作《鹧鸪天》所云“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基本上是对杜甫《羌村》诗中“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一联语意的袭用;而陈氏诗尾联“了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则在继承杜诗之意的基础上又有引申和开掘。[4](P317)再如,同卷陈师道《次韵李节推九日登髙》诗颔联“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只作去年香”,与李煜诗句“鬓从近日添新白,菊是去年依旧黄”,都是以物事之轮回反衬人事之变迁,蔡正孙指出二者“意调”相同;此诗尾联上句“落木无边江不尽”,其意乃本于杜甫《登髙》诗颔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蔡氏亦特别予以拈出。[4](P321)
《冷斋夜话》卷一所记载的黄庭坚提出的“夺胎法”“换骨法”,基本要义也是如此。《诗林广记》亦特地予以拈出。如,后集卷三苏轼《纵笔》诗后称引《冷斋夜话》,借具体诗例标示“夺胎法”。[4](P253)卷五黄庭坚《登达观台》诗后称引《冷斋夜话》,也是经由诗例展示“换骨法”。[4](P301)按黄庭坚本人的解释,所谓“夺胎法”,含义是“规摹其意而形容之”,即在摹仿前人诗意的基础上又开掘出新意;所谓“换骨法”,指的是“不易其意而造其语”,即师前人之诗意而不师其辞或是点化其语。质而言之,这里探讨的是诗人如何在“师古”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诚如莫砺锋先生所言,当古典诗歌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各种艺术技巧(尤其是修辞手段)都有了相当数量的积累之后,诗人们要想“一空依傍”地自创新意、自铸新词,就非常困难了。[12](P190)在这种情势之下,借鉴前人诗的语意而点化出新,也就成为诗歌写作的重要法式。《诗林广记》承纳了这一诗歌创作观念,在具体诗作的评释中,经由相关诗话的称引,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此一写作技法。
其三,诗意的创造、翻新。《诗林广记》中论列的诗意创新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方式,是借鉴前人诗语,反其意而用之。如,后集卷二王安石《钟山即事》诗后,称引胡仔评语云:“李太白有云:‘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还忆谢玄晖。’黄山谷则曰:‘凭谁说与谢玄晖,休道澄江静如练。’王文海有云:‘鸟鸣山更幽。’介甫则曰:‘一鸟不鸣山更幽。’皆反其意而用之,不欲沿袭耳。”[4](P211)所谓“反其意而用之”,即对于前人诗句语辞,翻转或否定其意,表达新的见解。又如,后集卷五所选黄庭坚《戏咏暖足瓶》诗二首之一的后两句“千金买脚婆,夜夜睡天明”,蔡正孙称引《山谷内集诗注》,点明其反用杜甫《客夜》诗首联“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之语意。[4](P300)另外一种方式,则是对于前人诗中的意象、事料,翻转或颠覆其惯常的构思和命意,由此表达新的思想观念、情感意趣。如,后集卷六陈师道《归雁》诗后,称引胡仔评语,借以指出:杜牧《早雁》诗、欧阳修《自河北贬滁州初入汴河闻雁》诗,“皆言幽怨羁旅,闻雁声而生愁思”;而陈氏诗却摆脱套路,不再将雁声作为羁旅之情的表征,故能别开生面。[4](P333)卷十所选罗邺《赏春》诗和刘敞《春草》诗皆以春草为题咏对象,但所表现的题旨、诗意则迥然相异;蔡正孙将二诗并置,指出后诗是对前诗语意的翻转。[4](P429)
上述创新诗意的方式,大致相当于周裕楷先生所归纳的宋代诗学中“翻案法”的两种形式,即“反用诗句法”和“反用故事法”。[13](P201)据卞东波先生的研究,《联珠诗格》中入选诗作所用的“翻案法”基本上也是这两种形式;该书蔡氏的评语,则反映了他对宋代诗学中有关“翻案法”之论述的全面承袭。[5](248-250)这一论断同样也适用于《诗林广记》。出于向初学诗者提示门径的目的,此书选入许多以“翻案法”进行诗意创新的诗作,一一加以评释,具体地显现了此一诗歌创作技法的精神面目。
《诗林广记》中的格法评释,基本上以称引宋代的诗话、诗格、诗注等诗学文献为主,可以说是对宋代诗学重诗法探讨这一精神风气和批评传统的承纳。蔡正孙将格法作为其诗歌批评的一个基本视角和重点内容,一方面是他经由诗歌选本的编纂和评释以开展诗学教育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受到了当时诗学风尚(包括诗社中以切磋诗艺为中心的风气)的深刻影响。
[1]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马婧.《诗林广记》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7.
[3]曹艳贞.《诗林广记》的诗学观[D].沈阳:辽宁大学,2014.
[4]蔡正孙.诗林广记[M].常振国,降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5]卞东波.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9.
[6]郭绍虞.宋诗话辑佚[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张健.沧浪诗话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8]钱志熙.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9]吴正岚.宋代诗歌章法理论与“起承转合”的形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3(2).
[10]张健.元代诗法校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1]魏庆之.诗人玉屑[M].王仲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
[12]莫砺锋.黄庭坚“夺胎换骨”辨[J].中国社会科学,1983(5).
[13]周裕楷.文字禅与宋代诗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