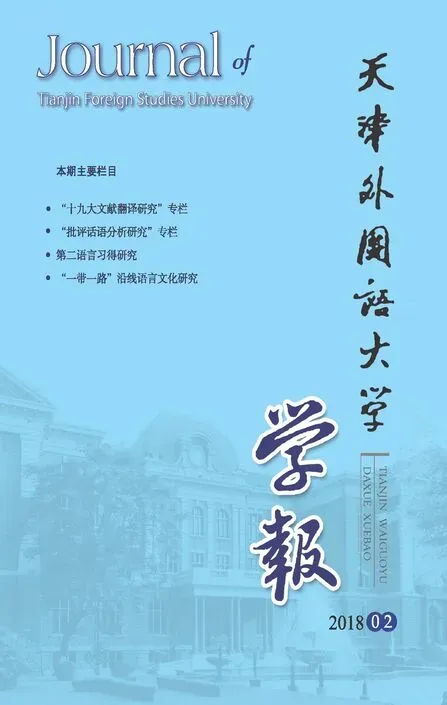多模态话语分析中的批评特征探析
潘艳艳,郑志恒
多模态话语分析中的批评特征探析
潘艳艳,郑志恒
(江苏警官学院 基础课教研部,江苏南京 210031;国防科技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江苏南京 210039)
在多模态话语分析向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发展这一研究背景下,在回顾多模态话语分析目前现有的研究路径和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中美征兵宣传片为例,具体探讨了多模态话语分析中批评特征的社会符号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呈现路径,同时描述了多模态话语中意识形态生产机制以及多模态话语生产者建构社会文化语境的动机,对传统的多模态话语分析模式形成补充。
多模态话语分析;批评路径;社会符号学;认知语言学
一、引言
多模态话语(multi-modal discourse)是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通过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张德禄等,2015:4)。多模态话语分析(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则是将人类交际活动中的多种符号模态进行系统的分析。自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标志性著作《阅读图像——视觉设计语法》(Kress & van Leeuven,1996)出版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多模态话语分析主要有以下九种研究路径:系统功能语言学多模态话语分析(O’Halloran,1999,2000)、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Kress & van Leeuwen,2001,2006;Jewitt,Bezemer & O’Halloran,2016)、多模态隐喻分析(Forceville & Urios-Aparisi,2009)、多模态互动分析(multimodal (inter)action analysis)(Norris & Jones,2004,Scollon,2001)、会话分析(Goodwin,2000;Jefferson,2004)、地理符号学(geo-semiotics/discourses in place)(Scollon & Scollon,2003)、多模态民族志(multimodal ethnography)(Flewitt,2011;Street,Pahl & Rowsell,2014)、多模态语料库分析(Bateman,2014)以及多模态感知分析(multimodal reception analysis)(Holsanova,2014)。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也有所拓展,从漫画、广告、电影海报、网页等静态的多模态话语延伸至诸如影视作品、电视访谈、舞台演讲、课堂教学等动态的多模态话语(潘艳艳、李战子,2017)。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更是体现在言语、手势语、视觉、互动、身份、符号学、系统功能语法、计算机媒介、语境和隐喻等问题上(国防,2016)。
随着新媒体日益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多模态话语同单模态的语言一样,不仅是人们传递信息的方式,还是人们参与社会活动、构建知识以及再现事实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话语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以多模态话语为分析和研究对象的多模态话语分析也具有揭示多模态话语中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的作用,因而有学者(如Machin,2013)提出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的命题,将多模态话语分析赋予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批评的使命。对于多模态话语分析向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发展的新取向,田海龙和潘艳艳(2018)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阐释了它的一些特征,本文则结合中美征兵宣传片的实例分析,论述如何结合社会符号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这两个理论来凸显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批评特征。
二、批评的内涵
批评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概念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吹毛求疵,而是一种基于理性的思辨和基于目的的实践。批评的概念在批评话语分析领域已被充分阐释。Fairclough(1989),Wodak(2001)和van Dijk(1993)三位批评话语分析的著名学者对此都有论述,尤其是Locke(2004)在对批评话语分析中的批评概念作了系统的阐述。综合这些学者的观点,田海龙(2009)将批评的概念概括为:(1)批评即是揭示,如揭示话语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2)批评即是反思,如反思研究者自己的立场;(3)批评即是实践,如批评要注重效果,要导致社会现实的变革。因此,批评是基于理性的思辨,它并不以揭露话语中的负面意义为终极目标,而是揭示话语的创造者怎样采用隐晦的话语策略将其意识形态遮蔽起来,使其合法化,进而达到被轻而易举认可和接受的目的。换言之,批评就是通过对话语的语言学分析将话语中不易被人们发现或已经习以为常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揭示出来,将话语中包含的社会、政治方面潜在的价值观揭示出来。正如豪厄尔斯(2007:58)所言:“用意识形态分析可以揭示出过去与当下的社会状态,人们需要明白当前社会与政治的设想都是有历史根源的,而不是自然产生的,这点尤为重要。”
批评这一概念所含有的揭示话语中意识形态意义的内容使其与话语分析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批评话语分析这一新的研究范式。沿着这一学术传统,近年来有学者(如van Leeuwen,2013)提出对多模态话语进行批评性分析,以揭示多模态话语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和权力关系。还有一些学者(如Machin,2013,2016)提出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尝试在多模态话语分析的实践中体现批评的含义,通过对游戏、音乐、建筑、图像、影像、颜色、版面这些多模态话语进行批评分析,揭示权力关系及意识形态通过娱乐、休闲、玩耍等人们喜闻乐见的交流形式被认可、被接受的方式。
实际上,既使Machin(2013,2016)不提出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批评性也是无法忽视的。这是因为话语的意识形态意义已经深深植根于多模态话语形式之中,二者不可分离,只有通过多模态话语分析才可将其从隐性表述中凸显出来。例如,在美国的一些政治漫画中,中国作为图像隐喻的源域常以图像dragon的形式呈现,目标域以文字形式China呈现。但是漫画中的dragon和中国的龙完全不同,前者是怪物的象征,后者则是尊贵、祥瑞的象征(潘艳艳,2011)。美国的这些政治漫画通过创造新的相似性颠覆了中国龙的正面形象,导致对中国的妖魔化,形成了具有负面意义的隐喻。对这些漫画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可以揭示出美国主流媒体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形成一种批评的态势。即使是同样的语类,由于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在源域的选择上也会有差异。因此,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模态话语进行对比分析,深入讨论源域所包涵的意识形态特征,可以揭示多模态话语创作的不同视角,这本身也是多模态话语分析批评取向的体现。
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在应用层面遵循着批评话语分析的原则和方法,概括起来就是既注重话语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发挥的作用,又植根于对文本扎实的语言学分析之中(田海龙,2016)。因此,在具体的案例研究中,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既要以揭示各种符号资源被用来构建知识和再现事实的方式为目的,同时又要强调这种揭示需要建立在对多模态符号资源的技术分析基础之上。例如,田海龙和张向静(2013)在揭示中英两国媒体在报道同一事件时通过刊发不同的图片来传递不同的意识形态意义,就先运用Kress和van Leeuwen(1996)提供的读图方法对所刊发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种采集仪式上事件的不同图片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明示其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揭示中英媒体采用不同图片体现出的不同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及报道目的。
三、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批评路径
上述多模态话语分析的九种研究路径其实并不是各自独立的,它们在理论背景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社会符号学分析对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多模态话语分析的传承,其他路径对社会符号学的借鉴等。尽管在研究方法、目的和关注点上不尽相同,但本质上都是探索语言和其他符号模态是如何共同作用,从而实现人类交际活动,进而启发新的研究方法和范式。
本文所试图探讨的凸显多模态话语分析批评特征的路径同样基于社会符号学、认知语言学等理论之上。所选取的多模态语篇实例分别为中国2017年的征兵宣传片《中国力量》(片长2分48秒)和美国2014年的征兵宣传片《勇士之歌》(片长3分41秒)两个视频。视频中的图片通过截屏软件获取,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截图,截图间隔为每秒一帧,去除因时间间隔短重复截图的画面后,《中国力量》共截图124帧,《勇士之歌》截图76帧。作为视频类语料,征兵宣传片是典型的多模态话语。正如Hart(2016)所言,视频已经成为话语交流的重要形式,对话语视频化的研究可为语言交流研究提供洞察力。本文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以视觉(画面)和语言两种符号模态为主,从社会符号学和认知语言学这两个路径,例示如何凸显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批评特征。
1 基于社会符号学的批评路径
Kress和van Leeuwen(1996,2001,2006)将系统功能语法、Saussure和Halliday的符号学思想以及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相结合,发展了以视觉语法为基础的社会符号学,将语言符号之外的其他符号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社会符号学旨在发现各种符号模态的普遍规律,关注社会文化语境,同批评话语分析一样致力于揭示交际行为中的权力和意识形态。社会符号学认为,符号使用者的意图、兴趣决定了他们对符号资源的选择,因此意义是选择的结果。例如,Abousnnouga和 Marchin(2013)结合对战争纪念碑进行的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指出,在战争纪念碑这个符号资源上,纪念碑的矗立者没有在纪念碑上表现暴力、羞辱、痛苦,而是加入了古典因素和象征不朽和坚固的材料,屠杀也被坚定向前的脚步和挺拔的卫兵所代替。通过隐去、添加和替代某些符号资源,战争纪念碑的矗立者成功地实现了他的意图。
影视艺术中的特写和近景镜头具有突出、强调的功能,同时通过图像的放大凸显某种象征意义。其中人物面部的特写最能表现心理和情感(潘艳艳、郑志恒,2017)。因此,我们根据社会符号学这一路径的主要理论——视觉语法(Kress & van Leeuven,1996/2006),结合中美征兵宣传片中的人物特写镜头(见图1~8)讨论通过图像的互动意义所传递的意识形态意义。图1~4为中国征兵宣传片《中国力量》中的截图,图5~8为美国征兵宣传片《勇士之歌》中的截图。

图1
图2

图3
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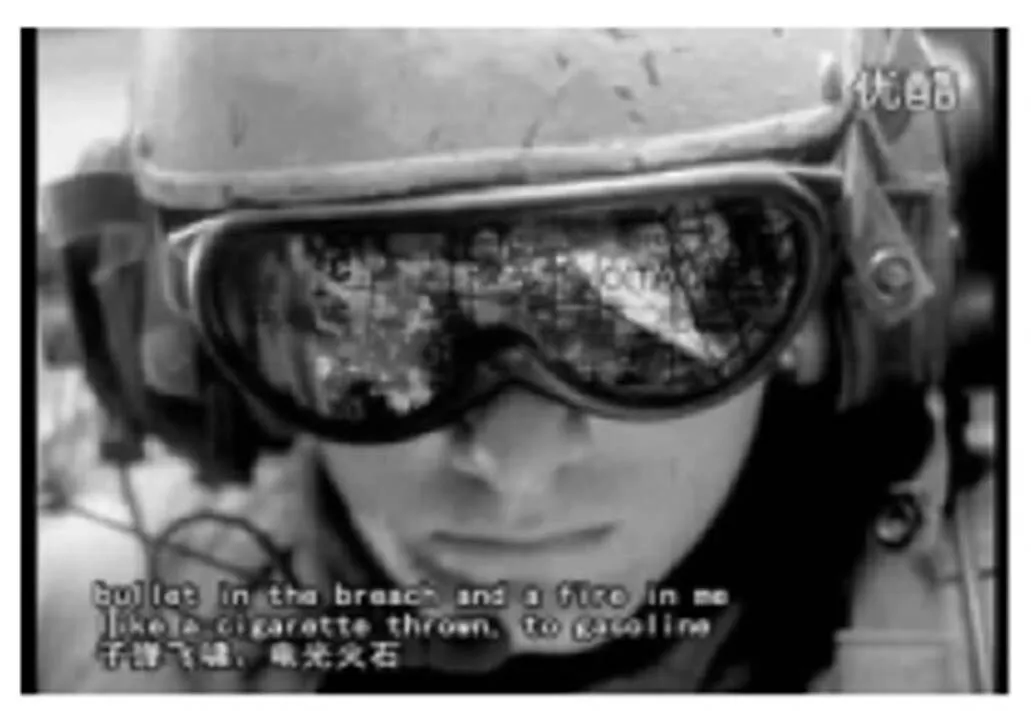
图5
图6

图7
图8
根据Kress和van Leeuwen(2006:117-118)的观点,画面中的人通过矢量(目光)和面部表情与观众交流。这样的构图有两个功能:一是形成和观众的直接交流,二是构成了图像行为,要求观众作出回应,建立起某种想象中的关系,具体哪种关系由人物的面部表情决定。图5中的人物虽然带着护目镜,观众仍然可以感觉到他的目光,严肃的面部表情传达给观众的是一种威慑力。图6中的人物是微笑的,与背景人物的表情融合在一起,仿佛在热情邀请观众加入。图7则是在向观众称赞武器的先进性,传达人物的兴奋之情。而图8则是向观众展示他和妻子或女友的合影,传达的是一种热情。这些直视的目光和丰富的表情极富感染力,和观众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产生强烈的互动,激发年轻人参军的热情。与之形成鲜明的对照,图1~4中的人物表情严肃,单一且没有变化,人物大多是侧脸特写,拍摄的角度不是平视就是仰视,人物的目光没有和观众的目光有所接触,因而拉开了与观众的距离。这可以引发观众的崇敬之情,进而唤起热血青年成为一名军人的荣誉感,但也造成了图像单向传达军人的刚毅和坚强之精神,没有和观众形成有效的互动。以上依据社会符号学的研究路径对多模态话语进行批评分析,揭示出了中美两国征兵宣传片中所蕴含的不同意识形态意义,不仅呈现了中国军人凝重的单一表情与美国军人多样表情之间的鲜明对照,也体现了这两个征兵宣传片的制作者各自希望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以及希望建构的各自国家的军人形象。这些都从幕后走向前台,隐性的含蓄通过分析成为观众清晰的体验。
2 基于认知语言学的批评路径
认知语言学并不是某个具体的理论,而是一种语言学的研究范式,由多个相关联的理论组成。目前应用到多模态分析领域的主要还是多模态隐喻分析。受到社会符号学的启发,认知语言学的学者们将社会符号学、隐喻理论、转喻理论以及关联理论相结合,认为隐喻不仅表现于语言,还表现在其他符号模态中,因此提出了多模态隐喻(Forceville,1996,2006;Forceville & Urios-Aparisi,2009)这一概念,即源域和目标域分别或主要由两种不同符号模式呈现的隐喻现象,在很多情况下其中一个符号模式为语言符号。多模态隐喻分析主要关注多模态语篇中隐喻和转喻的建构和解读。本文基于认知语言学的批评路径仍然以分析隐喻和转喻这两个人类基本认知方式为重点,对多模态话语中隐喻和转喻的源域以及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方式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多模态话语中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
隐喻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之上,是不同认知域之间的映射。隐喻除了表达审美和诗意,更多的是传递隐喻使用者的思想、观点和态度,体现隐喻使用者对社会现实的解读和理解,同时隐喻也能够影响受众的行为,在情感上引起共鸣。最具代表性的是政治隐喻,其中的意识形态偏见具有操纵听者(观众)的效果(Musolff,2016:4)。因此,有学者(如Charteris-Black,2004)结合批评话语分析理论提出了批评隐喻分析的方法,为多模态话语分析提供了具有批评特征的研究视角。
转喻指处在邻近关系的两个概念之一为理解另一个概念提供心理可及性(Radden & Kövecses,1999:21)。转喻的映现与一个认知域中次认知域的心理凸显(mental highlight)或激活相关联(Barcelona,2000)。转喻的理解在于对源域所指代的目标域——某个概念或复杂事件的推理上,这一推理建立在与源域相关的普遍信仰、民间习俗以及百科知识的基础之上。源域的推理能够揭示转喻使用者的社会身份、视角、立场和态度,可以为从批评视角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提供借鉴。
宣传片与其他影视作品的最大区别是其现实性(realistic)语类特征,即其所展现的内容必须真实存在,不能虚构,否则说服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征兵宣传片在真实性的基础上,通过镜头的剪辑和主题歌曲,以明快的节奏,从不同的方面展现军队的力量和现状,同时也展现军队形象和军事实力,激发广大优秀青年参军报国的热情,吸引更多高素质青年入伍参军。征兵宣传片的这一语类特点决定了隐喻和转喻的解读以及数量和分布。经分析发现,中美征兵宣传片中隐喻数量较少,多是阐述主题思想,转喻数量较多,多是进行细节描写和强调。
批评总是和情感密切相关,影视作品的情感表达则是基于对同义画面的凸显,即不同的画面或镜头表达相同或类似的情感取向。基于中美征兵宣传片中转喻较普遍的特点,本研究仅以中美宣传片中与情感相关的转喻为例进行讨论。《中国力量》讲述了新兵从入伍到成为合格军人的成长过程(潘艳艳、郑志恒,2017)。这一过程涉及到的表达情感和价值观的转喻主要有军功章代表荣誉(图9),心形图案代表爱国之情(图10)和接过军旗代表接受使命(图11)。这三个转喻表达了年轻人入伍成为合格军人以后形成的荣誉感、爱国之情、保家卫国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勇士之歌》强调美国军人的两面性:一是战场上全副武装、冷酷嗜血的杀人机器,二是有着战友情、爱情、亲情和同情心的军人(同上)。其中涉及到情感和价值观的转喻主要有使用的物品代表使用者(悼念阵亡的战友)(图12),拥抱代表爱情、亲情、同情(图13~15)。这些转喻体现了战场温情的一面,同时也反映出战争的残酷,会有牺牲的危险,会思念家人和爱人,也会伤及无辜平民。

图9
图10

图11
图12

图13
图14

图15
中美征兵宣传片的发布者都是通过展示各自的尖端武器和军队战斗力的方式来吸引年轻人参军,但是他们各自的叙事方式却是完全不同。中方是从新兵的成长过程这一叙事角度进行线性论证,强调参军入伍的爱国之情、荣誉感和军人的使命感。美方则是从军队生活的多个角度进行论证,强调参军后的英雄形象及会遇到的各种情况。这些体现在多模态话语中的不同叙事方式实际上构成了征兵宣传片发布者所要建构的各自军队的形象。
本文的实例分析不是要评出两者之间的优劣,而是要揭示中美征兵宣传片各自勾勒出的社会政治语境及隐含在多模态符号资源背后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突出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批评特征。事实上,对比分析更容易发现一些本质的东西,同时也能为今后的话语实践提供参考。如中国征兵宣传片可借鉴美国宣传片中目光交流以及人文关怀方面,美国征兵宣传片可以借鉴中国强调军人的崇高地位方面。
3 两种批评路径所揭示的意识形态
不论是社会符号学还是认知语言学批评路径,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达到批评的目的,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结合多模态话语产生的社会政治语境,以上两种路径能够揭示出发布征兵广告片的机构所要实现的意图以及意识形态特征。
中国近年来面对的主要挑战是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最近又发生了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事件。面对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中国必须有一支能够充分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发展利益,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提供强大力量的军队。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军网(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官方网站)在2015-2017年相继发布了征兵宣传片《有你中国强》、《战斗宣言》和《中国力量》,意图就是塑造中国军队形象,吸引年轻人参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中国军队能打胜仗的恢宏气势。
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军事大国为了达到称霸全球的目的屡屡发动战争,而自从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就遭遇了征兵荒,征兵计划很少能够顺利完成(张旺,2009)。后来的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等加剧了人们对战争的畏惧,同时美军虐囚事件等各种丑闻的发生也使得军人形象大打折扣,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参军。为了完成征兵任务,美国军方推出了各种征兵海报、广告以及宣传片吸引年轻人参军,其中最让美国人称道的就是《勇士之歌》,它被认为是美国的征兵之歌。《勇士之歌》中表现战友情、亲情、爱情和人文关怀的画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战争的恐惧。片中多次的目光接触和人物丰富的面部表情树立起美国军人亲民的形象,有助于缓解虐囚事件等一系列丑闻对美军形象的负面影响。
四、结语
本文以中美宣传片为例主要论述了多模态话语分析应该具有的批评特征与多模态话语分析中批评性的体现以及体现批评性所能借助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一个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多模态话语分析中批评特征的体现并不限于社会符号学和认知语言学这两个路径,还可以参考并结合其他理论。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希望将来会有更多的多模态话语分析者们发掘出更多体现批评性的路径和方法。
[1] Abousnnouga, G. & D. Machin. 2013.[M]. London: Bloomsbury.
[2] Barcelona, A. 2000. On the Plausibility of Claiming a Metonymic Motivation for Conceptual Metaphor[A]. In A. Barcelona (ed.)[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3] Bateman, J. 2014. Using Multimodal Corpora for Multimodal Research[A]. In C. Jewitt (ed.)[C]. Oxford: Routledge.
[4] Charteris-Black, J. 2004.[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5] Fairclough, N. 1989.[M]London: Longman.
[6] Forceville, C. 1996.[M]. London: Routledge.
[7] Forceville, C.2006. Non-verbal and Multimodal Metaphor in a Cognitivist Frame-work: Agendas for Research[A]In G. Kristiansen (eds.)[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8] Forceville, C. & E. Urios-Aparisi. 2009.[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9] Goodwin, C. 2000. Action and Embodiment within Situated Human Interaction[J]., (32): 1489-1522.
[10] Jefferson, G. 2004. Glossary of Transcript Symbols with an Introduction[A]. In G. Lerner (ed.)[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1] Hart, C. 2016. The Visual Basis of Linguistic Mean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Integrating Cognitive Linguistic and Multimodal Methods[J]., (3): 335-350.
[12] Holsanova, J. 2014. Reception of Multimodality: Applying Eye Tracking Methodology in Multimodal Research[A]. In C. Jewitt (ed.)[C]. Oxford: Routledge.
[13] Jewitt, C., J. Bezemer & K. O’Halloran. 2016.[M]. London: Routledge.
[14] Flewitt, R. 2011. Bringing Ethnography to a Multimodal Investigation of Early Literacy in a Digital Age[J]., (3): 293-310.
[15] Kress, G. & T. van Leeuwen. 1996/2006.[M]. London: Routledge.
[16] Kress, G. & T. van Leeuwen. 2001.[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 Locke, T. 2004.[M]. New York: Continuum.
[18] Machin, D. 2013. What Is Multimodal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J]., (4): 347-355.
[19] Machin, D. 2016. The Need for a Social and Affordance-driven Multimodal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J]., (3): 322-334.
[20] Mosolff, A. 2016.[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1] Norris, S & R. Jones. 2004.[C]. London: Routledge.
[22] O’Halloran, K. 1999. Towards a Systemic Functional Analysis of Multisemiotic Mathematics Texts[J]., (1-2): 1-29.
[23] O’Halloran, K. 2000. Classroom Discourse in Mathematics: A Multisemiotic Analysis[J]., (3): 359-388.
[24] Radden, G. & Z. Kövecses. 1999.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A]. In K.-U. Panther & G. Radden (eds.)[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5] Scollon, R. 2001.[M]. London: Routledge.
[26] Scollon, R. & S. Scollon. 2003.[M]. London: Routledge.
[27] Street, B., K. Pahl & J. Rowsell. 2014. Multimodality and New Literacy Studies[A]. In C. Jewitt (ed.)[C]. Oxford: Routledge.
[28] van Dijk, T. 1993.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J]., (2): 249-283.
[29] van Leeuwen, T. & G. Kress. 2011. Discourse Semiotics[A]. In T. A. van Dijk (ed.)[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30] van Leeuwen, T. 2013. Critical Analysis of Multimodal Discourse[A]. In A. Chapelle (ed.)[C].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31] Wodak, R. 2001. What CDA Is about?—A Summary of Its History, Important Concepts and Its Developments[A]. In R. Wodak & M. Meyer (eds.)[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32] 国防. 2016. 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J]. 外语与外语教学, (3): 58-66.
[33] 理查德·豪厄尔斯. 2007. 视觉文化[M]. 葛红兵等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4] 潘艳艳. 2011. 政治漫画中的多模态隐喻及身份构建[J]. 外语研究, (1): 11-15
[35] 潘艳艳, 李战子. 2017. 国内多模态话语分析综论(2003-2017)[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3): 49-59.
[36] 潘艳艳, 郑志恒,2017. 国防话语的多模态认知批评视角——以中美征兵宣传片的对比分析为例[J]. 外语研究, (6): 8-15
[37] 田海龙. 2016. 批评话语分析精髓之再认识——从与批评话语分析相关的三个问题谈起[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 1-9.
[38] 田海龙, 张向静. 2013. 图像中的意义与媒体的意识形态:多模态语篇分析视角[J]. 外语学刊, (2): 1-6.
[39] 田海龙, 潘艳艳. 2018. 从意义到意图——多模态话语分析到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的新发展[J]. 山东外语教学, (1): 22-33.
[40] 张德禄等. 2015. 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与外语教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41] 张旺. 2009. 美国征兵广告特点与启示[J]. 国防科技, (4): 85-88.
2018-02-01;
2018-02-0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模态视阈下的国防话语研究”(16BYY062)
潘艳艳,讲师,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话语分析
郑志恒,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媒介语言研究、语料库语言学
H030
A
1008-665X(2018)2-007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