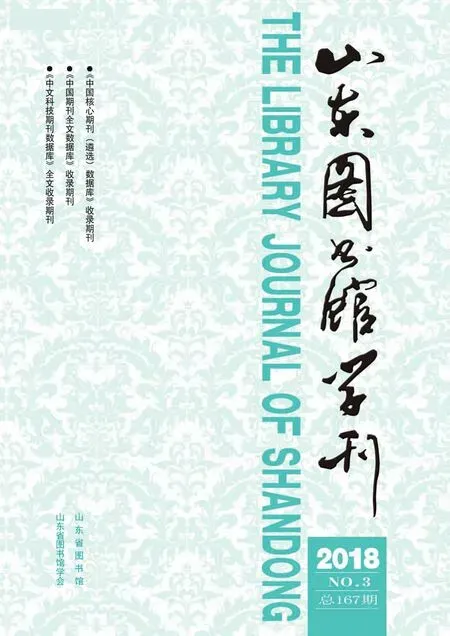国图所藏耿文光二十卷本《目录学》考*
张宪荣
(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耿文光,字斗垣,一字星垣、酉山,号苏溪渔隐,是晚清时期山西灵县的一位藏书家和目录学家。其所著《万卷精华楼藏书记》(以下简称“《藏书记》”),煌煌一百六十四卷,是一部内容赅博、体例严整、价值颇高的目录学著作,故今人对之研究的论文也有数篇。但是很少人对其另一部目录学著作即《目录学》进行过专门研究。有之,也不过进行简单的介绍,如李艳秋、郑伟章等的论文*目前对耿氏《目录学》的介绍的文章有:李艳秋《耿文光的目录学成就》(《文献工作与研究》,1998年第4期),郑伟章《善读书者必通书目——目录学家、藏书家耿文光考述》(《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李琦《晚清藏书家耿文光研究》(2006年苏州大学硕士论文)等。。其中李文较为详细些,但具体论述时却出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其开篇云:“《目录学》九卷,北京图书馆藏抄本,存六卷。清光绪间刻《耿氏丛书》本,九卷。”*李艳秋.耿文光的目录学成就[J].文献工作与研究,1998年第4期:95-98。按,今检《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文字学门》于“耿氏丛书”下著录为“《目录学》,存六卷”*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组编.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文字学门[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995:22。,又“《目录学》九卷,(清)耿文光撰,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刻本”*同上,79页。。其中,前者未云原卷数,后者则明确列出。回头再看李文,其第二条所录尚无大误,而第一条中的卷数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承第二条而来的。事实上,国图所藏那个“抄本”即其所说的“原二十卷”本,因内容首尾皆阙,故仅著录了存卷(其实所录存卷亦有误,见下文)。李文则以为此残本亦九卷,显然有误。而国图在其馆目中著录为“抄本”,亦不确。今检《清代私家藏书目录题跋丛刊》于此书著录为“清光绪十四年(1888)稿本”,理由是“书中夹纸条‘戊子八月十三日寓津门覆校一过’”*(清)耿文光编.目录学二十卷[M]//清代私家藏书目录题跋丛刊:第10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207。,近似,但亦值得商榷。因为此书天头及正文内皆有批改和圈点,显然正在修订。笼统题作“稿本”并不能反映此书的真正面貌。再检耿氏的《苏溪渔隐读书谱》云“五十九岁寓津門,覆校《精华书目》。”*(清)耿文光编.苏溪渔隐读书谱[M]//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490。其五十九岁即清光绪十四年。那么,问题就来了,此年耿氏到底是校《目录学》,还是《藏书记》呢?再进一步说,此两种书目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还有,《目录学》到底是如何流传的呢?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探讨。笔者参诸相关文献,拟对此书进行较为详细的考证。
1 《目录学》的编纂情况考
同《藏书记》一样,《目录学》也是耿文光最为重要的目录学著作之一。不过流行不广,故鲜有人进行研究。
关于是书的编纂情况,其前所附序中阐述得非常清楚。今将《苏溪渔隐读书谱》(以下简称“《读书谱》”)卷三所收《目录学叙》中相关内容节录于下*(清)耿文光编《苏溪渔隐读书谱》:340。按,此叙现在有三个版本,除本文所引外,九卷本《目录学》、二十卷本《目录学》皆有之。三本略有不同,当以《读书谱》所载最早,故今采用之。:
目录学者,学读书也。古人读书最重目,欲治群书,先编目录,目录成而学问未有不进者。余自幼嗜书,以书为师,先收者多陋,既乃精好。昔苦无书,今有书而不能读,同一太息。爰发所藏,定为日课(初名“日课书目”,后改今名)。其中有成篇者,皆旧稿也,随手抄录,积久渐多。以此引导童子,俾早知书,无伤老大。诚读书之门径,下学之阶梯也。
据此,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以下几点:
(1)此书编写的缘由有两点:第一,耿氏认为编纂书目可以治理群书增长学问,此可算作其对编目的基本观念。第二,随着藏书越来越多,越来越精,其有心读书却精力不足,故“定为日课”,随读随录,久而成篇。这是其编目的直接动因。
(2)此书编写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学童读书,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通过此书知道“读书之门径”。有关这一点,其在《万卷精华楼藏书丛记稿序》中也说:“余先著《目录学》以为入门之法,每考一书,动成篇卷,然仅仅知书之名目而已”*(清)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M]//丛书集成续编:第70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1。,说法大同小异。
(3)此序“定为日课”下小注云“初名‘日课书目’,后改今名。”说明此书原有旧稿,而此时方改现在的名称*《日课书目》与《目录学》虽有旧名、新名的关系,但不能据此认为二者是同一部著作,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有关二者的讨论笔者另有《国图所藏耿文光〈日课书目〉考》一文。。考《读书谱》卷三,此序修在同治十年,那么也可以说此时也是《目录学》编纂之始了。《读书谱》又载同治十年修经部,至十三年修集部,则可知此同治十三年当为《目录学》编成之时。
那么,此书在编成之后又有哪些修订呢?
今考存世的刻本《目录学》之《凡例》云:“此甲集也。原本二十卷,因无力发刊,去其十一而为九卷。开雕于光绪二十年二月十五日,至七月二十五日工毕。所删之卷重新整比为乙集,续刻嗣出。”据此可知,此书原有二十卷,光绪二十年因无力全刊,而仅刻九卷,故此时余十一卷尚未刊行。
又,《藏书记》卷二十经部“小学类”小序末云:“《目录学》已刻九卷,余十一卷之未刻者重加整理,统并于此。”按,此识语写于“十七日”,但不知月份。依上文所引《凡例》推测,应当为七月以后了。此时正是《藏书记》第四次易稿、录完经部之时,同时也是《目录学》九卷本刚刚刻完不久。这时未刻的“余十一卷”就随着修订《藏书记》而融入其中了。
综上所述,如果推测无误的话,至少在清光绪二十年前后,原二十卷本《目录学》随着有选择地刊刻和重新整理,应该会重新进行修订的。但到底在这之前有无修订,修订过几次,尚无可靠的证据。
随着微时代的到来,微技术的飞速发展引领着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微课即是这一形势下的产物。“微课程”最早由美国圣胡安学院高级教学设计师David Penrose教授提出,他把微课程称为Knowledge Burst,产生一种更加聚焦的学习体验[1],“微课”主要由微视频组成,它来记录老师在课堂内外的整个教学的过程,其中包括教学设计、课件、教学反思、练习测验、反馈及答疑及一些辅助性的教学资源。微课教学时间短、主题突出、内容明确,微课的时长一般10分钟之内,每个微课都能解决一个问题;微视频资源容量小、查找和下载方便;微课形式多样化、反馈及时,这是微课的3个特点。
在这里需要注意一下,前面所谓“去其十一而为九卷”并不是专门挑出某一类著作进行刊刻,而是四部之中各选若干部定为九卷。其中“所删之卷重新排比”似乎暗示了此目在刊刻前后确实有过整理。另外,所谓“统并于此”,也并非意味着此目原稿因此就没有了,要知道《藏书记》当时尚在重新誊抄,可能仅仅是将“余十一卷”的内容有选择地抄录了过去。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研究今存于国图的稿本《目录学》与《藏书记》的关系时,才会发现二目中虽然有很多相同的书籍,但具体到每一书所录内容则有同有异,并非完全相同*关于《目录学》与《藏书记》之间的关系,详见笔者《论耿文光〈目录学〉与〈万卷精华楼藏书记〉的关系》一文,待刊。。
此外,有关此目的体例,《目录学》所附《凡例》亦有明确说明,开篇便云:“是编先列书名、卷数,次撰人名氏,次编辑序第,次板本,次序跋,次举要,次诸家论说,末附案语。”*(清)耿文光.苏溪渔隐读书谱[M]//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345。据此,此目共有九大著录项。同时,它们的排列顺序也是有意义的,如《凡例》第二条云“目录之学,首重卷数。卷数不明,识者鄙焉。……自古校书,篇卷为重。是编于卷数有无,两本互异者,悉为著明。”因为在耿氏看来,卷数自刘向校书以来就明确注明,故需要排在最前面。又因为一般“书成而后镂板”,所以版本项排在了编辑序第之后了,这是根据书籍编纂刊刻顺序来安排这些著录项的。再看看与之相关的《藏书记》,则撰人名氏后接以版本,然后才是编辑序第,恰好与此目相反。
那么,这样做有何意味呢?笔者以为前者体现了对书籍内容的重视,后者则体现了对书籍形式的关注。前者反映了耿文光早期对编目的态度(受刘向校书的影响较大),即其《凡例》所明确说的“为读书而作,非藏书之目。”后者则反映了耿氏对清代以来编目重视版本之风的影响(重视版本价值和版本源流的梳理),他自己也在《藏书记》的序中说“次稿备著版本、节录序跋,如《天一阁书目》之例;三稿略辨版本,如《书目答问》之例”等,所以对于后者,虽然他也多次提到为读书而编之类的话,其实在思想上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因此,《目录学》与《藏书记》在著录上看似有很多相同,但其实已经有了诸多差异。
2 二十卷本《目录学》版本考
以上我们对《目录学》的编纂缘起、目的、时间及体例进行了一些梳理,那么,今存于国家图书馆的那本《目录学》到底是怎样一个本子呢?
今检此本凡5册,格纸抄写。半叶八行,大小字不等,大字行二十二字,小字双行同,行四十二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黑鱼尾,鱼尾上题“状元及第”,下题“八行廿二”,下书口题“书业德”。首目录学叙(首全尾残)。
是本首残缺过甚,直至《国语》一书,卷端才题“目录学卷七 灵石耿文光斗垣甫”“史部”,接着卷八亦史部,卷九集部,卷十一至十二史部,卷十六、卷十九集部,故明确标明卷次的仅有七卷,余或残或佚。但从残存卷次可以推知,原书应为二十卷无疑。
此本在分类上,我们虽可推知其大致依四部划分,部下无小类,但在编排上却颇为混乱,如上面史、集部交相排列等。具体到所录书,如《太元》《珊瑚木难》,一为术数类著作,一为艺术类,此则皆归于卷十二史部了。如果此本确为耿氏书之原貌的话,那么,可以看出其尚处于待整理状态,并非一个已定的稿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初步推知,由于此本在分类与归类上皆较为混乱,文内和天头处皆有批改,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尚待修订或正在修订的稿本。但到底是第几次呢?又是何时编订的呢?
今再检此本,笔者以为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此本所收书之书名天头处,大多有墨笔“○”,或题“乙”,或题“Ⓩ”等。其始于《香祖笔记》十卷(天头处墨笔“○”),之后便陆续有之。如《国语》二十卷,书名天头处墨笔“○”;《华阳国志》十二卷墨笔“Ⓩ”,《十七史蒙求》十六卷墨笔“乙”等。
(2)此本正文内序跋处或有“∟”符号。如《历代史表》五十九卷中李邺嗣序末,《中说》十卷中陈亮之说末等,皆有此符号。
(3)此本开篇有一浮签,墨笔题“戊子八月十三日寓津门覆校一过 正史四卷”。
那么,以上三点究竟何意?
首先,第(3)条所注的时间为“戊子八月”,即光绪十四年。是年据《读书谱》所载,耿氏“寓津门,覆校《精华书目》,意欲往上海刻之而力有不足。”*(清)耿文光.苏溪渔隐读书谱[M]//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490。又《藏书记》卷二十小学类序末云“《藏书记》成于丁亥冬日,戊子寓津门,复校一过。”*(清)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M]//丛书集成续编:第70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210。又,卷四十五史部《赤雅》末云“戊子夏寓津门,重录书目至‘地理·外纪类’。”又,九卷本《目录学》所收《淳化秘阁法帖考正》末云“戊子夏,寓居津门,意欲付梓而茫无伦次,心窃忧之。”*(清)耿文光.目录学九卷[M]//清代私家藏书目录题跋丛刊:第9-10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69。以上几条皆明确指明耿氏在清光绪十四年寓津门所校定的是刚刚编成不久的《藏书记》,而此本则云校定的是“正史四卷”。考今本《藏书记》正史类有八卷,而此本史部正好存有四卷(卷七、八、十一、十二),如果不是巧合,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呢?笔者由此想到了《藏书记》中《石刻铺叙》一书末的一条识语,其云:“余先纂《目录学》二十卷,体例未纯洁,因删其杂糅太甚者而刻成九卷。其所删之说,弃之可惜,复割截补缀消纳于《藏书记》内……”*(清)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M]//丛书集成续编:第70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481。此次刊刻发生在光绪二十年。在此之前,耿氏曾对原二十卷《目录学》大加整理,最后挑出若干著作,编成甲集,即今传世的九卷本《目录学》,而余十一卷皆“消纳”于《藏书记》。这至少可以暗示我们《目录学》与《藏书记》曾经有过相互参考,彼此融合的阶段。那么,此本中的这个浮签,是否也是暗示早在光绪十四年,已经有部分内容为《藏书记》所吸收了呢?如果这个推测没错的话,那么上面的那个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今再检此本,在史部四卷中所收凡62部(含不同版本),其中与《藏书记》不同者仅6部。从内容上,二本相同的那些著作亦有密切关系*二本的关系,笔者另有《论耿文光〈目录学〉与〈万卷精华楼藏书记〉的关系》一文详细论述。。或为《藏书记》全部采纳,或部分采纳。可见,此本确实在《藏书记》的修订过程中发挥过很大的作用。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再看第(2)条,发现只要这个符号“∟”出现的地方,《藏书记》所录文字便止于此。如《后汉纪》一书,此本的邵氏序在“史家之雄也”句下墨笔加一“∟”,而《藏书记》恰好仅节录至此。由此我们才知道,此符号原来是提示节录内容于《藏书记》的。
继而我们再看第(1)条,发现除了前面那些符号外,尚有墨笔批注别的文字的,如《昌黎诗集注》《颜鲁公集》《龙川文集》,天头批“已录”。那么,录到哪里去了呢?今检《藏书记》,三书皆见于其“集部·别集类”。如果再将前面那些有符号的与《藏书记》相校,可以发现大多皆见录于后者。由此我们才知道,所谓“乙”“Ⓩ”等这些符号,应该是“已”之误,因书写潦草,故而冷眼一看,不知所云。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白,此本残存的约180种的书,大多都与《藏书记》有密切关系。无论是天头处所批,还是文内的符号,都足以说明此本具有一种工作稿的性质。因为其中的批注大多不是为了自身内容的进一步完善,而是为了便利《藏书记》的进一步修订。考《藏书记》自光绪十三年初步编成后,次年耿氏便携之入津门,虽欲刊行未果,但其时却进行了一次覆校,此本的这些批注和符号估计便是在此时写上去的。所以此本题作“清光绪十四年稿本”大致是没错的,但是还不很具体。到底是第几次的稿本尚需进一步考证。
今国图藏有一部《日课书目》,版式、用纸及字迹皆与此本同,所以可知二书应该是在同一时间抄写的,修订时间也大致相同。后者《集古录目》残存有耿氏两则案语,其天头处有“初藁”二字,所以我们推知这些案语来自初稿。那么这样的话,后者之底本就应该是第二次誊录了,无怪乎其字迹如此整洁。但不可否认,其誊录时亦有所修订*见笔者《国图所藏〈日课书目〉考》一文。。此本之底本亦然。如果加上这些批注和符号的话,那么,此本应该可以说是“第二次修订稿本”了。由此我们觉得准确一点的话,此本应该题作“清光绪十四年第二次修订稿本”。
最后,我们觉得还得补充一点,前面说《目录学》的原名是“日课书目”。而现在国家图书馆正好藏有这两部著作,皆为稿本,且用纸、版式等皆同。那么,是不是说它们本来就是一部著作而最后被分拆为二了呢?笔者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既然它们的正文中有了明确的题名,那么说明耿氏是有意将二者进行区分的。而且两书还著录有相同的书籍,如果是来自同一部书,不至于如此。另外,虽然二者对《藏书记》的修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几乎都在充当类似于工作稿的角色,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不一样的。因为二十卷本在光绪二十年左右的时候,其中的一部分已经被挑选出来,编成九卷而刊行了,其余的部分则又一次被消融到了《藏书记》中。而《日课书目》则默默无闻,消失在了茫茫历史当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