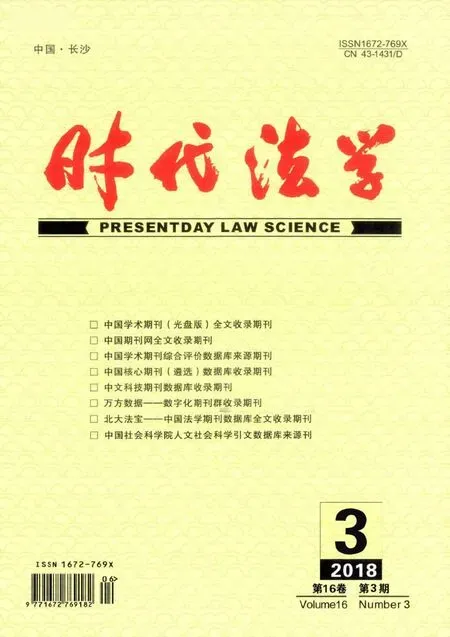论涉外侵犯知识产权法律适用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阮开欣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2011年4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第50条规定:“知识产权的侵权责任,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律,当事人也可以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协议选择适用法院地法律。”该条后半句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了侵犯知识产权法律适用方面的意思自治原则,但该规定似乎并未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被正确适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2017年7月31日对于项某诉彭某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以下简称“醉荷”案)*一审案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知)初字第9141号;二审案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京知民终字第1814号。作出二审判决,法院根据《法律适用法》第50条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对于该案发生于外国的侵权行为完全适用了中国著作权法,该做法不符合我国现行法律的成文规定*阮开欣.涉外版权侵权的法律适用是否存在意思自治原则?[N].中国知识产权报,2017-08-25(09).。但同时值得反思的是,在侵犯知识产权领域的意思自治问题上,现行的法律规定是否难以满足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是否符合法律在应然层面的发展趋势和规律。笔者试图对该问题进行梳理与探讨,并对我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提出相关建议。
一、国际上的现状和趋势
长期以来,涉外侵犯知识产权的冲突规范中几乎不存在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目前,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对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采取专属管辖,没有选择外国法适用的可能,则自然也不会产生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问题。欧洲在草拟《罗马条例II》的过程中曾讨论过该问题,在2005年的第一次草案中曾允许意思自治原则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适用,但2007年通过的《罗马条例II》(第8条第3款)最终明确予以了排除,其关键原因在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Hamburg group for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Comments o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draft proposal for a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non-contractual obligations,2002.。在《罗马条例II》之前,部分欧洲国家就明确采取了完全排除的态度,如德国和奥地利*P Rummel (ed), Kommentr zum allgemeinen buergerlichen Gesetzbuch Band II, Teil 6, para 4 (Manz, 2004).。德国最高法院在1993年的Alf案和1998年的Spiebankaffaire案中分别明确排除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Supreme Court decision of 17 June 1992-I ZR 182/90-Alf, 24 IIC 539(1993); Supreme Court decision of 02 October 1997-I ZR 88/95-Spiebankaffaire, MMR35 (1998).。可见,《罗马条例II》跟从了德国的司法实践,排除了意思自治原则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适用,但这一直受到一些学者的批判*例如:N Boschiero, Infrin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 Commentary on Article 8 of the Rome II Regulation, IX Yearbook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87, 107 (2007). Th M. de Boer, Party Autonomy and its Limitations in the Rome II Regulation, IX Yearbook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19, 25-26 (2007).。
不过,部分欧洲国家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意思自治原则予以限制性的认可,如比利时和瑞士。《比利时国际私法法典》第104条第2款规定了准合同之债可以适用意思自治原则,该条曾被认为可适用于侵犯知识产权。《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案》第110条第2款规定:“基于侵犯知识产权所引发的诉讼请求,当事人总是可以发生侵权损害之后,协议选择适用法院地的法。”其在三方面限制了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1)当事人只能在纠纷发生之后选择;(2)所选择的事项仅限于针对侵权的救济请求,并不包括知识产权的内容;(3)所选择的准据法只能是法院地法。由于瑞士并不属于欧盟成员国,其不受到《罗马条例II》的约束。
在欧洲以外一些国家也存在侵犯知识产权中的意思自治原则。例如,《日本法律适用通则法》第21条规定了当事人在侵权发生之后可以选择改变所适用的法律,日本最高法院在2002年的“读卡器”案中指出该规定可以延伸适用至知识产权侵权*Supreme court decision of 26 September 2002, Minshu Vol 56, No 7,1551.。
可以说,在国际上,意思自治原则在侵犯知识产权领域处于扩张的趋势。国际上的一些权威学术机构关于知识产权国际私法制度的提案,均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法律选择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了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美国法学会的《知识产权: 调整跨国纠纷中管辖权、法律适用和判决的原则》(《ALI原则》)第302条第(1)款规定:“受制于本条的其他条款,当事人可以在任何时间(包括争议发生之后),指定对其全部或部分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原文表述:Subject to the other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the parties may agree at any time, including after a dispute arises, to designate a law that will govern all or part of their dispute.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知识产权冲突法原则》(《CLIP原则》)第3:606条第(1)款规定:“……因侵犯知识产权而发生争议的当事人,可以在争议发生之前或之后,就其侵害而请求的救济,通过订立协议而选择其所适用的法律。”*原文表述:the parties to a dispute concerning the infringement of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may agree to submit the remedies claimed for the infringement to the law of their choice by an agreement entered into before or after the dispute has arisen.日本学者提出的《关于知识产权的管辖权、法律选择和外国裁判的承认与执行之透明度提案》(《透明度原则》)第304条也明确了,当事人了在知识产权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发生之后,可以改变诉讼请求的形成和效果所适用的法律。韩国和日本国际私法协会的《知识产权国际私法原则的共同提案》(《日韩共同提案》)第302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任何时间对于全部或部分争议指定所适用的法律,其还包括知识产权的内容事项,如权利的成立、有效性、撤销和转让。
二、意思自治原则在侵犯知识产权中的正当性和特殊性
(一) 正当性
随着民法领域私法自治原则的扩张,国际私法领域的意思自治原则也不断发展。从上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意思自治原则在传统侵权领域的适用开始兴起,许多法域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予以认可。如比利时、德国、立陶宛、瑞士、俄罗斯和日本等对于传统侵权领域认可限于“事后”(ex post)的意思自治原则,而奥地利、列支敦士登、荷兰对于传统侵权的意思自治原则包括“事前”(ex ante)的情形*Thomas Kadner Graziano, Freedom to Choose the Applicable Law in Tort-Article 14 and 4(3) of the Rome II Regulation, in: William Bingchy/ John Ahern(eds), The Rome II Regulation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Non-Contractual Obligations: A New Tort Litigation Regime, Leiden 2009, 113-132.。基于欧洲的现有基础,《罗马条例II》也对于传统侵权允许意思自治原则,其中第1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非合同之债的准据法”*原文表述:the parties may agree to submit non-contractual obligations to the law of their choice.。
在传统侵权领域允许意思自治原则的理由在于:(1)民事侵权诉讼中,当事人本身就可以处分自己的权利,被害人总有权利决定是否提起诉讼或撤诉,原告和被告也可以共同选择和解,因此双方也应当有权选择侵权的准据法;(2)允许当事人选择侵权的准据法有利于消除法律适用的不确定,从而提供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3)当事人可以将所有的法律关系(包括合同关系和非合同关系)都适用某一特定的准据法,以便当事人可以通过选择准据法来最好地保护其利益,并达到所希望的结果;(4)从司法实务的角度说,当事人可以选择法院地的法律作为侵权的准据法,有利于诉讼效率,减少司法成本*Thomas Kadner Graziano, Freedom to Choose the Applicable Law in Tort-Article 14 and 4(3) of the Rome II Regulation, in: William Bingchy/ John Ahern(eds), The Rome II Regulation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Non-Contractual Obligations: A New Tort Litigation Regime, Leiden 2009, 113-132.。
总的来说,上述理由主要在于意思自治原则在保障法律公平价值的同时可以促进法律的效率价值,这也同样可以作用于侵犯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透明度原则》的专家组指出了其采纳意思自治原则的目的:(1)侵权诉讼在许多法域都允许当事人随意处分,并不具有很强的公共政策属性;(2)当事人之间的规则变得更加清晰,有助于矛盾的解决;(3)意思自治符合对于法律明确性和可依赖性的需要*Rita Matulionytè, Calling for Party Autonomy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Cases, Journal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9. (2013).。《ALI原则》的评论中指出其“没有遵从《罗马条例II》是因为允许当事人之间协议选择准据法更能符合效率利益”*原文表述:The Principles do not follow the Rome II approach because efficiency interests are better served by allowing the parties to agree among themselves on the law that will determine what will usually be the monetary consequences of their conduct.。侵犯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对于意思自治原则的需求在以下三种情形下特别明显:(1)当知识产品在多国被利用,涉及到多个保护国的知识产权法,当事人可能愿意将侵犯知识产权的准据法限制为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法;(2)当权利人和侵权人的经常居所都处于同一国家,该国法院受理侵犯外国知识产权的案件,当事人可能希望适用法院地法(如“醉荷”案);(3)当事人在签订利用知识产权的合同时(特别是长期合同),可能希望对其适用当事人之间关系最密切的法律*Rita Matulionytè, Calling for Party Autonomy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Cases, Journal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9. (2013).。
(二) 特殊性
基于一定的公共政策属性,知识产权相比于其他民事法律具有特殊性,这是许多国家以及《罗马条例II》对于侵犯知识产权没有允许意思自治原则的关键原因。德国国际私法法案的修改草案过程中曾出现过对于侵犯知识产权是否允许意思自治原则的争议,其中第42条规定了对于侵犯知识产权之债允许事后法律选择的备选条款*〔17〕〔18〕See European Max Planck Group on Conflict of Law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nflict of Law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Clip Principles and Commentary art. 3:606.N13 (2013).N13 (2013).N14 (2013).。对此,德国慕尼黑的马克斯·普朗克(外国和国际专利、版权和竞争法)研究所公开发表声明并强调,被请求保护国法规则背后的公共政策目标不能被无视,侵权的认定和侵权的救济在这方面应被视为无法分离〔17〕。然而,该声明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救济排斥意思自治原则,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而遭受批评〔18〕。
随着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不断显现和加强,意思自治原则在侵犯知识产权领域也应当呈现扩张的趋势,因此各学术机构所提出的四个“软法”都不同程度上纳入了意思自治原则。虽然知识产权具有公共政策属性,但并不一定需全然否定其中存在意思自治原则的空间。在冲突规范中本身就存在公共政策例外的原则,可以用于防止一国的强制性规范被当事人通过法律选择进行规避。不过,公共政策例外作为原则性的兜底条款不宜被泛化适用,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意思自治原则需加入相关的限制规定,从而避免公共政策或他人利益受到影响。
例如,第三人利益影响的限制规定则可以用于防止意思自治原则在侵犯知识产权领域被滥用。大多数“软法”也都纳入该规定,《ALI原则》第302条第(3)款规定:“第 (1) 款中的任何法律选择的协议不得不利地影响第三方的权利。”《透明度原则》第304条和《日韩共同提案》第302条第(2)款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试举一例:甲制造通过单纯机械步骤(没有人工干预)而生成的照片,许可乙在多个国家出版发行这种照片。如果A国版权法对于作品独创性门槛极低,这种照片可以在A国受到版权保护,而B国版权法由于独创性门槛相对较高而不对这种照片提供版权保护。甲与乙约定发行这种照片的行为只适用A国的法律,该法律适用的约定只能约束甲与乙,两者之间的合同不能在其他法域创建出绝对的专有权,与其合同无关的第三人丙发行这种照片不受到该法律选择的约束,丙在B国发行这种照片不会侵犯甲的版权*See ALI Principles § 302 Illustration.。
三、意思自治原则在侵犯知识产权中的事项范围
我国《法律适用法》第50条关于意思自治原则的规定显然借鉴了《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案》第110条第2款规定,其意思自治原则的事项范围主要在于知识产权侵权的救济,而非权利的内容。《法律适用法》第48条规定:“知识产权的归属和内容,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律。”可见,《法律适用法》对于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事项采取了一定的分割制,区分了知识产权的归属、内容和侵权责任,对于“归属和内容”的准据法明确仅为被请求保护地国法,不存在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空间,即当事人对于“归属和内容”的准据法不能自行选择其他法域的知识产权法。而《法律适用法》对于“侵权责任”的准据法则为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留有一定空间,即允许当事人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对于“侵权责任”事项可以协议选择适用法院地的法律。
需要指出的是,侵犯知识产权与传统侵权在认定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侵犯知识产权的事项更多地在于权利内容的问题上,权利内容包括:专有权利的范围(被控侵权行为是否落入专有权利的范围)、权利期限(如版权人的作品是否超过保护期限)、权利的限制(如涉案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或法定许可)等。而传统侵权主要仅是侵权责任的问题,侵权责任事项包括归责原则和侵权救济的问题,如侵权责任是否需要以过错为要件、损害赔偿的认定和计算、是否包括惩罚性赔偿、针对侵权所采取禁令的标准等。知识产权与传统财产权有所不同的是,其在不同法域的权利内容(包括权利客体的适格性和有效性)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相同的行为根据不同法域的知识产权法很有可能得出不同的合法性评价。
我国《法律适用法》第3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该条作为意思自治原则的原则性规定已表明,当法律规定了法律适用规则而没有赋予当事人以选择权时,只能适用该规则所指引的准据法,而不能采取意思自治。2013年1月7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也对此予以确认,其中第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当事人选择适用法律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选择无效。”因此,根据《法律适用法》第48条规定,当事人无权对于权利内容事项作出法律选择的约定,法院只能对此适用被请求保护地国的法律。
在“醉荷”案中,被告彭某临摹了原告项某的美术作品《醉荷》,该临摹复制品被标注为“绢画作品《荷中仙》作者:田七”。被告带其临摹复制品参加了莫斯科和柏林的画展。涉案行为所适用的被请求保护国法应当主要是俄罗斯著作权法和德国著作权法,而非中国著作权法。一审法院对该案直接依据了我国著作权法,认定被告的涉案行为侵害了原告对美术作品《醉荷》享有的署名权、修改权、复制权、展览权,应当为此承担销毁侵权复制品、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十万元的法律责任。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的判决,对于法律选择问题引用了《法律适用法》第50条规定,并对该案适用我国《著作权法》作出了解释:“本案系侵害著作权纠纷,故除了可以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律外,也可以由当事人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协议选择适用法院地法律……各方当事人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已经就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做出了选择。本案中,项某在一审中虽然没有明确列明其法律适用的选择,但其起诉状所列理由完全系从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出发;项某在一审法庭辩论时明确依据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的规定,主张上诉人彭某的行为是非法复制,而非临摹。彭某亦是依据我国《著作权法》对其行为进行了辩论,即双方当事人均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因此,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已经就本案应适用的法律做出了选择,故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可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法律适用法》第50条规定中的“侵权责任”吸收了“权利内容”的事项,直接导致《法律适用法》第48条“形同虚设”,显然违背了立法的规定。
各“软法”也对于意思自治原则的事项范围存在分歧。《日韩共同提案》允许意思自治原则延及知识产权的内容,包括权利的成立、有效性、撤销和转让。而《CLIP原则》对于意思自治原则的事项范围只限于权利救济的法律适用。《CLIP原则》的起草者认为,对于救济事项(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和其他事项(适用被请求保护国法)可以适用不同国家的准据法,没有必要避免分割制*See H Schack [1985] GRUR Int 523 at 525. See European Max Planck Group on Conflict of Law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nflict of Law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Clip Principles and Commentary art. 3:606.N14 (2013).。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救济更多地是关于私人主体的利益,无关于知识产权的公共政策而专属适用被请求保护国法*See Dário Moura Vicent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 (2009) pp 348, 351. See European Max Planck Group on Conflict of Law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nflict of Law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Clip Principles and Commentary art. 3:606.N14 (2013).。
《ALI原则》在这个方面通过负面列举的方式,排除了权利成立、权利内容等事项的法律选择,其第302条第(2)条规定了当事人不能选择的事项:“(a) 注册权利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b)权利的成立、属性、可转让性和期限,无论其是否注册;和(c)登记转让和许可的形式要件。”根据《ALI原则》的评论,该条文中的“属性”(attributes)也称为“具体内容”(specific content),应当包括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范围、权利的限制与例外等事项。根据《ALI原则》,负面列举以外的事项属于意思自治的范畴,如侵权责任的事项。需要注意的是,严格地说,权利的限制不同于侵权责任的限制,前者实际上属于私人权利的对立面,即公众使用知识产品的合法权利,如合理使用;而后者则是侵权责任上的限制,如诉讼时效抗辩,其属于积极性抗辩(affirmative defense),需要侵权人在诉讼中主动提出并承担举证责任。
不过,根据《ALI原则》的评论,虽然当事人不能通过选择法律来改变一国知识产权的成立和内容事项,但是当事人仍然可以提起违约之诉获得救济。在前文的“机械照片”例子中,如果乙停止向甲支付在B国使用照片的版权许可费,甲无法以侵权为由主张权利,因为甲和乙之间的合同不能对于涉案照片创造出在B国的版权,但是,甲可以以违约为由请求救济*See ALI Principles § 302 Illustration.。可见,虽然《ALI原则》表面上对于第302条第(2)条中的事项不允许意思自治原则,但其仍然可能允许当事人通过合同在实质上进行法律选择。
四、 意思自治原则在侵犯知识产权领域中的限制
(一) 时间限制:事前和事后
当事人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协议选择准据法的时间可以分为侵权行为发生之前和侵权行为发生之后,即事前和事后。我国《法律适用法》第50条只允许事后的意思自治原则,因此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发生之前进行法律选择的约定则没有法律效力。而“软法”大多对于侵犯知识产权允许事前的意思自治原则(《ALI原则》《CLIP原则》和《日韩共同提案》),只有《透明度原则》仅允许当事人在知识产权侵权发生之后协议选择准据法。
事前的意思自治原则可以增加法律的可预期性,基本也符合前文所述的正当性,具有可取之处。在侵权发生之前协议约定准据法的情况通常都是当事人之间存在某种在先存在的法律关系(pre-existing relationship),当事人大多在先存的合同中约定了将来发生侵权所适用的准据法。《罗马条例II》对于传统侵权允许事前的意思自治原则,第14(1)(b)条规定了当事人可以在导致损害的事件发生之前协议选择适用非合同之债的法律,其条件为“当事人各方在从事商业活动的,且协议是通过自由协商”*原文表述:where all the parties are pursuing a commercial activity, also by an agreement freely negotiated before the event giving rise to the damage occurred.。《罗马条例II》第4(3)条还规定了“先存关系规则”,即使当事人没有对于侵权的法律适用作出约定,也可以将先存关系(具有最密切联系)所适用的法律作为适用于侵权的法律。
事前的意思自治原则同样也可以作用于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律适用,有助于知识产品利用过程中法律的可预期性,避免当事人调查各国知识产权法的成本。《CLIP原则》也纳入了“先存关系规则”,其中第3:606条第(2)款规定:“如果侵权与当事人之间的先存关系存在密切联系,如合同,那么适用于先存关系的法律也应适用于该侵权的救济,除非(a)当事人明确表示对于侵权救济排除适用先存关系所适用的法律;或(b)根据个案综合情况,案件的诉讼请求明显与其他国家具有更密切联系。”*原文表述:(2) If the infringement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a pre-exis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es, such as a contract, the law governing the pre-existing relationship shall also govern the remedies for the infringement, unless (a) the parties have expressly exclude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governing the pre-existing relationship with regard to the remedies for infringement, or (b) it is clear from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that the claim is mo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another State.
(二) 弱者保护原则的限制
侵犯知识产权的法律选择可能不公平地侵害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的利益,因此弱者保护原则有存在的必要,特别是当事人之间具有先存关系的情形。通常来说,这种情形发生于知识产权持有人与个人消费者之间的格式合同,也称为“规模市场”(mass-market)协议,例如在软件的终端用户许可协议(end-user license agreement)中约定准据法。知识产权持有人在“规模市场”协议中约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的准据法,可能并非个人消费者所能合理预料到的,个人消费者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地位,也没有协议谈判的能力,这可能导致不公平的结果。
因此,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扩张意思自治原则的同时也有必要引入弱者保护原则。《ALI原则》对于弱者保护原则的引入提供了典范,其中第302条第(5)(a)款规定“格式协议中,只有当法律选择条款具有合理性,使非拟制方当事人在订立时可以容易地接触到,并且法院和当事人在之后可以参阅,该法律选择条款才有效。”*原文表述:(a) In addition, choice-of-law clauses in standard form agreements are valid only if the choice-of-law clause was reasonable and readily accessible to the nondrafting party at the time the agreement was concluded, and is available for subsequent reference by the court and the parties.其中第302条第(5)(b)款对于(a)款中的“合理性”给出了考量性因素:“(i) 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程度、协议的性质和所选择国家的法律;(ii)当事人的居所、利益和资源,特别考虑非拟制方当事人的资源和老练程度。”*原文表述:(b) Reasonableness under subsection (a) is determined in light of: (i) the closeness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arties, the substance of the agreement, and the State whose law is chosen, and (ii) the parties’ residences, interests, and resources, taking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 resources and sophistication of the nondrafting party.
五、对我国立法和司法的建议
我国《法律适用法》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意思自治原则范围过小:(1)意思自治的事项范围仅限于知识产权的侵权责任;(2)意思自治的时间仅限于事后;(3)意思自治的准据法仅限于法院地的法律。这难以充分发挥意思自治原则在解决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方面的应有价值。
现行《法律适用法》第50条借鉴于瑞士国际私法,其对于意思自治原则的规定似乎仅仅是为了方便法院在审理侵犯外国知识产权案件时适用本国法律,提高诉讼程序的效率。然而,现行规定对于事项范围限于知识产权的侵权责任,几乎将这一意思自治原则的立法目的落空。判断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更多地在于知识产权的内容,而并非仅在于知识产权的侵权责任。知识产权内容不属于意思自治范围的情况下,难以减轻诉讼中查明外国法的负担。而且,在审理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采取分割制,对于知识产权内容和侵权责任适用不同的法律,反而可能会增加审理案件的复杂程度,甚至关于如何分割知识产权内容和侵权责任的事项可能引发新的法律问题。
笔者认为,随着知识产权地域性的削弱,我国立法应当在侵犯知识产权领域适当扩张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从而增加法律的可预期性以及效率价值,这也符合法律的发展规律。但立法在扩张意思自治原则的同时,应当引入防止第三人利益影响和弱者保护原则的限制规定,避免一味扩张而带来负面影响。笔者建议将条文拟定为: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侵犯知识产权适用的法律。任何选择适用法律的约定不得影响第三方的权利。格式协议中,选择适用法律的约定应具有合理性,否则约定无效。
虽然从应然层面,我国立法应当扩张侵犯知识产权领域的意思自治范围,但我国司法实践目前应当遵守现行立法的规定,对于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不应将“侵权责任”代替侵犯知识产权的所有事项,违背《法律适用法》的现行规定。肆意扩张解释法律条文无疑会使法律具有不确定性,伤害法律的权威性,意思自治原则甚至可能存在被滥用的危险,从而影响知识产权法的公共政策。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司法实践若希望避免外国法查明的司法成本,仍然应当依赖外国法无法查明的相关制度。《法律适用法》第10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由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或者行政机关查明。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应当提供该国法律。不能查明外国法律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出于诉讼效率的考虑,我国法院在审理侵犯外国知识产权案件中,应当适用《法律适用法》第10条规定来避免外国法的查明和适用,而非《法律适用法》第50条中的意思自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