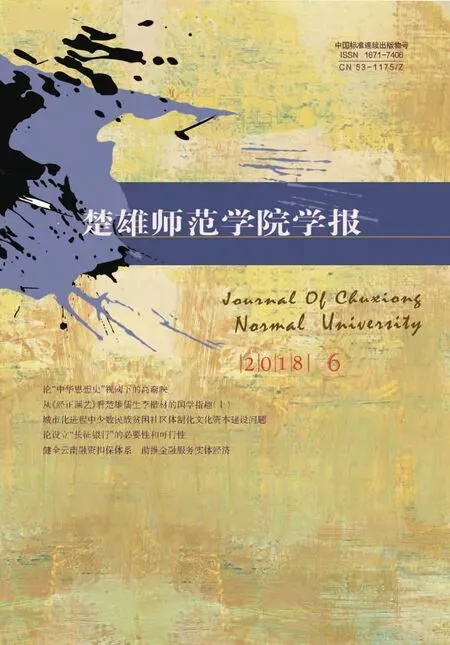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贫困社区体制化文化资本建设问题*
卜文虎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云南 丽江 674100)
一、社区体制化文化资本概念和研究问题的提出
(一)社区体制化文化资本概念
为了系统阐释社会阶层结构在社会世界中如何进行再生产的机制,克服经济决定论观念对此问题的不合理解释,皮埃尔·布迪厄在其总体性实践经济学分析中,引入了体现积累性特征的 “资本”概念,以此诠释社会世界的积累性本质,来分析经济社会地位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之再生产和合法化机制。总体性实践经济学认为,象征活动 (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同样属于交换形式,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交换形式。[1](P241)因而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等交换形式,本质上与经济交换形式一样,也产生经济利益和象征利益,实质上也是通过积累性活动来型塑并再生产社会结构。依据不同资本形态实现经济利益和象征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空间之不同,布迪厄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三种基本形态。[2](P192)
文化资本以三种形式存在,一是具体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 “性情”的形式;二是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 (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等);三是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这一形式必须被区别对待 (就像我们在教育资格中观察到的那样)。[2](P192~P193)上述三种形式的文化资本,分别称为具体化、客观化和制度化的文化资本。[2](P166)
体制化文化资本,就是文化资本 “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这一形式必须被区别对待 (就像我们在教育资格中观察到的那样),因为这种形式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完全是原始性的财产,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2](P193)也就是说,体制化文化资本是以体制认可的教育文凭的形式存在的,它是能合法产生物质利益和象征利益的一种 “原始性的财产”,这与具体化文化资本、客观化文化资本以及自学者所具有的类似的文化资本就划清了界限。体制化文化资本对于个体或群体的发展来说,显得至关重要,是因为 “文化资本正在变成越来越重要的新的社会分层的基础”[3](P89),体制化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构成了现代社会不平等的关键因素之一。但正是因为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最终以体制化、合法化的教育文凭的形式即体制化文化资本表现出来,掩盖了初始条件下个体或群体所占有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的不平等性。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体制化文化资本概念所关注的社会事实是,个体或群体所获得的制度化学校教育体系的教育资格文凭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本文欲通过考察社区青少年接受学校教育的程度和状况来分析衡量社区体制化文化资本。
(二)研究问题的提出
从体制化文化资本的概念可以看出,体制化文化资本构成了影响个体和群体的社会阶层地位、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拟通过对丽江纳西族城市化贫困社区W村的个案研究,来论述三个逻辑关系上递进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贫困社区的体制化文化资本建设变迁状况如何?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贫困社区的体制化文化资本建设状况对社区发展产生什么重要影响?地方政府应该运用哪些公共政策的理念和方法,促进社区体制化文化资本建设,重构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贫困社区迈向内源性发展、参与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础?
W村征地及城市化过程。W村地处城市远郊,离丽江市城区6公里,离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县城4公里;至2014年12月,全村150多户居民,人口530多人,有3个村民小组,村民都是纳西族,除5户居民之外,其余居民均为和姓。2003至2004年第一次征地,2011年第二次征地,除菜地和房前屋后的自留地之外,村民的耕地在两次征地中被全部征用;村民在征地之后,以城区打工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兼以小本生意收入为辅。2004年,所有村民的户籍转变为非农户口。第一次征地补偿款人均分配1.1万元,另加户头每户0.6万元;第二次征地补偿款按3个村民小组被征用的土地面积在组内村民之间进行分配,虽然略有差异,但3个村民小组按户头和人头分配的征地款相差不大,户头和人头均为6万元左右;以每户4口之家计算,每户村民在两次征地中获得约35万元征地补偿款。从2014年12月对50户村民家庭进行调查访谈的结果来看,因家庭生计投资效率低下、家庭经济收入较低、社区缺乏集体经济,再加上改善居住条件、日常消费等两项重要支出不断消耗村民家庭的征地补偿款,村民家庭的经济储蓄状况普遍不佳,W村在丽江纳西族城市化社区中属于经济上较为贫困的社区:14的受访家庭的经济储蓄为5万元以下;24的受访家庭的经济储蓄为5万元至10万元;28的受访家庭的经济储蓄为10万元至15万元;16的受访家庭的经济储蓄为15万元至20万元;18的受访家庭的经济储蓄为20万元以上;受访家庭的经济储蓄的中位数为13万元,平均数为14.6万元。①根据田野调查资料整理。时间:2014年12月;地点:W村社区。
二、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贫困社区的体制化文化资本建设与社区发展
(一)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贫困社区的体制化文化资本变迁建设状况
1.城市化之前社区体制化文化资本建设状况
城市化之前,W村社区传承纳西族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村民普遍重视提高青少年接受学校教育的程度。
W村现代教育体制起步较早,1921年,在W村观音寺建立了木堡里国民小学,该村和邻村的学龄少年儿童从此开始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村落由此形成较为良好的文化教育传统。20世纪50至90年代,因该村在丽江坝区地处偏僻,交通、生活有诸多不便,该村小学难以长久留住优秀教师,村干部和村民以自觉的社会行动争取社会资源来改变此种困境,同时社区运用公共资源积极支持在该社区办学的中学,社区和学校之间形成良性的社会互动。1969年,几位村干部与村民说服了一位社会声誉较好的老教师HYS来该村任教并担任小学校长,为留住该老师,村民给他划分了一块宅基地并帮助其建设住宅,HYS老师在该村任教至20世纪80年代初退休,为该村和邻近村落培养了不少人才。20世纪80年代初期,村落刚刚落实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行政村书记HSZ动员W村村干部和村民无偿出让部分耕地,用于村完小扩建,尽管村民对土地利益极为重视,但没有村民表示反对意见,村完小校园面积扩大至24亩。1988年至1989年,行政村书记HSZ和几位W村干部从丽江县县委、丽江县教育局、丽江县水电局、丽江地区水电局等单位部门争取5.5万元资金和5吨钢筋,行政村每户出资5元,每户投工投劳5天,各户自愿捐助米面、肉、蛋、蔬菜等生活物资,建设了村完小第一栋砖混结构的教学楼;1996年,行政村书记HSZ和几位村干部从丽江县人民政府、丽江县黄山镇政府争取54.7万元资金,行政村村民投工投劳,建设了村完小中心教学楼、教师宿舍、围墙、大门等,校园基础设施建设基本成形,校园面积扩大至28亩。W村和邻近村落村民也积极支持中学教育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至1998年,原丽江县某中学在W村办学,学校设有初中和高中,为当时丽江县规模较大和教学质量较好的中学之一,校园所占174亩土地均为W村、CS村、SY村等村社无偿出让;W村村干部和村民主动划出60亩良田作为该中学的校田,村民出工出力为学校耕种田地,学校收获了粮食之后养猪养鸡、给教职工发放面粉,改善教职工生活,村民支持该中学办学的类似行为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①根据田野调查资料整理 (且与2012年9月出版的HS镇教育志相印证)。时间:2015年2月、4月;地点:W村社区。
W村社区从民国时期至20世纪90年代重视文化教育、充分运用社区公共资源和外部社会资源积极支持社区学校教育、尊师重教、社区与学校之间良性社会互动的集体行动,源于村民对文化知识和学校教育在社区发展及社会流动等方面所起重要作用的经验性社会认知。笔者调查访谈了8位在20世纪50至90年代考上大中专学校之后获得公职的W村人员,访谈的主题为 “你读中小学的时候,村民与村里学校老师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村里学校和老师有困难,那时候村民会怎么样做?”“你读书的时候村里学风怎么样,为什么?”三个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8位受访人员皆认为村民与老师之间的关系很好,都强调当时社区内尊师重教的氛围,“学生父母亲很尊重老师,见面都热情打招呼,那时候虽然学生家长忙于生计,但见了任课教师总会询问孩子在学校的学习和品德状况,逢年过节会请老师来家里做客,我们学生也把老师看作父母亲一样”。针对第二个问题,受访人员都提及村民帮助学校的普遍行为以及村民与教师之间的积极互动,例如为学校砍伐柴禾、种植蔬菜送与学校等生活上的社会支持行为。对于第三个问题,受访人员均认为当时村落青少年的学风较好,特别是某中学在村落办学之后,学风受到更好的影响,谈及原因,“我们村和邻近村落的经济一直较为落后,当时村民普遍贫困,农家子弟要跳出农门,改变命运,最重要的就是读书这一条路,即使上了高中没考上大学,有点文化知识总是对自己、家庭和村落有好处,所以家长重视教育,学生学习风气也很好”。②根据田野调查资料整理。时间:2014年2月;地点:W村社区。
由此可见,从民国时期至20世纪90年代,W村社区由于村民在经济上普遍较为贫困,青少年读书上学也就成为村民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村民对文化知识的此工具性作用具有明确的经验性社会认知,社区形成了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社区与学校、村民与教师之间也形成良性的社会互动,一方面社区体制化文化资本获得长期的积累,W村通过读书获取公职的人数比例远高于邻近的W上村、WB村等村落,另一方面社区内学校教育也自然融入社区发展之中。
2.城市化之后社区体制化文化资本建设状况
其一,尊师重教、重视文化教育的社区社会氛围逐渐减弱,村民与教师之间的社会互动减少,社区内学校的建设发展难以获得村民的积极支持,教师对社区缺乏认同感,社区内学校的建设发展与社区发展之间出现了断裂。首先,征地之后,社区村民获得了短期内的经济地位提升,而同时期当地中小学教师的经济社会地位变化不大,引起了村民与教师之间社会互动性质的变化,尊师重教的社区社会氛围渐趋减弱。W村完小两位教师的访谈表述了这种社会互动的变化,“我到这个学校快10年了,很少遇到学生家长主动打电话或到学校来,了解孩子的情况,这种状况很不正常。当需要家长的配合来教育好孩子的时候,我们教师也没有办法。村民有点不尊重我们老师。家长因为获得了征地补偿款,手头有点活钱,对教师态度特别傲慢。我们教师在村子遇见家长,家长不会主动打招呼,一般会装作没有看见,我们都觉得心寒。更不用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长给老师电话道谢或问声好。” “我家在邻村WS村,我在这儿教书的时间很长,差不多有15年了,对这儿的变化,也可以说感同身受。征地之后,这个行政村的家长都不太喜欢搭理老师。以我的经验,也就是学习成绩特别好的孩子的家长还经常来了解一下孩子的情况,绝大多数家长根本就不主动和老师交流沟通,我们教师该做什么做什么。”村民与教师之间社会互动的变化,致使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之间难以融合,W村完小召开家长会,多数家长委托爷爷奶奶前往,后来学校硬性规定必须由家长参加,但教师与家长之间的交流沟通难以改善,导致多数知识文化层次并不高的家长的教育观念、态度和行为的积极转变较为困难。其次,因社区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的下降,村干部和村民对社区内学校发展的支持普遍减少,社区和学校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从W村2003年第一次征地以来的10多年间,W行政村各个社区对W村完小的资金支持仅限于每年教师节两三百元的慰问金;仅有几位村组干部和村民运用其社会关系对学校发展给予支持;除此之外,在学校建设和日常生活之中,W行政村各个社区的村组干部和村民积极支持学校发展、社区与学校之间密切社会互动的状况已经荡然无存。笔者对W村村民的访谈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社会事实,笔者对W村20位中青年男性村民进行随机调查访谈,访谈的问题为“近十年来,你为村完小的发展做过事情吗?为什么?”20位受访村民的回答均为 “没有”,问及原因,17位受访村民的回答均诸如,“现在大家都各顾各的事情,哪有时间精力去管学校的事情,真要做点事情,村里也没有组织带头的人”;而3位受访者的回答则是 “想为学校发展做点事情,但自己缺乏能力,不知道做什么好”。①根据田野调查资料整理。时间:2015年3月;地点:W村社区。
其二,征地之后,村民对子女家庭教育的观念、态度和行为发生了变化,家庭变故日益增多,诸多因素相互叠加,青少年的学业成绩从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社区体制化文化资本的积累建设出现了困境。在W行政村各个社区,征地之后村民在短期内可供支配的钱较之以前增多,受现代消费社会的文化的影响,一些中青年村民的生活方式转变为休闲娱乐生活方式,对子女家庭教育不够关注,其观念和行为对子女也产生消极影响。据W村完小统计,W行政村各个社区共有7岁至12岁读小学的适龄儿童120多人,其中80多人就读于W村完小,任课教师了解的因父母离异、父母长期不回家、父母吸毒等家庭变故而长期由祖父母照顾抚养的儿童有17人,比例超过20%,有些儿童自然出现了行为偏差问题而影响其学业成绩和社会化程度。例如,HYF老师所带班级里有父母吸毒的两位WB村儿童,其父母不知去向,由其祖父母抚养照顾,尽管两位儿童均智商正常、知识接受能力强,但经常未完成家庭作业,学习习惯和行为也出现偏差。2003年至2010年,W行政村各个社区400多户村民,无一人考取一本院校,从2011年开始,每年有一两位学生考取一本院校,从2003年至今,每年高中入学率均远低于城市社区,青少年学业成绩在整体上明显下降。②根据田野调查资料整理。时间:2015年3月19日、20日;地点:W村社区。其中以WB村的状况最为严峻,不仅高中入学率远低于邻近村落,少年儿童的学业成绩在整体上普遍较不理想,而且在青少年群体中出现了吸毒亚群体和“混混”阶层,已经演化为影响社区发展的严重社会问题。③根据田野调查资料整理。时间:2015年2月4日、5日;地点:WB村社区。
(二)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贫困社区体制化文化资本建设与社区发展
以制度化、合法化教育文凭或资格所体现出来的社区体制化文化资本,构成了社区村民群体适应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习得文化的基础,从而社区体制化文化资本就以习得文化中“知识文化”的形式构成了社区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建设的基础。更进一步说,社区体制化文化资本,就其功能和作用而言,建构了社区内村民群体参与市场经济竞争、实现向上社会流动、扩大社会和政治参与性的文化能力和文化资格。
在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贫困社区,社区体制化文化资本一定程度上的总体性下降,导致村民群体的文化能力不适应参与市场经济竞争、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需要。换个角度说,在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贫困社区,摆脱了土地束缚的村民,似乎拥有了积累新的文化资本和寻求新的生活方式的 “自由”,而这种没有任何 “保障”的自由,却往往意味着一种新的奴役方式的开始而不是获得生活境遇机会的起点。正如鲍曼的精辟论述,“没有保障的自由必然导致痛苦,丝毫不亚于没有自由的保障。但是,两者之间的妥协也不会保证获得快乐,因为妥协必然带来部分牺牲。人类既需要自由,也需要保障——牺牲任何一方都会成为痛苦的根源。”[4](P38—39P)当然,鲍曼是在对新自由主义社会福利政策造成新贫困和自由剥夺进行批判的语境下讨论自由与保障之间的关系。而将这种对自由与保障之间的关系分析引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贫困社区体制化文化资本建设的现状之中,那么呈现出来的就是既没有“自由”也缺乏 “保障”的现实困境,它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村民群体新生活 “惯习”的形成。而这种新生活 “惯习”以持久性的性情和行为的形式改变着社区村民群体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与社区发展产生重要的关联。
社区体制化文化资本建设滞后所带来的就业知识技能普遍缺失使多数村民处于社会排斥的状态,社区中青年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对长远生活进行预期和规划的能力,因而就出现了对生活持有消极态度的心态和行为的新“惯习”。一方面,这不仅损害了社区内个体和群体依赖自我发展来处理解决家庭和社区事务的文化能力和社会条件,长期对社区的内源性发展、参与式发展、可持续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与社区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工具性关联。另一方面,则导致村民群体难以拓展经济参与性、普遍缺乏向上社会流动渠道、难以提升文化能力、无法扩大社区公共事务参与等等,凡此种种,对村民群体的基本自由和权利体系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剥夺,侵蚀了社区发展的基本建构性因素。鲍曼指出,“观光者与流浪者的对立是后现代社会主要的、首要的分离。我们都处在 ‘完美的观光者’和 ‘不可救药的流浪者’这一连续谱两级之间的某个位置——而且,我们在两级之间的各自位置,是根据在选择生活路线时所拥有的自由程度而表示出来的。”[5](P109)于是,对生活的 “选择自由”程度,就成为社会分层结构中不同阶层或群体的重要社会特征。对于社区中青年群体中的不少个体而言,对生活未来不承担责任的行为,抑或休闲娱乐生活方式的兴起,表面上看是个体对生活的一种自由选择,而在本质上是个体在没有选择自由的状况下,面对社会排斥只能以没有长远生活目标的 “流浪者”的生活方式来适应社会变迁。在W村社区,笔者对30位年龄在36岁至60岁的中年男性进行了随机的调查访谈,访谈的问题为 “现在的生活感受和未来的生活打算”,其中有21位受访者长期从事打工。有17位受访者提到 “现在的生活没有多少意义,以前有地种的时候感觉充实”,占受访者的57;有22位受访者谈到 “生活没有奔头,很少看到希望,得过且过”,占受访者的73。①根据田野调查资料整理。时间:2013年7月;地点:W村社区。对W村20位18岁至35岁男性青年的调查访谈结果与中年群体没有显著差异,其中有9位受访者长期从事打工。有13位受访者谈到生活感受为 “过得轻松点,该玩的时候就玩,没有什么更高的追求”,占受访者的65;有16位受访者提及对未来生活的看法为 “因知识技能缺乏,对未来不抱多少期望,没有条件对生活进行长远计划,想过上自己期望的生活很难”,占受访者的80。②根据田野调查资料整理。时间:2013年8月;地点:W村社区。
三、对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贫困社区体制化文化资本建设的公共政策思考
结合经验研究之中社区体制化文化资本建设和变迁的关键影响因素,运用恰当的公共政策理念和方法推动社区体制化文化资本的建设,引致社区发展的文化基础之建设和重构,以推动社区迈向内源性发展、参与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贫困社区发展所不容回避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
地方政府应该对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贫困社区体制化文化资本变迁可能导致严重社区社会问题这一社会事实引起相应的关注,运用社会政策方法干预和促进社区基础教育的发展,建设注重文化教育的社区社会环境,提升社区体制化文化资本,由此不仅拓展社区青少年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社会空间,而且长期为社区的内源性发展、参与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建设坚实的文化基础。其一,在地方层面上基础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践之中,应重视和激发社区建设与社区文化教育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政府相关部门和机构应建构增进社区村民与社区学校之间密切社会互动的公共政策,重新培育社区和社区村民对社区学校教育发展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团结精神和自主意识,从而自主建设注重文化教育的社区社会环境,促进社区学校教育发展与社区发展之间的相互融合。其二,在社区体制化文化资本建设过程之中,需要引入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和组织的积极干预介入,一方面对社区家庭教育的观念和行为实施相应的社区疏导矫正,并积极建立社区教育家长互助组织,以促进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相互协调、家长与学校教师之间形成良性社会互动,为社区体制化文化资本的提升创造最基本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则对因家庭变故而由祖父母辈抚养照顾的青少年、儿童给予制度化、常态化的专业社会工作的社区疏导矫正并进一步构建相应的社区社会支持体系 (包括教育层面的社区照顾和经济互助),对社区内过早辍学 (未就读普通高中或职业高中)的青少年,特别是有长期越轨行为的青少年实行相应的专业社区疏导矫正并建立社区矫正的长期机制,预防社区内出现与之相关的严重社会问题,逐渐消除社区结构性因素对社区学校教育和社区家庭教育的消极影响,总之通过专业社会工作干预介入和引导的社区建设来重建注重文化教育的社区社会环境和社区社会支持体系。其三,从本文的经验研究来看,少数民族地区从事基础教育的教师阶层的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缓慢构成了影响社区体制化文化资本建设的一个显著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地方政府应以长期对文化资本进行社会投资可以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种社会政策理念为立足点,逐步提高从事社区基础教育的教师阶层的工资待遇、对社区基础教育教师的职称晋升实施倾斜性政策、改善社区基础教育学校的办学条件、提升社区基础教育教师的职业认同和社会认同,来逐步消除此社会结构性制约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