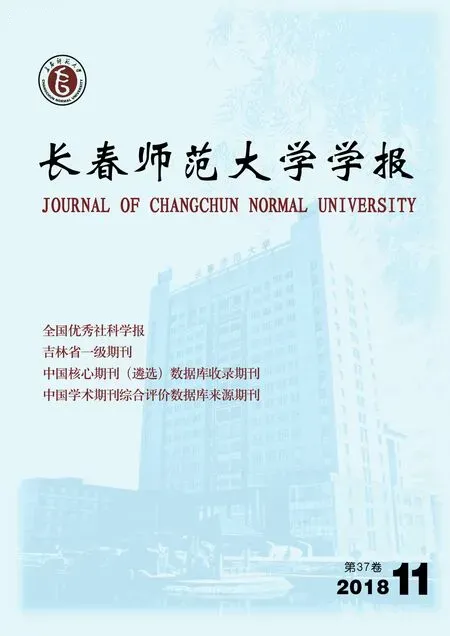玛格丽特·杜拉斯“印度系列”文本间互文性研究
张 来
(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现当代法国文坛上极具代表性的作家。作为“新小说”流派的代表人物,杜拉斯于1964年发表了她一生中最为珍爱的作品《劳儿之劫》(法文:Le Ravissement de Lol V. Stein,又译《劳儿的劫持》或《劳儿·维·斯坦茵的迷狂》)。这部作品一经问世,便引起文学界的强烈反响。法国精神分析大师雅克·拉康在1965年公开发表文学评论《向玛格丽特·杜拉斯致敬——论〈劳尔之劫〉》,并在文中对杜拉斯的这部作品大加赞赏。然而,关于女主人公劳儿·维·斯坦茵的故事并没有随着《劳儿之劫》的出版而结束。1966年的小说《副领事》、1971年的小说《爱》、1973年的电影剧本《印度之歌》和《恒和之女》相继问世以后,杜拉斯笔下关于“劳儿”的故事才真正讲完。由于故事背景都围绕印度支那展开,作品人物存在似有似无的重复性,中外的文学评论家和杜拉斯研究专家习惯于将《劳儿之劫》《副领事》《爱》《印度之歌》《恒河女子》这五部作品统称为杜拉斯的“印度系列”。
然而,“印度系列”作为杜拉斯文学创作的巅峰却很难像其所著《广岛之恋》《情人》等作品那般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原因在于这五部作品的情节设计极为独特,表达主旨极为抽象,人物的语言和对话极为破碎,常常只有与上下文毫无关系的一个词,甚至是一个字。同时,其故事发展显得缺乏逻辑,给广大读者和研究者造成了一定的理解障碍,因此曾一度被评价为内容空洞、缺乏主题的失败作品。在这种背景下,尝试利用文本间的互文性理论对“印度系列”五部作品进行整体分析和解读显得尤为必要。
一、故事发展的互文性
互文性又称“文本间性”或“互文本性”,是一种源自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文本理论,近年来广受欢迎。该理论的概念最早由法国符号学家、文学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也就是说,每个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文本与文本之间都是彼此的镜子,每一文本在形成过程中必定要经过对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不同文本之间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开放网络以供人无限延展。杜拉斯“印度系列”中的五部作品实际上就是相互改写、补充和扩展的关系。每一部作品都不能单独作为一个文本被阐释,否则将会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遭遇几乎无法逾越的困难,难以理解作者想表达的真正含义。
杜拉斯这五部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绝不仅仅在于故事背景的雷同,甚至也不完全在于主人公的重复。实际上,《劳儿之劫》讲述的是年少时在订婚舞会上亲眼目睹未婚夫背叛的劳儿的故事,以及她在遭遇残忍抛弃后的一系列疯狂举动。《副领事》讲述是的法国驻拉合尔的年轻副领事官在爱上大使夫人后陷入绝望直至开枪杀人的故事。《爱》更像是一出舞台剧,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惨遭抛弃的疯女人、一个故地重游的旅行者和一个疯囚犯在海滩上的行走与对话。《印度之歌》实际上是小说《副领事》的剧本,1975年在杜拉斯亲自导演下拍成了电影。《恒河之女》则是小说《爱》的剧本,以更为舞台化、立体化的方式呈现了三个主人公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杜拉斯《印度系列》的五部作品之间的真正联系其实在于文本间的互文性。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在“印度系列”五个文本中,《劳儿之劫》应被视为中心文本,是整个故事的始发点,也是对几个人物特点、性格进行分析的参照母本。在《劳儿之劫》中,主人公劳儿在十九岁那年被未婚夫当众抛弃。经过一段时间的静默之后,劳儿与一位音乐家闪婚,生育三个孩子,移居他乡过起了看似正常的生活。十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劳儿随丈夫搬回故乡,并在街上偶遇儿时闺蜜塔佳娜。一些看似已经被劳儿遗忘的记忆慢慢浮出水面,侵蚀着劳儿的人格和生活。劳儿故意制造了与塔佳娜的重逢,成功引诱了塔佳娜的情人雅克·霍德,并且享受于躺在旅馆后面的黑麦田里透过窗户偷窥二人偷情的过程。在雅克的陪同下,劳儿回到十年前被未婚夫抛弃的舞厅里,一切记忆都变得鲜活起来。随后,劳儿最后一次躺在黑麦田里偷窥雅克和塔佳娜的私会,疲惫不堪地睡去了。《劳儿之劫》这部小说为读者呈现了开放性结局,对于劳儿“疲惫不堪地睡去”,杜拉斯没有给予任何定论。关于劳儿为什么要抢夺闺蜜的情人,是不是已经陷入疯狂,以及睡去之后的劳儿在醒来之时会恢复正常还是进一步沦陷,似乎只能在《爱》中找到一丝答案。因此,《爱》可被视为《劳儿之劫》的一种续写,其互文性在于对人物形象的补充和对故事结局的交代。虽然作者杜拉斯在《爱》中完全没有提及三个主人公的名字和身份,但细心的读者仍然可以从微妙的人物关系和对话中发现,曾遭遇情变的疯女人应该就是劳儿。这个疯女人始终跟着一个疯囚犯,他也许就是雅克·霍德。而跟在疯女人身后,试图通过故地重游来寻找当年记忆的旅行者就是劳儿的未婚夫麦克·理查逊。三人一同在劳儿的故乡S海市行走,似乎互不相识,又似乎在寻找着共同的记忆。疯女人已沦为欲望的奴隶,哪个男人要她她就跟谁走,多次怀孕,孩子生出来也不知父亲是谁,于是直接抛弃在荒郊野岭。当疯女人和旅行者重新回到舞厅,关于十年前那场背叛和抛弃的记忆席卷而来。旅行者哭泣着问疯女人那个当年抛弃了她、与情妇远走高飞的未婚夫是不是已经回来,疯女人只漠然地回答:他已经死了。
《爱》实际上很难被定义为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正如法国评论家克里斯提安娜·布洛-拉巴雷尔所言,在《爱》的创作上,“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作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缺少通常的情节支持和传统的叙述话语”。甚至不夸张地说,这部作品是一部没有情节、没有人物塑造、更没有叙事逻辑的文本,语言常常时断时续,处处透着残缺和破碎。无主题、无主线、无人设等特点使得《爱》一旦作为独立文本,几乎不存在可阅读性。唯有结合《劳儿之劫》的人物特征和情节发展,才能依稀推理出《爱》中的人物身份和对话含义。读者一定要通过《爱》才能知道《劳儿之劫》中劳儿是否疯狂以及结局如何,同时一定要通过《劳儿之劫》才能知道《爱》中的人物身份和看似荒唐、无逻辑的对白背后的真正含义,这便是存在于这两个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在《爱》的“剧本”《恒河之女》中,劳儿的故事由画外音讲述,并且也没有交代主人公的名字。对于《劳儿之劫》中劳儿在黑麦田中疲惫睡去这一突如其来、令人匪夷所思的结局,《恒河之女》给出了较为明确的交代:“救护车来到黑麦田把她接走”,但劳儿的“记忆丧失了”,成为了“灰烬”。
二、人物塑造的互文性
《副领事》与《劳儿之劫》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互文性联系。《副领事》中虽然也有劳儿,但只是以一个疯女人的画外音形式出现。电影《印度之歌》将《副领事》的故事搬上荧屏,其开头与结尾都是疯女人劳儿的歌声,凄凉、悲切。《副领事》的主人公是因工作失误被上级从拉合尔调任到加尔各答的年轻副领事让-马克·德·H。他本就是沉默寡言、性格内向的人,因在拉合尔被人指证而贬职到加尔各答,所以遭人排挤,只得处处小心畏缩。在加尔各答领事馆举办的舞会上,他遇见了法国大使夫人安娜-玛丽·斯特雷特。从见到这个女人的第一刻起,他便神魂颠倒、无法自拔,以至于在舞会上变得更加局促紧张。大使夫人是加尔各答最美的女人,却公然与年轻男子麦克·理查逊保持情人关系。长相丑陋的副领事由于爱上了永远无法得到的人而陷入极度的绝望中。当情感的冲动冲昏了理智,他失态地向大使夫人表白。遭遇拒绝和羞辱后,他当场失控大声尖叫,向邻居家发疯一般地开枪,最终被安保人员强行拖出舞厅。实际上,《副领事》中大使夫人安娜-玛丽·斯特雷特的形象对于杜拉斯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在早先出版的《劳儿之劫》中,劳儿的未婚夫正是因为在订婚舞会上对这位大使夫人一见钟情、难以自拔而当众背叛和抛弃了劳儿,与这个年长女人双双离去。杜拉斯在《劳儿之劫》中对安娜-玛丽的形象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她那“举手投足一动一静中的优雅”令人不安,身穿“一袭黑色连衣裙,配着同为黑色的绢纱紧身内衬,领口开得非常低”。她有着一头棕红色的秀发,如同海上夏娃。这个极度性感、风姿绰约的女人带着“死鸟般从容散漫的优雅”与“发自身心的果敢”走入了未婚夫麦克的视野。杜拉斯在此处用大段的篇幅、华丽的辞藻展现了一个不折不扣的“femme fatale”(法文,意为“有着致命魅力的女人”),不禁令人想起王尔德笔下令希律王神魂颠倒、言听计从的莎乐美,和古希腊神话中拥有一切天赋并令男人疯狂的潘多拉。因此在《副领事》中,杜拉斯并未花费多少笔墨对这个充满魅力的女人进行描写。这体现出《劳儿之劫》的文本在对《副领事》的理解和阐释中起到了关键的互文性效果,使得《副领事》中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情节发展也因此变得合乎逻辑。
与此同时,《劳儿之劫》的文本与小说《副领事》和电影《印度之歌》之间的互文性联系也体现在对劳儿当年的未婚夫麦克·理查逊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劳儿之劫》中,杜拉斯只向读者交代了麦克是大地产主的独子,无所事事,却让原本性情冷漠的劳儿情窦初开,陷入了热恋之中,不惜中断学业与之订婚。而麦克这一形象真正呈现在读者面前,是在1975年拍成了电影的《印度之歌》中。麦克作为大使夫人的情人也出席了使馆的舞会,始终伴随在大使夫人左右。这个由英国青年演员克劳德·曼扮演的男子英俊、高大,风度翩翩,非常绅士,有着耀眼的金发和湛蓝的眼仁。此人物一登场,《劳儿之劫》的读者们便可以立刻明白劳儿这个情感上极为淡漠的少女为何会对他一见倾心,以至于在被他抛弃后陷入疯狂。
此外,《劳儿之劫》中的舞会与《副领事》和《印度之歌》中的人物情感也存在互文性联系。《劳儿之劫》中,十九岁的劳儿亲眼目睹未婚夫爱上大使夫人无法自持,想要挽回爱情却无能为力,因为她深知当安娜-玛丽进入到麦克视线的那一刻起,麦克的眼中便不再有她这个未婚妻。因此她只能在舞厅的角落里静静注视这一切的发生,仿佛经历着一场暗无天日的凌迟。直到凌晨舞会结束时,眼看着未婚夫跟随者安娜-玛丽毅然决然地离去,她终于爆发了,尖叫着喊着毫无逻辑的话语,最终昏倒在地。对于劳尔来说,这是一场因爱而产生的绝望。而这种绝望在年轻副领事身上有一种近乎同质的体现。《印度之歌》中,安娜-玛丽在无意间成为副领事的一生所爱。当她无情地拒绝和蔑视副领事的表白,这种打击对于年轻副领事来说其程度不亚于《劳儿之劫》中亲眼目睹爱人背叛给劳儿带来的折磨和摧残。一场“无法挽回的爱”和一场“永远得不到的爱”,其本质都是注定令人绝望和疯狂的爱。这种爱令人战栗、疯狂、喊叫,无论对于脆弱的劳儿还是对于年轻的副领事,都是毁灭性的,因此他们才会有相似的反应。杜拉斯或许有意或许无意地向我们展现了爱与绝望的二重奏,劳儿与副领事看似演绎着各自不相干的故事,实际上却诉说着同样的悲剧。通过劳儿的疯狂,我们可以理解副领事的疯狂;通过副领事的绝望,我们可以理解劳儿的绝望。这便是《劳儿之劫》与《副领事》和《印度之歌》之间更为深层的互文性联系。
三、结语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杜拉斯《印度系列》作为其先后发表的五部作品的集合,并不单纯意味着人物的重合和故事背景的相似。从首先发表的作品《劳儿之劫》展开,杜拉斯通过其他四部作品进行了补充、续写、扩展和交代,使得每一部作品似乎都无法成为独立文本,必须结合其他几部作品才能得到较为深入、合理的阐释。因此,对“印度系列”的整体解读和分析应建立一种向心的圆圈思维模式,《劳儿之劫》为中心文本,《爱》《副领事》《印度之歌》及《恒河女子》则围绕着《劳儿之劫》进行滚动输送。《劳儿之劫》的故事脉络和人物性格、情感不断向周围几个文本进行投射并提供基础参照,而其他几个文本也对《劳儿之劫》进行有机反射、补充。与此同时,作为外围的四部作品之间也存在着极大的内在关联性和动态互补性。五个文本间的互动关系并非单一、单向、平面的,而是丰富、多向、立体的。
实际上,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联系是基于符号的游戏,也是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能动、巧妙的相互作用关系。《印度系列》中五个文本之间互相为彼此的“镜子”,如罗兰·巴特所说,“在一个本文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本文”,在每一个文本的能指背后都蕴含着由五部作品共同砌成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所指。正因为此,以互文视角阐释杜拉斯的《印度系列》才具备某种意义上的必要性。也只有基于互文性理论的文本分析,才能为杜拉斯的“印度系列”提升可读性与可研究性,使广大读者与文学研究者充分意识到其伟大与精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