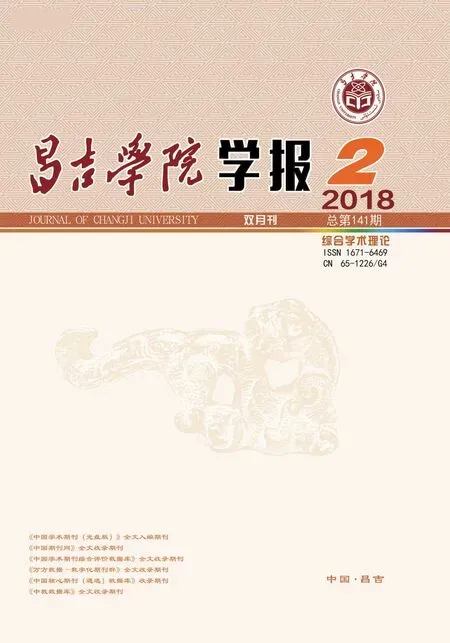苔丝焦虑的双维解读
魏懿颖
(阳光学院外语系 福建 福州 350015)
苔丝·德伯是托马斯·哈代笔下经典的小说人物,对苔丝形象的阐释在评论界可谓汗牛充栋。目前国内研究者多囿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评指苔丝人格的冲突失衡与其悲剧形成的关系,而对苔丝焦虑心理的研究却涉足甚少。鉴于此,本文试从两种维度,运用古典精神分析和新精神分析的双重焦虑理论,深入解析苔丝生理内因形成的现实性、神经性、道德性焦虑和社会文化外因造就的身份认同焦虑,同时阐析苔丝为了克服焦虑所调用的种种心理防御机制。
一、古典精神分析解读苔丝的焦虑与防御
(一)现实性焦虑:与贫苦现实的焦虑抗战
哈代笔下的苔丝一直被贫困和苦难所困扰,这是苔丝源自现实层面的焦虑,即现实性焦虑(reality anxiety)。弗洛伊德认为,当个体面知客观现实的危境便会产生现实性焦虑。[1]苔丝的祖先虽为赫赫有名的贵族,但现实的家境已落魄到小贩阶层,因工业革命的波及而岌岌可危、艰难竭蹶。社会环境的不利、贪杯懒惰的父亲、肤浅虚荣的母亲、年幼待哺的弟妹们,如是种种招致了苔丝赤贫的生活。面对贫穷,苔丝的自我感知到了生存的压力、现实的危境,产生了现实性焦虑。当德伯夫妇在酒馆里喝酒消遣、炫耀祖宗时,只有苔丝在焦灼担心第二天的蜂窝买卖、养家糊口的生计;当老马横死、营生解体时,德伯照样懒惰松散,只有苔丝焦虑地预见庞然森然的艰难窘迫;正因贫困带来的焦虑,即使是被亚雷奸污后、被安玑抛弃后,苔丝仍为生计抛头露面、不顾流言蜚语。
除了生活的赤贫,苔丝所经历的生命的苦难,也是引发她现实性焦虑的重要原因。当得知父亲德伯的心脏病时,苔丝焦心父亲将赴那冥漠之都;当孩子病危时,为人母的苔丝更是焦急心疼,想象这个私生未受洗的罪孩,到了地狱受尽酷刑;当母亲突发大病时,苔丝焦炙不已、不畏春寒料峭、不惧夜行危险赶回了家;当再次直面病重的母亲、无用的父亲,苔丝对弟妹们无望未来的焦虑被亚雷一语中的;当因父亲突然辞世、家人无处容身时,苔丝又有了新的现实焦虑。
然而正确且适当的焦虑却是有益的。因为焦虑是个体发出的警示信号,当人意识到时,就会采取有效的措施,或激励斗志应对消解,或维护生存逃避自保。[2]面对源自现实的焦虑,苔丝一直积极应对、设法消解。无论是在学校里的好学努力,还是在家操持家务、养育弟妹、辛勤耕作的尽心竭力,或是外出打工晨兴夜寐的辛劳,苔丝并没被现实所吓倒,而总是怀揣希望、尽其所能地迎战贫苦,以期克服焦虑、改变命运。尽管苔丝的悲剧结局与其焦虑不无关系,但现实性焦虑于苔丝在一定程度是积极的,而苔丝应对现实性焦虑的方式也是积极的。
(二)神经性焦虑:肉欲与自我的博弈冲突
神经性焦虑(neurotic anxiety)可在非理性的本我将要在个体的言行中表露之时,或有强烈需求的本我不受自我控制之时产生。[3]苔丝的神经性焦虑源于她肉欲本我与理性自我的冲突矛盾。
亚雷无疑代表了苔丝本我爱欲中的肉欲。初遇亚雷的苔丝未沾半点世俗尘埃,但看着却是妩媚成熟的妇人模样。涉世甚少、阅历有限使得苔丝人格中的超我未尽完善,驾驭本我全靠势单力薄的自我,然而本我欲望却已随生理的性成熟而日渐强大。苔丝本能地想要满足肉体欲望、遵循快乐原则,然而只遵从理性原则的自我,一方面不允许苔丝失陷于肉欲,另一方面恐惧着不合礼教的行为会招致的惩罚。在一次次登徒浪子亚雷引诱中,苔丝的反应显示了本我与自我剑拔弩张的较量。当亚雷挑逗般地往苔丝嘴里喂草莓,她虽面带难色,却终把嘴张了、把草莓噙了;当亚雷要亲吻苔丝时,她惊慌掉泪、严词拒绝,最终却默从;当亚雷把苔丝从窘境中带走时,她既有些得意、仍有些疑惧;当亚雷要她作情人时,苔丝并未严拒,相反,应词暧昧而矛盾。在这场本我与自我的兵戈相向中,本我屡屡得胜,自我节节败退。本我的强大已让自我备感无法驾驭,苔丝深陷恐惧的神经性焦虑中。在铸成悲剧的树林中,苔丝的强大本我肉欲彻底战胜了自我,因为她既没表现出应有的警惕也无殊死的拒抗。
同时值得提出的是,因为亚雷所诱发的神经性焦虑,困扰苔丝之深、影响苔丝之巨,可由苔丝的恐怖症略观一二。作为神经性焦虑的表现之一,恐惧症是指对特定外界事物所具有的强烈恐惧情绪。[4]在文本中,苔丝恐惧的特定对象便是亚雷。无论是初见亚雷时的疑惧、还是对亚雷非分要求的惊惧、亦或是失身后的骇惧,苔丝对亚雷的恐惧自始至终一直存在。与亚雷冤家路窄的再面逢,苔丝更是不由地张皇惊恐、瘫痪无力、不能进退。为了防御对亚雷的恐惧,苔丝的自我防御机制采取了替代(displacement)的防御方法。[5]那原本对苔丝而言“是美的”“很熟悉”的绿色山谷,因为打上了“失贞地点”的烙印,而变得可怕起来。从心理层面解释,这种突然的不合理的害怕,实是一种象征性替代,苔丝把对构成威胁的亚雷的恐惧转移到了不具威胁的山谷上,以消解对亚雷的恐惧。
(三)道德性焦虑:“爱”“恨”与超我的冲突较量
首先,灵性爱恋与超我道德冲突较量,构成苔丝道德性焦虑的主旋律。宛若“智慧精灵”的安玑,象征着苔丝本我爱欲中的灵性爱恋。再遇安玑的苔丝,离她的伤心事已有两年,年轻的苔丝又重新点燃起生活的希望,无法抑制寻找快乐的本能。与安玑的日日接近,苔丝坠入了情网,但不同于对亚雷的肉欲需要,苔丝对安玑克莱的情感是升华了的灵性爱恋。苔丝奉安玑为智慧化身、倾心他的温文尔雅、欣赏他的随和待人、仰慕他的博学多才、新奇他的新派思想。然而,灵性爱恋却未能恣意生蔓、开花结果,因为此时的苔丝已不同往日。肉体的磨难、世俗的嘲讽、信仰的禁忌,经历如斯种种,苔丝已接受并内化了维多利亚传统的贞洁观、道德观,形成了她苛刻且强大的超我。依据超我的评判,苔丝认定自己为不洁之身、有罪之人;自认为没有权利去爱别人或者得到别人的垂青;她更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结婚、并发誓不结婚。但是,苔丝对安玑的灵爱、对安玑爱慕的接受、对安玑求婚的同意等等,明显违背了超我内化道德评判。根据弗氏观点,当自身思想和行为有违超我内化的价值观、自我理想、良知时,自我惩罚的道德性焦虑(moral anxiety)就会产生。[6]在牛奶厂与安玑相处的过程,是苔丝饱受道德性焦虑的痛苦过程。苔丝的超我好似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于苔丝的头上。当苔丝的本我爱欲驱使苔丝寻找快乐、满足欲望时,严厉的超我制造出羞耻感、罪疚感、自卑感等情绪来胁迫苔丝可怜的自我,使自我按照理想原则行事。而苔丝的自我被夹于超我本我之间,顾此失彼、矛盾痛苦。
当安玑示好地把好挤的奶牛安排给苔丝时,苔丝不当的回应引起了安玑误会,苔丝的超我立刻严厉谴责自我,苔丝生起自己的气,即便事后,她仍焦虑不已。当安玑并不高明地演奏乐器时,本我爱欲驱使下的苔丝竟像着迷的小鸟般不舍离开、如痴如醉。但限于超我的严苛,只得藏身树后。当苔丝掩盖姿色、躲避安玑,打算牺牲自己、成全伙伴时,她的拒爱却不够斩钉截铁。当安玑不由自主抱住苔丝时,她喜悦而冲动,片刻后因超我的理性认识,痛苦得泪流满面。最终,苔丝那点可怜的良知在强烈的爱欲面前败下阵来,苔丝接受了安玑却未摆脱她的道德焦虑,因为嫁给安玑更是一件超我不允许的罪行。饱受良心谴责的苔丝,难定婚期、欲吐真情,却被本我爱欲次次阻挠。新婚之夜,难敌焦虑的苔丝终于坦白了自己的“不洁”。
可以看出,苔丝对安玑的灵爱具有强大的力量,它步步紧逼、次次越矩、屡屡得胜,苔丝在本我灵爱的驱使下,一次次触犯了超我的道德底线而焦虑焚心。为了摆脱道德焦虑带来的羞耻感、罪疚感,苔丝的自我采取了各种防御与措施,例如她的压抑、躲避、拒爱、牺牲和自白。而面对道德性焦虑带来的自卑感,苔丝的自我采取了认同机制和合理化机制。
在苔丝超我的构建中,安玑象征苔丝超我的自我理想,因为安玑渊博明慧、拥有不可测量安地斯般的智力和有身份有地位的家庭出生。面对“天一般”的安玑,“地一样”的苔丝自卑不已。实现不了自我理想的苔丝,一方面,为了克服智力欠缺的自卑,采用了认同(identification)的防御机制,潜意识地模仿安玑、等同安玑。[7]苔丝崇拜安玑似拜天神一般,不知不觉地模仿安玑说话的语音语调,一字不差地记下他教的知识,学唱他喜欢的歌曲。凡是安玑信的,苔丝绝对相信。甚至在宗教观念上苔丝也与安玑趋同,认同安玑“离经叛教”的思想,以求在精神方面跟他一致。这样的认同,即便在苔丝被安玑抛弃后也仍然在继续。认同帮助苔丝增强了自我的价值感,使苔丝接近超我自我理想的苛刻要求,从而部分克服了道德焦虑带来的自卑感。另一方面,因身份和地位的悬殊差异带来的自卑感,苔丝则采用合理化机制克服。合理化(rationallization),指个体为了掩饰真实动机,用自我可接受、超我能宽恕的理由来文饰自己的行为。[8]自卑的苔丝为自己挣扎辩解:像她和安玑这般高下悬殊的爱恋终成眷属,早有先例;将去开拓殖民地草场的安玑,娶她这样的庄稼人的女人,才近情合理。这些“自我能接受、超我能宽恕”的理由文饰了苔丝的实际卑微的地位、片刻缓解了其焦虑自卑。
其次,与“恨”的较量,是苔丝道德性焦虑的附歌。在安玑抛弃苔丝后,苔丝的超我把一切罪过归咎于自己,认为一切加到苔丝身上的惩罚都是应当的。苔丝愿做奴隶、听他使唤、舍身送命,就是自尽也不愿拖累安玑。然而面对安玑的次次无情决绝,苔丝不可避免地对其产生怨恨。在写给安玑的信中,激愤的苔丝指责安玑的铁心石肠,对她的不公待遇,并表示永不饶恕安玑。这种对安玑的敌意,自安玑抛弃苔丝时便已产生。但是苔丝严厉的超我不仅认为罪过在己,更不允许苔丝有恨安玑的想法。苔丝因这不被超我允许的“恨”的存在,再次产生道德性焦虑。为了宣泄恨意、摆脱焦虑,苔丝选择把敌意心力内投,即通过心力内投(introjection)的焦虑防御机制,把超我不允许的对安玑的恨,内投到自身,形成自残与自虐。[9]苔丝有文化,却自虐到最贫瘠的土地上去艰苦务农;苔丝年轻貌美,却故意衣着褴褛、遮颜蔽貌;从面上,把自己弄成一个“毫无生气的无机体。”[10]对自己的虐待与敌恨,帮助苔丝宣泄了怨恨,消除了焦虑。
最后,需指出的是,道德性焦虑是导致苔丝杀人自陨的根本原因。父亲的离世、家境的窘迫,迫使苔丝再次沦为亚雷的情妇。这是苔丝严厉的超我绝不容许的,因为这既有悖于超我内化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同时又亵渎了超我中的良心。饱受道德性焦虑折磨与惩罚的苔丝,最终用极端的方式结束了亚雷的生命。正如韦恩博恩斯所指:苔丝若想抹去对亚雷肉欲的、鄙俗的情感,只有通过消除亚雷的肉体来实现,如此才能归还安玑一个纯洁的妻子。[11]为了根除焦虑、为了还原“纯洁”、为了保守最后一丝道德底线,苔丝亲手酿制了亚雷和自己的悲剧。
二、新精神分析阐释苔丝的身份认同焦虑
卡伦·霍妮是新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弗洛伊德不同,霍妮认为人的焦虑虽有生理的内因,但更有社会文化的外因。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当个体偏离社会文化的共同模式(即心理行为模式)时,便会产生焦虑。[12]对自身贵族身份认同的过程中,苔丝产生了焦虑。而追根结底,这份身份认同焦虑与故事所处的社会文化密不可分。
哈代将苔丝的故事置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后期,一个旧世风雨飘飖、新世艰难诞生的时代。社会的转型、秩序的重构,使得社会文化领域中的意识形态也演变分化,尤其体现在对贵族阶层的观念态度上。一方面,虽然贵族阶层已若强弩之末、特权不复,但是依旧存在的阶级观念加之弥漫于各阶层的怀旧的情绪,使得许多人仍对贵族敬慕认同。另一方面,新崛起的中产阶级欲重划社会阶层,提升社会地位。没落的贵族便是他们的嘲讽对象、登高的绊脚之石。此外,部分贵族徒留虚名、奢靡腐化,这也让众人不满敌视。由此可见,对于贵族的评判,当时的社会给其个体成员强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标准。亦即对贵族的看法,在该时代的特定社会文化中存在两种心理行为模式——敬慕认同与讥嘲敌视。在对自身贵族身份认同的过程中,苔丝的心理频繁地摇摆于这两种模式之间,合此离彼、焦虑不断。
贪钱财、好面子的苔丝父母和图虚荣、用假姓的亚雷,无疑属于敬慕认同贵族的人。不同于父母激动忘形、假此谋利,当知晓自己的贵族身份后,苔丝无意用此自抬身价。相反,对这名存实亡、毫无钱权的没落贵族,苔丝最初的心理更倾向于讥讽嘲弄的模式。在露天草场的舞会上,当安玑未邀苔丝跳舞时,苔丝嘲讽祖宗的功绩,若无财富相助,又有何用?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苔丝在潜意识中渐渐认同了自己贵族的血统、复苏了高傲的气息。乡村舞会上,面对粗俗女人的恶语相向、露臂握拳,苔丝仪态俨然、不怒自威,活脱脱一个贵族形象。
然而此刻的认同与那时的嘲讽,于苔丝而言都只是暂时的。事实上苔丝一直游离在这两种心理模式之间,不可避免地焦虑矛盾。结识登徒子亚雷、招致失贞之祸的“始作俑者”,正是那象征贵族身份的“德伯氏”。懊悔不已的苔丝打定主意:无论是梦想还是现实,都不许再有虚无缥缈的德伯氏存在。去往牛奶厂的苔丝宣称:对于她的无用祖宗没有敬只有恨。可矛盾的是,牛奶厂之所以让苔丝感兴趣,正是因为它离祖宗的故土很近。即便只是一名挤奶工,苔丝举手投足、言谈举止无不流露贵族气质,让安玑觉得无论是性格还是体貌,苔丝几乎拥有国母王后般的庄严威仪。苔丝甚至想对安玑透露自己的嫡系祖先、地道的贵族身份,好让安玑对她尊重。这些无不是苔丝选择敬慕认同的心理模式的表现。
安玑克莱对贵族的观念,吻合了新兴中产阶级对待贵族阶层的态度。贵族“老门户”是天地间最招安玑憎恨的东西。安玑嗤笑贵族的没落无能和腐朽思想,厌恶的贵族阶级“血统高于一切”的主张。为了获得安玑的倾心,苔丝的心理又再次偏离了认同敬慕的模式,对自己的祖先绝口不谈。当苔丝为自己对安玑的爱恋辩解时,她以“庄家人家的女儿”自居,会田地农活、能养殖牛羊是农民女儿引以为豪的优势,是安玑娶她近情近理的理由。对贵族的认同被苔丝暂时地驱赶至潜意识中,直至苔丝向安玑坦白过往时,因苔丝的口误,重回意识层面。无法接受苔丝的不洁过往,安玑怒责苔丝是个不懂事儿的乡下女人。苔丝听罢,不觉发了一阵火儿,并反驳:论地位,她是个乡下人;但看根本,她可不是乡下人![13]这足以证明,那时苔丝的心理又重新回归了敬慕认同的模式。
括而言之,对贵族阶层的评判,在维多利亚后期的社会文化中存在两种判然不同的标准,社会成员拥有两种似霄壤之别的心理行为模式——敬慕认同与讥嘲敌视。这样的时代文化之殇深深地烙刻在苔丝对其贵族身份的接受过程中。无论苔丝的心理选择哪种文化共同模式,都是对另一模式的偏离与违背,而矛盾的苔丝却总是游离于两个极端,不可避免地焦虑痛苦。
结语
在苔丝的世界中,焦虑一直是她的主导情绪。在古典精神分析和新精神分析焦虑理论的观照下,一个被焦虑湮没的苔丝得到了更全面和深入的形象阐释,苔丝焦虑产生的生理层面的内因、社会文化的外因得到了更为准确的把握。无论是面对生理内因亦或文化外因,苔丝总是积极地调动心理防御机制进行抵御,却又常常无功而返,而焦虑最终导致了苔丝的悲剧。同时,从一定意义上说,哈代对焦虑苔丝的塑造,既是他本人焦虑“心相”的反映,也是时代焦虑“世相”的投射。
参考文献:
[1][2][4][5][6][7][8][9]车文博.车文博文集:弗洛伊德主义(第六卷)[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23,227,225,246,226,240,243,240.
[3]B.R.赫根汉著,郭本禹等译.心理学史导论(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98.
[10][13]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一个纯洁的女人(张若谷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394,327.
[11]Burns Wayne.the Flesh and the Spirit in Seven Hardy Novels[M].California:Blue Daylight Books,2002:138
[12]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孙名等编)[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