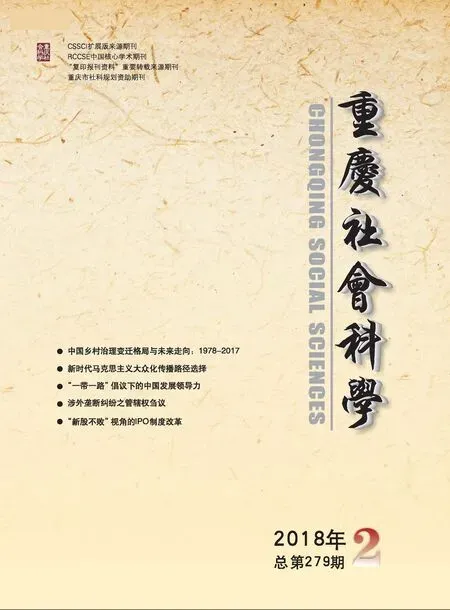董仲舒对荀子天论的继承与改造
刘 龙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200241)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荀子的天论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之中扮演着奠基性的角色,荀子对人性论的具体阐发及其关于社会与政治思想的建构都是建立在其对天的论说的基础上的。①我们有理由同意Edward J.Machle的如下说法:“任何一个研究古代中国哲学和宗教的人都不能不注意到荀子,而任何人若不研究荀子的《天论》,便不能究明荀子的思想。”Edward J.Machle,Natuer and Heaven in the Xunzi—A study of the Tian Lun,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Albany,1993,p.xi.自20世纪以来,海内外学界对荀子的天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但是其中大多数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对荀子天论的客观叙述与正面分析,而对荀子天论中所蕴含的内在张力和理论困境则鲜有深入的剖析。实际上,我们发现,在关于天的一系列论述之中,荀子其实并未能协调好天与人的分离性与关联性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带来了天人关系的紧张,这进而造成了荀子的人性论言说中的内在张力与理论困境。西汉之后,董仲舒在继承了荀子天论的基本观点的同时,又对之加以进一步的改造,以通过建立起“天人相副”的人的法天机制这一方式将天人关系的分离性与关联性有机地统合起来,从而有效消解了在荀子那里表现出的天人关系的紧张。
在荀子思想之中,“天”具有十分丰富的、多个层面的涵义。在荀子文本之中,荀子在论及天时,往往并没有明确指出自己是在“天”的何种意义和哪个层面上进行言说的,即荀子对于天的不同层次内涵的使用往往是不加清晰界定的。为厘清荀子天论的内在理路,有必要先对荀子论天的多方面向度进行逐一疏解,本文前两部分便是试图对荀子的天论做一义理疏解,厘清其对天的涵义的几层论述,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其天论内在的理论张力与思想困境;第三部分则探究董仲舒对荀子天论的继承与改造,并且考察董仲舒是如何有效化解荀子天人关系的紧张性的。
一、荀子文本中“天”的三层涵义
在荀子对天的论说之中,“天”主要有以下三种涵义。
(一)作为与“地”相对的“天”
在《荀子》中,“天”的第一个涵义是与“地”相对的天。比如荀子有云:“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荀子·儒效》,下引荀子原文之时,为求简略,只标注篇章名)又比如荀子说:“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儒效》)荀子又云:“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王制》)又云:“天地者,生之始也。”(《王制》)在以上所举的荀子言天的几个例子中,荀子将天、地或天、地、人对举,可见此时天乃是与地、人并列的存在物,所以很明显,在这几处之中,荀子所说的“天”便是指我们头顶上的茫茫之天,即是“天空”之“天”。这也是在中国思想中,天的最通常、最朴素的涵义。
(二)作为大自然之总体的“天”
在荀子的文本之中,“天”的第二个涵义是人与万物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的气候、土壤、地理、水文等自然环境或自然条件的总和,其范围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自然界。这个涵义也是从“天地”之“天”的意义扩展而来。盖天空与大地,乃是人类与万物活动空间的上限与下限,人类与万物皆存在并活动于天地之间,而不能出离此范围。这一整体性的自然环境本身,在荀子这里,可以用“天”一言以蔽之。比如荀子在《天论》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天论》)我们知道,在现实世界之中,“水旱”(即洪涝)与干旱这样的自然灾害的发生与众多的自然条件有关。“水旱”之发生一方面要关乎天(天地之“天”)之降水的多寡,另一方面还关乎地上的地理条件的现状,比如诸如河流、土壤、气候等一系列自然情况。所以此处,荀子所言说的天并不只是指涉“天空”之“天”,其所指向的乃是人之生活于其中的整个自然界。
(三)作为万物尤其是人所本具的先天机能
在荀子文本中,“天”的第三个涵义乃是万物尤其是人所本具的先天机能。人本身亦是自然界中的成员,非在自然界之外,人亦依托天地而生,为天地之子。人在经验生活之中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活动机能也是属天的。比如荀子有云:“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天论》)喜、怒、哀、乐原本是人在日常生活之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状态,而荀子却将其说成是“天情”,即在荀子看来,人的喜、怒、哀、乐等情感活动乃是得自于天的,是“天职”和“天功”,即“天的职分”和“天的功劳”。可见,对荀子来说,喜、怒、哀、乐乃是属天的自然情感,是人所本具的先天机能。
同样,人之耳、目、鼻、口等感觉器官具有不同的器质构造与由此导致的不同的感受功能,这也是天所给定的,“各有接而不相能”,即耳、目、鼻、口等感觉器官各自有其不同的职能而不能互相替代,比如耳的“天职”或“天功”是听音,目的“天职”或“天功”是辨色;耳不能辨色,目不能听音,这是由天所决定的,是耳、目具有不同的先天机能所导致的,所以人们不可能去违逆“天职”“天功”,而试图让耳朵去辨色,让眼睛去听音。
所以对于人来说,“天情”“天官”“天君”等乃是天之所给定于人的,是人之出生便已经所禀赋的。对于喜、怒、哀、乐之“天情”、耳听目视之“天官”、心治五官之“天君”等来自于天的运作机制,人只可以遵循或背逆,但是这种机制是人所不能创造的。所以荀子说:“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论》)这种天的机制虽然很幽深、很博大、很精密,但是人却“不加虑”“不加能”“不加察”,即无法干涉和改变它们。所以荀子会说“不与天争职”。在荀子这里,所谓“不与天争职”便是人应该明确人与天的分限,而提醒自己不要企图僭越这种分限,即人不要去试图干预已经不属于人力所及而专属于天的职分,所以荀子会说:“唯圣人不求知天。”(《天论》)
但是,荀子在《天论》的另一处表述之中,又明确提出了人应该要求“知天”的主张。①荀子说:“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天论》)这便产生了一个让人们非常困惑的问题,即在荀子《天论》乃至整个荀子文本之中,荀子的“知天”与“不求知天”之间是否有思想上的矛盾呢?其实仔细考察《荀子》全文,我们发现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在荀子这里,“知天”与“不求知天”是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言说的。“知天”意味着“知其所为”和“知其所不为”,即是知道人之所为与人之所不为的分限。而“不求知天”实际上是对属于天之职分,而“人之所不为”之处保持沉默。只有做到了“知天”,即明晰了对于人来说的可知与不可知这两个不同领域的分限,人们才能做到“不求知天”。所以后来唐代学者杨倞对于“唯圣人不求知天”便有如下的注释:“此明不务知天,是乃知天也。”[1]从思想史上来看,荀子提出“不务知天”的主张,实际上反映了他对当时的流俗对天的两种通常的理解的摒弃。荀子同时代的学者对天的理解一般有这样两种类型:一是将天理解为一种具有神秘属性的意志,天人之间可以以巫术、祥等神秘性的活动达成沟通;一是将天理解为作为道德根据的人格化的存在,即孔子之“性与天道”的“天”、孟子所谓“尽其心也,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天。②徐复观先生说:“但到了孔子、孟子,则是在以仁为中心的下学而上达的人格修养中,发现道德的超越性、普遍性;由此种超越性、普遍性而与传统的天、天命的观念相印合,于是把性与天命(天道)融合起来,以形成精神中的天人合一。这是通过道德实践所达到的精神境界,是从人自身的道德精神所实证、所肯定的天,或天命(道);所以孔子要到五十才能知天命,孟子一定要从“尽心”处以言知性、知天。因此,春秋时代所说的道德性地天,乃属于概念推论的性质;而在孔子、孟子,则不仅是概念推论的性质,同时,却是精神的实证的性质,也可以说是自己的人格化的天。(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203页。)荀子不仅反对前一种对天的神秘化言说,也拒斥了后一种对天的道德人格化的言说。在摒弃了时人对天的以上两种理解方式之后,荀子将天进行了彻底经验化的处理,此正如徐复观先生有言:“他(指荀子,作者按)一切的论据,皆立足于感官所能经验得到的范围之内。为感官经验所不及的,便不寄与以信任。”[2]与其经验论的立场相关,荀子所致力于的知天,便是不必知道天何以如此,只需知道在经验生活之中如何顺应自然规律,即只要能顺着“天职”“天功”就可以实现“官天地”“役万物”了,人类不必深究天的深邃的运作原理。③荀子说:“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于地者,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天论》)在荀子看来,对于天地,人们只要了解星象的变化与土壤、水文状况等信息,用以指导人们的农业生活就行了,至于天地运行背后的深层次机理则没有必要去了解。
总之,在荀子这里,“知天”与“不求知天”是有机统一在一起的,二者所共同指向的乃是“明于天人之分”“不与天争职”,即天人相分的思路。荀子明确了天与人的分限,正好为人的活动预留和允让了一个独立的空间。
二、天与性
荀子对天的言说,真正的关切点并不是在宇宙论层面上,而是意图在人的世界中发展一种关于人性的学说,并且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通过“化性起伪”,用礼制教化来建构起一个和谐的社会。因此,荀子对天的论说必然会落实到人性上去。
(一)荀子论人性的内容
天在人中的表现形态便是性,在这里,荀子明确指出了人性的根源便是“天之就”,是“不可学”“不可事”的。①荀子云:“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性恶》)可见,在荀子这里,人性之来源便是上面第一节所讨论的第三种意义层面上的天。那么,人性的内容是什么?荀子说:“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荣辱》)荀子在这段话中所论述的人之性有两种层次的涵义。第一个层次是眼、耳、鼻、口、皮肤等人的感觉器官所分别具有的视、听、味、嗅、触的功能,即人的感官机能。第二个层次是建立在人的感官机能上的人的感官欲望,即“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以上二者便是人的性情,是人所不能加以改变的,是天职在人身上之体现。
(二)化性起伪与礼义的来源
荀子认为,“好利”与“疾恶”二者都是人天生的本性,如果在人类社会之中,每一个人都顺着这个本性而不加以限制与范导的话,那么社会成员之间便会因互相争夺利益而彼此残害,辞让、忠信这样的品德便不会在人类社会之中表现出来。耳目、声色之欲也是人的本性,如果每个人都顺着这些感性欲望而不加节制的话,那么便会出现人人相互争夺,导致“犯分乱理”的社会现实。可见,在荀子看来,如果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完全顺应“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这种天性的话,那么人类社会便会遭遇到巨大的灾难。②荀子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性恶》)那么在人类社会中(如果这时还有社会的话)每一个人都像狼一样凶残,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会被别人伤害。这种状况就如同英国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在《利维坦》中所描述的“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战争的状况”[3],这样的生活状况对人类世界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梦魇一般的存在。基于这样的对人性状况的理解,荀子用“恶”来标画人性。他说:“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性恶》)所以,在荀子看来,如果人类社会要想走向一比较健康的发展道路的话,就必须在人类世界中引进另外一条迥异于天性的行为原则来引导、矫饰人的天性。这种行为的原则在荀子看来便是“伪”,便是礼义。
在荀子看来,礼义对人性有一种“矫饰”的功能。③荀子有云:“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性恶》)在荀子这里,“矫饰”并不是对人的性情的遏制和堵截,而是一种对人的性情的疏导和文饰。以荀子的观点来看,“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是天性,是人无法改变的。“矫饰”并非旨在改变天性,其只是通过引进另外一种机制,即礼义来改变人满足这种欲望的本有形式。荀子说:“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论》)在荀子看来,先王制作礼义,用礼义来节制、疏导、规范社会生活中每个人的欲求,使得在整个社会之中,每个人的欲求都能在一定限度上得以满足,但同时又允让了其他人欲求得以满足的可能性。这样对社会整体来说,欲求与欲求的对象之间达到了一个最佳的平衡状态,这便是荀子所说的“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的状态,此时社会的整体幸福达到了最大化的实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如果按照西方伦理学的术语来说,荀子所持有的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念。①所谓功利主义道德观,其归根到底只有一个根本的道德原则,即效用原则(priciple of utility),“按照这个原则,每当我们能够在可供取舍的行动历程或者社会政策中作出一个选择时,我们必须选择这样一个行动历程或社会政策,以至于那个行动历程或社会政策会对每一个相关的人都产生整体上最好的结果。”见徐向东:《自我、他人与道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63页。在荀子看来,礼义运作的目的乃在于达成每个人的平均幸福的最高限度,道德的事业是完全属人的事业,是完全在人的职分之内的自我营为,其作用方式是达成对人的天性的调燮,而此时作为人所本具的先天机能的“天”不仅仅成了与道德无关的事情,反而被标画为道德的阻碍。
三、荀子天论的理论困境与董仲舒对荀子天论的继承与改造
我们注意到,在荀子文本中,荀子对天的各种论述之间并不是完全逻辑自洽的,相反是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张力和理论困境的。董仲舒继承了荀子天论的某些核心观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有效消除了荀子天论之中的理论困境。
(一)荀子天论的理论困境
荀子说:“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天论》)在荀子看来,人只要做到了“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便能够“全其天功”,即人对天的“正”“备”“顺”“养”都是对天性的一种顺应。可是根据荀子其他的相关论述,“正”“备”“顺”“养”这些功夫又恰恰都需要礼义的引导和规范才能实现。而根据荀子,礼义的实施恰恰违反天性,是一种“伪”的行为。于是,在荀子这里,便有这样一个逻辑,即人只有通过“背天(化性起伪)”才能达到“顺天(成就天功)”,即只有通过“伪”,才能尽天性。但是荀子又分明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以善、恶这种截然相反的涵义来区分“性”“伪”,于是在这一段话中,“伪”与“尽天性”又好像不能兼容。①所谓功利主义道德观,其归根到底只有一个根本的道德原则,即效用原则(priciple of utility),“按照这个原则,每当我们能够在可供取舍的行动历程或者社会政策中作出一个选择时,我们必须选择这样一个行动历程或社会政策,以至于那个行动历程或社会政策会对每一个相关的人都产生整体上最好的结果。”见徐向东:《自我、他人与道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63页。由此可见荀子在对性伪关系方面的论述有一定的矛盾性。
另外,荀子既然认为“性”是“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的,是完全属天的,那么与之相对,在荀子看来,“伪”便自然是属于人的后天营为的范围,是属人的了。其实伪之所以可能,是以性作为根基的,即只有“化性”才能“起伪”,即人所具有的能够“起伪”的能力本身是来自于天性的,并且这种能力在每个人身上都是具备的。在荀子看来,在现实生活之中,人人皆有成为圣人的可能,皆具备成为圣人的资质,这种资质其实本身便是属于天性的。③荀子说:“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为禹。足可以遍行天下,然而未尝有能遍行天下者也。”(《天论》)按照荀子的观点,人之能够化性起伪,从而成就礼义与道德乃是背天属人之事,然而人之可以化性起伪,具有可以成就礼义与道德的能力,这乃是属于人人所具备的一种固有的“天性”。可见,对于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上的每个人来说,其实“伪”也具有天的根源,是对每个人所具有的天性的一种顺应。如果荀子用“善”来刻画“伪”的话,那么在作为善的基础的天性中也必然有善的根芽,而荀子却径以“恶”来标画人性,则显得有些武断。
总之,荀子一方面已经关注到天与人之间的分离性与异质性,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继续保持了天与人之间内在的关联性。但是由于对“明于天人之分”的过于强调和性、伪异质性的过分突出,荀子并不能很好地将天与人的分离性与关联性有机统合在一起,这带来了荀子思想中天人关系的紧张,造成了荀子人性论的内在张力与理论困境。
(二)董仲舒对荀子天论的继承
荀子的天论对汉代思想界影响较大,有学者指出:“西汉儒家提出的‘天人相参’的思想大体继承了荀学的路向,以此展现出与荀子相似的性、命观念。”[4]对比董仲舒在其主要著作《春秋繁露》中对天的论述,我们发现董仲舒的观点在很多方面都继承自荀子。
在《春秋繁露》之中,董仲舒所理解的天也基本上不出于上文所分析的荀子论天的三项基本涵义。比如董仲舒说:“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下文引董仲舒文本,凡出自于《春秋繁露》一书,如有再引,只标出篇名)在这段文字之中,先后出现了两个“天”字,第一个“天”与“地”对举,很明显乃是“天空”之“天”;但是董仲舒所云的“形体骨肉”与“空窍理脉”乃是地之象,人不仅取象于天,而且取象于地。所以这段话中,第二个“天”乃是总括天地,即表征整个自然界。与荀子类似,董仲舒也用“天”来表征人天生的生理和心理机能,董仲舒说:“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实性》)“性者,天质之朴也”,在董仲舒看来,性之来源不仅归于天,而且是“朴”,此论明显受到了荀子的影响,荀子说性是“本始材朴”①荀子云:“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礼论》),所谓朴,便是人先天的机能,是生之而然者。
董仲舒又对性的涵义进行了词源学意义上的考察,认为性之名来源于“生”,是对人的后天材质的描述。②董仲舒又云:“今世闇于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试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与?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诘性之质于善之名,能中之与?既不能中矣,而尚谓之质善,何哉?性之名不得离质,离质如毛,则非性已,不可不察也。”(《深察名号》)“性”本身并不附著着善、恶这样的价值论上的意涵。董仲舒说:“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实性》)董仲舒用米与禾的关系来说明善与性的关系。在董仲舒看来,就像米是从禾中长出来一样,善也是人性在后天的经验生活之中所发展出来的结果,并不意味着人性本来就是善的。由此,同荀子一样,董仲舒也反驳了性善论。
董仲舒又说:“天之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性,止之外谓人事。”(《深察名号》)在这里,董仲舒对天性与人事之间的界限做出了明确的标定,此种说法与荀子所谓之“明于天人之分”的观点非常相似。与荀子一样,董仲舒通过对天性与人事进行区分,从而为人的后天修为预留了空间。
(三)董仲舒对荀子天论的改造
然而董仲舒之论天,毕竟与荀子有不同之处。董仲舒对荀子“天论”的某些论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用另一种不同于荀子的方式重构了天人关系,并且克服了荀子思想中天人关系的紧张性。
在荀子看来,人性是恶的,所谓“恶”者,乃是指如果人顺情欲之发展,不加节制,放浪而无所约束的话,便会导致“犯分乱理”(《正论》)的恶行,所以圣王要制作礼义以“化性起伪”,即圣王用“伪”(也就是后天的礼仪法度)去约束、范导社会成员的各自的天性。在荀子这里,作为人的后天修为的主要内容的“伪”是背逆于人的性情的。这样,人之后天的修为在有顺承天性的一面的同时,又有了限制、规训天性的一面;于是在荀子这里,在天与人的关系之中,呈现出了一定的张力,天、人之间表现出相当的紧张性。
董仲舒尽管也不同意性善说,但是却没有走向荀子所坚持的性恶说,而是持有一种“性未善论”的人性观。[5]前文已经指出,董仲舒将性与善的关系比作米与禾的关系;米不是禾,但是从禾中可以长出米来,同样,性本身不具有善的性质,但是善可以从性中生长出来。所以在董仲舒看来,性乃是善之成长的一个基石,其可以称之为“朴”,但不能称之为恶。人的后天的修为虽然是天性之外的东西,但是并不是对性情本身的背逆,而是一种对性情的发展和增益,此之谓“继天”。董仲舒说:“善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深察名号》)“继天”便是在继承了上天所赋予的材质的基础上再加以发展的过程。比如一个孩子具有音乐方面的天赋,我们会说不要败坏了上天赋予这个孩子的天才,在后天的经验生活之中还要多加练习,刻苦努力才能将这个天赋实现出来。在董仲舒看来,上天生我们为人,是说我们的材质中已经蕴含了为人的所有的潜质;这一可成就为人的潜质便是上天之赋予人的。所以,在董仲舒看来,人的后天修为并不是违背天性的,相反还需要顺应天性,还需要“继天”,而“继天”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法天”的过程。
董仲舒说:“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栣,与天道一也。是以阴之行不得干春夏,而月之魄常厌于日光,占全占伤。天之禁阴如此,安得不损其欲而辍其情以应天?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犹天也,禁天所禁,非禁天也。”(《深察名号》)通过这段论述,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相比于荀子,董仲舒对人的后天修为问题上所内蕴的天人关系的论述,表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路。前面已经提到,荀子认为人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之中克制自己的情欲完全是出于一种功利主义的角度,其根源是人类社会维持正常秩序的需求和追求社会整体幸福最大化的目标。对于荀子来说,克制情欲这种行为本身却是违背人类自身所具备的天性的,乃是一种“伪”。但是董仲舒却认为,人之“损欲辍情”这样的行为其实并不是对天的违背,反而是效法天的一种体现。董仲舒云:“四气者,天与人所同有也,非人所能蓄也。”(《王道通三》)因为天人一气,天的阴阳二气表现在人身上便是贪仁二气,既然天有阴气与阳气相对,那么人之有仁亦有贪。对于天来说,只有让阳主于阴,天道才能正常运行;因此同样,人宜当效法于天,去“损欲辍情”,扬“仁”抑“贪”。
需要指出的是,在董仲舒的所论述的法天机制之中,天其实并不只是一个可供人模仿的与人利害无涉的对象和楷模。天还会以“天人感应”的方式对人的法天行为进行反馈。董仲舒有云:“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王道》)在董仲舒看来,天人之间存在着感应关系,当人间的统治者能够法天施政的时候,天便以风调雨顺示人;而当人间的统治者不能法天施政的时候,那么此时天便会现出“贼气”,便会降下灾祸,对人进行谴告。也就是说在法天机制之中,由于“天人感应”,天人进行着双向的沟通。一方面人要去效法天,另一方面,天又要通过“天人感应”的方式对人的法天活动进行检视,并且给予反馈,当人不能效法天道的时候,便会给人以谴告甚至威吓。①董仲舒又云:“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必仁且知》))又董仲舒《天人三策》有云:“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汉书·董仲舒传》,见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174页)
可见与荀子将人类的道德行为的终极根据建基在人类之自我营为之上不同,在董仲舒认为,人类后天道德行为的终极根据乃是来源于天的。通过人的“法天”,天会继续在人身上起作用;如果人不能有效地“法天”,天还会给人类社会降下惩罚。但是需要指出,在董仲舒的关于“法天”的论述之中,人与天乃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即天作为外在于人的客观对象而供人所学习、效法。即使是天对人的惩罚或奖赏也是以一种外在于人的方式进行的。这种天人关系不同于后世宋明理学家以“性即理”或者“心即理”的方式所达成的一种内在的天人合一①此处可参加拙文:《天的重新发现与宋明理学的开端:基于二程的考察》,见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编:《哲学评论》,第21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如果借用康德哲学的术语,我们发现,在董仲舒这里,天对人的指导是一种范导性的而非构成性的关系,即天为了人之美好生活的建立设立了一种方向的引导,并且当人不遵守这种引导之时还会带给人以惩罚。但是对于人来,毕竟能不能或愿不愿实现对天的效法是系之于人自身的意愿的,这种意愿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外在于天的。
在董仲舒这里,天对人的作用蕴含有两个层面。一是在人的先天层面,天能生人,并赋予了人的先天机能,这便是人性,并且天已经赋予它尚未显发的但是可以为礼义的潜能。②董仲舒说:“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疢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物疢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人副天数》)二是在人出生之后的后天层面,天又在两个方面起到的作用。第一,人之先天赋予人的机能会继续发挥,这样会有利于先天之性中所隐而未发的可以为善的潜能逐渐显发、朗现。第二,提供了人的后天之政治行为(主要是对君主以及治民者而言)和个人道德行为(对所有人)的行动的指南,人遵循了这样的指南,便可以做出能够参天地的事业。③董仲舒说:“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当之,此见人之绝于物而参天地。”(《人副天数》)在董仲舒看来,人之所以能够参天地,乃是由于人所禀得的天性最正,并且天的作为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所以董仲舒说:“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王道通三》)
董仲舒说“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这让我们联想到荀子也曾有“人为天下贵”的说法。④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王制》)虽然荀子与董仲舒都认为“人为天下贵”,并且都认为“人为天下贵”的原因乃是人有仁义道德,但是荀子认为人之贵乃在于人可以通过礼义的施用,在人类社会之中达到“明分使群”的效果,通过“明分使群”,人类进而可以操纵自然,宰制万物;即在荀子这里,人之贵乃是体现在冲破天对人的束缚方面,即是人可以通过“背天”而所达致的“治天”的功业。而董仲舒的观点则与荀子不同,在董仲舒看来,人之所贵之处乃在于人最能体现、并展现天道,人之可贵乃在于人能最大程度地“顺天”。
在天人关系上,董仲舒“顺天”思想与荀子“治天”思想的不同,体现了二人不同的伦理学旨趣。从某种意义上讲,董仲舒改变了荀子功利主义的道德建构,放弃了荀子以经验性标准来为人类的道德事业奠基的尝试,转而将在荀子那里务加排斥与坚决摒弃的具有神秘性的意志之天又拉了回来,来充当人之道德事业的最终根据。由此,原本在荀子那里存在的天人关系的内在张力,得以通过“天人相副”的法天机制得以消解。最终,董仲舒在消化荀子思想的基础上,又成功开辟出一条新的儒学的发展道路,对后世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2:302.
[2]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202.
[3]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97.
[4]余亚斐.荀学与西汉儒学之趋向[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81.
[5]周桂钿.董学探微[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