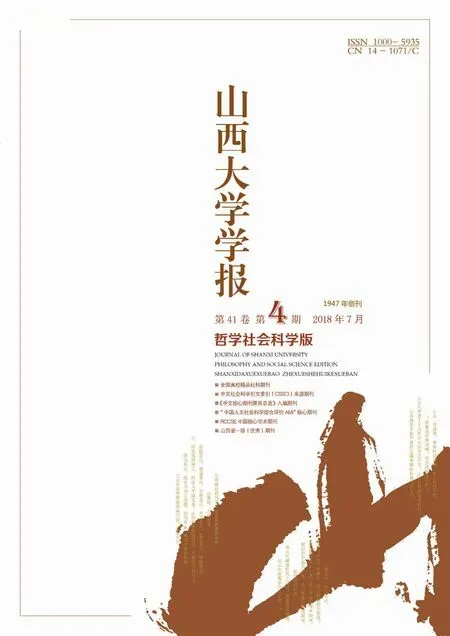苏轼诗画关系理论发微
——以故为新的赋诗
李 制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句,是探讨诗歌创作的方式,理解诗义的重点在于厘清“赋诗”与“此诗”的关系,难点在于检讨“赋诗”的意涵。实际上,苏轼所论的赋诗,“就宋人看来,其精神无非是‘绕路说诗’,……‘于题外立意’”。[1]54但是,从元代以降,即有另一种观点认为,“赋诗”指的是诗歌创作(及创作论),并将苏轼诗义解作“论诗必此诗”或“作诗必此诗”。*“论诗必此诗”之说,见于明代陈继儒《眉公杂著》;“作诗必此诗”之说至晚在元代汤垕《画鉴》处即已出现,明代李贽《焚书·诗画》、清代邹一桂《小山画谱》和李修易《小蓬莱阁画鉴》继承此说,现当代学者如胡明《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等,也以作诗为起点而探讨苏轼诗画关系理论。另,“定知非诗人”又作“定非知诗人”。考察宋人诗作,在一些具体的语境中,“赋诗”确有诗歌创作之义*在一些语境中,赋诗即指作诗。从诗题看,苏轼有《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苏辙有《偶游大愚见余杭明雅照师旧识子瞻能言西湖旧游将行赋诗送之》等;从诗句看,苏辙有“九日真佳节,年年长赋诗”等。苏氏昆仲的这些诗题、诗句中的“赋诗”大都是因事而赋,此时,“赋诗”与作诗差别不大。但在如苏辙“赋诗《柏舟》,至死不渝”等诗句中,“赋诗”与作诗见出差异,详见下文。,然而,若将诗义直观解作“作诗必此诗”,则主体当下所作之诗与“此诗”间就呈现出逻辑冲突,使诗义变得含混。可知,领会“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之论的关要在于不可将此处的“赋诗”完全等同于作诗。接下来的论述,即以“赋诗”为出发点,考察苏轼所论的诗画关系。
一 文学史中的赋诗传统
“赋诗”在诗学传统中是一种不断发展衍变的诗歌创作方式。先秦时期的“赋诗”是指各诸侯国使节在外交场合中引用并跳脱出《诗经》中的某章,通过“断章取义”而“赋诗言志”,借以表述既不同于《诗经》原句,又带有特定政治目的之特定意思的一种外交辞令。朱自清先生指出:“春秋时通行赋诗,在外交宴会里,各国使节往往点一篇诗或几篇诗叫乐工唱,……表示这国对那国或这人对那人的愿望、感谢、责难等等,都从诗篇里断章取义。断章取义是不管上下文的意义,只将一章中一两句拉出来,就当前的环境,作政治的暗示”[2]30。南朝以降,在诗歌创作的意义上讲,“赋诗”逐渐发展出“赋得”和“分韵赋诗”等形式*一般认为晋、宋前无赋得体,应起于沈约《江蓠生幽渚》,但沈约并未在诗题前冠以“赋得”二字,唐宋科举程试诗多有以古句为题,称赋得,又有不依古句,而在咏物、别离等题材的诗题前冠以“赋得”的,不赘。,在一些特定情境中(如因事而赋等),“赋诗”略同于作诗,如庾信的《赋得荷》《赋得集池雁》等。发展到宋代,“分韵赋诗”成为士人交游的重要手段。笔者试图在宋前诗作与苏轼诗作中各取典范,通过考察文学史中的赋诗传统,呈现苏诗中“赋诗”与“此诗”的关系。
在宋前典范中,我们围绕“赋得”而拈出《古诗十九首》中的《涉江采芙蓉》,以及南朝、唐代的两种《赋得涉江采芙蓉》为例:
1.“此诗”——《涉江采芙蓉》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3]9
2.“赋诗”——梁元帝萧绎《赋得涉江采芙蓉》
江风当夏清,桂楫逐流萦。初疑京兆剑,复似汉冠名。荷香风送远,莲影向根生。叶卷珠难溜,花舒红易倾。日暮凫舟满,归来度锦城。[4]1666
苏诗中的“赋诗”,以分韵赋诗为主,此类诗作多是作于酬唱情境之中,数量众多。本文撷取以《诗经·六月》中“元戎十乘,以先启行”为韵的一例:
1.“此诗”——《诗经·六月》截句
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织文鸟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启先行。[5]262
2.苏轼“赋诗”——《送范中济经略侍郎,分韵赋诗,以“元戎十乘,以先启行”为韵,轼得“先”字,且赠以枕杯四,马箠一》
梁李久乐祸,自焚岂非天。两鼠斗穴中,一胜亦偶然。谋初要百虑,善后乃万全。庙堂选世匠,范氏真多贤。仁风被宿麦,绿浪摇秦川。号令耸毛羽,先声落虚弦。我家天一方,去路城西偏。投竿困障日,卖剑行归田。赠君荆鱼杯,副以蜀马鞭。一醉可以起,毋令祖生先。[6]1165-1166
以上诗例中,萧绎的赋诗是赋得体,苏轼的赋诗则为分韵。萧绎《赋得涉江采芙蓉》虽是源于古诗的诗题,但其诗义与原诗有较大差异;苏轼等八人的分韵赋诗,固然是源于《诗经·六月》的诗句,但也只是用原诗中十个字作为韵脚而已,他们各自的诗作同样与原诗大有不同*相关诗作可参见《法书赞·元祐八诗贴》。。此外,《赋得涉江采芙蓉》的诗题延续到清代,乾隆皇帝及时任吏部尚书的汪由敦(1692-1758)作有《御制赋得涉江采芙蓉》和《恭和御制赋得涉江采芙蓉,得“江”字》。
从先秦时期的赋诗断章,到南朝的赋得体,再到苏轼等人的分韵赋诗,而直至乾隆君臣的赋诗唱和,以上所举的一系列诗作,较集中而有力地反映出文学史中“赋诗”意涵的嬗递。由这些典范诗作,可以做出初步判断:文学史发展到北宋中晚期,赋诗的确可以泛指诗歌创作,但也可以特指“赋诗断章”“赋得”“分韵”等。
二 苏轼诗文中的赋诗意涵
(一)断章取义与分韵赋诗
《苏轼诗集》中固然有为数众多的“分韵赋诗”的作品,但就具体语境看,《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所论的“赋诗”,却既不是赋得,也不属分韵。这令我们很难将赋诗与此二者中的任何一种做逻辑上的关联之论证。虽然如此,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据此断定苏轼所论的“赋诗”,就是泛指诗歌创作,而与宋前的赋诗传统毫无干系。一个典型的例子,如苏轼感慨曹操的“横槊赋诗”。
1.《诗经·子衿》截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来?[5]127
《诗经·鹿鸣》截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5]230
2.曹操《短歌行·其一》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7]446
3.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序言断章
建安置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8]600
4.苏轼《赤壁赋》断章
酾酒临江,横槊赋诗,而今安在哉![9]6
5.苏轼《送钱承制赴广西路分都监》截句
踞床到处堪吹笛,横槊何人解赋诗。[6]1487
从《诗经·鹿鸣》《诗经·子衿》到曹操(155-220)《短歌行·其一》,再到元稹(779-831)《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而直至苏轼(1037-1101)《赤壁赋》《送钱承制赴广西路分都监》,所引的一系列材料,凝聚着从《诗经》到苏轼的漫长历史阶段中“赋诗”意涵的嬗变进程。
《短歌行·其一》是曹操根据乐府古题的创作,属于拟古之作,在此种意义上,我们尚不可将其归入先秦的“赋诗断章”的传统。但曹诗中所化用的《诗经》典故又的确体现且符合朱自清所论的“赋诗言志”“断章取义”的先秦赋诗标准。曹操的用典方式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使节所惯常使用的“赋诗”的外交手段如出一辙,遂被元稹视为“赋诗”。南宋施元之(1102-?)在《注苏诗》(即后世所谓“施注苏诗”)中,又将苏轼诗句“横槊何人解赋诗”的出处归于元稹的论述,遂形成了一条“赋诗”意涵衍变的线索。在这一线索链条中,赋诗意涵在唐人元稹的论述中呈现出较明显的转变:严格地说,作为乐府之一种,《短歌行·其一》虽引用了《诗经·子衿》《诗经·鹿鸣》的语典,但也不意味着它就不是曹操自己的创作了。实际上,曹诗虽也有其政治目的,但与朱自清所考论的先秦时期作为外交手段的赋诗相比,曹操又有其不同的语境。元稹之所以将《短歌行·其一》视作曹操的赋诗,实是抓住了朱自清所论的先秦赋诗的核心——断章取义和诗言志——认为他的创作符合赋诗的两个核心标准。
元稹将曹操的这种有新意地借用《诗经》旧典而言己志的创作方式视为赋诗,与苏轼诗论中的“用事当以故为新”(《书柳子厚诗二首·其二》),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但苏轼的“用事当以故为新”更侧重于论述诗歌创作的用典应在诗学传统中生发新意,毕竟没有直接地将此论与“赋诗断章”关联起来。实际上,翻检苏轼的诗论、文论,少见有直接论述“赋诗”的,同时,翻检其《诗集》《文集》,发现除了前文所引述的“横槊赋诗”外,更多的是他在与同僚、好友燕饮聚会时“分韵赋诗”式的创作。“分韵赋诗”只是用原诗特定的几个字为韵,诗句的具体意义本就与原诗章句无干,则此时的“赋诗”当然就可以不“必此诗”了,也正因如此,分韵赋诗就不以作品是否能跳脱出原诗为价值判断标准,也就与苏轼所论曹操的赋诗见出差异。
据以上材料和相关分析,可以做出进一步判断:第一,苏轼的诗歌创作是自觉不自觉地处于诗学赋诗传统之中的;第二,苏轼所论的“赋诗”至少有“用事当以故为新”之义;第三,就现有材料看,《书鄢陵王主簿》中的“赋诗”,与“分韵赋诗”并无干系。
(二)赋《诗》必此诗
前文已述:首先,赋诗虽是诗歌创作的方式之一,却不完全等同于作诗;其次,苏轼的赋诗多属不以新诗、原诗关系为价值判断标准的“分韵赋诗”。根据前文所引的材料及相关分析而做出的判断,虽然尚不足以确定《书鄢陵王主簿》中“赋诗”之意涵,但是,从《书鄢陵王主簿》的语境和诗义看,当我们将“赋诗必此诗”解作“赋《诗》必此诗”时,即将赋诗解作先秦“断章取义”之义时,却恰能展现出“赋诗”与“此诗”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苏轼诗论、文论及其诗文作品虽少有涉及赋《诗》的,但在其《易传》中找到了直截了当的论述:
“大畜”“小畜”皆取于“畜”而已,“大过”“小过”皆取于“过”而已,不复论其大小也。故《序卦》之论易,或直取其名而不本其卦者多矣,若赋诗断章然,不可以一理求也。[10]149-150
此段材料源于《东坡易传·序卦传》。《序卦传》是对六十四卦排序因由的说明,其中就有大畜卦、小畜卦、大过卦、小过卦。《序卦传》述说此四种卦象的方式,苏轼认为是“直取其名而不本其卦”,并将此种《序卦传》所呈现的方式比作诗学传统中的“赋诗断章”。应注意到,苏轼此处运用了类比的修辞手法。在这一修辞中,“赋诗断章”是喻体,“直取其名而不本其卦”是本体。类比修辞的目的在于用喻体的显著特征去说明本体的问题,这一目的从根本上要求喻体必须是人们耳熟能详,且熟知其义的,否则修辞失去意义。
由此可以判定:北宋中晚期的读书人对于“赋诗断章”的先秦诗学传统是熟悉的。这意味着我们虽然尚难以确然地说苏轼诗画关系所论的“赋诗”就是指先秦诗学传统,但不容置疑的是,这种诗学传统在宋代仍有留存。
苏辙《祭亡婿文逸民文》截句:女有烈志,留鞠诸孤。赋诗《柏舟》,至死不渝。[11]1384
可以确定的是,苏辙笔下的“赋诗《柏舟》”,是以《诗经·柏舟》为原诗而赋《诗》,而他的赋《诗》,正是先秦赋诗传统仍流传、应用于北宋中晚期的有力证据,而此时的赋诗已然摒弃其政治目的。因这篇祭文是为已亡故的女婿而作,笔者认为,此处的《柏舟》应不是指《邶风·柏舟》,而是指向《鄘风·柏舟》。
《鄘风·柏舟》截句: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5]64
《鄘风·柏舟》描述女子以其强烈的措辞而向母亲表达维护自身爱情的决心。应该注意到,在《柏舟》的描述中,既未明白指出,也未暗中隐喻女子所爱之人的亡故情节。苏辙活用《柏舟》典故,将女子“之死矢靡它”的决心写于祭文之中,代女儿向已故女婿表明心迹,并明确地将这一创作形式称为赋《诗》,这实际上与曹操《短歌行》的创作方式并无二致,既符合苏轼所论的“赋诗断章”,也符合朱自清所论的“赋诗言志”和“断章取义”的判断标准。
综上可知:第一,苏轼所论的“赋诗”,确有作诗之义;第二,自先秦以降,“赋诗”意涵呈现出较复杂的发展演变进程,在宋前已经历过“赋诗言志”“赋得”“分韵赋诗”等多种义项和体式;第三,在宋代,在苏轼诗文中,“赋诗”除泛指作诗之外,至少还包括“分韵赋诗”和“赋诗断章”等多种情况*苏诗中的“赋诗”,除指创作诗歌、“分韵赋诗”和“赋诗断章”外,在一些情况下也有和诗之义。因此义既无益于且无碍于本文论述,故只以注的形式略作说明。此义典型的例子,如《书石芝诗后》的记述:“中山教授马君者,文登人也,盖尝得石芝食之,故作此诗。同赋一篇,目昏不能多书,令小儿执笔,独题此数字。”,而无论是哪种义项和体式,宋代的“赋诗”总体上是要求在相应的限定中进行诗歌创作。
由此三点而得出的结论是:仅将苏诗《书鄢陵王主簿》中的“赋诗”单纯地理解为诗歌创作,现在看来是草率的。有意味的是,若将“赋诗”解作先秦“断章取义”的赋《诗》,却也存在逻辑上的矛盾:第一重矛盾在于,若那些能够依据《诗经》诗句“断章取义”而“言志”的作者才是“诗人”,那么春秋时期的外交使节也就大都可以被称作是诗人了,但这是不成立的;第二重矛盾在于,自《诗经》之后,宋前文学史中留存有大量的跳脱出诗三百的作品,如《楚辞》,如乐府,虽然这些诗篇的作者都不以赋《诗》为创作方式,但他们也都是确信无疑的诗人。这些矛盾都使“定知非诗人”中“诗人”的意涵,成为另一个必须论述的关键概念。
三 “诗人”意涵辨析
(一)苏轼诗文作品中的“诗人”
与古人不同,由于知识结构和受教育方式等因素的影响,现代人领会“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的诗义时,往往不假思索地将“赋诗”理解为诗歌创作,并将“诗人”理解为创作诗歌的人。前文已述,“赋诗”不必指向诗歌创作,实际上,“诗人”也不必指创作诗歌的人。考察《苏轼文集》发现,“诗人”在一些语境中也特指那些作《诗》的人,即那些早已湮没于历史长河中的《诗经》的作者:
1.昔者仲尼删《诗》于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圣王,至于幽、厉失道之际,而下讫于陈灵。自诗人以来,至于仲尼之世,盖已数百年矣。[9]59
2.《诗》有“騋牝三千”,美其富不讥其僭,不害其为诗也。夫千乘之积,虽然七万五千人,而有羡卒处其半也。故三万者,公徒而已。鲁襄公之十一年,初作三军,僖公之世,未至于三万。愚又疑夫诗人张而大之也。[9]222
3.七月流火,纪令节于诗人。[9]697
4.此诗人所以赋彤管,而史氏所以传烈女也。[9]1088
5.杜子美在困穷之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9]1515
《苏轼文集》多有指向作《诗》的人之义项的“诗人”,篇幅所限,此处不再列举。需要强调的是,作《诗》的人这一义项决非苏轼处“诗人”的全部意涵,这一概念在更多的情况下,仍是指称作诗的人,相关诗文作品不再一一标举。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轼的一些作品中,此两种义项时有混用的情况,这一点在其《评诗人写物》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诗人有写物之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林逋《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决非桃李诗。皮日休《白莲》诗云:“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决非红莲诗。此乃写物之功。[9]2143
这一材料从诗学中的“体物”传统出发,论述诗人对物象的描摹,其中,创作“桑之未落,其叶沃若”(《诗经·氓》)的人,显然是指称作《诗》的人;其余如林逋、皮日休等,显然是指称作诗的人。应意识到,此例中苏轼所举三种诗歌创作方式,严格地说,都属于源自《诗经》赋、比、兴三种创作方式中的赋。综合起来看,苏轼所论的“诗人”,首先,在不同的语境中,其意涵包容蕴藉,有多重可能性;其次,诗人应掌握和具备“写物”的方法和能力,这种方法和能力,源自于《诗经》以降的体物传统,而这种传统直接指向《诗经》六义中“赋”的创作方式。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如何判定“定知非诗人”中“诗人”的意涵?此处的关要在于,若将“赋诗”解作赋《诗》,则不可以将“诗人”理解为作《诗》的人,因赋《诗》必是《诗经》成书之后的事情,而作《诗》的人绝无可能通过赋《诗》去达到言志之目的。但是,若将“赋诗”理解为创作诗歌,则再一次陷入“作诗必此诗”的逻辑冲突中,而无法确定当下所作之诗与“此诗”之间的关系。为解决这一难点,接下来的论述将在更为广阔的文学史视界中探讨“诗人”的意涵,目的在于确定北宋这一历史时期中为人所广泛认可和接受的诗人的标准。
(二)文学史中的“诗人”
在文学史发展进程中,“诗人”的称谓最初仅特指作《诗》的人,如《楚辞·九辩》所论的“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又如司马迁所论的“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史记·周本纪》)。“汉初的诗歌是续《楚辞》的”[12]80,与“诗人”相对应,从先秦而至于汉代的其他诗歌创作者被称为“骚人”“辞人”,加上“诗人”,此三者虽都指称诗歌的创作者,但它们又各有所指,不可混淆。西汉扬雄对此有明确论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南朝刘勰沿用扬雄论调:“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人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文心雕龙·辨骚》)。可知,至晚到南朝,“诗人”仍以其所特指的意涵,而有别于如屈原等为代表的“辞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诗人”的意涵是随着诗歌概念的拓展而拓展的。
通过对网络数据库和图书馆相关书籍的查阅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等指导性文件的研读,掌握研究设计的理论与方法,为构建竞赛教学模式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撑,为实验研究的测试指标提供准确的依据。
在今人看来,《离骚》无疑属于诗歌,但在古人处却不是如此。汉代以降,随着五言诗的逐步发展,诗歌的概念被进一步拓展,“诗人”的意涵终于冲破了《诗经》藩篱,而逐渐开始泛指作诗的人。钟嵘《诗品》有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描述,学者已有详尽论述,此处不赘。[13]150唐宋以来,泛指作诗的人得到广泛认同和接受,白居易、元稹、欧阳修、苏轼等著名诗人诗作中,以及宋代诗话的论述中都对此多有体现,此处不再展开。[14]87-93
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以诗取士”成为唐宋时选拔官员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北宋,特别是在庆历新政之后至王安石熙宁变法之前,时人在应考时,甚至有“但以诗赋进退,不考文论”和“专业诗赋以取科第”之论。*北宋科举科目更迭繁复,从“初,……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贴论语十贴,对墨义十条”,到“时范仲淹知参政,……试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再到“神宗始罢诸科,而以经义、诗赋取士,其后遵行,未之有改”,再到王安石所论的“策论为有用,而诗赋为无益”,间之以神宗时期苏轼所论的“昔祖宗之朝,崇尚辞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由这一历史进程可知,所谓“以诗取士”也并非是贯穿北宋的固定不变之科考政策。由此,北宋科场程试诗的价值判断标准也就为本文提供了苏轼所处的历史时期,由官方主导,且为时人接受的评判“诗人”的权威性标准。
学者认为,“宋代‘以诗取士’逐渐趋于程式化,主考官从贴题、韵律、对仗、用典几方面审视应试者的诗文”[15]32。《中国诗学大辞典》指出,程试诗是“按一定程式所作的应试诗”,并依据和经由司马光《温公续诗话》中的“科场程试诗,国初以来,难得佳者”的论断指出,随着宋代科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分韵、限韵、拈题、赋得之类”被纳入考试范畴而作为应试诗,被统称为程试诗。[16]2166据此可知,宋代官方主导下的科考程试诗,要求应试者在分韵、限韵、拈题、赋得等程式范畴之内进行诗歌创作,而此四种程式,除“限韵”*“限韵”,指唐以降的科考程试诗将诗韵限定在某一个韵部或某几个韵字之中。外,都与前文论述的宋代“赋诗”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金人王若虚在解读苏轼所论时,即将此二者关联起来,云:“命题而赋诗,不必此诗”。[17]8-9也就是说,应试者的诗作,在很大程度上要在前文所述的宋代“赋诗”的相应限定*此处所谓“相应的限定”,即指前文所述的韵部、诗题、章句等宋人赋诗的限定。在这一意义上讲,程试诗中的限韵,与宋人赋诗的一些限定有通同之处。之中进行诗歌创作。这意味着那些不合于“赋诗”限定的应试者,就会相应地被代表朝廷的考官归入“非诗人”之属。
四 超越限定的诗画一律
前文考察诗学传统时,发现自先秦以降,赋诗大概分为四种情形:第一种,依据《诗经》章句而进行再创作,如苏辙的“赋诗《柏舟》”,又如曹操的横槊赋诗;第二种,依据《诗经》中的文辞为韵而进行再创作;第三种,依据前人诗题而进行再创作,如两种《赋得涉江采芙蓉》;第四种,因事而赋诗,如庾信《赋得荷》等。此四种赋诗虽各有所指,但它们也有较明显通同之处,即诗人必被某种既定要求所限制,有学者将此义概括为“命题赋诗”[18]97。由此可以说,无论《书鄢陵王主簿》诗中的“赋诗”指向哪一种情形,诗人被既定要求所限,这一最基本的意涵是决计不会改变的。这样一来,我们终于可以断然地将“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解作“在某种既定要求中进行诗歌创作,而被此要求所限制住了的人,一定不是诗人”,反过来,苏轼其实表述的是:在某种限定中进行诗歌创作,而不拘于且能超脱出限制的人,就是诗人。在苏轼诗画关系论点中,这种限制明确地指向以下两条:
1.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9]2210
2.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也。[9]2109
赋诗对用韵的限定,实质上是从“法度”层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诗人的自由;对诗题、诗句的限定,则是在用典方面极大地限制了诗人的自由;苏轼认为,在此双重限定之下,还能够“寄妙理”“出新意”的人,当无愧于“诗人”的称谓。从这种意义上说,与赋《诗》之诗人相对应的辞人及其作品,典型者如司马相如的以“工为形似之言”为特质而被相应限定所拘束的作品,在苏轼看来,其文辞难免多有未尽之意,而其价值也就不可以与李杜相提并论。
苏轼以故为新的赋诗,是在限制中有所超越,绘画创作亦如是。所不同处在于,绘画主要是被具体的形象所限定。一方面,虽然苏轼画论有“常形常理”之论和“观物须审”之说,但他更在意的是绘画能否呈现出内蕴于常形之中的,如《庄子》“天下马”般的“超逸绝尘”和“自然天真”[19]109;另一方面,虽然苏轼诗论有“诗人有写物之功”的论述,但他更注重的,是在继承前人典范的基础上,能“出新意”。通过深入发掘“赋诗”和“诗人”的种种义项,“诗画本一律”的意涵得以进一步展现:诗、画两种艺术门类共同遵循的规律,是既要遵循相应的限制,又要超越所限。在这种意义上,黄公望(1269-1354)题画诗《秋溪清咏》,便是本文论述的最好注脚:“万壑千岩拥翠螺,人家出处掩松萝。溪头静坐者谁子?赋就新诗拟《伐柯》。”[20]542
——论《贝多芬:阿多诺音乐哲学的遗稿断章》的未竞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