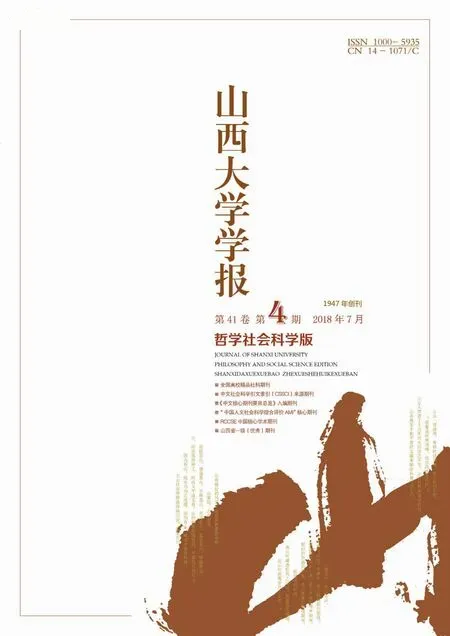永乐宫壁画艺术范式研究
——基于陆鸿年与庞薰琹之模写的讨论
曹 栋
(山西大学 美术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每一个有意愿返回传统,或者希望从古代作品中汲取美学精神的艺术工作者,当他面对古代艺术作品,试着去理解或接受,模仿或验证,说明或引述的时候,大都会经验到自己的艺术观念获得了某种验证,这种获得验证的经验使得他愿意相信自己对于传统艺术的信念真实可靠,相信基于自我经验的传统被给予的方式具有真理性。
在当代的永乐宫壁画艺术研究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美术学家们基于不同的言说方式推论,建构它的艺术特征,或技法色彩,或图式结构,或典型形象,或文化思想,或神话原型,或现代艺术观念等等,每一个视角都为人们揭示出一种含义,提供一种显像维度。可以说,每种诠释都有它的真理性,只要诠释者负责任地朝向壁画本身而使其在场呈现,他就具有了显露真理的资格。这正如古代艺术作品能够在知觉上被给予许多观看者一样,研究者也能够在许多面目下获得对它的理解与思考。
但是,多样的永乐宫壁画艺术特征的研究成果,并不能代替我们对其艺术“本有”的独一无二的追问,也不能满足当代中国美术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对于传统艺术范式之明见性的需要。永乐宫壁画所具有的超越多样性的同一性,并不是它所有艺术特征的总和,也不能用其中一种特征去囊括。正如尼采的格言:“只有一个人的话,总被认为是错的,真理始于两个以上的人,因为只有一个人不能证明自己是对的,而若是有两个人便已毋庸辩驳。”[1]143一个人的理解必定是有限的,传统艺术被给予任何一个观者的仅仅是一个显像,而我们相信同一性无法还原为任何一个孤立的显像,只有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完整解释,才能支持我们更接近正确的解释。因此,当诠释者执着于赋予永乐宫壁画以更新的解释的时候,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它的同一性,使其超出显像之维的同一性变得难以捉摸。
这种情况使我希望从多样性诠释的积淀物中挖掘它们的范畴结构;希望回到永乐宫壁画还没有被认定为经典的时刻,探寻其艺术特征原始分化过程中被确立并给予我们的东西。这一理解的诉求让我关注到了陆鸿年与庞熏琹,他们开启了永乐宫壁画艺术特征诠释之滥觞,陆鸿年是第一次永乐宫壁画临摹与复制工作的指导教师与带队者;庞熏琹最早将永乐宫壁画带入工艺美术与设计艺术教育领域,将其作为装饰基础课程的核心内容之一,进而融入关乎人民生活的艺术设计中,使之成为被广泛认知的文化事物。不可否认,他们的诠释已经成为我们当代继承下来的内容,其中关于永乐宫壁画艺术特征的范畴形态,以及他们与存在相互关涉的发生性结构,显现着他们返回传统的脚步;也包含着他们借以揭示永乐宫壁画明见性的艺术范式的想象。
一 陆鸿年与庞熏琹的艺术经历及理性生活
永乐宫壁画进入美术学界的视野,似乎是凭空而来,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在1952年的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永乐宫被发现,“在这以前它一直湮没无闻”。首先被关注到的是它的建筑,据当时文化部派遣的建筑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意见,认为它“是以表现宋、金、元时代的为统治者服务的建筑风格”。[2]直到1957年,国家兴建三门峡水库,处于工程淹没区的永乐宫需要整体搬移,文化部组织中央美术学院及华东分院的师生和民间艺人展开临摹复制工作,永乐宫的壁画艺术才进入学界的视野。这一临摹工作正好契合了当时美术领域“走出去”的潮流,聚焦民族民间艺术传统,整理洞窟、宫观、墓葬艺术,临摹古代工匠制作的壁画,希望以此为依托,建构新的符合劳动人民审美文化的传统艺术之维。在这一思潮影响下,永乐宫壁画临摹复制工作引起了美术界的高度重视,在随后数年间,永乐宫壁画的临摹复制作品被频繁展出,1959年在中央美术学院[3];1960年在故宫文华殿[4];1963年赴日本展出,并被故宫博物院永久保存。与此同时,相关图像资料及研究文章也陆续登载于各种期刊之上,并迅速被转化为教学范本,进入新中国的美术教育体系中,成为大众公认的民族艺术经典作品。
回顾这一事件,我们看到了一个古代艺术作品进入当代,并成为具有当代意义的历史文本的过程。对于千里迢迢奔赴永乐宫,进行壁画临摹与研究的人们来说,永乐宫壁画显然是陌生的,这种陌生感不只是因为地理位置上的遥远,更因为文化上的异己。在经历了近现代一个多世纪的西学东渐之后,与永乐宫壁画相关的道教信仰、道家思想及其主导的生存方式,已经从社会的主流文化中消失殆尽,特别是在新中国十余年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艺术逐渐成为文化意识主导的艺术形态。在这样的诠释情境中,土生土长的永乐宫壁画艺术完全成了“他者”。可以说,从它跨越历史,进入美术学家视域的第一天起,就处于被排斥的、支离破碎的、不完整、无关联的处境中。美术界为之雀跃的不是发现了一个早已遗失的、可以拼接传统文化连续性的环节,而是发现了“劳动人民创造的艺术和精神财富”,一个不同于的传统文人士大夫系统的审美维度。
不只是一般考察队成员感到陌生,即便是负责带队的陆鸿年,他对永乐宫壁画也是陌生的。陆鸿年早年毕业于天主教辅仁大学艺术系,那是一所致力于天主教艺术本土化的学校,他师承陈缘督(受刚恒毅主教洗礼),遵从西方传统的透视画法原则,曾经创作了许多本土化的天主教圣像图,主张结合中国传统的工笔重彩技法,以通俗易懂亲近大众的艺术形式传播天主教的宗教观念。从他学生时期的作品《圣母圣婴像》及《耶稣圣心像》[5]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天主教思想的深刻领悟,执着于表现“受难之爱”的宗教情怀,满怀对实际生活艰辛的同情,背负爱之责任。在陆鸿年的视野里,古代的壁画艺术是有“用”的技法,他认为当代人物画要“推陈出新”,就有“对古代壁画的绘画风格、制作技术有深入研究的必要”。[6]
庞薰琹的学术背景与永乐宫壁画也没什么联系。1925-1930年间,他留学欧洲,那正是欧洲现代艺术激变的时代,野兽派、立体派已经成为经典,巴黎派、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正红火。[7]他着迷于现代主义艺术,回国后发起了决澜社运动,开启了现代主义艺术在中国传播之滥觞,弥漫于其个性情绪中的是现代主义式的“焦虑”。[8]74对于传统艺术,他基本上持“反”的态度,在《薰琹随笔》中,他引述了柏格森的话,“世间绝没有固定的事物……世间一切在流动着,我们自己也在流动着”,这显现出他对“流变之美”的领悟,反对“捉定一个固定的派别来表现流动的情感与思想”。[9]68他强调艺术的自我表现,更自由、更个性化,同时又极推崇中国自身的传统艺术思想,主张中西方艺术的融合,例如,他以情感的实在性解释谢赫的“气韵生动”,称“气韵是画家的情感,是画的生命力”。从巴黎到上海,从发起决澜社运动到主持创办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即便是后来,他的个人生活境遇发生变化,从激进的现代艺术实践转向服务于大众民生的设计艺术教育实践,他的艺术信念一直没变,始终保持着一种自我的精神性,一个“乌托邦”计划,“一种自觉的社会主义意识”[8]156;始终坚守着现代主义艺术家的自我。
陆鸿年与庞薰琹先后把目光投向永乐宫壁画。遥远和陌生感、贫乏的考古资料并没有阻碍他们言说自我的理解,相反,给了他们极大的阐释空间,允许他们更自由地生活在对过去和未来的想象中,不受限制地将属于回忆、记忆和思维的东西融入其中。另外,1958—1960年间正值“大跃进运动”的年代,面对这样一个处于明确的历史阶段的民族群体,陆鸿年与庞薰琹对创造“新美术”有着一种自觉的意愿,确信过往存在并一直延续着的艺术范式,需要被改良、革新或重构。这种不安分、不满于现状的冲动,因永乐宫壁画的出现而更加震撼人心,这无疑是一个富有巨大承载力的载体,允许诠释者悬置它的原生语境,而以激进的方式把自我的艺术信念投射其中。同时,诠释者对于“劳动人民创造的艺术和精神财富”的虔敬,又迫使他们有意识地拒斥自身已有的观念,从生活实际出发,去审视被抛入自己视域的永乐宫壁画,在朝向壁画本身的直接体验与先验自我的争执中探寻它的真理性。
临摹工作之前,陆鸿年撰写了《怎样用传统方法复制古代壁画》指导工作。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员,他对文本及语言层面的交流非常重视,复制工作完成后不久,即发表多篇论文,诸如《永乐宫壁画艺术》《临摹汉钟离读吕洞宾的一些体会》等,对永乐宫壁画艺术特征提出自己的见解,同时也将临摹的作品带到了美术界乃至大众的面前。庞薰琹在1962年完成了元代装饰绘画研究初稿(内容主要是介绍永乐宫壁画),并将其直接应用于当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装饰绘画教学中。
二 不同的模写方式——实体部分与要素两个层面提供了不同的显像之维
从陆鸿年与庞薰琹先前的理性生活和艺术成就来看,构成他们先验自我的内容与永乐宫壁画艺术之间的距离非常大,所以当他们面对永乐宫壁画的时候,其理性远不止于当下的观看与反映,还包括他们从时代的需要出发,立足于历史之一特定点借以确立自己责任的各种意向性。
这复杂的意向性在他们的模写中获得了充实。作为切身从事艺术实践活动的诠释者,他们具有不同于其他人的体验方式——模写。模写不是简单的复制或者摹仿,其中包含着作为诠释者的画家惯用的艺术手段,也包含着存在于其中的被投向他将经验的古代作品时所需要的各种意向性。“‘模’是以外在标准创作绘画为主要内涵,而‘写’则是以吐露、排除和移置内心情感为主要内涵。”[10]通过模写,诠释者将自己置身于不熟悉的古代作品中,与古代的同行们照面,重新经历了一次壁画的生成过程,使壁画中曾经存在的东西,重新成为现在存在。无论是用实在的工具模写,或在意识中调动作为画家经验的意向性进行模写,在模写过程中,诠释者都必然会面临恢复与弃置、本己与异己、敞开与遮蔽的判断,以此,在恢复壁画的实存的同时,将现实的观念带入其中。
陆鸿年的模写建立在严格的临摹复制基础上,因为要服务于永乐宫整体搬移工作,所以,必须尊重壁画遗存的当下的面貌状态,原封不动地复制,不能有丝毫的自由发挥,甚至是那些因时间久远而产生的色彩褪变、地仗剥落、水渍痕迹等等也都必须一丝不苟地复制下来。这种移画式的临摹方式,使得陆鸿年必须直接进入壁画的实体部分;把画面的每个实体部分作为新的整体,而不是整个画面的局部。
在陆鸿年的阐释文本中,这种着力于实在部分的理解表现为对壁画整体空间结构的忽略,同时,也表现在他对画面内容的观看的“肤浅”。他没有说出我或者任何别的观众所能看到的表象以外的其他东西。武将、真人、主像、玉女“有的对话,有的沉思,有的在倾听,有的在注视”;“每个人的不同性别、年龄、性格、动态、表情”,他赞叹古代画家“创造了多种类型的面部造型,而且刻画出不同的典型性格”[11],显然,陆鸿年只言说他看到的表象,至于表象背后的象征、隐喻,以及宗教的意味却丝毫没有触及。
这种基于实体部分的模写形成了一些明显依据个人经验辨识获得的见解,例如,他在手稿中确切地提到这样一个认知:(那些沥粉贴金的器皿)“和16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的油画‘戴金盔的人’表达金盔的质感异曲同工。”[12]这显然是从自我理解中演变出来的东西,希望在永乐宫壁画中发现类似西方写实绘画特征,把自己经验中已经知道或者希望看到的东西带到了壁画呈现的现场。事实上,壁画中器物所呈现的逼真的视觉效果,只是由于金箔氧化不均,加之年代久远,尘埃蒙翳所致,并不是古人刻意为之。非常明显,永乐宫壁画与伦勃朗的油画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信念世界的基础。或许,陆鸿年本人也意识到这样的演变太过牵强,在后来正式刊发的文章中,删去了这段文字,但是,它还是被流传到美术院校的教学中,成为学生们关注到的永乐宫壁画的一个显像。
在我看来,陆鸿年的这一演变是一次冒险而非返回,是为迎合现实主义艺术范式而做出的表达,它隶属于历史的、文化的甚至是个人的视角,虽然触动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但这种见解无论如何不能被验证为“普遍的”。
与陆鸿年的临摹不同,庞薰琹并没有直接参与壁画的临摹复制工作,在此期间,也没有资料显示他曾亲赴永乐宫考察,他对永乐宫壁画的最初认识来自陆鸿年等人的临摹作品。虽然复制的图像与原作一样都是具体的,而且,陆鸿年等人的临摹复制几乎完全遵从了原作的当下面貌,不存在刻意的变动或模糊,但是,这种观看影像的行为与直接临摹的知觉行为还是有差别的。对于陆鸿年来说,画面中每一个形象都是一个具体被经验之物;对于庞熏琹来着,不同视点获得的图像、色彩、线条联系融汇在一起,才是画面的整体,“方位”、“结构”、“构图”、“整体”这些要素需要在壁画表面空间中延展才能持存。因此,庞熏琹看重构思的价值,强调用联系的、融合的视域,相互衬托中充实壁画的含义。他“提醒人们注意整体与细节的关系。”指出“三清殿东山墙和西山墙壁画的构图,采用了‘层叠式的结构’。南北朝时期龙门宾阳洞浮雕《帝后礼佛图》,采用了同样的构图结构。”[13]86
在分析蓝袍太乙的造型时,他说:“在三清殿西山的壁画上,在‘白玉龟台九灵太真金母元君’座左,一个玉女双手捧着博山炉,向金母元君走来。在玉女身后,一个穿天蓝色袍的‘太乙’,双手平举手板,手板就是朝见时用的笏,平举手板,表示他有事奏禀报。”“一根纯白色的细带,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条细带上,于是这块蓝色面积也就不显得太大了。”“没有这些描写,没有这样那样的衬托,单单一个蓝袍太乙,起不了什么作用”。 另外,我们注意到,他特意引用了一句俗语,“牡丹虽好,全靠绿叶扶助。”并且在描述壁画的过程中,反复十余次使用“衬托”一词,诸如“衣领的纯白色,为了衬托出脸部,袖头上的纯白色,为了衬托出博山炉,腰间一小点纯白色,是为了与衣领衣袖上的白色相互呼应。”“加上这个太乙的动作,人们当然更加注意金母元君了。玉女手捧博山炉,是为太乙引进奏禀,所以这个动作既衬托出金母元君,同时也衬托出兰袍太乙。”[13]87这些反复使用的“衬托”让壁画的形式结构在我们眼前逐渐趋于完整。
三 理解的冲突源于对于壁画意义来源的不同判断
经过上述考察,我们发现陆鸿年与庞熏琹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模写方式,一种是直接描绘看到或经验到的人物形象,直观到他们的表情动作,在其中辨识与自我相像的心灵和体现。另一种路线则是间接地,通过共同面对的壁画中的要素获得经验,在看到壁画的一部分的时候,意识到另外一个部分也存在着,在内在时间的意识中获得对壁画整体性的领悟。
这两条基于各自经验的道路,在两人的诠释中出现了对立与冲突。冲突集中表现在对纯阳殿壁画的评价上,陆鸿年认为纯阳殿壁画的艺术水准很高,极为推崇,并着重临摹了其中“纯阳帝君仙游显化之图”的“钟离权渡吕洞宾”[14]一部,还特意写了一篇文章,细致入微地把临摹过程中的体会记录下来。相反,在庞薰琹看来,“纯阳殿壁画的气质则比较软弱”;“表现手法比较平凡”;缺乏“整体的装饰效果”;“受到题材的限制太大,所以画面上显得顾此失彼,舒展不开”。[13]89
显然,由于视角上的差异,诠释者从壁画中经验的显像不同。陆鸿年对壁画的经验是在自然态度中实行的,他一笔一画地临摹复制,经验到画面人物的顾盼有情,那些如实际生活般的真实,让他找到了自己熟悉的“爱”、人物的情感以及对生活实景的模拟。在临摹“钟离权渡吕洞宾”一部时,更是变现出了情感的世界,他写道:“钟离身体前倾,袒胸露腹,姿态潇洒自然,性格豪爽,脸上充满了健谈的神情和说服对方的信心。”吕洞宾则“拱手危坐,敬听老师的教导,俯首沉思,目光凝视,内心充满激烈的斗争。左手大指轻捻右衣袖,这一小动作更有力地衬托出他思想深处的矛盾”。在他看来,作品的成功在于“使两个人(钟离权、吕洞宾)活现于墙头,达到传神阿堵的妙境扣人心弦,使观众徘徊不能离去。”[14]他的诠释中充满了劳动人民情感与生活情趣,唤醒了壁画的存在感,使其中的某些情感化的东西做出反应。这种直接进入实在部分的视角,使得他对壁画的理解充满新鲜感,似乎总在试图招引出新的、与当下实际生活相关的东西,比如,他“从实际生活中领会衣纹的转折与内部肢体运动的关系”;感觉到“勾画的金鼎似乎可以敲打出声音。而荷花瓣表现了含朝露的质感,画人物须眉则根根见肉,勾衣带则飞舞当风。”[11]
从陆鸿年的诠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努力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范式靠拢,弃置原有的宗教信念。不过,这并没有遮蔽先验自我的实存。比如,在壁画中,蛇的形象极不显眼,如果不是被特别提及,一般人不会注意,但是陆鸿年却特意关注到“蛇画的真实生动,蛇与神的情绪与情调一致”[11],这不得不让我联想到陆鸿年早年的宗教画经验。因为,在天主教绘画中,蛇的形象有着明确的文化属性与象征意义“作为生物的蛇被定位为不洁净之物,作为宗教器物的蛇则被赋予了神性的光辉。”[15]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十余年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思想的教化,陆鸿年已经完成了新的自我的认定,从宗教情节转向了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关怀。虽然先前的经验还是引导他注意到了“蛇”,但是,他这时已经弃置了其中属于宗教内容的象征意味,而只保留了“真实生动”“情绪与情调”的直观感受。1953年陆鸿年被评选为北京市先进文艺工作者,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他弃置了象征性的宗教绘画观念,而向现实主义绘画这种已经成形的既定的权力靠拢。
可以说,陆鸿年在摒弃掉宗教信念的同时,也把永乐宫壁画生成年代相关的文化信息悬置了起来。以壁画客观实在的再现作为理解的源头,把“家庭生活情况”“乡村旅店的景象”“贫富悬殊的社会生活”[11]作为壁画内容的主要含义,这让人们看到了相似的生活世界;辨识到了相似的情感体验,也让他的诠释不是站在外部的旁观与见证;不是单向的朝向壁画投射理性的射线;而是具有揭示本真意义的明见性。
对于陆鸿年关注的蛇,庞薰琹并不在意它的表情,而是从空间形式的角度予以阐释,指出“玄武是用蛇身缠在龟的背腹部,蛇头对着龟头的形象来代表的”,“是北方之神,也代表冬天,用白色来表现”。“东扇面墙外侧墙面‘南极’”“西扇面墙外侧墙面‘东极’”“东山墙上画两个主神”“西山墙上也是一男一女两个”[13]88,由此,他联系到“五代时期敦煌窟内四角装饰的四大天王,实际上也是方位神。”通过还原形象在壁画空间中的状态,恢复空间的完整性,引导观者在意识中构造一个完整的象征意象。结合他在1960年10月关于汉代时期的装饰画的言论,“在一幅作品上,装饰性强不强,要根据几个方面来看,首先看它的构图。装饰画的构图不仅是画面上的安排问题,也不仅是要表现它的题材内容,而是要看它有没有装饰效果,是不是和周围环境相适应,同时又能使自己突出。”[13]127其中可以看出,庞薰琹对壁画的诠释是紧接在画面实在内容之后的,他让人们认识到壁画的世界需要重新被构造、激活,而不是仅仅把局部实在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意义来源。这样看来,他称赞壁画中“每一个人物的脸部描写,都是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特点反映出我国的装饰画绘制者对观众、对工作的高度负责。”[13]86并把表现“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事”看作装饰画发展方面的突破。这些言语显然只是为了融入当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诠释语境所采用的修辞技巧,他真正关注并提请大家注意的是古代工匠为了传达其观念而刻意谋划的形式。
另外,庞熏琹不只是以自己认知到的形式示人,更将把壁画拉回到历史的结构中,以此谋求一种“有历史依据的理解”。他把永乐宫壁画置于《历代装饰画讲义》的序列中,并试图把已经遗失了的神话、历史重新归还其中。在谈论永乐宫壁画之前,他首先提及道教关于“孔丘见李耳”的典故,“‘鸟我知其能飞,鱼我知其能游,兽我知其能走。至于龙,我不能知其风云而上天,今见老子,其犹龙乎。’”[13]85这段文字似乎是在隐喻他对永乐宫道教壁画的琢磨不透,以及揭示被壁画所描绘的世俗表象隐藏起来的“真理”的艰难。同时,他追溯了汉代以来道教对装饰画的影响,甚至不厌其烦地考证壁画中各个神袛的全名,比如:“‘东极’,全名是‘东极青华太乙救苦天尊’”、“西山墙上,也是一男一女两个,男的是‘东华土相木公清童道君’,女的是‘白玉龟台九灵太真金母元君’”。以此,把永乐宫壁画重新置于历史的结构中,充实其内容的含义,使其获得更新的明见性,而一种新的关于永乐宫壁画有效转化的艺术范式也随之呈现出来。
四 “力”与“气”的范畴结构推动壁画含义向意义转度
根据陆鸿年与庞熏琹在模写中呈现的显像之维来看,他们两人执持着两种不同的意向性,两种不同的认定,我们似乎无法将他们对永乐宫壁画艺术特征的判断建立同一个经验的共相基础之上。但是,在进一步的解读中,我们发现,这两种由局部的解释引发的冲突,在他们各自返回整体性,并对于壁画经验进行反思的过程中,被整合了起来,而某种同一性的东西也暴露在他们构造的艺术范式中。
陆鸿年从实在部分进入壁画的模写中,他似乎开始与画中的人物交谈,按照人物的表情理解他们的意思;通过人物的肢体语言揣测他们的情绪,并且把这些事态进一步转变成壁画的含义,在一丝不苟地模写中检验到其中的真实性。在这个自我移置的实践过程中,他的视角逐渐从壁画的实在部分转度到要素,关注到了构造形象所使用的线条。这些线条是古代画匠遗留在壁画中的痕迹,当陆鸿年以模写的方式,重演壁画从无到有的过程时,线条生成时所凭借的身体的力道与情绪的变化便显现出来,本己与异己身体之间的相似性被唤醒,“这种相似性是通过在这两者之间直接被构造的相合性而形成的:一方面是被感知的外部空间形态,另一方面是以动感方式被感知的本己身体的运动。”[16]286因此,这些旁人看来普通的或者个性化的线条,在负责任地模写的画家眼里,却包含着可以被普遍感知的实在性,它们与人物形象的情态一样真实,可以通过与自我体验的相似性予以辨识,从而具有了跨越时间的可理解性。由此,陆鸿年在线条的模写中体验到了“力”的存在,他说:“三清殿壁画在衣纹用笔方面,从唐代细密和宋代的顿挫,而变为圆浑,沉着而有力”。[11]他在文章中也多次使用“力”来表达自己对壁画要素的感受,比如“转折有力”“勾勒有力”“简练有力”,把壁画的表现力归功于用笔与线条的有力,由此,使得壁画中线条的含义变得充实起来,不只是构造实在形象的一个要素,更是具有了揭示壁画整体意义的功能性。
与陆鸿年体验到的“力”的范畴结构不同,庞薰琹透过壁画构造出来的是“气”。在他的言说中,“气”首先指的是人物动态的气势,例如,在谈到壁画的“层叠式结构”时,他指出“由于站得有前有后,每行不是很整齐,这样好像显得人数很多,气势宏伟”。进一步来说,指的是画面的整体气氛,他指出,“为了使画面能表现出严肃的气氛,同时也要想办法使画面不至于显得死板,所以每幅画的前边都画一个武将”。这里所说的“气”的前两层概念——气势与气氛,我们可以通过与相关事物的联结与同构在意向性活动中获得,也可以通过画面实在的结构明见,但是,庞熏琹最终指向的是“气质”,却不是从自然的态度中可以获得的。所谓“风格不同,气质也不同,三清殿壁画的气质厚实,而纯阳殿壁画的气质则比较软弱。”[13]86显然这个层次的“气”无法在命题性反思中明见,而需要在想象中被给予,正如庞熏琹所主张的“形在意里,意在形外”[17],气质是形外之意,是超越多样性实在的范畴结构。不同于他对气势与气氛的规定,“气质”既是对我们能在壁画实在部分经验到的东西的统一,又是激起反思的质料。从实在层面来说,当我们跟随他的脚步,在画面上巡视,一个又一个实在部分相继显现有退隐到幽暗中,一个又一个要素在眼前明晰又相继落回到模糊状态,在这有序显现的显像之间,存在着间隙,这些间隙是“空”并不被意向性活动所凸显,但是,它却唤醒了我们的想象,让我们可以把自我的体验与前后相继的连贯性的事物相联系,继而进入诠释的情境中,将壁画的意义带到澄明之境。
可以说,陆鸿年与庞熏琹在永乐宫壁画中推演出来的“力”与“气”,这两个范畴都是在知觉经验上建立的。虽然“力”的范畴更接近于自然的态度,而“气”的范畴则需要在意向性的反思中显现,这种渐次更新与深化的理解也与两人前后相继的模写相对应,但是,关于永乐宫壁画的“气”与“力”的范畴构造使超然的想象与哲思成为可能,也使观者借此可以回溯到一个更具奠基意义的生命感的普遍性上。
五 结 语
通过一层层地揭示陆鸿年与庞熏琹朝向永乐宫壁画的模写、诠释与想象,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经历了一个从表象知觉到意义反思的理解过程。面对被抛入自己视域的永乐宫壁画,他们将自我的本真体验带上前来,真诚地朝向壁画,并将自己习惯的绘画语言引入其中,重演壁画的生成过程。陆鸿年以壁画为生活的世界,在实在的写实层面予以转化;庞熏琹以壁画为形式的世界,在要素的形式层面予以转化。无论从哪个局部理解,他们都将自我本真的生存与壁画思想的意义整体联结在一起,这使得他们的诠释不再是相互矛盾的杂多,而具有了揭示壁画本有之同一性的能力。
对于今天的传承者来说,陆鸿年与庞熏琹在对永乐宫壁画艺术诠释中最初确立并给予我们的东西,已经成为我们先验自我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他们的诠释已经成为我们理解永乐宫壁画的前提,即使随着时代的流变,他们揭示的显像被重新退回到模糊状态,但是,他们在其中增加了的东西,依然是我们不得不关注的对象。同时,陆鸿年与庞熏琹在永乐宫壁画艺术模写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思想与实践的交涉,也提示我们,在传统艺术之传承过程中,要让传统艺术本有之真理进入澄明之境,就必须努力回归同一状态,在艺术思想与忘我实践的融会贯通中,揭示传统艺术所本有的同一性。这是我们在理解自身艺术传统过程中,必须坚持并不应被改变的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