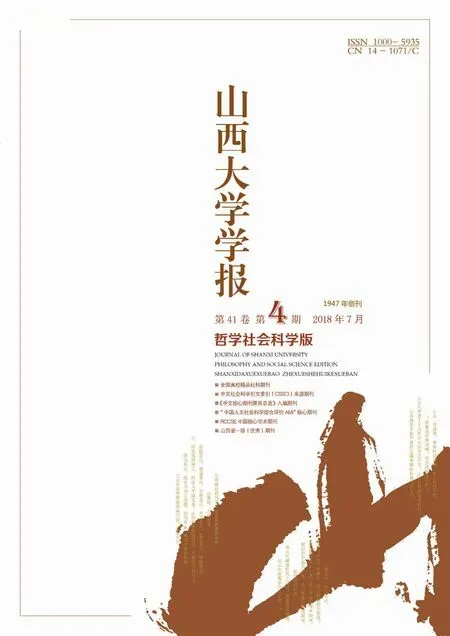庄子审美之“游”与中国艺术精神
梁晓萍
(山西大学 哲学社会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游”是中国古代艺术理论领域中存在场域比较广泛,理论统摄功能比较强大的一个范式,从“游”范畴视角切入来探讨中国艺术精神的命题中有两个核心词,其一是“中国艺术精神”,其二是审美之“游”。中国艺术精神的自觉始于先秦,而将其视为一个研究对象,对中国艺术精神进行理论研究却已至20世纪初。倘以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1]为比较早的中国艺术精神研究的个案,则宗白华为最早提出“中国艺术精神”的学人[2]。此外,20世纪上半叶,钱穆、方东美等一批学人都在其文章中提及“中国艺术精神”*钱穆在研究“比兴”问题时说:“中国文化精神,则最富于艺术精神,最富于人生艺术之修养。”[3]。不过,真正把“中国艺术精神”作为一个问题,挖掘中华文化之精神,实现重建人文精神之目标的则是唐君毅,其意欲在中西方文化比较的大视域中凸显中国艺术精神。然而,唐氏仅偏重于儒家之游,却忽略了道家之游的重要维度;其后,徐复观兼论儒、道两家之游,并采用分而论之的方法,高扬了道家之游之于中国艺术精神的重要作用,然而却有机械地以中国画代表中国艺术之典型(忽视文学等其他艺术)、以偏概全的嫌疑,又因其忽略了个体内心的生命体验,而未能全面理解中国艺术精神。因此,通过庄子审美之“游”来审视中国艺术精神,考察审美之“游”的形成及其主要在哪些维度影响了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它在当下又能带给人们怎样的启示便有了研究的必要。
一 “游”之历:审美之游的形成
以“游”范畴为切入点来理解中国艺术精神,首要的任务便是理解“游”的内涵及其演变,理解审美之游如何建构而成、又如何可能等问题。许慎《说文解字》释曰:“游,旌旗之旒也。”段玉裁注曰:“旗之游如水之流,故得称流也。”又“引申为出游、嬉游。俗作游。”[4]旌旗所垂之旒,即旌旗上梳齿状条带装饰物,其随风摆动之状如同水依势而流之状,均有自然而然的情貌,给人以自由自在的感受,故而被引申为游戏之游。然所垂之旒还不仅有装饰之意,因其属于旗帜的重要部分,故有着更为庄重严肃和神圣的内涵。旗帜至迟于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主要通过颜色、图案等的不同以区别氏族[5],表达崇拜,凝聚人心,协调行动,分旗杆和布帛两部分,《列子·黄帝篇》中记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先驱,雕、鹖、鹰、鸢为旗帜,此以力使禽兽也”[6],其中的诸种动物极有可能便是各氏族的图腾崇拜之物。以存在方式看,旗帜有固定之旗和行动之旗之分,前者寄托了古人对于世界的体认,是古人“立中”之世界观的具体显现*古“中”字即为旗帜。张法认为,古代氏族常将房屋聚集于一个圆形场域,中间留下一处立杆之地,这种地上统一的“中”,应该与原始人对天上恒显区的体认有关。立于中央空地上的杆,用来观察天象和测影,恒定不变的东西是天上的北极和地上的标杆。以所立之中为基点,观察范围就是整个天体宇宙,于是就产生了中国人最初的整体宇宙观。[7],因之具有一定的神性。后者将这种神性移动起来,成为原始人精神的象征物,在采集活动或战争中发挥着区别族类、统摄人心的作用。至周代,旗帜上的“旒”又与礼联系了起来,成为一种明示身份的象征物,以数目的多少代表着主人的地位与等级:“龙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鸟旟七斿,以象鹑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龟蛇旐四斿,以象营室也。”[8]斿,同“旒”,唐人孔颖达释曰:“族之旗旒皆仿其星”[8]544,如此,自远古至周代,“旒”(游、斿)便成为人与星、人与天、人与神、人与礼之间的一种连接物,并以其独特的神性内涵和现实指向,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精神。
在通向审美之“游”的过程中,儒家之“游”率先登场,其最为突出的贡献是解除了套在“游”身上的神性束缚,使其从浓抹重彩的原始图腾崇拜过渡为现实人生的道德指向和人格塑造。《论语》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朱熹释“游于艺”曰:“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缺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物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9],并对该句该章进行了详解。依朱熹之解可知,其一,就“游于艺”自身的内容而言,“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并非仅指乐,“游”指对包括乐在内的“六艺”等诸种技艺的一种掌握与游历;其二,从与道、德、仁关系的角度讲,艺为方法与手段,道、德、仁则为目的与保障,彼此之间有本末之分,先后之序;其三,何以有此“分”与“序”?从深层原因的角度讲,志道可以使心存正不斜,据德可以使道得而不失,依仁可以节制物欲,使其被堵塞在通道之外;其四,从“游”的功效角度讲,游可以使人“忽不自知”而“入于圣贤之域”,具有安顿身心的功效,王阳明所谓“调习此心”*王阳明对此有过精彩的比喻:“只‘志道’一句,便含下面数句功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于道’是念念要去择地鸠材,经营成个区宅。‘据德’却是经画已成,有付据矣;‘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区宅内,更不离去;‘游艺’却是加些画采,美此区宅。艺者,义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诵诗、读书、弹琴、习射之类,皆所以调习此心,使之熟于道也。苟不知‘志道’而‘游艺’,却如无状小子,不先去置造区宅,只管要去买画挂做门面,不知将挂在何处?”[10]之作用也。较之后人对孔子此语的一些过度阐释,我认为朱熹之解更为切合孔子原意。孔子所面对的是春秋末年周天子的权威被一再挑战与解构的“礼崩乐坏”的现实情景,因此,“乐”的存在是为“仁”政的实施,也正因此,儒家之“道”乃一切之本,“游于艺”是儒家仁学体系的一个部分,一方面,它不同于原始之游的神性指向,将这种有着放松身心之可能的“游”从部落联盟的旗帜上拉回人间,直切人身,从而为中国艺术精神的审美建构提供了可能,也为中国艺术精神的真正形成奠定了非常丰富的“原始的物质实践”的基础*李泽厚指出:“对物质技能的掌握,包含着对自然合规律性的了解和运用。对技能的熟练掌握,是产生自由感的基础。所谓‘游于艺’的‘游’正是突出了这种掌握中的自由感。”[11];另一方面,此“游”最终意旨依然是道德与政治,其中所能够体验到的自由感在本质上并没有脱离实用的目的,尽管其可以成为古代士人精神退守的一条途径,但其本身还不能被解释为超越现实功利性的审美情感,仅仅是一种不自觉的艺术精神。
真正从游于艺而至游于心,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精神,从而具备了自身调节与转换功能的是庄子的逍遥游。庄子之“游”是通往“道”以及体“道”的凭借,《庄子》一书,内篇七篇,篇篇有“游”:“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逍遥游》),“游乎四海之外”(《齐物论》),“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养生主》),“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人世间》),“游心乎德之和”、“游于形骸之内”(《德充符》),“游乎天地之一气”(《大宗师》),“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垠之野”[12] 28、98、116、146、171、176、227、251(《应帝王》);其他诸篇,也多次提到“游”。与儒家之游相比,庄子之“游”有如下特点:首先,庄子之游是游于“心”的无待之“游”。在孔子“游于艺”的路径规划中,礼、乐是其通向“仁”政的凭借,“人而不仁”,礼乐不过王阳明笔下想撑门面却无处安身的挂画,这是因为孔子的游是有待之游,其欲驰骋的精神总是被现实的功利拖拽而回;而庄子却直接悬置肢体,放逐形骸,凸显“心”(精神)的重要作用;放弃自我,驱逐功名,高扬超功利的无待之游。《庄子》中的至人、神人、圣人都是在经历了“不知”到“充实”,再到放弃偏私、舍弃功名的“无”,在有待中完成了升华与简化,从而抵达无己、无名、无功的无待之境,最终抛舍形器而抵达心之愉悦与精神之自由,此为庄子之游之主体的特征。其二,庄子之游是齐于物也顺应“物”又合于“道”的自然而然之游。庄子之游没有偏执的我见,不给自己戴上权威的帽子,不把自己规定为制定标准的一方,也不给自己与物之间人为地设置界线鸿沟,“乘天地之正”,顺应天地的自然之性,如同庖丁解牛,所见无非全牛,合于桑林之舞,恰中经首之会,无物与心的隔阂,亦无手与心的距离,无牛无我,无拘无束,无往而不可。又如同五柳先生与南山,各自随心而在,却又不期然而遇,任情适性,自由逍遥,此为庄子之游在主客关系方面的特征。其三,庄子之游是连接生命与关切现实生存之游。庄子确然反对有待之游,但并不等于其不关心现实人生,相反,庄子无待之游的思想恰恰源于庄子对现实人生的思考,是其安顿个体生命的积极探索,正如闻一多指出的那样,庄子之游是离家远行的游客眺望故乡与寻找精神家园的一种沉思,因其能够充分发挥人的精神作用,从而能够实现对现实人生的超越,故而具有了审美的特质,此为庄子之游在现实功能方面的特征。以上几点,体现了庄子之游既澡雪精神,无所依待,又自然而然,关切生命的整体性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在多个维度启迪和塑造了中国的艺术精神。
二 无待之游与中国艺术精神
从原始图腾的旗帜之“旒”至先秦儒家的“技艺之游”,再行进至庄子之“游”,“游”渐渐扩展与凝聚为一个既可指具体的山水之行,又可指无所待的精神之游,既可向外游乎昆仑,又可向内游于太虚的审美之游,并在多个维度开启了中国艺术的独特精神:庄子的无待之游开启了中国艺术精神的超功利性特征,其虚静坐忘的思想启迪了中国艺术家开阔的审美心胸,也为其打开了高远深邃的想象通道,从而架起了中国艺术家的山水之乐及其与自然之“道”之间的桥梁;庄子遵道顺物的齐物之游参与了中国艺术活动主体在心物关系方面的心灵建构,塑造了中国艺术家超越主客观对立的思维方式,并影响了中国艺术喜好自然的精神特质与价值取向;庄子之游还从审美之维完成了中国艺术关注生命与现实的特殊气质。
庄子的无待之游参与了中国艺术创造和审美主体的精神建构,使中国艺术活动主体成为追求超脱世俗羁绊,向往精神自由的一个群体,继而影响了其对于世界与人生的观察与思考。世间常为有待之游,此等“游”依赖于外物,为世俗的功名利禄所累,而庄子的无待之游却能反其道行之,主张个体突破形骸与世俗情感,突破时空,与万物相通;突破现实功用,看到无用之用;突破名利,追求精神的自由与充盈,“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做到无己,无功,无名。陶渊明躬耕南野,阮籍任诞风流,均为超脱牵系,追求精神自由的艺术人生实践。宋代苏轼见《庄子》,始得其心,他于《答秦太虚书》讲了自己“为仕宦所縻”,在天庆观斋居四十九天,调养自我的亲身经历,指出自己正是通过摆脱功名的羁绊与纠缠,才使心灵的和谐得以维持,从而恢复了精神的真正自由,也正是有此放达之胸怀,苏轼才成为进退有据的一代文豪。“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哨遍》),这就是一种无所待的艺术之境。
庄子的无待之游因其虚静、坐忘之追求而塑造了中国艺术家宽阔的审美心胸和自由的心灵状态。庄子的坐忘说承继老子的虚静理论,有虚有静亦有动[13],有坐忘亦有充实。庄子之游之主体自觉廓清自己的心灵,使其呈现为一种虚空状态,一无挂碍,无我亦无物,继而静静地体验与观照,以专注的精神完成心与物的交流,此为坐忘(虚与静)。坐忘的核心是去物去我。从去物的角度而言,庄子之游首先表现为将可导人利害的外物移出实用功利之辖,从而在审美距离中对其进行审美观照,受此影响,中国艺术家能够摒弃实用功利而审美地观照外物,能够不为物像所拘,视其为充满生命活力的自为对象,而非欲望之物;能够轻世俗而高蹈独步,将世界人生看作自由生命之聚集,而非御用之物;从而能够如庄子般回归内心,实现真正的精神自由。其次,庄子之游将物像从有限的时空中移出,关注其深邃永恒的美与哲理内蕴。中国艺术从不限定于具体的物象,而是力争使物象在艺术家心灵的感知与体悟中跃变为一个永恒的存在,高飞的大鹏,对面的南山,山间之清竹,水里之游鱼,在它们的身上,都凝聚着独特而恒久的审美意蕴。再次,庄子之游剥离物像的外在形态而寻求其内在的精神意旨。中国艺术家尽观世间山水,也模拟山水之态,然这些都为山水之精神而来,“神”而非形,才是艺术家走近山水的真正目的。郑板桥画竹,眼中之竹已非可食可用之物,而是烟光、日影、露气中美轮美奂的绝妙境界;亦非眼前之竹,而是转换了万种时空,辗转腾挪千次,变换出无数姿态的百变之竹;至胸中之竹则已成为艺术家想象中具有非凡精神气质的艺术形象了,如此才会有郑板桥笔下疏密有间、灵动无比的竹子。节节比高与虚空其心的竹子,使其成为一个从特定时空中超脱而出的永恒生命本体,成为不以色相迷乱神情,而以精神与审美主体相遇相知的一个象征物,这时,竹子还是竹子,却又不是原来的竹子,已然成为中国艺术活动中的一个具有审美特质的独特意象。
庄子的无待之游还包括“去我”的层面,它是坐忘的另一个维度,强调去除掉情感躁动的我,以安宁的眼神打量外界的物象;斩断欲望束缚的我,以无欲的心态面对审美对象;除掉被知识包裹的我,从习惯与僵化的自我中跳出,摒弃逻辑知识的执见,而对对象作纯然的审美观照;去除刻意为之的我,不处心积虑苦思冥想,而以恬淡之心体物与为文。中国艺术强调创作主体要“乘月反真”,强调如陶渊明般“遇”,而非“即”,强调“倘然适意”,“不作”而为,这些都是受庄子无待之游影响的具体体现。苏轼更是将庄子所开创的审美胸怀发挥至极致,苏轼论画,强调神与万物相交,成竹于胸,身与竹化。其评画曰:“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14]苏轼认为,要想胸中有丘壑,务必要心中先无一物,即抛弃掉自己的杂念与对外物的成见,做到离形去智,忘我忘物,方可有万象“扑”入胸中,方可抵达“胸有成竹”、“兔起鹘落”的境界。
庄子坐忘之游中物我交流的“我”又绝非被动之存在,它会主动畅想,在艺术世界中飞越遨游,不受时空的限制,无边无际,任意东西,充分享受自由精神带来的无限快感,此为虚静坐忘的又一成果:充实(动)。要之,虚空其心,涤荡精神,在无待中畅游世界人生,这种去物去我,在静中蓄势而动,在坐忘中展开想象的翅膀,遨游于宇宙的心灵历程成为中国艺术活动主体的重要精神特质。刘勰曰:“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正是由于精神聚集,心思专一,弃智弃我,方才思接千载之前,视通万里之外,从而抵达神游的自由境界,然而“寂然凝虑”绝非易事,情辞并茂更是难为,如何才能做到?其曰:“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15],这里的核心在于守静、致虚,在于坐忘,恰如刘永济所释,人心所忌在于俗,在于留情于庸鄙,摄志于物欲,于是灵机窒息而不通,天君昏而无见,当然便难以窥天巧而尽物之情了[15]303,唯有腾空内心,想象之窗才可真正打开,方可如医者治结疾,荡其宿垢,理其清虚,落笔时的“俚俗、庸腐、窒板、拘牵、隘小、肤冗种种结习”亦便可避免。南宋宗炳的“澄怀味象”,米友仁的“静室僧趺,忘怀万虑”,刘学箕的“心胸有尘俗之气”,“不若不画之为愈”,明李日华的“廓然无一物”,明吴宽的“胸次洒脱,中无障碍”,清人恽寿平的“澄怀观道,静以求之”,齐白石之“夫画道者,本寂寞之道”等思想,均为承继庄子无待之游的审美心胸。
三 齐物之游与中国艺术精神
庄子之游的齐物思想塑造和强化了中国艺术家超越主客对立的整一思维方式。庄子之游是建立在尊重物之“道”即物性基础上的齐物之游,讲究顺应物性,以物为量,这便与西方主客对立二分的思维不同。西方强调“我”的存在,外物不过“我”去接见与征服的对象。而庄子却主张“吾丧我”,要求摒弃掉那个因个人成见而徒有气焰的小我,排除掉我与物之间的隔阂,还原我之真心,放我于世界之中,在此基础上再去与物接触和对话,则物与我无异,而我亦可以游刃有余物我之间了。《庄子·达生》中,孔子曾观山水于吕梁,见一男子在鼋鼍鱼鳖都无法存在的激流中游泳,以为其寻死,让弟子去救他,发现其没水很久,游至对岸,披发吟歌,甚是自由。问其何故,答曰:“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即与漩涡一起没入,与涌流一起浮出,顺着水势身不由己,以性相合,一切自然而然。那此人又何以敢于游于漩涡呢?这是由于其“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12]565,常人眼中,此水高三十仞,有吞人之相,而之于该男子,则直抵其性,忽略水之外形,故能抛弃常人战战兢兢之心态,体验到物我相融的愉悦,这也就是庄周化蝶之境,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也就是苏轼的身与竹画,王国维的无我之境。
庄子齐物之游对于主客二分思维的超越为中国艺术家发现自然并寄情于山水提供了精神指引,为其体悟和弘扬山水之乐打通了精神关隘。美学意义上的山水之乐通常有两种,一种以山水比附道德,因其有治国安身所需之品格,故乐在其中;一种忘却功利之心,直视山水自身之美。前者兼容善的维度审视自然,强调的是自然之美的外在功利性,后者突出的才是自然本身,延展的是美和艺术的独立性,因而对美学更具有意义。孔子曾有过“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的感叹,然而其审美对象不是山水本身,而是蕴涵在山水中的伦理道德,指向的是“知者”、“仁者”如山水般的人格美,而庄子的审美观则是与之截然不同的自然审美观。在庄子看来,人与物同归于道,如果人能内心凝静,顺物运转,不伤于物,则物也将向人展示其独特的魅力,在此情景下,山林、原野向我绽放其美丽,我亦欣然而悦:“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12]677(《知北游》),这种物我同一思想指引下的山水之美就在于山水本身,在于其能够直抵人心、怡情悦性的本真之美,它使中国艺术家摆脱了诸种功利的束缚,摒弃了大人主义的立场,与自然零距离相视相拥,在忘我中欣赏自然之美,体验人生之乐。“置身空虚,谁为户庭。遇物自肖,设象自形。纵意恣肆,如尘冥冥”[16],艺术家在一片玄虚中化我为物,物我同一,以“林泉之心”体验山水,故体悟到自然山性即我之性,自然山情亦即我之情,这就是中国艺术所谓“化工”的至高精神境界。
齐物之游强调尊重物性,平等以待万物,在对于物的表现及艺术风格上强调自然而然,从而深刻影响了中国艺术追求自然之美的审美精神。“自然”一说源自《老子》(《老子》六十四章)[17],其意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指万物本其所是的一种存在状态。庄子承继其思想,并在人生哲学的维度有所发展,强调无论是个体的生命长度、人之禀性,还是治理天下,都要顺应自然本性,而不要人为地干预与强迫,如庖丁解牛,因其固然,依乎其理,以锋利之剖刀,行进于骨缝之间,使牛在甚微的动刀中如土委地;也正是庄子,使出现于老子那里的哲学思想普照人间,继而成为中国艺术非常重要的审美追求。《南史·颜延之传》曰:“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18]鲍照所推崇的谢灵运的“初发芙蓉”之美,正是自然天成的美。李白亦曾取此意来表明自己的审美取向。苏轼极爱自然,认为作文当“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如此,则可抵达“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陆游提倡妙手偶得的天成之文,曾言“琢雕自是文章病”(《读近人诗》)。毛宗岗论文,厌臆造之文,赞造物自然之文。李渔论曲,亦强调自然之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庄子之游是尊重生命的达生、赏生之游,它从审美之维塑造了中国艺术关注生命与现实的特殊气质。庄子之游的起点是人生与现实,在他看来,现实生活中充满了诸多冲突、斗争、杀戮与戕害,尤至战国时期,贪婪肆虐,野心泛滥,争夺频仍,格杀横行,在这一行进过程中,人类积累了不少机心与学说,而正是这些所谓的智慧,使人迷失了生存的方向,丢失了自己的生命故乡,因此,庄子如游子般思家,执着地眺望着自己的故乡*闻一多:“庄子的著述,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运用思想,与其说是寻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19],守护着人类的真实生命。由此可见,庄子之游所反对的以欲望和识见对待人生,正是基于生命本体与现实考虑的一种生命观,它对于中国艺术精神的启迪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使中国艺术注重活泼泼的生命书写,偏爱气韵生动、风骨、意境等展现生命活力的审美品格。譬如中国艺术对富有生命力的“韵”格外垂情,喜欢“韵”带给人们的节奏与律动之感:中国书法讲“神韵”,音乐讲“余韵”,绘画讲“气韵”,诗歌讲“韵外之致”,戏曲讲“韵味无穷”等,都是以艺术关注跳荡的生命。二是使中国艺术绝不仅仅停留于物的直观感受,更试图从物的背后探讨其对于人的生命启迪和现实安顿意义。中国艺术家对于静物并不感兴趣,透纳的《射击山鸟》中那只被猎枪打死的鸟在中国画中是不被理解的;而庄子中呆若木头的鸡也并非没有生命力,恰恰是蕴蓄了无穷的力量以等待对手的到来;中国艺术中也有关于瘦石清竹枯木等的书写,但体悟并彰显清瘦枯朽背后的生命力才是艺术家的真正目的,他们常常会越过感性对象的表象,追逐深层的生命启迪。三是与儒家思想一道,赋予中国艺术家以一种真诚的现实情怀。儒家以积极入世为世人所称道,与此相反,道家的现实情怀却常被人忽视。实际上,庄子之游乃因看到世间乱象而游,此游欲为个体生命寻求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引导人们超越现世处处受限的困境,这是一种赤子般的终极关怀,其对于现实不是不关注,恰恰是更为深刻的关注,“漆园之哀怨在天下”,“漆园之哀怨在万世”[20]。乐在山水之间、饮少辄醉的太守欧阳修,不仅在乎鸟儿之乐,宾客之乐,更以游人之乐为己之乐。
四 庄子审美之游的当代价值
源于老子哲学的庄子之游,以其对世界人生的诗性思考,在多个维度启示了中国艺术精神。庄子之游以无待之心游物,启迪中国艺术家以自己的真实生命契合于天,不诱于欲,不惑于智,使其能够畅神于世界,遨游于无际;在虚静之心的引领下,庄子之游一方面为中国艺术家的心胸扩容,另一方面也赋予其以非凡的想象力。庄子之游遵循“物物”之道,强调物我同一,人融于物,极力反对为自然立法的霸道思想,中国艺术中的“秋水精神”(平等精神)即源于此。庄子的齐物之游进一步强化了中国艺术家天人合一的学理思维,影响了中国艺术追求自然而然的审美取向。庄子之游与其哲学思想一道,都源于其对于人类文明的深刻思考,螳螂捕蝉,异鹊在后,异鹊捕螳螂,人的弹弓在后般的物类相互牵累,是其最为担忧的画面,它从生存和审美之维塑造了中国艺术关注生命与现实的特殊气质。
研究庄子之游对于中国艺术精神的建构,说到底仍是为了发掘其在当代强大的生命力和蓬勃的生长性,发扬其现代意义,为当代艺术的生产以及艺术家审美精神的保鲜提供必要的思想给养。
首先,庄子之游的审美方式对于当代艺术活动中即将滋生或已经滋生的诸种功利思想具有一定的防范和纠偏作用。中国当下的艺术活动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表现在艺术主体方面则为急功近利,忽略生活而追逐市场;或利用权威与名气,占据评判领地,进行艺术买卖。这种被功名利益绑架的艺术创作丢失了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由于眼睛瞄准的是市场,脑中思考的是金钱,心中琢磨的是如何迎合,因而只想快快生产,投向市场,多多宣传,名扬天下。然而我们知道,赛场上短、频、快的乒乓球技艺靠的是台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优秀的艺术作品需要扎根生活,入乎其内,认真观察,深刻体验,然后与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出乎其外,寻找恰切的艺术形式,准确地传递对于宇宙、社会与人生的思考,这是一段艰苦的过程。庄子审美之游中的非功利性追求对于当下艺术活动中这种急功近利的倾向无疑具有纠偏作用。
其次,庄子审美之游中的虚静、坐忘思想不仅有助于艺术家淡定心理的养成以及艺术心胸的扩容,也有助于当代艺术家内心的沉淀与功夫的修炼。当代社会,人们精神时间的长度不断缩减,朱光潜“慢慢走,欣赏啊”的提醒仅仅成为一种口号,就连假日的旅游也蜕变为一种快餐式的经历,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中,大众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去倾听,去体验,而是沉浸于日常的感官狂欢,使肉身性战胜了精神性,现实性屈服于虚拟性,在此情形中,不少艺术家也混入人群,追求肤浅的、粗糙的、临时的、匆忙的趣味。这种追求的结果是,艺术表面繁荣,形式眼花缭乱,艺术的精神含量却大打折扣。究其根源,在于艺术家不能虚静其心,庄子审美之游则引导人们放逐追赶,静心游于世界之水,如庖丁般专心致志,在《桑林》、《经首》之曲的聆听中完成艺术创作。
第三,庄子审美之游可以有效规避西方二元对立思维对于中国艺术精神的负面影响。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力度的不断加大,中国艺术活动,包括艺术创作、艺术理论、艺术鉴赏、艺术美学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尤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二元对立思维,与成就了西方先进科技的分析思维一道,对中国艺术精神形成了很大的冲击。这种思维尽管在某一阶段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急于发展的中国人的开拓精神,促进了美学学科在中国的接受与发展,也拓宽了中国艺术家的思维视域,但对于美学与艺术,却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的弊端,由于其将主观与客观、人与世界、内容与形式等生硬地分为对立的双方,“思戡天役物,申张人类的权力意志”[2]110,仅对事物作片面、孤立、抽象的研究,容易造成只顾一面、不见其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强调概念、忽略体验等偏颇,故而并不利于保存事物天然的多维联系从而全面把握事物的美,相反,庄子的审美之游遵循的是齐物思想,将人与物视为世界中共同存在的、别无分致的平等之物,故而能够以牛观牛,以物观物,在游目骋怀中观照世界律动的美,在世界的复杂之网中看清事物无限的美,并在具体表现上避免当下过于重视形式而忽略内容的不足,从而创造出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艺术作品。
总之,受庄子审美之游影响的中国艺术精神在全球化的时代不可或缺,它所提供的为人、做艺、体道统一的原则,将为涤荡艺术家的灵魂,提升艺术的品位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的积极参与也将有助于拓展世界艺术精神的内涵和维护世界艺术精神的生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