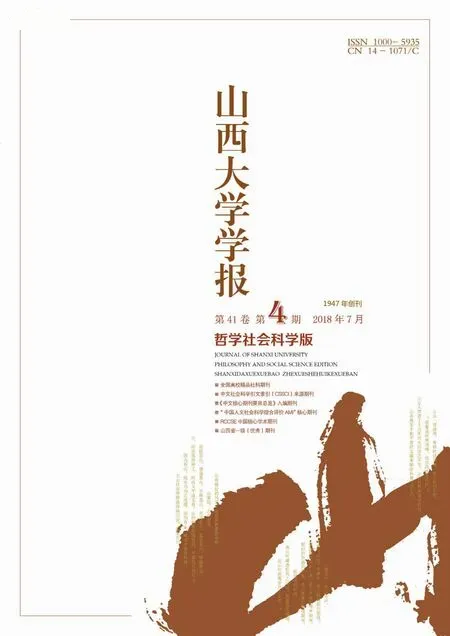教育、天才、文化和国家的使命①
——尼采《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解读
彭正梅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上海 200062)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由尼采1872年在巴塞尔所做的关于公共教育问题的五次公开讲演及两个前言构成,本应是他继《悲剧的诞生》之后的第二部书。在发表第五次讲演的前一天,尼采写信给出版商弗利施(Ernst Fritzsch),拟把计划中的六次系列讲演作为自己的第二部书,出版商也认可了他的提议。但几周以后,尼采又写信给出版商,声称自己要“花上几年时间”再对文稿进行修改,“使之更好一些”。尼采认为,“这些内容不够深入”,引起了读者的“干渴”,最后却没有提供“甘泉”。但这可能不是尼采的初衷。计划中的、但没有进行的第六或第七次讲演,也许会提供“甘泉”。尼采后来并未履行承诺去完善自己的教育报告。《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的纲要在1893/1894年出版,但严格说来仍然属于尼采遗稿。在最近几十年尼采教育学的国际讨论中,《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被视为尼采最重要的教育文献。它延续了《悲剧的诞生》的文化批判,把这种批判聚焦在教育之上,并由此形成了早期尼采关于自然、文化、天才、国家和教育之间关系的神秘学说,强调教育的最高任务在于孕育天才,但德国当时的教育机构又迫使天才从教育机构中离开。
一 自然的目的在于生产天才
尼采在自己的讲演中并未直接说出自己的观点,而是宣称他太年轻,没有经验,也没有智慧去谈论教育改革这个主题,因而只能重述他和他的朋友曾经碰巧偷听来的一场对话。这种对话性的讲演设计,显然是一种写作方式,同时也在暗示,讲演者与这些讲座观点、从而也与听众保持着某种自由的关系。
对话发生在夏末的夜半时分,莱茵河边远离尘嚣的、充满神话传说的高山密林之中。对话带有强烈的戏剧色彩,剧中有白发哲学家及其曾是中学教师的年轻弟子,两个渴求成长的理想主义的偷听者,一个被等待的老朋友,一条狗;剧情中有射击、尖叫、拥抱、狗咬、流星、点燃火炬的队伍,有轻柔的自然的音乐,也有黄钟大吕般的慷慨陈词和最为深沉的忧虑。
在这神秘的场景中,白发哲学家通过其弟子之口指出,真正的教育只存在于少数天才之中;真正的教育机构应该为这些极少数的天才而设。这是一个不能公开的自然的秘密,否则,就没有那么多人去接受和追求教育了。这种观点来自于尼采对古希腊的另一种解读,也体现了早期尼采典型的自然目的论的观念。
与温克尔曼、歌德和席勒不同,尼采认为希腊文化的伟大不在于他们所发现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而是在于充满嫉妒、暴力、野蛮和竞争的古风时期的文化。尼采从古风时期的希腊文化中,揭示出某种关于自然、天才、文化、国家和教育之间关系的秘密学说。这在《悲剧的诞生》中已有端倪,在《不合时宜的考察》中有所发展,但更为简明地体现在《希腊国家》和《荷马世界中的竞争》这两篇小文章之中。
尼采声称,自然通过产生天才来表现和观照自己;天才的使命是创作永恒的作品;永恒的作品构成了真正的文化;国家和教育机构的作用在于养育天才并保护天才完成自己的使命。因此,天才的任务就是能够让自然通过自己去表达自己,去创作能够支撑自己和人类的伟大作品。他们的作品像是生命的必要幻象引导着芸芸众生;像是遮蔽太阳直射的云层呵护着脆弱的生命。没有伟大作品的呵护,生命就无法抵御人生虚无的本相的侵袭,就会枯萎,无法存在。
一般而言,人性这个概念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分离,但尼采认为,这种分离实际上并不存在。自然的特性和人的特性往往是相互交织而生。伟大的天才如阿喀琉斯和亚历山大大帝,就是具有最伟大、最高贵能力之人,其本身就是自然,是自然的“黑夜之子”,因此,也具有自然那种可怕的本性,具有那种凶残、猛虎般的摧毁欲望。在尼采看来,这种通常被认为是可怕的、非人性的能力,就是肥沃的土壤,而且,唯有通过这种土壤,所有人性中的情感、行动和作品,才会发荣滋长。
因此,自然在产生天才方面,是采取残酷竞争的方式。尼采在《荷马世界中的竞争》中指出,希腊天才的生存和负罪具有同一性。猜忌、暴怒和妒忌的厄里斯女神,激发着人类采取行动、竞争性地相互厮杀。这不是人性的缺点,而是一种善意的神性的结果。一个希腊人越是伟大,越是崇高,他内心越会爆发出最好胜的火焰,就越会吞噬每一个与他在同一跑道奔跑之人。
但是,自然并不放任这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而是会产生保护性的国家。因为天才需要制度保护,才可以进行伟大行动和伟大创作。国家的目的就是把人聚拢到一起,通过奴隶的劳作,来为天才的工作创造条件。国家是自然的铁石心肠的客观化。国家把战败者及其妻儿、财产收归己有,把他们作为奴隶以及盲目的文化鼹鼠来为天才的工作服务。
尼采认为,希腊国家就是建立在暴掠、阴郁的狄奥尼索斯原则以及理性、明朗的阿波罗原则的稀有平衡之上;而且,从这种稀有的平衡中,会产生新的精神的金字塔。在这金字塔的顶端,天才通过自己的工作和作品,来创造伟大的文化,并借以实现自然的目的。因此,国家是自然的手段,因为没有国家这个铁夹子,自然就无法通过社会,进而通过天才的镜像来观照自己,在天才的作品即文化中展示自己。显然,按照这种逻辑,国家是天才的工具,亦是文化的工具。
那么,天才是如何工作的呢?通过自然固有的竞争。尼采认为,天赋必须在奋斗中发展起来,这不仅是希腊国家,同时也是希腊国民教育的建立原则。在尼采看来,只有竞争才会使人成为伟大的诗人、诡辩家和演说家。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竞争,天才才能创作自己伟大的作品,也就是创造文化。尼采指出,可以“把辉煌的文化比作血淋淋的胜利者,他在凯旋的队伍中把绑在战车上的战败者当作奴隶拖着走”。[1]768-769
因此,奴隶和奴性是一个国家的正常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的本质。因为它是竞争的必然结果。争斗及争斗教育也是城邦的福祉。尼采指出,如果把竞争从希腊生活中剔除,我们就会看到前荷马时期那可怕的野性的深渊。如果这种竞争逐渐停止,那么希腊城邦永恒的生命基础就会面临沉沦和崩塌。希腊国家的衰弱就是因为理性的明朗的阿波罗原则的过度扩展,压制甚至消除了残酷的竞争性的“狄奥尼索斯”精神。
现代国家把苏格拉底的平等原则作为政治理想灌输到社会中去,并表达为“无限制的乐观主义”、“相信所有尘世的幸福”。追求财产以及平等的乌托邦主义者以及他们更加蜕化的后代,还有每个时代的“自由党”的白人种族,并不尊重希腊天才的古典艺术,[1]767而是赞赏人的尊严、劳动的尊严这类幻象,并刺激奴隶去做出关于自身和自身之外的思索,用知识树的果实毁掉了奴隶本来的纯洁状态。
《希腊国家》赞颂了柏拉图关于国家和天才之间的秘密学说,强调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孕育和保存天才。“国家存在的固有目的就是天才的奥林匹克式的存在及其不断地重新地产生和准备。”[1]776尼采认为,希腊国家并不存在现代社会所谓的人的尊敬和劳动的尊严,而只有作为天才手段的尊严。每个人及其全部活动,只有在他有意无意地充当天才工具之时,才有尊严。
尼采对希腊文化的阐释带有某种达尔文主义色彩。不过,相比之下,尼采尽管也同意自然进化的意图,但他对于这种意图的理解带有更为明显的目的论色彩,而且他不太强调环境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天才的作用。
二 真正的教育机构在于孕育天才
按照尼采的理解,自然在于生产天才,天才的使命在于创造真正的文化,国家是天才的工具。因此,教育和教育机构的目的在于养育极为少数的天才。但德国的教育机构,特别是德国人文中学(Gymnasium)正遭受着深刻的危机。一种尽可能扩展教育的力量和一种尽可能削弱教育的力量,正在导致人文中学放弃沃尔夫(F. A. Wolf)和洪堡所确立的高贵使命,背离了聚焦古典课程和人性教化(Humanitä tsbildung)的理想,而去追求外在于教育的目的。
在第一种力量影响之下,教育被作为生存斗争的工具,变成了谋取成功、挣取面包的工具。这样,一种“教育=利益=快乐”的功利主义倾向,促进了教育的快速扩展,也促进了非形式化的教育进入到学校教育之中,以服务于非真正的文化和教育的目的。另一方面,社会各阶层对宗教压迫的记忆和恐惧,导致他们过度追求教育,以驱散其宗教本能。国家也利用大众教育作为手段来在国内扩展自己的影响、权力和控制,在国际上增加竞争优势。尼采认为,这就导致了原本属于天才的教育特权被民主化,教育被尽可能地拉平以适应普通大众。教育不再赋予特权和激发尊重;广泛的大众教育伤害了德意志民族在分娩和孕育天才的健康无知和天真本能。尼采认为,一个民族的健康沉睡,是一个民族分娩天才的心理前提。
在第二种力量的影响之下,德国人文中学放弃了其最高尚、最高贵和最崇高的养育天才、帮助天才创作伟大作品的使命,转而服务于生活的其他领域如国家,从而降低了智力和文化的标准。人文中学变成了培养公务人员和官员的官方机构,沦为国家的工具,导致天才被放逐、窒息和扼杀。
这种危机鲜明地体现在德国的教育机构如人文中学和大学之中。在尼采看来,德国的人文中学和大学不再是为了文化而教育,放弃了曾经是少数天才孕育之所的古典教化,并转而去培养律师、技术专家和政府官员,敌视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文化,从而沦为一种追求平等、功利、学术、个性和自由的教育机构。
人文中学的德语教学并未给予学生严格的训练,未能很好地教授德国经典作家以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作品,反而在德语作文中鼓励儿童个性的形成和自由人格,但他们在这个年龄恰恰需要严格的纪律约束和服从,需要保护去抵制非德意志的当代文化以及庸俗的报刊德语影响。对于当代德国的人文中学学生来说,希腊作为希腊已经死亡了,他们也喜欢荷马,但当代小说家斯皮尔哈根(Spielhagen)对他们的影响力更为强大。尼采指出,一个人如果不对报刊惯用的某些词汇和措辞感到生理上的恶心,那他就不配去追求真正的教育。
在大学层面,如果从对哲学的需要,对艺术的本能,从作为所有文化的绝对命令的古希腊罗马文化,来考察大学生的教育,同样令人感到失望。大学变成了追求为知识而知识的学术之地。康德在1798年的系科之争中曾把大学描述为专业知识生产的工厂,并认为这是不坏的做法。[2]到尼采做讲演的时代,德国研究型大学的知识分工已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但尼采认为,这种无聊的、没有生命关怀的、过分的学术知识,创造了现代性的弊端并使其永恒化。这种对于博学和历史研究的偏好,同样也存在于人文中学。尼采批判了这种乐观主义的历史文化,认为博学并不是真正文化的手段,也不是它的标志。知识是为了生命,为了教化,而不是相反。
按照尼采的理解,德国教育机构应该遵从自然的秘密,去养育极少数智力优异之人,使之能够完成其命定要完成的伟大作品。《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所追求的真正的教育是一种属于天才、为了天才的教育。这也体现在尼采讲演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即“Bildung”的理解上。
“Bildung”是德语中的一个很独特的词汇,其意义比较复杂,不仅有“教育”(education)和文化 (culture)义,而且还指一种教育和文化化的过程或产物;不仅是一种状态或目的,更是一种过程和手段,是指某种潜在的、内在的和尚未完成的东西变成现实的、外在的和确定的有机的自我创化、自我实现的过程。我国译界多把“Bildung”译为“教化”,而将教化的结果即自我创化的结果“Gebildete Menschen”译为“有教养者”。席勒在《德意志的伟大》(Deutsche Gröβe)中认为,“Bildung”是德国文化意识形态的核心元素,意思是它与某种内在性、灵魂的深度和高贵有关,而其他民族只活在生活的表面。
尼采在自己的讲演中更多使用的是“教化”这一概念,而较少使用德语中另一个“教育”概念即“Erziehung”(相当于英语中的Education)。实际上,尼采对这两个概念是有所区分的,讲演中的“迈向教化的教育”(Erziehung zur Bildung)的短语也显示了这种区分。在他看来,“教育”指向个体教育的早期阶段或特定阶段,而“教化”则是一个终身持续的过程。教化与教育有重叠的时期,但总体而言,教化是教育的目的。天才的教化之路,就是其创作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之路。天才的教化就是文化的生成。尼采讲演中所指的“教育机构”,其德语是“Bildungsanstalt”,即一种教化之所,是一种对天才的教化和生成的一种保护性养育所(Anstalt),而不是中文的“教育机构”,也不是英文“educational institutions”。尼采在讲演中提及服务于功利和国家目的的教育使得学校变成了教育机构,而非天才的养育之所。
在尼采看来,真正的为了少数人的教育,恰恰是一种最为严格的教育。而德国当时的教育太过自由,没有把学生置于天才导师的严酷的王权之下,因而需要一种铁锤的教育,使之迈向教化之路。所有的教育都开始于顺从、服从、纪律和臣服。因为这里存在着一种自然的精神的等级秩序。
按照这个秩序原则建立起来的教育机构,才是真正的教育机构,即教化机构,一种为了少数天才的教化的机构。但尼采所言的天才,生活在众人或民族中间,因此,我们必须教育所有儿童,这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少数天才。那些不能跟上步伐的儿童,会在追求教育的过程中掉落下来,从而会自然形成一种精神的金字塔。
实际上,当时的俾斯麦德国并非那么民主化,其人文中学也并没有促使德国社会比英国或法国更加民主化。当时的德国社会甚至抱怨,强调希腊文化学习的人文中学,并未为德国的民主做准备,连德国的皇帝也在抱怨德国人文中学在“培养希腊人,而不是德国人”。被尼采认为是过度扩展的德国人文中学仍然是精英学校,很多保守主义者仍然把人文中学视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尽管如此,尼采仍在讲演中攻击人文中学太多民主了,未能很好地服务于自然所意图的极少数天才,违背了自然的目的论。而自然的目的论不仅在于少数天才,更在于少数天才的教化结果即文化。
尼采坚定地认为,当时号称的德国文化并不是真正的德意志文化。那些自称为“我们就是顶峰,我们就是文化”的德意志当代文化,是一种伪德意志文化。这种伪德意志文化如记者文化和新闻主义等严重侵蚀着德国的教育机构。在当时的一些保守主义者包括尼采眼中,德国报纸特别是报纸副刊(feuilleton)是冒着泡沫的法国激情饮料,去除了所有学科的思考,把内容置于形式之下,强奸和贬低了理智,并把理智变为妓女。尼采担心,这种堕落、欺骗和非德意志的形式会主导德国文化,败坏德国青年学生。尼采甚至认为,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的世界观的根源就是在于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这种世界观是非日耳曼的、完全是罗马的浅薄哲学,必须抵制和反对其在德国的扩展。[3]46
因此,人文中学必须把学生置于保护性的玻璃罩之内,使其严格地学习经典作家和古代作品,形成高贵的品位,从而能对流行的风格产生直觉上的生理反应,即恶心。
显然,从养育天才和天才创造德意志文化这个角度来说,德国都不存在真正的教育机构。尼采心目中的一个真正的教育机构就是被德国政府视为威胁并加以镇压的早期兄弟会。
但是,这个真正的教育机构恰恰遭受了国家和政府的镇压。而按照尼采的理解,国家应该成为真正的教育机构的提供者,应该成为天才和天才创作的庇护者和支持者,而不是谋杀者,应该像希腊国家那样喊出“若动我的孩子,请从我的尸体上踏过”。
尼采认为,普鲁士国家把自己作为最高原则或被颂扬为最高原则,威胁到了真正的教育机构,威胁到了真正的德国文化,而在根本上威胁到了天才的教育和自我教化。由于德国社会的麻木漠然和对抗力量,德意志天才的代表如克莱斯特、荷尔德林、莱辛、温克尔曼和席勒,过早地凋落或被扼杀。
尼采叹惋道,如果存在真正的教育机构,那么,这些德意志天才也许会逃脱当代德国“文化”的毁伤性的忽视、误解和敌意。如果在一种强有力的保护性的教育机构之下,那么谁能想象,这些英雄的男子汉们会取得什么样的成绩;而没有这一保护性的温暖的故乡,德意志天才就不可能展翅作其永恒的飞翔,他们就会像被放逐在冬日荒原的异乡人,过早地、悲惨地从其贫瘠的故土蹒跚离去。
但是,到哪去寻找这一温暖的故乡,从而使得德意志天才能够创作其永恒的作品,创造真正的德意志文化。
三 建立天才共和国
尼采坚信,存在着一种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的独特的德国文化,一种具有统一风格的德国文化,尽管这种文化目前还并不存在。
尼采孜孜以求的高贵的德意志文化的理想原型就是古风时期的希腊文化。这也是尼采《悲剧的诞生》中所不断表明的。他预言这种悲剧精神会在当代德国得到重生。这种重生的标志就是叔本华的哲学和瓦格纳的戏剧。
尼采把以叔本华和瓦格纳为代表的文化称为德意志精神,这是他心目中另一个文化的理想原型。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把德意志精神界定为“一种壮丽的内在健康的古老的力量;诚然,这种力量只有在非同寻常的时刻才会强有力地发动一回,而后重又归于平静,梦想着下一次觉醒。”[4]167他所谓的德意志精神体现在路德、巴赫、席勒、贝多芬、歌德、瓦格纳、海涅、叔本华、莱辛、荷尔德林和温克尔曼等创造性天才身上。这些天才体现了德意志精神能够攀登的辉煌的高度。德意志精神就像神秘宝库,是德国教育和文化更新可以凭借的资源。
因此,古希腊和德意志精神可以作为标准去评价和谴责现存教育体制;还可以作为号召点去创造更伟大、更高贵的文化。尼采相信,德意志精神和希腊古风时代存在着密切、甚至神秘的亲缘性。德国文化可以从希腊天才那里的这种永恒的联盟中获益,并将继续获益。德国古典作家关于古希腊的创作已经成为德意志精神的一部分。而且,尼采认为,今天的德意志天才要想寻找古希腊,必须经过德国古典学家。没有他们的帮助,德意志天才难以振翅飞向希腊的魔山。德意志天才如果不挽起希腊天才之手,就难以完成创造真正的德意志文化的使命。只有在希腊天才和体现德意志精神的天才的引导下,德意志文化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故乡。
在尼采看来,天才就是文化的本质。尼采把真正的德意志精神与希腊文化的连接,理解为德意志天才与希腊天才的连接。这样一种连接,是文化的本质,也是自然的意图。在他看来,一个时代的高度并不在于大众,而是在于极少数伟大天才的作品。历史的进展就表现为少数天才的进展。后世在对历史进行观察和判断之时,也根本不再去观察大众如何吃饱、如何谋生以及如何幸福,而是观察那些伟大天才所构成的历史高峰,观察天才之间的对话、回应和竞争。
文化的本质是天才,反过来说,文化的本质也是奴隶制。尼采认为,强调平等和人的劳动尊严的现代文化,敌视真正的文化,敌视天才的工作,敌视天才的教育。但问题是,社会的不平等和奴隶制恰恰曾是希腊文化成就的前提,因为少数奥林匹斯的天才要创造艺术世界,必须存在为其提供服务之人。
但是,尼采并不是把天才与大众对立起来。相反,天才创作永恒的作品恰恰是为了生命,为了他自己和大众的生命的丰盈。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无限的求知冲动导致了希腊悲剧精神的消逝,斩断了艺术、民族、神话、风俗、悲剧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希腊人的特性的堕落和扭转,撕毁了笼罩在生命之上的保护性的神话气氛。生命需要某种遮蔽太阳直射的云层即幻象,才能繁荣丰盈。生命会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遭受来自太阳直射的暴晒而枯萎,从而堕入缺乏幻象的虚无主义。“要是没有神话,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失去自己那种健康的、创造性的自然力量。”[4]166因此,大众的价值在于充当天才的工具,而天才的价值在于通过创造性的生产,去创造新的神话,去提供新的生命视野,生产保护生命的大气云层。这些天才与过去的天才的创作,构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精神山脉,构成了早期尼采所谓的“天才共和国”。
这种天才共和国的观点,隐含在《悲剧的诞生》之中。尼采认为,现代性崇尚的是一种堕落美学,导致了衰退的德性和衰退的生命。只有希腊天才所创造的悲剧文化,才可以提供一种肯定生命的形而上学的安慰,才能让人在现象背后观照永恒生命的坚不可摧,才能给予那些觌见酒神音乐所揭示的自然的恐怖的大众以安慰,肯定生命的壮丽和欢乐。也就是说,唯有作为审美现象,此在与世界才是永恒合理的。天才的艺术活动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学活动,也是大众不可缺乏的必要的生命视野。尽管如此,尼采还是相信,“亚历山大文化需要有一个奴隶阶层,方能持久生存下去。”[4]132因此,《悲剧的诞生》所揭示的天才与大众之间权威性的关系,不仅构成了《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的教育论述的基础,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原则,是一种政治共同体的基础。
实际上,尼采在《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中同样是在要求建立一种基于他在希腊悲剧中发现的原则之上的政治体制。他相信,这一悲剧体制要求一种相应的教育,或者称为一种政治教育。对这个政体的参与,需要一种新的智力习惯和纪律约束,需要一种新的文化的统一性和风格性,因此,需要对其成员进行相应的智力和心理装备。
因此,早期尼采所青睐的天才共和国是一种审美的国家,其政治学是一种审美的政治学。尼采的理想国必须满足四个方面:第一,必须体现世界意志或生命之基的音乐特性;第二,必须是这一基础的健康表达,也就是说,在其机构和权力使用中表现出一种体现生命最高发展的统一风格,并与健康的本能相一致;第三,必须鼓励悲剧艺术家或者创作音乐的苏格拉底的创作;第四,不能迎合病态的本能。[5]尼采的政治学不是启蒙的政治学,不是理性探究或理性争论的产物,而是一种带有哲学分析的美学共和国,是音乐家苏格拉底的政治学。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不同,尼采的理想国是一种审美的国家,不是一种理性的国家。
艺术和生命的关系是早期尼采的政治思考之根。他从文化的视角来探讨政治问题。伟大的文化天才和审美天才通过其哲学和音乐活动所提供的生命视野,是其政治思考的根本。这样一种审美的理想国,显示了尼采的政治思考属于德国的浪漫主义传统。他把文化、政治、生命甚至民族统一等同起来。大众成为少数天才的仆人,少数天才的任务则是创造他们自己以及大众所需要的审美和哲学视野。
尼采在《希腊国家》中清晰地指出,国家作为天才的工具,必须建立天才得以创造真正的文化的教育机构。希腊人认识到,如果没有舒困救急的国家机构的保护和呵护,任何文化的萌芽不会得到发展,希腊无与伦比的文化,也不会如此兴盛繁荣。因此,国家不是文化的监管者、调节器和监护人,而是文化的强壮威武、准备并肩作战的同伴与同路人。[1]709国家的根本使命在于文化,这是尼采的政治观点。
但是,尼采并不是要求德国去复制希腊,复制那个曾经的健康的审美共同体,而是号召德国人不要沉溺于那种与生俱来的勤奋及博学,而是要带着悲剧精神去面对生命,寻求一种伟大的一致性的文化风格。尼采像黑格尔一样,认为时代的伟人就是能把其时代的意志转化为言语的人,并告诉他的时代这个意志是什么,并促使时代去完成它。天才所做的就是时代的核心和精华,他的行为体现他的时代。德意志天才的个人身上体现了民族的独特精神,但这种民族冲动根本上是一种自然的宇宙性的冲动:“一个民族的价值——一个人亦然——恰恰仅仅在于,它能够给自己的体验打上永恒的信念。亦即关于时间之相对性和关于生命之真实意义、即生命之形而上学意义的信念。”[4]169
德国的统一激发了尼采对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的向往,但是,他越来越发现新政府更加喜欢自吹自擂和骄傲自满,越来越变成一种对文化具有高度危险的力量。尽管国家和政治是必要的,但在尼采看来,最重要不是政治和国家,而是文化、艺术和天才。他并不赞成黑格尔把国家等同于“神圣意志”。把国家作为最高原则,作为社会中最重要的机构,会毁坏德意志精神。
普鲁士国家通过任命官方哲学家,来要求他们对国家效忠。但实际上,国家并不看重哲学和真理,而是害怕哲学和真理。官方哲学会把国家置于真理之上。在尼采看来,普鲁士对法国战争的胜利,是一场军事胜利,并不是德国文化战胜了法国文化。相反,这场胜利有可能伤害真正的德国文化和德意志天才。在历史上,希腊国家的最大不幸就是希波战争的胜利,因为这场胜利太大了,以至于战争的胜利变成了文化的灾难。
因此,尼采认为,普鲁士国家绝不是孕育天才、发展文化的天才共和国,也不存在真正的教育机构。普鲁士国家把最有天赋之人都吸引去当官,引诱每个人都产生从政的冲动,并把人文中学视为进身之阶的所在。国家自命为文化的引路人,强调所有的教育努力都必须从属于国家的目的。在国家即目的的逻辑之下,德国形成了两个教育队伍。第一个队伍人数众多,充满利益和光环;第二个队伍人数稀少,充满荆棘和坎坷。由于时髦的现代文化和国家的持续引诱,这些较低天赋之人被拖离了其真正轨道,疏离了其本能和本性,背离其服从和服务天才的使命。[1]729
那么,真正的教育机构,真正的天才共和国在哪里呢?在拜罗伊特。在《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结尾,尼采对这个天才共和国进行了想象:在一个天才的指挥下,一个原本沉闷平庸的乐队如何变成了引导者和被引导者之间的前定和谐的共同体。[1]751-752
这种共同体同时也是一种前定和谐的师生关系的共同体。尼采再次指出,“所有的教育开始于人们现在欢呼为学术自由的相反的东西,开始于顺从、服从、纪律、臣属和奴役般的服务精神。就像伟大的引导者需要被引导者一样,被引导者也需要引导者:这里主导的是一种相互倾慕的精神等级秩序,也就是一种前定和谐。……如果命定相遇的双方,也就是引导者和被引导者经过艰苦斗争,带着累累伤痕相聚之时,他们内心会燃起深刻的喜悦之情,就像一个永恒奏响着的竖琴的回声。”[1]750
因此,这里的天才指挥家既是悲剧哲学家,也是教化大师,也是政治家。在《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中,尼采探讨的不仅仅是教育、哲学和艺术的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他的理想的天才共和国是一种悲剧的共和国。在这种共和国里,教育、艺术、哲学和政治是统一的,具有一种鲜明的独特的风格。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强调教育和文化是最为优先和急迫的事情,优先于国家,优先于宗教,优先于愚蠢的世界;强调要与现代的野蛮做斗争,把人文中学变成战场。国家成为文化和教育的好友也不够,必须成为文化和教育的仆人。《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最后引用了席勒的革命性戏剧《强盗》以及革命的秘密协会即兄弟会。看来,天才共和国的建立,不仅需要一个天才指挥家,还需要有枪的年轻人。
四 结语:成为你自己的舞者?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这一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也体现了尼采的个人成长。我们甚至可以从作品推断,那个白发哲学家以及被等待但最终仍未出现的哲学家,就是尼采成长阶段中所出现的两个重要人物:瓦格纳和叔本华。但从这部作品里,我们很难完全理解尼采关于教育的见解,因为那个被等待的哲学家始终没有出现。尼采并未像其所承诺的那样,去完善这部作品,因此,在严格意义上,这是一部未完成之作。而且,由于其采取的是对话的形式,尼采对《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中的观念保持着某种距离。这个作品带有某种缺憾的神秘性和扑朔迷离。
尼采随后出版的《不合时宜的考察》曾几乎原封不动地使用了这五次讲演的两个段落。据此可以推测,《不合时宜的考察》中的部分内容可能就是尼采曾许诺要对《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进行修改的内容。我们从其思想的连续性上也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联系:《不合时宜的考察》的前两篇延续了《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中的文化批判,它借助批判大卫·施特劳斯来揭露合乎时宜的当代伪文化,借助批判过分的历史教化,来显示历史的科学化会伤害生命和民族;《不合时宜的考察》的后两篇把叔本华和瓦格纳作为时代的不合时宜的救赎者,则揭示了《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中被等待的哲学家朋友以及“乐队指挥”隐喻的身份及其伟大的特性及活动。因此,可以说,《悲剧的诞生》《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和《不合时宜的考察》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体现了早期尼采的文化关怀、教育关怀和政治关怀。
但是,我们不能把《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视为尼采稍前出版的《悲剧的诞生》的附属和稍后出版的《不合时宜的考察》的序曲。这部作品有其自身的重要地位,显示了尼采的一种教育转向,一种从《悲剧的诞生》的文化批判到《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的教育或教化关注的转向。它是一种对大众的劝谕,一种公开的呼吁,会让我们想起《圣经》里沙漠中的施洗者约翰不断地对众人说,“天国近了,悔改吧!”去迎接和服务于天才的诞生,去建立为了天才、从而也是有利于芸芸众生的教育制度和天才共和国。
如果说《悲剧的诞生》显示了尼采作为文化医生的诊断,那么,《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则是在揭示出病苦后,去寻求疗救的药方,其论证的逻辑就是天才的教育与真正的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认为,尼采此后的创作就是在寻求疗救,或者说,在往返于更深刻的诊断和疗救之间。因此,可以推论,讲演中白发哲学家所等待的朋友,在《不合时宜的考察》那里是作为教育大师的叔本华,而后来也许是作为教育者的查拉图斯特拉。他们都是孤寂的隐遁的教化天才,都“生活”在远离喧嚣的蓬莱山上,但他们都会下山行使教化职责,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关于尼采为什么没有去加工和出版《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有研究者认为,尼采发现自己的作品与当时拉加德(Paul de Lagarde)的观点类似,没有什么原创性而放弃出版。但德国当代尼采教育思想研究家尼迈尔(Niemeyer)认为,尼采后来因为与拉加德和瓦格纳保持距离,才决定不出版这些讲稿。[3]56-66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至少《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表现出了明显的瓦格纳的风格,甚至当时的尼采也认为自己应该全力服从和服务于瓦格纳这样的天才。这个作品显然是加入了尼采个人的教育经历。
不过,稍后的作品《人性的,太人性的》以及《偶像的黄昏》显示,尼采克服了瓦格纳和叔本华,走上了自己的教育道路。
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尼采仍然把叔本华和瓦格纳尊为教师,但他宣称他也同时洞悉他们难以治愈的缺点。对伟大的教育导师的信任和忠诚,是教育和成长的代价,是自我欺骗和自我保存的狡黠的必要行为。因为人无法忍受不存在如此伟大的精神或典范这样一个事实。
尼采发现,真正的导师是如此的稀有,以至于不能指望导师。学生不能只是学生,应该成为自己的教师。这个作品所等待的人物始终没有出现,也暗示学习者只有一条选择,就是自己教育自己,努力成为你自己。“成为你自己”“成为你自己的舞者”成为后期尼采教育哲学的新特点。
在1876年出版《瓦格纳在拜罗伊特》之后,尼采很少再谈“德意志精神”,对之前所崇敬的德意志天才,也展现出批判的态度。尼采在后来的作品中强调超人学说。他利用查拉图斯特拉之口指出,“我来把超人交给他们!人类是某种应当被克服的东西。……超人乃是大地的意义。让你们的意志说:超人是大地的意义!”[6]9-10相比于《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中严厉的教化大师,作为教育大师的查拉图斯特拉的教育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查拉图斯特拉鼓励学生去自我寻求,去寻求一种更高的自由,他甚至还通过舞蹈向他们演示这种自由的狂放境界,以鼓励学生通过“我应”的骆驼、“我要”的狮子和“我是”的小孩的三种精神变形,去过一种具有创造意义的本真的生活。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尼采所钟情的“权力意志”和“永恒回归”。权力意志就是超人意志,一种自我超越的意志,追求更多、更高和更强的意志。永恒回归是对权力意志的提醒,提醒那些致力于“成为你自己”之人,要每时每刻去追求这种权力意志,否则我们将难以忍受生命的永恒复归。毕竟,每一个不能舞蹈的时刻,都是对生命的浪费、辜负和否定。有意识地追求权力意志,有意识地追求自我克服和创造性,是每个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要任务。
实际上,追求本真的自我、追求更高的自我,也就是“成为你自己”的教育思考,在早期作品《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中就已经明确提出。因此,如果这里把早期尼采和晚期尼采的教育思考联系起来,可以说,“成为你自己”是尼采教育哲学的主要关怀。进而言之,尼采哲学就是一种广义上的教育(Bildung)学说。这也说明,除了语言学尼采、文学尼采、哲学尼采,还存在着教育学尼采。尼采到处都在讨论文化、教化、教育和生命问题。尼采的最高的目标是成为广义上的“教育者”。
尼采也深深知道,过一种创造的生活是极为艰难的。查拉图斯特拉刚刚离开一会,回来就发现许多弟子在崇拜一头驴子。[6]496-507这也说明,有时人很难摆脱风俗加于自己的奴性以及人性本身的脆弱。《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都强调真正的教化大师是一种能过孤寂生活的人物,而这种自主的孤寂的生活,对于有些人来说,是难以达到或难以维持的。
因此,早期尼采和晚期尼采的教育哲学对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并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教师必要的权威和指导仍然是教育关系的必要组成部分;扭转习性的学习(umlernen)是异常艰难的,因而仍需要铁的纪律约束;而且,如果人已经可以凭借自己“成为他自己”,那这已经不存在教育和教育关系了,而是已经步入尼采说的自我教化了。
另一方面,没有变化的是,早期尼采和晚期尼采都认为,人的成长都是痛苦的。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尼采仍然强调,一种比较高级的文化只能在有两种不同社会等级存在的地方才会产生:劳动等级和能真正有闲暇的等级。或者用更激烈的说法:被迫劳动的等级和自由劳动的等级。[7]302其理想的乌托邦仍然类似于早期的天才共和国:在一个更好的社会秩序中,艰难的工作和生活的困苦将要分配给那些最少为此感到痛苦之人,即那些最麻木的人;然后逐步上移,直到对各种最高尚的痛苦最为敏感的人,这种人就是在生活已然最大限度地变得轻松时仍然痛苦不已。[7]316越是在精神的金字塔往上的人,越是受苦最多的人。学习者进步的程度应该是其受难的程度。进而言之,尼采的乌托邦,仍然是一种带有悲剧美学原则的乌托邦。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虽然只是早期尼采一个未出版的作品,但总体上还是体现了一种尼采整个时期的革命性的一致性的教育哲学,尽管对于尼采的另一种解释总是可能的。
国际上对尼采教育哲学的理解存在着争议。英美学者多重视晚期尼采的教育思想,把尼采的“超人”理解为一种能够创造新的价值、过一种创造性生活的理想人,尼采甚至被理解为模范的民主教育者。但是,在德国,人们对于早期尼采的教育思想更加关注,认为尼采精英主义教育理想与现代民主社会的教育理念不相符——“也不应相符”,“超人”不可以被理解为教育学概念。尼采对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敌意和他前法西斯和纳粹主义的“思想元素”是一致的,这导致他的教育概念与“操纵、驯兽”等别无两样。正是因为德国的教育阐释者对尼采哲学被操纵和滥用十分敏感,导致他们和英美同事的观点不同,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对尼采作为教育者这一观点持保留意见。[8]
实际上,早期尼采既然没有说谁是精英、谁是天才,那么所有人都可以通过竞争去证明自己,并寻求发展自己的特有的天赋。这也带有一定的民主性。民主的教育并不意味着拉平、抹平或排斥精英和大众的区分。尼采教育思考的终极目标与其整个哲学体系一样,都试图通过造就天才或更高类型的人类来创造更高的真正的文化,并借以给社会全体以获得最珍贵的回报。因此,这对于强调大众教育和民主教育,但同时又渴望创新、渴望真正的生命的今天社会来说,尼采偷听来的这个故事所强调的信息,即国家是文化的工具,教育和教育机构的根本任务在于孕育天才,并期待实现天才的共和国,都具有持久的警示意义。人类应该为产生伟大的个体作持续的努力。这,而且唯这个,才是它的任务。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这种荒原上的呼吁,对沉溺于时髦的现代文化中的人们来说,并非每个人都能听懂,而是指向特定读者:只有他们才能猜度只能暗示的意义,才能补充所必须省略的内容。尼采后来同样拒绝对号称第五福音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作让人容易理解的解释。这里,尼采寻求的是读者与作者的前定和谐。尼采不愿意出版这些讲演,主要是认为它应该和能够变得更好,同样,也担心读者的素质。
这本书既然宣示了教育的秘密,但又不可能向所有人明示。因此,它寻求自己的读者和私人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