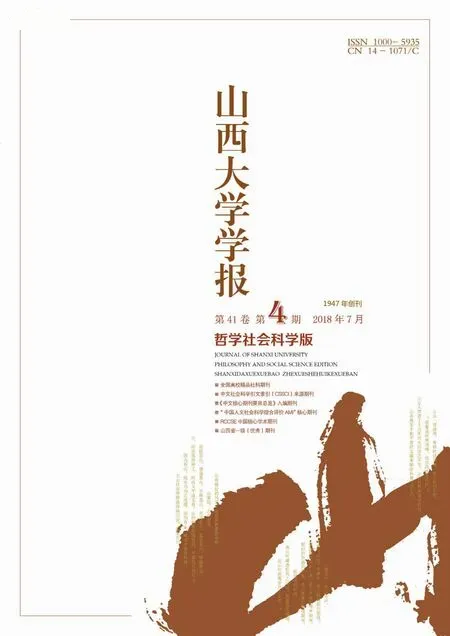唐玄宗置中都之始末及其深层意义
丁 俊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唐玄宗在蒲州置中都一事,由于史料记载时间不一,且维持半年即废,历来不为学界所多加措意。大家对于蒲州的地位或重要性的认识,多侧重于唐后期。一般在述及唐初屈突通、尧君素等人对河东的拒守之后,就进入安史之乱以后的各个阶段。*参见:张丽花《略论永济在隋唐时期的战略地位》,山西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任颖卮《唐代蒲州研究》,山东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贾发义,史诤罡《试论蒲州在隋唐五代时期的特殊地位》,《山西档案》2014年第4期;高显《论蒲州在唐代军事中的重要地位》,《运城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史料所提供的依据,也是如此倾向。至德二载(757),李泌建议肃宗在部署平叛计划时,先令“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取冯翊,入河东”,使叛军“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数千里”,唐军可以以逸待劳。[1]4633郭子仪也认为,“河东居两京之间,得河东则两京可图”。[2]7135实践证明,在收复两京的过程中,河东郡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于是,同年,升河中防御使为河中节度使,领蒲、晋、绛、同等七州。*《新唐书》卷六六《方镇表三》,第1836页。《旧唐书·肃宗本纪》所载时间不同,曰“(乾元三年)二月癸巳朔,以右丞崔寓为蒲州刺史,充蒲、同、晋、绛等州节度使。”第258页。乾元三年(760)三月,“甲申,以蒲州为河中府,其州县官吏所置,同京兆、河南二府。”[3]258宝应元年(762),为中都。元和三年(808),复为河中府。[4]卷68在此期间,李光弼与郭子仪都曾出镇河中,河中由此成为拱卫长安,防御河朔藩镇的重要力量。有鉴于此,颜真卿描述蒲州为“尧舜所都,表里山河”,“扼秦晋之喉,抚幽并之背”。[5]3403大历五年(770),元载上疏亦曰“长安去中都三百里,顺流而东,邑居相望,有羊肠底柱之险,浊河孟门之限,以轘辕为襟带,与关中为表里”。[3]297;[5]3743这类认识都是基于当时的客观形势或史实现状而加以总结与深化的。但是实际上,蒲州的重要性或者特殊性,早在唐初就已经为统治者所意识到。尤其是唐玄宗第一次在蒲州置中都,更是通盘考虑,其相关部署也直接影响到后期的二次置中都。
一 京邑所资:河东之蒲汾晋绛
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自晋阳起兵,进入长安称帝,建立唐朝。但是,作为大后方的山西地区并不稳定。武德二年(619)闰二月,刘武周在突厥的支持下进攻并州,随后兵锋南下。九月,裴寂与宋金刚战于介州,败绩。李元吉奔逃京师,并州陷落。刘武周派遣宋金刚攻拔晋州,“进逼绛州,陷龙门”。十月,又陷浍州,“时王行本犹据蒲坂,未下,亦与武周相应,关中震骇”。[1]9;[3]3-9;[2]5850-5868面对如此形势,李渊认为“贼势如此,难与争锋”,打算放弃河东,谨守关西。秦王李世民上表曰:
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精兵三万,必能平殄武周,克复汾、晋。[3]25
李世民之所以坚持太原与河东不可弃,是因为前者乃“王业所基”,后者乃“京邑所资”,即河东是京畿地区的重要粮食补给区。这里的河东并不等同于后来的整个河东道,也不仅限于隋代的河东郡、唐代的蒲州这一域*任颖卮认为,隋唐时期的河东地区,其空间范围定格在稷山以南,黄河以东、以北,中条山以西的运城盆地。(《唐代蒲州研究》,第24页。),而是大致包括了太原以南汾河、涑河流域的蒲、绛、晋、汾诸州在内。上述“克复汾、晋”即可视为概括之语。这种认知来自隋代以来关中地区的粮食供应状况。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开皇三年(583),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诏于蒲、陕、虢、熊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6]683可见,汾、晋粟米是京师仓廪的重要来源之一,而蒲州则是这些粟米由河入渭的转运地,部分运丁也出自这里。不仅如此,寻常庸调的运送也是同样路径。“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阪,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6]681-682这里的“河北”是指黄河以北地区,主要包括河东道与河北道各州县,其庸调物皆取路蒲坂,达于京师。严耕望先生指出,蒲津关地当关内、河东、河南之交会处,为“河东、河北陆道进入关中之第一锁钥”。[7]99任颖厄也指出,隋唐之际,从蒲州渡河至关中的津渡由北向南依次有:龙门山与陕州韩城之间的龙门渡、蒲州河东城西的蒲津渡、河东城西南的风陵渡。其中,龙门渡、风陵渡水势较为湍急,需乘船渡河,而蒲津渡口建有浮桥,水流平缓,是河东进入关中的最佳通道。[8]142元载所谓“长安去中都三百里,顺流而东”,可谓是最佳写照。[9]324
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关中饥,监察御史王师顺奏请运晋、绛州仓粟以赡之,上委以运职。河、渭之间,舟楫相继”。[3]2113此次转运规模应当很大,唐高宗专门设置运使,将晋、绛一带粟米,经蒲州由河入渭,运至关中。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玄宗以裴耀卿为江淮转运使,进行漕运改革,其首要目标虽然是扩大江淮租米的运送量,但是同时也“益漕晋、绛、魏、濮、邢、贝、济、博之租输诸仓,转而入渭”。[1]1366可见晋、绛之粟仍然是京仓的重要补给来源,河南、河北沿河诸州也在其中。另外,根据开元《水部式》,“胜州转运水手一百廿人,均出晋绛两州。”胜州位于黄河向南大拐弯处,南下可达长安,东去河东道,据任艳艳推测,不仅胜州的转运水手来自晋、绛二州,而且其转运的粮食物资等一部分也来自河东。[10]也就是说,晋、绛两州不仅是“京邑所资”,而且也兼具供军功能。史念海先生指出,隋唐时期,黄河流域的富庶地区,大致可以分为四处,最为广大的当推黄河下游,其次为伊洛两水的下游,第三为汾水下游和涑水流域,第四为泾渭两水下游的关中平原。[11]82这里的汾水下游和涑水流域,具体就包括河东道的蒲、晋、绛、汾诸州。这些地域之所以富庶,除了本身河流众多,土地肥沃之外,也是因为自唐初以来就注重农业的恢复生产,集中了众多的水利工程。[12]尤其是绛州龙门县,贞观二十三年(649),县令长孙恕凿十石垆堰,“溉田良沃,亩收十石”。[1]1000-1001这样的亩产量大约是当时平均亩产量的五倍以上。*杨际平认为,唐代中等旱土的亩产常在一石左右,上等旱土则可达到二石或二石以上。(《唐代尺步、亩制、亩产小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而且,蒲、晋、绛、汾诸州作为汾水、涑水流域的富庶区,人口密度也比较大,贞观年间大致都在15人/km2以上,到天宝年间也普遍在50人/km2以上。[13]22
因此说,在唐前期,作为“京邑所资”的河东地区,就其经济力量与实践功能而言,当指山西中南部的黄河流域及其支流所在的蒲、晋、绛、汾诸州。其中,蒲州的特殊重要性还在于,它是黄河以北尤其是河东道与河北道租税物进入关中的重要通道。
二 从中都到北都:唐玄宗的战略选择
唐初定都长安,显庆二年(657),洛阳正式成为东都。长寿元年(692),武则天置北都,改并州都督府为太原府。[4]1407-1409任艳艳认为,武周时期是唐代河东道政治、军事地位提升的关键时期。[14]40-43这个认识值得重视。神龙元年(705),中宗即位,罢北都为并州大都督府[4]1409,依旧保留东都洛阳、西京长安的二京制。
河东道地位的进一步提升,或者说其经济、军事等功能的再度凸显,是在唐玄宗开元时期。唐玄宗即位初期面临着两大问题。第一,“钱谷不入。”这个问题与蒲州被置为中都有很大关系。第二,边境问题。其中由突厥降户所引发的北部防御格局的变化,应当与北都太原府的建立直接相关。这二者之间往往也互为因果。
开元二年(714)六月,吴兢上疏曰,“陛下承天后、和帝之乱,府库未充,冗员尚繁,户口流散”,他强调经过武则天、唐中宗之后,唐玄宗首先面临的是仓廪空虚的问题。[5]1801类似的言论在这一时期不断出现。同年正月,靳恒为拾遗,曾言“陛下绍登大位,初启中兴”,“郡国凋敝,仓廪空虚”。[5]1622十月,苏颋表谏玄宗亲征吐蕃时也指出,“频岁以来,百姓不足,岐陇河渭,动无储廪”。[5]1536-1537这种糟糕的状况承自中宗、睿宗两朝。景龙三年(709),宰相韦嗣立谏曰,“今陛下仓库之内,比稍空竭,寻常用度,不支一年”。[3]2870这是迄今为止对于当时财政状况最为清晰的表述。睿宗景云二年(711),魏知古也进谏,“今风教颓替,日甚一日,府库空虚,人力凋敝”,“太府之布帛以殚,太仓之米粟难给”。就连睿宗本人也认为,“府库益竭”的状态毫无好转。[3]3062因此,玄宗即位,首先就要改变仓廪空虚、“钱谷不入”的状态。
但是,正如孟宪实先生所言,姚崇执政,对武则天以来的政策多有改革,但在财政方面并未采取扩大财源措施,最多只是减少开支而已。宋璟继任,亦无改变。直到宇文融括户为止,朝廷对地方的政策皆以清净为主。[15]230这个概括非常准确。姚崇、宋璟之所以未采取大的开源措施。原因之一在于这一时期水、旱、蝗灾相继,百姓必须休养生息。[2]6785;[3]172-181其次,政治稳定是首选。唐玄宗在财务行政方面开创新局面,是从开元八年(720)开始,其突出表现就是财政使职的兴起与专业职能部门的整体发展。[16]97与此同时,唐玄宗也在其他方面进行着改革与尝试。其中的举措之一,就是在蒲州建立中都,改为河中府。
唐玄宗置中都的时间,史料记载不一,有开元元年正月、开元元年五月、开元六年、开元八年、开元九年正月八日、开元九年正月丙辰(九日)、开元九年五月共七种记述,停罢时间也各有不同。*《通典》卷三三《职官十五·州郡下》记在开元元年正月,“六月而罢”。(第903页)《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二《河东道一》记在开元元年五月,“六月诏停”。(324页)《旧唐书》卷一八五下《姜师度传》记在开元六年。(第4816页)《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与《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三》记在开元八年。(第1469页,1000页)《唐会要》卷六八《诸府尹》记在开元九年正月八日,六月三日停。(第1410页)《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与《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皆记在开元九年正月丙辰,即正月九日,不过罢停日载在不一,前者曰“七月戊申(三日)”罢,后者曰“六月己卯(三日)”罢。(第181-182页,6862-6864页)《通典》卷一七九记在开元九年五月建。(第4726页)《太平寰宇记》卷四六《河东道七》记载,开元九年置,“七月诏停”。(中华书局,2007年,第950页。)严耕望先生认为,《旧唐书·玄宗本纪》与《资治通鉴》所载时间一致,故取开元九年正月九日丙辰。[7]104田尚先生认为,当以《旧唐书·玄宗本纪》、《唐会要》的记载为是,即开元九年正月八日或九日。[17]华林甫亦持此观点,并且认为新旧《唐书·地理志》所录开元八年是动议时间,也就是河中置府的申报年代。[18]总之,蒲州置中都并改河中府的时间,大致始于开元九年正月八、九日,终于同年六月三日,或七月三日。维持了大约半年的时间。
唐玄宗于蒲州置中都的原因,史籍未明。田尚认为,蒲州为京城东边的军事重镇,而且“富贵”,蒲州的得失,往往危及东西两京的安全,故置中都。[17]这仍旧是侧重于安史之乱以后蒲州的战略地位。不过,他指出蒲州乃长安东边的一个重镇,而且“富贵”,这是比较重要的。杨炎在《安州刺史杜公神道碑》中云,“开元初,上以中都稍食,省河漕之徭”,由是置使。[5]2553其重点在于强调蒲州的经济功能。第一,蒲州为“京邑所资”,具备粮食供应功能;第二,此地距长安比较近,漕运便利。这是相对于东都洛阳而言的。陈寅恪先生指出,“自隋唐以降,关中之地若值天灾,农产品不足以供给长安帝王宫卫及百官俸食之需时,则帝王往往移幸洛阳,俟关中农产丰收,然后复还长安。”[19]162因为洛阳更接近富饶多产的黄河下游平原以及南方地区[20]33,因而成为天子“逐粮”的首选之地。但是,就这一点而言,蒲州同样具备类似的功能,不同之处在于它接收的是黄河以北的租税物,而洛阳更易于接收黄河以南广大地区的税物。而且,蒲州地处长安、洛阳之间,无疑可以使皇帝在辗转东幸或者西归的途中有个中转站,甚至直接多一个选择,弃洛阳而选蒲州为目的地。更何况河东作为“劲锐强兵,尽出于是”的股肱郡,[5]1786-1787它在唐初折冲府数量居天下第二的军事力量*谷霁光指出,贞观十年,全国折冲府657府,关内道288府,河东道164府,位居第二。(《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54页。),也足以保障其作为一都的安全。另外,蒲州盐池还负责供应京师*《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蒲州安邑、解县有池五,总曰‘两池’,岁得盐万斛,以供京师。”第1377页。,其潜在的经济价值不言而喻。
因此,唐玄宗在开元九年正月置中都时,特以“颇知沟洫之利”的姜师度为河中尹。[3]4186其中大概有两层考虑。第一,加速地方租税物向中都、长安的集中与流动。在这方面,姜师度是有经验的。*《旧唐书》卷一八五《姜师度传》:“开元初,迁陕州刺史。州西太原仓控两京水陆二运,常自仓车载米至河际,然后登舟。师度遂凿地道,自上注之,便至水次,所省万计。”第4816页。第二,挖掘蒲州的盐池之利,为解决“钱谷不入”问题增添新的收入渠道。毕竟唐朝沿袭隋代以来的政策,“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不像北周那样,“百姓取之,皆税焉”。[6]679-681总之,朝廷在置中都的问题上一定是有所讨论并最终获得通过。根据《营缮令》,“诸在京营造及贮备杂物,每年诸司总料来年所须,申尚书省付度支,豫定出所科备。”[21]672换言之,若要营建中都,其人功、支料等都要提前一年申报,并且列入年度支用计划。这个计划应该始于开元八年,至次年才付诸实施,正式营建。
姜师度作为新任河中尹的工作之一,就是“缮缉府寺”,扩充官署,同时“置中都官僚,一准京兆、河南”。[2]6862根据《唐六典》记载,河中府若参照京兆府、河南府的标准,当置官员自河中尹以下,共28人。府、史、执刀、典狱等杂职、杂任328人。相比之下,蒲州此前即使为上州,也仅置官员18人,杂职、杂任等胥吏214人。*赵璐璐指出,唐代州县胥吏基本分为杂任和杂职两类,其中杂职仅包含执刀、典狱、问事、白直四类人员,余为杂任。(《唐代县级政务运行机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54-56页。)也就是说,蒲州从州升府,所属官吏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充一半。不仅如此,还要增加属县,从河东县析置河西县。蒲津渡口就在新析县内。[1]1000
以上工作可能并未彻底完成,因为朝中很快出现了反对意见。丽正殿学士韩覃上疏,请求“罢事中都”。其缘由大致如下:
曩者韦氏称制,万邦忧惶,实赖陛下神武,克复社稷。其初也,贱珍宝,禁奢华,罢土功,敦朴素……奈何简易未几,而又兴建中都乎?……顷年已来,水旱不节,天下虚竭,兆庶困穷。户口逃散,流离艰苦,巩洛暴水,所丧尤多,江淮赤地,饥馁者众。加以东北有不宾之寇,西凉有丧失之军,干戈岁增,疆场骚动。近又胡羯逆命,征发不宁,料事度宜,岂应更建中都乎?至若两都,虽旧制矣,然而分守官众多矣,费耗用度,尚以为损,岂况更建中都乎?夫河东者,国之股肱郡也,劲锐强兵,尽出於是,其地隘狭,今又置都,十万之户,将安投乎?夫惟所造城阙,爰及苑囿,毁拆闾阎,令其别创,损坏冢墓,令其改卜,殷富者破其产业,贫窭者莫知所从。……且陋东都而幸西都,自西都而造中都,取乐一君之欲,以遗万人之患。务在都国之多,不恤危亡之变;悦在游幸之丽,不顾兆庶之困,非所以建深根固蒂不拔之长策矣。……臣愚诚愿陛下发德音,垂明诏,深恤黎庶,罢事中都,则福履无疆,天下幸甚。[5]1786-1787
韩覃的核心论点大致有三。第一,“顷年已来,水旱不节”,百姓困穷,加上边境“干戈岁增”,“征发不宁”,从国家用度来看,不宜营建中都。第二,长安、洛阳作为帝王巡幸之都,已经足够,且官员众多,耗费过大,不宜再复置一个与洛阳功能类似的中都。第三,河东“隘狭”,若置中都,百姓有可能丧失安身之所。主要还是从反对营造之功,反对帝王为追求享乐而增加百姓负担的角度来论述的。这属于传统观点。这种观点如果当时能够发挥作用,那么营建中都的计划就不会付诸实践。*田尚认为,玄宗罢中都的原因,是考虑蒲州地狭人多,修建宫殿供自己巡幸娱乐。恐并未切中主旨。(前揭文,第93页)唐玄宗之所以同意在半年之后罢中都,关键原因在于出现了新的不利状况,也就是韩覃谏表中所提到的边境形势的变化。
开元四年(716),突厥默啜死,毗伽可汗新立,突厥降户相继叛归。开元五年七月,并州长史张嘉贞奏请于并州置天兵军,“集兵八万”,以镇抚太原以北的突厥部落。开元八年,改天兵军大使为天兵军节度使。[22]405-406但是与此同时,朔方大使王晙却采取不同策略。六月,计诱突厥降户于受降城,杀八百余人,“河曲降户殆尽”。随后,在王晙的主导下,唐朝对突厥展开主动进攻,西发拔悉密,东发奚、契丹,共袭毗伽可汗牙帐,但是结果连兵失败,毗伽可汗大振,“尽有默啜之众”,时在开元八年九月。到开元九年四月,兰池胡康待宾反叛,攻陷六胡州,有众七万,进逼夏州。此即韩覃所云“近又胡羯逆命,征发不宁”的由来。玄宗令朔方大总管王晙、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共讨之,天兵军大使张说也协同作战。[3]181-182战争规模扩大,成为朝廷当务之急。
突厥毗伽可汗的崛起,以及康待宾等降胡的反叛,迫使唐朝重新将战略防御重心转回北部边境。天兵军大使张嘉贞、张说先后入朝为相,也足以说明这一点。*据《旧唐书·玄宗本纪上》记载,开元八年正月,并州长时张嘉贞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五月,为中书令;开元九年九月,并州长史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第181-182页)直到开元十年九月,张说擒康待宾余党康原子,并将河曲六州残胡移置河南、山南等道的许、汝、唐、邓诸州,这个问题才算告一段落。[3]181-184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唐玄宗选择增置边兵,弃置中都。开元九年,唐朝正式设置朔方节度使,“领单于都护府,夏、盐等六州,定远、丰安二军,三受降城”。而太原作为北方的军事重镇,张嘉贞、张说两位宰相出将入相之地,其地位也凌驾于深入中原腹地的蒲州之上,于开元十一年(723)置北都,并置太原以北节度使,“领太原、辽、石、岚、汾、代、忻、朔、蔚、云十州”。[2]6874
由此可见,唐玄宗政策重心从中都向北都转移,其实涉及朝廷的政策选择。如果边防状况有变,朝廷需要前压式防守,那么北出长城与阴山大漠相连的太原就显得更为重要。如果采取收缩性防守,则河中就变得重要。安史之乱以后在蒲州再置中都,就属于收缩性防守总体态势下的举措。它来源于唐玄宗对于蒲州的持续经营,也进一步验证了唐玄宗的战略眼光。
罢都之后,唐玄宗并没有彻底放弃蒲州,而是进行下一步调整。他选择将蒲州回收,与关中连为一体的政策,从而使蒲州成为京师长安的东大门,蒲州地位也稳步上升。《旧唐书·地理志》记载道,“其年,罢中都,依旧为蒲州,又与陕、郑、汴、怀、魏为‘六雄’。十二年,升为‘四辅’。”[3]1469可见,蒲州在罢中都后,很快就升为“六雄”州之一。根据刘禹锡的理解,“大凡环天子之居为雄州”。[5]6121但是就开元六雄州而言,环居二字并不足以涵盖其全部要义。这六州当中,蒲州是由河入渭、由河东进入关中的最佳通道,陕州有太原仓,又有三门之险,怀州与郑州紧邻河南洛阳,又靠近河口,汴州仅次郑州之东,也是汴渠的重要运段,而魏州虽然在河北道,但同样毗邻黄河。也就是说,这六个州都是黄河沿岸最重要的粮食转运枢纽,也是黄河流域最富庶的地域,它们都是京师的主要供应地。至于沈亚之所云,“蒲河中界三京,左雍三百里,且以天子在雍,故其地益雄。”[23]4251仍然属于唐后期对于蒲州之“雄”的认识。唐玄宗首先在经济功能上把蒲州与关中连为一体,这一点必须重视。《唐会要》卷五九《长春宫使》记载道:
开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敕:“同、蒲、绛、河东西并沙苑内,无问新旧注田蒲萑,并宜收入长春宫,仍令长春宫使检校。”[4]1222
所谓注田蒲萑,是指水泽边可被改造的滩涂荒地等。长春宫与沙苑都在同州界内。[9]36-38沙苑为畜牧养马之地,长春宫亦有屯田*据《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长春宫有十一屯。(第223页)又据《唐会要》卷五九《长春宫使》,开元八年六月始置长春宫使。(第1221页)。这道敕文之意为,位于黄河东西两岸的蒲、绛、同三州,其界内的水泽滩涂等地,与沙苑之地一并归入长春宫使管理,用以扩充屯田。这显然是增加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而蒲、绛两州的沿河之地则被跨地域纳入关内道的使职进行管理。类似状况在军事方面也是如此。
开元十一年,张说于京兆府与蒲、同、岐、华四州募兵十二万以宿卫京师,号为“长从宿卫”,后更名彍骑。[2]6876其中唯有蒲州隶属河东道,其余皆在关内。次年,蒲州的地位再次上升,与同、华、岐三州共为“四辅州”。《唐六典》特别注明,“蒲新升入”。[24]66蒲州正式具备辅翊京师的地位。而且,也正是在开元十二年,玄宗下诏修建新的蒲津浮桥,用铁链串联船只,两岸各铸铁牛四尊,“一人策之,牛下有山,皆铁也,夹岸以维浮梁”。[1]1000蒲州入关中的交通更有保障。另外,根据《唐六典》记载,“凡关内团结兵,京兆府六千三百二十七人,同州六千七百三十六人,华州五千二百二十三人,蒲州二千七百三十五人。”[24]157可见,团结兵与彍骑的兵源相似,只是少了京师西翼的岐州。任颖卮认为,唐人视蒲州为关内,所以才会在统计“关内团结兵”时,把蒲州列入其中。[8]27这与唐玄宗对于蒲州的一系列部署与规划,显然是高度关联的。蒲州在罢中都之后,虽然在行政区划上仍旧隶属河东道,但是实际上在经济与军事职能上已经实现了跨河西属,与关中连为一体,正式成为长安的东大门。这就是元载所谓的蒲州“与关中为表里”的缘由。
三 蒲州盐池与财务行政之新趋向
蒲州罢中都之后,除了唐玄宗对于它的部署调整之外,还有一项工作对于后期的行政运作也影响深远,那就是姜师度对于安邑盐池的治理以及相关政策的变化。《旧唐书·姜师度传》记载道:“先是,安邑盐池渐涸,师度发卒开拓,疏决水道,置为盐屯,公私大收其利。”[3]4816其他史料的记述也基本一致。[4]1901-1902;[25]5591姜师度的做法,应该是先开沟引水。张泽咸先生指出,池盐的生产是垦地为畦,按畦依次灌水,盐卤经日光照射,水分得到蒸发而成盐。[26]158安邑盐池此前渐趋干涸,因此姜师度用兵卒开畦灌水,至于晒盐等工作,可能也是招募百姓为屯丁,所以才“公私大收其利”。*吉成名也认为,蒲州盐池的劳动者可能是招募来的百姓。(《唐代盐业经营方式》,《盐业史研究》2001年第3期。)其收益若是参照屯田的比例计算,据《晋书·傅玄传》记载,官方的纯收益在50%以上*《晋书》卷四七《傅玄传》:“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第1321页。,安邑盐屯的收益比例大概也相距不远。
安邑盐池的具体收益数字应当是年底才上报中央的。按照制度规定,各州刺史及上佐为朝集使,每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京都,十一月一日于户部引见,将其年终勾账即一年的财务账,送至户部与比部接受审计,然后方“集于考堂,应考绩之事”。[24]79;[27]129-130正因为安邑盐池获利惊人,于是十一月五日,左拾遗刘彤上表,建议效法汉武帝,“煮海为盐,采山铸钱”,“诏盐铁木等官收兴利”。于是,皇帝召集宰相与群臣商议,皆以为“盐铁之利,甚益国用,遂令将作大匠姜师度、户部侍郎强循俱摄御史中丞,与诸道按察使检责海内盐铁之课”。[3]2106-2107
唐玄宗命姜师度与强循等人“检责海内盐铁之课”,应该是打算将安邑盐屯的做法在全国推广。李锦绣先生就持同样的看法。[28]175进一步讲,还是想通过官屯的方法,将全国食盐的生产进行统一监管,以扩大中央的财政收益。但是,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唐会要》记载道:
(开元)十年八月十日,敕:诸州所造盐铁,每年合有官课,比令使人勾当,除此更无别求。在外不细委知,如闻稍有侵克,宜令本州刺史、上佐一人检校,依令式收税。如有落帐欺没,仍委按察纠觉奏闻。其姜师度除蒲州盐池以外,自余处更不须巡检。[4]1902
这道敕文看似回归原政策,但也不尽然。它首先透漏了一个信息,“使人勾当”时出现了“稍有侵克”的现象,这其实反映的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就是地方政府不配合,与宇文融括户时所遇到的问题一样。[29]敕文云,此前各产盐州只需交纳数量不多的盐课,其余收益很可能在当地官府与“富强者”之间分享。*例如,《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记载:“河东郡有盐池,旧立官司以收税利。至是(显祖皇兴时)罢之,而民有富强者专擅其用,贫弱者不得资益。”第2862页。如今派遣使人检责,一定会压缩他们的这部分利益。故巡检工作遇到阻力,朝廷不得不适当让步。需要指出的是,姜师度等人检责海内盐铁之课,与宇文融括户是同时进行的。后者之所以几经周折,终于在开元十二年获得成功*《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开元十二年,“凡得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岁终,增缗钱数百万,悉进入宫;(宇文融)由是有宠。”第6880页。,而前者只能中途暂停,原因还是在于检括逃户与隐匿之田属于国家正税范畴,而盐铁之利并非正规的国家税目。仁井田陞所复原的唐令中有一条,曰“山川薮泽之利,公私共之”[30]783-784,虽然用语不够明确,年代也不详,但是至少不像汉代那样,“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31]1127,帝室财政与政府财政截然分开。因此,玄宗君臣尽管皆知“盐铁之利,甚益国用”,但是在实施上还是会遇到现有制度上的不便与掣肘。
不过,开元十年的敕文表明,姜师度等人此番检责海内盐铁之课,并非对现行制度没有推进。首先,玄宗保留姜师度巡检蒲州盐池的权力,安邑盐池依然由中央派遣盐池使进行检校。其次,其他产盐州虽然将使职召回,但是“令本州刺史、上佐一人检校,依令式收税。”这里的“依令式收税”,大概是延续之前官收商税的老办法[32]113,但是“令本州刺史、上佐一人检校”,显然是新规定。这可以归结为财务行政中的事权上移与专知官现象。
事权上移,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吴宗国先生指出,唐宋以后官僚政治体制重大变化之一是行政权的扩大和分化,宰相在行政权扩大的同时,事权开始下移,分层决策进一步发展。[15]9但是就各级行政机构而言,恰恰出现了事权的上移。这种现象始于皇权对于重点政务的集中把控。开元三年敕曰:“钱谷刑狱等事,有宣付诸司处置者,宜更令覆奏,候旨敕施行。”[4]1091这说明钱谷、刑狱作为国家的两项重要政务,其最高决断权收归皇帝手中。而盐铁作为钱谷之务中的新加事项,由州一级长官专知,同样属于事权的上移。这种趋势在开元天宝时期日益明显。《唐会要》记载道:
(开元)十六年七月敕:“诸州税及地税等,宜令州郡长吏专勾当,依限征纳讫,具所纳数及征官名品申省。如征纳违限,及检覆不实,所由官并先与替,仍准法科惩。”[4]1816
租税物的征收本由州仓曹具体负责[24]卷30,747,但是如今改由“州郡长吏专勾当”,换言之,州郡长官成为财税事务的专知官。专知官的特点就是躬亲事务,它属于唐后期的行政运作体系,其萌芽在开天时期。[33]35-40吐鲁番文书中出现的较早的专知官,是开元九年的一块庸调布上所写的“主簿苑”[34],他显然不属于州县长官。财政专知官的层级上移,首次出现于开元十年的盐铁管理,它属于新加事务,然后就是开元十六年敕旨。到天宝三载(744),又制曰:“太守县令兼能勾当租庸,每载加数成分者,特赐以中上考。”[35]22这就更加强调,州县长官当以检校租税为第一要务,其中“赐以中上考”的做法,与使职系统中的论功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有关使职系统中的论功原则,笔者拟另著专文讨论。
总而言之,唐玄宗开元九年在蒲州置中都,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蒲州在税物集中与转运方面具备东都洛阳的类似功能。而且有地近之便。但是由于边境形势的变化,唐朝采取前压式防守政策,故弃中都,改置北都。不过,蒲州在唐玄宗的持续经营下,逐步实现了跨河西属,与关内连为一体,成为京师长安的东大门。其地位也同步上升,成为“四辅州”之一。与此同时,安邑盐池以及相关事务在管理模式上的变化,尤其是事权的上移与专知官现象,开启了唐代财务行政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