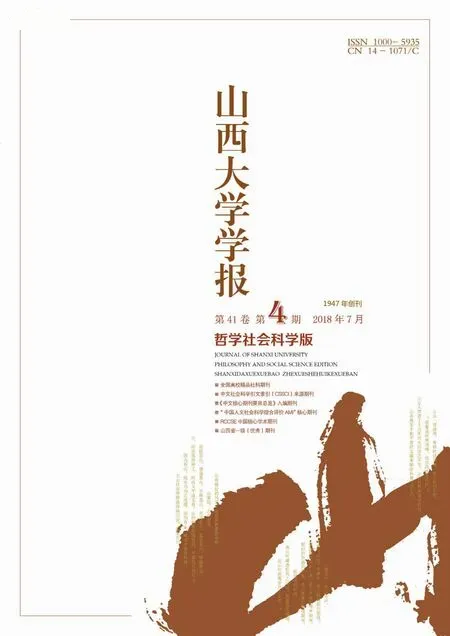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
——尼采教育哲学中的矛盾关系及其解决思路
刘良华,覃晓思
(1.华东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上海 200062;2.广西老年大学 教务处,广西 南宁 530022)
尼采(F. Nietzsche,1844-1900)以权力意志的强弱为标准把人类分成两类。大概在40岁那年(1884年),尼采给朋友写信时说:“可能是第一次,我有了这么个把人类分割成两半的思想”。[1]433在他看来,权力意志强大的人属于社会的精英,权力意志弱小的人则沦为大众。大众的天职是服从精英的统治,但是,苏格拉底(及柏拉图)、基督教和民主启蒙的三次“鼓动”导致了奴隶的反叛和大众革命,也导致了精英的没落并由此而引发现代性的危机(因社会的平等而导致社会的平庸)。为了缓解现代性的危机,尼采设计了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精英教育包括“牧人”式领导者教育和“孤独者”的哲人教育,他们需要培育强大的意志力,以便迎接和克服永恒轮回的悲剧意识。
就时代危机而言,尼采的确更重视精英教育以及与之相关的新道德教育。尼采并不因此而仇视大众。尼采依然承认大众以及大众教育的必要。大众教育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宗教、奴隶道德、“求假意志”来使大众学会“服从”。奴隶道德本身并不坏,它是大众的需要。尼采只是不赞成用大众的奴隶道德来使精英束手就擒。
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研究视角以及分析框架的意义在于:如果不从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区分来阅读尼采的教育哲学,就难免会被尼采文字的表面所迷惑。尼采教育哲学貌似存在两个矛盾,这两个矛盾给读者带来了相应的困惑:第一,尼采为何既强调权威又重视服从?第二,尼采为何既强调阳刚的权力意志,同时却又重视柔软的宗教与善意的谎言?从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分析框架来看,尼采教育哲学中表面的矛盾就会迎刃而解。
一 尼采的天才教育论
尼采教育哲学的关键文本至少有三个:一是《悲剧的诞生》;二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三是《权力意志》。三者之中,《悲剧的诞生》最有原创性和学术性。这本书看似粗糙,尼采本人后来对之也不太满意,但,它依然算得上尼采所有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书。尼采的中后期的著作都可以视为《悲剧的诞生》这本书的拓展本。
尼采在28岁那年(1872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悲剧的诞生:源于音乐的灵魂》。《悲剧的诞生》是尼采少有的有“学术感”的作品。在后来所有作品中,只有《不合时宜的沉思》(1873年开始陆续出版)接近它的学术风格。
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始于对古希腊文化的重新评估。一般人认为古希腊文化的核心精神是“明朗”,显示出“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2]185但尼采看到的古希腊文化是阿波罗(太阳神精神)与狄奥尼索斯(酒神精神)的对立、冲突与统一。“对立统一”的研究视角虽然显得老套和俗气,但这个视角为尼采重新理解希腊文化并由此而重新理解“人的本性”提供了强大的支持。阿波罗的造型艺术和狄奥尼索斯的音乐艺术的“对立”和“统一”贯通整篇论文(该书其实是一篇较长的学术论文)。
尼采所谓的“悲剧”精神,其实就是“男子汉气概”(或血性、激情、力量之美)。他批判基督教,也是因为基督教贬低激情、使人变成温顺的羔羊。这样看来,该书的标题似乎在暗示“男子汉的诞生”或“血气之美的诞生”、“主人道德的诞生”。
尼采的这本青年时代的小本子为他本人后来所有的作品定下了基调。后来的超人、主人道德、权力意志、永恒轮回等概念几乎都与早期著作《悲剧的诞生》一脉相承。如果说尼采的第一部作品是“悲剧的诞生”,尼采此后的所有其他作品乃是与之相关的“超人的诞生”。
1872年,尼采在巴塞尔大学做了5次以教育为主题的讲演。在发表第5次讲演的前一天,尼采写信给出版商,打算把系列讲演作为自己的第二部书,但几周以后,尼采又写信给出版商,声称自己要“花上几年时间”再对文稿进行修改,“使之更好一些”。但这本书在尼采生前一直没有出版。他曾把这些讲演稿分发给自己的朋友阅读。后来这本书以《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为书名在尼采去世后出版。该书(讲演)的核心主题是,把教育教化集中于少数人乃是自然的必然法则。这是普遍的真理。在他看来,大众是精英生长的土壤,教育机构的真正目标是少数天才教育而不必让大众(土壤)因接受过度教育而受惊扰和破坏。正因为大众是精英的土壤,精英应该感激和善待大众,尊重大众的生活方式和道德情感。如果说《悲剧的诞生》显示了尼采作为文化医生的诊断,那么,《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则是在“揭出病苦”后,去寻求“疗救”的药方。尼采此后的创作则往返于更深刻的诊断和“疗救”之间。
与天才相关的是等级制。尼采重新提出柏拉图式的等级制,建议精英要和大众保持一种“若干个生理类型之间的自然距离”[3]1137而且,“高踞于前者之上”[4]487。精英与大众保持距离并非完全离开大众,相反,精英应当成为大众的“下命令者和立法者”。他们需要“热心于伟大的责任,统治性的目光和俯瞰之威严,觉得自己不同于人群及他们的义务和德性,心平气和地保护和捍卫被误解和被诽谤的东西”[5]233。
尼采鼓励精英成为领导者和创造者,但认为成为领导者和创造者是不可兼得的两件事。“人们能够做到其中一件事,就不该想望另一件了”[4]672。对于希望走在前面的精英,尼采认为他们应该被培育成具有可怕而又友好精神的“牧人”角色,他们要领导羊群式的大众。而创造者高居金字塔的最顶端,他们是遗世而独立的“孤独者”。
在尼采那里,“牧人”式精英被归为了第二等级,“他们是法律的守护者,是秩序和安全的维持者,他们是高贵的武士,特别是作为武士、法官和法律维护者的最高形式,他们是国王。”[6]157尼采赞赏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的主张:君主必须变得兽性一些,学会像狐狸一样狡猾,又应该承袭狮子的勇猛。在尼采这里,“谎言、暴力和最无情的利己主义”将成为牧人式精英的统治技术。[7]168“牧人”也会赞颂那些大众认可的德性,但“牧人”自己不必相信那些道德。尼采的美德是一种权力意志,相当于马基雅维利的Virtu。“尼采实际上是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热烈崇拜者。”[8]44在对马基雅维利及其《君主论》的理解上,尼采与卢梭所持的观点也完全不同。尼采所理解的《君主论》正是超善恶的教材,而卢梭却说马基雅维利是在“给人民讲大课”。[9]91
而比“牧人”更高的是孤独者。“牧人”式的领导者属于第二等级,孤独的创造者属于第一等级。“孤独者”和“牧人”分享了共同的价值观,甚至“孤独者”式的精英也参与了领导和统治,但“孤独者”的地位高于“牧人”。因为“牧人”虽然明知真理却仍然用隐微教诲讨好、拉拢大众,而“孤独者”既知晓真理且独善其身,他们宁愿选择追求真理的自我统治。在尼采看来,“孤独者”最大的特征就是“忍受着孤寂,偏爱孤寂,要求孤寂,把孤寂当作幸福、特权”[4]370。亚里士多德认为,离群索居的人“非神即兽”[10]9。在这点上,尼采的孤独者与亚里士多德的“超人”构成呼应,同时也担当了亚里士多德的神兽角色。
对于这类精英,尼采的警告和教育就是“提防‘为了真理’而受苦!”孤独的哲人到大众那里去反驳或质疑公众的智慧和信仰只会将他们自己逼入绝境,尼采告诫这些精英,“不如退到边上去!躲避到隐蔽处……你们不要忘记了花园,带有金黄色的格状结构的花园!”[5]142也许尼采在这里想到的是“菜园哲人”伊壁鸠鲁,或者是查拉图斯特拉的高山:“在这里,你可以说出一切,倾吐一切理由。”[11]234-235
二 大众道德与大众教育
尼采认为大众“革命”蓄谋已久,绵延千年。大众革命发端于苏格拉底,经过柏拉图、基督教和启蒙运动的三次浪潮,大众成功地战胜了精英。大众革命使原先的金字塔型社会被改造成橄榄球型的扁平结构。
(一)大众的革命
第一次浪潮始于苏格拉底。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为大众的革命种下了“祸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没落的征兆”[12]44。苏格拉底之“祸”就在于“他发明了新的争论方式”。[3]995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是大众崛起的根源。只有大众才会把这种通过不断提问的方式让对方陷入矛盾当中的做法当作自我防护的手段,而精英并不需要辩证法加以护身。柏拉图则由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发展为“理念”。柏拉图的“理念”几乎就是世俗版的基督教及其“上帝”形象。尼采反柏拉图时,似乎故意忽略柏拉图思想中的等级制以及高贵的谎言等哲学思路。而等级制、高贵的谎言正是尼采所采纳的。尽管如此,尼采仍然把柏拉图、赫拉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并列为三大哲人。“真正的哲人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恩培多克勒式的人物。”[13]126
第二次浪潮来自基督教运动。尼采认为基督教是一个只适合大众而不适合精英的宗教。它最善于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彰显一切卑微,从而打倒高贵和强大的力量,使强者变得病态,“直到强者毁灭于自我鄙视和自我虐待的过度放纵”[3]697。它将世界置于一种虚假的负罪状态。于是,“一个缩小的、几乎可笑的种类被生产出来,一个群居动物,某种心甘情愿的东西、病态的东西和平庸的东西,今天的欧洲人……”[5]172-173
第三次浪潮来自18世纪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对科学、理性的倡导使人们不再对基督教怀着狂热的虔诚,取而代之的是对“科学”和“民主”(以及平等)的追求。启蒙运动直接引领了大众的“革命”。尼采以卢梭为标靶,批判启蒙运动“是人的衰败和渺小化形式,是人的平庸和低俗”。[5]217尼采认为卢梭造成了法国大革命那场最大的奴隶反叛,“以其万丈豪情和滔滔雄辩,要求用革命来推翻所有的社会秩序,误以为公平人性的最骄傲神殿随即会自动拔地而起。”[7]246经过启蒙的大众早已不把精英放在眼里,他们需要的是平等,把所有人都拉平、扯平。“奴隶道德、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的相遇并达成惊人一致,生命的酒与火席卷一空。”[14]5大众的时代已经到来。
(二)大众道德或奴隶道德
尼采以“权力意志”的强弱作为区分大众和精英的标准。大众身上存在的权力意志是比较弱小的、基本的权力意志。尼采称之为“虚无意志”、“基本的精神意志”。虽然尼采对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并不全然赞同,但尼采不反对将自我保存视为“权力意志”的一种类型。大众所追求的恰恰是如何能够生存,他们意愿成为一个“末人”,然后去寻找他们所谓的幸福。
尼采认为大众只具有自我保存的生存意志而没有更强大的权力意志。这种弱小的权力意志使大众逐渐制造了有关“恶”和“善”的道德价值和道德判断。大众“把不图报仇的无能吹捧为‘善良’,把怯懦的卑贱吹捧为‘恭顺’,把屈服于所仇恨的对象的行为吹捧为‘服从’。弱者的非侵略性、绰绰有余的胆怯、倚门而立和无法改变的消极等待,在这里还获得了‘忍耐’的好名声,它或许还被称为品德;没有报仇的能力叫作没有报仇的意愿,或许还美其名曰为宽恕……他们还说‘爱自己的敌人’。”[5]28在大众这里,同情、宽容、和平、无害等等只有他们自己身上才有的特性都成了“善”。
奴隶道德的核心是耻感(内疚)、罪感(罪孽)和同情。同情是卢梭道德的重要主题,也是尼采反卢梭的重要原因。尼采认为卢梭是典型的“现代人”,是一个“怪胎”,“理性主义者与流氓无赖集于一身,而且是因为后者之故而成为前者的。”[4]461在尼采看来,自然人的本性是残忍而不是同情心,而且,人恰恰因为残忍而雄壮、高贵。他认为“同情心是一种情感挥霍,一条危害道德健康的寄生虫。”[4]310他甚至认为卢梭式的同情是一种传染疾病,是现代人的三大恶习之一(另外两个恶习是过度劳累和好奇)。[4]477卢梭式的同情以及建立在同情基础之上的道德,否定生命,敌视主人。即便卢梭重视立法家式的天才教育,卢梭对天才的理解与尼采对天才的理解也完全不同。
(三)大众教育
尼采把混杂着苏格拉底问题及柏拉图主义、基督教和民主启蒙气息的大众比喻成“羊群”,有时把大众比作寿命极长且难以灭绝的“跳蚤”。但,尼采并不否认大众的存在价值。大众为社会创造了普遍的利益,他们为社会提供了一种“舒适感”。“常规的持续存在乃是特殊者价值的前提”[4]490。大众又犹如基座一般,让精英在其上立身。“他(精英)需要群众的对抗,需要‘被拉平者’的对抗……他站在他们上面,依赖他们生活。”[15]591既然大众是必要的,就需要为大众提供相应的教育。大众教育的核心是服从,服从教育的基本途径是谎言,一种是宗教(立足于“同情”的奴隶道德)的谎言,另一种是哲学的谎言(求假意志)。
第一,服从教育。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尼采对人的教育有双重特点,要么是‘驯养’,要么是‘培养’。驯养人这种动物,意味着在平均化的意义上使人安静下来或软弱下去。与此相反,培养意味着提高人的水平。他认为这两者都是必要的。”[16]299大众遵循奴隶道德,大众无法承担成为超人的责任,但大众仍然可以被教育,这种教育便是“驯养”。驯养并非唤醒大众,相反,它乃是让大众借助宗教而处于“健康的睡眠状态。”[16]297卢梭在《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化风俗》中把他的同时代人厌恶地称为“快乐的奴隶”。[17]21与之相反,尼采倒是鼓励大众自愿地保持“健康的睡眠状态”。有时尼采也将这种“健康的睡眠状态”称为动物状态。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开篇就提醒说:“想想在那边吃草的那些牲口,它们不知道昨天或是今天的意义;它们吃草,再反刍,或走或停,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忙于它们那点小小的爱憎,和此刻的恩惠,既不感到忧郁,也不感到厌烦。人们在看到它们时,无不遗憾,因为即使在他最得意的时候,他也对兽类的幸福感到嫉妒。他只是希望能像兽类一样毫无厌烦和痛苦地生活。但这全都是徒劳,因为他不会和兽类交换位置。”[18]1
尼采认为,“与少量的命令者相比,总有很多的服从者。”[5]212既要有发号施令者和命令的意志,也需要有服从者和服从的意志。服从乃是大众的本性。[4]325为了让大众心服口服地服从,最好的办法是借用宗教的力量。
第二,宗教式的教育。尼采认为“宗教是庸众的事。”[19]103这个说法既隐含了对宗教的批判,也肯定了宗教对大众的价值。宗教用撒谎满足了大众的需要。“宗教和宗教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把太阳的光辉投到这些总是受折磨的人身上,并使他们本身忍受自己的处境,就像伊壁鸠鲁哲学通常对较高档次的受苦人发挥作用那样,宗教和宗教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提神地、使人有教养地、对受苦仿佛加以利用,最后甚至加以神圣化地和加以辩护地发挥作用。”[5]171这样看来,尼采为大众保留宗教,与康德的思路是一致的。海涅在谈到康德保留宗教时就说:康德虽然袭击了天国,杀死了上帝,但为了他的那个善良的可怜的仆人老兰培那样的人,“使得那个被理论的理性杀死了的自然神论的尸体复活了。”[20]113
第三,求假意志以及喜剧艺术的教育。除了宗教式的谎言,大众还需要哲学的谎言,尼采视之为“求假意志”或“高贵的谎言”。在尼采看来,大众对真理不感兴趣。“绝大多数使更精雅的和更挑剔的趣味,使任何较高级的本性感兴趣和具有吸引力的东西,看来对一般的人来说是完全不感兴趣的。”[5]238查拉图斯特拉下山后,向大众大肆讲解超人的意义和末人的恶劣,但大众反应冷淡甚至还急于把他轰下台,并要他把末人赐予他们。大众更愿意等待一场搞笑的绳索表演。如果说尼采肯定悲剧对统治者和哲人式的精英的教育价值,那么,类似绳索表演的喜剧艺术,构成了大众所需要的教育。大众向查拉图斯特拉推荐一位智者,因为他善于宣讲道德,他帮助大众获得“良好的睡眠”。查拉图斯特拉由此醒悟到“我的嘴对不上他们的耳朵”,“不该向群众讲话”。因为大众“既不喜欢事实,也不喜欢质朴:他们喜欢小说和江湖骗子”[3]811。
三 精英道德与意志教育
尼采认为大众的胜利导致人们只追求什么是善的(平等的),而不再追求什么是好的。[5]280人们只相信相对的平等,而不再相信永恒的普遍的价值。启蒙运动甚至推动了“上帝之死”,导致了“消极的虚无主义”的流行。针对这种消极的虚无主义的流行,尼采发动了一场“积极的虚无主义”——重新评估一切价值,推行精英教育,重建主人道德。
(一)精英的诞生与新生
尼采以自然人和古希腊人为范本,以不同于卢梭的方式,还原精英的形象。尼采心目中的精英虽然也需要受教育,但首先不是教育而是遗传的结果。尼采认为现代教育用一个谎言欺骗了受教育者。“这个谎言就是:根本没有什么可以遗传,一切重要的东西都可以通过教育改变。”[13]214
尼采沿着卢梭的自然主义的方向继续往前走,但尼采嫌卢梭把自然人想象得太“人道”,尼采主张更彻底的自然主义。尼采也讲“回归自然”,但紧接着又说,“这根本不是一种‘回归’,而是一种‘上升’,……在战略上,拿破仑就是‘回归自然’的。”[4]461-462
尼采也以“古希腊人”作为精英的模本。尼采认为古希腊人是迄今为止最高等的人。古希腊人拥有狄奥尼索斯式的诸种美好的品质:“孩子的天性。轻信。热烈。他们在无意识中为了产生天才而生活。冷漠和犹豫之敌。痛苦。自然流露的举止。尽管他们天性乐观,阳光灿烂,但他们却对苦难有一种敏锐的直觉和洞察。他们深刻把握和美化切近的事物(火,农事)。非真理性。非历史性。”[21]39尼采渴望从未来精英的身上发现古希腊人的身影,发现狄奥尼索斯的精神。
虽然尼采把自然人和古希腊人当作精英的范例和模本,似乎也有回到古人那里去的倾向,但尼采意识到,“(现代人)宣称每个人都应该‘自我统治、自我服从’,都应该成为‘自律’、‘自我立法’的平等自由人”[22]145。“奴隶革命”使返回自然、返回古希腊不再成为可能。尼采也并不愿意把未来的精英等同于过去的精英。在尼采看来,如今的人类已经在出发,处在前往未来的途中,这条道路是一个悬挂在深渊上的绳索。精英是应运而生的更强大更高级的类型。尼采把这样的精英的新生称为“超人”,他要教会精英的也是“超人”。精英要向超人靠拢,须实现精神上的三次变形。尼采以骆驼、狮子和孩子比喻这三次变形。[11]23-24终有一天,一个由精英所组成的特选的民族将成长起来,这个民族是“具有自己的生命领域,具有一种力之过剩的种族,一个肯定性种族”。[4]488在此基础之上,将产生出“超人”。
(二)精英的主人道德
尼采认为生命的本性就是“追求权力,追求权力的增加”。[3]1032所谓快乐或幸福,只是权力意志得到满足之后的副产品。“快乐是伴随而来的”,权力意志是快乐的推动力。“一切推动力都是权力意志”,此外没有任何别的推动力。[3]1032主人道德的核心就是追求权力意志。
在尼采看来,权力意志强大的人成为社会的精英,权力意志弱小的人成为社会的大众。大众耗其一生追求如何更好地自我保存,而精英的权力意志则显示为生命本能的勃发。狂野的生命需要与其相配的主人,而唯有精英才与这生命相得益彰。精英的生机勃勃,活力十足,为了权力,精英甚至不惜将生命孤注一掷,让生命沿着上升路线不断上扬。他们显示出“纯洁无邪的精神放荡”,追求性爱和享乐,“首先重视的是身体的优先性”,把婚姻视为“某种根本性的欺骗”。[4]553权力意志不仅使精英超越大众道德,而且使精英不拘泥于实证主义式的经验事实。就认识论而言,每个权力意志强大的人都是一个视角主义者或透视主义者。衰弱的实证主义者拘泥于事实。实证主义“总是停留在现象上”,认为“只有事实”。而尼采却坚持,认识的唯一可能是“解释”而不是“说明”。[4]124“没有事实,而只有阐释。”[4]362-363这种视角主义的解释既来自人的权力意志又增强人的权力意志,并因此而增强生命感。
大众信仰关于“恶善”的美德,把他们不具有的一切说成“恶”,将自己所具有的一切说成“善”。精英把一切大众作为安慰的比较之物置于一边,使用完全相反的顺序,先找到了“好”,顺便设定了“坏”。在精英那里,“坏”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精英只要认为自己是“好”的,那就与“坏”无关。作为“好”的附带品和补充色调,“坏”被精英用以形容那些在他们看来是得过且过的大众,尼采对“坏”的注释是:“胆小如鼠、卑贱、微不足道而且考虑蝇头小利之徒受到蔑视;此外,目光闪烁不定而受到怀疑的人,自甘堕落之辈,甘为鹰犬、狗彘不如之徒,沿街乞讨的马屁精,尤其是撒谎者,同样被嗤之以鼻”。[5]280相反,“好”乃是与贵族身份相关的词语。“好”最初是来源于一个概念的不断转化:社会等级意义上的“高尚”“高贵”等词汇到处都成为基本概念。[5]14
尼采将精英视为了一种“强壮的人的状态”,从而认为“这种人本身将需要、因而将拥有一种使人变得强壮的道德”,[4]567尼采称之为“主人道德”。尼采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史中回溯了大众的“奴隶道德”的起源,同样,尼采也在历史的洪荒时代找到了精英的“主人道德”的源头——对习俗道德的挑战。打破习俗道德意味着致命的危险。但是,总有某种人不愿服从习俗,他们宁愿选择“疯狂”和“自愿受苦”。而随着他们在寻找和确定自我道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离经叛道者也会接受到越来越多习俗道德所给予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和痛苦,但为了换取自我信仰和自我立法,他们选择了“自愿受苦”作为代价,力图成为自己的“主人”。*在黑格尔看来,成为主人的前提条件是“不畏死”。主人道德意味着“强壮有力的体魄,情感豪放的健康”,以保持体魄健康为条件的战争、冒险、狩猎、舞蹈、竞赛和所有包括强壮、自由、快乐的行为。[5]18在尼采看来,“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11]348主人道德显示为生命的自我认可、自我崇拜,将自己当作道德的判定者。“主人道德是身体强加的象征,是升华生命的象征,是作为重要原则的权力意志的象征”[23]63。也正是在这点上,尼采与卢梭分道扬镳。卢梭宣扬平等,尼采宣讲贵族;卢梭讲同情,尼采强调残忍。尼采呼吁人拿出足够强大的权力意志以肯定生命中随时发生的悲剧。
(三)精英的教育
尼采大众教育是对个性、特立独行的反对和反攻。大众教育为了“维护规则”而毁掉“特殊者”。这种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把特立独行当作罪犯来处理和压制”。[4]380与之相反,精英教育恰恰是对个性和特立独行的鼓励和保护。
尼采把意志力教育视为教育的第一课程。在尼采看来,对意志力教育第一课程的轻视和遗忘导致了现代教育的衰败。“我们荒唐的教育界(呈现在它眼前的乃是作为规整模式的‘可用的国家公仆’)相信有了‘课程’、有了脑力训练就足够了;他们甚至理解不了,首先必须有另一种东西——意志力的教育;人们要通过所有的考试,唯独不要这门主课:人们是否能够意愿,人们是否可以许诺:年轻人甚至连对自己的本性这样一个最高价值难题的疑问和好奇都没有产生,就要完成学业了。”[4]635-636
尼采的“意志”来自叔本华。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这是常识,但叔本华第一个为之提供了哲学的论证。意欲得不到满足时人处于匮乏的痛苦之中,意欲得到满足的那一刹那虽然给人带来欢乐,但满足之后又陷入餍足、厌倦的痛苦之中。而且,即便一个欲望暂时得到满足,必有别的更多的欲望依然处于匮乏之中。在人的一生之中,幸福是短暂的,痛苦是永恒的。[24]273叔本华为此提供的哲学解决方案是:只有采取佛教式的消除意志的道路,人生才可能被拯救。叔本华的悲观哲学给尼采带来了智慧的震颤,但,尼采反其道而行之。他保留了叔本华的意志概念,但使之增加了新的内容,并使叔本华消极的“悲观”哲学上升为积极的“悲剧”哲学。如果说,叔本华的永恒轮回打败了他的意志,那么,尼采执意用他的意志打败永恒轮回。叔本华以向悲观的后退的姿势回应永恒轮回,尼采以悲壮的向前进的姿态迎接永恒轮回。
在叔本华和尼采那里,永恒轮回与意志(权力意志)是相反相成的概念。尼采意识到,要拯救和肯定叔本华的意志,必须打败叔本华式的永恒轮回。永恒轮回显然并非由尼采首创,因为它已经隐含在叔本华的永恒痛苦的悲剧哲学之中,甚至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尼采称之为拥有帝王气派的自尊和自信)那里也有永恒轮回学说的影子。赫拉克利特留给后人的著名格言是“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句话表面上强调世界的生成和流变,实际上,它提示了变化的永恒轮回。这种轮回的关键在于:生命之悲壮,如同西西弗斯的石头。于是,尼采对精英提出一个悲壮的教诲:必须用“我意愿”来迎接生命的悲剧感。既然生命就那样地悲壮,何妨再来一次。时刻准备去热爱生命,永不知足地喊“从头再来”。[5]166后来加缪以“西西弗的神话”为尼采式的“永恒轮回”、“永恒地,不知足地喊着从头再来”提供更形象的解释。[25]155-161
精英不仅呼喊从头再来,而且愿意加入古希腊式的“竞赛”。尼采认为竞赛就是古希腊人的生活,古希腊人的生活就是竞赛。每一个荷马时代的希腊人都在竞赛的氛围当中成长。不同的是,古希腊人为共同体荣誉而竞赛,在尼采那里,乃是为了个体生命而竞赛。[26]1-29意志力教育意味着对苦难的超越和自我肯定。在大众寻找“末人”的幸福之时,精英却把“超越北方、冰冻、冷酷、死亡”当作了自己的生命和幸福。“在别人发现是毁灭的地方发现了幸福……他们的快乐乃是自我征服,苦行源于他们自己的天性……调戏压在他人肩上的重担对他们来说乃是一种修养”[27]159
总之,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问题(及柏拉图主义)、基督教和民主启蒙的三次“浸染”导致了奴隶的反叛和大众革命,构建了“奴隶道德”。同时,尼采以自然人和古希腊人为范本设计了“超人”形象和“主人道德”。尼采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教育,一是大众教育,通过宗教、“求假意志”来使大众学会“服从”。二是精英教育,包括“牧人”式领导者的教育和“孤独者”哲人教育。尼采虽然重视精英以及精英政治,但他并非仇视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