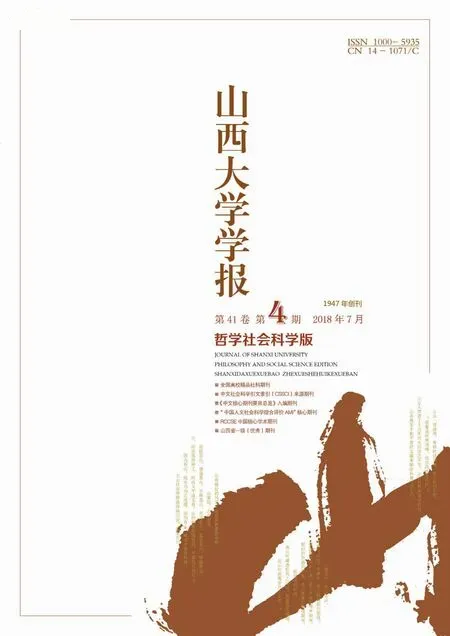论刘慈欣“大艺术系列”科幻小说
——以《诗云》为中心
吴宝林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2015年,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三部曲(原名《地球往事》)获得国际科幻文学界最高奖“雨果奖”。这一文学事件客观上将科幻文学从“边缘文类”提升到与所谓“纯文学”相抗衡的位置。虽然在主流文学界,谈及科幻文学依旧是“科普”或“儿童文学”的刻板印象,既有的文类等级秩序并没有被完全改变,但刘慈欣的出现,确实又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当代文学”的格局与版图,在密不透风的主流知识框架内部署了一个不断扩展的裂隙,重新将人文学的想象力提升到了“世界高度”,再度擦亮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可见度”。
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学界一般集中讨论的是《三体》,而相对忽略刘慈欣的其他中短篇小说。在笔者看来,《三体》并非“横空出世”,其叙事的肌理和创作思路以及对科学与人性的洞察,对社会政治尤其是冷战遗产的关注,在中短篇小说中都有着力描写,并且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三体》是对其前期小说叙事的某种“综合”。本文试图通过刘慈欣未完成的“大艺术”系列科幻小说来分析其创作特征,以中篇《诗云》为焦点文本,从叙事分析延展到科幻文学作为文类的独特性,并探究刘慈欣中断这个系列小说写作的原因。
一 混杂:文体实验与形式创造
刘慈欣的一个创作特点是喜欢写系列小说,按照主题的不同层面来构思自己的作品,这或许也是科幻文学自身的特征。在他的创作计划里,“大艺术”系列小说共有六篇,分别为音乐艺术篇、冰雪造型艺术篇、雕塑艺术篇、绘画艺术篇、文学艺术篇和行为艺术篇,但实际完成的只有三篇,即《梦之海》(2002)、《诗云》(2003)和《欢乐颂》(2005)*《诗云》发表于2003年第3期《科幻世界》,获2003年第15届银河奖读者提名奖;《梦之海》发表于2002年第1期《科幻世界》;《欢乐颂》发表于2005年8月《恐龙·九州幻想》“贪狼号”。。至于中断写作的原因,刘慈欣自述道:“读者并不认同这样的作品,我尊重大家的感受,不会把这个系列写下去了。”*参见:《球状闪电》新闻发布会,http:∥www.xiexingcun.com/zgkh/219.htm,访问日期2016-04-25。事实上,当“大艺术”系列正在构思、还未完全创作出来时,刘慈欣就很兴奋地表示“希望大家喜欢”,并且认为这是他自己“目前最看好的一个系列”。他也毫不掩饰创作的自由畅快与想象力的恣意发挥,认为“这是最能够反映自己深层特色的作品。这两个短中篇(《梦之海》和《诗云》——引者注)描述了两个十分空灵的世界,在那里,一切现实的束缚都被抛弃,只剩下在艺术和美的世界里的恣意游戏,只剩下宇宙尺度上的狂欢(奥尔迪斯一本科幻理论著作的书名)。”[1]但读者却“不买账”,这对于非常在乎读者感受的作家,尤其是从事科幻创作的作家来说异常痛苦。
几年后,刘慈欣自我反思,认为“这种创作是难以持久的”,他在“创作伊始就意识到科幻小说是大众文学,自己的科幻理念必须与读者的欣赏取向取得一定的平衡。”[1]当《三体》在国际上获得雨果奖后,很快就有忠实的科幻迷给予刘慈欣及其作品以历史的定位:“论地位,‘三体’是要进中国文学史的——注意,我说的不是中国科幻小说史。”[2]这似乎又要回到科幻史研究的常见思路上了,即“科幻将自身融入主流,从而获得文学上的尊崇地位的渴望”[3],对自身文学身份充满焦虑与自觉。不过在刘慈欣的意识里,科幻文学终究是大众文学,其“野心”倒并非是要进入主流文学史,而是“把科幻从文学中剥离出来”,其对主流文学的“敌意”也多有流露。在文类等级的意识中,刘慈欣可能更将科幻看作更高一阶的叙事文类:“主流文学描写上帝创造的世界,科幻文学则像上帝一样创造世界再描写它。”[4]
《梦之海》的主题可谓是艺术创作与生存之间的张力,“艺术是文明存在的唯一理由”*引自刘慈欣:《梦之海——刘慈欣科幻短篇小说集》(第2部),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出版。下文所引小说片段除非特别标注,皆选自该书。[5],同时又对这一信仰展开了反讽。来自高级文明的低温艺术家冰冻并运走了地球上的海水资源,在地球轨道创作了精美的艺术品,从而导致地球生存环境日趋恶劣。低温艺术家批判人类艺术家的雕塑说:“过分写实,过分拘泥于形状和细节。当你们明白宇宙除了空间什么都没有,整个现实世界不过是一大堆曲率不同的空间时,就会看到这些作品是何等可笑。”这无疑是刘慈欣以科幻的想象力对所谓现实主义文学追逐细节和模仿的批判。而《欢乐颂》的想象更为奇特,将联合国大会的终结置于一位来自宇宙深处的“恒星演奏家”的审视下,这个灵感似乎来自超弦理论的中译本书名“宇宙的琴弦”。这位“镜子”音乐家在浩渺宇宙弹奏太阳的行动,形成了一个意义坐标系,最终改变了现实世界的轨迹,使得联合国大会得以继续保留而未被废止。小说中的联合国秘书长说,“当文明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它也可能通过反射宇宙来表现自己的存在”,这与“镜子”通过反射太阳光线以此弹奏太阳的方式形成了某种共鸣结构,将文明的生存法则同步于宇宙自然规律的展演,小说这种奇特的并置,不愧为“大艺术”的称号。
在一般读者眼里,《诗云》描述的是“技术与艺术的对抗”,这个主题语也是刘慈欣小说选集本出版社的宣传语。《诗云》的主线故事其实很简单,描写了一个拥有超高级文明、代表宇宙至高智慧的技术之“神”,如何被生活在三维空间的低等文明“人类”(虫虫)的古典诗词所吸引,进而化身唐朝诗人李白的躯体,模仿其行为方式,意欲用技术创造一种实体的“诗云”。这位“李白”将一切汉字组合成矩阵,用量子计算穷尽所有可能的诗,并试图终结诗词创作这个艺术门类,但最后由于无法在“诗云”中搜索出超越李白的诗而宣告失败。在“技术主义者”刘慈欣笔下,似乎“诗意”战胜了“技术”,如物理学家玻尔所说,“进入原子领地,你只能使用诗的语言”[6]。但从技术与诗意对立的角度,是对故事框架简化后的解读方式,并无助于我们对这篇小说包括“大艺术”系列小说的理解,也无助于从根本上把握刘慈欣的写作。
如果换个角度,从叙事或形式层面来解读或许会有新发现,这与刘慈欣小说对“方程式”科学形式之美的呈现也相契合。首先,在阅读《诗云》的过程,读者会直觉地想起鲁迅的《故事新编》所构筑的神话模式,尤其是《补天》。如果说科幻小说的最重要特征是“现代神话”[1],那么在“创世”的主题与叙事手法上,《诗云》所表现出的视角、讥刺、幽默或油滑,与鲁迅的《故事新编》有着潜在的联系,两者都是讲述“创造”的故事。而人类的卑劣品质、那些“小东西”与“虫虫”的称呼也可对应。有趣的是,创世者的命运其实都是“失败”的:女娲劳力而死,“神”被作为“虫虫”的人类“逆袭”,也难逃失败的结局。而且,两者都表现了“神”的有限性,所谓神圣的限制(divine limitation),“神”会被自己的创造物所具有的密集惯性压垮[7],这与“诗云”作为大集合的实体存在何其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刘慈欣的短篇小说《乡村教师》中也曾引用鲁迅的《呐喊·自序》的段落,以在科幻的框架内展开与启蒙叙事的对话。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融入科学幻想,这是刘慈欣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或许可以说,从“现实”起飞,向宇宙纵深作“惊险的跳跃”,由此形成“视差”,这是刘慈欣小说的基本结构。如果做个类比的话,在小说文体发展史上,这也类似于西方哥特小说的出现,如《奥特朗托堡》(the Castle of Otranto)是将现实主义叙事与超现实情节和远古的故事背景结合起来,由此开创新的小说文体[8]。相比而言,刘慈欣在现实主义场景与科幻情境之间常常自由切换,让两种叙事互为背景,这一点在《中国太阳》等小说中较为明显。
进一步看,《诗云》的叙事如同一台戏剧,实际的主角就是三个“人物”:技术之神“李白”、大牙和伊依(按:这位教授古典文学的人,其名字可能是“意义”的谐音)。这是典型的三角人物关系。小说中其实也有这样的暗示:
伊依想到自己正身处距太阳1.5 个天文单位的茫茫太空中,这个无限薄的平面(即使在刚才由纯能量制造物品时,从远处看,它仍没有厚度)仿佛是一个漂浮在宇宙深渊中的舞台,在它上面,一头恐龙、一个被恐龙当做(作)肉食家禽饲养的人类、一个穿着唐朝古装准备超越李白的技术之神,正在演出一场怪诞到极点的话剧,想到这里,伊依摇头苦笑起来。*引自刘慈欣小说《诗云》,见:《镜子》,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年出版。下文引用该书不再单独标注。[9]
这是在“宇宙深渊中的舞台”,上演的一场怪诞话剧。虽然场景会时而变化,但结构却是固定的。大牙这头插科打诨的恐龙扮演的是小丑的角色,正剧则是围绕技术之神与伊依之间展开的。恐龙处在四维世界,而人类处在三维中,这是对历史现实的一个“颠倒”。这种“颠倒”的机制实际上是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核心,也是其主体塑造、讲述历史现实的关键。神“降格”“降维”为李白后,无疑是人格化的技术,可以说是占据了人的主体性和历史性。在描述完空心化的地球之后,小说开场部分最后一句话是:“这就是新世界的创造者,伟大的——李白。”这位技术之神创造了这个“新世界”,而伟大的李白也是新世界的创造者,两个新世界在此仿佛融为一体。
再者,《诗云》也可看作是童话寓言的结构。人类的逆袭既打败了“神”,也嘲弄且借助神之手毁灭了大牙的帝国。这就像是格林童话《农夫与魔鬼》中,农夫用自己耕田的艺术打败了魔鬼一样。这一点还可以从《诗云》结尾所暴露的童话式结局看出来,而这个结尾也已经成为今天的网络流行语:
“我和那位村姑后来怎样了?”伊依好奇地问。
在诗云的银光下,李白嘻嘻一笑:“你们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是伊依所有可能生活中的一种。这个结尾貌似展示了人类未来的乌托邦世界,大团圆式结尾,如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所描述的那种(以喜剧的形式出现的)结尾——“最后分发奖品。有抚恤金、丈夫、妻子、孩子、数以百万的票子、附加的段落和令人鼓舞的言论”[10]。实际上,“诗云”不仅穷尽了诗的可能性,还穷尽了生活的可能性,因此这个结尾确实是一种“终结”,而不是完满。除了上述结构,这篇小说同样遵循了神话故事中“愿望”的辩证性:“一种满足总是伴随着一种特别不受欢迎的附属效应,人们希望消除这种效应的话,也必须遵从这个顺序(放弃这一满足也会带来另一个不想要的结果)。”[11]
在这篇科幻小说中,也包括《梦之海》和《欢乐颂》,刘慈欣融合了戏剧、寓言、童话、神话等各种文体,层层叠加嵌套,构成一种混杂的面貌。这已不是对现实本身的模仿,而是对文学(艺术)丰富复杂性的展示,“文学的命运”不仅是“诗云”作为诗词集合体的失败映照出的,而且是其自身参与到这种对失败的展示中,通过这样一个混杂的框架,逼近文学(艺术)“自身”。正如刘慈欣的自述,“科幻文学可以是任何文学”[12]。
实际上,恐龙大牙对古诗的解释显得异常“先锋”,用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的术语即是“陌生化”(“奇特化”),“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13]。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中略)
大牙解释说:“它的意思是:恒星已在行星的山后面落下,一条叫黄河的河流向着大海的方向流去,哦,这河和海都是由那种由一个氧原子和两个氢原子构成的化合物质组成,要想看得更远,就应该在建筑物上登得更高些。”
这种解释模式其实不同于科幻文学理论上常采用的苏恩文的术语,虽然两者的英译词是一致的:Estrangement。按照苏恩文的看法,科幻文学作为文类,根本的条件是某种疏离(陌生化——引者注)与认知的互动,其主要的形式方法是用一种想象的框架代替作者的经验世界[14]。苏恩文的落脚点在于科幻文学的整体结构上。大牙对古诗的解释类似于古诗的白话翻译,只是这种解释混杂了科学术语,将人间意象“还原”成了宇宙的宏大事物,在空间上其实超出了人类的感知范围,造成了某种奇特的感官体验,去掉了本雅明意义上的“灵晕”。我们可以将之命名为“大牙阐释学”。如果说大牙的阐释还运用到“还原”的程序,显出某种诚实的话,那么伊依在阐释那首量子计算机写出的第一首诗“啊啊啊啊啊”时,就透露出理性的狡黠与反讽,甚至可以说,“伊依(意义)阐释学”本身就是刘慈欣对当代文学及批评的一种戏仿。面对伊依这个“虫虫”的解释,“李白”显得很高兴很满足,这里的描写也是相当准确的,揭穿了技术之神的“鉴赏力”,因为鉴赏或体验是与第一人称直接相关的,与主体相联系。这相当有趣,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文学的机制。
二 “透明”叙事:特别的想象机制
《诗云》开头部分描写了地球变成气球之后的景象:“今天,天空和海水都很清澈,对于作诗来说,世界显得太透明了。”同样,《欢乐颂》中那个恒星演奏家(一面镜子)则是“宇宙中最光滑、最光洁的表面”,而“这个东西没有厚度”。刘慈欣似乎对“透明”有一种特别的期待,这不仅是指他的科幻作品中不断描写到宇宙中透明的事物,也是说他的某种想象方式与现代主体的基本形态和相应的语言机制密切相关。
现代主客体认识论的一大前提即是笛卡尔式的透明、实体化的、完全拥有自身意识的主体,它能彻底控制其命运之“我”[15]。在某次采访中,刘慈欣认为“科幻文学的语言,一大要素就是透明。你让读者直接看到的是内容而不是语言,科幻是内容文学,不是形式文学,我的语言努力想做到这一点,让读者忘记你的语言,看到内容。”[16]这种对语言透明性的追求相当自觉,而这种透明性对应的也是对主体的想象与塑造。我们知道,(西方)现代主义的一大追求是回到自然、追求透明与无中介,这既是对主体的想象,也是对再现主体的语言本身的要求。而前现代的语言观即是认可语言的透明化,将语言等同于观念[17]。这里,刘慈欣想象了某种透明的语言机制,可以直接将文学的“内容”呈现给读者,并与读者进行“交换”与“对话”。这如同刘慈欣写作中的“上帝视角”,可以同时看见过去与未来,“站在同时可以看见两个过程的地方”,在这样的观照下,“历史也是透明的”[18]。《诗云》中的地球“被掏空了”,变成了气球。那个“宇宙深渊中的舞台”,是“无限薄的平面”,“没有厚度”等等,这些小说中描写到的细节也印证了上述机制。
事实上,《三体》中最关键的一个细节是关于思维的“透明”与否,这甚至关乎文明根本的差异及其存亡。三体入侵者的思维是“透明”的,这也对应着面壁者与破壁人之间的激烈交锋。这是小说中非常具有想象力的设置。因此,小说对“透明”机制的呈现也是双重的,既有具体宏观细节与微观事物的描绘,也是对某种想象力的自觉实践。某种意义上,科幻小说的诞生即来自这种“透明”的欲望与神秘感。刘慈欣将艺术与科学进行有机融合,创作“大艺术”系列小说,或许也是意识到这之间的“透明”或“不透明”的媒介关系。正如诺贝尔奖得主和科幻小说迷赫尔曼·穆勒所言:“透过科学的眼睛,我们愈来愈领略到:现实世界并非如人类童年时所见的、秩序井然的小花园,而是一个奥妙绝伦、浩瀚无比的宇宙。如果我们的艺术不去探索人类正在闯入这大千世界时所碰到的境遇及反思,也不去反映这些反思带来的希望和恐惧,那么,这种艺术是死的艺术……但是人没有艺术是活不下去的。”[19]《梦之海》中所谓“艺术是文明存在的唯一理由”虽然遭到嘲笑,但最后人类还是要“重新把自己从一群大灾难的幸存者变目为艺术家”。
此外,“透明”还与写作的“轻逸”有关。卡尔维诺论述过“轻逸”的写作,而他也是幻想文学这种文类的实践者:“当我觉得人类的王国不可避免地要变得沉重时,我总想我是否应该像柏尔修斯(柏尔修斯是希腊神话里的人物,他有双飞行鞋,砍下女妖的脑袋后借飞行鞋远走高飞)那样飞向另一个世界……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以另外一种逻辑、另外一种认识与检验方法去看待这个世界。”[20]这种快乐的“轻”并不是单纯的“娱乐”体裁,而是具有严肃思考的文学。从某种意义说,《诗云》可以看成是刘慈欣科幻小说的元叙事,结构上具有寓言性质。同时,也可以看成关于文学(艺术)自身的叙事,甚至是后现代文学理论的隐喻,所谓文本与作品的区分,前者是语言的编织体,那里没有“作者”,不是因为“作者已死”,而是因为“作者”是量子计算机。
刘慈欣曾回忆自己看球赛的情景,他望着球场,球员的动作细节他都看不见,只能看到球场上23个点:“我后悔没有带望远镜。但同时由于细节的隐去,球赛呈现出清晰的数学结构。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星空的样子。”[21]《诗云》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描写,与作者的现实经验不谋而合:
飞船前方那两个发出白光的物体,那是悬浮在太空中的一个正方形平面和一个球体……那个完美的球体悬浮在平面上方,两者都发出柔和的白光,表面均匀得看不出任何特征。这两个东西仿佛是从计算机的图库中取出的两个元素,是这纷乱的宇宙中两个简明而抽象的概念。“神呢?”伊依问。
“就是这两个几何体啊,神喜欢简洁。”
表面上,这是表达了数学、技术之美,但又不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模型,是某种想象出的几何造型——这种形式主义的“意志”同样可以出现在对文本自身的构造上,这与上文所述的“透明”机制也密切相关。在《SF教——论科幻小说对宇宙的描写》一文中,刘慈欣有一段特别动人的回忆:“记得二十年前的那个冬夜,我读完那本书(按:《2001》)后出门仰望夜空,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脚下的大地变成了无限伸延的雪白光滑的纯几何平面,在这无限广阔的二维平面上,在壮丽的星空下,就站着我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人类头脑无法把握的巨大的神秘……”这个切身经验如放在小说中,不啻是经典的“风景”机制,即主体的“颠倒”机制。或许是由于科幻文学特殊的想象方式,个人自我在面对头顶之上的宇宙时,似乎可以直接相通,一种“类”宗教的方式,所谓“SF教”。
幻想文学的这种超越性视角,可以将微观事物与宏大叙事(事物)的关系颠倒或重新安排其中的空间关系。因此刘慈欣说可以把“对历史的大框架叙述成为小说的主体”,既可以浓缩,也可以无限放大。看不见的结构与看得见的“诗云”,呈现有趣的对应。“诗云”作为具象化的实体,却并不构成诗的来源,因为无法检索出来,更无法成为判定诗的好坏的标准,因为一切都“取决于时间”。正是因为“诗云”穷尽了所有的可能性,成了必然性的牢笼、形式的牢笼,排斥了连上帝都无法预测的偶然性,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所以小说的结尾只能是童话式的结尾。
如上文所述,科幻小说重新建立了纵向的联系。如果说横向的联系是社会关系的重构,那纵向联系除了宗教意义,更主要的是为自我的主体世界建立精神上的坐标,将个人从这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中超拔出来。所以主体在宇宙这种级别的俯照之下,自然是微弱尘埃的。刘慈欣曾说自己刚开始创作理念的最大特点就是对人和人的社会完全不感兴趣。《诗云》借伊依之口说:“他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并不在意。”到创作的第二阶段,这种横向联系才由被迫变成自觉,而后来刘慈欣又反思了第二阶段的创作理念,还是决定回到初衷。在纵向上,这种主体甚至不是个人的主体,而是人类作为一种生物意义上的存在及其创造的文明的总和。如果说理想的文学是要再现出“世界的总体性”,那么科幻文学则进一步将宇宙的总体性展示了出来,这种总体性之下,主体的再现机制、想象方式等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那么,“幻想使我们更具批判性还是仅仅使我们更唯我独尊、自我放纵,最终取决于它是否可以解释那些非幻想的事物”[22]。也就是说,科幻文学的重点或许并不在于描绘未来,而是在对现时的“想象”,套用齐泽克的话说,“想象世界的终结甚至比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都要容易得多”*转引自周秀菊:《詹姆逊文化批判思想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第172页。。《诗云》中“终极吟诗”一章描写地球恢复原状后,人类的感受与伊依的区别:
在返回地球的途中,人类普遍都很沮丧,但原因与伊依不同:回到地球后是要开荒种地才有饭吃的,这对于已在长期被饲养的生活中变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们来说,确实像场噩梦。
但伊依对地球世界的前途充满信心,不管前面有多少磨难,人将重新成为人。
“开荒种地”“五谷不分”等话语揭示出这是典型的“劳动”画面。小说这个结尾的处理极有意味。“人将重新成为人”,如果不仅意味着从“虫虫”的动物性复归到“人性”,而且也意味着恢复(地球)世界的总体性的话,那么《诗云》也就重新夺回了那个创造的“新世界”。
三 结语
未完成的“大艺术”系列科幻小说,在刘慈欣的创作谱系里,占据重要的位置。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他是要将“禁锢里冷酷的方程式”中的“伟大故事”解放出来,将“相对论诗一样的时空图景,量子力学诡异的微观世界”用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诗云》及《梦之海》《欢乐颂》所运用的想象,也证明了“物理即伦理”的文学机制。而文体的混杂本身就是试图对既有文学样式和认知的超越。
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观点看来,现代艺术是表象艺术,具有含混朦胧、非确定的意义,科学是探究实在事物。到了现在,这种趋势也在改变,尤其是近年来的现代装置艺术和认知主义科学的发展,改变了既有的评价模式[23]。正如齐泽克所言,科学追求和谐平衡之美,如相对论和超弦理论,后者如格林(Brian Greene)的畅销书《宇宙的琴弦》(TheElegantUniverse),而现代艺术则使人痛苦。但现代认知主义科学尤其是脑科学对人的主体存在持怀疑态度,试图将“意义视域”从主体之中切割出去[7]。在《诗云》中,对“意义”的悬置也是“诗云”得以生成的前提。在这种模式下,“人类的思维被视为对计算机运作的模仿”(而不是相反),典型者如前段时间的“人机大战”,阿尔法狗战胜了世界围棋冠军。《诗云》中,一方面是“诗云”的“默默运行”,另一方面是技术之“神”即使化身李白,也无法体验“意义”(experience of meaning),从这一点上说,刘慈欣的小说才正是“古典”的。
——徐诗云素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