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实”与“叛逆”
——以葛浩文《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例
陈 达 高小雅
(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成都 610039)
一、“忠实”与“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这个概念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1918—2000)在其《文学社会学》(Sociologiedela littérature)中提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1]33。我国学者谢天振教授对于“创造性叛逆”概念非常赞同并在《译介学》中对此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阐释。谢天振教授指出,“创造性叛逆”概念尤其抓住了文学翻译的灵魂[1]33。这个观点无疑为文学翻译绝对“忠实”和“二次创造”的争论提供了新参考。
“创造性叛逆”强调翻译文学与文学不能直划等号,这肯定了译者再次创作的重要贡献。西方翻译学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进行了文化转向的研究,并于90年代末完成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就文学翻译中译者“能否二次创作”这样较为“带刺激性”的话题而言,美国著名诗人、翻译家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提出了“历史的可译性”概念和“译作既是新作”的原则[2]58。英国诗人、评论家、剧作家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认为,“每个时代都必须有自己的翻译”[2]58。国内也有著名翻译家表明,翻译只有插上“创造性”的翅膀才能在新的语言里让原作二次投胎获得新生[3]10。“二次创作”主要围绕作者创作意图和文本本意进行推敲,并深掘字面背后的文化内涵和本质意义,再以“新面貌”重现,从而更好地横贯古今和融合中外。
近百年来,“忠实”在翻译里占据了绝对性的位置。我国古代翻译家支谦(约3世纪)等人认为,“辞达而已矣”,并强调在这一原则下翻译要原原本本传递原文的意思,丝毫不得加入其它粉饰[4]79。清末时期,我国外交家、学者马建忠(1845—1900)提出“善译”,即在确定明白原文所指的基础上,绘声绘色地准确传递出原文的神韵,这样的翻译才是“善译”[5]82。17世纪,法国著名翻译家和翻译思想家达尼埃尔·于埃(Daniel Huet,1630—1721)认为,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不要施展自己的写作技巧,也不要“叛逆”地掺入译者自己的东西去欺骗读者,因为他要表现的应该是原作者的风采,而不是他自己,而是应当遵循“一分不增,一分不减”的标准[1]38。所以,在这种传统翻译学的背景下,翻译家们始终如一地忠实于“一分不增,一分不减”原则,将源语和译入语进行完全的对应,秉承“忠实”的理念,不做任何改变,只将原作单纯转换为目的语传达给读者。
综上所述,“叛逆”和“忠实”看似是一对矛盾,也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在没有预料到的新语言环境下“叛逆”,但又不是胡乱的“背叛”,能否反映出内涵,即“忠实”地表达出原文实质和原作者意图才是关键。“创造性叛逆”的降临对于翻译界而言是非常宝贵的概念,为译者困境提供了新出路。
二、葛浩文的翻译观
美国著名的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 1939—)认为,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出发,翻译是对原作的一种“救赎”而非“背叛”[6]72。“背叛”的帽子太沉重,因而译者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完全按照原文一一对应,译作会显得“死板呆滞”;如果进行“二次创作”,又会被批判为“肆意妄为”。葛浩文用“救赎”来形容,无疑肯定了译者的贡献,这意味着译者将帮助原作“增添色彩”,让古今和中外文化融合,扩大读者群规模,从而提升国际影响力。此外,葛浩文还认同出彩的翻译能够让一部旧作重获新生,并推动文化“走出”国界[6]73。只有在翻译能传播精髓的前提下,才能融合不同国度的文化,实现“海纳百川”,成为一种可持续而又强大的生命力。
虽然葛浩文肯定译者主体性地位,但也强调“忠实”是十分重要的前提。学者孟祥春把葛浩文的这种翻译标准总结为“忠实”前提下的“可读、平易、有市场”[6]74。没有“忠实”的基本保障,译作好似“无本之源”。“可读”意味着译者不能机械对应原文与译作,否则会造成作品枯燥乏味没有吸引力;“平易”则要求译者不能用过于难懂生涩的词句给读者带来理解障碍;“有市场”说明译者选择的作品应满足目标语读者的喜好,译作内容要被读者所接受和认可这样的要求看似平淡无奇,而对于译者而言难度却相当高。葛浩文在翻译实践中很好地处理“忠实”与“创造性叛逆”的关系,高质量地完成英译创作。
三、翻译中的文化传播
《生死疲劳》作为我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代表作,涵盖了很多文化负载词,有着浓厚的民族特色。这种独特的文化特色会因为中西文化的不同而造成翻译的障碍,所以译者需要了解源语背后的文化。美国语言学家、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Nida,1914—2011)在《翻译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of Translation)一书中把文化因素分为:生态文化(Ecological Culture)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社会文化(Social Cu ture)、宗教文化(Religious Culture)和语言文化(Lin guistic Culture)五类[7]。翻译家葛浩文熟知西方文化和读者的喜好,同时由于大量的翻译实践具备中国文学翻译的经验,在克服文化障碍促进中国文化远传西方作出了努力。
(一)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是指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保护生态环境、追求生态平衡的一切活动和成果,也包括人们在与自然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8]326-328。生态文化对各民族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民族习俗和习惯方面会各具特色。如果对异域文化背景不了解,译者面对这样的生态文化翻译可谓满路荆棘。
原文呈现出当时的地理生态环境,拖拉机是主要的交通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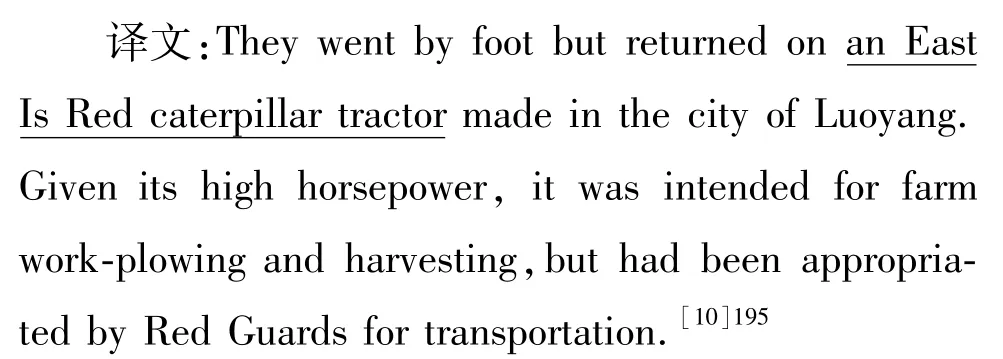
译文对原文逐一翻译,展现原生态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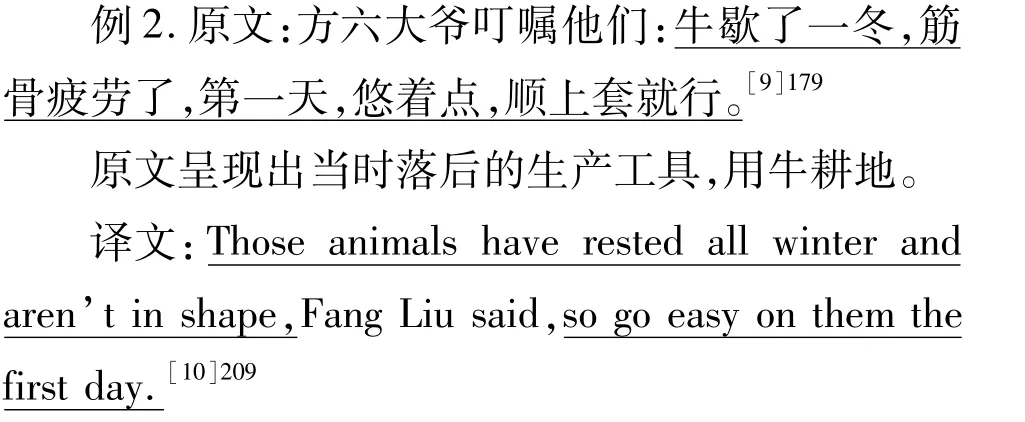
译文对原文的生态意象进行对应。此处表现出在没有影响外国读者理解这种“生态文化”的前提下,“创造性叛逆”地将“牛”译为“animal”,将“筋骨疲劳了”意译为“aren’t in shape”,将“第一天,悠着点,顺上套就行”意译为“so go easy on them the first day”。noxious fumes.[10]234

译文采用意译的方法。译文中将“通风透气”“采光良好”用简单词汇“airy”(通风的)和“sunny”(阳光充足的)表达,将“所有建筑材料都是环保型的”创造性地译为“constructed of environmentally appropriate materials”(由环保材料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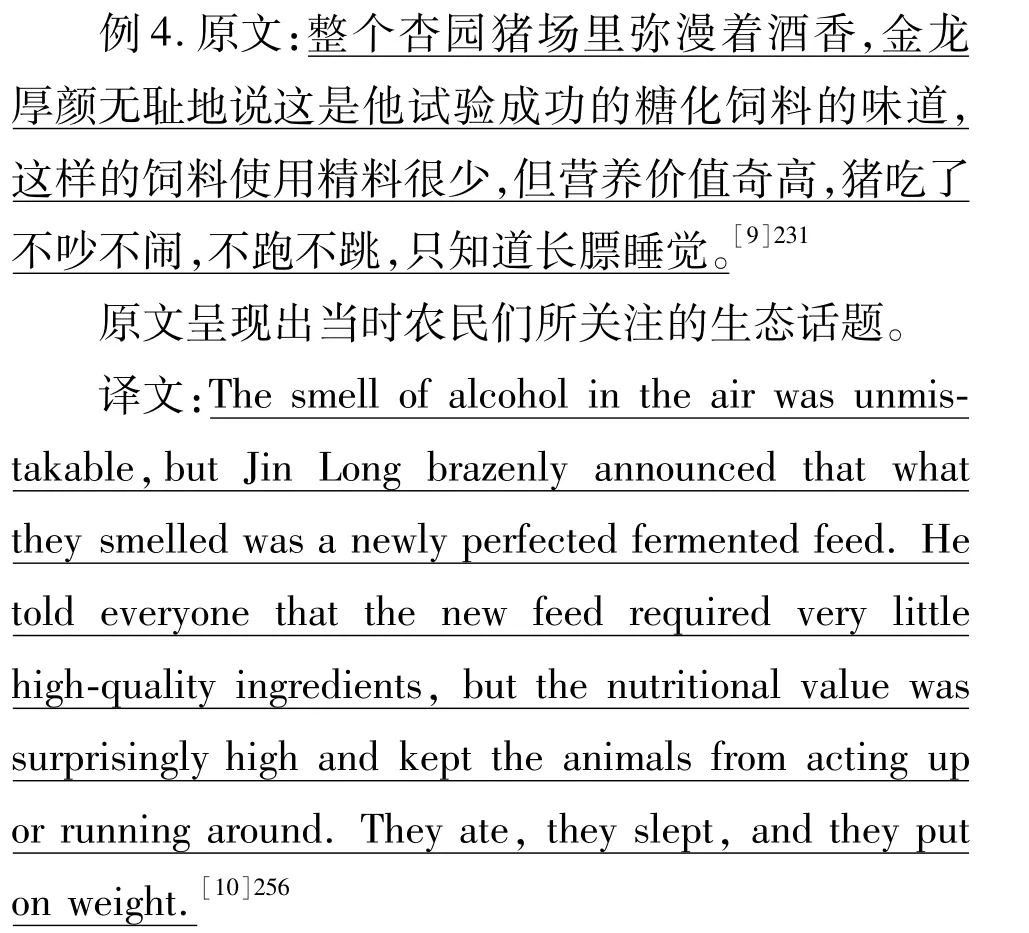
译文中将“整个杏园猪场里弥漫着酒香”译为“The smell of alcohol in the air was unmistakable”,将“糖化饲料的味道”译为“a newly perfected fermented feed”,将“这样的饲料使用精料很少”译为“the new feed required very little high-quality ingredients”,将“猪吃了不吵不闹,不跑不跳,只知道长膘睡觉”译为“kept the animals from acting up or running around.They ate,they slept,and they put on weight”。译文采用翻译中的归化策略和意译的方法,“创造性叛逆”地进行很好的翻译。
莫言以故乡山东省高密县为《生死疲劳》的创作背景,作品中充分反映出胶东半岛与山东内陆结合部的生态环境,那里气候宜人,四季分明,雨量集中,雨热同期。葛浩文很好地处理了“忠实”与“叛逆”的关系,原汁原味地传达出原作的乡土气息,传播原作的生态文化。
(二)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指物质生产、物质生活及其行为与成果,包括劳动工具、食品、居室、衣着、服饰、日用器皿等[11]475。物质文化在中国文明与世界文化融合里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虽然一种物质在不同的文化中不一定存在对等物,但如果“胡翻”“乱翻”,会使原文本意遭到曲解,不利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所以,翻译需要力求精准,避免读者产生误解,影响文化传播与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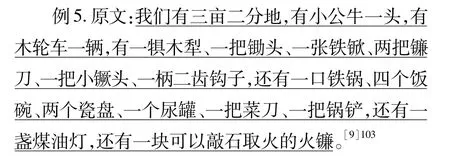
原文呈现出当时落后的生产工具和日用品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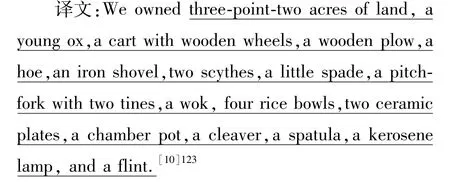
译文采用直译方法,保持原文的文化特色。
例6.原文:互助提着一桶饲料到达圈门。她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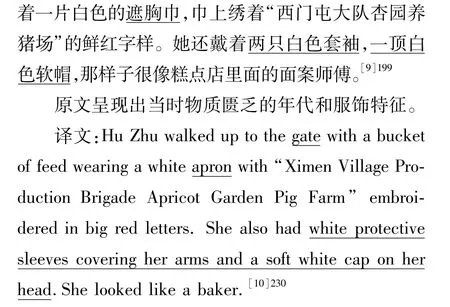
原文中“圈门”应该是“猪圈门”(sty,pigsty,hog-lot,hogcote,hogpen,pigpen),译文创造性叛逆地译为“gate”;译文将“遮胸巾”创造性地译为“apron”。译文注重服饰传神,形象生动地再现原文的服饰文化。但出于对外国读者的考虑,将“两只白色套袖”创造性地译为“white protective sleeves covering her arms”,并与后面的“一顶白色软帽”“a soft white cap on her head”表达方式一致。
例7.原文:我的房子后边是一棵大杏树,半个树冠笼罩在圈舍的上空。圈舍是敞开式的,后檐长,前檐短,阳光可以无遮拦地照射进来。圈舍的地面全部用方砖铺就,角落有洞,洞上架铁箅子方便粪便流出。[9]204
原文呈现出当时的圈舍建筑和圈舍周围的生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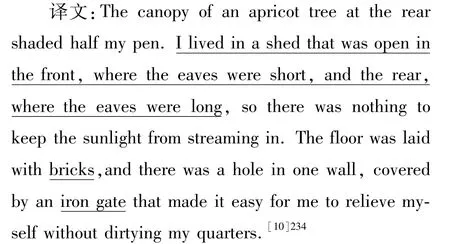
译文对原文中“方砖(square brick;square tile quadrel;square stone)”的形状省略,用“brick”译出将“洞上架铁箅子”创造性叛逆地译为“iron gate”译文采用直译与创造性意译相结合,保持原文的物质文化特色。
《生死疲劳》诉说着1950年至2000年中国农村面貌的变迁,阐述农民与土地这个永恒的话题译文通过“忠实”与“叛逆”,生动再现原文的服饰衣着、生产工具和日常用品等物质用品。
(三)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是人们的价值观、思想、态度、道德规范、风俗习惯及社会行为等的综合体,它是人们生活在某种社会中,久而久之必然会形成的某种特定文化[12]32。所以,优秀的社会文化的翻译可以折射出源语国家的独特文化。

原文呈现出当时存在的少数消极社会文化。如“猜拳行令”即“划拳行酒令”,形容宴饮欢畅;“玩弄野‘鸡’”即和野姑娘嬉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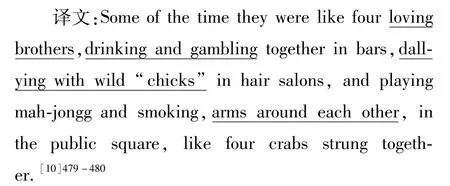
译文直译与意译相结合,注重文化传递,如将“亲兄奶弟”“猜拳行令”“勾肩搭背”创造性地意译为“loving brothers”“drinking and gambling”“arms around each other”;将“玩弄野‘鸡’”直译为“dallying with wild‘chic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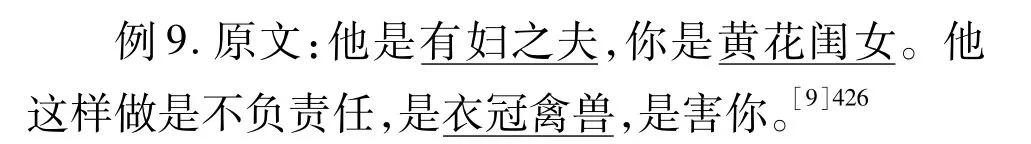
在汉语中“有妇之夫”和“有夫之妇”即表示有家室的人,“黄花闺女”即表示还没婚嫁的女孩子,有时表示处女,“衣冠禽兽”即表示徒有其人的外表,行为却如同禽兽,指品德败坏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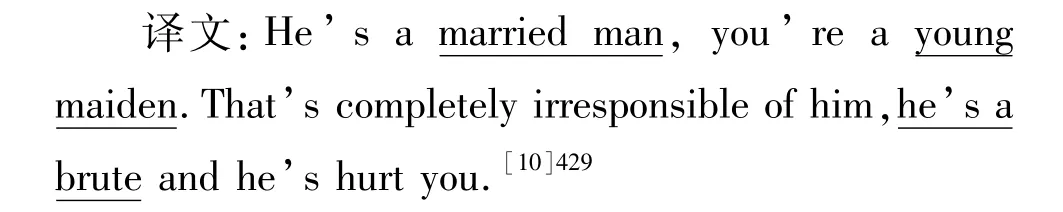
译文通过直译、意译的翻译方法,采用简单词汇,有效地传达原文含义。汉语喜欢“四言八句”,如上例“有妇之夫”“黄花闺女”“衣冠禽兽”,含义深刻;而英语喜欢言简意赅。因此,译文采用“归化”性翻译策略,在直接准确地传达原文语义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阅读理解。
葛浩文深谙中国文化,通过直译、意译等不同的翻译方法,有效地帮助外国读者理解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
(四)宗教文化
宗教文化指由民族的宗教意识、信仰所形成的文化以及外来宗教(如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等)对本国影响所形成的文化[13]54。莫言小说《生死疲劳》通过西门闹冤死到六道轮回,从驴、牛、猪、狗、猴和大头婴儿的视角去描写从1950年到2000年中国社会的变革,葛浩文的译文帮助了中国文化进入异域文化的视线。

在中国宗教和民间传说里,人死后经过“奈何桥”转世投胎,而在桥边驻着一位年长的女性神祗“孟婆”,她专为每个前往投胎的灵体鬼魂提供“孟婆汤”,以遗忘前世的记忆,更好地投胎转世到下一世。“望乡台”就是鬼魂在阴间眺望阳世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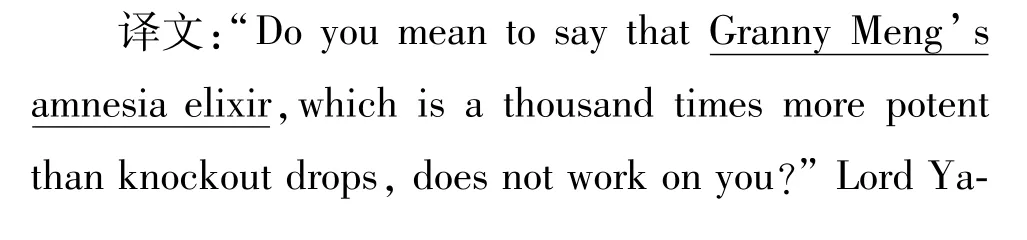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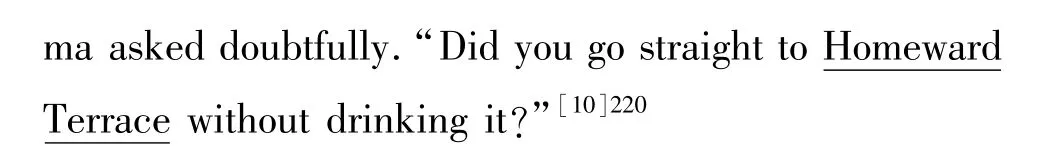
译文保留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贴切地向外国读者传递了中国宗教文化和民间神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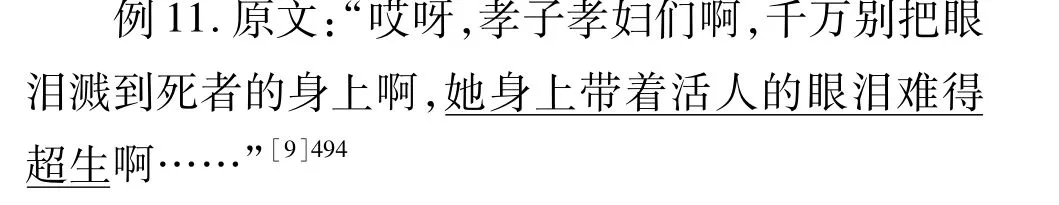
在中国宗教和民间传说里,如果死人身上带着活人的眼泪,就很难转世投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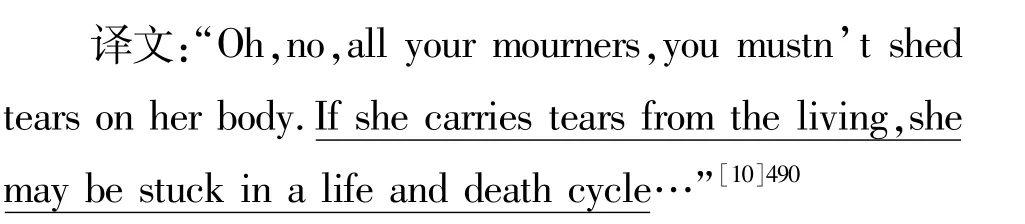
译文采用意译的方法,有效表达这一民间传说。
在中国宗教和民间传说里,人死后要去阴间报到,接受阎王的审判。“阎王”与希腊神话中的冥界之神哈德斯(Hades)相似。
译文:“There are too many,far too many,people in the world in whose hearts and hatred resides,”Lordsaid sorrowfully.“We are unwilling to allow spirits who harbor hatred to be reborn as humans.Unavoidably,some do slip through the net.”[10]510
译文采取翻译中的异化策略,直接选取“Lord Yama”表达“阎王”,传递佛教文化。
佛教、道教和儒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葛浩文将自己领悟到的中国文化,生动贴切地传播给国外读者,成功构建跨文化之桥。
(五)语言文化
语言文化是最基本的文化。语言的产生、运用和发展有着丰富的文化现象,这类文化现象叫做“语言文化”。语言文化通过逻辑方式和修辞手法等表现出来[14]60。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不同语言的转换需要熟知其语言特点,以便翻译将民族文化信息传达给异域读者。
“不倒翁”是中国一种古老的儿童玩具,利用重心原理,不论怎么触动其摇摆,最后始终处于直立状态。在中国语言文化里,“不倒翁”通常是贬义词,比喻某些有权位的人,善于应付环境,始终处于不倒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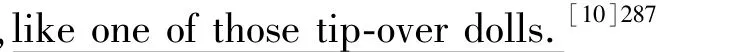
译文创造性地将“仿佛一尊挨了巴掌的不倒翁”译为“like one of those tip-over dolls”,消除了外国读者的文化障碍,符合他们的阅读习惯。
例14.原文:我的神经像葫芦蔓子一样坚韧粗壮,吊着十几个葫芦在风雨中打秋千都不会断。[9]269
原文独具口语化特色,形象生动。
译文:My nerves are as thick and tough as gourd vines,which won’t break even when supporting a dozen gourds that swing back and forth in the wind.[10]294
译文充分保留了原文的语言文化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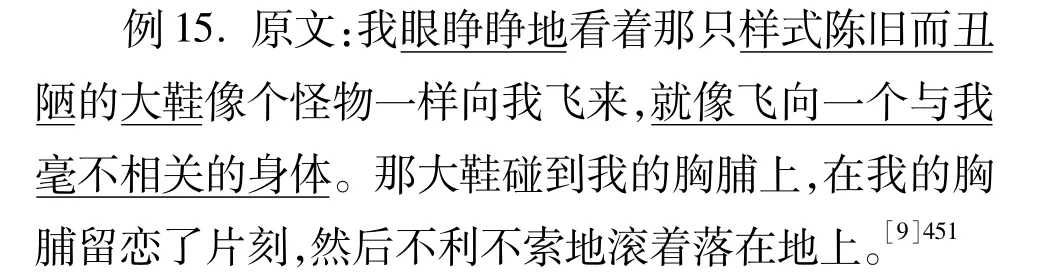
汉语口语方言中“眼睁睁”、“眼巴巴”,通常表示“没有办法”或“无动于衷”或“无可奈何”之意;“不利索”、“不利不索”表示“不灵活”或者“不敏捷”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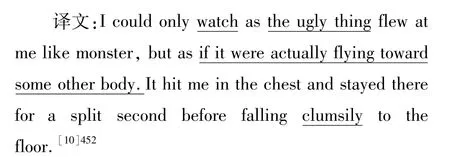
译文有效地回避了汉语口语方言,消除外国读者的文化障碍,符合其阅读习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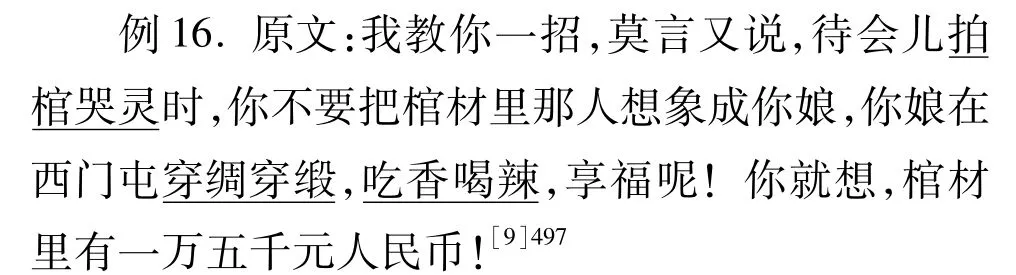
“拍棺哭灵”指在死者灵柩或灵位前痛哭。“绸缎”泛指丝织物,中国古时有钱人家用此做衣料,“穿绸穿缎”表示衣着华丽。“吃香喝辣”即吃美味佳肴,喝昂贵美酒。
译文:Here’s the trick:do not mix this woman in the coffin up with your own mother,who’s back home

译文省译“拍棺哭灵”,直译“穿绸穿缎”,意译“吃香喝辣”,整个译文传神达意。
除以上典型例子外,《生死疲劳》中还有很多的文化负载词(句),葛浩文进行了有效地翻译,例如:
直译:“红木太师椅”(the mahogany chair)、“八仙桌”(an octagonal table)、“火上浇油”(adding fu to the joyous fire)、“天津卫十八街的大麻花”(frie fritters on Tianjin’s Eighteenth Street)、“把头摇得如货郎鼓似的”(shook his head like one of the thos stick-and-ball toys)、“死猪不怕开水烫”(Like a dea pig that’s beyond a fear of scalding water)。
替换:“银元宝”(silver coins)、“金锞子”(gol ingots)、“挥金如土”(spending money as if they had to burn)、“阴曹地府”(the underworld)、“解铃还需系铃人”(he’ll save the day.)、“黄泉路”(th Yellow Springs of Death)。
注释、释义:“文房四宝”(writing brush,in stick,ink slab,and paper)、桃花运 (be lucky i love)、“画蛇添足”(unnecessarily)。
意译:“五子祝寿图”(a longevity scroll)、“六畜兴旺”(the yard was filled with farm animals)、“石头蛋子腌咸菜,油盐不进”(stubborn)。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葛浩文对文化负载词翻译问题处理十分恰当,有效地传播源语文化,实现了翻译目的。当然葛浩文在翻译中有时过分强调译作读者的接受问题,而出现的删译现象,颇受争议。如,

葛浩文翻译出版了中国30多位作家的50余部小说,译作享誉海外,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家
对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他的翻译实践中,葛浩文不断探索“忠实”与“创造”、“忠实”与“叛逆”间的处理策略。葛浩文洞悉汉英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在“忠实”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强调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探索“创造性叛逆”的真谛。葛浩文是翻译莫言作品最多的英语译者,他翻译的《生死疲劳》被《华盛顿邮报》推荐为世界优秀文学作品,同时莫言由此获得首届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更值得一提的是葛浩文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出一定的贡献。葛浩文译作的成功除了他具有深厚的英汉语言与文学功底意外,还有如下因素:一是对中国文学的热爱;二是对译作读者强烈的责任心。当然,葛浩文虽然一直秉承“忠实”原则,但在他的译作中仍然存在“叛逆”过度以及过分强调译作读者接受度的问题,由此,损失的中国文化元素值得商榷。
[1] 谢天振.创造性叛逆:争论、实质与意义[J].中国比较文学,2012(2).
[2] 赵丽娜,邹德刚.情绪与意境的传递——浅析庞统翻译理论中对译者职责的规约[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8).
[3] 郭建中.创造性翻译与创造性对等[J].中国翻译,2014(4).
[4] 王福美.辞达而已矣——重读支谦的《法句经序》[J].上海翻译,2011(4).
[5] 顾卫星.试论马建忠的“善译”理论[J].江苏大学学报,200(6).
[6] 孟祥春.葛浩文论译者——基于葛浩文讲座与访谈的批判性阐释[J].中国翻译,2014(3).
[7] NIDA E A,CHARLESR T.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8] 余谋昌.生态文化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9] 莫言.生死疲劳[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10] GOLDBLATT Howard.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anov[M].New York:Arcade Publishing,2012.
[11] 张斌.现代汉语(第2版)[M].北京:中共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6.
[12] 纪娇云.管理学理论与案例[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11.
[13] 曾毅平.华语修辞[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14] 王道森.法律语言运用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