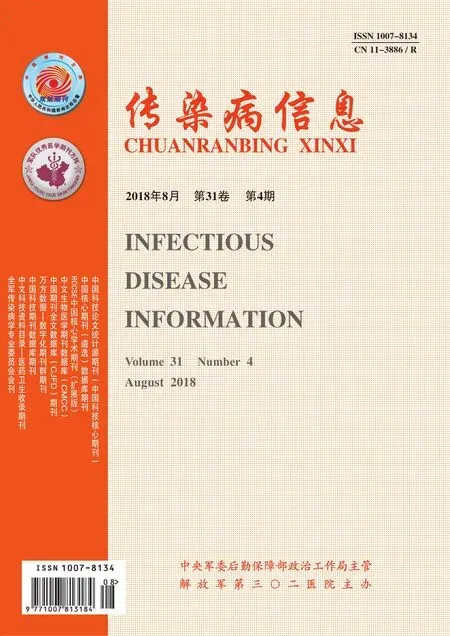肠道菌群与肝脏疾病研究进展
周 达,范建高
人体肠道菌群,定植于整个消化道,是人体内复杂的共生系统,对维护机体内环境稳定起重要作用。其中,拟杆菌门和厚壁菌门是主要的菌门,占比达90%,其他的由变形菌门、疣微菌门、放线菌门、梭杆菌门和蓝藻菌门构成[1]。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近端消化道至远端消化道逐渐提高。影响肠道菌群的因素众多,如饮食、免疫、行为和健康状况等外在因素及宿主基因等特异性因素[2]。机体肝脏与肠道起源于同一胚胎层,肠肝间存在机械、化学、免疫、生物等屏障,肠道菌群通过门静脉系统,将各种代谢性或免疫性物质、细菌成分或产物运输到肝脏[3],而肝脏亦可通过分泌胆汁或免疫成分影响肠道功能,使得肠道与肝脏间联系紧密,称为肠-肝轴。以肠道菌群为靶向的干预也许可以成为一种全新的疾病干预策略[4]。本文主要讨论肠道菌群在肝脏疾病中的生物学作用及机制。
1 肠道菌群与肝脏疾病的交互作用
肠道上皮系统是肠道外源性病原体的天然屏障,菌群失衡可增加肠道通透性,进而促进肠道病原体和肠道毒素通过门静脉系统入肝,并引起一系列病理生理反应,严重者可引发全身多器官功能障碍[5]。肠道上皮功能的维持主要依赖紧密连接,其主要功能是调节营养物质吸收,抑制有害物质进入机体。紧密连接主要由一系列穿膜蛋白构成,如occludin、claudin和zonulaoccludens蛋白,而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对紧密连接有直接或间接的调控作用[6],如IL-17可诱导claudin的表达而降低肠道通透性,IL-10对肠道屏障也有保护作用,短链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s, SCFA)之一的丁酸可以促进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进而减少菌群移位[7-8]。
肠道菌群产物如甲胺(一种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病原相关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PAMPS)包括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 LPS)、脂磷壁酸、肽聚糖、鞭毛蛋白和未甲基化的CpG DNA等可通过肠-肝轴入肝后与肝星状细胞、Kupffer细胞或肝细胞表面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 TLR)结合,从而激活肝内炎症关键信号通路[9];LPS是革兰阴性菌菌壁成分之一,其可以与CD14、TLR4结合而激活MyD88-TNF-α通路,促进炎症、氧化应激等级联反应。脂磷壁酸是革兰阳性菌细胞壁成分之一,同样也是TLR2配体,具有维持肠道屏障完整作用,其功能缺陷与LPS入血循环增多,胰岛素抵抗的出现密切相关[10]。此外,一类称为NOD样受体(NOD-like receptor, NLRP)3的胞内蛋白复合体(包括NLRP-1、NLRP3、NLRC4和人黑素瘤缺乏因子2)形成炎症小体,是PAMPS和SCFA的内、外源性传感器,参与调节促炎因子如IL-1β、IL-18介导的炎症反应,从而增加肠道通透性[11-12]。菌群产物SCFA,包括乙酸、丙酸、丁酸,可直接调节肠源性激素的分泌而调控糖脂代谢、胰岛素抵抗等,亦可通过肠-肝轴直接入肝调节肝内免疫、炎症等相关基因表达而起到一定的肝脏保护效应,具体机制可能通过SCFA与GPR43/109a/41受体结合介导或通过SCFA对组蛋白去乙酰化酶的抑制作用介导[13-14]。肠肝间相互协同作用复杂,高效特异性的干预靶点有待更精准的研究,下面就肠道菌群与脂肪性肝病、肝硬化、胆汁淤积性肝病的研究作逐一论述。
2 肠道菌群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目前已超越慢性乙型肝炎(慢乙肝)成为国内外第一大慢性肝病[15],其发病机制仍有待阐明[16]。最近研究提示:肠道菌群通过多种机制密切参与NAFLD的发展[17]。首先,肠道菌群可以调节食物能量代谢与转化,而高脂饮食可以导致肠道菌群失衡,促进促炎因子释放从而促进NAFLD进展;其次,肠道菌群与机体免疫系统之间互相作用,已证实机体免疫系统的失衡可以促进NAFLD发生发展,并且提示肠道菌群可通过免疫介导NAFLD发病。再者,肠道菌群代谢产物,如内源性乙醇和其他有毒介质,通过肠道被吸收后从门静脉系统进入肝脏而诱发相关损伤,如刺激Kupffer细胞产生促炎性细胞因子、促进醋酸盐生成,后者是合成脂肪酸和乙醛的底物,从而加重氧化应激反应[18-19]。综上,肠道菌群的改变及其代谢产物可诱发肝脏脂肪变性和炎症产生[20]。
有研究表明,与对照小鼠相比,转基因肥胖小鼠的拟杆菌比例显著降低[21]。肥胖人群中也观察到同样的现象。与体型正常人群相比,肥胖人群肠道菌群厚壁菌门比例更高,而拟杆菌门比例更低;同样,与没有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NASH)的肥胖人群相比,NASH患者的拟杆菌数量较低,失衡的菌群可促进热量摄入、脂质沉积[22-23]。更深入的研究发现,与健康对照相比,NAFLD患者球形菌门比例更高,在菌属水平,埃希菌属、厌氧杆菌属和链球菌属比例显著升高;而疣微菌科,另枝菌属和普氏菌属在健康对照的肠道微生物群中的丰度显著高于NAFLD组[20]。也有研究发现被认为是益生菌的乳杆菌属在NAFLD患者中也有升高,该菌可通过改变肠道微环境而参与NAFLD的进展[20,24]。益生菌的活性具有菌株依赖性,并不是所有乳酸杆菌菌株都对机体有益处,但在临床试验中,特定乳酸杆菌菌株组成的益生菌已被证实对NAFLD患者有益[25]。
有研究显示在肥胖患者中小肠细菌过度生长(small intestinal bacterial overgrowth, SIBO)比正常体质量指数者更常见,SIBO加速了NAFLD进展至NASH,可能由于细胞间紧密连接破坏造成肠道通透性显著增加,进而使肝脏暴露于肠道有害代谢产物[16,26],同时肠道菌群的失衡可诱导肝脏脂肪生成酶、脂肪酸合成酶和乙酰辅酶A羧化酶的表达增强,促进肝脏脂质从头合成[27]。在慢性肝脏疾病中,由肠道菌群诱导的脂肪酸代谢和初级胆汁酸向次级胆汁酸的转化显著减少[28],胆汁可以调节脂肪乳化、胆固醇代谢、脂溶性维生素代谢和激活或抑制肠道中不同的信号通路。胆汁酸核受体X参与肠道菌群调控NAFLD发病,可被胆汁酸激活而诱导抑制胆汁生成的信号级联反应[29-30]。研究表明损伤相关的分子模式激活促进活性氧的产生,从而活化NLRP3[31],Henao-Mejía等[32]研究发现NLRP3和NLRP6协同IL-18通过调节小鼠肠道菌群的构成负向调节NAFLD的进展。
从治疗方面而言,益生菌和益生元均被推荐作为膳食补充剂以维持肠道通透性的完整和肠道健康。益生元已被证明可抑制肝脏脂肪酸的从头合成来改善NAFLD,并参与机体脂质代谢调节[27,33]。在遗传型肥胖小鼠(ob/ob)动物模型实验中,与对照组相比,益生元低聚果糖的摄入可以显著降低血浆LPS和促炎细胞因子水平,提高肠道胰高血糖素样肽2的表达,降低肠道通透性,抑制肠道细菌移位[34]。益生菌亦通过减少有害菌对肠道上皮细胞的粘附及其移位,从而抑制NAFLD进展,减少NASH并发症[5,26]。使用益生菌混合物VSL#3(其富含嗜热链球菌、乳杆菌、双歧杆菌)干预NAFLD小鼠模型4周,显著减轻肝脏脂肪变性和炎症,血清ALT、AST,血脂和胰岛素抵抗指数亦明显改善。这些参数的改善与肝脏NKT细胞调控有关,通过对TNF-α/IKK-β信号通路抑制、降低Jun N末端激酶活性以及降低NF-κB DNA结合活性来实现[35-36]。在蛋氨酸胆碱缺乏饮食诱导的小鼠NASH模型中,其发病机制与肥胖、代谢综合征无关,给予VSL#3可减轻肝纤维化发生[37]。另一项研究提示给予小鼠高脂高蔗糖饮食可引起肠道菌群稳态失衡,造成机体内活性氧、IL-6、TNF-α和LPS的显著升高及SCFA的失平衡,给予益生菌干预后,上述指标显著好转,同时失调的肠道菌群得到改善[38]。另外,在儿童和成人的随机临床研究中显示,一些益生菌对治疗脂肪性肝炎有一定的益处,表现为AST和ALT、TNF-α、血胆固醇、HDL和稳态评估模型评分的明显改善,当然各研究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可能是由于所用菌株的多样性所致[25]。一项针对肥胖脂肪肝患儿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中,观察到那些服用VSL#3益生菌4个月的患儿获得了类似的效果[39]。因此,益生菌和益生元在NAFLD治疗中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前景,同时也支持以肠道微生物群为靶向干预的可行性[40],但仍存在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首先,上述研究多为观察性探索,缺乏机制的深入;其次,各项研究间缺乏可比性,缺乏标准化流程或诊治方案,循证证据较弱;再者,整体菌群移植或选择性菌群移植可否应用于NAFLD尚缺乏研究,其与单纯益生菌或益生元相比有无优势值得进一步探索。
3 肠道菌群与肝硬化
近年,肠道菌群与肝硬化的研究亦较为深入。有研究显示与正常对照相比,SIBO在肝硬化患者中更常见,而肝硬化患者肠道屏障紧密连接蛋白表达显著下调[41],导致肝硬化患者更易发生细菌移位,肝脏也更多地暴露于肠道毒素如内生性乙醇、LPS等,进一步加重肝损害[26,42]。肝硬化患者肠道通透性增加可能与一氧化氮诱导的氧化应激增加及肠道黏膜表达炎性介质如TNF-α增加有关,同时门静脉和血循环细菌内毒素水平也显著升高[26,43]。菌群移位造成的感染或菌群代谢产物可引起肝硬化患者门静脉压力升高诱发静脉曲张出血[44]。此外,肝硬化患者血清、腹水中细菌DNA含量的升高提示出现急慢性肝功能衰竭的概率显著提高,进一步提示肠道菌群可能与肝硬化患者血液动力学恶化、临床并发症的出现密切相关[45]。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肝硬化患者唾液中梭杆菌科,普雷沃氏菌科和肠球菌科比例显著增高,同时还发现肝硬化患者的唾液和粪便中的微生物群结构类似,这种肠道微生态失调与菌群正当防御、机体炎症状态改变及由肝功能衰竭引起的住院风险增加密切相关。在合并肝性脑病(hepatic encephalopathy, HE)的肝硬化患者中,肠道天然分类群毛螺菌科和疣微菌科的丰度显著下降,而具有潜在的致病性分类群普氏菌科和梭杆菌科的丰度显著增加,同时发现此类患者血液循环中致炎性Th1、Th17细胞显著活化。肝硬化患者菌群失衡预示黏膜免疫的失衡,也暗示着未来与肝硬化预后相关的菌群研究目标与方向[46]。有研究显示酒精性肝硬化患者肠道内革兰阴性菌过度生长,造成肠道氧化与抗氧化失衡,进一步导致肠道通透性的增加。同样,一项临床研究显示,肝硬化患者十二指肠菌群富含厚壁菌门(韦荣球菌属、巨型球菌属、小杆菌属、奇菌属和普氏菌属),而健康对照者却富含变形菌门(奈瑟菌属、嗜血杆菌属和嗜酸乳杆菌属)[47]。
一项系统综述显示益生菌可用于HE的发生(一级预防)和复发(二级预防),使用3个月益生菌后,患者血氨浓度显著降低,健康状态显著改善[48]。Dhiman等[49]的研究显示:使用VSL#3进行HE的二级预防,显著降低了HE患者6个月内的住院率,同时改善了HE相关脑病症状,降低了血清炎症标志物、改善了肝功能等相关生化指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患者生活质量显著提高。VSL#3亦可降低酒精性肝硬化患者机体的氧化应激参数;在针对肝硬化的研究中发现益生菌可恢复中性粒细胞的吞噬能力,通过促进IL-10分泌和TLR4表达,降低肠壁通透性,减少细菌移位和改善内毒素血症,从而抑制肝脏中的氧化应激和炎症损伤[41,50]。益生元乳果糖亦成为HE治疗方式之一,可能依赖于其对粪便的酸化和清除作用,从而改善粪便菌群和促进氨的排泄[38];另一项研究显示合生元亦降低了肝硬化患者血清内毒素水平,改善近50%患者的Child-Pugh分级;同时显著提高了患者粪便中不产尿素酶的乳杆菌丰度,这可能与患者血氨和内毒素的降低有关[41]。至于其他慢性肝病或肝移植的荟萃研究显示益生菌干预显著降低了患者的感染率和住院时间,而对病死率无明显影响[38]。美国一项针对肝硬化合并HE临床研究提示粪菌移植对于复发性HE有较好的改善作用,患者的认知功能和肠道菌群丰度及有益菌含量得到显著改善,此研究探索了粪菌移植治疗HE的安全性及疗效,展示了一定的应用前景,但仍需要更长随访期的纵向研究及更大样本量的临床研究验证[51]。同样,亦有我国学者使用粪菌移植方法治疗慢乙肝。慢乙肝易发展为肝硬化、肝癌,因此对其有效治疗的研究迫在眉睫。此项研究发现:与对照组相比,经粪菌移植治疗的慢乙肝患者HBeAg清除率更高,并未见严重不良反应。虽然此研究为小样本临床观察,但该研究成果对慢乙肝尤其药物疗效欠佳患者的临床处理策略具有重要的创新和启发意义,后期仍需要大样本临床试验的深入验证[52]。
此外,治疗药物对肝病患者肠道菌群的影响亦不能忽视。肝硬化患者使用质子泵抑制剂后肠道内根瘤菌属显著减少,小杆菌属不同程度地升高[47];给予肝硬化患者口服抗生素亦可显著降低血清内毒素水平[41]。同时不同的肝硬化病因亦可对患者肠道菌群有轻度的影响,可能与不同病因所导致的胆汁酸水平、免疫状态不同有关[47]。
4 肠道菌群与胆汁淤积性肝病
目前,对肠道菌群与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 PBC)的研究较少。有研究报道PBC患者菌群多样性降低,同时发现该病患者肠道菌群特征表现为4个种属菌丰度的下降和8个种属菌的丰度增加,而熊去氧胆酸的干预可一定程度逆转PBC患者失衡的肠道菌群,尤其表现为柔嫩梭菌群菌属丰度的下降[53]。Sabino等[54]发现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rimary sclerosing cholangitis, PSC)患者菌群多样性下降明显,而肠球菌、梭杆菌和乳杆菌丰度显著升高。多项研究提示在合并炎症性肠病的PSC患者中韦永氏球菌属丰度明显升高[55-56];有体外研究显示韦荣球菌属有促炎特性,与其他慢性炎症性疾病密切相关[57]。一项英国的研究显示PSC患者肠道菌群表现为埃希菌、毛螺菌和巨型球菌的丰度显著增加,而普氏菌和罗斯氏菌丰度下降,同时表现为拟杆菌丰度的缺失[58]。上述主要为观察性研究,肠道菌群对胆汁淤积性肝病发病的作用、诊治的贡献仍需更多的实验研究和临床探索。
5 总 结
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与肝脏疾病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有望成为肝脏疾病诊断、治疗、预防的新切入点,干预肠道菌群的方式众多,如饮食、运动、益生元、益生菌、抗生素等,针对不同类型的患者可以精准应用以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为靶向的干预手段;但目前仍属于观察性或实验性研究,缺乏高质量的循证和机制研究,往后须开展更为深入的机制研究,以及开展大样本随机对照临床研究证实以肠道菌群为靶向干预的有效性及安全性,从而为肝病的预防和诊治提供可靠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