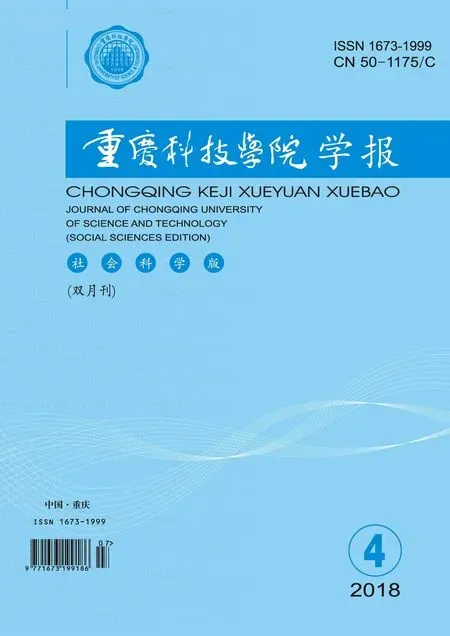词语时代色彩的类型及新词语的语言时代色彩
——以《元刊杂剧三十种》新词为例
谢晓晖
词语色彩也称“附加义”“伴随义”“陪义”“表达色彩”等,它所反映的是客观对象在本质之外的某种抽象的倾向或情调的意义,是附加的,非独立的部分。词语时代色彩是词语色彩的一种,笔者拟厘清其类型,并以《元刊杂剧三十种》⑴为例说明新词语的语言时代色彩。
一、词语时代色彩的类型
关于词语的时代色彩论述不多,下面择其要述之。
杨振兰从语言的社会性的角度认为,词的时代色彩即是词所体现出的特殊的时代氛围和时代气息,是社会历史变化发展在语言词汇中的投影和烙印,是时代的风貌在词身上的一种凝固[1]193。时代色彩属于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并不是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词都具有时代色彩,也不是某个时代的所有新生词都有时代色彩,只有那些反映了比较重要的社会历史内容的词,才具有时代色彩[1]193。 比如,“跃进”“钢帅”“促进派”“促退派”体现了20世纪“大跃进”的时代色彩;“搞活”“热销”“软件”“特区”体现了 20 世纪 90年代的时代色彩。随着时代的变化,不少词语的时代色彩逐渐消退,变为通语。例如,“火车”“铁路”“邮政”“机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无疑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当这些词语在脱离了其时代背景被长期使用时,其时代色彩也逐渐消失。
汪维辉认为,每一个词都有其时代性和地域性[2]。他从词汇史的角度认为,时代性指的是词只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使用。比如,“行”的本义是道路,这个义位在上古是通行义。上古时代,不管大路还是小路都可以叫“行”,如《诗经·豳风·七月》:“女执懿筐,遵彼微行”,“微行”是小路。 《诗经·周南·卷耳》:“嗟我怀人,寘彼周行”,其中“周行”是大道。大概到了战国时代,“行”的“道路”义就逐渐少了。到了汉代,这个词(义位),可能已经从口语中消失,后人用“行”表道路义,乃是仿古。有的词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昙花一现”,如“戴屋”一词。南朝梁《周氏冥通记》卷4多次用到此词,如“其正月欲戴屋,而所顾(雇)师永不来”。清代黄生《义府》卷下的“冥通记”解释说:“戴屋,盖屋也”,是就建造房屋时铺上屋顶这一工序而言的。此词后代未见,盖为南朝时流行于金陵一带的方言口语词。有的词从古到今都在使用,它们的时代性表现为“泛时性”,如 “山”“水” “人”。
张志毅将词语的意义称为义位,义位的色彩称为陪义。他对时代陪义的定义是:语言整个义位系统经常吐故纳新,新陈代谢。这种变动性规定了义位在时间轴上的位置,这就是义位的时间属性,由此义位便产生了一种补充义值,即时代陪义……按时间层次,义位划分为:历史义位,古义位,旧义位,现代义位,新义位[3]。张志毅与汪维辉一样,是从语言本身的角度来定义词的时代色彩的。
周荐立足于当代,把时代色彩分为两类:一类是崭新的时代色彩,即刚出现或刚出现不久的词语,人们使用它们,说者和听者都倍感新奇的时代色彩[4]179。例如“洋倒爷”,指到中国大陆来从事倒买倒卖的外国人。这是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具有崭新的时代色彩。带有崭新时代色彩的词语是一般词汇中的新词语。任何一个为本语言社会所新造的词语或由彼系统借入此系统的新词语,在一定时期内,人们往往对这些词保持着新鲜感,这些词有着崭新的时代色彩。超出一定时限,使用已久,词语新鲜感便会失去,没有了先前那种崭新的时代色彩。另一类是陈旧的时代色彩。具有陈旧时代色彩的词往往使人联想到特定的、过去了的时代。如“北平”唤起了人们对民国时代北京的回忆与怀旧,有一种陈旧的时代色彩。又如“完璧归赵”,使人想起战国时期,该词的时代色彩也是陈旧的。
综上所述,杨振兰从社会角度来定义词语的时代色彩;汪维辉、张志毅从语言本身的历史的角度来限定词的时代性;周荐立足于现代,把词语分为崭新的时代色彩与陈旧的时代色彩。基于前人的相关论述,笔者认为:
第一,词语的时代色彩分为2类:一类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风貌;另一类是新词语(包括新词和旧词的新义),是在时代语言系统中具有时代色彩的词。首先,第1类词语反映当时社会经济、文化、习俗等,同当时社会潮流密切联系在一起,如元代杂剧兴盛;体系化的戏曲角色名称,如“净”“正旦”“正末”等,折射了当时的社会潮流,具有社会时代色彩。另一类是在该时代语言自身系统中具有时代色彩。其次,新词语具有时代色彩。正如周荐所认为的,带有崭新时代色彩的词语是一般词汇中的新词语。任何一个刚为本语言社会所造的词语或刚由彼系统借入此系统的词语,在一定时期内都会在人们心目中具有新鲜感,有着崭新的时代色彩[4]183。元代出现的新词“常川”“大古里”“小旦”,“勾当”的新义位“本领”,“堕落”的新义位“荒废”等,这些新词语当时都具有崭新的语言时代色彩。
第二,一些词兼具语言时代色彩与社会时代色彩。凡能反映时代新变化、新潮流的词都具有社会时代色彩。所以,社会时代色彩词可由旧词充当,也可由新词充当。据此,可将具有社会时代色彩的词分为两类:第1类,由旧词充当,只有社会时代色彩,而无语言时代色彩。如《诈妮子调风月》第1折:“[赚煞]〔云〕许下我包髻、团衫、绣手巾!专等你世袭千户的小夫人”。其中,“包髻”“团衫”分别是金朝就有的头饰、衣服,“绣手巾(绣花手巾)”更是由来已久。这3样东西也是当时娶妾“必不可少的聘礼,元曲中多见”[5]。“包髻”“团衫”“绣手巾”3个词连在一起,虽都是旧词,却体现了浓郁的元代婚嫁特色。第2类,由新词语充当,这类词既有社会时代色彩,又有语言时代色彩。这类词又分为2种:一是指称对象是新事物、新现象的新词语。如元代的杂剧发展成熟,许多杂剧术语也随之产生,这些术语反映了元代社会的流行娱乐色彩。具有元代社会色彩的这些杂剧术语,有的是新词,如“正末”“外孤”“小驾”“断出”“散场”等;有的是旧词的新义位,如“俫儿”“孛儿”“关子”等。这类词既具有语言时代特色,又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新变化,故也具有社会时代特色。二是指称对象是旧事物、旧现象的新词语。如“放解”指做典当买卖盘剥取利,是元代典当行业的习语。“放解”这一现象早已有之,但元代“放解”蔚然成风,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故此词不但具有语言时代色彩,也具有社会时代色彩。
第三,词语的时代色彩是个历史范畴。每个时代都会产生具有该时代色彩的词语。比如,“青苗法”一词反映了宋代王安石变法时期的重要经济制度,在当时此词具有强烈的社会时代色彩。从现代着眼,“青苗法”体现了宋代的社会时代色彩。“行”作为“道路”义,在刚产生时,具有当时语言的时代色彩。从现代来看,“行”的“道路”义则具有上古语言的时代色彩。
第四,时代色彩是相对的。每一个在当时具有时代色彩的词语,随着时间的流逝,或成为没有时代色彩的化石语素,或成为陈旧时代色彩的半化石语素,或累世通用成为现代词汇的一员。
二、新词语所反映的语言时代色彩
目前,关于词语的时代色彩的研究不多,笔者以《元刊杂剧三十种》中的词语为例对此进行讨论。词是形式与指称概念的统一,根据这两方面情况,笔者将《元刊杂剧三十种》中的新词语分为4类:第一,新指称新词。这类词所指称的概念与词形都是新的,如“互联网”。第二,新指称新义。这类词所指称的概念是新的,词形是旧的。它是一个已有词的引申新义,表达的是新的概念。如“下课”本指学生一堂课结束了,下课课间休息。现在泛指停止某人的工作或者被解雇。第三,旧指称新词。这类词指称的概念是旧的,词形是新的,如“香波”“颜值”。第四,旧指称新义。这类词所指称的概念是旧的,词形也是旧的。确切地说,它是一个词引申出来的新义,这个新义是已有概念。如“小姐”的常用义是泛称未婚女子,今天“小姐”有了新的义项——妓女的婉称。任何一个新词语的产生,都反映出当时人们的认知观念,表达方式的变化。《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新词语反映出元代人们的认知观念与表达方式。
(一)新指称新词
新指称新词在表达内容上体现了社会经济文化及日常生活中的新事物、新现象,在表达形式上填补了表达空位,为词汇增加了新的成员。因此,这类词语最能体现语言与社会的双重时代色彩。如“料钞”是元代纸币,是元代第一次全国性流通纸币,该词反映了元代纸币的流通情况。下面以戏曲术语来举例说明。
《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出现的新指称新词共29个,其中,25个为戏曲术语,如“小驾”“俫儿“打悲”“作意”“断出”等。这与元代戏曲的成熟是分不开的。戏曲行业语的增多与体系化,是戏曲成熟的标志之一。这些词语具有浓郁的社会时代色彩,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民众娱乐生活。有不少行业术语词后来成了一般通用词汇,如“散场”在元杂剧中指演出结束后,演员下场,观众离开。此词后来通过比喻引申,词义发生了改变,使用语域扩大,成了通用的一般词语。时至今天“散场”有“各类聚会结束后,人员离开聚集场地”“人与人之间的分开、离散”“生命的终结”等多个义项。又如“招儿”,指戏曲海报,是戏曲名物词。贴“招儿”目的是将所演之戏广而告之。人们在熟知此词后,将其词义泛化,不仅指戏曲海报,还指各类带有广而告之性质的招贴、招牌、启事,使用语域也随之扩大。“招儿”在各行各业中使用,完成了通用化,成为一般词语,如明代施耐庵的《水浒传》第26回:“那婆子取了招儿,收拾了门户,从后头走过来”中,“招儿”是招牌的意思。从行业用词成为通用的一般词语的前提是该行业术语需具有强烈时代色彩,流行到一定程度,为全民所熟知。
(二)新指称新义
新指称新义,即旧词引申出来的新义位所指称对象的是新产生的事物、现象。新义与旧词之间有某种关联,反映了人们用既定的语言习惯来认知新现象、新事物的思维定势。如“楔子”的本义是用来加强、支撑或保持固定位置的固体物。“楔子”作为戏曲术语,是原义的比喻引申。戏曲中,引子对折与折之间的紧密联系所起的作用,犹如木工制作木器为了使其牢固,而在榫缝或空隙处插入的楔子,故称引子为楔子。新指称新义在不增加词形的情况下,填补了表达空位,是语言经济化的表现。《元刊杂剧三十种》中的新指称新义,或反映了当时社会潮流,或体现了当时社会热点,故具有双重时代色彩。这类词有7个:“楔子”“孛老”“关子”“披秉”“邦老”“卜儿”“鸦青”。 前 6 个是戏曲术语,反映了当时杂剧的盛行。最后1个词“鸭青”是指元钞,因当时元钞的颜色是鸦青色的。
(三)旧指称新词
虽然这些词(旧指称新词)所表达的概念在前代已经出现,但是,它们并非简单地更换了表达形式[6]。旧指称新词除了新词语的语素结构能够更科学、更恰当地表达概念之外,还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语言的要求,折射出语言的时代色彩。
第一,体现了人们对语言的求新求变。人们对语言的理解,是人们在接受语言信息时,大脑皮层对语言信号的刺激作出了一系列反应的结果。某个词经常重复使用,与语言相对应的神经机构受到这个词的反复刺激,对其有了自动感知进而就会变得“餍足”。所以,任何词语长时间使用后,其理据及感情、形象、时代色彩都会因频繁的使用而棱角尽消,价值变弱,这就是词义磨损。在此情况下,表达者需要有意制造一些不能自动感知的东西,延长接受者的审美过程。于是,即使不产生新事物、新现象,人们也会积极地造出新的更具理据意义的,或更富感性色彩的词语来指称现有的事物、现象。旧指称新词的产生是人们对语言求新求变的表现,因为体现了当时人们的语言心理,也就具有了时代气息。不妨以今推古来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如现代汉语词汇有“表演”“美女”“洗面奶”,但有的人不用这3个词语,而代之以“走秀”“靓女”“洗颜液”。后3个词的词义与前3个词相同,并没有表达新义,也没增加新形象或感情色彩,人们之所以选择后3个词,只是为了语言上的新鲜感。《元刊杂剧三十种》也有这类旧指称新词,如“乔人”“药婆”“夸扬”“推拥”“搬调”“屈杀”“穷暴”等,它们的出现,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人们为了求取语言表达上的新鲜感。
第二,更细致化的表达。一些概念虽然早已存在,但是一直没有相应的词语来表示,这类新词的出现,填补了语言的表达空位,体现出人们对成功交际的需求。如《元刊杂剧三十种》中新词“血泊”“肩窝”“腰截骨”。 “血泊”指“一大滩血”,“肩窝”指“肩膀凹陷处”,“腰截骨”指“腰椎骨”。3个词所代表的概念虽一直存在,元代以前却没有恰当的词语表达,这3个词是人们为了准确指称概念,填补表达空位而产生的新词。又如,元代之前用“聒”来表示频繁地称说。如《庄子·天下》:“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也。”但是,表达“话多达到某种程度”概念的词一直没有出现。于是,元代产生了“口困”一词。“口困”指因话多而累得仿佛想睡觉,非常形象化地表达了话多的程度。
第三,体现社会生活的改变。社会生活的改变与词汇的变化息息相关,从词汇中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强烈的时代色彩。“赛羊”,用羊祭神,泛指祭神。《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第4折:“[后庭花]瞒天地来赛羊,欺穷民心不良,昧神祇烧襜状。”《好酒赵元遇上皇》第1折:“[那吒令]前日是瞎王五上梁,昨日是村李胡赛羊,今日是酒刘洪贵降。”用于祭祀的羊称“神羊”,故又称“赛神羊”。元代有以神羊祭祀神鬼的习俗。用神羊祭神时,把羊的两条前腿在杀死后弄得向后弯曲,似屈膝作跪状[7]。新词“赛羊”可能与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畜牧业不断扩大,北方羊的数量大增有关。由于蒙古人传统的畜牧业的经济生活方式,大量牧场与蒙古贵族的分地进入农牧交错带内,甚至分布在关中这样传统的农耕区内[8]。畜牧业的发展,羊的数量大增,使得人们祭神以羊为主,北方随之以“赛羊”泛指“祭神”。又如蒙古入主中原后,在辽阔的疆土内建立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规模之大,分布地区之广,邮驿往来之高效都超出以往任何时代。在这种背景下,蒙古语“站”强势进入汉语,“站”代替了“驿”,“站车”代替了“驿车”。 元代疆域广阔,交通前所未有的发达,马是主要交通工具,对马的装备自是重视,为方便称呼有鞍与无鞍之马,人们创制了“刬马”一词。我们从“刬马”一词可以窥见当时人们对马的依赖。另外,受蒙古语后置词的影响而产生的“以此上”、蒙式汉语“道不是”,这些词是汉人与蒙古人密切接触在词汇上的体现。
第四,倾向为词语增加感性色彩。词语的感性色彩是词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感性色彩使得词语表达多姿多彩。《元刊杂剧三十种》“脑浆”所表示的意义,原本由“脑髓”一词表达。汉代刘向《说苑·辨物》:“俞柎之为医也,搦脑髓,束肓莫,炊灼九竅,而定经络。”一方面,“脑浆”比“脑髓”更富口语色彩;另一方面,“浆”是人们日常生活常见之物,人们认知中,“脑浆”比“脑髓”具象化。元代口语化程度较高的新词“脑浆”在人们的日常语言生活中代替了“脑髓”。到了现代“脑髓”一般用在书面语特别是科技语体中,而“脑浆”更大众化,使用语域更广。又如,“卖俏”,装出妖媚的样子诱惑人。“俏”是抽象的姿态,而“卖”的宾语一般是实物,“卖俏”一词将抽象的“媚态”当成具象化的商品,不仅有讽刺意味,而且具有形象色彩,比其近义词“媚惑”要生动活沷得多。
(四)旧指称新义
新义产生的过程就是把新的观念、新的想法、新的内涵融入旧词的过程。新义在不增加新词形的情况下增加了新的意义,减轻了人们的记忆负担,是满足人们对世界认知表达的简便、有效的途径,它从另一个角度体现着词语的时代色彩。
第一,新义位的产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与精神。词义的发展史寄托了一个民族的思想史和精神史。反过来,每个时期的词义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与精神,体现出时代气息,旧词引申出的新义位亦如是。如《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大嫂”衍生出新的义位“妻子”,“婆子”由老年妇女引申为“妻子”。这都是从卑幼称呼自己的妻子,带有尊敬的意味。对妻子敬称的产生,与宋朝后期及元代妇女地位的提高有一定关系。宋朝后期的城市经济发展让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得到提高,而蒙古族妇女在家承担着重要的生产劳动,故蒙族妇女地位不低。加之元代儒家统治地位大为削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妇女地位有了一定提高,男性对妻子也就相对尊敬了。又如《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第2折:“[幺篇]飘不了你放课钱,失不了你诸人债。”此句中的“课钱”为“债款”义。“课钱”的本义为“税金”,新义位“债款”是从本义引申而来,其引申根据是“债款”与“税金”在“不得拖延,非交不可”上性质相似。元代统治者出于对财富的渴望,重视商品经济,借贷盛行,借贷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元人视借贷为常事。在元代人看来,借贷,哪怕借的是高利贷,还钱都是天经地义,并无不妥。关汉卿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窦娥就因其父为高利贷所逼,不得已将她卖给蔡婆做童养媳。可以说高利贷是窦娥之死的首要原因之一,但由于作者默认了借高利贷还巨额利钱的合理性,故文中并没有直接谴责高利贷制度。元代“课钱”的“债款”由原义位“税金”引申而来,正是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借贷的看法。“课钱”的新义位沿用至明。明代周履靖《锦笺记》第14出:“近闻陈宅大娘广放课钱,不免与他称贷几文。”明代冯梦龙《喻世明言》卷39:“(柳妈妈)借得羊坝头杨孔目课钱,借了三千贯……”今湖北孝感农村有老年人向人借钱,不好意思明说,就说:“向你课几个钱用下”。这种借钱是有条件的,还时会多还些钱,或者除了还本钱,再给人以物。
第二,新义位的产生是当时人们主观能动性认知的结果。人的主观能动认知是语言历时发展的必备条件。人们的认知倾向于把相近、相似的事物、现象归为一类。新义位与原引申义位的关系,折射出当时人们的认知观念。如《霍光鬼谏》第3折:“[倘秀才]几句话,记在心头,休交落后。”此句中的“落后”义为遗忘、忘记,是元代“落后”一词产生的新义位。这个新义位是由本义“行走时落在别人后面”引申出来的。原义与新义位关联点在于人们认为落在后面有听不到、看不见的可能性的经验认知,属于原因-结果的引申。又如,“开荤”原义位为“久茹斋后开始肉食”,新义位“借指用武器杀伤人或把人击毙”。新旧义位虽语域不同,但有相似点——开杀戒与肉食。用武器“开荤”来借指杀伐,不仅体现了当时人们的隐喻思维,又大有“杀人者非我也,兵器也”的诙谐感。
第三,新义位的产生反映了认知经验的时代传承。旧词被赋予新的意义,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照顾人们当时既定的语言习惯和认知思维习惯,体现了那个时代认知经验的传承,如“迟疾”。《赵氏孤儿》第2折:“[红芍药]你20年可报主人公,恁时节正好峥嵘。我迟疾死后一场空,精神比往日难同,闪下这小孩儿怎建功?”此句中,“迟疾”是新义“早晚”的意思。“迟疾”的原义位为“或快或慢;快慢”,是指向某空间位移的速度,所指称的现象是具象的。而新义位“早晚”,是指近段时间的某个时候,所指事物是抽象的。汉族人思维习惯是从空间到时间,从具象到抽象。“早晚”的引申新义折射了当时人们认知经验的传承。
综上所述,新词语从多方面反映了语言的时代色彩:新指称新词、新义具有语言及社会的双重时代色彩;旧指称新词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语言的时代要求;旧词新义的新义位与原引申义位的关系,折射出当时人们的认知观念。
注释:
⑴参考资料:古本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元刊杂剧三十种[M]//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1]杨振兰.现代汉语词彩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2]汪维辉.论词语的时代性与地域性[J].语言研究,2006(2).
[3]张志毅.词汇语义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45.
[4]周荐.词汇学词典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5]秦新林.元代生活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172.
[6]曲丽玮.《元刊杂剧三十种》复字字汇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0.
[7]那木吉拉.中国全史·中国元代习俗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08.
[8]韩茂莉.中国历史农业地理: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