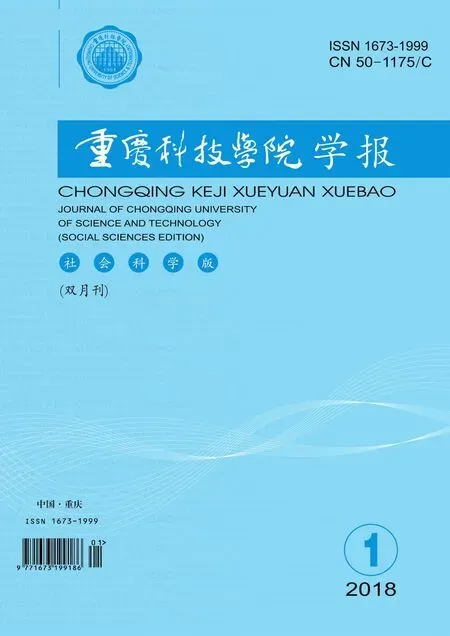巴赫金对话理论视角下的翻译人员主体性研究
涂文婷
尽管在人类语言文化交流活动之初,翻译人员(以下简称“译员”)已经出现,但能够在历史文献中留名的译员极少。传统翻译理论认为,译员应处于“透明”的“隐身”状态。因此,译员在口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往往被忽视。但是,在实际的口译活动中,译员完全超脱于口译各方,始终与口译各方保持“职业的疏离”(1)现象几乎不存在。译员根据实际工作情况或多或少发挥着主体性。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最早用于文学研究领域,因其强大的解释功能,近年来,一些翻译研究者将巴赫金对话理论引入翻译研究,为翻译研究引入了新理论,打开了新思路。笔者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分析口译过程,探讨译员在口译过程中的主体性。
一、巴赫金的对话理论
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1895—1975年)是前苏联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文学理论家和语言哲学家之一。他于20世纪初提出的对话理论虽然源于文学批评,但由于其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被广泛应用到哲学、文学、语言学、美学和诗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巴赫金提出“生活就其本质说是对话的”。这里的“对话”不局限于语言、文学和日常交流,它还能用于解释人的自我对话、人与人、人与文本、乃至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对话[1]。
巴赫金话语理论的核心是对话性(dialogicality),即“具有同等价值的不同意识之间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2]。在巴赫金看来,任何一种口头交际都是以对话的形式进行的,“话语不是单个人的事,而是在事先知道听话人反应的情况下与其相互作用的结果”[3]。话语同时与发话主体和对象主体有关,与前后话语都产生对话关系,对话关系无处不在。
二、对话与口译的关系
部分国内外学者撰文讨论了对话与翻译的关系。国外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他提出用“对话”模式分析译者从原语文本向目的语文本的“转向”,解释了译者、原语发出者及目的语接受者在伦理准则框架下的对话关系,凸显创造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从而使一直以来被压抑的译者主体性得以彰显[4]。贺微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文本不能被视为一个完全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客体,文本意义的实现有赖于读者的参与,“文本和读者之间有一种能动的相互作用,有一种对话关系”,提出“翻译是文本和译者的对话”[5]。 由此可见,翻译的对话本质毋庸置疑。
巴赫金认为,对话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生活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对话,思想和意义不是在独白中显现,而是在对话中产生,说话主体必须在具体的语境下与其他话语主体在思想、情感和信息方面展开沟通与交流,才可以产生能够被理解和接受的话语意义。在巴赫金看来,存在就意味着交际,而交际必然要通过对话来实现。口译是在一定社会文化语境下发生的交际行为,由译员和当事双方共同参与的一场为实现某一交际目的而进行的对话,通过言语或非言语的方式呈现出来[6]。译员和当事双方构成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三者之间呈现出一种不断变化的关系,没有哪一个人是固定不变的说话者和听话者,每个人都在动态的交际过程中又说又听,又听又说;交流的信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形成于对话过程之中;交流的信息不是固定地由一个人单向传递给另一个人,而是作为一个意识桥梁形成于他们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由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可以得出:首先,口译中的意义产生机制依托于对话的(dialogical)过程。译员与当事双方共同参与了交际活动中的意义生成,而且一旦译员参与了意义的产生、解释和转化,就很难摆脱个人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情感偏好,因而不可能总是保持中立与隐身。其次,译员既与说话人产生对话关系,又与听话人产生对话关系,而说话人与听话人则通过译员的语言转换产生对话关系,三方之间是互相依赖又互相制约,平等参与对话的整个过程。
三、对话与译员主体性的体现
口译是“一种通过口头表达形式,将所感知和理解的信息准确而又快速地由一种语言形式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形式,完整并即时传递交流信息,是现代社会跨文化、跨民族交往的一种基本沟通方式。”[7]口译表面上似乎是被动、单一、机械性的语言转化行为,实际上是积极的、复杂的、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意义再生产活动。译员是口译活动的主体,也是跨语言跨文化交际活动的共同参与者,译员的主体地位不容忽视。然而,由于受到传统口译标准的束缚,译员的主体地位长期受到抑制不得彰显。
在中西方口译史上,译员始终处于从属地位,一直被要求以隐身为代价,达到对讲话人语义的忠实。因而,在中国翻译史上,译员往往被称为只会模仿他人的“舌人”,或者是学舌的“鹦鹉”;在西方翻译史上,译员大多被比喻成:“管道”(conduit)、“回音器”(echo machine)等,认为译员应当像是“一块玻璃”(a pane of glass)。 在“忠实”(faithfulness)这一首要口译标准的统摄下,译员长期受到压抑。译员只能永远生活在讲话人的权威之下,以自我消隐来逃避“不忠”的指责,以此来践行口译“忠实”的最高标准。但是,在实际口译工作中,译员要做到完全隐身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为了更好地完成口译任务,往往需要译员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地在口译过程中凸显译员角色。译员的主体性是指译员为实现当事双方的交际目的而自觉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体现出译员的价值取向、文化背景和独立人格。口译也是一种主体作用于客体的对象性活动。作为翻译主体的译员要对原话进行意义阐释和语言转换,将原话的意义转达给听话人,使他听懂并做出讲话人预想中的回应或实施期望中的行动。在这一过程中,译员必须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才能确保交际的顺畅和翻译目的的实现。简而言之,译员的主体作用体现在口译的整个过程中[8]。
译员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译员对信息的把关、译员对谈话的参与以及译员对交际过程的协调。
(一)译员对信息的把关
根据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译员不再是隐身于对话之外的“透明体”,而是口译交际活动中积极能动的对话参与者。译员对口译的对话参与作用主要体现在口译过程中译员对信息的把关。这种把关主要有2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信息内容的把关;另一方面是对信息表现形式的把关。对信息内容的把关主要是指由于文化差异引起的具有文化敏感性或禁忌性的话题内容,主要涉及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规约问题。比如:在东西方交际过程中,东方人喜欢打听别人的年龄、收入,而西方人的交际禁忌则是男不问收入,女不问年龄。因此,在口译过程中,如果遇到触及文化禁忌的话语,译员可以在对话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醒对话一方,此问题可能引起对方的不快,最好规避;或者根据交际的目的,译员主动规避此类禁忌问题,转而由可接受的语言替代。对信息表现形式的把关则主要是指谈话人对词语、句式的选择,以及语气、语调等副语言的使用问题。比如:西方人讲话比较直截了当、开门见山,而东方人说话比较委婉。如果不作处理,直接翻译,可能会引起交际双方的交际不畅,甚至不愉快。译员可以根据交际双方的语言表达习惯,主动采取交际双方喜欢的说话模式,面向西方人的翻译可以尽量简单明了,而对东方人的翻译要适当客气婉转,才能使对话顺利进行下去。例如,笔者某次为美国某咨询公司担任译员,对某小学教育专家进行访谈。当美方人员问及中国小学生主要的校外课余活动时,中方老师的回答比较凌乱和啰嗦,大致意思是由于家长工作繁忙没有太多时间陪同孩子玩耍,多数孩子放学后以看电视为主要休闲活动,而孩子一看电视就表现比较乖巧,家长也乐于让孩子看电视来解放自己。笔者觉得没有必要把中方老师零散的、意思几乎相同的几句话逐字逐句翻译出来。结合之前笔者读过的一篇美国教育专家写的描述美国儿童看电视时间过长、美国家长过于依赖电视安抚孩子的现象把电视(TV)称为“电子保姆”(electronic babysitter),笔者直接用一句话翻译出来,即:“Many Chinese parents take TV as a perfect electronic baby-sitter.”(很多中国家长把电视当作一个完美的电子保姆。)美方人员听到翻译后,也感同身受,频频点头。
(二)译员对谈话的参与
根据巴赫金对话理论,我们把口译视为发生在一定社会文化语境下的交际行为,一场由译员和当事双方共同参与的、为实现某一交际目的而进行的对话,译员与说话人、听话人同时产生对话关系,说话人与听话人二者之间也通过译员产生对话关系。译员在动态的、多重的对话过程中既翻译他人话语,又贡献自己的话语,在成为不可或缺的交际谈话共同参与者的同时,也使自己在交际过程中显身。在实际口译活动中,译员的话语绝大多数是对讲话人语义的传达,也就是在说别人说的话;但有时译员也会参与到谈话过程中,把自己视为交际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成为谈话行为的共同建构者,也就是在说自己的话。而这类“自己的话”并不是由于没有听清楚或没有听懂讲话人的意思而请求对方予以重复或解释之类的话语。所以,一旦译员开始说“自己的话”,也就是在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或实施某种基于自己主观想法的行为,也就是在发挥译员的主体性。比如:在很多口译场合,如果译员只按照说话人的字面意思翻译,听话人可能会因为历史文化背景知识的欠缺而造成理解不畅。这时,译员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起到跨文化交际桥梁的积极作用,利用自身双语言、双文化的知识图式,在翻译出说话人字面含义的同时,主动说明潜在含义并适当补充相关文化背景,使聆听的一方更好地理解说话人的意思,达到更好的口译效果。再比如:说话人就某一个问题,单方面寻求译员的意见时,译员所做出的回答不再是客观的传递别人的思想,而是表达自己主观观点的行为。
(三)译员对交际过程的协调
对话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话的参与者轮流发言,对话参与者都有进入或退出对话、继续或放弃发言权的情况出现。对话的基本结构单位就是话论[9]。在实际口译过程中,译员与交际双方共同参与谈话过程,话轮种类、话轮交换都比单语对话更为复杂。因为在交际活动中,只有译员能够既通晓2种语言又了解2种文化规范和话语策略,所以通常也只有译员可以调整和维系对话过程,并及时对话语结构和语言使用中的偏误进行修正,以推动对话向前发展。尽管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总认为交际双方在交谈时应该是直接注视对方,忽视译员的存在,但在实际的口译工作中,笔者注意到,无论是讲话人还是听话人,常常不知不觉地将目光转移到译员这边,用语言、眼神、手势或肢体语言对译员做出种种言语或非言语的反馈。实际上,译员自身也意识到自己在交际过程中的主体作用,除了会对谈话中的某些语言文化信息进行把关,对不利于交际目的的话题内容和表达方式进行适当调整,会产生自己的主观话语以推动交际活动进行之外,还会主动承担管理话论和协调话论的责任,有意识地帮助交际双方传递、制造、打断和终止话论。在笔者曾参与的一次口译工作中,中方谈判代表过于激动,一个人独占话论。虽然,每讲几分钟会给译员翻译的机会,但每当译员刚翻译完毕,立刻继续话论。在这个过程中笔者注意到外方代表几次欲言又止,没有来得及插上话的表情。所以,笔者在中方代表讲话间隙以咳嗽、眼神、手势等信号向他暗示要中断话论,待翻译完中方代表的讲话以后立刻用眼神和手势提醒外方代表开始讲话,将话论传递到外方代表的手上。还有一次,笔者临时到某单位举行的接待晚宴为中外双方做口译。因为宾主双方之间,以及宾主各方与译员之间都不熟悉,除了刚见面时的寒暄和慰问,很快宾主双方就无话可谈,陷入令人尴尬的沉默。笔者担心这样不仅不利于宾主双方接下来的合作,也会对译员自身的工作产生不利影响。于是主动询问中方主人今天晚宴的菜品和安排。恰巧,笔者所在城市地处长江边上,当地人以吃江鱼、江虾等江鲜为待客之道。于是,中方主人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江鲜之美之营养,笔者顺势开始为他进行翻译。笔者听说美国人似乎不吃江鱼,又询问美方客人,美方客人也很热情的讲解美国的饮食习惯。宾主双方由吃鱼谈到中美的饮食差异,由中美的饮食差异谈到各自家乡的气候和人文习俗,整个晚宴宾主双方话论不断,谈笑风生。这是译员根据实际情况主动制造话论,维系话论的实例。
四、结语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认为对话无处不在。口译活动是译员和语言文化不同的交际双方共同参与的一场对话,译员是对话的共同参与者,话语意义是由包括译员在内的所有谈话参与者共同生成的。译员不可能“透明得像一块玻璃”,完全隐身于交际双方身后,而必须与谈话双方一起构成平等互动的关系,积极主动地参与整个口译过程。当然,译员主体性的发挥是有具体情况限制的,不能过分夸大和强调译员的主体性。
注释:
(1)澳大利亚翻译协会(AUSIT-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preters and Translators)的规定是:“译员/译者应在履行所有的职业合同上遵循好不偏袒的原则。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职业的疏离(professional detachment)。”参见 https://ausit.org/AUSIT/Documents/Code_Of_Ethics_Full.pdf.
[1]王瞳.口译中的“超视”[J].科技信息,2007(35).
[2]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的修订[C]//诗学与访谈.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74.
[3]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M].蒋子华,张萍,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253-254.
[4]ROBINSON D.The translator’s turn[M].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1:101-117.
[5]贺微.翻译:文本与译者的对话[J].外国语,1999(1).
[6]任文.联络译员的主体性意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98.
[7]梅德明.口译技能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2.
[8]吕炳华.译员主体性的体现[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5(1).
[9]任文.从话语分析的角度重识口译人员的角色[J].中国翻译,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