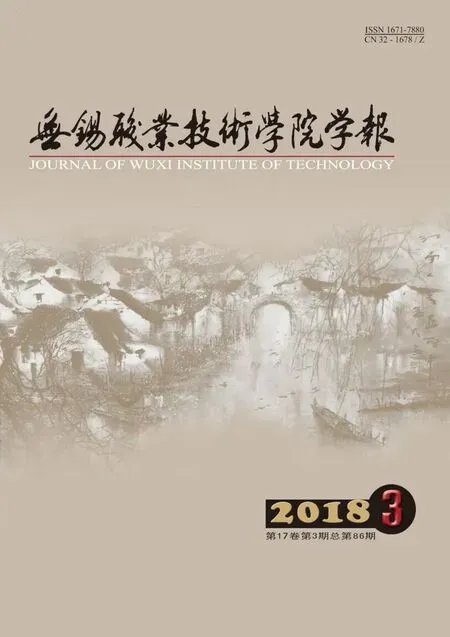《白鹿原》的“实录”特色
唐 嘉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白鹿原》以白鹿原的白、鹿两个家族三代人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展现了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五六十年间,中国大地所经历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辛亥革命、清朝统治的结束、北伐失败、军阀混战、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失败、抗日战争、40年代的大饥荒与瘟疫、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在《白鹿原》中都作为时代背景和推进情节的事件以及小说的重要内容展现出来。除了对历史大事件的记录,陈忠实同时执着于书写白鹿原上特有的历史,不仅仅是写人的历史,还着重表现历史中的人,从而“在大的历史背景上,作品演绎了一根两枝的白、鹿两家族史。写的人生、人的心灵,而不是历史事件。作者不是从党派政治观点,狭隘的阶级观点出发,对是非好坏进行简单评判,而是从单一视角中超出来,进入对历史和人、生活与人、文化与人的思考,对历史进行高层次的宏观鸟瞰”[1]。
学界对《白鹿原》的史传特点早已热切关注,《〈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王仲生)、《负重的民族秘史——〈白鹿原〉对话》(畅广元、屈雅军、李凌泽)、《史志意蕴·史诗风格——评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白烨)、《一部可以称之为史诗的大作品》(北京《白鹿原》讨论会纪要)等文献,对其所拥有的史传特点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与研究。从史传传统和《白鹿原》研究现状进行考量,本文主要对《白鹿原》所继承的史传传统的“实录”特色进行研究,从叙述方式、环境氛围、男权意识三个方面对《白鹿原》的“实录”特色进行探索。
1 叙述方式
社会历史小说客观冷静的叙述方式是它最为重要的“实录”特征。这种叙事方式,可以追溯到中国小说源头之一的史传中的叙事特色。“中国古代没有留下篇幅巨大叙事曲折的史诗,在很长时间内,叙事技巧几乎成了史书的专利。”[2]中国史传写作技巧归纳起来具有明显的特点:一是作者本人作为叙述者,选用第三人称进行叙述;二是一般以人物自然时序描述人物的一生。这两点《白鹿原》皆而有之。
《白鹿原》采用第三人称进行叙述,作者本人就是叙述者。在采用何种叙述方式的时候,陈忠实并不是心血来潮或灵感突至而选定了这样的叙述方式,“我确定尽量不写人物之间直接的对话,把人物间必不可少的对话,纳入情节发展过程中的行为叙述;情节和细节自不必说了,把直接的描写调换一个角度,成为以作者为主体的叙述。”[3]在进行了大量的作品阅读和多年的小说写作之后,陈忠实选定了以作者叙述为主、描写人物对话为辅作为他写作《白鹿原》的叙述方式,这样的方式让他感觉到自然与得心应手,也是这种叙事方式使《白鹿原》能具有近似“实录”的写作特点。“‘镜中取影’最终直达‘观者自知’的‘无我’之境,此中玄妙尽在对‘史传’文章义理有所反驳的转捩点中,看看‘最忌掺入作者论断’、‘未必尽肖其言’就可以通晓一二。”[4]众多的各色人物在这种“实录”性的叙述中,复杂的性格特点被自然而然地塑造出来。陈忠实没有在叙述中直接评价人物,暴露他对各种人物的个人态度,也就让《白鹿原》中诞生了很多值得品评的有争议的人物,如白嘉轩。白嘉轩作为族长,一直以“腰杆硬和直”为标志,他可以说是白鹿村乡约的真人版,从他坚决不允许田小娥入族谱、进祠堂,不同意建庙、执意修塔,原谅黑娃和鹿子霖的所作所为,责怪鹿三背地里杀了田小娥等事情中都可以看到他所代表的儒家文化所传扬的“正气”与“仁义”精神。在小说结尾之时,白嘉轩回顾一生觉得自己做下的唯一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是当年用计谋以卖地形式作掩饰巧取鹿子霖慢坡地做坟园的事。白嘉轩完全不能容忍田小娥与黑娃的婚姻关系,可他的儿子孝义不能生育时,他没有选择冷先生让孝义媳妇去棒槌会的建议,反而亲自设计了让兔娃和孝义媳妇睡觉,以求神不知鬼不觉地给孝义留后。当孝义非亲生的孩子可以光明正大地进入祠堂与田小娥至死不被祠堂接受,两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时候,白嘉轩道德尺度上的多标性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显现出来。陈忠实对《白鹿原》中的所有人物基本上都没有进行直接的评定,他运用客观而悄然的叙述让人物形象自然而然地圆润和丰满。
从叙事所采用的时间顺序上来看,《白鹿原》采用的是史传中最常使用的纪传体与编年体结合的方式。一部《白鹿原》从人物上来看,有着贯穿始终的两个人物“白嘉轩”“鹿子霖”,整部作品从时间线索上来说,由白嘉轩娶妻到鹿子霖死亡,通过两个人物的一生经历贯穿了整个白鹿原、关中乡村甚至整个中国的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从大的时间拐点上来看,《白鹿原》虽然没有运用明确的公元纪年时间,但大事件的发生发展都用的是顺时记录,可以说《白鹿原》依然属于“年鉴派”,“二月里一个平淡宁静的早晨”[5]60“这年冬天”[5]74“‘交农’事件的前后一年多时间里”[5]109“蒋介石策动了‘四·一二’政变,国共分裂了”[5]227“这一年的春节新年”[5]314“大饥馑是随着一场透雨自然结束的”[5]399“一场空前的大瘟疫在原上所有或大或小的村庄蔓延”[5]449等等,时间虽然模糊,却仍可以理出重大时间点中顺时发生的大事件的时间脉络。《白鹿原》中有着大量的插叙,有的章节中插入了对某个人物过去事迹的记叙或者是人物自身的回忆,但不可否认的是小说中大的时间点都是以顺序的方式进行安排,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生活经历都是按照顺序的方式进行叙述,这样的时间顺序安排,更容易使读者形成《白鹿原》是史诗的阅读感受。
2 环境氛围
《白鹿原》能成为史诗般的长篇小说,还得力于他成功写出了一方水土上的一方人。有地方特色的作品常常被视为是历史真实性的作品,《白鹿原》之于陕西关中乡村,“大概就是《西游记》之于淮安,《三言》《二拍》之于苏州,《金瓶梅》之于临清,《红楼梦》之于南京、北京,《废都》之于西安,《人生》之于陕北等”[6],《白鹿原》能够成为大家所相信的书写陕西关中乡村史的作品,也源自于他将清末到新中国这段历史时期,陕西关中独特的地理风貌、民俗民风、方言口语融入了《白鹿原》的写作之中,从而给虚构的“白鹿原”建构了真正的历史环境氛围。在这种环境氛围之中,他笔下的人物才能真正地在“白鹿原”上生活着,那些已经过去了的历史才能真正地在“白鹿原”上发生过。
中国自古以来地大物博,不同地区与省份有着不同的地理风貌和民风民俗,“夜里落了一场大雪。庄稼人被厚厚的积雪封堵在家里,除了清扫庭院和门口的积雪再没有什么事情好做”[5]18“从白鹿村朝北走,有一条被牛车碾压得车辙深陷的官路直通到白鹿原北端的原下,下了原坡涉过滋水县城很近了”[5]26“二月里一个平淡宁静的早晨,春寒料峭,街巷里又响起买罐罐馍的梆子声”[5]60“麦茬地全部翻耕一遍,让三伏的毒日头曝晒,曝晒透了,如落透雨,再翻耕一遍,耱一遍,土地就像发酵的面团一样绵柔,只等秋分开犁播种麦子了”[5]138等,文中写到的村中祠堂和乡约、新粮归仓丰收后的“忙罢会”、婚丧礼俗、向关公求雨的仪式、修补族谱过程、“棒槌会”风俗、买卖田土房屋程序等,这些地理风貌和民风民俗在《白鹿原》章节中的展示,都给读者阅读带来强烈的现场感,让读者可以透过穿越时空文字,了解那个历史时空中关中乡村应有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
《白鹿原》地方历史性还体现在“实录”了关中的方言口语。史传在记录历史人物的时候,经常记叙人物的语言对话,这种通过语言对话来写人物的方法后来也成为中国传统小说的一大写作特点。《白鹿原》不仅仅重视用人物的语言对话来突显人物性格,同时,还通过人物语言展现白鹿原上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方言口语。同时还值得注意的是,与人物使用方言口语不同,作为作者所使用的叙述性文字,陈忠实并没有选用关中地区的方言口语,而且使用普通话书面语。可见,让小说人物说着白鹿原的方言口语是陈忠实清醒而自觉的选择,这种自觉的选择从“实录”的角度来看是有深意的。从“哩”“拾掇”“谝”“乡党”“先人”“大”等单个的词,到“母亲当即说:‘今黑就去请法官,把狗日的一个一个都捉了。’”[5]16“冷先生开导他说:‘兄弟,请个阴阳先生来看看宅基和祖坟,看看哪儿出了毛病,让阴阳先生给禳治禳治……’”[5]17等每章都有整句整句方言口语的对话,白鹿原的人都说着白鹿原的话是陈忠实有意识地对地方语言进行“实录”。随着时代的进步,电视、电脑和手机都走进了千家万户,中国大地上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受普通话的影响方言逐渐不地道甚至慢慢消失的现实情况。《白鹿原》让人物使用方言口语也就让这片土地独有的语言被记录下来,这种对语言的“实录”让语言有了历史记录,同时这种“实录”也增加了《白鹿原》的历史真实性。
3 男权意识
从性别意识的角度考虑,《白鹿原》从头到尾所呈现的男权意识是不能被忽略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女性成为他者,作为第二性存在的历史几乎在所有民族历史发展中都出现过。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古老历史的国度,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历史的书写中经常看到被男人描绘和塑造的女性形象,这些女人形象常常是以模式化的样貌出现在历史和文学之中,不是圣洁如圣母一样,就是荒淫的恶毒祸水,没有美貌和生育之用的妇女成为男人不屑一顾的存在。陈忠实立足于写生活在白鹿原上男人女人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同时在《白鹿原》中也“实录”了史传传统之中难以根除的男权意识。
历史要记录的是大事件大人物,被禁锢在家庭生活中的女人,难以成为大事件的参与者和决策者,也就难以成为大人物,中国历史上皇帝中也就出了一个女皇武则天。更多的女性在史书中要不成为男性的同盟者如长孙皇后、马皇后,要不就成为褒姒、陈圆圆那样的祸国妖姬,传统史传中的女性没有独立的价值,从而也影响到中国历史小说中对女性的形象塑造和心理把握。
《白鹿原》中最突出的两个女性形象“田小娥”和“白灵”,依然是男权意识下的女性,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到上千年来中国人固有的性别意识。田小娥和白灵都是白鹿原上的女性叛逆者,一个是从未接受过新思想、新教育的旧女子,另一个是从小便是在五四思想之下成长起来的新女性;一个出自原始冲动不受束缚地追求婚姻自由,一个在新时代崇尚民主、自由而反抗包办婚姻;一个最后变成了人尽可夫的娼妇,一个成为在革命中寻找到爱情并为革命牺牲的女烈士,但小说中对两位女性生命轨迹的刻画依然弥漫着浓重的男权意识。田小娥从最初与黑娃私通,到最后被鹿三手刃,《白鹿原》里并没有将她所经历的内心矛盾和艰难处境呈现出来,甚至借鹿三的手对田小娥作出裁决,认为她是白鹿原的一切祸事的根源,连白鹿原那场不可遏制的瘟疫之因也假托到田小娥的身上,这自然也就陷入了“女人是祸水”的传统男权思维之中。不满足这类女鬼怪修庙的要求而是建上宝塔好像就可以永远避免瘟疫的发生、大祸的降临,这种男人自以为是的一劳永逸、正义凌然的解决方式却是对田小娥这类悲惨女性们最用心险恶的挞伐。田小娥和黑娃来到白鹿原,不被白嘉轩接纳,后来被鹿子霖所迫,与白孝文苟且,最后为鹿三所杀,这一路呈现的是一个被家门所弃、无家可回、被众人唾弃的悲剧女性的人生,最后居然她死了还要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成为所有女性成长过程中的反面教材。田小娥作为贞洁烈妇的对立面出现在《白鹿原》中,自始至终被白鹿原村民们孤立,没有爱护自己的父母、安稳的婚姻家庭、心灵相通的朋友,命运极度悲惨,男权意识将她一步步推入绝境。
“白灵”是白鹿原上罕见的新女性,如果鹿家最大的叛逆者是鹿兆鹏,那么白家最大的叛逆者就是白灵。白灵生命轨迹紧紧相连着鹿兆鹏、鹿兆海,她短暂的生命经历了与鹿兆海在革命思想萌芽初期的青梅竹马、两情相悦,经历了与鹿兆海因为选择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而导致的关系破裂,经历了因革命追求一致而对鹿兆鹏心生崇拜和爱恋由假夫妇转为真夫妻的婚恋过程。“白灵”这个拥有美貌、智慧、勇敢的佳人,舍弃鹿兆海选择鹿兆鹏,仅仅是出自革命道路的原因,也就让“白灵”这个女子依然成为符号化的女性形象,走的还是美女与英雄的老路,只有真正的新时代英雄才能赢得新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佳人芳心。女人最终还是成为男人的人生附属品和成功道路上的战利品,白灵婚恋选择体现的仍是美人配英雄、男人为主女人为次的男权意识。“白灵”这样的新女性最后也没有走出属于女人应有的人生道路,她的思想与意识最终还是以男人为主、以婚姻恋爱为主,没有彰显出新型女性应有的独立意志。
历史是男人的历史,史诗是男人的史诗,白鹿原上的革命是男人的革命,陈忠实“实录”了关中地区千百年来男性对女性不能平等以待的性别意识。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对女性心理觉醒的深层次记录和揭示,还是需要摒除千年以来长期存在并难以根除的男权意识的作家来完成。《白鹿原》浓郁的“实录”特色,为它成为史诗性作品奠定了基础,它的史诗品格和继承的中国史传传统,都为它增添了厚重的魅力。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时期的人们对它将会进行不同的研究,甚至产生相异的评价,但必须肯定的是小说《白鹿原》对白鹿原世界的建构,是陕西关中乃至中国乡村历史的文学书写中极其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