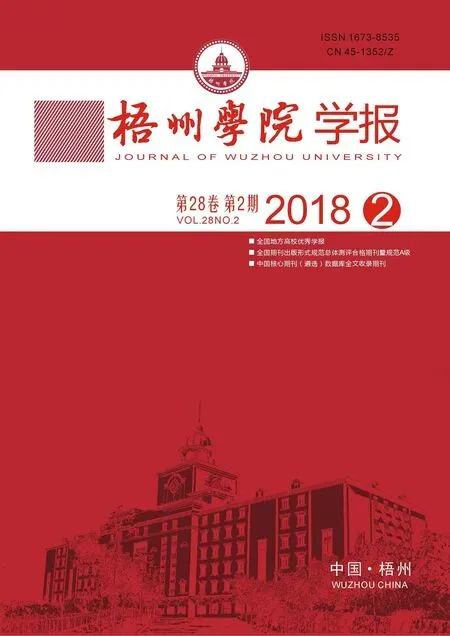李大钊平民主义的政治哲学观
丁忠甫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488)
李大钊是我们党历史上伟大的开拓者,他幼年清苦,立志求学,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他深切感受到民主自由对于我们民族的稀缺,在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他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虽面对白色恐怖也从未退却,最后从容就义。透过对李大钊生平的了解,我们见识了他对于民主自由的渴望,在他的理论主张中,民主自由占了相当的地位。
一、善良政治的理想追求
李大钊认为,“盖人生有欲,政治亦达其欲之一术耳。”他把正义和人道主义看作衡量政治的一个重要尺度,他认为政治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应该是一致的,政治的本质即良好政治理想的本质是需要体现人的本质性追求的,而人生世间最为需要的是民主和自由,进而代议制是可以满足人们实现其本质需要的途径。为此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往往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来宣传和践行自己的目标。李大钊恰是对于政治理论进行探索和对于政治实践躬行的人。他自己曾经这样论述政治理论上和政治实践中进行求索的人们,他把这两类人称为政论家和政治家。李大钊认为“从事于政治者之为政治家,与为政论家,均当听其自择,而无所于优劣。惟必用其所长,率其所言,以终始其事,而后其成功乃有可观。”[1]511-512“政论家宜高揭其理想,政治家宜近据乎事实;政论家主于言,政治家主于行。政论家之权威,在以理之力推法之力,而以辟其新机;政治家之权威,在以法之力融理之力,而以善其现状。政论家之眼光,多注于将来;政治家之眼光,多注于现在。政论家之主义,多重乎进步;政治家之主义,多重乎秩序。政论家之责任,在常于现代之国民思想,悬一高远之理想,而即本之以指导其国民,使政治之空气,息息流通于崭新理想之域,以排除其沈滞之质;政治家之责任,在常准现代之政治实况,立一适切之政策,而即因之以实施于政治,使国民之理想,渐渐显著于实际政象之中,以顺应其活泼之机。”[1]515李大钊对政论家与政治家从6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概而言之,政论家是做理论研究与宣传的,政治家是做具体政治实践的。李大钊自己既做了政论家的事又做了政治家的事。其一,李大钊对于政治理想的论述直指未来,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之际,他热情地讴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作用和进步意义。先后写了多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最为人耳熟的有《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日本帝国主义的赤化观》等等;李大钊不仅仅做理论上的探索阐明,还积极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他在北京大学秘密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织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他还在一些集会场所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演讲,并且还走上街头亲自散发革命理论的宣传传单,一次李大钊和陈独秀一起散发传单被暗探盯住,结果陈独秀被抓,后来陈独秀没有办法继续在北京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李大钊化妆成车夫,亲自驾马车把陈独秀送到天津码头,陈独秀自此去了上海,从此开始了南陈北李创建共产党的伟大实践。其二,李大钊积极投身政治实践活动。如上所述,他亲自参加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组建地下秘密组织开展活动,创办报纸进行理论宣传,提携新人一起战斗等,直到最后被捕和从容就义。那时李大钊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活动的领导核心在活动的,他从来就没有把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分开,而是密切地把二者结合在一起。其三,李大钊参与革命斗争全是处于对时代国家的忧患而无半点私心。在李大钊走上革命道路上曾经有两个人给他很大的震动,一位是他在法政专科学校的同学,一位是他在法政专科学校的老师。那时他们就写下了“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他们壮志未酬身先死。李大钊在就义时非常从容,死后家里非常困难拮据,这是一个全心身为革命的先烈。其毕生追求是希望人们能够过上有德性的生活,后来的革命者正是在这种革命精神的感召下,不断前行的。
二、尊崇民彝找到革命的动力
李大钊在进行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宣传的过程中认识到要使专制制度被推翻必须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他说政治良好与否,关键要“视乎其群之善良得否尽量以著于政治;而其群之善良得否尽量以著于政治,则又视乎其制度社俗于涵育牗导而外,是否许人以径由秉彝之诚,圆融无碍,……,盖政治者,一群民彝之结晶,民彝者,反事真理之权衡也。”[2]341在李大钊看来,民彝才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取法需要合乎民众的根本需要和根本利益,而不能仅仅单方面地好心办事,因为“彼其非常之法,果为政治之良图,而离于其民,于失其本然之价值,不能收功,反以贻害。”[2]338李大钊认识到民彝的力量正是革命所需要的。其一,民彝的力量是符合真理的要求的。民彝也就是人民群众,他们的需求是最为朴实的,他们的需求最终推动着人类历史的运动,发现了民众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又发现为了民众的利益是最为符合真理的,革命的实际行动就是顺应时代的呼唤了。其二,民彝力量的发挥是要求自发自主的。人民群众改变历史的活动是客观的,不是凭主观热情所能造成的,所以在实际的工作中需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而不能干拔苗助长的傻事。其三,民彝力量的发挥是要冲决束缚的。人民群众的力量一旦发挥就将冲决一切阻碍。剩下的事情就是帮助民众来积聚革命的热情。
李大钊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是切实走在人民群众的道路上的。他当时在北京大学的威望之高、在革命队伍中的威望之高都和他坚定走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道路是相一致的。就在1927年李大钊被捕之时,反动军警带来先期被捕的革命工人,让其指认李大钊,这位老工人摇摇头说这个人我不认识。李大钊先生在革命中的这些做法和认识对于当今也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三、平民主义政治理想
李大钊把民主翻译成平民主义,他认为这样才便于接地气,他说自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观历史观被接受以来,很多早年学习的英雄崇拜的观念、圣贤思想等都被打破了,剩下的就只是知道在新时代代之而起的是多数的劳动者,这才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力量。“讫于今兹,工人们曾被历史家,政治家完全蔑视。”[3]而人类的历史从来就不是少数人的历史,也不是由少数人所创造的,历史的真相是由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来创造世界的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因此,历史活动的主人应该属于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人民群众。
对于平民主义,李大钊是这么认识的“平民主义是一种气质,是一种精神的风习,是一种生活的大观,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实在是一个抽象的人生哲学,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理解的产物,实在是濡染了很深的感情、冲动、欲求的光泽。”[4]105他把平民主义看成是包含着人的情感的德性表现和追求,而平民政治的精神在李大钊先生看来包含着这样几层意思:其一,机会公平。在机会公平的前提下,人们在社会生活或政治生活中都可以获得和他们的能力与意愿相一致的实践机会。其二,各安其分的生活心态。“在国家法令下,自由以守其规矩,自进以尽其职分;以平均发展的机会,趋赴公共福利的目的;官吏与公民,全为治理国家事务的人;人人都是治者,人人都非隶属,其间没有严若鸿沟的阶级。国家与人民间,但有意思的关系,没有强力的关系;但有公约的遵守,没有强迫的压服。”[5]676-677李大钊先生认识到民主对于建构基于民主上的社会具有了以下的一些特点。其一,民主是要求自治的。民主不需要别人的强力,更不需要别人的压迫。人民群众不是处于谁人多谁人少的意见,而是在协商的基础上进行自治。其二,民主是要求人人平等的。人人平等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还需要实现实质上的平等,这种平等不仅表现在人民群众在参与政治的能力方面的平等,还有机会上的平等和资源分配、福利分配上的平等,因为资源分配上的平等可以保障能力上的平等得以实现,同时,资源分配上的平等可以使得机会的平等成为可能,人人平等需要摆脱了人对人的依附,需要摆脱人对外在条件的依附,也只有当人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时,平等才能实现,而只有当人是平等的时候,民主的意义才不会因为人的地位的不同而有高下之分。其三,民主需要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之上。李大钊的民主观显然受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影响。人们是独立的个体,人们依据于契约而联合起来。当然这个认识在那时是比较通行的,笔者在此增加一点思考,中国社会是有人伦关系的,一个重人情人伦关系的社会不能随着契约一下子都变成了形同陌路的陌生人,所以这里契约还必须和一定的文化因素相结合。以便更好地发挥规章制度对人的约束作用。其四,李大钊在谈到构建服务型政府时,认为政府不过是公民用来实现自己政治事务的工具,这是具有一定前瞻性意义的。从而也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在那时就具有了对未来政府性质的规划。现在我们提倡政府要增强服务意识,多做便民利民的事。和李大钊先生那时的提法是多么的一致。我们认识到李大钊对民主重要性和民主将要象什么样的认识,接下来需要思考的是民主何以能实现?李大钊说平民主义的真精神是自由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大钊道出了民主实现的条件。
四、自由对于民主实现的作用
李大钊说,“自由政治的神髓,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而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态度,为充分的讨论,详确的商榷,求一个共同的认可。……,自由政治的真谛,不是仗着多数的强力,乃是靠着共同的认可。取决多数不过是表示公同认可的一种方法罢了。”[5]154-155自由所需要的能力是需要有保障自由的政治条件和自由的人的素质条件的。不是我要自由于是便有自由的,自由能力的获得和自由政治条件的获得是互为条件的,当然在这二者中,自由政治条件的获得更为优先。因为只有当人们有了自由政治条件的保障才可以有用来发展个体能力的机会,从而使得个体在自由的政治活动中具有积极参与政治的能力。在李大钊生活的那个年代,外部的自由政治条件是不具备的,更不用说自由的人的条件了,然而他那时能够认识到这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实在是很了不起的。
李大钊赞赏民主,但需要知道民主是需要自由来支撑的,没有自由民主就无法站立,同样没有民主自由也会遭到侵犯,自由也将不保。因此,李大钊对民主进行了如下几个层次的理解:一是,民主对于人的个性的尊重是和社会主义对人的尊重的立场是一致的。民主对于人的个性的尊重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无论人的经济状况、政治地位、文化程度如何不同,都将获得同等的尊重。二是,凡是以他人为手段和工具的行为,凡是对他人进行奴役的行为,都是于民主所不容的,“无论富者统治贫者,贫者统治富者;男子统治女子,女子统治男子;强者统治弱者,弱者统治强者;老者统治幼者,幼者统治老者;凡此种种擅用与治服的体制,均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所不许。”[4]110-111因此,民主也是同旧社会、旧制度决裂的根本因素。三是,民主要能真正贯彻下去,必然需要同旧制度决裂并战斗的,唯有打破旧制度,方能释放出民主的精神,才能革除一切人对人的统治、人对人的战争。四是,民主演进的步骤是先由经济的斗争上升到文化价值观的斗争。最终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破除与重建,即破除掉一个旧世界,重建起一个新世界。李大钊在他的论述中提到了这样一些认识是非常有见地的,不管过去还是将来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其一,他指出民主与社会主义的一些共同点。民主是见不得人对人的残忍的,是见不得人的不平等不自由的,而社会主义也是这样,这为我们理解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开拓了思想上的先河。社会主义本质上是民主的,而民主的精髓是自由,反过来看就可以看出,自由对于民主的保障作用了,自由是一个个体作为人受人尊重的条件,自由是个体自己决定自己并参与政治的自愿,自由还是个体享有平等机会的权力,有了自由的精神,民主的活动就能够开展起来。其二,他指出民主是对人的尊重。人要成为人就不能受奴役,摆脱奴役则是自由,获得自由就可以获得民主,相互之间的关系更深刻了一层。其三,社会主义在那时首先是摆脱经济上的奴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具有决定的作用,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也见出经济力量对于一个人行为和思想的影响。在工人阶级那里更是需要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其四,李大钊在提出社会主义的时候为着要克服经济上的困境,为了要获得自由与民主,为了要实现公平正义,就必须以工人政治来克服当时的现状,一味地追求平民政治,平民政治并不会自动的到来,而发动广大劳工,无产阶级起来行动并进而取得政权和施行无产阶级专政则可以保证社会主义对于经济困境的克服和其他理想的追求。李大钊那时就初步有了这些见识,一方面是和他自身的阅历相关,另一方面是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穿透力相关。所以,从上面关于民主实现手段来看自然少不了自由的争取,而自由的争取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非得有无产阶级的集体行动不可。
五、结论
李大钊从对善良政治的追求开始,探索了近代中国的出路问题,而在那时横亘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很多,如何从众多的问题中发现问题的本质,从而找出疗救的方法就成了那一代先进的中国人的追求,李大钊在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行动中发现了革命的动力,他发现了人类历史的真正推动者不是少数伟大人物而是千千万万的民彝,这些民彝有摆脱奴役的强烈愿望,他们希望获得平等、自由和民主,他们首先需要的是生存的权力,需要摆脱经济上受奴役的状况。后来李大钊在思考平民主义即民主的时候,发现民主有着和社会主义一系列相通的地方,这些共同的追求为民众享有权力、自由、民主以极大的鼓励,而如何实现民主,李大钊对此的思考从民主的本质是自由开始,要获取民主就需要行动的人是个行动上和思想上都是自由的人,而在那时要实现思想上和行动上的独立自由首先需要克服的是经济上的困境。没有经济上的解放和独立就没有办法支撑起民主和自由的行动。至此我们清晰地看到李大钊在民主理论探索和实践中的心路历程:善良正义和德性的政治——民彝的力量的发现——追求民主——实现民主需要自由——要实现自由民主需要克服经济上的困境——无产经济的行动,也即民彝的行动。
[1] 朱文通,等.政论家与政治家:(一)[M]// 朱文通,等.李大钊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2] 朱文通等编.民彝于政治[M]// 朱文通,等.李大钊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3] 朱文通,等.孔道西的历史观[M]// 朱文通,等.李大钊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285.
[4] 朱文通,等.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M]// 朱文通,等.李大钊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5] 朱文通,等.平民主义[M]// 朱文通,等.李大钊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