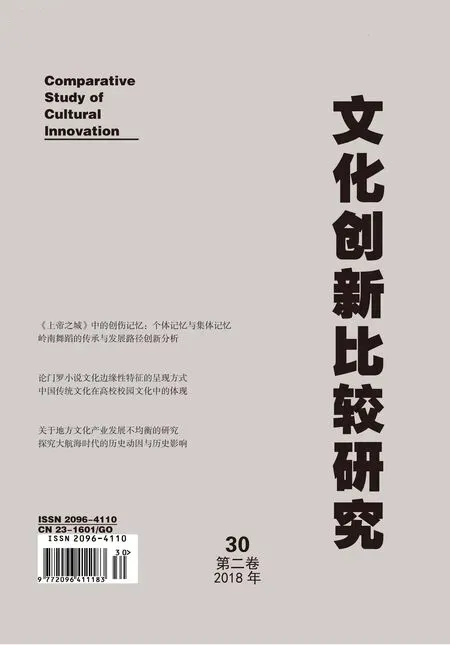《上帝之城》中的创伤记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
谢 凝
(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 110034)
创伤理论的出现,不仅给文学作家提供了一个新的创作思路,也给文学批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并将创伤理论应用于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之中。20世纪是充满创伤的世纪,也是人类印象中最为深刻的时期。尤其是对于犹太人来说,已经渐渐远去的20世纪是而痛苦的。在这一世纪,犹太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人说“二战” 赋予世界以全新的秩序,是新世界诞生的涅槃之火,但对于犹太人来说,“二战”意味着“屠杀”,意味着永远不能忘却的民族噩梦。
“创伤记忆”。创伤经历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一种集体记忆,对战争、屠杀、恐怖事件等历史创伤记忆的研究有助于人类反思历史。对于犹太人来说,创伤记忆的另一个要素就是强调创伤事件在经历者内心深处的深刻体验。犹太人将自己的个体记忆与民族的集体记忆交织在一起,这种创伤不仅带来精神上的打击,更压抑了创伤记忆。创伤记忆在家庭的范围内通过代际交流而传递,在同时代人或有共同经历的幸存者中通过集体记忆来传播和保存,起到了情感宣泄和修复创伤的作用。
“创伤记忆”是指创伤主体对创伤事件的记忆,是一种心理及生理的不正常状态,主要是由严重的创伤事件所引起的。创伤事件以“闪回”、“噩梦”、“意象”等形式在大脑中再次或反复出现。“创伤记忆”包括两个要素,一是创伤必须以强度足够大的精神事件作为诱因,二是强调这种精神事件在创伤主题内心深处的体验。这些“创伤记忆”是对创伤事件及犹太人创伤的见证,是犹太民族创伤记忆讨论的关节点,这种创伤记忆成为美国犹太文学的一部分。
美国犹太裔小说家E.L.多克托罗(E.L.Doctorow)在20世纪末描写犹太人曾经的苦难,利用创伤作为凝聚犹太人的重要精神力量,重新唤醒民族意识,激起了无数犹太人的精神回归。《上帝之城》是多克托罗正面描写犹太创伤的小说,其实仔细剖析多克托罗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犹太创伤一直是他小说里隐含的主题,并且影响着他的小说创作。多克托罗不同的时期对美国犹太问题自始至终的关注和他对犹太传统的珍视和张扬。多克托罗关注犹太民族的历史,并对犹太民族几代人的发展进行哲学思考,利用二战期间犹太人的苦难史,建构了二战期间犹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而且还揭示了犹太人所处的历史和文化困境。而犹太人在格托中的生存及其对纳粹的反抗,犹太人的尊严、英雄主义精神及向往公正和正义之决心和理想也成为其小说《上帝之城》的一大亮点。
《上帝之城》中对于犹太人的创伤记忆,不但体现了多克托罗对犹太族裔意识或身份认同之寻求和反思,而且揭示了犹太人所处的文化、历史困境,建构了犹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多克托罗通过犹太女孩莎拉之父断续的叙述,再现了犹太人的创伤记忆,使创伤记忆成为一种显性的在场,从而使创伤幸存者个人经验成为整个民族创伤的缩影。
小说《上帝之城》发表的时候正值20世纪末期,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屠杀的幸存者和目击者逐渐年老离世,因此将创伤主体的真实感受记录下来成为一个紧迫的任务。创伤主体在严重的精神创伤的作用下,其知觉往往是以对事件的碎片式记忆来储存的。他们往往在创伤之后经历各种记忆碎片,如,视觉碎片、听觉碎片、情感碎片、记忆闪回等等,这些是创伤主体的创伤记忆最初方式;而后随着记忆碎片密度的加大,创伤才逐渐进入创伤主体的潜意识,激发出各种各样的记忆形态。因此创伤事件对于创伤主体的危害不仅仅存在于事件本身,更深深地存在于创伤主体的记忆和意识中。
小说通过对莎拉之父的创伤描写,一步步阐述犹太人的创伤记忆。莎拉的父亲是创伤主体,集中营的幸存者,他在失去记忆之前,将当年在集中营的经历作为创伤记忆藏在心中,并通过口述的方式传递给女儿,之后便的了老年痴呆症,这段创伤经历是由一名犹太作家写进其小说中,才得以记录下来,这便是一种精神遗产传递的含义。在这种状况下,创伤经历有可能无法被吸收而使其记忆碎片被转入其他神经网络。这些无法被吸收的记忆碎片就是“创伤记忆”。创伤主体既无法理解也无法控制所发生的一切,从而不断地被动体验创伤,这令创伤主体痛苦不堪。这种创伤记忆通常会有潜伏期,即创伤主体对创伤事件的记忆仿佛被“封存”起来,当创伤主体经历另一次创伤事件或再次受到相关刺激时,早期的创伤记忆有可能被“激活”。德国入侵前,他父亲曾是大学里的农业经济学家。母亲则在同一所大学攻读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搬进犹太居住区后,“一切都完结了”。在战争前,莎拉之父一家搬到慕尼黑。他曾有过幸福的童年,可是学校“旧耳曼式的通过暴政受教育的原则”却“全是毁灭”的。当他坐在教室因想到“欧儿里得几何”和“毕达哥拉斯定理”而“暗自在微笑”时,老师却声言他对班级带来了“坏影响”而要将他“转走”。此时,他“在一瞬问洞察到了所有人性的秘密”。那就是“权威”和“好战”。此后,“父亲到飞机厂的流水线上干活,母亲到犹太人居住区的学教里教书。后来,限制越来越多,学校也被关闭了,母亲也到城里的劳动大队去了”。他一人呆在家,“等着父母,向上帝祈祷他们会从城里干完一天的活回来”, 有时还带回了一点和立陶宛人交换的偷来的食物。”一天,他的父母出门后,再也没有回来过。他们“被卡车拉出城运到河边的老堡垒里枪毙了”。但他宁愿相信父母仍活着,他们参加了游击队。就在他父母没回来的那天晚上,隔壁的拉比格林斯潘将他送到一个叫斯瑞波尼茨基的裁缝那里,因为“纳粹是不允许让没人照管的孩子活着的”。德国人占领后,犹太人就被赶到破烂的贫民窟里,后来就成了犹太人居住区了。”(李战子,2005)
作为创伤叙事者的莎拉之父身上具备了犹太幸存者们的许多特征。他们在受到精神创伤后,表现为不安与矛盾,陷入早期经历中无法自拔,并将这种记忆和情感变化隐藏在重述创伤事件的过程中。他们会用许多不同的形式挣扎着去遗忘。莎拉之父的叙事是对记忆和历史的一种阐释。他九岁时说话很慢,后来就干脆用外语了。在生命的前三四年不说话,后来又变得结巴。犹太人在民族流散的历史中,他们一直处于被排外的状态,可以说他们一直生活在“外语”的环境中。并且在这种语境中一生活就是几十年。他的这些原本零散的记忆片断在历史转变的过程中,逐渐地经过组织和串联,零散的记忆碎片慢慢地具有了意义。莎拉之父最初并不愿讲述创伤经历,因为他不想让女儿过上一种噩梦般的生活,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记忆的逐渐衰退,他断断续续的叙述成为了幸存者的创伤回忆,而且也成为女儿莎拉对整个犹太民族创伤史的记忆。在《上帝之城》中,佩姆伯顿牧师也对大屠杀了解的积极透彻,但是他了解的越多,就越开始怀疑基督教的原则。他在布道中说向大家传递了自己对基督教的诠释——大屠杀是基督徒对基督教的滥杀,对犹太人的迫害。
多克托罗在小说中对犹太人的创伤记忆的阐述体现出他强烈的犹太意识,他对纳粹的愤怒也表现在他对报复前纳粹的描写之中。莎拉一直努力将格托的纳粹军官施密茨少校送上法庭,却因缺乏充分证据而难以做到。当最终找到格托日记证明其身份时,他却已死亡。由于法律和法庭未能惩罚纳粹对犹太人的罪行,多克托罗又安排了一位前《时报》(Times)记者作为一个复仇者去寻找这些凶手,为被杀的犹太人伸张正义。这些杜撰的故事表明多克托罗想抓住前纳粹并对其进行审判的愿望。
犹太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到严重的压制和排斥,而多克托罗作为犹太后裔,他身上的责任感促使他要向世人展示大屠杀给犹太人带来的集体创伤以及犹太人痛苦的挣扎和奋斗的过程。20世纪末,随着后代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的逐渐同化,犹太人的精神、文化以及生存都出现了多种危机。多克托罗将这种犹太个体及民族的创伤作为主题书写小说,旨在唤醒现代犹太人的民族意识,以此来探索美国犹太文化的未来。在《上帝之城》中,创伤主体的记忆成为整个故事发展的连接点,让读者通过这些故事来了解犹太人的精神创伤。这种对创伤的分担表达了一种想得到集体承认和理解的渴望。
创伤是幸存者精神伤痛的见证,犹太幸存者创伤记忆更是已经成为犹太历史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经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犹太民族的创伤记忆传递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让人们去记住什么,最主要的是怎样去记住这些伤痛。这些伤痛可以是充满恐惧、死亡和威胁的经历,也可以是政治、历史发展历程中的一部分,更可以是一个民族文化记忆的一种形式。创伤记忆在作家们不断的重述中被重建、被再现。只有这样才可以帮助我们犹太民族创伤记忆的再现过程进行特征描述和归类,从而更好地在概念和经验上揭示和解释创伤事件的原因及其给创伤主体乃至整个犹太民族所带来伤痛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