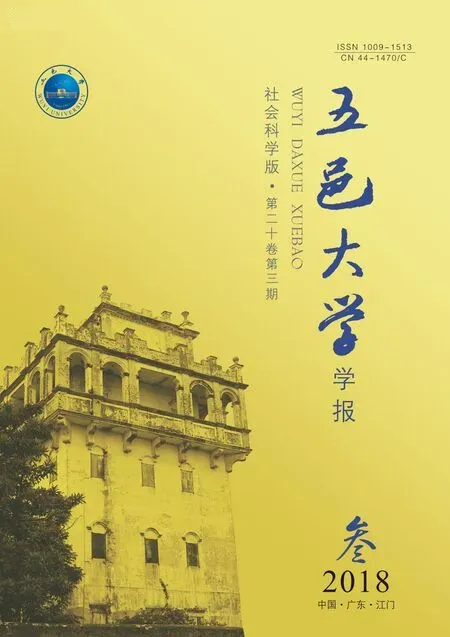从《搜神记》的归类看古代目录学的小说观
张 泓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社科部,浙江 杭州 311231)
在《隋书·经籍志》中,《世说新语》被归入子部小说类,而《搜神记》则被归入史部杂传类。内容真实的《世说新语》被归入小说,而荒诞不经的《搜神记》被归入历史,对这一似乎不合情理的归类,陆续有学者提出自己的见解。但仔细阅读他们的研究论文,可以发现其研究标准无一例外都是文学类小说观,而用现今的文学类小说观来评价古代的目录学小说,总觉得其研究有点牛头不对马嘴。
一、《隋书·经籍志》对两者的归类
《隋书·经籍志》对史部杂传和子部小说的论述有很明显的区别,杂传为:
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非独人君之举。……是以穷居侧陋之士,言行必达,皆有史传。……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原,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鲁、沛、三辅,序赞并亡,后之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1]981-982
可见杂传种类包容甚广,隐士、高僧、孝子、忠臣,只要是君主言行之外的记载均可归入杂传,甚至神仙鬼怪等内容也可列入其中。而小说则是:
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涂(途)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而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1]1012
即小说是来自于街谈巷语的道听途说,是朝廷以此了解民情的一种手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清谈之风的兴起,民间产生了大量品评他人的言论,这些言论是典型的街谈巷语,通过这些言论,朝廷可以体察民情、了解风俗,刘义庆作为刘宋王朝的宗室,自觉地承担起这个责任,搜集民间言论,整理成《世说新语》,所以把它归入小说类确实是适得其所。
从源头来说,《世说新语》等小说也应该归入子部,“志人小说这种题材类型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诸子散文,《论语》和《孟子》记载了孔丘和孟轲的某些言行,许多片段言论和行为汇集成书,这种言行记录方式成为志人小说文体的基本特征之一。”[2]112如果把《世说新语》和《论语》作比较,很容易发现它们在形式上的相似之处:
徐孺子年九岁,尝月下戏。人语之曰:“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3]30-31
这段记载和《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记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论语》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反映孔子的思想,形式上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世说新语》从书名即可知其是“世间众说的最新记载”,也是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通过人物言行反映其思想,只不过因为其言论过于琐碎,没有任何体系,不能归入九流中任何一流,所以只能归入子部中之小说家。
杂传体的创作源头则来自于史部,既名之曰杂传,一定和传有关,赵翼曾道:“惟列传叙事,则古人所无。古人著书,凡发明义理,记载故事,皆谓之传。……是汉时所谓传,凡古书及说经皆名之,非专以叙一人之事也。其专以之叙事而人各一传,则自史迁始,而班史以后皆因之。”[4]可见杂传的写作一定是在《史记》、《汉书》等纪传体被人喜闻乐见之后,有人模仿其创作方法,记载各种各样之事,故称为杂传。正如程千帆所说:“西汉之末,杂传渐兴,魏晋以来,斯风尤甚,方于正史,若骖随靳。其体实上承史公列传之法,下启唐人小说之风,乃传记之重要发展也”[5]。
杂传中有一类是叙述“鬼神奇怪之事”的,而小说则是采自民间的街谈巷语,从这一个角度来说,《隋书·经籍志》把《搜神记》归入杂传、而把《世说新语》归入小说确实是准确的归类。
二、从篇幅看《隋书·经籍志》的归类
《搜神记》和《世说新语》除了起源截然不同以外,两者在形式上有更重要的区别。仔细阅读《搜神记》和《世说新语》就可以发现,这两部书籍虽然篇幅都短小,但其叙述方式有很明显的不同:前者是杂传体,而后者则是杂记体。“中国叙事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有写实和写意两种艺术表现形式,形成两种艺术流派。写实注意情节的完整合理以及细节的周到逼真,而写意则表现着一种诗化倾向,不注重情节,甚至淡化情节,追求意境,追求意趣的隽永”[2]85。换言之,写实的是杂传体,而写意的则是杂记体。比如《搜神记》里著名的《董永》:
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疋。”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6]14-15
这就是典型的杂传体,它从董永的故里、家庭情况、性格等谈起,一直写到与织女的相遇为止,就如史传中某人的传记类似。它有一定长度的篇幅,故事比较完整,内容比较复杂,情节比较曲折,突破杂记体丛残小语式的结构,注意环境描写和艺术形象的塑造,以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作为作品的结构中心,谋篇布局与传记十分接近,所以应该归入史部杂传。
而《世说新语》中的记叙则是典型的杂记体,它仅仅记载一个片段,而对身份、故里等毫不涉及,例如: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3]209
该则笔记记载的仅仅是一个片断场景。纵观整部《世说新语》,如果不是截取生活中的某个片断,就是刻画人物的某个瞬间,要么描写人物之间的几句对话,有时甚至只是人物的某个侧影,正如鲁迅所评价:“六朝人小说,是没有记叙神仙或鬼怪的,所写的几乎都是人事;文笔是简洁的;材料是笑柄,谈资;但好像很排斥虚构”[7]。
综上所述,《搜神记》和《世说新语》尽管篇幅都较短,但相比较而言,前者篇幅比后者要长得多,所以石昌渝曾道:“杂史杂传虽非正史,但篇幅并不短……古小说却不拘体例,一本书可以写许多人许多事,每篇独立,而且篇幅短小,我们习惯称它们为尺寸短书。”[2]108而陈平原也道:“像记述周处由横行乡里到弃旧图新,再到成为忠臣孝子那样类乎传记的文字,在《世说新语》中可谓绝无仅有;截取最能体现主人公精神风貌的生活片段,而且点到即止,让读者自己品味,这才是其主要的叙述风格。”[8]229其实,《世说新语》等之所以被称为小说,本身就与其篇幅短小有关:“轶事小说之‘小’,也含有限定其篇幅的意思。桓谭称‘小说’为‘短书’,王充称之为‘短部小传’、‘短书俗说’,刘知几名之曰‘短书小传’、‘短才小说’,用语大体相同,内涵亦基本一致”[9]。
正因为《搜神记》和《世说新语》的叙述方式有如此明显的区别,所以《隋书·经籍志》把前者归入史部杂传类,而把后者归入子部小说类。
三、从叙述视角看《隋书·经籍志》的归类
除了篇幅长短以外,《搜神记》和《世说新语》的叙述视角也截然不同。叙述视角可以分为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等,而最常见的第三人称又可分为全知视角、受限视角和客观视角。全知视角中叙述者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他的叙述没有任何客观限制,即便世界上永远不可能有人知道的事情也可以真实再现,例如某人自杀前的心理独白。受限视角是从作品中某个人物的角度出发,作者的叙述不能超越这个人物的认知,可以描写此人的心理活动,但不能描写其他人的心理活动,也不允许描写此人不可能了解的情况。客观视角中的叙述者是纯客观地描写,叙述者从客观的角度了解事件,所以绝对不能直接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而只能记录人物展现出来的语言和行为。
历史作为一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重要文体,其撰写者必须如同上帝一样具有洞悉世事的能力,所以历史叙事一般会采用全知叙事。但全知叙事会让事件失去真实感,所以其中又会穿插限知叙事。《左传》中描写鉏麑刺杀赵盾,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这一段描写其实是鉏麑的内心独白,作者之所以把它写成鉏麑的自言自语,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历史事件的真实感。因为从真实的角度来说,自杀前的内心世界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得知的。
《史记》也采用了在全知视角中穿插限知视角的手法,叙述事件时经常从其中人物的角度出发。如《淮阴侯列传》中描写韩信逃亡的经过:“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郊,请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这里的“我”即是史书中人物韩信,而并非叙述者司马迁。韩信并非全知者,他并不知萧何到底有无告知,尽管穿插了心理描写,照样是限知视角。
《搜神记》的叙事视角完全是史家视角,和《史记》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也是在全知视角中穿插限知视角。比如《宋定伯遇鬼》只写宋定伯的感觉却不写鬼的感觉,《刘晨阮肇》只描写刘晨阮肇的心理却不写仙女的心理,采用的均是受限的全知视角,因为鬼和仙的心理作为凡人是无法得知的,石昌渝将之评价为“志怪小说采用单人物角度叙述”[2]127,非常准确,这是典型的在全知视角中插入某一人物的有限视角,从某一人物的角度看人看事。
《世说新语》的叙事则是典型的客观视角,作者绝对不涉及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王子猷访问戴安道一则,仅仅描写王子猷的言行,让他自己说出“乘兴而行,兴尽而返”,具体的心理变化,作者和读者一样根本无从得知。淝水之战得胜时,谢安继续从容下棋,具体的心理变化,作者也和读者一样根本无从得知。
杂传是历史中的一类,《搜神记》的叙事视角是纯粹的史家视角;小说是街谈巷语,《世说新语》的叙事则是典型的客观视角、新闻视角。从叙事视角的角度来说,在《隋书·经籍志》中,《世说新语》被归入子部小说类,而《搜神记》被归入史部杂传类,也是非常准确的归类。
四、唐以后《搜神记》的归类
如上所述,《隋书·经籍志》将《搜神记》归入史部杂传中是最符合目录学标准的归类,所以《旧唐书·经籍志》因袭《隋书·经籍志》,也将《搜神记》归入史部杂传鬼神中。但欧阳修等所撰的《新唐书·艺文志》却将《搜神记》等和鬼神相关的二十六家归入了子部小说家中,此后《搜神记》在传统目录学中的归类一直被归入子部小说家。
现今众多学者都认为宋代以后将《搜神记》归入小说家是因为小说是虚构的文体,而神仙鬼怪之类很明显并不真实,所以这种归类代表了古人小说观的成熟,其实这是对传统目录学小说观的误解。
“不管是归在子部还是归在史部,传统目录学所指的‘小说’都不容许内容有虚构,丛残小语也好,刍荛狂夫之议也好,都必须是实录。”[10]从叙述视角来说,客观视角肯定比全知视角更为真实可信,《世说新语》等小说采用纯客观视角就是为了保证其内容的真实性。研究传统目录学的小说,一定要把握一个关键:此小说是子部中的小说,并非文学中的小说。所以将《搜神记》归入小说与内容是否虚构无关,却与其内容的来源途径有关。
众所周知,最初将《搜神记》归入小说的是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他将《世说新语》等以记言为主的称为小说中之琐言者:“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已。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此之谓琐言者也”[11]459;而将《搜神记》等以记事为主的称为小说中之杂记者:“阴阳为炭,造化为工,流形赋象,于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此之谓杂记者也”[11]462。刘知几所谓的小说是历史中的一类,并不归入子部,他将《搜神记》和《世说新语》一起归入小说,并不是将原本属于史的内容划入子,而是将原本属于子的内容划入史。《史记》采用史传手法,描写人物委曲详尽,《搜神记》也是如此,所以《隋书》将其归入史部杂传类;《论语》采用子部手法,叙述事件简约梗概,《世说新语》与此类似,所以《隋书》将其归入子部小说类。刘知几却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将其均归入史部,前者为杂记,后者为琐言。可见,《隋书》以形式区分,《史通》以内容和形式相结合加以区分,但均不涉及虚构、真实等问题。
如果以真实作为标准,无论在叙述形式还是表现内容上,史书都并不比目录学小说更可靠。在叙述形式上,无论《左传》还是《史记》,因为采用了全知视角的叙述方式,所以其中的语言描写并不具有纪实性,难怪方中通曾道:“苏、张之游说,范蔡之共谈,何当时一出诸口,即成文章,又谁为记忆其字句。”[12]吴汝煜也道:“李斯厕鼠之叹,有谁当场笔录。”[13]而且在《史记》中甚至有大量的心理描写,如《高祖本纪》中“高祖乃心独喜,自负”、《淮阴侯列传》中“上且怒且喜”等。这就令《史记》在后人的心目中显得非常不可信,但照样不影响它在史书中的崇高地位。在表现内容上,刘知几曾道:“古之国史,闻异则书。”[11]95可见,唐前史书作者的取材并不完全舍弃传说与荒诞内容,而是经常采纳一些志怪材料,甚至可以说志怪是史书的重要内容,如《史记·殷本纪》就记载:帝辛“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汉书·五行志》中甚至记载更为荒诞的内容:“史记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马生子而死”。
“大概每一个民族历史的发展,最初都是神话与古史不分,其次便是故事与史实的混合,经过此二阶段后,历史乃有单独的发展。”[14]就叙事的主体而言,有民间叙事、文人叙事、官方叙事等,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隋唐以前的史书将这三种叙事互相联系、互相转化,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撰史的风气非常盛行。而隋唐以后则完全抛弃了民间叙事,隋文帝明确下诏道:“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1]38在此种背景下,隋唐及其以后的历史和以前有很明显的区别,“唐宋以还,官修史书取材僵化、视角单一的问题多为人诟病。……日益强化的官方色彩与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使修撰者日趋保守,不论是内容还是态度上,都僵化凝固,不同的史实和人物,面目趋于一致”[15]。
民间叙事已被史书抛弃,而《搜神记》的内容和题材却大多来自民间传说,正如《搜神记·序》中所道:“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6]2可见其题材来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民间传说,采集途径和小说是一模一样的。
综上所述,从宋代开始,《搜神记》之所以被归入小说,主要原因在于其题材来源。
五、小 结
总之,四部分类法对文体的归类有很严格地要求,在史和子两者中,以叙述为主的入史,以议论为宗的入子。《世说新语》源于《论语》,是典型的杂记体,自然被归入子部小说类;而《搜神记》源于《史记》,则归入史部杂传类。唐以后对史书的要求愈加苛刻,史书记载的内容必须来自官方正统记录,《搜神记》来自民间传说,即班固所谓的稗官,所以被归入子部小说类,而与其是否神怪故事无关。“我们的小说理论从诞生就是一个彻头彻头(尾)的殖民式理论体系”[16],今人以西方的小说观来考察古代小说,认为小说是虚构的故事,《搜神记》既然在古代被归入小说,自然是因为其中的神鬼故事,如此把文学小说和目录学小说混为一谈,越研究离事实真相越远。
“唐人小说中,被后世命名为‘传奇’者……唐人宋人提及此类作品,多以‘杂传’或‘传记’名之。”[8]254换言之,今人所谓的唐传奇,古人是将其称为杂传的,而众所周知的是:“小说到了唐人传奇,在体裁和宗旨两方面,古意全失。”[17]即杂记体的小说和杂传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体。杂记和杂传在叙事上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新闻叙事,而后者则是历史叙事。纪昀曾指责《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就是指其将杂记体和杂传体混为一谈。例如《聊斋志异》中卷七《赤字》就是典型的杂记体小说,只有记录没有创造,只有叙述没有描写,而其他众多的篇章却又是杂传体。最正宗的目录学小说必须是新闻叙事的杂记体,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世说新语》和《阅微草堂笔记》等才是真正的传统目录学小说,所以纪昀指责《聊斋志异》体例驳杂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将《搜神记》和《世说新语》一起归入子部小说类,照样犯了体例驳杂的错误,尽管这是不得已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