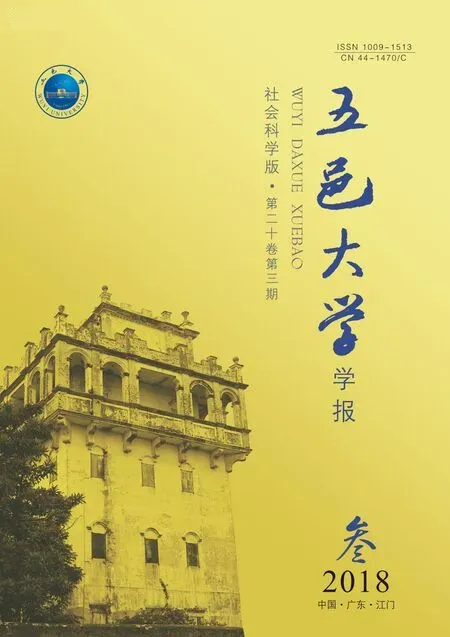江门学派的道统体系
刘红卫
(五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北宋时期,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新的诠释,构建了以宇宙生成论、本体论、工夫论为核心的新儒学理论体系。南宋时期,因受到战乱、南北分裂及民族问题的困扰,新儒学出了分化,形成了朱子学和陆学两个主要流派。元朝建立后,朱子学基本上占据统治地位。明朝建立后,大一统的历史文化背景为儒学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了机遇。吴与弼从《伊洛渊源录》中洞察了二程新儒学的理论体系,受此启发,他的儒学思想较之朱子学,风格为之一变,阐发新儒学的“自然”理念成为吴与弼儒学的重要特征。吴与弼儒学对明代儒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吴与弼的学生胡居仁、娄谅、陈白沙对他的儒学思想的阐发基本上奠定了明代儒学的发展趋势。胡居仁阐发了吴与弼的理学思想,形成了余干之学。娄谅注重自然、易简的学术风格对王阳明有一定的启发。陈白沙则由吴与弼儒学上溯至周敦颐、二程,比较全面地继承了二程新儒学的宇宙生成论、工夫论和本体论体系,形成了江门学派。
一、 江门学派道统体系的师承关系
江门学派由陈白沙创立,经由湛若水、唐枢、许孚远、刘宗周、黄宗羲依次师承,被学者称之为濂洛之学。对江门学派道统体系的形成和传承具有重要作用的是陈白沙、湛若水和刘宗周。陈白沙师从吴与弼,是将崇仁学派与江门学派贯通的桥梁。湛若水师从陈白沙,是整理、汇总、阐发陈白沙心学思想及将江门学派发扬光大的关键人物。刘宗周是江门学派在浙江一带发展、传承的重要人物,他与阳明后学的儒、释之辩,以及他与东林党人的关系进一步佐证了江门学派晚期的道统脉络。除了依次师承的陈白沙、湛若水、唐枢、许孚远、刘宗周、黄宗羲之外,在江门学派的早期和中晚期也有几个人物对于江门学派核心思想的阐发和传承具有很大的影响。在陈白沙的弟子之中,陈白沙比较器重而且对传播江门学派比较重要的,除了湛若水之外,还有张诩、林光和李承箕。湛若水的弟子之中,除了唐枢之外,还有蒋信等人。在江门学派中后期的重要人物当中,除了上文提到的许孚远、刘宗周、黄宗羲之外,冯从吾的影响也至关重要,他是将江门学派与关学贯通的桥梁。
江门学派理论体系的源头来自吴与弼创建的崇仁学派。关于陈白沙与吴与弼的师承关系,学者有不同的见解。例如,《明儒言行录》的作者沈佳认为陈白沙师从吴与弼期间,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明儒言行录·吴康斋》云:“白沙来受学,先生绝无讲说,使白沙劚地植蔬编篱。康斋作字,使白沙研墨,或客至则令接茶。如是者数月而归。”[1]沈佳得出如此结论的依据是什么?《明儒言行录》中并没有给出结论的依据来源,但从陈白沙对这段求学历程的描述中可以得出蛛丝马迹。陈白沙《复赵提学佥宪》云:“仆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日靠书册寻之,忘寝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2]145“未知入处”意思是对吴与弼儒学不得其门而入,“卒未得焉”指回归江门之后继续对吴与弼儒学进行思考、琢磨,仍然没有收获。此外,张诩《白沙先生行状》云:“自临川归,足迹不至城府。……闭户读书,尽穷天下古今典籍,旁及释老、稗官、小说。彻夜不寝,少困则以水沃其足。久之乃叹曰:‘夫学贵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后博之以典籍,则典籍之言我之言也。’”[2]879从张诩的描述来看,陈白沙的学问源自“自得”,而非源自吴与弼。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云:“先生学宗自然,而要归于自得。”[2]864由以上三段材料中所透露的信息来看,陈白沙师从吴与弼这一段时期似乎没有大的长进,而他以后的学术成就是靠他自己体悟出来的,即所谓自得。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陈白沙师从吴与弼真的无所得吗?事实并非如此。陈白沙《祭先师康斋墓文》云:“先生之教不躐等,由涵养以及致知,先据德而后依仁,下学上达,日新又新。启勿忘勿助之训,则有见于鸢鱼之飞跃;悟无声无臭之妙,则自得乎太极之浑沦。弟子在门墙者几人,尚未足以窥其阈域。”[2]107其中“启勿忘勿助之训,则有见于鸢鱼之飞跃;悟无声无臭之妙,则自得乎太极之浑沦”这句话,恰如其分地反映了陈白沙心学本体论和工夫论的核心内容,是江门学派理论体系的核心构架。“鸢鱼之飞跃”与“太极之浑沦”讲的是江门学派以道体诠释心体的路径及“本体自然”[2]776的本体论体系,“勿忘勿助”讲的是江门学派“勿忘勿助之间”的恰到好处的体认、体证工夫。陈白沙以尊师重道的精神将江门学派的源头归之于崇仁学派,是符合客观事实的。那么如何解释“未得”与“自得”呢?所谓“未得”要从两个层面分析:在求学过程的层面,沈佳所谓的“未得”指的是吴与弼让陈白沙研墨、接茶及参加劳动,而不是让陈白沙利用求学的宝贵时间潜心学术。实际上,在实践生活中体认、体证儒学的哲理正是吴与弼的教学方法。他不仅仅对陈白沙如此,对其他的学生也是如此。例如,娄谅是上饶的大户,平时不务细务,求学吴与弼时,吴与弼与门人亲耕,召娄谅前去观看,以此点拨娄谅儒学需要进行笃的体证。娄谅由此折节,事必亲务,学风为之一变。吴与弼让陈白沙研墨、接茶及参加劳动,是让陈白沙从生活实践中体证儒学的哲理。江门学派继承了吴与弼笃实的体认、体证方法,在充分理解、掌握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来诠释人的精神世界,湛若水将之称为“随处体认天理”。“未得”的第二层内涵,即谓陈白沙师从吴与弼而没有收获。事实上,此处对“未得”的理解与陈白沙的原意是有分歧的。陈白沙在师从吴与弼之前,走的是传统理学即朱子学的路径。朱子学阐发的核心理论是性体与仁体,性体讲的是性、理,亦即牟宗三所谓“只存有而不活动”[3]。将性体置于生生不息的生命体的视域下审察即仁体,仁体审视的仍然是性、理。陈白沙在师从吴与弼之前,他所理解的儒学的核心理念即性体、仁体;师从吴与弼之后,接触到了吴与弼对心体的表述。仁体与心体的区别在于:仁体表述的核心理论是性与理,是将性与理置于鲜活的生命体的视域下进行审察;心体表述的核心是体用关系。程颐提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体用关系之后,明代心学心体阐释的主要对象就是“体用一源”的体用关系。吴与弼以敏锐的嗅觉洞察到二程新儒学的“体用一源”的体用关系对于儒学发展的重大意义,他以“自然”与“勿助”来理解和阐释这种体用关系。与此后陈白沙提出的“本体自然”、王阳明提出的“良知流行”、湛若水提出的天理流行、冯从吾提出的道心流行而言,吴与弼儒学的本体论尚是一种不甚成熟的范畴体系。吴与弼对心体的阐发,陈白沙理解得尚未透彻,也就是对从性体、仁体上升至心体,由朱子学重新回到二程新儒学这一新的变化,陈白沙尚未完全理解,他的心理处于一种矛盾、彷徨的状态,此即所谓“未得”。这种矛盾、彷徨的心态是陈白沙结束求学而返回江门的主要原因。自此之后,这种矛盾、彷徨的心理一直困扰着陈白沙十余年之久。这十余年之间,陈白沙一直在反思、琢磨,期间由于用功过度而几致心疾,直到他在江门风景如画的自然环境中放松身心时,看到万物生生不息,各遂其性,联想到二程“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4],由道体之承体起用、即体即用,联想到心体之承体起用、即体即用的体用关系,亦即由道体之自然流行联想到心体之自然流行,方才茅塞顿开,豁然贯通。陈白沙儒学的理论体系包括宇宙生成论、本体论、工夫论三个组成部分,每个部分都与吴与弼儒学有着渊源关系。吴与弼注重在实践中去体证天道、天理,江门学派亦是主张在体认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阐发人的精神世界,陈白沙和湛若水明确提出了“随处体认天理”的体认路径。在本体论方面,吴与弼虽然没有提出完整的本体论体系,但他对自然的阐释即蕴涵着心体承体起用、即体即用的体用关系,陈白沙在吴与弼自然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本体自然”的本体论体系。在工夫论体系方面,吴与弼明确继承了二程的“勿忘勿助”的体认、体证工夫,并将之言传身教于江门学派,江门学派以“勿忘勿助之间”作为体认、体证工夫的恰到好处。
在江门学派的道统体系中,湛若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对陈白沙思想的梳理、总结为后来的学者认识、研究陈白沙心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江门学派传承的后期,刘宗周也是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唐枢、许孚远列入甘泉学案,这两个人属于江门学派不存在疑问。但黄宗羲对许孚远的学生刘宗周单独列传,引起后世学者分歧。对于刘宗周的学派划分,不应该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和限制,不能因为刘宗周生长在浙江而理所当然地将他划归为阳明后学。划分刘宗周的学派归属,要依照两个客观的标准:一个是师承关系,一个是儒学思想的内涵。首先,从师承关系来看,刘宗周从小跟随外祖父章颖学习,陶望龄等人也师从章颖。但随着刘宗周的成长,他对阳明后学的理论始终抱有质疑。考中进士后,他师从许孚远,数次就正许孚远,才解决他在学术上的困惑。他与许孚远另外两个学生冯从吾、丁元荐相互推重。在许孚远去世之后,他与注重笃实体证的高攀龙等东林党人走在一起。因此,从师承关系上讲,刘宗周应该归属江门学派。其次,从儒学理论的体系上讲,刘宗周儒学和阳明学、阳明后学是完全不同的,而是继承了江门学派中正、自然的儒学理念和笃实的体证工夫。其一,从德性进路来讲,刘宗周遵循了江门学派以道体诠释心体的路径,他的自然观与阳明学、阳明后学的自然观是不同的。例如,刘宗周提出“意”为心之定盘针,此“意”之萌芽与自然界之“一阳来复”相互对应、相互参照。其二,在工夫论上,刘宗周以诚意、慎独为主要修养工夫,这与阳明学以单提直指、正念头为核心的修养工夫不同,与阳明后学中的现成良知派以易简为特征的体认、体证工夫亦不同。其三,在本体论上,刘宗周心体之承体起用、即体即用的体用关系是以“意”为本原而萌发的,这与阳明学及阳明后学的良知流行以良知为本原而萌发不同。以意为本原而萌发,与江门学派的本体自然、天理流行、道心流行的本体论体系是一脉相通的,只不过刘宗周以“意”为心之定盘针的理论的提出,更进一步从本原上阐发了本体自然、天理流行、道心流行的原始根据。关于刘宗周究竟归属江门学派还是阳明后学的分歧,与一则重要的史料相关,即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师说》中纪录刘宗周对陈白沙的评述。《师说》对陈白沙心学有“似禅非禅”的论断,学者往往根据这一论断而将刘宗周排除在江门学派之外。对这一则史料需要仔细地甄别。《师说·陈白沙》出自刘宗周所著《皇明道统录》,成书比较早,是刘宗周对陈白沙心学早期的认识。而刘宗周对陈白沙心学的认识有一个由质疑到肯定的过程,其佐证资料出自《学言》,而《学言》的成书时间要比《师说》晚。《学言》曰:“只‘无欲’二字,直下做到圣人。前乎濂溪,后乎白沙,亦于此有得。”[5]401又曰:“‘静中养出端倪’,今日乃见白沙面。”[5]446刘宗周在会讲中曰:“静中养出端倪,端倪即意,即独,即天。”[5]517以上佐证充分说明了刘宗周对江门学派的肯定。
二、 江门学派道统的思想理论体系
江门学派的思想理论体系由宇宙生成论、工夫论和本体论三部分组成,三个组成部分联动成一有机整体。宇宙生成论是江门学派理论体系的根基,一本论是宇宙生成论的核心内容。江门学派认为“气化”是宇宙及天地万物产生、发展的根源,人既然是天地的一分子,那么就要将人类社会的发展放到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中去审视。在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阐发人的精神世界是江门学派的基本原则,即以道体诠释心体、心体与道体相互印证。以此为起点,江门学派在德性进路上坚持以道体诠释心体的路径,以道体中正、自然的特质阐发心体中正、自然的理念,从而避免了对心体阐发的随意性及对体认心体易简性的过度诠释。江门学派在工夫论上遵循“随处体认天理”的路径,强调笃实的体认、体证,以“勿忘勿助之间”为体认、体证的恰到好处。在本体论上,江门学派在遵循以道体诠释心体的路径下,在道体承体起用、即体即用的体用关系的参照下,形成了心体之本体自然、天理流行、道心流行的本体论体系。
北宋四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在构建新儒学体系时,遵循了以道体诠释心体的路径,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先秦儒学天人合一思想全新的阐发。与先秦儒学不同之处在于,北宋四子以本体论作为阐发天人思想的核心,心体与道体构成了新儒学本体论的两个支点。气化论、天人一本及道物无对构成了北宋新儒学天人关系的核心内容。江门学派经由吴与弼儒学而上溯至濂洛之学,继承了北宋新儒学的宇宙生成理论。江门学派宇宙生成论的核心是气化论,以及建立在气化论基础上的天人一本及道物无对理论。“惟仁与物同体”[2]884是江门学派一本论思想的典型体现。陈白沙诗云:“窗外竹青青,窗间人独坐,究竟竹与人,元来无两个。”湛若水注云:“动植虽殊类,而所以为生者,本乎宇宙一气之浑然同体。”[2]784“一气之浑然”是江门学派一本论的物质基础。湛若水在解释“人者,天地之心”时说:“人如何谓天地之心?人与天地同一气,人之一呼一吸,与天地之气相通为一气,便见是天地人合一处。”[6]529“相通为一气”是天人一本的物质基础,从形而上的角度讲,天人一本的核心内涵是性、理相通。湛若水曰:“性者,天地万物一体者也。”[7]141又曰:“性者,心之生理也,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8]185“夫子川上之叹,子思鸢鱼之说,及《易》‘大人者天地合德处’见之,若非一理同体,何以云然?”[7]144湛若水进一步指出“理一即性一,性一即情一”[8]65,学者通过澄心去欲的修养工夫,纯熟之际便能实现“以仁存心,视万物为一体”[8]230、“浑然灿然,本同一体”[9]。湛若水的学生蒋信深得湛若水的真传,他说:“孔门精神命脉所在‘物我同体’四字耳。”[10]338《九山读书记》云:“蜀有号斗阳子者,尝游道林子之门,闻万物一体之学,以为从之没由也。”[10]293可见,万物一体之学已经成为江门学派的理论标志。以气化论作为儒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对江门学派的长远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也是江门学派与阳明学、阳明后学发生分歧的根本点。以气化论作为儒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意味着江门学派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的充分尊重的基础上的,这决定了江门学派的德性进路上是以道体诠释心体,工夫论的路径必然是随处体认天理。随处体认天理的工夫论论,将江门学派与重内轻外的阳明学、阳明后学区分开来;以道体诠释心体,给江门学派阐发心体设定了客观、科学的范畴,以道体中正、自然的特质阐发心体中正、自然的理念,避免了对心体阐释的随意性,即避免了认知觉为性而导致的流禅或狂肆,从而在本体论上将江门学派的本体自然、天理流行、道心流行与阳明学、阳明后学的良知流行区分开来。江门学派之所以有强劲的生命力,归根结底还在于其对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尊重及在此基础上对人的精神世界的阐发。
随处体认天理的体认路径、勿忘勿助之间的体证工夫、以静坐为形式的修养工夫构成了江门学派工夫论的基本内容。“随处体认天理”明确指向人伦之理及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前者指向心体,后者指向道体,随处体认天理就蕴藏着心体与道体相互引证的内涵。在修养工夫上,江门学派以“勿忘勿助之间”为体认、体证工夫的恰到好处。“勿忘”即提撕、唤醒的工夫,亦即惺惺法,时时提醒而固执于善。“勿忘”是朱子学最重要的修养工夫。“勿助”有三层含义:其一,由恻隐之心、亲亲之情达致仁、善是一个顺理推演的过程,在逻辑上无须助长;其二,道体承体起用、即体即用的体用关系可以类比心体承体起用、即体即用的体用关系,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体用关系,无须助长;其三,致力于儒学是至广大的事业,容不得急于求成,容不得助长。江门学派的修养工夫在“勿忘”与“勿助”之间即在儒学体证的艰辛性与易简性之间寻求平衡,体现了儒学体证工夫的科学性。在修养工夫的形式上,静坐是江门学派的显著特征。陈白沙的静坐既非禅定,也非坐忘,而是一个反复思索、琢磨、体认、体证的过程。不能因为陈白沙主张静坐而认定陈白沙流禅,不能因为静坐与禅定的形式相同而一律归之为禅定。朱熹也有静坐的修养工夫,朱熹曾经谈论过静坐时的数息法,陈白沙亦谈论过数息法,因此,要在静坐与禅定之间仔细地甄别。陈白沙临终前曾作诗以澄清自己与佛、道的关系,他说:“托仙终被谤,托佛岂多修,弄艇江门月,闻歌碧玉楼。”[2]897陈白沙知道自己因静坐而受到流禅的误解,这种误解对他的仕途可能造成莫大的伤害,例如海南的丘濬就因儒、佛之辨而阻挠了陈白沙的仕途。尽管如此,即使在晚年工夫纯熟的境界下,陈白沙始终认为静坐是修行儒学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它可以使学者摆脱世俗事务的牵扰,而静下心来进行体认、体证。在陈白沙的工夫体系中,静坐与随处体认天理是儒学休养工夫的双翼,静时涵养与动时省察均很重要,要动、静夹持,工夫纯熟时方能贞定德性,即“动亦定,静亦定”[2]702。随处体认天理、静坐及“勿忘勿助”是构成江门学派工夫论体系的三个支点,是江门学派强劲生命力的有力保障。
在江门学派的本体论体系中,道体与心体是两个支点。陈白沙《偶得寄东所之二》云:“岂无见在心,何必拟诸古?异体骨肉亲,有生皆我与。”湛若水注曰:“见在心者,人之本心,古今圣愚所同有,而何必拟古圣人之心哉?此二句指出心之本体也。又言民吾同胞,其实骨肉之亲。而天地间凡万物有生者,皆我之与,即浑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意。此二句指出道之本体也。然以此心会此道,一而已矣。”[2]780以心体类比道体,心体与道体相互印证,由道体之承体起用、即体即用开出心体之承体起用、即体即用,此即陈白沙的自然之学。湛若水将陈白沙心体的核心内涵概括为中正、自然,中正为大中至正之体,自然为即体即用之用。江门学派中正、自然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明代儒学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中正理念取代中和标志着明代儒学已经超越德性修养的层面而对社会公平、正义提出诉求,这种诉求因为原发于道体之中正,因而将原发于人性的公平、正义放在首位,从某种意义上讲,虽然在现实社会中不去讨论原发于人性的公平、公正与等级制度的关系,但至少在逻辑上公平、公正是凌驾于等级制度之上的。自然理念的成熟标志着明代儒学已经超越德性自由的层面而对人性自由提出诉求。黄宗羲正是在江门学派中正、自然理念的基础上产生了反君主专制的民主思想萌芽。当然,自然并不意味着心性的肆意或放纵。阳明学及阳明后学单提直指的易简的体认、体证据路径容易造成工夫上的浮光掠影,从而形成流禅或狂肆。江门学派的自然之学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并在和阳明学、阳明后学的辩学中予以矫正。针对流禅或狂肆,江门学派根据儒学发展环境的变化对陈白沙本体自然的体用关系进行了修正,湛若水提出天理流行,冯从吾提出道心流行,以区别与阳明学、阳明后学的良知流行,使江门学派的本体论体系更趋完善。
三、 江门学派的道统体系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及意义
儒学作为仁学必然关注人的双向度发展:一个方向是向内发展,使人之成为人,能够自持、自立,这其中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德性修养;另一个方向是向外发展,是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亦即社会和谐。向内发展是向外发展的条件和基础,向外发展是实现、展现个人价值的需求。向内发展是个人的德性诉求,向外发展是社会的德性诉求。社会层面的和谐是通过外在礼制的制约和个人的德性自律来实现的,这种和谐是制度制约下的和谐。如果制度存在着不合理因素,必然造成制度与德性的冲突。在个人不得不遵从制度的前提下,要维护人性的尊严,必然形成对德性自由的诉求。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指的就是德性自由。既然存在矛盾,解决制度缺陷和人性尊严的矛盾就是儒学发展的方向。自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学诞生之后,解决制度缺陷和人性尊严的矛盾就是儒学潜在的目标。但是,由于历史发展的曲折性,这个潜在的目标往往因战争或民族问题隐而不显。随着儒学自身理性的不断增强,这个潜在的目标在逐渐浮出水面,在机会成熟的条件下,它会超越德性自由的层面而提出人性自由的诉求,它的诉求会越来越强烈,矛盾斗争也会越来越激烈,最终以突破制度的方式获得新生。这个过程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儒学自身的防范机制是有力的保证。纵观儒学发展史,这个防范机制指向的对象就是以佛、道为代表的异端思想以及认知觉为性而导致的流禅或狂肆。因此,儒学的发展就是在儒学防范机制的保证下儒学理性逐渐觉醒、日臻完善的过程,儒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始终指向制度缺陷与人性尊严之间的矛盾,最终人性尊严突破制度缺陷而获得新生。在这一过程中,明代儒学是至关重要的发展阶段,而作为濂洛之学的江门学派对儒学的科学发展及最终的突破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江门学派和阳明学、阳明后学是明代心学的两大流派,两大流派学术风格迥异,发展的最终结果也大相径庭。江门学派以宇宙生成论作为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础,遵循了以道体诠释心体的路径,以道体中正、自然的特质阐发心体的中正、自然的理念,从而保证了对心体阐发的科学性。在工夫论上,江门学派在“勿忘”与“勿助”之间保持均衡,从而保证了修养工夫的科学性。在科学理论体系的保障下,江门学派始终沿着正确的路径稳步前行,并随着时代条件的变迁在调整哲学体系的形态,但又始终保持了中正、自然的核心理念。最终,在明朝末年天崩地裂的历史背景下,由黄宗羲提出了反君主专制的民主思想萌芽,将儒学的发展推向高峰,这是在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儒学自身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阳明学在体认路径上以单提直指为特征,直接指向良知。其在工夫论上以正念头为核心,有重内偏外的倾向。概括起来讲,易简是阳明学、阳明后学的总特征。阳明学、阳明后学易简性的最大弊端就是可能导致认知觉为性,造成在工夫上浮光掠影,在本体上玩弄光景。明代的儒学发展史证实了阳明后学最终发展成为空疏之学,明末清初的一些学者认为明朝的灭亡与阳明后学的空疏之学有关。江门学派与阳明学、阳明后学在明朝中后期相互交融、激辩,其在明代儒学史上的时代作用和意义就表现在对阳明学、阳明后学的矫正上,使儒学始终沿着理性的道路向前发展。江门学派与阳明学、阳明后学之间发生过四次有名的辩学,分别发生在湛若水与王阳明、黄佐与王阳明、许孚远与周海门、刘宗周与陶氏兄弟之间,辩学的目的在于纠正阳明学、阳明后学易简的教法所可能导致的流禅或狂肆现象,特别是湛若水、冯从吾在陈白沙“本体自然”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天理流行、道心流行,以矫正阳明学、阳明后学的良知流行,对明代心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为濂洛之学,江门学派的重要作用在于由吴与弼儒学上溯至北宋四子,使北宋四子所构建的新儒学体系重新展现在学者的视野里,使新儒学的宇宙生成论、工夫论和本体论体系在明代得以传承。明代儒学就是在这个庞大的体系内掀起了蓬勃的发展浪潮。江门学派在与阳明学、阳明后学的交融、辩学中始终保持了笃实的体证工夫和中正、自然的理念,加之言传身教对于儒学传承的重要意义,江门学派的道统始终保持着完整的体系。当江门学派的哲学体系移植到浙江之后,丰厚的文化土壤更快地促进了新思想的诞生。刘宗周“意”为心之定盘针的理论及黄宗羲反君主专制的民主思想萌芽,就是典型的例证。江门学派的道统体系是儒学道统体系的重要一环,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