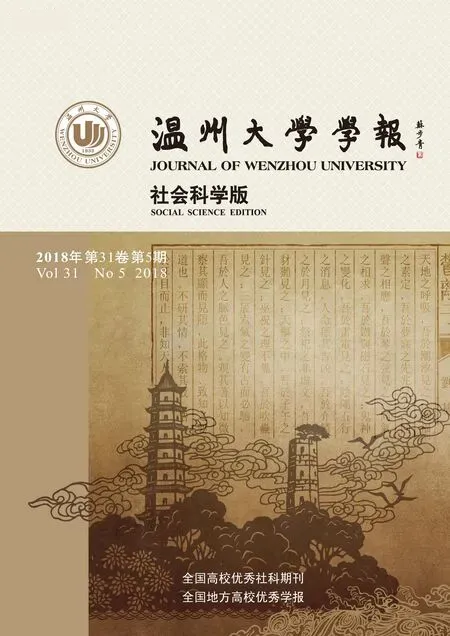太公祭的公共化历程
胡铸鑫,胡正裕
(1.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2.中共文成县委党校教研室,浙江文成 325300)
刘基祭祀是一种活态的非物质文化,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得到过官方的认可,刘基后裔对于刘基祭祀的推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始终有一种“公共性”取向,希望能扩大刘基本人以及刘基祭祀的影响力。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刘基祭祀也曾被边缘化。可喜的是,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开展,刘基祭祀被“二次命名”,得了“太公祭”之专称,并且成功地被“遗产化”。“非物质文化成为遗产,或者简单地说,被命名为遗产的程序就是一种公共文化的产生机制。‘非物质文化’是一个表示自在状态的概念,只是表示特殊样式的文化的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彰显文化自觉历程的概念,表明特殊样式的文化已经完成了权利主张、价值评估、社会命名的程序而成为公共文化。”[1]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标志着太公祭在新时期正式成为公共文化并获得国家体制的再次认可,这对其社会声誉与现代传承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一、历史上诚意伯祭祀的官方认可
刘基是明朝的开国功臣之一,其祭祀在明代后期受政治形势的影响较大,不同程度的朝廷认可与官方致祭或断或续,但总体而言,其规模和范围是在不断扩大的。对于刘基的官方致祭并非单向性地发自朝廷,而是主要来自刘基后裔持续不断的努力。明代刘基后裔们已开始促使刘基祭祀得到官方的认可。
刘基子嗣有二,长子刘琏于洪武十二年(1379)三十二岁时“为惟庸党所胁,堕井死”[2]2508,自此而后至次子刘璟遇难之前,家族安全的重担遂主要落在刘璟与刘廌(刘琏长子)身上。刘璟在遇难之前,即主要在朱元璋居帝位期间,他对于刘基祭祀的存续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在险峻的政治环境下,刘璟、刘廌叔侄想出了一个避祸自保的高招,即于洪武十六年(1383)约请正八品的秦王府(明朝“天下第一藩封”)纪善黄伯生写了《诚意伯刘公行状》,该《行状》最后一段写道:“今公薨而琏没,仲璟与琏之子廌请录公遗事,因辑乎昔所闻大略为行状。至于皇上知人之明、倚注之重,公之遭遇感激、以天下公议辅人主者,观纶綍之文、考成效之绩可见矣,其筹策帷幄有不能尽详者,亦不敢强质也。”[3]636刘璟、刘廌叔侄首次苦心安排,以探皇室的态度,因为秦王乃朱元璋次子朱樉,洪武三年(1370),封秦王,他在诸王中最为年长,身份特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皇室意见,这由他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被封为宗人令可见一斑,宗人令掌皇族属籍等事,秦王朱樉为明朝第一任宗人令。黄伯生任职于秦王府的身份以及他作为纪善的角色使得他所作的《行状》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与社会意义。该《行状》很好地宣扬了刘基的丰功伟绩,而刘基既然对大明王朝的建立有着不可磨灭的辅佐之功,那么料想朝廷对于刘基后人的生杀予夺,或许会三思而后行,在某种意义上该《行状》可谓刘基身后殊荣之滥觞。“太祖念基,每岁召璟同章溢子允载、叶琛子永道、胡深子伯机,入见便殿,燕语如家人。洪武二十三年,命承父袭。璟言有长兄子廌在。”[2]2509朱元璋打算由刘璟袭诚意伯爵位,但刘璟深知这会违背宗子承袭制度,坚持让刘琏长子刘廌承袭爵位。其后刘璟“(十二月)二十五日,钦奉圣旨:‘我考宋制,除尔做閤门使,……。我如今着你叔侄两个都回家去走一遭,把你老子祭一祭,祖公都祭一祭,便来。’”[3]670再后刘璟、刘廌叔侄奉圣谕,“三十日辞,回乡祭祖”[3]670,洪武二十四年(1391),刘璟叔侄奉圣谕“春祭”刘基,有学者认为,正是这一次祭祖开启了后来正月初一“春祭”刘基之俗[4]80,太公祭传承人刘一侠亦持此观点。此外,刘璟、刘廌叔侄还资助创建青田昊天圣阁的崇道观,并与该观住持立约:“首以资助建昊天宝阁,次于阁下东首为令先公诚意伯大人,洎领先兄参政相公立祠追忌之用及立台座寿星堂,预为百年之计备悉。”、“其本观与吾先兄立祠奉祀,凡遇忌日,设供务必精严,须在简当,不得因时泛费及草率”①参见:刘耀东.南田山志[M].温州:文成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2008:124,177。,从而使得刘基祭祀开始越出宗亲的范围,此乃扩大刘基祭祀影响力的重要举措。
“靖难之变”后,刘璟因触逆明成祖朱棣而死,他称“殿下百世后,逃不得一‘篡’字”,刘璟“而后下狱,自经死”[2]2509-2510,堪称英豪,虽未像方孝孺那样被诛“十族”,但“靖难之变”给刘家带来的打击是灾难性的。
刘基长孙刘廌“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嗣伯”[2]2508,虽得爵,但于“明年(洪武二十五年)坐事贬秩归里。洪武末,坐事戍甘肃,寻赦还。建文帝及成祖皆欲用之,以奉亲守墓力辞。”[2]2508“其孙廌等集其御书诏诰、行状事实等文,名之为《翊运录》,盖取诰文‘开国翊运’之语也,请予序其首简。”[3]678刘廌深知仕途之难,便一意奉亲守墓,并取朱元璋赐刘基《诚意伯诰》诰文中“开国翊运”之名,将与祖父相关的御书、诏、诰、行状集成《翊运录》,并得翰林学士王景的《翊运录序》置于其前,此举对于扩大刘基的影响亦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翊运录》之外,早期的刘基诗文集有《写情集》、《郁离子》、《覆瓿集》、《犁眉公集》等,皆以单行本的形式刊印问世。每次刘基诗文集子的刊行于世,其子孙后代都会约请文坛高手或名贤如叶蕃、徐一夔、吴从善、罗汝敬以及李时勉等等为之作序并置于卷首,如洪武十三年叶蕃的《写情集序》、洪武十九年徐一夔的《郁离子序》以及吴从善的《郁离子序》、宣德五年十月罗汝敬的《覆瓿集序》、宣德五年十一月李时勉的《犁眉公集序》等,序言作者的记述,如“今先生既薨,其仲子仲璟与其长孙廌,谋以是编锓梓垂远”[3]675、“今公已薨,其子仲璟惧其散轶,以一夔于公有相从之好,俾为之序”[3]676、“故御史中丞龙泉章公虽已刊置乡塾,然未盛行于世,先生之子仲璟与其兄之子廌谋重刻以传”[3]677、“其孙刑部照磨貊间以嘱余”[3]679、“先生之孙为刑部照磨,名貊,字士行,以才贤笃厚见称于人”[3]680(序中特记刘貊,可知此序必为刘貊所请),充分表明:从《诚意伯刘公行状》到其后刘基各种单行的诗文集的数次刊印,刘基后裔对刘基做了相当多的“正面宣传”。《行状》对刘基的美化乃至神化自不必说,这些名家的具有一定时序性的系列序文对刘基的美化或神化之于刘基形象的树立也起到了相当巨大的作用。
刘璟长子刘貊于宣德元年(1426)被授予刑部照磨一职,品级较高,为正五品,与他相关的有一荣誉纪念物名为“联簪坊”。“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十月,处州知府郭阴、金武,同知曹綋,通判黄聪,青田县知县林川、张乐等立‘联簪坊’,旨在为开国太师刘基、谷王府右长史刘璟、行在刑部照磨刘貊立。”①参见:佚名.联簪坊楹联[EB/OL].[2017-10-25].https://tieba.baidu.com/p/3369459162?red_tag=3307328284。此牌坊所立的时间比刘基祠堂(刘基庙前身)的建成时间早二十一年,虽然是以刘基次子刘璟一支的“宦绩”即所谓“次房宦绩”(刘基后裔常分别称刘琏和刘璟为大房太公和二房太公)为主题,但很明显,这对于刘基功绩的宣扬以及刘基勋臣形象的树立具有重大意义。此外,刘貊于正统十四年(1449)曾撰《先人舍拨寺观田租示诸子书》②参见:刘耀东.南田山志[M].温州:文成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2008:177。,特意重记其父刘璟资助创建青田昊天圣阁的崇道观之事,以刷新并强化子孙后代对于刘基祭祀方面的相关记忆。
明景泰三年(1452),明景帝授刘基七世孙刘禄五经博士,而刘禄于天顺元年(1457)奏请皇帝敕建刘基祠堂(现温州市文成县南田镇刘基庙前身),明英宗准奏,天顺三年(1460)祠成。
刘基九世孙刘瑜则谋请兴建刘基祠堂于处州府城(明朝时的南田属处州府),明孝宗虽未允之,但同意原有祠堂按建制扩建成庙,并御赐诚意伯刘公庙一块“翊运祀碑”。此事事关重大,笔者以为在某种程度上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建刘基祠堂于处州府城”,因为如果说建祠于处州是“横向扩展”,那“扩建成庙”就是往“纵深发展”。经此“祠改庙”,刘基在民间的影响力剧增,因为现实人物的“庙化”本身就是其“神化”的重要途径。正德年间,经刘瑜等人的继续努力,刘基得到了有明一代官方的最高评价,即明武宗朱厚照所评“学为帝师,才称王佐。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3]662,此外明武宗还追赠其为“太师”,并追谥为“文成”[3]664。
嘉靖五年(1526),经刘瑜多次建言,其好友处州知府潘润奏请重建刘基祠,未果。
嘉靖十年(1531),刘瑜又动员刑部郎中李瑜建言以刘基配享太庙,并恢复刘基后裔世袭诚意伯爵位,朝廷准奏[3]664。两年后,刘瑜袭爵。其后刘基后裔世袭诚意伯爵位直至明朝灭亡。在刘基建功立业的明朝,经一代代刘基后裔的努力,刘基祭祀大体上是受到官方认可的,而且总体上其规格有递升的趋势,尤其是九世孙刘瑜使刘基祭祀的公共性得以进一步扩大。
到清朝,明代伯爵世袭制的取消使祭祀主体的社会地位大为降低,因而刘基祭祀受官方认可的程度渐减。然而刘基祭祀的社会影响力在一定范围内依然较大,官方致祭也时有出现。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处州知府窦日严曾以一猪一羊清酌庶品致祭刘基;嘉庆二十五年(1820),青田县知县董承熙曾以牲礼不腆之仪致祭。中华民国期间,刘基祭祀的官方色彩消失殆尽,仅少数名流如章太炎等依然关注刘基祭祀。在此后的数十年中,刘基祭祀主要以家族祭祀的面貌存续。
二、非遗语境下太公祭的“公共化”
“太公祭”一词很年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伴而生的新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新概念,但它已经深深嵌入中华民族的话语体系。它也是一个具有整合性功能的学术概念,虽然可谓“新瓶装旧酒”,但它确实是经整合后的一种新事物,代表着一种新型的文化观。它是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命名,这样的再命名,意义非凡,“等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在中国成为全国性的运动,在民众生活中寻找文化认同对象的途径才一下子顺畅起来”[5]。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内源性文化”,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随着这一概念的广泛普及,民众渐渐开始知道自己的身上也有“文化”。在某种意义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并支撑了民众的文化自觉。非遗保护已被纳入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成为各种利益博弈的对象。
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意义还不仅仅在此,还在于非物质文化之成为遗产,正是一种公共文化的产生机制。“世界文化遗产,不管是早先所讲的物质的、自然的,还是现在所讲的非物质文化的,都是要把‘你的’或‘他的’转化为‘我们的’,都是要把私人性和共同性打通……物质文化遗产是取消个别拥有而得到公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充分肯定个别而得到公益”。“‘不否定私人性而共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化创新”。“在‘你的’之上增生‘我们的’技巧,不仅是一个文化工作上的新思路,而且是人类在新技术条件下开创共享的未来的思想方法。”[6]公共文化少不了公共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某个人的,即便是被认定为某项非遗的传承人也不能说这项非遗是其个人的,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根本上是群体性的,传承人个体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者群体的代表者。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成为公共文化的过程中,它们的共享群体的范围在不断扩大。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由文化部确定并发布,可见非遗名录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官方认可。2011年6月10日,太公祭正式成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①参见:辰序.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EB/OL].[2017-10-25].http://www.ihchina.cn/3/18566.html。。刘基祭祀终于迎来了全新的历史机遇,再度获得了高度的官方认可。如前所述,刘基后人历来都是倾向于将刘基祭祀官方化的,现今的刘基后裔依然有着相近心理,他们希望太公祭能获得更高程度的官方认可,以至进入国家级“文化庙堂”,也就是希望太公祭能成为一种“公共文化”,从而扩大其影响力。
地方性可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特点。“地方性知识”一词提炼于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的表述,是解释人类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太公祭作为一种地方文化,在浙南山区刘基故里这一特定的时空中为特定的群体与个人所传承,它是维系刘基故里社会历史记忆以及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其“本生态”是一种日常生活意义上的文化传统,为当地社群共同传承与享用。它在很多层面上都具有鲜明的地方性,诸如祭祀空间、祭祀的时间以及祭祀仪式等等,是一种根植于地方社会特定人群的文化传统,因而可以说是有悠久历史的地方性知识。然而,在太公祭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它便有了“上升”的发展视野,开始被“资源化”,进而有了一定程度的公共性。刘晓春认为:“非物质文化的遗产化,就是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广泛的公共性的过程。”[7]太公祭被遗产化之后,开始广泛地为原传承主体之外的“文化的他者”所发现、认识甚至利用,理所当然地被纳入到地方政府乃至“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成为具有较强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的文化产品。
太公祭分为春祭和秋祭。春祭以家族祭为主,从每年除夕的前一日开始,其高潮在大年初一,明显具有过年祭祖的性质。而秋祭的参与者不限于刘氏宗亲,并在镇内主要街道举行巡游,其社会性或曰公共性较强。秋祭日期正是刘基诞辰的纪念日,在刘基被不断神化后,其诞辰纪念日已渐渐有了“神诞”的色彩,因而其仪式功能渐趋多元化、公共化,如具有保境安民的色彩以及问卜祈福等。从刘基祠变刘基庙再到刘基庙中出现塑像、筊杯(圣筊)、诗签以及庙祝等,均能凸显刘基神性的不断加强。从显耀的祖灵变为地方性神灵,便是一种公共性的生成过程。
刘基第二十世裔孙南田宿儒刘耀东成文于民国时期的《刘族大宗祭祀须知》中没有春祭“巡游”的记载,而刘基二十二世裔孙现任太公祭祭祀委员会秘书长刘日泽的《太公祭》的祭祀程序中记有此项,笔者曾就春祭巡游一事问询于刘日泽先生,他说据传其实民国时已经有了春祭巡游的雏形,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巡游规模有所扩大,但当时的巡游队伍还着民国味的服饰,直到太公祭开始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巡游规模才进一步扩大,并且设计了新的服装。有学者认为“巡游使春祭原先具有的家祭私密性和封闭性得到突破。”[4]130并指出巡游“既有官员出衙的阵势,又有俗神巡境的功能。然而从明代品官家祭考察,无巡游案例;从地方村庙祭神仪式看,却一直保持着巡境保平安的传统。”[4]134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明显具有过年祭祖性质的春祭也渐渐带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了。
在刘基祭祀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前,人们更多地认为它是南田的祭礼,现在则被更多地认可为文成的太公祭了,将来也许还会被称为温州的太公祭甚至浙江的太公祭。社会认同中太公祭所属地域范围的扩大是其公共性扩大的典型标志。非遗化的太公祭不仅成为地方社会文化认同的象征,也成为“文化的他者”想象、认识和理解地方社会的代表性形象。诚如詹杭伦教授所言:传说的真实已经作为文化史的一部分活在百姓的心目之中,人们用传说来缅怀过去,滋养现在,并憧憬未来[9]。
有明一代,历代刘基后裔努力请求明朝政府对刘基祭祀的认可及参与,以增加这种家祭或族祭的公共性,近年来太公祭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则是使这种家祭或族祭成为国家公共文化的一部分,这两种“公共化”有其相同之处,也有本质的不同:前者主要是依靠刘基的功绩或地位来获得朝廷和地方政府的更多认可及参与来提高祭祀的地位,后者则主要依靠刘基祭祀和刘伯温传说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影响来进入非遗名录,从而提升了这种民俗文化的社会地位。
——围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