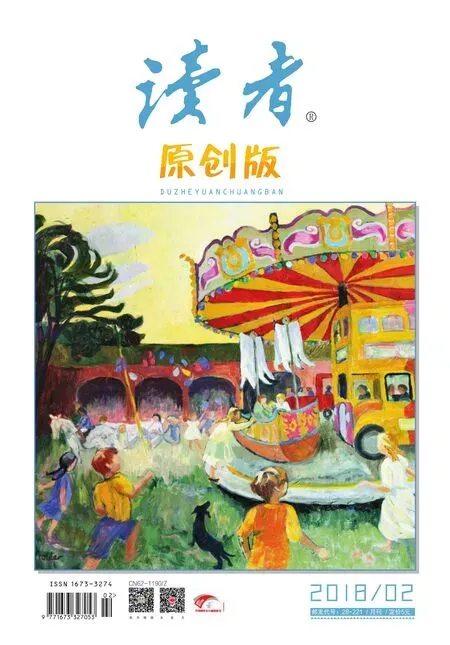看,他好像一个青椒啊
文|严复初

一
雷思温是一个“青椒”。
这个判断句出现在大学校园里就不是病句了。青椒,这种原本属于茄科植物的蔬菜,如今指向了一个颇为庞大的群体:高校青年教师。他们生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一路苦读,取得学位后在高校谋得教职。
你很难从外形上将他们和大学生区分开—稚气未脱,学校图书馆、宿舍和食堂里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在校园里思考和讨论问题,用研究成果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从照片上看,“青椒”雷思温很像一个大学生,但他已经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一名讲师了。在他的简介里,研究领域一栏填着古代中世纪哲学和早期现代哲学,它们像两扇虚掩的门,高冷而悠远;三行简单的履历显示了这位守门人的学术道路: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本科,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硕士,比利时(荷语)鲁汶大学哲学硕士、博士。
很少有人知道,雷思温曾经组建过乐队,对音乐近乎狂热。
如今他依旧喜欢音乐,但也已经习惯了在哲学世界里寻找久违的激情—“音乐充满了规律性和结构性,哲学著作也是一样。”
很少有人知道,他最早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热门专业,就业前景广阔,但他不满足。入学一年后,他开始读王小波的著作。王小波的一句话始终萦绕在他心头:“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这句话说出了他心中淤积太久的感受。他隐隐觉得,自己的人生道路还有很多的可能性。他开始旁听不同专业的课程,想寻找有趣的世界,想给自己一个答案。除此之外,他还广泛参加各种读书活动,结交同好,这种趋势一发不可收拾。
直到大二快要结束时,他开始琢磨换专业的事情。音乐、文学、艺术史、哲学、政治学—最后他筛选出了五种可能性,然而何去何从仍然无法定夺。直到有一天,他读到了尼采的一句话:“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
这句话像闪电一样击中了他,使他明白,人就是一种追求意义的动物。哪怕这个世界毫无意义,人也会奋力去创造一个意义,甚至包括虚无。他一下子感觉到,无论是摇滚乐,还是管理学,都无法像哲学那样直指人心,哪怕是坦然承认生活的无意义。这道光芒的突然降临,使他毅然选择了哲学这条不归路。
除了精读一些重要的西方哲学原著之外,雷思温还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最多的时候,他一个礼拜组织过五个读书小组—“这让哲学不仅成了读书思考的活动,同时也成了我的生活方式。”
大三开学,雷思温正式决定改学哲学。
本科毕业,他考入了北大哲学系攻读硕士。
如果说人大是起点,那么北大就是拐点。硕士生导师吴增定老师不要求雷思温立刻确定论文题目,而是敦促他阅读不同类型的哲学著作。这接续了雷思温本科时的储备,如果当时立即收缩甚至圈定阅读范围,或许可以探囊取物,但终究少了些曲径通幽的妙处,他需要找到闪耀其间的星辰,那才是方向。
二
他找到了笛卡尔。
受黑格尔的影响,人们通常认为笛卡尔奠定了现代哲学的基础,这当然是一个很经典的哲学史定位。雷思温在研究笛卡尔时,却有另外的思考:笛卡尔是如何从西方的中世纪哲学传统中走出来的?如果说大部分哲学家更关注笛卡尔们与中世纪哲学传统背离的部分,他则将目光投向了其中的连续性。自本科起阅读的书籍与受到的熏陶在这时暗暗发力,之前出于兴趣做出的选择,至此成了清醒而自省的判断—这是一个突破口,通过对早期现代哲学的研究,逐步深入西方的中世纪哲学传统,从而获得更为宽广的理解西方哲学的视野。
出国深造成为必然选择。
然而,出国的选择太多,究竟该何去何从?雷思温又一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最终,比利时的鲁汶大学进入了他的视野—不仅因为这所始建于1425年的大学是现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大学,同时也因为它的中世纪哲学研究居于世界顶尖水平。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研究特别强调中世纪哲学与近代哲学的关联,这完全契合雷思温的研究思路。鲁汶大学藏书丰富,直追中古,同时又以高度国际化的视野延揽各国留学生。雷思温由此推开了一扇大门—不同族群、国家、信仰的人的确具有很多共性,但又有很多根本上的差异,不同的文明传统会以自己的方式逐步改变我们对于人类未来一元化的想象。
在鲁汶大学,雷思温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西方人觉得重要的问题,在中国未必会成为焦点;而中国人关切的话题,也未必是西方人在意的主题。因此,他既是那里的成员,又是一名旁观者,观察着西方学术的争执与讨论。跳进去,深入问题;跳出来,看见答案。抽离之后的清醒,才是一个中国研究者该有的自省。那里丰富的藏书,也让雷思温不再觉得西方中世纪哲学思想幽远而陌生,反而处处让他觉得亲切。但这种亲切感也让他感到不安:这些古老思想的当代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战乱之中找到的。
读万卷书,还需行万里路。他决心去那些仍处于古代与现代纠结中的国家看一看,他要亲身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假期里,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埃及、伊朗等国家都在他的行程中。那时这些国家大多处于动荡和战乱中,雷思温穿行其间,亲历战火、动乱与灾难。
在土耳其东部,他遇见了安卡拉大学的老师,他们一起畅聊帕慕克;在凡城,他走后不久那里发生了地震,这场灾难不但埋葬了他住过的宾馆,还埋葬了他刚认识的朋友。
在叙利亚的帕尔米拉,当地人告诉他,他和宾馆里的另外一个人是开战半年以来仅有的两位游客。这处古罗马的伟大遗址,在雷思温离开之后被IS摧毁,他成为地球上最后领略过那里风光的人之一。
在黎巴嫩,他见到了很多坦克与铁丝网;在埃及开罗,他遇到了数不清的示威活动;约旦的奇妙风光和以色列浓郁的宗教氛围,都让他难以忘怀。值得一提的是,伊朗的社会秩序良好,文物古迹丰富,教育水平相对较高,与过去刻板印象中的有很大的不同。
当地人天天都在问雷思温:“伊朗到底好不好?”这种渴望得到认同背后的民族自尊心,令他深深觉得,这些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道路上遇到的坎坷与艰辛,更值得中国人去关注与理解,因为它们与近代中国有着相似的命运。理清中世纪哲学与现代世界的关联,不再只是一个书斋里的论文题目,它切切实实地与中东、与中国,甚至与西方社会纠缠在一起。在战火与动荡之中,他真切地感受到,古老的哲学思想不仅没有远去,反而更为激进地呈现在当下与未来中。而从旅行中获得的精神财富,也不是通过阅读就能得到的。
三
有过阅读的浸润,有过万里行路的经历,这位喜欢人文的学者,在求学之路上渐渐自觉寻找到了出路与归途。他身在书斋,却能走出书斋,奔向源头,走向人类思想闪耀过的地方。哲学是如此美妙,如此激荡人心,愚蠢的思考与狭窄的视野,都被他抛在了身后。
雷思温写的学术论文都很艰深,比如《笛卡尔普遍怀疑中的上帝、数学与恶魔》《邓·司各脱论原因秩序与上帝超越性》《笛卡尔永恒真理学说的内在悖论》等。
这些文章拦住了普通读者,但拆解一下,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一篇文章探讨的是笛卡尔的“恶魔假说”—笛卡尔认为,我们可以假定上帝不是真理的来源,有一个强大而狡猾的恶魔欺骗了我们,让我们相信天、地、空气、颜色、形状这些东西,让我们相信自己拥有四肢、脑袋、血液等。那么,上帝还存在吗?他还是全能而善好的吗?数学还是真的吗?这是笛卡尔怀疑论的开端。笛卡尔做了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思想实验,让我们开始产生怀疑: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真的是看到的那样吗?我们的思想、意识、情绪真的是自己的吗?我们的灵魂能不能与身体分开呢?我们究竟是一个自由的个体,还是恶魔的奴隶?
如今,雷思温的时间一分为三:研究、教学与参加学术会议。
学界前辈与同事常常带给他灵感和思想的火花,让他不断推进自己的研究,避免热闹几年之后陷入失语、停滞和简单重复的境地。回国三年来,雷思温的学术收获远超预期,尤其是与师长和朋友的交流、讨论,都让他深感国内的学术共同体才是他思考与做学术研究的真正源泉。所谓同道不孤,就是如此。
在校园里,学生们已经开始互相传信,说有一位教哲学的老师与众不同。渐渐地,开始有学生提前查好雷思温的上课时间,早早地去占座;也有学生在雷思温的课程评价里写下这样的评语:“课程内容编排合理,讲解深入浅出,节奏张弛有度,少有的能够一学期带着大家读完一本思想巨著的老师。”很多人喜欢哲学,但找不到入口,他要做的,就是把那些艰深的、晦涩的思想光芒折射为可被感知的光线,带领学生穿梭其中。
四
雷思温很早就想开一门“哲学史通识”课程,他希望这门课能够尽可能地涵盖哲学史上的重要思想,并且能够借助这些思想揭示哲学对于人的意义。从表面上看,哲学史无非是前人的智慧、方法,但雷思温从中看到的更多是思想者的勇气。这勇气是不媚俗的自由精神—每一位伟大的哲学家都是异端,因为他们敢于在大部分人想不到、也不愿意发问的地方发问。
改变方向并为之努力的勇气、穿行于战场的勇气和如今将艰深的思哲光芒化为平白话语的勇气,就是雷思温倚仗的力量。
在思想领域,人类从未也永远不会安分守己。
雷思温的这门课取名叫“哲学闪耀时”,《桃花源记》里的一段文字道尽了他的想法—“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雷思温希望自己可以是那个带灯前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