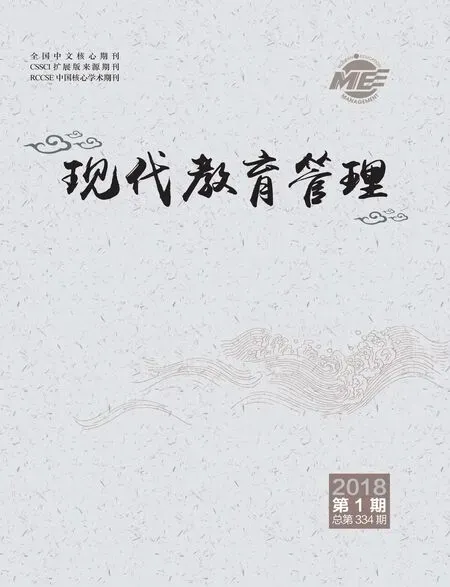从知识至上到生命关怀:建国以来课堂教学质量观的演进轨迹①
一、课堂教学质量观的内涵
人们对教学本质的认识不同,所形成的教学质量观自然也不同。质量观作为一种个人价值选择,既有个体性、发展性与现实性的一面,又有群体性、稳定性与历史性的一面。我们只有深入理解它的内涵与构成,才能避免在分析它不同时期特征时犯以偏概全的错误。
课堂教学质量观是人们对课堂教学活动效果优劣的认识与看法,是对教学品质所作的一种价值判断。评价主体诉求的多样性必然导致评价内容与方式的丰富性。因而,有人断言教学质量评价是没有标准的,“什么样的课是一堂好课”如同“什么样的知识最有价值”一样无法判断。诚然,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背景的人对教学质量的评价标准会有不同,这是质量观内涵的现实性、发展性与个体特征所致。但若过度夸大质量评价的具体性、发展性而撇开评价所依据的客观基础,抹杀质量观中适用一切社会与时代的普遍性与一般性特征,则容易犯随心所欲、以偏概全的错误,进而滑向唯心主义与相对主义泥潭。为此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教学质量观内涵的特征。
具体来说,教学质量观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它是稳定性与发展性的统一。评价主体无论如何丰富,都是存在于特定历史时期中的个人,其评价视角与范围受到该时期主流意识和认知水平的制约而形成一致的认识。但稳定不意味着一成不变,评价主体对教学本质的认识会随社会的发展而逐步调整与完善,呈现出动态发展的态势。第二,它是群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在同一群体中,评价主体因相同的文化、习俗而形成相似的、有别于其他群体的质量观。而在群体内部,评价主体间又会因不同的经历而形成相对独特的质量观。但无论群体或是个体,他们之间都是相互渗透的。也就是说,他们对教学质量的看法会受其他群体或个人的影响而改变。第三,它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人们对教学质量的评价总会受到传统质量观念的影响,但人们也总会根据现实生活的需求对教学质量提出新要求。我们在审视质量观时既不能割断历史的联系,也不能抛开现实的需求,要将二者有机结合。
二、建国以来课堂教学质量观的演进:从知识至上到生命关照
(一)模仿与建构时期的质量观:“知识至上”的尊崇与“生命关怀”的缺失
建国初期,我国移植、照搬苏联教学模式,西方教学思想遭到贬斥。其结果是,杜威的“儿童中心”“做中学”等突出主体生命价值的教学理念被学校拒之门外,教学重回传统“教师、课堂、书本”为中心的老路上。这种沿袭自赫尔巴特的教学观,经凯洛夫改良后变得更具操作性。它强调系统知识与技能的学习,突出教师课堂权威,认为“教学就是把客观的、真正科学的知识教给学生”。[1]其中,知识被严格规定为“各种事实及其概括体系(概念、定理、结论、法则等)”,[2]是客观的、真理性的,是被教学大纲框定了范围的教科书。换言之,教学就是教书。教师作为闻道在先者、知识占有者,其言行被视为真理,其权威不容挑战。而且,作为教学内容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科书是国家统一规定的,不允许教师随便更改”[3],这限制了学生学习涉猎的范围,使其无法撼动闻道在先者的权威,同时也影响教师选择与行动自由,导致教学教条化、程式化现象严重,教师很少根据学生的课堂反馈调整教学方法。
该时期对“知识至上”的尊崇导致教学质量评价的单向性,即只关注知识传授的达成度、教师教授的有效度等,忽视了学生素质整体发展,以及学习对于学生生活的意义。具体而言,“知识至上”取向的教学质量观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指向智力发展的目标达成度。在以文化基础知识传授为中心任务的课堂中,智力发展被片面看成是学生的全部发展,且被狭隘地理解为知识占有的多寡。因而,知识讲解是否具有逻辑性、系统性,是否易于理解,是否影响学生知识学习效果与智力发展,是评价教学质量优劣的关键。二是指向客观规范的内容忠实度。建国伊始,教育教学内容的选择重视规范与正确。规范不仅体现为教学大纲、教材要统一标准,也表现在对科学上存在争议和未经确定知识的摒弃。[4]而正确则要求教学内容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不能偏离社会主义道路。课堂上,教师要忠实传递科学规范的内容,超出或偏离都将影响质量评价的结果。三是指向衔接流畅的过程清晰度。1953年北师大女子附中在苏联专家指导下,总结《红领巾》一课教学法,受苏联专家高度赞扬,并在《人民教育》杂志上进行宣扬。此后,《红领巾》一课的教学模式几乎成为我国中小学阅读教学的基本模式。[5]这种沿袭自凯洛夫“五阶段”教学观的模式强调过程的流畅性与清晰性。它要求教师课前准备充分,并对知识要素进行透彻的分析。可见,教学流程是否清晰、效果是否显著是评价教学优劣的重要指标。四是指向教师权威的课堂掌控度。工具理性影响下的质量观突出教师的权威地位,认为“教师的每一句话和每一项指示都具有法律的性质”[6],强调教师对学生的控制,把学生视为执行指令的服从者,课堂多以教师讲授为主,而讲授内容多着重知识说明,少有广泛性的概念讨论。
(二)探索与颠覆时期的质量观:“知识至上”的扭曲与“生命关怀”的失落
1957年,中苏关系恶化,加之西方对华封锁,我国教育开始走上独立探索之路,这种独立探索就是与外界“隔绝”的本土化探索。在教学领域,“隔绝”表现为:既反对杜威等以“儿童、生活、活动”为中心的教学观,也反对凯洛夫等以“教师、课堂、书本”为中心的教学观。它认为前者所倡导的“遵循儿童天性,量力而教”夸大自然力量而低估了学生的主动性、能动性,是一种消极的“先天论”思想,教学应有所作为而不是“听天由命”;它认为后者“过度强调知识而忽视劳动”必然使学生脱离实际,是一种“有知识无生活”的教学观,是“教育即生活”的另一种极端,也应予以肃清反对。该时期的本土化探索在对二者批判基础上澄明了我国教学的方向。首先,教学不该在腐化的资产阶级生活中进行,也不应局限于课堂,而应扩大到生产劳动各个领域,倡导现场教学,主张“用社会‘大课堂’(田间地头和工厂车间等)代替学校‘小课堂’”[7]。其次,教学不该“以儿童为中心”迁就其天性,也不该以“教师为中心”对客观知识盲目崇拜,而应以“群众”为中心,以政治方向正确、掌握生产技术的“能者”为师。最后,教学不该脱离实践而一味强调知识,应以“生产技术”为中心,“以直接经验为主的所谓’实践知识’代替系统的科学理论知识”[8]。这种强调“知识教学与劳动技能相结合”的教学观虽有效扭转了过度强调知识传递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丰富了教学内容与形式,但其把教学内容框限于与生产相关的知识与经验、把教学形式限定为生产劳动、把教师定位为具备生产技术与经验的“能者”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教学对功效的狂热追求,以及对知识实用性的极度尊崇。
该阶段课堂教育质量观在评价教学优劣时呈现出四个特征。一是指向智力与劳动技术协调发展的目标达成度。在强调教育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同时,也要求教学应密切联系实际。认为学校教学不能单纯教授文化知识,其所教授的知识应与生产建设相联系,否则这样的教学是无效的,所传授的知识也是毫无意义的。二是指向本土化、多样化的内容灵活度。教学与生产相结合使得劳动成为重要课程之一,教学中需包含指向工农实践和指向新兴生产领域的内容。由于实践形式的多样性,教学内容自然也就五花八门,既有关于水稻种植、钢铁冶炼的内容,也有导弹研制的内容等。此外,除沿用已有国家教材外,还通过改编、生产经验总结等方式增加了传统与本土化教学内容,如民族手工制作等内容。三是指向集约高效的过程自由度。对量力性原则与博爱式教学的批判源于对西方教学思想的敌视,也是大跃进“多快好省”浮夸思维在课堂中的延伸。认为教学不能低估学生能动性,教学过程不应以人道主义隐晦式的诱导方式进行,而应直截了当与学生讲道理,力图简洁高效。但同时又要警惕凯洛夫框架式的“阶段论”对师生行为的控制,应根据具体情况而选择最有效的方式进行,既可全程讨论,也可注入式与启发式相融合,教学过程应灵动而自由。四是指向“和谐”的课堂民主度。教学中不以教师为中心而推崇以“能者”为师,“能者”是掌握生产技术、思想端正的工农群众,自然也包含学生。课堂中没有绝对正确的真理,应有革命式的民主讨论。
(三)博弈与较量时期的质量观:“知识至上”的困惑与“生命关怀”的凸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校教育重回“以教学为中心”轨道上,强调知识的教授与技能的训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外的一批教育理论,如苏霍姆林斯基的学生全面和谐发展理论、赞科夫的发展性教学理论等,被引入和学习。教育界开始反思我国过往片面把“学习知识理解为发展智力”“智力发展等同于全部发展”的问题,并掀起了一场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大讨论。讨论加深了人们对发展内涵的认识:学生的发展应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和谐的发展,教学要在促进学生认知、情感、意志品质、体格等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尊重学生个性与自由选择。此外,讨论也对教学中忽视学生主体性、忽略学生非智力因素参与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与纠正,并促成一批教学改革实验的开展,如愉快教育、成功教育等强调知情互补的教学改革,又如洋思、杜郎口中学等强调以学生学习为中心、先学后教的教学改革。该时期对学生整体素质协调发展的关注是我国教育在人文精神培养方面的重大突破,也是价值理性在教学领域的复苏,过往教学中“只教书不育人”的现象得到一定缓解。
该时期开始坚持发展全面性,尊重学生主体性与差异性,注重教学启发性与探究性,教学质量观呈现出以下四个特征:一是指向素质全面和谐发展的目标达成度。教学对发展性的强调不再片面局限于智能和技能,而是全方位的覆盖。它不仅要促进学生认知与狭隘道德的发展,更要通过启发诱导等方式培养学生协同合作、主动探究等精神。可以说,该时期对课堂教学的评价是多维度的综合,达成度越高则质量越好。二是指向主动探究的内容丰富度。教学内容的丰富体现在对学生个体差异与主体能动的尊重上,它要求教学内容的编排应避免过度的事实陈述,应指向富含寓意、能激发学生深入探索的内容。换言之,教学内容的丰富性与探究趣味性决定了课堂的活跃度与教学的深度,是评价质量优劣的重要指标。三是指向整体优化的过程综合度。学生的成长不是智力或体力某个方面单因素发展,而是德、智、体、美、劳整体协调发展。因而,教学过程中应把五育都包含在内,各育不是单独地、孤立地进行,而应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成为全面发展的组成部分。四是指向学生主体的课堂参与度。优质教学必须能激发学生兴趣和参与热情。学生不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获得知识的主动参与者。只有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过程,学生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而,优质教学应尽量让学生动眼观察、动脑思考、动手操作、动口表达,通过积极参与学习活动提升自主意识、自主能力。
(四)反思与重构时期的质量观:“知识至上”的超越与“生命关怀”的回归
20世纪90年代至今,信息化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人们的生活逐渐从实体转向虚拟、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共享,这彻底改变了人们固有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也对传统封闭而僵化的课堂教学提出了挑战。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对学生主体性的关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教书不育人”的现象,但“知识至上”笼罩下的单向性教学理念仍然根深蒂固。许多教师还是没能领会素质教育的内涵,依然“把丰富复杂、变动不居的课堂教学过程,简约划归为特殊的认识活动,把它从整体的生命活动中抽象隔离出来”,[9]课堂中“重教轻学,重智轻德、体、美、劳”的问题没能得到实质性的改变。随着“以人为本”指导思想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关怀,人们开始关注师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认为课堂教学应该是多元、开放、动态生成的过程,而不是单一、封闭、静态的流程。开放意味着教学不是知识单向传递的过程,而是师生间在平等、民主基础上交往与分享知识、价值观、情感的过程;动态生成意味着教学不是机械、教条、僵硬地执行预设教案的流程,而是一种“理智的探险”,是“即席而作”[10],是在不确定性中探寻生活意义的过程。过往那种把教学简单看成认知过程的观念忽略了人存在方式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忽视了师生教学过程中的体验与探究。教学应是师生结伴而行的知识之旅、生命之旅,沿途每一次驻足(每一堂课)都充满价值、意义非凡。
具体而言,“生命关怀”取向的质量观呈现出以下四个特征:一是指向人性释放与完满发展的目标达成度。价值理性的回归让人反思传统教学对人性的压抑与发展的控制,认识到教学“绝非仅仅是增长知识本身,它的目标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11]这种解放以追求生命的独特性与完整性发展为起点与归宿。因此,以学生素质发展为旨趣的课堂教学不仅要关注全面性与和谐性,更要关注其对于学生生命发展价值的意义。无论是教学内容或是过程都应回归学生真实的生活世界,抛弃遮蔽人性的单向性思维。唯有如此教学才能引领学生走向人性的完满与幸福。二是指向生活意义的内容体验度。“知识至上”的教学质量观把知识视为认识的对象,以对象性思维把主客体分离,侧重知识的客体属性而忽略知识对于主体的意义。价值理性的回归使人们关注认知主体的内在需要,强调教学内容与学生生活世界的联系,提倡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到生活的丰富性与意义性,进而发展学生理解生活与世界的能力。强调教学质量优劣评价不应局限于内容的抽象度与概括度,而应转向内容的意义度与体验度。三是指向生命价值的过程生成度。人的生命源于自然却又超越自然,人与物的区别在于人拥有丰富的、不断发展的内心精神世界。人不是先在、预设的存在物,而是生成、发展的过程体。工具理性支配下的质量观把学生视为待加工的客体,把教学过程看成工业流水线上对产品的加工流程,强调操纵与控制,这不仅导致教学过程的机械化、同质化,也漠视和贬损了学生生命存在的价值。新时期整体性教学质量观倡导预设与生成相融合的过程观,这既是人性生成与发展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学生生命意义与价值的尊重。四是指向师生交往的课堂合作度。工具理性思维下形成的主客二分关系已然被批判与否定,教师和学生不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是独立精神主体间理解、交往与合作的关系。师生间的交往与合作只有建立在民主与尊重的基础上,课堂中分享的知识与价值观才能被对方内化并赋予意义。因而,有意义的师生交往与合作成为教学质量评价的重要考量因素。
三、课堂教学质量观演进轨迹的思考
回溯建国以来课堂教学质量观的演变轨迹,可以发现教学质量观的变迁实质上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相互博弈的过程,它的演变遵循一定的规律,与对人本性之认识程度相关,并随之变化。但是,教学质量观的变迁与教学实践变迁并非总是亦步亦趋,而是存在观念与实践脱节的现象。
(一)教学质量观的演进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的博弈过程
“以价值为内容的评价过程,总是处处渗入了理性的关照。”[12]教学质量观作为一种价值选择,必然与理性思维交错互融。自柏拉图把共相与个体分离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只有理性才能洞察真实的理念世界,才能从变动不居的质料中把握形式,它具有求真与向善双重功能。可是现代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物质满足使人们逐渐把求真的工具理性视作唯一的理性,而向善的价值理性被其光芒所遮蔽,日渐萎缩并走向迷失。我国建国以来“知识至上”的教学质量观正是受此影响:它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用实证科学的量化模式来衡量知识,注重教学实效却对学生主体发展漠不关心。在工具理性支配下,教学质量评价追求实效,以最大效率达成既定教学目标为评价指标;追求计算与量化,以高升学率和分数等为评价指标;追求预测性与确定性,以对学生行为与心理问题的预见性和对教学过程的预设性为评价指标;追求控制与操纵,以教师对学生的行为有效控制为评价指标。然而,随着对人主体性认识的加深,工具理性作为教学质量评价指导思想的弊端日益显现,人们开始思考教学对于人的意义与价值,不再以线性、数量化的模式来评价教学,而是以人类的自由、平等、幸福来衡量教学质量优劣,强调教学“绝非仅仅是增长知识本身。它的目标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13]价值理性的复苏促使教学质量评价开始关注人的发展价值,并追求人发展的完整性。在它看来,人的存在是完整的而不是割裂开的,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因此,教学不仅要促进学生形式逻辑认知能力的发展,也要促进学生整体素质全面和谐发展。同时它还强调教学的生成性与意义性,即人不是先在、预存的,而是生成、发展的。
(二)教学质量观的演进与生命价值的追求交相辉映
教学是人之文化生成的活动,其本真追求是解放人的自由、促进人的发展。回顾教育史上的一切教学变革,我们都可以从对人之概念的认识中找到动因,正如哈梅斯贝克所说,“所有的教育行为,都与人的概念有关”。[14]如果说人是教学活动开展的起点与归宿,那么对人的理解与认识则是教学价值取向的方向指针,是教学质量评价的内在依据。纵观建国以来教学质量观由“知识至上”到“生命关怀”的演变轨迹,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变迁实质上与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人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追求交相辉映。在工具理性主义支配下,人的概念被抽象化、概念化,甚至机械化。工具理性的极端化不仅使人丧失为人的本质特性,也抹杀了个体独特性。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国课堂教学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把学生抽象化,将工业化的标准与流程带到课堂中,视学生为知识填充的器物与操纵的对象,视教学过程为生产商品的流程。与之相呼应的是,教学质量观呈现出单向度“知识至上”的特征,如只关注认知发展达成度而忽视综合素质发展。改革开放后,人们摆脱了封闭思想的禁锢,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和高扬,价值理性开始复苏与回归。由此,人们开始反思与批判把人抽象化的观念,进而提出人应该是具体存在的、是丰富多样与动态生成的。基于对人生命价值的认识,课堂教学提倡回归学生生活世界,强调关注学生生命独特性、整体性,重视教学内容、过程与学生生命意义的联系。由此,教学质量观也趋向对人生命的关怀,开始关注过程的体验度、内容的意义度等。可见,教学质量观与对人生命价值之认识程度相依共振并随之变化。
(三)教学质量观的演进与教学实践的发展存在脱节
观念的演变遵循特定的逻辑,即社会存在决定主体意识,影响着观念的形成,新观念在指导实践基础上进行修正和发展。教学质量观作为评价主体根据自身需要对教学质量进行价值判断与选择的观念与态度,归根结底是由教学实践的发展决定的,并反过来指导教学实践。然而,在教学实践中却存在大量行为与指导质量观相背离的现象。通过回顾建国以来教学质量观的演变轨迹,我们能清晰地发现:质量观的变迁与教学实践变迁并非总是亦步亦趋,而是存在观念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即人们常说的“观念超前、行为滞后”。改革开放后,价值理性的复苏唤醒了人的主体意识,主体性的觉醒与凸显要求教学重视人的价值与发展。然而,在新历史时期的课堂教学中依然存在大量“知而不行”“知而错行”的现象,许多教师“对教育价值的选择还停留在‘传递知识’上,其中有一些教师虽已关注到学生技能、技巧,甚至能力和智力的发展,但大多仅为点缀。至于认识范围以外的目标则更少涉及”。[15]这种价值理念与实践行为脱节的原因在于前价值理念对行为主体的干扰,表现为主体虽然认同新价值理念并向其倾斜,但依旧无法彻底摆脱前理念的影响,行为上依然受前价值理念影响。因此,许多教师虽在观念上接受了趋向整体性的“生命关怀”教学质量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教学中会践行这种质量观,他们观念的变迁仅停留在价值认同与价值判断上,而非价值行为上。由此观之,当前教学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新旧价值观间的较量,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的博弈,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价值观指导实践的滞后性。
[1][2][3]凯洛夫.教育学(全一册)[M].沈颖,南致善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56、73、56.
[4][6]郑金洲,瞿葆奎.中国教育学百年[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193.
[5]熊明安.中国近现代教学改革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202.
[7][8]张敷荣,张武升.建国以来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回顾与展望[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4):58.
[9]叶澜.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论中小学教学改革的深化[J].教育研究,1997,(5):4-5.
[10]罗祖兵.课堂境遇与教学生成[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202-221.
[11][13]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232、232.
[12]杨国融.理性与价值[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1.
[14]冯增俊.教育人类学教程[M].贺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41.
[15]叶澜.重建课堂教学价值观[J].教育研究,200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