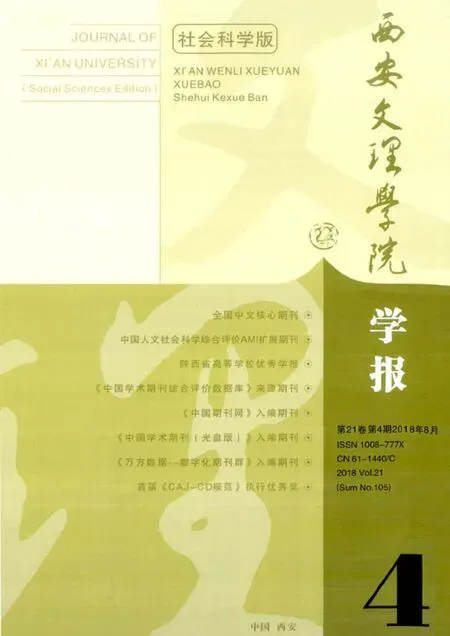论《白鹿原》的乡贤文化内涵
李 铮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乡贤”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产物,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乡贤”一词始于东汉,多指饱学之人、贤达之士,古时候称为“乡绅”“士绅”等。[1]“乡贤”一词系指在民间基层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2]由于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结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乡村中有一定经济基础和威望的乡绅在日常的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中贡献诸多力量。这些乡绅之中的大部分饱读儒家诗书,因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被当地乡民尊重,被称为“乡贤”。因此,在乡村之中,围绕着这些被当地民众尊重的乡绅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形态,便是我们所称的“乡贤文化”。这种文化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在乡村社会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儒家文化理想在现实生活实践中的具体产物。分析乡村中的“乡贤文化”因素,对我们在当下的现代化进程中充分把握和理解当代乡村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熔变有着极大的意义。
《白鹿原》是陕西作家陈忠实的代表作,书中塑造的宗族族长、大儒先生等地方士绅形象深受当地民众敬重,这些地方的乡绅构成了白鹿原上的乡贤群体,而围绕着他们,白鹿原上也就存在着一种在乡贤主导与影响下的社会文化形态,这便是乡贤文化。然而,在围绕着《白鹿原》众多的研究之中,却罕有以乡贤文化为基点来观照这部作品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白鹿原》是一部意蕴深厚的作品,在书中,作者以浓厚的笔墨将乡贤文化的土壤——儒家文化作为贯穿全书的背景,同时不仅塑造了白鹿原上以白嘉轩、冷先生、朱先生等为代表的乡贤势力,还充分表现了这些乡贤势力对以白鹿村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村落日常生活的积极影响。统而言之,书中的这些因素,毫无疑问地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从乡贤文化角度对该作品进行分析解读的可能性。因此,当我们将视线聚焦于白鹿原上的历史文化背景、自成体系的权力结构与管理路径、日常生活的规训与治理时,便能够从中发掘出丰富的乡贤文化内涵。
一
《白鹿原》中的乡贤文化内涵首先体现在白鹿原这片土地的历史文化与社会这双重基础之中。在作者陈忠实笔下,白鹿原这片土地拥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累和宗族势力强大的社会基础。这些基础不仅是乡贤文化得以存在的土壤,更是白鹿原上乡贤文化内涵丰富的必要条件。
在《白鹿原》一书中,作者用了大量篇幅表现了白鹿原上的儒家文化基础。有论者如是说:“《白鹿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一部正面书写传统儒家文化的作品。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和各种家族叛逆者的挑战,朱先生和白嘉轩以‘乡约’规训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乡土中国的日常秩序,建构了‘仁义白鹿村’的理想社会形态。……‘仁义白鹿村’成为百姓心中曾经的‘乌托邦’。”[3]这段话明白无误地指出,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构建了一个儒家文化为基础的社会形态。持有类似观点的研究者不在少数,著名评论家雷达指出,白鹿原所在的关中地区乃多代封建王朝的基地,具有深潜的文化土层,而生成于这个土层的白、鹿两族的历史也就典型地积淀着我们民族的文化秘密。[4]这无疑意味着,这片“积淀着我们民族的文化秘密”的白鹿原,正是一片浸润着儒家文化的沃土。作者陈忠实自身也有着同样的感受,他自小时便受身边亲友、社会群体这“一本无形的大书”无所不在的影响,听他们说在关中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听他们说一个传统家族的序列,听他们说一位腰总是挺得端直直的族长式人物把那些在街巷里袒胸裸怀给娃喂奶的女人们全都吓得跑回街门里头去,这林林总总的一切,在他心中集聚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心理结构”,在后来的创作过程中,他更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发现了宋代名儒编撰的中国的第一本治理乡民的条约准则……最后,陈忠实说:“当我第一次系统审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时,又促进了起初的那种思索,进一步深化而且渐入理想境界。”[5]所以,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白嘉轩、朱先生等乡贤势力会积极发挥自身作用,去引导和维护白鹿原上乡民们的正常生活秩序。由此亦可见关中地区雄厚的历史文化积累,隐含了《白鹿原》中乡贤积极为乡土贡献力量的历史文化原因。乡贤之所以热心桑梓,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来源于传统文化的长期积累发展给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带来的“集体无意识”。
在历史文化基础之外,白鹿原上的社会基础也被作者着力表现。白鹿原是黄土高原上一块聚族而居的坡塬,最大的白鹿村由白、鹿两姓组成,形成一个大宗族,一个典型的基层文化单元,一个血缘共同体组成的初级社会群体,“它具有初级性和稳定性,外延可以很方便地伸向广大社会,内涵可以是广大社会的缩影”[6]。正因如此,有评论家便直接指出,《白鹿原》采用了“通过一个初级社会群体来映现整个社会”[7]的方法。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认为: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关系的基础。[8]这无疑指出了以白鹿村为代表的白鹿原,向大处说甚至是整个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正是一种宗族血缘联结的初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宗族族长有着来自于家族内部的绝对权威,同时,儒家文化中对“礼”的提倡,同样强化了长幼之间的层次和秩序。因此,在白鹿原这样一个大宗族生存的地区,宗族的领导势力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自带权威的一支领导力量。当这支力量热心桑梓,回报乡民,做出贡献之后,无疑就成为当之无愧的“乡贤”。于是,白鹿原上的这种社会基础,无疑也隐含着乡贤文化内涵的丰富要素。
二
《白鹿原》中的乡贤文化内涵其次体现在作者对白鹿原上自成体系的权力结构与管理路径的书写。白鹿原上丰富的历史文化基础与社会基础,蕴含了乡贤文化生根发芽的“基因”。而作者对村子中自成体系的权力结构与管理路径的书写,则在无形当中将乡贤文化内涵变得更加丰富与具体。
自秦代建立“郡县制”以来的2000多年中,政权只设置到县一级,国家最低管理到县级。[9]这就是所谓的“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乡村主要就依靠“地方自治”。从《白鹿原》一书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虽然基层乡村没有政府组织,但白鹿村中的日常生活并非毫无秩序。因为,乡村中的生活受着一种特殊的领导结构来管理与维持。这种结构来源于上文所述的历史文化沉淀与社会基础。文化历史带来的沉淀意味着儒家文化占据着社会价值评判的制高点;社会基础意味着血缘与宗族势力影响着当地社会的权威话语。所以,在这些条件下,儒家文化评判下的精英阶层,典型如科举进士朱先生、救死扶伤医德高尚的冷先生;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宗族领袖,典型如家族族长白嘉轩,都成为对乡村施行管理、维护的领导力量。从书中可以看出,村子中的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常依于白嘉轩为首的宗族势力解决;甚至于当危机超出一村,几十万大军兵临城下,三秦面临屠城浩劫的时候,也是幸于儒家文化熏陶下的朱先生挺身而出才力保一方安宁。从这一角度来看,他们可以说在《白鹿原》一书中共同建构了一种基层乡村的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之所以能够形成与存在,是由于乡贤利用自身威望来主动承担公共事务且确确实实解决了问题,还得到了民众的信服。这种“权力”不是一般由暴力做后盾的政治强权,而是一种不依靠国家机器、暴力强权却能让百姓心中信服的力量。所以,白嘉轩能够在村子中较好地澄清风气,而冷先生能够成为远近闻名的神医,朱先生能够一声令下尽毁原上罂粟。家族族长、儒家先生、贤明医者,他们称得上是儒家文化所谓“士”的阶层,是担负社会责任的中坚力量,而且也更是我们在开头所提到的乡贤,即“在民间基层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而由书中乡贤们形成的这种权力结构,为乡民服务,被乡民信服,无疑直接体现出了乡贤文化的内涵。
与白鹿原上这种权力结构相伴而生的是一种具体的管理路径。这种管理路径便是明文的乡规民约和默认的乡约民俗。乡规民约,亦称乡约,它的制定与履行,使乡村的日常生活有据可循,也使得这种权力结构行使权力时有章可依。在《白鹿原》一书中作者写道,辛亥革命成功后,剧烈的社会变化让族长白嘉轩开始发愁“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在这时,朱先生一纸《乡约》给他带来了希望。其实,这种形式由来已久,《乡约》是一种由地方制订,形成书面具体条文,并由村民们共同监督遵守的乡规民约。有分析指出,最早的完整而规范的《乡约》产生于一千多年前的北宋时期的陕西蓝田,由当地的吕氏大儒编写,当时这份《乡约》推行后,“遂使关中风俗为之一变”,作者陈忠实创作《白鹿原》时,以此史实为据将《乡约》写入书中。《白鹿原》中,白嘉轩将这份《乡约》带回,随即便在村中倡导实行。不久后,“村子里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不再发生,白鹿村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都柔和纤细了。”不难看出,《乡约》的制定与执行,使乡村的日常生活有了有据可循的规范,村民的生活在一段时间内也因此变得更加文明与和谐。
除了明文的乡规民约,还有一种默认的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祠堂议事制度。这是一种对村子进行管理的具体路径,每当村中有重要的事情需要讨论、宣布时,或者是进行公开的惩戒时,祠堂就变成了一种管理与惩戒得以实施的场所与路径。所以,当白嘉轩宣布要整修祠堂时,当田小娥、白孝文先后因违反乡约族规而要接受刺刷的惩罚时,人们都会聚集在这里。这时的祠堂,已经不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物理场所,而是一种方法、一种习惯。人们这里一起议事协商,随后才会达成共识,然后精诚协作;人们在这里惩罚违反乡规民约的人,随后才会赏罚分明,令行禁止,共守乡约。
这两种对乡村生活的具体管理路径,无疑都依赖于乡贤势力的推动。《乡约》条文来源于大儒朱先生,《乡约》在村中的提倡与弘扬和祠堂议事的主持者与惩戒的实行者都是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宗族势力。正是由于乡贤的着意设计与竭力推行,这种结构、路径才得以建立与维持,而这也就自然而然地体现出了乡贤文化的内涵。
三
除了以上方面,《白鹿原》中的乡贤文化内涵还体现在以白嘉轩为代表的乡贤对乡村日常生活的强大规训能力与治理功能。从书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村中的矛盾调解、教化风习还是承担公共事务,乡贤的积极参与使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良好的解决。
首先,作者笔下表现了村中的矛盾调解。白鹿村小姓李家的一个寡妇因生活困难而贪心作祟,将同样一块田地先后出售给了鹿家和白家。结果,不明真相的白、鹿两家因地权而生纠纷。矛盾所至,竟演变成了“白鹿两姓阵势分明的斗殴”,一场混战下来,场面狼狈不堪,“满地都是撕破的布片和丢掉的布鞋”。这场斗殴本无必要,因为双方事后得知,贪心的李家寡妇先把地卖给了鹿子霖,但后来得知卖给白家能获得更多的钱,于是又改变了主意,签下了第二份地契,这才出现了“两主争地”的情况。
面临这种矛盾,白鹿村中医堂的冷先生与大儒朱先生,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调解的任务。远在异地的朱先生写信劝慰两家,冷先生则竭力奔走其中。在这两方的共同努力之下,白嘉轩与鹿子霖终于在在冷先生专门设置的酒席上握手言和。不仅如此,在得知卖地的李寡妇确实面临严重经济困难后,白、鹿两家不计前嫌,不仅归还了李寡妇的土地,还主动施以援手。最终,挑起此次事端的李寡妇羞愧得泪流满面,而一度因误会地分离白、鹿两族人又和好如此,这件事情就这样圆满而又和谐地解决了。
其次,书中表现了对风习的教化和对歪风邪气的高效遏制。在白鹿村里出现了赌窝后,抽鸦片的人也出现了。有两个烟鬼抽得倾家荡产,家中的女人引着孩子四处乞讨。针对这种情况,白嘉轩恩威并施,将赌窝一锅打散,将庄家的不法所得还归因赌博而倾家荡产的村民。随后,又对赌徒当众惩戒,使其痛改前非。对于两个倾家荡产的烟鬼,白嘉轩首先遣人将他们的妻子、孩子接回,然后又提议给予救济,“将祠堂官地的粮食周济他们几斗”。在这之后,随即又戏谑式地给这两个烟鬼开出了一份“良药”,而在这之后,这两个烟鬼羞愧难当,果然戒了大烟。还有一次,白嘉轩看到了一家的妇女“扯襟袒脯”地在大街上给孩子喂奶,当天晚上他在众人聚集的祠堂里将此事当作违反礼仪的事例讲给大家。这个妇女的丈夫羞得满脸通红,“当晚回去就抽了丢人现眼的女人两个耳光”,从此之后,“女人给孩子喂奶全都自觉囚在屋里”。
再次,书中还展现了对公共事务的有力承担。上文提到“皇权不下县”,所以村子当中的公共领域没有纳入政府的统一维护与管理之中。村中的祠堂就是如此。白鹿村中的祠堂是祭祀祖先的地方,但“毕竟又是公众的官物没有谁操心”,年久失修的祠堂“落叶积垢,绿苔绣织”,破败不堪。此外,村中没有自己的学堂,适龄儿童入学只能跑到七八里外的神禾村,极为不便。于是,族长白嘉轩萌生了一个想法:整修祠堂,新建学堂。于是,在他与鹿子霖的综合统筹下,村民自发捐赠了三分之二的钱粮,白、鹿二人承担了剩下的三分之一,于是祠堂的翻修工作才得以热热闹闹地展开。而村中的学堂也得以开办,村中的适龄儿童都进了本村学堂,甚至之前从未想过接受教育的黑娃,也被白嘉轩要求去了学堂。这件事情无疑体现了乡贤的强大作用。正因为有了他们,无人承担的公共祠堂得以翻修,适龄的儿童得以入学接受教育。
除了祠堂、学堂的建立与维护,村子的公共安全问题也是公共事务中的重要部分。有一段时间,白鹿原上白狼肆虐。而此时,晚上守卫白鹿村村子的只有一位打更的跛子老汉和豁豁牙牙的堡子围墙。用白嘉轩的话说,“甭说白狼,匪贼骑马进村也无个挡遮!” 在这种情况下,村中人心惶惶,担忧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经过白嘉轩与鹿子霖的商议,决定“把(村子)豁口全部补齐,晚上轮流守夜,立下罚规,不遵者见罚!”这项工程顺应了村民们的意愿,也保障了村民对安全的需求,因此得到了广大村民的热烈拥护。书中对于这项工程有着详细的描写:
按照修建祠堂的惯例,白嘉轩负责收缴各家各户的粮食,鹿子霖负责指挥工程。围墙工程经过短促的准备,当天后晌就响起石夯夯击粘土的沉闷的声音。民众的热情超过了族长和工头,一致要求日夜不停,轮换打夯,人停夯不停。白嘉轩和鹿子霖商量一下就接受了。翻修祠堂时拆掉的锅台又垒盘起来,日夜冒着火光,风箱昼夜呱嗒呱嗒响着,管晚上打夯的人吃两顿饭。五天五夜连轴转过,围绕村庄的土墙全部修补完好。白嘉轩和鹿子霖又把十六岁以上的男人以老搭少划分成组,夜夜巡逻放哨。放哨的人在围墙上点燃麦草,手执梭镖和铁铳,在高至屋脊的围墙上严阵以待。
不久后,肆虐的白狼真的来了。有一夜,白狼入侵,所幸值班巡逻的村民及时发现,惊天的铳声惊醒了村民,赶跑了白狼,保卫了村子安全。此事一发生,村民们纷纷庆幸,愈加觉出了提前修复堡子围墙的举措无比英明及时,也对白嘉轩等人愈加敬佩。
总之,《白鹿原》一书中对矛盾调解、教化风习、承担公共事务这三个方面的书写直接展现了白嘉轩、朱先生、冷先生等人在规训与治理乡村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与达成的良好效果。这些贡献与效果的达成并非毫无来由,其背后是乡贤本身的积极引导与乡贤本身的强大声望,这两者的结合对乡村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而这些积极作用无疑正是围绕着乡贤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形态所带来的影响的具体体现。
四
《白鹿原》自出版以来,已经走过了24个年头。在这24年中,围绕着它研究大致集中在儒家文化主题的反思、文本写作的魔幻手法、书中塑造的丰富艺术形象和与中外文学文本的对比等方面。但是《白鹿原》作为一本具有丰富思想文化内涵的作品,仍旧留存有巨大的分析空间。
在作者笔下,白鹿原上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典型的血缘宗族社会,作者投入大量笔墨书写原上人们的日常生活,通过这些生活体现出传统文化和宗族文化的印记;在这基础之上,村中还有白嘉轩、鹿子霖、冷先生等有名望的乡绅领导着、维持着,解决着生活出现的种种问题;在他们的领导与规范之下,村子里外的种种事务,甚至是危机,都能得到有效应对与解决。
书中这种书写看似平淡无常,看似是日常生活的平坦流动,但是当我们将这些现象串联起来分析,就会发现这些现象的背后有着一种结构力量的支配。这种力量是无形的,是潜藏在日常生活的传统秩序之中的,而这就正是我们着力于发现的乡贤文化内涵。
发掘乡贤内涵,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无声呼应。因为这种乡贤文化内涵,不仅在白鹿原上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还似乎在启示着我们,乡贤作为一种领导力量,对当下现实日常生活而言,或许同样有着我们意料之外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