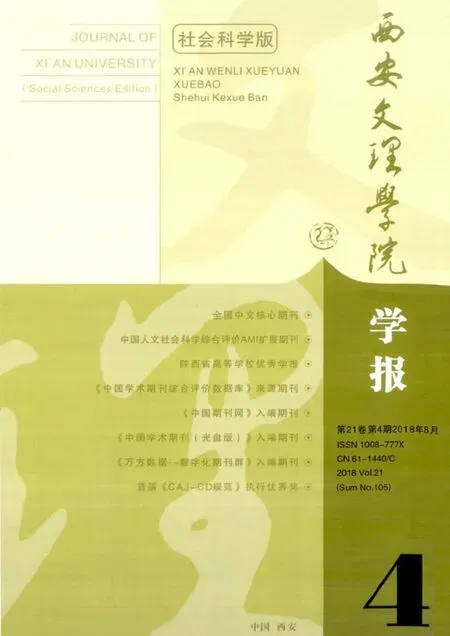清代才女王筠精神文化透视
——以题画诗和剧评诗为例
彭 磊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119)
明清女性文学是中国文学史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明清以来,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天然标志,因此,明清女性文学的研究对于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诗词曲画互通的才女代表,王筠的精神文化透视尤具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王筠,字松坪,号绿窗女史,陕西长安县人。出生在行伍起家、军功卓著的家庭,家族后代皆是耕读传家,是“嘉庆年间著名女诗人、剧作家,擅画花卉人物。”[1]王筠“幼时随父官居山东、江苏等地,博览群书,年无暇日,十三四岁就能吟诗填词,并能自成一家,长短句亦工,有《槐庆堂集》,收诗、词二百余首,尤喜戏曲,遍览元人杂剧与明清传奇,深受影响,有影剧、观剧诗三十多首,传奇两种,有‘临川四梦’风格,被誉为‘长安才女’”。[2]
刊于嘉庆已巳(1809)年秋的紫泉官署刊本《西园瓣香集》为一函三册,分为上、中、下三卷,分别是王元常、王筠、王百龄的诗集。王筠的诗集前有乾隆乙巳(1785)年梁国治和嘉庆己巳(1809)年宗侄王克允的题词。诗集开篇有“长安王筠松坪氏著,愚侄杨孝陆、外孙李岩校订”等字样。通过统计,中卷共收王筠诗113题233首,在中卷的末尾又附有诗馀,其中有诗9首,词24首。王筠的146首诗词作品中共有12题30首的剧评诗,占全集21%;5首题画诗,占全集3.4%。因其不同凡俗的题画诗作和数量可观的剧评诗作,王筠的题画诗和剧评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人对其评价很高。然而关于王筠剧评诗和题画诗的研究成果比较少,本文以王筠的题画诗和剧评诗为例,浅析清代才女王筠的精神文化内核。
一、王筠的人生观
明清时期受到大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女性文学创作呈井喷状态,创作类型也丰富多样,涉及诗歌、弹词、戏曲、绘画、小说等各个方面。“有着极高艺术修养的清代女诗人,也常常以题画诗作为他们‘小慧’的试纸,数量之多,超越前代女性题画诗的综合。”[3]如顾春《天游阁诗集》共收诗800余首,其中题画诗约80首;席佩兰《长真阁诗余》共收诗18首,其中题画诗9首。然而数量虽多,明清时期女性的题画诗还是以山水、花鸟、景色、人物为主,难免千篇一律,面目雷同。在王筠的诗词作品中共有五首题画诗,分别是《里人持麻姑渡海图索题》《题苏武牧羊图》《题观海高表兄春江归棹图》《题壁间毛女图》四首诗和一首词《如梦令·题小青絮影图》,王筠的题画诗跳出了山水、花鸟的题画窠臼,反映出王筠独特的精神诉求和人生态度。
“昔人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然绘画者不能绘水声,绘物者不能绘物之影,绘人者不能绘人之情,诗则无不可绘,此所以较绘事为尤妙也。”[4]可见文人的题画诗确实可以“绘人之情”,是一个了解诗人精神内核的窗口。“与男性题画诗追求表达自我与社会交际功能不同的是,女性题画诗因受制于绘画题材与交流圈子,完全是女性倾诉自我,抒发一己之怀的需要,因而带有较强的自我抒情意味。”[5]通过对王筠题画诗的分析,透视才女王筠的人生观。
其一是看破生死尘缘,向往虚静的彼岸世界。如《里人持麻姑渡海图索题》:
一念超凡悟死生,披云卧月万缘清。
碧桃花下春长在,白玉壶中月正明。
弱水三千天路近,孤云一片海风轻。
仙姿今向丹青认,不共飞琼隐姓名。[6]122
麻姑作为道教的神仙,一直以来被当作长寿的象征。葛洪《神仙传·王远传》言:“莫知麻姑是何神也……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于顶中作髻,余发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锦绮,光彩耀目,不可名字,皆世所无有也。……麻姑自说云: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昔,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陵陆乎?方平笑曰:圣人皆言,海中行复扬尘也。”[7]麻姑见证了东海三为桑田、行复扬尘的瞬息变化,对于沧海之一粟的人事变迁早已看破,只求旦夕披云卧月、抱静守虚。碧桃花下春色常在,白玉壶中月色正浓,正如唐代朱华《海上生明月》中所言:“影开金镜满,轮抱玉壶清”[8]。又如李白《对雪醉后赠王历阳》:“君看昔日汝南市,白头仙人隐玉壶”[9]。无论是海中团团升起的皓月还是费长房修道于玉壶之中的神仙趣事,都是为人所向往的清虚极乐之地。苏轼《金三妙高台》中“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10],认为弱水是神仙出没、遥不可及的去处,而王筠在这首题画诗中指出“弱水三千天路近”,认为去蓬莱弱水之处也是十分容易的,正如麻姑渡海般海风轻荡便至蓬莱仙境。唐人孟棨《本事诗》“事感”第二:“诗人许浑,尝梦登山,有宫室凌云,人云此昆仑也。既入,见数人方饮酒,招之,至暮而罢。诗云:晓入瑶台露气清,坐中唯有许飞琼。尘心未断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复至其梦,飞琼曰:子何故显余性命于人间?座上即改为:天风吹下步虚声。曰:善。”[11]作为西王母的侍女许飞琼尘心未断,仍然想要隐姓埋名十里下山,向往红尘滚滚的凡尘生活,而麻姑了悟生死,摒弃凡尘,皈依大道,向往清虚的彼岸世界。王筠在题这首麻姑渡海图时,认为蓬莱路近、清虚月明、碧春常在、海风轻盈,也想要像麻姑一般不做隐姓埋名向往红尘的许飞琼,而是了悟生死,向往清虚的彼岸世界。
其二是笑对人生,追求随缘自适的旷达生活。如《题壁间毛女图》:
水玉精神烟月姿,长空秋水映琼枝。
诸缘静处凭琪树,笑看人间岁月移。[6]132
“毛女者,字玉姜,在华阴山中,猎师世世见之。形体生毛,自言秦始皇宫人也。秦坏,流之入山避难,遇道士谷春,教食松叶,遂不饥寒,身轻如飞,百七十余年。所居岩中有古琴声云,婉娈玉姜,与时遁逸,真人授方,参松秀实。因败获成,延命深吉。得意岩岫,寄欢琴瑟。”[12]在这首题画诗中,王筠将壁间毛女写成有着水玉精神之态、细烟清月之姿、秋水映枝之美、静若处子之神的美人,任凭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壁间毛女在洞中得意岩岫,寄欢琴瑟,终其一生。这种“笑看人间岁月移”的自适与恬淡都为壁间毛女增添了不少风韵。明清时期,不少女性不再安于酒浆织补,他们广泛地参与到本属于男性活动的领域,渴望拥有与男子一样的权利和尊严,可是受制于社会的束缚和性别的阻碍,有了自我意识的女性只能不甘心地雌伏。长期处于劣势地位的才女,极易产生对自身性别的厌恶之感。但是“明清才女涉佛大多属于居家修行,因此多注重心性修持,较少关注戒律,形成了宗教信仰与家庭伦理的修行模式”[13]。虽然明清才女对自身性别悲剧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他们也同样借助宗教摆脱性别悲剧,而王筠这首题画诗似乎也在劝慰自己,要像壁间毛女一般,即使终年生活在阴暗逼仄的山洞中,也要懂得“得意与寄欢”,面对生活的种种艰辛与不易,都要诸事随缘、静处自适、笑对人生、达观度日。
其三是对文与武、智与力兼容的向往。明清时期,虽有不少开明的男性文人提拔奖掖女性文人参与文学创作,但是社会主流价值观仍然认为女性参与文学创作是有损妇德的行为,即使有文人公开出版发行闺秀才女的文学作品,也常常将闺秀、才女作品放在仙释、娼妓作品之后,仍然将闺秀、才女放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随着明清才女大量早夭事件的出现,一些素来反对女性文学创作的道学家便敷衍出“才高命薄”“福慧不能双修”的论调并且大肆渲染,试图限制女性参与文学创作,将女性束缚在传统的柔与顺、无才与无识的框架内。王筠作为一个自我意识觉醒的才女,大胆地挑战传统男性价值观,不但高歌赞扬女性的才学,为女性智识张目,还打破传统对女性顺从克制的要求,追求孤忠勇敢的男子气节,表现出男性化或者男士化的倾向,形成一种能文能武、智勇兼容的新女性期待。如《题苏武牧羊图》中尽笔勾勒出苏武仗节辞丹阙、守忠绘青史的故事。面对虏庭的刁难,群羊消暇、野鬼为伴、水饮雪餐的生活,苏武仍然仗节守忠,丝毫没有退缩。王筠通过对苏武牧羊图的描画,来展现“节劲清风凛,心昭白日寒”[6]123的孤忠傲骨,表达对这种持节尽忠、傲然不屈品格的赞颂与钦慕。而《题观海高表兄春江归棹图》一诗中以所咏之画寄寓主人之高雅,将其作画雅事与旗亭雅事相比,称赞高表兄“妙手倪黄可并驱”[6]124,借对男性友人才华的赞扬,为女性参与文学创作、显才扬名张目。
二、女性观
王筠从小就淹通经史、博闻强识,历史上为人所谈论的奇女子也深深地刻印在王筠的成长历程中,潜移默化间形成了她独特的女性观。
其一是红颜薄命的悲剧意识。王筠这种红颜薄命的悲剧意思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方面是从自己切身的生活实际中生发出来的感受。王筠自感人生悲苦,又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人生如梦之感随处可见。如《邯郸》“电光石火悲欢增,古今谁非梦里人”[6]119,又如《南柯》“晨钟猛击情魔断,足下莲花立地开”[6]125。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里,才女王筠内心的煎熬与挣扎也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明珠暗投之恨、“天壤王郎”之叹也加重了王筠悲剧人生的体验感。王筠的诗词作品共有146首,涉及王筠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却无一篇是写自己丈夫的,不堪的婚姻生活确实让王筠有“明珠暗投”之恨,恨对方不能慧眼识珠。如《秋夜读龙女传感成》中感怀落入沟渠的龙种因无人识别埋没一生而暗自落泪。“沧海自怜龙种贵,沟渠岂识夜明珠”[6]130,感叹龙女有柳毅传书得以独破愁城,而自己却只能在沟渠中老死一生。《读红拂记有感》则感叹红拂女胆识过人,于众多门客中慧眼识得李靖并与之夜奔,王筠不禁感叹“而今多少庸脂粉,谁解尘埃识卫公”[6]123。王筠红颜薄命的悲剧意识来源的第二个方面是女性群体感知下的悲剧总结。王筠共有4题15首品评人物的诗词作品,所评人物均为女性,分别是冯小青(9首)、王昭君(3首)、李香君(1首)、霍小玉(1首)、江梅妃(1首)。王筠所评点的人物全是薄命的红颜,在历史和婚姻的维度中展现其悲苦的一生。
作为同样有才华的女性,王筠能够深切地体会到古今历史上女性所遭遇的痛苦和折磨,于是王筠开始对女性生命价值和自我角色进行深刻的思考与探索,从王筠的剧评诗中可窥一斑。王筠认为相较于男子,女子生来多是薄命之身,多是承受痛苦和愁苦之人。如《明妃怨二首》“回收乡关无限恨,可知薄命是红颜。”[6]123又如《杂咏四首》“黄沙渺渺埋香骨,青冢千年恨未穷”[6]123“李郎去后无消息,遗恨侯家紫燕钗”[6]123“有金难买《楼东赋》,寂寞梅花老上阳。”[6]119在王筠看来,女子就是悲苦、穷愁、凄凉、薄命的化身,终其一生都难逃不幸结局的命运,唯有遗恨终老、凄苦一生。王筠红颜薄命悲剧意识来源的第三个方面是破除性别局限,由士人怀才不遇之悲和红颜才命相妨之哀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悲剧体验。王筠认为女子的才华对女人来说是一种负累,会影响其一生的福祉,认为女子有才无命。如《和小青原韵八首》中“才色何须与命争,可知有命即无名”[6]119、“明妃远去侯妃死,薄命红颜岂独卿”[6]120。王筠认为无才之人才会安稳地终其一生,认为“慧字何如福字高,痴痴蠢蠢自逍遥”[6]146。男性友人也是“雄才天命两难争,逐鹿徒骄霸主名”[6]146,“茫茫宇宙竟谁投,才与命何事苦相仇”[6]142等情况,身边的好友都是才子不遇、红颜薄命,更加加重了王筠悲剧命运的体验。
其二是对悲剧女性深切的同情和关怀。如《如梦令·提小青絮影图》:
小院啼莺娇弄,惊起梨花残梦。扶病步春池,细雨影儿相共。
心痛,心痛,生被红颜断送。[6]142
“冯小青是明代万历年间南直隶扬州人,是古今有名的怨女,嫁杭州豪公子冯生为妾,工诗词,解音律,为大妇所妒,移居孤山别业,亲戚劝其改嫁,不从,凄怨成疾,命画师画像自奠而卒,年十八。”[14]4小青絮影图画成之后,冯小青也曾作《七言古风·其三》一首:“新妆竟与画图争,知是昭阳第几名?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14]2。然而处处为大妇所不容,《七言古风·其一》:“垂帘只愁好景少,卷帘又怕风缭绕。帘卷帘垂底事难,不情不绪谁能晓。”[14]1冯小青日日夜夜左右为难,在夹缝中生存的情况可想而知。富家公子多无情,纵使生活不易若此,仍等不到“怜我之人”,冯小青在心灰意冷之余写下《无题》:“愿为一滴杨枝水,洒作人间并蒂莲。”[14]1冯小青唯有终日临池自照,与影相怜。王筠不禁为之惆怅:“春光何事到侬家”,然而“个人自是无情绪”,依然也只能与冯小青一般“辜负帘前几树花”。王筠面对这位怨女的小像,设身处地地想她所想,深感于冯小青在这场失败的婚姻生活中所遭遇的痛苦与折磨,真是“心痛,心痛,生被红颜断送。”对出塞和亲的王昭君,王筠虽知无可奈何,但仍然不无关切地问道:“弱质何堪塞路艰”。面对失宠的江梅妃,如若惊鸿重舞,断人心肠的人恐怕又会多加一个。总之,王筠以己度人,表现出对悲剧命运的女性无限的同情和惋惜。
三、传奇观
咏剧诗和题画诗一样,也包含了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思索。“剧评诗也是咏剧诗,是戏剧批评样式之一,系以诗歌方式对戏剧文本及演出、戏剧作家及演员、戏剧审美与传播等戏剧文化现象予以咏叹或者点评,从中体现出作者的美学情趣和思想观点,也透露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史信息。”[15]在王筠146首诗词作品中,剧评诗共有12题30首,又分为评剧作7题10首(《读旗亭记有感》《题汤临川四梦》《题桃花扇》《题郁轮袍》《秋夜读龙女传感成》《读红拂记有感》《读蒲山公传》)。评剧情有1题5首(《咏戏杂出》),所咏剧情片段为《青冢记》中的《昭君出塞》、《风筝误》中的《惊丑》、《西楼记》中的《错梦》、《回府刺字》中的《刺字》、《牡丹亭》中的《寻梦》。“剧评诗不仅反映了与戏剧表演有关的因素,更反映了不同时代与社会人们的不同心态与精神文化。”[16]王筠有着多次的观剧活动,因此具有十分丰富的观剧体验和独特的思维感悟。研究王筠的剧评诗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这位才女的独特价值。
其一,王筠认为“传奇曲折重团圆”,追求新意、曲折有利于引人入胜,但是大团圆的结局则又落入下乘。《读旗亭记有感》一诗中认为旗亭雅事、画壁风流,但是“假使有才真有命,更无人唤奈何天。”[6]118王之涣与谢双鬟几经曲折,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成就了《旗亭记》的风流韵事,使得整个故事跌宕起伏。然而最终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大团圆结局却冲淡了这份奇缘,使得整场戏有一种来源于生活但是并非生活的感觉,只不过是文人的文字游戏而已。《题郁轮袍》讲的是王维高中状元,与苏慧芳喜结婚姻的故事,剧中设置王颋和王推这样的角色就是为了使传奇更加具有“奇”的成分,使得故事大起大落、扣人心扉。虽然这些文人臆测的风流韵事不足以玷污名豪清誉,但确实是“文人聊作戏”。
对于传奇的理解,明代人与清代人的认识不尽相同。明代人认为传奇就是奇观、奇幻的意思,所以追求所写之事尽可能超出平常,追去奇怪、奇观之感。如明人倪倬为许恒《二奇缘传奇》所做的“小引”所云:“传奇,纪异之书也,无奇不传,无传不奇。”[17]1383而清人的传奇观有两种:第一种与明人相同,追求奇怪、奇幻之感,如李渔曰:“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新,即奇之别名也。”[18]第二种则更多地强调将传奇的社会教化功能置于艺术审美效果之上。如陈学震《双旌记》自序曰:“盖传奇者,传其事之奇者也,事不奇不传。将军之忠,夫人之节,奇而正者也,奇而法者也。”[17]2346而王筠作为一个剧作家和剧评家,能充分吸收当时的传奇观念又不为之拘束,王筠认为“事奇”就是指多注重采用美丑对比、巧合误会等方式,使得整个戏剧具有诙谐幽默的喜剧效果,或者多采用悲喜对比,使得戏剧产生巨大的感染力,而非单纯地将传奇往奇特、奇幻之路上发展。如《风筝误》中的《惊丑》一出,便是展现了误会叠出、错中有错的爱情喜剧故事。詹烈侯府中的千金,一位美丽多才,一位荒唐丑陋,因一架误飞的风筝与多情才子韩琦仲结缘,发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惊丑》片段。“黄昏错走东村路,引得旁观笑口开。”[6]124加入了误会、巧合等因素使得《风筝误》更加具有调笑、戏谑的喜剧因素,更适合舞台表演。又如《西楼记》中的《错梦》一出,书生于鹃和妓女穆素徽的爱情不被父亲许可,两人分离两地,书生于鹃相思成疾,抱病卧床上演了《错梦》一出。书生梦中去寻找穆素徽,不料“俺则受狠虔婆面数说,又被那小妮子轻抛撇,莫不待分开咱连理枝,敢待要打散俺同心结”[19]68,见到穆素徽竟是“全不似半些”[19]68,梦惊醒来却发现不过是噩梦一场。虽是虚惊一场,但是梦中的寡情与凉薄,更加让诗人追思远方的心上人,一句“我的真素徽此时何处也”[19]69让人深感悲戚。又如《昭君出塞》中的王龙丑态也是以乐景衬哀情,使人们切实体会到了王昭君的不幸与悲苦。在送诏的过程中,全剧沉浸在一个悲伤痛苦的氛围中,此时上场的副净王龙诙谐出场,“铁甲将军去跳井,跳了一个又一个,不登,不登,不登登。”[20]这句极富口语方言的句子又展示出欢愉轻松之景,然而想到此时的铁甲便是送往昭君出塞的人又不觉悲从中来。
其二是“文心润似菩提露”的至情观。王筠对于文人聊作之戏很少有共鸣,但对至情至信之剧则感怀不已。如“文心润似菩提露,孽境滋生并蒂莲”[6]118,认为只要情真意切,在逆境中也会喜结连理。又如“死生端不负情痴”[6]119,认为戏剧有情才感人,而这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之情更是不可被辜负的。《题桃花扇》:
传奇曲折重团圆,独有桃花扇可怜。
故国已同萍絮散,其心仍是金石坚。
香楼风雨悲情梦,霞巅松筠结静缘。
惆怅秦淮歌舞地,无情春色自年年。[6]124
王筠认为重团圆之戏不过是文人聊作罢了,只有《桃花扇》最惹人怜惜回味,并非是因为《桃花扇》反映了明末的民族斗争、总结了历史兴亡之案,具有揭示南明覆亡之教训的现实意义,而是因为“故国已同萍絮散,其心仍是金石坚”。《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以侯、李的爱情线作为明线展示出异代王朝的风云变幻。同时又在瞬息万变的时代背景中更显得两人之间的爱情愈加珍贵与动人,这也进一步表现出王筠重视“至情观”。
雍乾时期,浙西词派的“清空骚雅”和袁枚的“独抒性灵”统治文坛,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至情”的审美范式。作为明清文坛的有机组成部分,女性创作也必不可少地受到了影响。正如范端昂所说:“夫诗抒写性情者也,必须清丽之笔,而清莫清于香奁,丽莫丽于美女”[21]。因此,“情真”是王筠尤为看重。在舞台表演中往往最能打动人心的就是真心、真意和真情。《回府刺字》是清代秦腔剧目,经久不衰的原因就是岳飞忠孝报国的担当和岳母舍小家顾大家的谆谆教诲之情。“堂前刺字鬼神钦,报国精忠贯古今”[6]124,作为全剧的高潮,岳母为了激励儿子为国尽忠亲刺“精忠报国”四字,再送岳飞奔赴保家卫国之征途,这真心赤胆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所有人。又如《牡丹亭》中的《寻梦》也同样以感情之真为人所喜爱。《寻梦》是《惊梦》之后的一出戏,美梦醒来却发现生活依然是苍白乏味的,自己仍然生活在绣楼这般封闭的环境里,只能一任春色悄然消失。于是杜丽娘打算“寻梦”,勇敢地追求梦中之人,感情之专与追求之切让人为之感动。“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22]。为了深情缱绻、缠绵不尽的相思与爱恋,杜丽娘甚至愿意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定要寻遍亭台、徘徊断柳梅边。这一往而深之情,让《寻梦》一出成为经典。
综上,以王筠题画诗和剧评诗为窗口,一方面展现出王筠个人豁达自适的人生态度,窥探到王筠对于女性“红颜薄命”“才命相妨”的性别思索,表现其对女性深切的关怀。另一方面,王筠讲究“事奇情真”、注重曲折巧合、避免大团圆结局的戏曲话论也丰富了我国古代曲论。